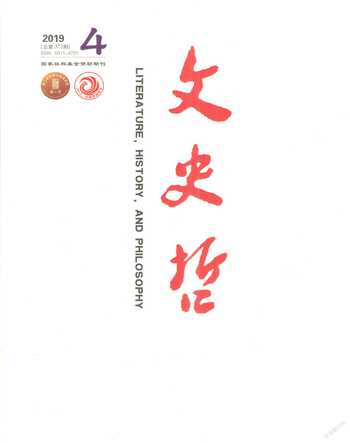如何破解正义底线与血缘亲情的冲突悖论?
摘 要:黄启祥教授撰文指出,孔子在“父子相隐”的命题里并未提倡父子“互隐其恶”,而是提倡“隐父而非隐罪”以彰显“正义的家庭属性和主动的道义担当”。但仔细分析会发现,这种新颖的解读既脱离了《论语》的文本基础,也缺乏充分的论证理据,同时还与黄文自觉认同的“不坑害人”的规范性立场相冲突,结果陷入了自败悖论而无法成立。
关键词:儒家;父子相隐;血缘亲情;正义底线
DOI:10.16346/j.cnki.371101/c.2019.04.03
黄启祥教授在《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以下简称“黄文”)一文中,通过解读大量文本材料,认真梳理了十几年来国内学界围绕《论语·子路》有关“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以下简称“父子相隐”)命题所展开的学术论战,具体分析了论战双方在立场观点、论证理据等方面的优劣得失,然后将《左传·昭公十四年》有关“叔向,古之遗直也。治国制刑,不隐于亲。三数叔鱼之恶,不为末减。曰义也夫,可谓直矣”(以下简称“不隐于亲”)的命题与“父子相隐”联系起来考察,强调两者之间的一致性,接下来又诉诸《吕氏春秋·当务》和《史记·循吏列传》中的两个案例,指出“父子相隐”并非提倡父子“互隐其恶”,而是提倡“隐父而非隐罪”①。笔者认为,黄文阐发了某些值得反思的新穎见解,有助于我们将这场论战深入下去,所以想围绕若干问题与黄教授商榷。
一、学问史和理念史的研究视角
黄文最重要的新颖之处体现在,它通过引入“不隐于亲”的命题对“父子相隐”命题做出了与论战双方都有所不同的理解,指出:虽然“双方对父子相隐的评价势不并立,但对父子相隐的理解却是相同的,即都认为父子相隐是互隐其恶”;然而,“面对孔子对叔向‘不隐于亲’的称赞,无论是反方的闪烁其词还是正方左支右绌的争辩都表明,他们对孔子‘父子互隐’之说的理解存在严重问题”。其实,尽管我此前也注意到某些论者引用了“不隐于亲”的命题,并认为这种引用在学理上没有问题,却从未就此展开讨论;而黄文对这个命题给予了充分重视,恰恰是促使我撰写本文的直接动因,让我有机会解释以往为什么会回避这个与“父子相隐”内在相关的命题。
① 黄启祥:《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文史哲》2017年第3期。本文所引黄说皆出自此文,不再一一标注。
② 见刘清平:《美德还是腐败?》,《哲学研究》2002年第2期。究路数。我则是将它分成以下三个层面来理解的。
最广义的思想史位于实然性的维度上,涉及历史上的每个人都出过思想的简单“事实”,如同罗丹的雕塑“思想者”暗示的那样,因此也可以名之曰“思者史(history of thinkers)”。相比之下,另外两个层面的狭义思想史则处在应然性的维度上,不再是一有了出思想的“事实”就会被并入思想者的行列,而是还要具有“价值”方面的“应当”资格才能挤进去。比方说,孔子当年三千弟子中的大多数人,肯定也出过自己的思想;但很不幸,他们的思想只是一些“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单纯事实,并不具有什么“历史性”的价值意义,所以就没法与孔子、有若、曾参等人出过的思想相提并论了。
进一步看,应然性思想史的两个层面又可以分别称为“学问史(intellectual history)”和“理念史(history of ideas)”,区别在于所涉思想的“应当”资格不同。学问史的意义是指历史上某些思想者出过的思想,在后来以研究学问为业的人们看来,或多或少具有“理知”方面的价值,有必要挑出来加以考察;当前高校的“哲学史”“政治学史”乃至“思想史”等专业,主要就是在这个层面研究以往思想者的思想的。相比之下,理念史的意义则是指历史上某些思想者出过的思想,能够凭借其中包含的“原创性深度理念”,对于普通人的生活发挥重要的影响效应,乃至塑型他们的人生活法。例如,像老子、孔子、墨子这类理念史层面的“思想家”,就是分别以“无为”“孝仁”“兼爱”作为各自的“标志性理念”的(一看就知道哪个理念是谁提出的);而两千年来无数炎黄子孙的生命历程,不管是否自觉意识到了,都在不同方面或多或少打下了这些理念的积淀性烙印。
依据上面的区分,学者们在研究思想史的时候,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训练和能力,分别从学问史、理念史或二者兼顾的视角入手(当然,这些视角本身并无高下优劣之分,只是研究的路数方法有别而已)。我当初在因为研究中国美学史而阅读《论语》和《孟子》的过程中发现上述三个命题的问题时,自发地采取了理念史的研究路数,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在我看来,这三个命题涉及的不只是如何理解文本自身的单纯学术性问题,而首先是与人们的伦理生活息息相关的深度理念性问题(事实上,我正是在研读这两部元典的过程中,第一次自觉意识到了孔孟思想对我的积淀性影响)。第二,我缺乏史料学方面的训练,几乎没有能力辨析《论语》之外各种典籍里以“子曰”或“仲尼曰”的形式出现的大量命题是否确实出自孔子之口,而这些命题之间的相互抵触之处又非罕见。
有鉴于此,我在着手研究的时候就给自己立了一条规矩:在遵守学术规范的基础上,将所考察的原初文本集中在《四书》尤其是《论语》和《孟子》上;在涉及这些元典的注解诠释时,则优先参考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至于其他古籍里的“子曰”或“仲尼曰”命题,尽可能不引用。毋庸讳言,这种研究视角肯定存在片面性的缺失,但由于以下原因,它在学理上还是可被允许的。
首先,虽然也有学者对其中的某些语句是否后世窜入提出了质疑,但《论语》和《孟子》毕竟是学界公认的有关孔孟话语最可靠的经典文本(当然,我们今天在学理上仍然有必要注意:不要把其中的所有命题都视为出自孔孟本人之口例如,《论语·颜渊》记载的子夏话语“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就时常被归于孔子本人,而没有注意到朱熹在诠释这个命题时特别指出:“盖子夏欲以宽牛之忧,故为是不得已之辞,读者不以辞害意可也。”(《论语集注·颜渊》))。所以,将原初文本主要限定在这两部元典上,能够有效地减少某些节外生枝的争议(如“这句话很难确定是孔子所说”),降低我的论证出现低级错误的风险。在我的研究包含了针对孔孟儒学的规范性批评时,尽可能降低这类争议和风险无疑是可取的。
其次,在理念史的意义上,其他儒家古籍包括《五经》的重要性都难以与《四书》相提并论,因为后者在近千年的历史中作为科举考试的国家级参考书,对于国人(不单单是科举人士)的现实人生具有的浸润式影响力,可以说无论怎样强调都不过分。同时,这也是尽管不少论者认为朱熹的注释偏离了孔孟原意(我也认为在不少地方的确如此,一个典型例证就是他在《论语集注·为政》注中竟然声称孔子已经认同了“三纲五常”的“礼之大体”),但我还是优先引用《四书章句集注》作为参照的主要原因(另一个原因是,朱熹也是重要的儒家思想家,系统阐发了“理”这一标志性理念):其他古代儒者的注释哪怕在学问史的意义上更切近孔孟原意,朱熹的注释在理念史的意义上也还是绕不过去的,因为近千年来国人在依据孔孟理念塑型自己的活法时,都会直接间接地受到这些注释的影响——尽管我们肯定不应当抱着“奉朱熹解释为圭臬”的盲目崇信态度,将其视为诠释《四书》的终极权威或学界共识,而应当仔细地辨析其中存在的众多曲解。换言之,既然我主要是从理念史的角度考察父子相隐问题的,那么对我来说,《论语》以及朱熹的注释就要比其他古籍或是其他儒者的注释更有意义。我们甚至有理由假设,即便今天发掘出了两千年前的《论语》古本,里面没有“父为子隐”的命题而有“不隐于亲”的命题,它在理念史的意義上也还是赶不上朱熹注释的《论语》。理由很简单:前者或许更切近孔子作为思想者的本来面目,并且因此具有学问史层面的重要价值,但却明显缺乏后者所拥有的深沉厚重的“效果历史”,因为孔子作为一位影响了国人两千年的原创性思想家,归根结底还是“真实”地“活”在了后者之中而非前者之中。顺便说一句,我们也能以类似的方式比较马王堆出土的帛书版《老子》和流行了上千年的今本《老子》。
按照我的理解,黄文可以说是从二者兼顾而偏重理念史的视角出发的,因为它是为了理解“父子相隐”才把“不隐于亲”的命题纳入考察范围的。黄文在阐述自己的主旨时也指出:“通过对《论语》以及相关文献的阐释,揭示久被遮蔽的孔子之言本身的意义”,明显呈现出看重《论语》胜过包括《左传》在内的其他文献的意向。进一步看,虽然“不隐于亲”的命题不像“父子相隐”那样具有深沉厚重的理念史意义,但黄文对它给予了高度重视无疑能够扩展我们的视野,尤其有助于我弥补以往回避这一命题的片面缺失。有鉴于此,我将在认同黄文下述见解的前提下展开讨论:“不隐于亲”的命题出自孔子之口,表明“孔子赞扬叔向不隐于亲,明确肯定叔向行事正义,可称之为直”。
当然,我的认同也有两个条件。首先是悬置了“不隐于亲”案例的具体内涵。邓晓芒教授曾对这个案例做过细致分析,黄文认为他的某些见解“十分牵强甚至毫无道理”,我倒认为颇有道理,但为了不偏离主题在此就不谈了。其次是我在拙著《忠孝与仁义》中曾论证说:孔子对“义”的看法比较含混,因为《论语》里的“义”字更偏重于“君臣有义”刘清平:《忠孝与仁义——儒家伦理批判》,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72页。。就我的研读范围看,最早把偷窃杀人等坑人害人行为界定为“不义”的先秦文献是《墨子·非攻上》:“今有一人,入人园圃,窃其桃李,众闻则非之,上为政者得则罚之。此何也?以亏人自利也。……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杀一人谓之不义。”此后,孟荀也主张“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孟子·公孙丑上》),“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仁者不为也”(《荀子·王霸》)。张岱年因此认为:“墨子最崇尚义,孟子的注重义,将义与仁并举,大概是受墨子的影响。”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268页。另见刘清平:《论墨子“正义”理念的现代意义》,《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不过,鉴于孔子的仁爱观念潜含着“不可坑人害人”的意蕴,并主张“苟志于仁矣,无恶也”(《论语·里仁》),把一切违反爱人助人原则的“不仁”行为都视为“恶”,我们显然也有理由说,“不隐于亲”的命题与孔子的仁爱观念在下面这种规范性立场上是基本一致的,因此可以视为出自孔子之口:“行事正义”的底线在于“不坑害人”,而隐匿父亲的盗窃行为则属于“坑人害人”的“不义”范畴。其实,如果说我在这场论战中的具体观点有所修正的话,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从最初围绕抽象笼统的“正义法律”揭示儒家的悖论,进展到了依据“不坑害人”这条规范性的“正义底线”揭示儒家的悖论,并且由此将我的学术兴趣扩展到了道德和政治哲学领域。
值得指出的是,黄文也自觉认同了“不隐于亲”蕴含的这种规范性立场,明确把隐匿父亲的盗窃行为视为不义之举,强调“如果父亲盗窃,子为父隐;儿子偷盗,父为子隐,这家人岂不成了相互包庇的犯罪之家?这个家庭岂不成了姑息养奸和藏污纳垢之所?又有何正义可言?”,并据此批评正方“论证隐恶的正义性乃至超正义性是于理不通的”。就此而言,黄文很难说是“不站在任何一方的立场上”,因为至少在把“子隐父罪”视为不义之举这种规范性的立场上,它与反方基本一致,却与正方正相反对。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主要就是出于这种与黄文的规范性立场基本一致的考虑,接受了黄文有关“不隐于亲”的见解作为进一步讨论的前提,因为在这种共同的立场上展开商榷,有助于澄清我与黄文在理解“父子相隐”命题方面的内在差异。
二、“隐父而非隐罪”的自败悖论
黄文在第二节阐发了有关“不隐于亲”的上述见解后指出,按照正反双方对于“父子相隐”命题的相同理解,他们势必面临一道难题——“不隐于亲与亲亲相隐不是正相矛盾吗?孔子既然主张亲亲互隐,又怎会称赞不隐于亲?”——并分析了正反双方的左支右绌和闪烁其词。然后,黄文在第三节又结合《吕氏春秋》和《史记》的两个案例,论证了自己对“父子相隐”的新颖理解:“‘子为父隐’是为父隐而非为罪隐,换言之,是隐父而非隐罪。”所以,它与“不隐于亲”并不矛盾,而是内在一致的,都彰显了“正义的家庭属性和主动的道义担当”。本节将集中论证我的一个看法:黄文的这种理解不仅缺乏扎实严谨的文本基础和论证理据,而且还会陷入一系列逻辑上和规范性立场上的自败悖论。
为了消解两个命题的矛盾,黄文在解读“父子相隐”时首先指出:孔子既没有否认叶公说的“子证父罪”具有正义属性,也没有赞同“子隐父罪”是正义之举,而只是“肯定”(更精确些说只是“描述”)了后者是当时“常人的一种做法,也就是正方所说的司空见惯的常态”。在我看来,这种解读虽然新颖,在学理上却似乎站不住脚。对语境稍加分析就能看出,在葉公把“子证父罪”评判为“直”之后,孔子立即提出了相反的看法,强调“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所以,在上下文关联中,与“子证父罪”对应并且明显得到孔子赞同的“隐”,只能是指“子隐父罪”,而不是指黄文主张的第三种选择“隐父而非隐罪”;否则孔子哪怕再惜言如金,至少也会做出某种解释,以便让叶公明白自己在“直在其中矣”的评判性(而非描述性)短语中赞同的究竟是怎样一种“隐”。也正因为这段文本的意思如此清晰,把“父子相隐”理解成“孔子公开主张父亲隐匿儿子的罪行或者儿子隐匿父亲的罪行是最正直的美德”,就像黄文承认的那样,“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这也是秦汉以降两千多年来人们的一贯理解。”就此而言,黄文宣称“父子相隐”的命题并未表明孔子赞同“子隐父罪”的立场,黄文相关论述虽是出于清除这个命题与“不隐于亲”命题之间矛盾的良好意愿,但似乎又扭曲了这个命题自身所在的文本语境。
然后,黄文紧接着反驳了正方(其实也包括反方)与上述“一贯理解”基本一致的观点:“正方认为孔子把这种所谓的常态称之为‘直’,但是他们却忽略了这样一个问题:自古以来何曾有人把他人隐匿父亲的盗窃行为称为正义之举?”遗憾的是,黄文作为关键论据提出的这个反问,不仅不符合事实,而且在它自身的语境中也潜藏着逻辑上的漏洞:不仅自古以来确实有许多人把他人隐匿父亲的盗窃行为称为正义之举,而且正是黄文提供了这方面的大量证据。首先,当前论战中的正方明显主张“把他人隐匿父亲的盗窃行为称为正义之举”,否则他们就不会与反方展开十几年的论战,而黄文也无需批评他们“论证隐恶的正义性是于理不通的”。其次,按照黄文的描述,秦汉以降两千多年来,那些不仅把孔子当作圣人尊崇,而且自觉接受了上述“一贯理解”的人们,当然也会“把他人隐匿父亲的盗窃行为称为正义之举”。再次,黄文明确承认:在孔子的时代“常人总是为父隐罪”,而“子证父罪”倒是“不同寻常,非一般人所为”。这岂不是足以表明,当时就有不少人把“为父隐罪”视为正义之举吗?否则它怎么能够成为“司空见惯的常态”呢?所以,鉴于黄文已经凭借这些论述自败性地否定了自己的关键论据,它从中推出的那个结论——孔子根本不像正反双方一致认定的那样赞同“为父隐罪”,以及所谓的在这场论战中“孔子的立场实际上一直都不在场”,也就有些草率而无法成立了。
如果说黄文背离《论语》文本和大量事实否定了“孔子赞同‘子隐父罪’”已经让人惊异的话,那么更让人惊异的是,它在接下来正面论证“孔子赞同‘隐父而非隐罪’”的时候,既没有诉诸《论语》的“父子相隐”命题,也没有诉诸《左传》的“不隐于亲”命题,而是求助于《吕氏春秋》和《史记》的两个案例:
楚有躬者,其父窃羊而谒之上。上执而将诛之,躬者请代之。将诛矣,告吏曰:“父窃羊而谒之,不亦信乎?父诛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诛之,国将有不诛者乎?”荆王闻之,乃不诛也。孔子闻之曰:“异哉!躬之为信也!一父而载取名焉。”故躬之信,不若无信。(《吕氏春秋·当务》)
石奢者,楚昭王相也。坚直廉正,无所阿避。行县,道有杀人者,相追之,乃其父也。纵其父而还自系焉。使人言之王曰:“杀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废法纵罪,非忠也;臣罪当死。”王曰:“追而不及,不当伏罪,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主法,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诛而死,臣职也。”遂不受令,自刎而死。(《史记·循吏列传》)
不难看出,在石奢的案例中,孔子才是不在场的,更谈不上表明态度了值得一提的是,《韩诗外传》和《新序·节士》在记述石奢案例时都加了一句“孔子曰: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矣”。但我们与其将它看成是孔子针对石奢的“纵其父”行为做出的评判,不如将它看成是后人引用《论语》的这一命题表达了他们针对石奢行为的评判,亦即按照秦汉以降对这个命题的“一贯理解”,认为这样做属于正义之“直”。所以,我们当然没有理由把后人的这种引经据典说成是孔子自己的评判意见。;而在楚躬的案例中,孔子虽然出场了,却对其行为发表了不赞成的见解诚然,黄文从孔子“一父而载取名焉”的不赞成见解中,进一步引申出了“躬可以把羊送还失主,登门道歉”的最佳解决方案。但从学理视角看,黄文提出的这种大跨距建议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两千多年前孔子本人的立场,或许还有必要打上一个问号。。有鉴于此,哪怕我们接受了黄文极力论证的“躬的故事只是实现了形式正义,石奢则要实现实质正义”的结论,所有这些又与孔子本人的立场何干呢?它们怎么能够证明“父子相隐”命题赞同的也是这类“隐父而非隐罪”的做法呢?不管怎样,单凭两个案例都涉及父亲犯罪儿子如何处理这一点,似乎还不足以证明它们与“父子相隐”命题在立场上一致;因为无论从学问史还是理念史的视角看,孟子完全赞同舜将父亲“窃负而逃”的见解与它们相比,都具有不知高出多少倍的实质相关度,更有助于我们理解儒家至圣和亚圣在倡导血亲至上主义方面的师承绵延(对此我曾做了大量论证)。事实上,黄文开篇也指出:“我们从孟子论舜可以知道他赞同子为父隐”;鉴于舜将父亲“窃负而逃”的做法明显只有隐匿父亲杀人行为的一面,却不包含任何出面指证父亲、事后登门道歉或最终自刎而死的情节,所以,如果承认了《论语》与《孟子》的相关度远高于它与《吕氏春秋》和《史记》的相关度,我们只能得出“孔子也像孟子一样赞同‘子隐父罪’”的结论,从而导致黄文再次陷入自败境地。
在指出这两个案例与孔子本人的立场没有实质性关联之后,现在来看黄文主张“为父隐”是正义的见解本身。按照我的理解,黄文借助这两个案例强调的与“为父隐罪”不同的“只为父隐”,主要是指在父亲偷窃杀人的情况下,儿子在指证或放走父亲后主动代父受刑乃至自杀而亡,以达到既“使父亲不受法律的惩罚”,又“使父子亲情免受伤害”的目的值得指出的是,黄文虽然明确反对儿子隐匿父亲的罪行,但在儿子是否应当指证父亲罪行的问题上却是前后矛盾的。一方面,它依据孔子的不赞成见解,认为楚躬指证父亲会让“其父落得窃贼之名”,从而“造成家庭内部的不义,使父子亲情受到伤害”;另一方面,它又赞同“石奢让人将父亲杀人之事报告楚昭王”,甚至还凭借跳跃式推理强调这一点表明孔子倡导的“子为父隐”是“为父隐”而非“为罪隐”,却好像忘了石奢的做法同样会让“其父落得杀人犯之名”而“造成家庭内部的不义,使父子亲情受到伤害”。就此而言,黄文可以说对自己选取的两个案例也采取了双重性的评判标准。。黄文认为,这类代父受刑的做法因此实现了形式正义乃至实质正义,甚至还有“与舍生取义内在相通”的崇高意味,彰显了“正义的家庭属性和主动的道义担当”。但细究起来,黄文的这种规范性见解不仅与它在反对“子隐父罪”时认同的不坑害人的正义底线正相抵触,而且也扭曲了这两个案例的本来面目,同样在学理上难以成立。
首先,撇开人格同一性以及与自由意志与自主责任相关的现代原则不谈,只要接受了“一人做事一人当”“冤有头债有主”的传统信念,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既然是父亲从事了偷窃杀人的不义行为,就只有他本人才应当接受正义的惩罚,子女没有理由基于血亲恩情的诉求,通过代父受刑豁免父亲的責任,使父亲不受法律的惩罚,否则黑社会小弟主动请求代替对自己有恩的老大坐牢的哥们义气,也将变成“实质正义”“与舍生取义内在相通”的崇高举动了。从这里看,黄文指出楚躬的案例表明当时法律允许“儿子可以替父亲受刑,而且这种行为还被视为一种孝行”,并不足以证成代父受刑彰显了“正义的家庭属性和主动的道义担当”,因为这类法条恰恰是试图凭借子对父孝的血亲情理转移罪责主体的不义规定。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朝廷曾站在维护君权的立场上,从另一个角度彰显了所谓“正义的家庭属性”,通过“连坐”“株连九族”“满门抄斩”等严刑酷法,把父亲谋反的所谓“大逆”罪责强加到原本无辜的全家老小身上。所以,一旦考虑到这类为了维系君臣大义不惜毁灭父子亲情的残忍现象,我们就可以看出“一人做事一人当”“冤有头债有主”的质朴信念是怎样的难能可贵,而在父亲偷窃杀人的情况下,子女代父受刑的所谓“道义担当”又是如何违反了“谁坑害了人谁就应当受到惩罚”的正义底线的。
此外,黄文在论证“正义未必一定要以当事人承担的方式来实现,也可以通过家庭承担的方式来实现”的时候指出:“就偿还被盗者的损失而言,即使在今天也还是可以家庭为主体来实现的。”但这种论证似乎混淆了“行为主体的人格同一性”与“家庭财富的成员共享性”两个不同的问题,不仅把刑事惩罚与民事赔偿混为一谈了,而且还把具有人格属性的个体之人与没有人格属性的家庭财富等同看待,因此在学理、法理和哲理上都很难成立。
其次,这两个案例中的儿子严格说来并未代父受刑,因此也没有以“为父隐”的方式实现正义,倒不如说仍然是以不义的方式“为父隐罪”。
先看楚躬。黄文指出:“从结果看,荆王最终赦免了他,也免其父无罪,父子完好。这似乎是一个圆满的处理方式。”不用细说,荆王基于“楚躬代父受刑是个孝子”的血亲情理就赦免了他们,让父子两人无需接受惩罚完好团聚,对于他们的确是再圆满不过了。但我们岂不是仍然有理由提出质疑:这个“圆满”的处理方式彰显的究竟是坑人害人理应受到惩罚的正义底线得到了遵守呢,还是子对父孝的血亲情理可以凌驾于这条正义的底线之上,以致只要儿子是个孝子,父亲偷羊的不义罪责就不复存在了呢?如前所述,黄文甚至指责楚躬指证父亲罪行的做法会让“其父落得窃贼之名”,“使父子亲情受到伤害”;但这种指责岂不是恰恰体现了主张“事亲至上”的“子隐父罪”意向,从而与黄文自觉认同的“子隐父罪”属于不义之举的规范性立场正相抵触吗?
再看黄文给予了更高评价的石奢。石奢自己的两次陈述可以表明,他自刎而死的原初动机,既不是承担“其父杀人”的应受罪责,也不是惩罚自己“纵其父”的包庇行为,而是主要基于“废法纵罪,非忠也”“不奉主法,非忠臣也”的考虑,所谓“伏诛而死,臣职也”。就此而言,如果说这个案例显示了“子为父隐与舍生取义是内在相通的”,那也不是“子为父隐”与“不坑害人”的正义底线的内在相通,而只是“子为父隐”与“君臣大义(君惠臣忠)”的内在相通。所以黄文也指出:“他之所以毅然赴死,是因为他把忠看得高于生命。石奢所面对的不是生与死的选择,而是生命与忠孝的抉择。让石奢自刎的原因不是法律的裁决,而是灵魂的决断。”但很遗憾,在这场忠孝不能两全的“灵魂决断”中,真正进入石奢视域的只有父亲和君王,那位被杀的受害者却一直不在场,以致石奢对他连一点愧疚也没有表露出来。有鉴于此,我们有多少理由宣称:石奢通过“灵魂的决断”从事的“毅然赴死”举动,实现了“不坑害人”意义上的实质正义呢?毋宁说,如同舜在窃负而逃时主动放弃王位不足以证明他的圣洁一样,石奢在纵父逃走后因为不忠之罪主动自刎同样不足以证明他的崇高;相反,两人在下面这一点上倒是内在相通的:都遗忘了被自己父亲杀死的无辜受害者,尤其是遗忘了坑人害人理应受到惩罚的正义底线。
更有甚者,黄文在称赞“当石奢释放父亲时,他知道自己犯下了死罪。而他之所以径直而为,是因为他视孝重于生命”的时候,同样背离了它自觉认同的“子隐父罪”属于不义之举的规范性立场,转而认为这类举动正当地体现了“孝父之心”的至高无上。理由很简单:石奢在“释放”父亲亦即允许父亲潜逃的时候,明显是在以“子隐父罪”的形式包庇犯下杀人罪的父亲;至于他后来让人将父亲杀人之事报告楚昭王以及自刎而死,并不会改变这个“释放”行为本身包庇嫌犯潜逃的不义特征。所以,要是我们站在“子隐父罪”属于不义之举的规范性立场上,至少应该对这个“释放”行为表示一定的谴责。但很遗憾,黄文却无保留地赞许它是“视孝重于生命”的“径直而为”,似乎没有意识到被石奢的孝父之心凌驾于其上的还有那位受害者的生命,结果就像石奢自己一样,仅仅把关注点聚焦在了对父亲的“孝”和对君王的“忠”之上,却遗忘了对于无辜受害者的“仁”,从而再次陷入了自败的境地。
本来,倘若如其所是地直面这两个案例(而不是试图用它们来证成某种先入之见),我们很容易看出,它们根本不可能彰显“为父隐”与“为罪隐”的实质性差异,因为在“父”犯“罪”的情况下,不管儿子采用怎样的手法把“父”隐起来,都会相应地把“父”犯的“罪”也隐起来,结果是在不正当地使父亲免受正义惩罚的同时,导致受害者的冤屈得不到伸张,甚至让原本无需担责的儿子受到不正当的惩罚,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谈不上“正义的家庭属性”。例如,假如不是恪守忠君至上的不义法律,而是按照不坑害人的正义法律,犯下包庇罪的石奢不仅不必付出生命的代价,而且还能因为“释放”的是自己父亲的缘故在受到惩罚时获得一定的“容隐”。当然,此处“容隐”中的“隐”字只能是指“为父隐罪”的不义之举,而非所谓“为父隐”的正义之举,不然的话就谈不上减免刑罚之“容”了。换言之,正如拙著强调的那样,正义法律允许的这种“容隐”,归根结底是指针对“为父隐罪”这种“不义之举”的减免刑罚;因此,它与儒家语境里针对“视孝重于生命”这种“崇高之举”的讴歌赞美有着天壤之别,不可是非不分地混为一谈刘清平:《忠孝与仁义——儒家伦理批判》,第278280页。。
所以,尽管黄文在撇开“父子相隐”和“不隐于亲”的命题而孤立地围绕上述两个没有多少相关度的案例展开讨论后,就以跳跃式推理的方式宣布:“孔子所说的隐是大隐,他把尊重亲情与法律而又超越亲情与法律的大义作为自己的成德途径。”但只要回归黄文将这两个命题联系起来的立论语境,我们很容易发现其中的种种漏洞:黄文强调的这种能够等价于“大义”的“大隐”之“隐”,是否包括“不隐于亲”的“隐”呢?如果说两个命题里的“隐”都是“大隐”之“隐”,为什么孔子在前一个命题里要求人们“隐”,在后一个命题里又要求人们“不隐”呢?在“大隐”即“大义”的情况下要求人们“不隐”,岂不等于怂恿人们去行“不义”么?反之,如果说前一个“隐”是指孔子赞同的“隐父”之“大隐”,后一个“隐”是指孔子反对的“隐罪”之“小隐”,同一个“隐”字的核心语义怎么会出现如此鲜明的断裂呢?倘若像黄文所说“不隐于亲”里的“直”字“非常准确地对应于叶公与孔子谈话语境中‘直’的含义”,为什么这两个命题里的“隐”字含义却会出现天壤之别呢?假如对这两个命题里“隐”字的核心语义都难以做出前后融贯的清晰解释,我们又怎么可能消解它们之间的自相矛盾或深度悖论呢?在我看来,如果黄文不能澄清这些显而易见的逻辑漏洞,似乎很难摆脱闪烁其词、左支右绌的窘境。
综上所述,黄文将“父子相隐”理解成“为父隐而非为罪隐”的立论,不仅无法从《论语》以及《左传》中获得文本基础方面的支撑,而且也无法从《吕氏春秋》和《史记》中获得论证理据方面的支撑,甚至无法从黄文自身中获得事实性描述和规范性立场方面的支撑,结果陷入了难以自圆其说的逻辑矛盾,严重缺乏学理上的说服力。
三、批判性的学术研究态度
公平地说,黄文不仅采用了兼顾学问史和理念史的研究视角,分析了古代文献和当前论战中的大量材料,而且还自觉认同了不坑害人的正义底线,甚至对论战双方也都持批判性的态度,几乎可以说是一篇没有片面性缺陷的完美论文了。那么,它怎么会在实质性立论上出现刚才分析的那些自败悖论呢?基于这一问题意识,我想超出单纯商榷的范围就学术研究的方法展开一些讨论。
在我看来,第一个原因或许在于,黄文未能把针对正反双方的批判性学术态度一视同仁地贯彻到孔子身上,而是将自己的立论建立在“孔子是道德高尚的圣人,不可能赞同‘子隐父罪’的不义之举”这个充满敬仰意蕴的预设前提上,结果不是依据《论语》的文本语境如其所是地考察“父子相隐”命题,而是设法找到一切能将这一命题与“不隐于亲”命题融贯起来的案例,却没有注意到这些案例与孔子本人的立场没有实质性关联的简单事实,最终反讽性地遮蔽了“孔子之言本身的意义”。
其实,黄文在第三节一开始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既然“子隐父罪”既为法律所不容,又违于伦理公德,“克己复礼、奉公守法、正直无私、大智大贤的孔子如何会不明白?他又怎会公然主张父子互隐并赞其为正义的美德?他怎会犯如此简单如此明显的错误”?不难看出,一旦对孔子做出了如此完美的价值评判,“父子相隐”内在包含的“将父子互隐其罪视为正义之举”的实际意蕴就已经被当成子虚乌有的东西彻底消解掉了,以致黄文所有论证的目的可以说就是尽一切努力不让孔子犯下“如此简单如此明显的错误”,哪怕它自己要为此付出犯下某些“如此简单如此明显的错误”的沉重代价。限于篇幅,在此主要分析一个简单而明显的案例。
前面提到,黄文在批评论战双方对于“父子相隐”的一致理解时,给出了一个既不符合事实、也有严重漏洞的反问:“自古以来何曾有人把他人隐匿父亲的盗窃行为称为正义之举?”从学理角度看,这其实是一个混淆事实性之“是”与诉求性“应当”的常见谬误,将自己希望或倡导每个人“都应当持有”的规范性立场说成是每个人“都实际持有”的规范性立场,在西方大哲那里也不时出现,不足为奇。不过,黄文居然没有察觉到自己通过大量事实性描述提供的否定性证据,反倒以这个反问作为立论的关键理据,却似乎主要基于下面的原因:只有凭借这个看似理直气壮的反问,才能通过下面的推理清除“父子相隐”命题“将父子互隐其罪视为正义之举”的本来意蕴:既然自古以来都没有人把他人隐匿父亲的盗窃行为称为正义之举,像孔子这样“克己复礼、奉公守法、正直无私、大智大贤”的圣人,就更不可能通过肯定“父子相隐”而把他人隐匿父亲的盗窃行为称为正义之举了;所以,这个命题必定与“不隐于亲”的命题内在一致,都体现了孔子反对“子隐父罪”、推崇“子为父隐”、“把尊重亲情与法律而又超越亲情与法律的大义作为自己的成德途径”的崇高立场。也正是基于这个敬仰性的预设,黄文中才会出现那些简单而明显的錯误,诸如引入没有实质性关联的案例以求证成孔子本人的立场,把同一个“隐”字生硬地区分出正义“隐父”之“大隐”与不义“隐罪”之“小隐”,脱离《论语》的语境而将秦汉以降两千多年来人们的一贯理解说成是遮蔽了孔子之言本身意义的曲解,等等。
我的一点不成熟看法是:学者当然可以站在自己的规范性立场上,对自己的研究对象(某些人物或思潮)怀有敬仰性的态度,甚至充分肯定和赞美他们本来持有的那些与自己立场根本一致的理念。但在我看来,学者在学术研究中却不应该基于这种敬仰性的态度,对于研究对象本来持有的那些与自己立场正相冲突的理念视而不见,甚至为了维护他们的完美形象,不惜脱离原初文本的语境和材料,设法掩盖这两类理念之间的自相矛盾或深度悖论。理由很简单:这样的做法无论有着怎样良好的动机,都违背了如其所是地揭示事实真相的学术规范,突破了“更爱真理”的学术底线,把自己从学术性的研究者变成了非学术的崇信者。当然,按照类似的道理,学者也不可以有意遮蔽自己不敬仰甚至不喜欢的研究对象本来持有的那些与自己立场根本一致的理念,甚至为了抹黑而将他们本来没有的理念强加在他们身上。换言之,学者的使命就是首先如其所是地揭示研究对象本来持有何种理念的事实真相,然后再依据自己的规范性立场,对这些理念该肯定的肯定,该否定的否定——这就是我所谓“批判性的学术态度”的基本内容。
我当然不敢断言自己已经将这种态度完全贯彻到了学术研究中,但的确是在努力落实。例如,尽管我的规范性立场与康德倡导的“人是目的”大体一致,但我对他作为哲学大师的敬仰性态度,并没有妨碍我依据他的文本揭示他建构的哲学大厦两大部分之间由于分别主张“理性在认知上不行”与“理性在道德上很行”所生成的深度悖论,以及他自己将“自由”这块联结两个部分的“拱顶石”变成了“绊脚石”的逻辑矛盾刘清平:《“理性”何以“实践”?——康德实践哲学的深度悖论》,《南京社会科学》2017年第4期;《康德哲学的拱顶石怎么变成了绊脚石:自由与必然的二律背反解析》,《人文杂志》2018年第3期。。再如,虽然从发现了儒家的负面效应时起,我就对孔孟持不加掩饰的批评性态度,但当我通过研读他们的文本发现普遍性的仁义理念蕴含着不坑害人的正义底线时,我同样给予了充分肯定,甚至在国内外儒学研究中率先提出了下面的见解:不仅孔子在人类文明史上最早意识到了不可坑人害人、应当爱人助人的质朴道理,“原创性地成就了人类道德意识上的一个伟大进步……对人类伦理思想的发展做出了无可替代的重大贡献”,而且孟子也主要是因为汲取墨子“公义”理念提出了将“仁”和“义”联结在一起的原创性见解,才成为后世儒家推崇的亚圣刘清平:《忠孝与仁义——儒家伦理批判》,第47页;《孟子何以“亚圣”?》,《人文杂志》2014年第10期。。换言之,我并未因为批评孔孟的血亲情理精神,就闭眼不看或断然否定他们的普遍仁义理念,而是试图凭借学术批判方法揭示二者之间的深度悖论,就像我在本文里试图凭借类似的方法指出“父子相隐”与“不隐于亲”的深度悖论一样。在我看来,倘若不是采取批判性的学术态度直面研究对象的深度悖论,而是想方设法加以掩盖,我们自己就有可能陷入“为了遮蔽某个悖论而生成更多悖论”的窘境。
不幸的是,在我看来,黄文似乎就陷入了这种窘境。例如,除了前面讨论的逻辑矛盾外,它还会因为自己的观点和论证面对一个更棘手的自败悖论:既然窃负而逃既为法律所不容,又违于伦理公德,倡导“仁者无不爱”的孟子如何会不明白?他又怎会公然主张窃负而逃并赞其为正义的美德,犯下如此简单如此明显的错误?然而,由于按照孟子自己的描述,舜将父亲窃负而逃只有隐匿父亲杀人行为的一面,却不包含任何出面指证父亲、事后登门道歉或自刎而死的情节,相反还直接进入了父子二人“终身欣然、乐而忘天下”的结局,黄文想破解这个由于敬仰性态度才会无中生有地形成的自败悖论,或许远比破解孔子面临的类似难题更为困难。所以,在我看来,与其这样大费周折地为孔孟儒学开脱,不如在保持敬仰性态度的同时,直面孔孟儒学原本包含的深度悖论,努力找到走出泥潭的途径。毕竟,不管我们对孔孟怀有怎样的批判性态度,他们在以往理念史上的那份深沉厚重肯定都不会因此烟消云散,相反还会由于悖论得以消除的缘故,在今后的理念史上重新焕发出生命力。
第二个可能的原因涉及到如何对待我所谓的“诸善冲突”。黄文对正反双方的主要批评是:正方过于强调血缘亲情而忽视了正义法律,反方过于强调正义法律而忽视了血缘亲情,所以它才试图通过对“父子相隐”的独特解读,找到一条既能使父子亲情免受伤害、又能维护正义法律的最佳途径。黄文这种全面兼顾的良好意愿无疑值得称赞,却似乎忽视了正反双方的“片面性”源于其中的那个简单事实:由于父亲偷羊杀人突破了不坑害人的正义底线,血缘亲情和正义法律这两种原本都是“可欲之善”的正面价值已经处在鱼和熊掌不可得兼的冲突状态了,根本不可能在任何一方都不受到损失的情况下全身而退,维持皆大欢喜的和谐美满。毕竟,假如父亲是个奉公守法的人,没有从事坑人害人的行为,儿子只需其乐融融地孝父奉亲、共享天伦就够了,干嘛还要自寻苦恼地为“隐”还是“不隐”的两难纠结不堪呢?可是,一旦父亲从事了偷羊杀人的行为,这种浪漫美好的理想局面马上就破灭了,以致儿子哪怕采取视而不见的鸵鸟政策,都会构成看重血缘亲情却轻视正义法律的变相之“隐”。
事实上,正是由于在论战中反复考察了类似案例,我才在道德和政治哲学的研究中发现了诸善冲突对于人生在世发挥重要作用的内在机制:从元价值学视角看,任何人的行为都只会趋于自己意欲的好东西,避免自己讨厌的坏东西,由此遵循“人性逻辑”的头号原则“趋善避恶”;而在两种好东西相互抵触的诸善冲突(包括人际冲突)中,任何人都会进一步遵循人性逻辑的二号原则“取主舍次”,通过权衡比较两种可欲之善的重要地位,做出以不惜放弃次要的好东西、忍受次要的对应坏东西为代价,来确保重要的好东西而防止严重的对应坏东西的艰难选择。所以,只有凭借诸善冲突的机制,我们才能说明为什么在善恶好坏的评判标准之外还需要进一步确立是非对错(正当与不正当)的评判标准的内在奥秘,澄清从“正当(right)”中怎样衍生出“权益(rights)”的语义绵延,揭示“意志自由”如何可能及其与“行为自由(现实自由)”的微妙区别和相互关联刘清平:《试析诸善冲突的根源和意义》,《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中国哲学语境下的善与正当问题》,《人文杂志》2012年第6期;《从“正当”到“权益”》,《同济大学学报》2014第5期;《自由意志如何可能》,《伦理学研究》2017年第1期。。
回到本文的主题上来:一旦引入了取主舍次的人性逻辑,我们很容易解释正反双方为什么都会陷入黄文指出的上述“片面性”:面对血缘亲情和正义法律不可兼得的冲突局面,他们要么肯定血缘亲情的至高无上而将不坑害人的正义法律视为次要的,并且因此把父子相隐的做法評判为“正当(正义)”的;要么肯定正义法律的至高无上而将血缘亲情说成是次要的,并且因此把父子相隐的做法评判为“不正当(不义)”的,从而形成规范性立场截然相反的两大阵营。换言之,虽然论战双方或许原本都有既要血缘亲情、也要正义法律的丰满理想,但一碰上父亲偷羊杀人这种充满张力的骨感现实,他们就不得不遵循取主舍次的人性逻辑,陷入黄文指认的那种“非此即彼”的“片面性”了。
不过,一旦理解了诸善冲突的这种机制,黄文努力寻找的“亦此亦彼、折衷和谐”的第三条道路似乎也就很难走通了。这一点不仅可以从前面分析的自败悖论中看出来,而且还可以从它看重的那两个与孔子本人的立场没有实质性关联的案例中看出来,因为它们没有一个实现了黄文希望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圆满理想,相反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是像正方主张的那样凭借血缘亲情压倒了正义底线,落入了连黄文也视为不义之举的“子隐父罪”结局。如上所述,在楚躬的案例中,虽然父子完好如初,但坑人害人理应受到惩罚的正义底线却被遗忘得无影无踪了。至于黄文赋予了悲剧色彩的石奢案例,更可以说是陷入了“此”被根本否定、“彼”也荡然无存的两败俱伤,唯一得到维系的是对君王的绝对忠诚:不仅那位被父亲杀死的无辜受害者一直不在场,以致坑人害人理应受到惩罚的正义底线被践踏于无形,而且儿子由于忠君至上的缘故也在“灵魂的决断”中毫无必要地“毅然赴死”,结果让犯下罪行的父亲失去了在余生中继续正当地享有亲情之善的机会,而不得不忍受刻骨铭心的丧子之痛。就此而言,石奢案例的确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不过彰显的并非正义法律和血缘亲情的可欲价值在冲突中均被毁灭的崇高伟大,而是具有严重扭曲效应的忠君至上原则的残忍冷酷。更不幸的是,这种忠孝不能两全的残忍冷酷还在此后阳儒阴法的历史进程中绵延了两千余年,在许多情况下以类似的双输方式既毁灭了正义法律,也毁灭了血缘亲情刘清平:《忠孝与仁义——儒家伦理批判》,第157179页,其中也讨论了石奢的案例。。
黄文指出,反方鲜有人回应下面的问题:“如果你的父亲杀了人,你将抱持何种心态,采取何种处理方式?……他们的沉默实际上表明他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也会陷入矛盾:他们驳斥父子互隐,却可能在现实中选择父子互隐。”其实,拙著不仅回答了类似的问题,而且还回答了有关“郭巨埋儿”的更棘手难题刘清平:《忠孝与仁义——儒家伦理批判》,第6364、282283页。,在此谨将我的立场简述如下:如果我父亲杀了人,我会先劝告他自首;如果他拒绝,我会配合有关的调查取证,同时尽我所能为他找到称职的律师;在他入狱服刑后,我会定期前往探望,而不会和他“划清界线”;哪怕他被判处死刑,我作为儿子也会安葬并祭奠他,以这种方式在恪守不坑害人的正义底线的基础上维系父子亲情。诚然,从获悉他杀人的那一刻起,我就清楚地知道我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与他一起正常生活、共享天伦之乐了;但同时我也清楚地知道:父子亲情遭受的这种严酷打击,是由于他突破了正义底线我们必须付出的沉重代价;而我绝不应该为了“使父亲不受法律的惩罚”“使父子亲情免受伤害”,就违背正义底线帮助他隐瞒或潜逃;因为在我看来,只有不坑害人的正义底线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任何要突破它才能获得的可欲之善(包括儒家特别看重的血缘亲情在内),都将因为这种突破变成“不正当的善”,乃至沦为“邪恶”。
当然,上述两个原因只是我研读黄文后的一些粗浅印象,并不敢断言它们一定符合事实,就像我不敢断言本文的见解一定能够成立那样。因此,我真诚地期待黄启祥教授和学界的批评指正。
[责任编辑 邹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