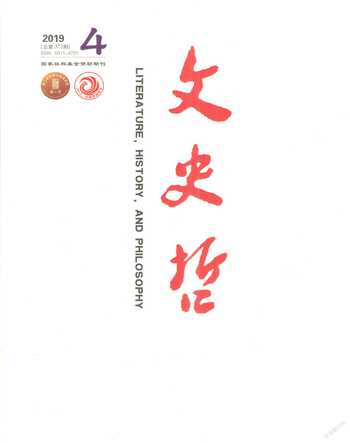知“道”
倪培民 钱爽
摘 要:从西方哲学的视角来看,中国哲学似乎拙于认识论。这是因为西方哲学的核心关注是真理认知,而中国哲学传统则更关注知“道”。从后者的角度来看,认识论需要突破其真理认知的狭隘框架,形成一个包括技能之知、默会之知、熟识之知、程序之知等知识种类的广义的知识——“功夫之知”,或生活的艺术——的学问。所谓命题之知和技能之知,是功夫认知中既互摄而又不能单纯归约为其中某一方的两种形态,而这两个形态也并非功夫认知的全部。功夫認知远比真理认知丰富得多。功夫认知要求体身化,即身体的参与和把所知变为身体的内容,它还要求知道“不知”甚至“弃知”的价值。功夫认知需要对语言的语用功能有足够的认识。从描述功能而言,语言的清晰性和明确性使人倾向于个体化的思路,它具有重要认知价值,但也不利于把握事物的关联和变化。就非描述性功能而言,语言更是丰富的行为方式。描述性的理论体系要求线性的逻辑关联,而功夫体系则遵循功法开展的要求。功夫认知要求功夫主体的全面修炼,即人的内在转化和面向万物的扩展,而不仅仅是理智的培养和资讯的获得。这种修炼的主要方法不是靠接受语言信息,而是通过对楷模的模仿(不同于简单的重复)进行。
关键词:功夫认识论;真理认知;技能之知;体身化;德性认识论
DOI:10.16346/j.cnki.371101/c.2019.04.07
从西方哲学的视角来看,中国哲学似乎拙于认识论。之所以如此,诚如当代美国中哲史名家孟旦(Donald J. Munro)教授所言:“在中国,一个哲学家接受一个信念或主张时,很少关心希腊意义上的真理或错误;这些是西方人关心的。中国人关注的重点是相关信念和主张的行为导向。”①也就是说,哲学在西方一向致力于“求真”(the pursuit of truth),而素以“诸子学说”著称的中国哲学传统则与西方哲学传统不同,它从未有过这一取向。它更专注于认识人生之道,正如中文的“知道”一词所表达的,其原意就是“认识人生之道”。
对纯粹客观真理缺乏兴趣,或许可说是造成中国自身科学技术滞后的原因(这是一个颇具争议的话题,须另作他议),但这却使得中国先哲由此而开发出了被宋明儒者们称作“功夫”的丰富资源。
文所引外文资料凡有中译者,译者均尽量标出,以便读者参考;并且,译文均对照了原文,纠正了原有汉译本的错译或不达之处。该术语可以从广义上理解为“生活的艺术”。从功夫论视角出发,我们发现被狭隘地限定为“有关真理认知的学问”的“认识论”观念必须加以扩充,以便把那些被描述为实践之知(practical knowledge)、技能之知(knowhow)、默会之知(tacit knowledge)、熟识之知(knowledge by acquaintance),以及程序之知(procedural knowledge)等的知识种类都包括进来。通过对“知识”概念进行如此这般的拓展,我们将会发现“知”与“思”的一些新特征,并由此而使认识论的诸多被忽视的方面得到彰显,这其中也将包括我们对“真理认知”的理解。
在本文中,笔者将首先尝试对知识所应包含的范围作一考察,并对此种广义的知识的本质——笔者用“功夫”这一术语标示之——加以讨论。继而,笔者将简析这种功夫知识与真理认知的关联,随后再对功夫认知(gongfu knowing)的一些突出特征作出概述。本文虽不敢声称是对功夫认识论的全面阐释,但的确力图通过陈述各类可能涉及的问题,来倡导对这种阐释的建构。笔者意识到,我们必须通过更为细致而广泛的研究,才能完成对这些问题的充分探讨。
一、功夫大师所具备的是何种知识?
我们首先通过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来展开讨论:功夫大师所具备的是何种知识?凡功夫大师,无论是武术大师,还是足球大师,抑或是语言大师,皆须具备某种与其所擅长的功夫有关的知识。虽然火能燃木、水可溺人,但我们并不把它们的这些能力称为“功夫”。我们以为,功夫是一种涵盖知识与智慧在其中的能力。那么,何种知识或智慧是功夫所必须具备的呢?
(一)技能之知(KnowHow)的“发现”
在我们脑海中直觉地闪现出来的一种回答是,功夫大师所具备的是实践之知,或者说是与命题之知(knowthat)相对的技能之知(knowhow)。
尽管早在古希腊时,哲人们就已经注意到了实践之知与理智之知的不同,但很大程度上却是通过吉尔伯特·赖尔(Gilbert Ryle,19001976)富有开创性的著作《心的概念》(The Concept of Mind),西方哲学探究的灯光才照到了技能之知的领域。赖氏对命题之知和技能之知的著名区分,响亮地提醒人们去关注一个看上去显而易见的事实:我们的知识范围不仅仅只包含关于“是什么”之类的命题,其中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关于怎样做事的知识。关于技能之知的本质,大多数人会认为这种知识是无法用命题性陈述来加以把握的。一个人也许可以把他所有骑单车的技能用命题性陈述表达出来,但实践意义上的有关他如何骑单车的知识却并不存在于他的这些命题性的理智意识中。在命题之知与技能之知的知识来源这个问题上,我们说,虽然一个人可以通过读书或经验观察学到有关骑单车的命题之知,但此人仍须从事相关的实践,才能最终学到这门功夫。至于如何评判知识,我们通常用真/伪来评判命题,而以有效性和美学价值来评判技能。
鉴于技能之知在人类生活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它与命题之知相比所受到的关注之少,确实令人感到惊异。整个近代西方哲学以其对认识论问题的特别关注为傲,但对技能之知却几乎完全沉默。从历史上说,命题之知与技能之知的这种区分可以直接追溯至古希腊哲学对“理论”(theoria)、“实践”(praxis)和“制作”(poiēsis)的区分。希腊人把理论智慧称为sophia,即理智智慧(intellectual wisdom)。“理论”(theoria)一词源于观察或思考某种神圣对象的行为,因此“理论”的对象被看作是更高、更实在的永恒圣域中的存在。与“实践”(praxis)相对应的智慧则是明智(phronēsis)或实践智慧(practical wisdom)。对于亚里士多德而言,有文化的人主要以两种生活为追求目标——1.以追求城邦正义为核心关注的公民政治实践生活;2.以“为求知而求知”作为核心关注的哲人理论思辨生活。“制作”(poiēsis)这一范畴指的是对客体对象进行工艺制作或生产与制作流程这种日常或普通的生活行为。与“制作”相关的知识被称为技艺(technē),或生产性知识。历史上,“技艺”被希腊人看作是与希腊城邦的自由领域有别且较之更低级的领域,而更不用说和纯粹理论思辨相比了当然,这一概括只是对总体趋势的一个描述,并非意在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即诸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希腊哲人皆对这些话题有着复杂的看法。正如孟旦所云:“在希腊人看来,学问的意义既在于它本身,也在于它对行动的引导(不管怎么说,柏拉图确实写了《理想国》,苏格拉底也认为‘知善者必行善’),但他们所青睐的,首先是以其自身为目的的学问。”([美]孟旦:《早期中国“人”的观念》,丁栋、张兴东译,第58页;英文原文见Munro, The Concept of Man in Early China, 55。)。
古希腊的主要哲人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并不认为这些生活方式是完全相互排斥的。它们在当时还依然被公认为是古希腊人生活中所不可或缺的存在方式。对于亚里士多德而言,“实践”指的是政治生活领域中的人类理性行为,因此无法与“理论”完全分离;而“理论”同样也需要训练和教导,是对第一原理、理性和知识的积极追求皮埃尔·阿多(Pierre Hadot)表示,亚里士多德“无意构建一个关于实在的完备体系。相反,他希冀训练他的学生在逻辑学、自然科学和伦理学方面掌握使用正确方法的技巧”。参见Pierre Hadot, Philosophy as a Way of Life(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ing, 1995), 105。。然而,他们的观点已然设定了这样一种等级次序:“理论”比“实践”更完美,而“实践”又高于“工艺”。此外,这些哲人自己的著作多集中于探讨理智智慧。中世纪新柏拉图主义思想者们最终将“实践”与“流程”归在了一起,把它们降格为平民领域的活动。同时,他们通过思辨把“理论”与完全超越的绝对者相结合,从而扩大了思辨生活与实践生活之间的距离。通常意义上的哲人参与城邦生活或实践生活的需求则不复存在,或者说是被下放至那些亟待从对物质财富与权力的追逐中解放出来的俗人那里去了。结果是,技能之知的这种实践知识被进一步地贬低,成了不配被哲学严肃考察的对象。“哲学”(philosophy)一词由philos(爱)与sophia(理智智慧)组成,而非philosphronēsis(爱明智)或philostechnē (爱技艺),这一事实已然暗示出了实践智慧与技能之知的上述命运。虽然对理智智慧的爱本身并不排除哲人们把实践智慧作为他们理智探究的主题,但“philosophy”(爱智)一词却还是很容易诱导(或者毋宁说是误导)学者而更加关注甚至只关注理智理性此处对这一历史渊源的概括得益于笔者一位名叫凯西·里奇(Casey Rich)的学生在其本科毕业论文中所做的出色工作。。
西方近代啟蒙运动虽然很具有革命性,但近代思想者们,无论是唯理论者还是经验论者,都明显受到了中世纪理智主义倾向的影响。真理认知占据了他们的整个哲学事业。技能之知这种实践知识似乎要么被看作不配成为哲学严肃探究的对象,要么则被归约为命题之知的问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赖尔对命题之知与技能之知的区分成了把研究的目光转向实践智慧的醒世之钟不过,“know that”与“know how”这两个英文术语是约翰·杜威(John Dewey)于1922年首次提出的。。
(二)对技能之知(KnowHow)的争论
然而技能之知与命题之知之间的关系远比表面上看起来的要复杂得多。赖尔的这一著名区分在当时迅速获得了广泛反响,同时亦受到了来自各方的挑战。其中的一个主要反对声音,就来自“理智主义者”(intellectualists)。他们认为技能之知实际上是命题之知的一个种类。例如,杰森·斯坦利(Jason Stanley)就表示,当一个人学会如何游泳时,他学到的实际上是有关游泳的某些真理,尽管它们不过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真理。斯氏还表示,一个人关于如何去F的知识可以用命题描述为该人具备这样一种知识,即“w是F这一行动的方法”。说“‘张三知道如何开门’或者‘一条狗知道如何接住飞盘’都是命题之知”,这并不意味着张三或者这条狗必须通过概念来描述或思考这种知识。尽管这条狗只能以实践的呈现模式(a practical mode of presentation)来显示它具有这种知识,这并不意味着它所得到的知识性质不是命题性的参见Jason Stanley, Know How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然而,我们可以用语言把这条狗的所知用命题性陈述表达出来,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这条狗有关如何做这些事的知识可以被归约为命题之知。而且,诚如休伯特·德雷福斯(Hubert Dreyfus)所云:
尽管当一个人在反思的时候可能把各种背景条件视为若干特定的信念,例如当你站立时应该与他人保持多远距离的信念,这些行为方式既不是作为信念而学到的,也不是作为信条从而以因果的方式对我们的行为举止发生作用的。我们不过是在做着我们已经被训练去做的事。而且,作为实践,当它们一旦被转变为命题之知时,其所具备的灵活性就会消失。Hubert Dreyfus, “Holism and Hermeneutics,” The Review of Metaphysics 34(1980:1): 8.
斯坦利似乎从未明确表述过他所谓的作为命题之知之特殊类型的技能之知的特征是什么,但是他确实赋予了命题之知以理智主义者通常不会归之的内容。理智主义者通常把“知”仅仅视为是与认知有关的,即更多地体现为信念的心理表征而非行动;而斯坦利却不仅认为命题之知可以是“非惰性”的参见Jason Stanley, Know How, 4.4.,他还承认,要具备命题之知,就需要具备某些倾向性状态(dispositional states)参见Jason Stanley, Know How, Chapter 5末。。上述这些,加之斯氏本人提出的技能之知的“实践的呈现模式”或命题性事实的“实践的思维方式”,使他看上去更接近于所谓的“极端反理智主义”(radical antiintellectualism),而非“反理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
极端反理智主义恰好是理智主义的对立面——理智主义主张技能之知实际上就是命题之知,而极端反理智主义者则认为所有的命题之知实际上都是技能之知译按:这里的“反理智主义”是有关命题之知和技能之知的一种特殊观点,与平时人们所说的那种对理智的怀疑和敌视的“反智主义”无关。。在过去几十年里,表象主义(representationalism)已经遭到了来自许多不同方面的攻击,如现象学、认知科学、科学哲学、语言哲学以及实用主义等。许多哲学家早已指出,我们的知识并非是简单的对于实在的心理表征。希拉里·普特南(Hilary W. Putnam)表示,知道某一术语的含义并非是一例命题之知,而是一例技能之知——即正确使用这一术语的能力;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表示,掌握语言并非意味着知道规则,而是意味着学会技能;大卫·刘易斯(David Lewis)表示,“黑白玛丽”(BlackandwhiteMary)一位假想的科学家,她具有关于颜色的所有科学知识,但却从未经验过颜色。问题是:一旦她经验到了颜色,她是否学到了新东西呢?这则公案中缺乏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技能之知——即辨别红与非红的能力参见David Lewis, “What experience teaches,” There’s Something about Mary, edited by Peter Ludlow, Yujin Nagasawa, and Daniel Stoljar(Cambridge: MIT Press, 2004), 77103.;后期维特根斯坦表示,理解本身类似于一种能力,它涉及“一项技艺的掌握”Wittgenstein,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Hoboken, New Jersey: WileyBlackwell, 4th edition, 2009),199。。上述哲学家都指向同一方向——命题之知如果不是等于技能之知,也至少是依赖于技能之知。
斯坦利的立场与这些极端反理智主义者的相似之处在于,他比诸如赖尔等反理智主义者更加拉近了技能之知和命题之知之间的距离,从而使两者联系得更加紧密。当然,这两者的重大差别,就在于他们的趋向是相反的:像斯坦利和威廉姆森这样的理智主义者设法运用有关命题之知的语言来描述技能之知,而极端反理智主义者则尝试反其道而行之参见Jason Stanley and Timothy Williamson, “Knowing How,”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98 (2001:8): 411444.。
(三)第四种立场和“功夫认知”
笔者欲提议的是,除了这三种立场(即:1.反理智主义,主张命题之知和技能之知是知识中的两个不同种类;2.理智主义,主张技能之知可以归约为命题之知;3.极端反理智主义,主张命题之知可以归约为技能之知)之外,还可以有第四种立场,即:技能之知和命题之知各自既无法归约为另一方,也无法完全分离。技能之知和命题之知是彼此不同的,但二者却又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所有的命题之知都牵涉到技能之知,就连“知道5+7=12”中也包含有运算能力。一个熟记5+7=12但却无法进行运算的人,算不上是“知道5+7=12”。在中国古代的墨家文献中,有一则关于儒家关于“知仁”的文字:
今瞽曰:“钜者白也,黔者黑也。”虽明目者无以易之。兼白黑,使瞽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瞽不知白黑者,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故(我曰)天下之君子不知仁者,非以其名也,亦以其取也。(《墨子·贵义》)
凡技能之知亦包含命题之知。诚如斯坦利所指出的,即便是一条狗所具备的接飞盘的知识,也包含有它知道飞盘在朝它飞来(尽管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条狗并不知道该物名曰“飞盘”)——无论这种命题之知在这条狗的头脑中是以命题的形式还是“以实践的形式”呈现出来的。
技能之知与命题之知彼此之间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显然,知道保险丝熔断可以使人知道如何修复电路。波兰尼举例所说的用拐杖探路的盲人,是通过知道如何探路来得知路况的。因此,技能之知和命题之知就像太极图里的阴阳两极,不可分离但又各有区别:首先,不可分离的意义是指每一方都包含在另一方之中(正如太极图里黑鱼的白睛和白鱼的黑睛);其次,每一方都是整体的一部分——二者皆是人类知识的特征;再次,二者可以彼此相互转化——命题之知能够使人获得技能之知,技能之知又可以产生命题之知。反理智主义的问题在于把二者过分严格地分离开来,而理智主义和极端反理智主义的问题则在于,这两派都力图把其中的一方归约为另一方。一个人唯有在既具备了命题之知又具备了技能之知时,才得以有知,尽管某些“知”表现出更多的命题之知特征,而某些“知”却又表现出更多的技能之知特征。
然而,命题之知与技能之知这种二分的概念框架依然存在着一个很大的局限,那就是它仍把一些重要的知识种类排除在外。例如,它并未把“熟识之知”(knowledge by acquaintance)包括在内。当我们说张三认识李四或者说张三熟识他的家乡小镇时,这种知识就属于“熟识之知”。熟识之知是我们实践智慧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很明显它既不是命题之知的一个种类,也非技能之知的一个种类。熟识之知不同于命题之知的是,它不可以用“真/伪”来评价。它亦不同于技能之知。张三有从一大群人中辨认出李四的能力,这仅仅是他相识或熟悉李四的一种表现,并不等于他之熟识李四就在于他有此能力假设张三在做了一些外科手术后完全改变了他的样貌,从而使得李四无法认出他,但这并不会影响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张三熟识李四。。另一种在命题之知与技能之知这种二分的概念框架中被遗忘的知识是鉴赏力(connoisseurship),它是对艺术的一种良好而精微的品味能力。一方面,它可以既是命题之知也是技能之知(例如,一位品酒师可以感知一种好酒所具有的微妙口感,同时他也知道如何将其同其他酒的口感区别开来);但另一方面,且更重要的是,它亦不同于命题之知,并且也不同于技能之知(例如,品酒师对口感的审美品味)。
就这一点而言,使用与“理论之知”相对的“实践之知”这一概念也许效果会更好,因为这一术语要比技能之知更具囊括性,并且它可以更自如地把其他非理论之知容纳进来,诸如熟识之知和鉴赏力。不过,把实践之知同理论之知区别开来,就会遮蔽理论之知亦具有的实践导向(practical implications)的一面。 “默会之知”这一术语强调了实践智慧的一个重要特征,而且它可以恰到好处地表征“熟识之知”。但由于与非默会的“显知”(explicit knowledge)之间存在着鲜明的区分,它略去了那些或多或少可以显性化的技能之知(如操作指南)。“程序之知”(procedural knowledge)则是与“陈述之知”(declarative knowledge)相比较而言的概念,但实践智慧中的知识却可以同样包含陈述之知在内。此外,把体现在技能使用中的知识定义为程序之知,往往会使人们聚焦于技能的程序性方面,而忽视了技能的体身化(embodiment,即转化为储存在身体中的能力)。
若把这些概念及其对应面视作语言手段而非构成宇宙的零部件本身,那么我们将会发现它们各自有其特性,能够按照不同的使用目的而有效地发挥功用,同时它们各自亦存在着局限性。为了让我们看到所有这些知识类型之间的联系以及这些语言手段的实践导向,除了现存的对各种不同知识的分类概念外,我们还需要一个能够把握住我们对待知识(无论这种知识是命题之知或技能之知,还是其他类型的知识)的视角的概念。
“功夫”似乎就是这样一个理想的概念。它对主流哲学界而言足够新颖,以至于不会携带进来太多的包袱;同时,它亦允许我们容纳上述概念簇所带来的各种洞见,并允许我们富有创造性和成效性地使用它。将“功夫认知”这一术语作为研究知识的视角,我们进而可以探索的不是它与哪一种知识不同,而是可以探索哪些知识在理智主义的倾向下被忽视了。在“功夫认知”这一概念范围内,我们可以确定这样一些知识维度,它們或者是技能之知的成分多于命题之知的成分,或者是默会之知的成分多于陈述之知的成分,等等。
二、功夫认知与真理
理智主义存在这样一个关键的问题,即它无法设想除了认识“真理”(truth)之外,还能在什么意义上谈论“知”。在本节中,笔者将考察功夫认知与真理认知之间的基本差异,并解释为什么从功夫认知的角度看,认知的内容远不止于真理,而且有时它还需要认识“不知真理”的价值。功夫之知关涉到这样一种认识,即任何信念,无论它是真是伪,都同时是行为。
(一)知识远比真理认知丰富得多
真理认知与功夫认知的关键区别,就在于前者旨在获得真理,而后者则以有效性为依归。因此,比如说同样是“一阴一阳之谓道”(《易·系辞上》)这句话,便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诠释。根据真理认知式的解读,这句话是一个形上命题,是对实在之存在状态的描述,即宇宙之运行乃是包含有阴之翕力和阳之辟力的交互作用的统一,有如那阴阳双鱼构成的太极符号所示。而根据功夫式的解读,该命题则是指导人行动的指示或教导,它告诉人们要在翕辟、动静、常变等之间保持一种平衡。
上述区分使我们发现,20世纪以来对中国传统哲学的诠释大都是从真理认知的视角来加以解析的,并因此错失了对于中国哲学传统而言至关重要的功夫认知维度。这也使我们认识到西方理智主义哲学家的局限所在。通过把对认知的理解限定为真理认知,把技能之知归约为命题之知的一个种类,这些哲学家代表的是拒绝珍视功夫之知的潮流。假设张三是一名典型的学分析哲学的学生,他渴求真理,但是现在他也渴望获得对骑单车这门功夫的更好理解。在理智主义为显学的当世,张三通过阅读斯坦利的专著Know How能学到什么呢?的确,他将学到命题之知对于技能之知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不过,他几乎不需要这样的提醒。告诉张三他需要知道的命题之知是“w是F这一行动的方法,在这里F代表的是骑单车”,这肯定是毫无帮助的。恰恰相反,他将被误导,从而认为他所需要做的无非就是学习一些命题。这就是禅宗所说的“错把指月之指当作了月本身”。理智主义者呈现给我们的这个有关技能之知的理论,好比是通过一幅某人的照片来告诉我们此人是谁。虽然这幅照片捕捉到了此人的形象,但其本人却因此而被平面化到了一个生机与精神并失的二维世界之中。
与此相反,反理智主义与极端反理智主义的各种论述则代表了克服理智主义倾向的逆流。考虑到理智主义很大程度上在认识论界占据主导地位,反理智主义与极端反理智主义作为理智主义的逆流有助于我们克服理智主义的局限性。在我们所举的例子中那个想从哲学中学到功夫的张三,便可以从反理智主义与极端反理智主义这些立场中获得启发。他可以学到,仅仅追求有关事实的理智之知不足以达到他的目的。但是,反理智主义与极端反理智主义这些立场亦有其潜在的问题。就反理智主义而言,对技能之知与命题之知进行对立二分可能会遮蔽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就极端反理智主义而言,它会混淆技能之知与命题之知二者之间的区别,并且会有走向拒斥理论之知的潜在危险(尽管总的说来,极端反理智主义在这方面的问题,比作为其对立面的理智主义要轻)。
说到真理,我们注意到:同样是半杯水,既可以被描述为“半满”,又可以被描述为“半空”。这两种说法的真值并无差别,但它们却涉及到两种截然对立的人生态度。“我将说出真相,全部的真相,且唯有真相”译按:这一表述取自英美法系证人宣誓。这一表述显然是一个虽然善良但却不可能办到的承诺,因为实际上无人能够说出全部的真相。即便是一个简单的行为,如我按一个开关,都可以有不计其数的真实描述,例如“接通电源”“开灯”“照明房间”“惊动一个正在行窃的盗贼”“在开关上留下指纹”“加剧全球变暖”等。每当你描述它时,你总是同时也忽略了它的某些其他方面,因此你选择的描述方式就已经把你的主观偏好引入了你的描述。没有一个真相可以在不涉及诸如语词选择、语调使用、微妙的肢体表达、表达时机的把握等因素的情况下说出来,也没有一个听闻者所接收的真相可以不通过听闻者的各种特定“背景”成分的诠释。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到最后说出来的故事的“真实性”。的确,整个当代诠释学能作证,不存在简单的真实故事。“诠释学”这个词本身就已经包含了“依赖于诠释”的意思,这使得“客观诠释学”这一表述成为了一个自相矛盾的说法。
不过,以上所论并不意味着我们选择用以描述事实的诸方式之间毫无区别。说半杯水为“半满”是乐观主义的心态,它使人看到其所已拥有的,并由此而增强信心;不过,它亦能使人感到满足,从而不再去尝试实现更多的目标。说半杯水为“半空”则是悲观主义的心态,它使人看到了尚有提升的空间,却又有可能使人气馁,感到没有价值,以致放弃。真知应当包含对这些实际差异的理解,并促使人们去相应地使用各种不同的表述。
所有的命题之知都包含有技能之知。这一认识意味着只要一个人不知道相关的“如何”(how),就不能说是真正知道与之相关的“是何”(what)。这一点早已被一些哲人强调过。有些人甚至进一步提出,除了知道那相关的“如何”,真正的知“是何”还必须伴随适当的感受和采取相应的行为的倾向。例如,在孔子看来,所谓“知父母之年”应当包括“一则以喜,一则以惧”这样一种心态(《论语·里仁》)——喜父母之寿考,惧父母之衰老也;所谓“知人”应当包括“举直错诸枉”,以“使枉者直”的能力(《颜渊》);所谓“知《诗》”应当包括从《诗》中获得德育意义的能力(《论语·学而》《论语·八佾》),以及在政务或外事中用《诗》应对的能力(《论语·子路》)。对于孔子来说,真知亦包括愿意并能够采取适当的方式,甚至以恰当的态度来行为。孔子会说,一个仅仅具备有关“礼”的理智之知的人并不能算作“知礼”(《论语·八佾》《述而》);一个不知道如何用恭敬有礼的方式对待自己父母的人,也不能被称为“知孝”(《论语·为政》)。出于同样的理由,我们也可以说,一个不知道如何适当地道歉的人,可以说是不知道何为道歉;一个不知道如何适当地驾驶的人,可以说就是不知道何为驾驶等等。
熟悉西方哲学的人会立刻发现,这里涉及了一个从苏格拉底起就为人熟知的所谓“意志薄弱”(weakness of the will)的問题。苏格拉底表示,没有人明知是恶而故意为之。信念是一种承诺——人们不可能真正地认识到某事而对它没有任何承诺尽管如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所指出的,承诺的程度取决于你所面对的选项是否“真实”(genuine)。所谓“真实的选项”,詹氏意指是活的而非死的、是无法回避而非可避免的、是重大而非琐屑的。一个选项是活的还是死的,由当事者是否愿意按此选择去行动来衡量。由此,则信念被定义为行动的意愿。“在任何有行动意愿的地方都有某种信念的趋向。”参见[美]詹姆斯著,万俊人、陈亚军编:《詹姆斯文选》,万俊人、陈亚军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438页;英文原文见William James, The Will to Believe and Other Essays in Popular Philosophy (New York: Longmans, Green, and Co,1919), 3。。或许有人会说,人不只是受自身理性(或最佳判断)支配,我们的行为也受到自身的情感和欲望的控制。但功夫大师会回答说:如果你能够做某件正确的事,却选择不去做它,那就说明你其实并未真正领会到这事是正确的!真正的技能之知意味着能够将自己的理智意识和情感、欲望和谐地统一在一起。
这就需要进一步引入被称为“知识的体身化”(embodiment of knowledge)的问题。对于理智主义者而言,“知识的体身化”这一措辞本身就显得非常奇怪,因为在他们看来,“知”是心(或灵魂)的职责,无关乎身体。而对于那些从未把身心截然分离的中国古代诸子来说,知识的体身化是不言而喻的。一如徐复观和杜维明所指出的,在中文中experience被称为“体验”,understanding被称为“体会”,examination是“体察”,knowing是“体知”,reflection是“体悟”,recognition是“体认”。孟旦解释道:
当“体”在把自我与事物联系起来的语境中用作动词时,它的意思是使事物成为身体或自我的一部分——简言之,即“体身”之。“体认”这一复合词表明,“体身化”包含某人与某事物之关系的扩充,也即超越对有关事物的常规知识。Donald J. Munro, Images of Human Nature, A Sung Portrai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8), 97.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体身化亦是成圣之道。圣人兼容并包,能够与万物为一体,恃万物以成其形Munro, Images of Human Nature, 99.。
更具体地说,“体身化”有两层相互关联的含义。它首先意味着身体参与到了认知过程中来,如“体感”“体认”等。主体并非被动地接收印象,也不会只用理智进行推理,而是通过身体的参与去体验,带着身体的倾向去体会,依靠身体的感受去体察。这些事物皆只能通过体行(bodily practice)的积极参与方可理解。那些追求学识但却仅从理智层面把它当作理论话语来追求的人,很难理解是什么使得孔子及其弟子颜回在生活拮据之时仍不改其乐(《论语·雍也》《论语·述而》),也很难理解是什么使颜回如此心驰神往以至于欲罢不能(《论语·子罕》)。这就解释了为何传统上中国人先是记诵并恪守经典,而后才设法领会之。他们用实践体验和反复诵读来发展更深层次的体会以及体鉴(appreciation)所需的精湛技艺(virtuosity)。诚如宋儒程颐所云:“今人不会读书。如读论语,未读时是此等人,读了后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读。”朱熹:《论语集注·论语序说》,《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3页。可以毫不牵强地说,用理智主义的路径方法去读儒家经典,就好比是镜花水月。
人们通常通过阅读入门指导和规则的方式开始学习功夫,但指导与规则更像是程式,而不是律令或描述性真理。它们旨在使人得到能力,而非给人们设置约束限制或使人们用理智去认识某事某物。其实,传统上衡量一个人的功夫艺术的标准,就是看此人是否能够自由超越既定的教导——不仅是能够权衡何时适合于不去遵循这些教导,而且能够自发地、不假思索地以这样一种适当的方式作出回应。这就是孔子认为的最难以掌握的“权”的艺术(《论语·子罕》)。“权”字原意是测定重量的衡器,并由此引申出“权衡”或“判断”的能力。一名功夫大师并非是教条本本的机械拥趸,而是一位艺术家。
其次,体身化意味着所获得的知识应当真正成为身体或人身的一部分。具备键盘打字技能的人,会觉得他们对于每个按键位置的知识,与其说是储存在大脑中,还不如说是在手指中。这种“肌肉记忆”体现在他们无须思考便能自动触及正确按键的处理过程中。他们亦会发现,借助键盘打字这项技能,键盘成为了他们身体的延伸。关于这一点,我们在第三节谈及“对‘知者’的培养”时,会进一步加以讨论与本文中所涉及到的许多其他议题一样,“知识的体身化”亦是一个大话题。该话题已被若干当代哲学家加以深入的讨论,如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汤浅泰雄、张再林等。。
(二)為何我们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掌握真理?
按照求真的要求,“知”总是好的,“不知”则是不好的。《老子》第七十一章中的“知不知,上;不知知,病”这一表述通常被诠释为“知道自己的无知,是最好的;本是无知却认为有知,是一种恶疾”。但王弼却认为这句表述应当作如此解读:“不知知之不足任,则病也。”王弼撰,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78页。对这一段话的更与众不同的解读是把第一个“不”字当动词“弃”来读:“抛弃彼所知者,乃为最佳;追求知彼所不知者,乃是病态。”造成这些解读各异的原因,是原文表达的简约。尽管最后这一种解读与我们的普遍观念相悖,但却是与《老子》第四十八章的以下思想相一致的:
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
常规的知识总是限制着我们的头脑。当我们说“这是一台洗碗机”时,我们常常忘记这亦是一台制造脏水的机器。当我们学习一门语言时,我们得到的是一种特殊的描绘世界的方式。一个人必须卸载掉所学的东西,才能够摆脱常规的束缚、无端的假设、不良的思维习惯等,从而回归到思维原初无拘无束的自然状态。
庄子亦谈到了“弃知”的益处。《庄子·齐物论》通篇都在讲摒弃常规区分。他说:“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庄子最著名的一则寓言极好地阐明了这一点:
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倏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庄子·应帝王》)
庄子用其典型的嘲讽语气表示:“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庄子·知北游》)正如何莫邪(Christoph Harbsmeier)所说,“因此不知(notknowing)绝不是无知,它是道家的docta ignorantia(有学问的无知)的高级版。它不是对科学知识的反理智主义式的拒斥,它本身就是一种先进的科学理论化的产物”Christoph Harbsmeier, “Conceptions of Knowledge in Ancient China,” Epistemological Issues in Classical Chinese Philosophy, ed. by Hans Lenk and Gregor Paul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3), 25.。何氏指出,在西方传统中亦可以发现相似的洞见。库萨的尼古拉(Nicholas Cusa,14011464)的杰作《论有学识的无知》(De docta ignorantia)就是以题为“为什么知识就是无知”(Quomodo scire est ignorare)的章节作为开始的。塞克斯都·恩披里柯(Sextus Empiricus,活跃于180200年间)和伊利斯的皮浪(Pyrrhn of Elis,约前360前270)都像庄子一样“培养了一种怀疑的态度,以此作为一种达到心平气和、心神安宁(思想的安定平衡)的方法”Harbsmeier, “Conceptions of Knowledge in Ancient China,” 27.。
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须对“欺骗(无论是自欺还是欺人)永远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这一断言提出质疑。一旦我们将认识论视野拓宽至一般意义上的对知识的哲学考察,并且从功夫的方法来反思对真话实言的执着时,我们就会发现,诚如罗伯特·索罗门(Robert Solomon)所指出的,“并非所有的假话都是恶意的,也并非所有的欺骗都是谎言。真话实言有时伤人甚至害人,但假话谎言有时却可以护人励人,欺骗有时亦可以出于高尚的目的”,“真话实言是为伦理服务的,而不是反过来由伦理为真话实言服务”Robert C. Solomon, “Self, Deception, and SelfDeception in Philosophy,” Self and Deception, A CrossCultural Philosophical Enquiry, ed.by Roger T. Ames and Wimal Dissanayake( Albany &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6), 92.。尽管欺骗有明显的危害性,但它有时却可以为产生积极效果而发挥重要的作用。
儒家传统中有无数故意欺骗(或自欺)的例证。其中一个普遍的假设,即圣王尧、舜和禹都是实际存在的。有关他们卓越品行的故事在传统时代从未遭受过质疑。这些故事是这种人道主义文化的共同资源,对它们提出质疑只会使人类的生活资源贫困化。有圣诞老人的世界要好过没有圣诞老人的世界。“汝终有一死”当然是一句真话,但并不适用于生日祝福。“无物常驻”亦是一句真话,但没有人愿意在婚礼上使用它。在获得功夫的过程中,欺骗(或自欺)常常是掌握功夫之知的必要环节。对于某些人来说,“精明的自我修炼者可以通过说服自己他所期盼的自我转化触手可及,用自欺作为激发自我的工具”Amélie Rorty, “UserFriendly SelfDeception: A Traveler’s Manual,” Self and Deception, A CrossCultural Philosophical Enquiry, ed. by Roger T. Ames and Wimal Dissanayake , 78.。然而,对于另一些人,则更适合反其道而行之。正如索罗门所提到的,一些高僧大德诱导沙弥相信他们自己“乃最恶之人”作为策略来促使他们提升自我Solomon, “Self, Deception, and SelfDeception in Philosophy,” 92.。我们当然可以对这些培养方法的有效性进行评估,但问题在于——我们的评估并非是要弄清楚哪一种方法揭示了真理,而是考察在何种条件下它們会趋向于产生什么效果或影响。激励法对于那些已经发现提升点但却缺乏勇气和决心的人也许更加有效,而反激法会对那些尚未发现有提升必要的人有着更好的效果或影响。
事实上,正如索罗门所非常确切地阐明的,“没有谎言这层隔膜,我们最简单的社会关系都将不复存在”Solomon, “Self, Deception, and SelfDeception in Philosophy,” 97.。从真理这一点来说,“我是对的,你错了”——这是非常重要的原则问题;从功夫来说,我们则会问:“这一问题的实际意义是什么?”厘清微不足道的真理果真有助于夫妻更加和谐同处吗?还是恰恰相反?无论是关于朋友为我们策划的惊喜派对,还是关于某个我们认为可以破解的谜语的谜底,或者是某个朋友的私生活秘密,乃至政府的机密信息,在许许多多的场合下,我们都会说“我不想知道”。
当然,这一洞见并非意味着拥有知识总是不好的而不知才是好的。通常,那些选择忽视由过去积累而来的知识的人往往会一事无成,甚至更糟。问题在于智慧并非总是由拥有某种知识来衡量的。道家的圣人是睿智者,尽管在有小聪明的人眼中,他们或许像是低智商的愚昧无知者。在道家圣人的理解中,智慧并不同于拥有许多真信念,而且信念无论是真是伪,都有自我实现的功能。我们通过认识某物是x,从而不仅把它当作x,而且亦使其成为x!正如庄子所言,“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庄子·齐物论》)。这亦是潜藏在佛教“思即行”的信念背后的道理所在。面对同样的半杯水,是那些视之为半空的人使之成为半空的,而那些认为是半满的人使之成为半满的。认为你有病就可以使你生病,认为你良好就可以使你身体好转。对社会产生混乱的普遍焦虑可以导致社会混乱。当所有人都认为股市即将崩盘时,股市就会崩盘。大多数情况并不是如此极端,但仍然会或多或少地有这样的效应。新闻记者常认为他们所做的事情无非就是报道真实故事,但他们的报道往往会影响到他们所报道的事情,从而成为故事的一部分。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揭示了这种现象在社会与人际关系中是多么常见:
例如,你是否喜欢我?在无数的例证中,你是否喜欢我都有赖于我是否主动迈步迎向你,而且愿意相信你必定喜欢我,并给予你以信任和期望。就我个人而言,在这种情况下,能使你对我产生喜欢的条件就是我先前持有这样一种信念,即你对我的喜欢是存在的。……在此,对某种真理的希冀,就是导致这个特殊真理的存在的原因,这在其他不计其数的情形中亦是如此。William James, The Will to Believe and Other Essays in Popular Philosophy, 2324.
简言之,对世界进行分门别类,就是在塑造我们的世界。一个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他自己所选择的信念构成的。
三、功夫认知的特征
功夫视角亦对“知”或“思”的方法有着重要意义,因为“知”和“思”的方法与所知或所思的对象是密不可分的。众所周知,许多主流西方哲学家并不愿意承认中国传统思想是哲学。其背后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中国的哲学著作常常显得支离破碎、含糊其辞、自相矛盾而且多有无根据的断言。为了使其合法化为哲学著作,现代中国哲学学者力图采取西方的方法使中国哲学理性化说有一种单纯的“西方的方法”存在当然是有问题的,因为西方人也采用多样的方法来思考问题。不过,在西方被广泛接受的观点是,思想的清晰性和推理的逻辑性是好的思维的两大基本要求。,诸如对关键术语提供定义并分析之、以时兴的辩论方式重构理论,乃至善意地对文本中出现的令人费解或玄秘深奥的部分视而不见。但通常来说,中国哲学这些所谓的短处事实上却是其功夫导向所要求的。因此,按照西方标准来重构中国哲学,将会遮蔽中国传统思想文本中有独特价值的内容。所以,我们应当把方向调转过来,从功夫的视角对以法国哲学家勒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为典型代表的西方哲学方法论及理性进行考察这并非意味着西方哲学家都是完全按照笛卡尔的思维方式去思考问题的,毋宁说笛卡尔的思维方式成为了西方的典型思维方式,并且大多数西方哲学家都带有笛氏思维方式的某些重要特征。例如,雅克·马里旦(Jacques Maritain)就指出,“每一位现代[西方]哲学家都把自己看成是从一种绝对的开端出发,并视自己肩负着带给人们有关这个世界的一种新观念的使命。就此意义而言,他们都是笛卡尔主义者”。Jacques Maritain, The Dream of Descartes (New York: Philosophical Library, 1944),166167.。
(一)对语言的建设性和诊疗性使用
大部分理智主义者都含蓄地支持这样一种假设,即任何能够知道的事物都可以用语词明确地表达出来。这一点是功夫认识论将明确提出质疑之处。我们的生活似乎告诉我们,我们的大量经验都不能通过语词明确地传达出来。当一名品酒师表示酒的味道就好像在舌尖上跳舞,或者当一名中国书法家表示行笔如仙人腾云驾雾时,他们并不指望读者无须凭借具备一定造诣才可获得的相关经验或体验就能够理解他们的用意所在。人们不会去抱怨这些术语是否得到了明晰的界定,因为缺少了相关的经验或体验,这些术语的内涵便注定是含糊不明的。
西方哲学是如此执着于清晰而明确的思考,以至于模糊性和晦涩性被认为是比谬误还要糟糕的情形——它们几乎与混乱、不通和无感知能力同义。笛卡尔把理解定义为具备清晰而明确的感知能力,他甚至提出把清晰性和明确性作为真理的标准。毫无疑问,清晰的思考与感知不仅对于认知真理,而且对于过上好的生活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它一旦被视为思考的唯一方法,就会阻碍我们超越那些可以被明确描述出来的东西。
这一点对于艺术来说是特别成问题的(须知功夫是一门生活的艺术),因为艺术需要体身性和创造性,但这一点甚至对于真理认知来说也带有局限性。坚持主张清晰而明确地看待事物,将会使人们形成一种原子论的世界观,把每个对象都视作本质上无差异性、无变化且无实在联系的个体。在这种原子论的观点看来,“一物与一物毫无二致。……在这种存在被理解为没有变化的学说中,差异性恰好是对存在的否定。自我同一性严禁事物发生改变,除非它确实不再存在。由于有了这种自我同一性,真正的存在被看作是一成不变的”Etienne Gilson, Being and Some Philosophers (Toronto: Pontifical Institute of Mediaeval Studies,1949), 11.。笛卡尔正是从其坚持主张的清晰而明确的思维方式出发,逐渐走向了身心分离、主客分离及物质和运动的分离。当他用明晰的方式去思考每一事物与众不同的抽象“本质”的时候,他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不可调和的二元论与两极分化的世界当中。
沿着相同的理性路线,休谟(David Hume)陷入了一个各自有别的观念世界之中。他发现,他找不到任何一种能够把那些观念“粘合”在一起的“粘合剂”。就因果关系而言,休谟发现我们能够经验到的不过只是“恒常连结”而已(它仅意味着一件事紧接着另一件事发生,这是恒常的,而人们察觉不到这两件事之间的任何实际联系);就人格同一性而言,休谟发现自己有的不过只是“知觉束”而已(即知觉以“捆束”的形式出现,但没有任何一个存在于不同的知觉之间的“绑定”是可以被感知到的)。在这两种情形中,休谟的问题就是——“心灵在各别的存在物之间无法知觉到任何实在的联系”[英]休谟:《人性论》下册,关文运译,郑之骧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674页;David Hume,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Second Edition), ed.by L.A. SelbyBigge (Oxford: Clarendon Press,1978), 636。。他所感知到的存在物都是惰性的(inert),既不能彼此相互关联,又不能发生任何变化。休谟认为,是我们把因果联系和人格同一性投射到不同的知觉上去了。他并没有认识到他之所以无法感知到联系,原因就在于他预先就把自己观察的视角设定在了“清晰和明确”那一档上。
与此相反,以《易经》为首要代表及后来反映在儒、道两家著作中的中国传统世界观,都是用整体论的视角来看待世界的,认为世界处在转变与转化的恒常流变之中。世界的静止和单纯性只能在相对的情形下来加以理解。之所以如此,一部分原因是我们主观地将事物个体化的兴趣使然,另一部分原因则是由于存在本身会有相对静止的凝聚收缩的阶段。由于“变易”是事物本身的性质,模糊性和差异性并非是对事物存在的否定,因为事物恰好是通过转化为他物而彰显自身并证实其存在的。
陈汉生(Chad Hansen)把中西这两种观点同中西语言的差异作了一个饶有趣味的联系Chad Hansen, A Daoist Theory of Chinese Though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4651.。他表示,在西方语言中,名词术语的单复数之分表明,西方思想事先就有了把世界设想为是由不同的个体对象集合而成的意向或倾向。故而,西方语言的使用本身,就是将事物进行个体化来思考并感知的训练或程序化过程。学习如何使用“cow”这个单词,就是在学习何者才算是一头乳牛,以及何者才算是同一头乳牛。与此相对比,中文名词一般来说更接近于西方语言中所谓的“不可数名词”(mass nouns),没有“可数的多”与“不可数的多”(many/much)、“可数的少”与“不可数的少”(few/little)之分。这表明,中国思想事先就有了把世界设想为一个连续统一体的意向或傾向,尽管这个连续统一体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加以分解。西方语言使其言说者们事先就有了把恒常不变者(它赋予个别对象以自我同一性)视作实在的意向或倾向,而中文则不是如此。
从功夫的观点来看,以分析的方式清晰而明确地看待事物,和以合乎情境的方式整体性地看待世界,这两种方式都有其实用价值。当你在驾车时,你不会想让你所能看见的东西变得模糊不清,但同时你也会希望从整体的角度和在变化当中把握路况。在接受外科手术时,你会希望你的医生用刀非常精准,也希望他能够运用精密的命名体系对你身体的每一个错综复杂的部位都加以区分;不过,你也会希望医生把你视为一个完整的人来看待,并认为你身体的各部位是与作为整体的你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的,而不是武断地强行使二者判然割裂开来。问题并不在于我们不需要分析型思维方式,而是在于除了发现区别和“个体事物”之外,功夫还要求我们发现联系、趋势和事件。笛卡尔式的理性的问题恰恰在于它自诩是解读世界的唯一正道。笛卡尔的方法成为解读世界的主导方式后,确实成就斐然,尤其是在科技方面;但是,它亦对我们理解和重视事物的联系、转化和空无制造了诸多困难。在极端情况下,分析法甚至会要求我们把“我跑步”和“我以每小时10英里的速度跑步”当作两件不同的事情Jaegwon Kim, “Events as Property Exemplifications,” Action Theory, ed.by M. Brand and D. Waiton (Dordrecht: Reidel,1980), 159177.。不错,从逻辑上是可以把这些非常清晰地区分开来,但这样就丢失了万事万物之间的联系,最终也将无法理解何谓“变”!在一个我们自以为明晰地看待事物,而恰恰因此而对这些方面全然熟视无睹的世界中,我们需要想到模糊性具有的建设性和富有成效性的功用。
上述这一点使我们引出了这样一个对比,即真理认知的认识论假定语言的功能仅仅在于陈述命题性真理,而功夫认识论则对语言的使用所具有的非描述性功能更敏锐入微。功夫大师在提供指导及传达其知识时,经常使用他们的语词来影响或感染其学生,而不是去描述事实。注意不到这一点,就会产生非常严重的误解。
陈汉生受孟旦的启发,表示:
西方哲学有关语言的论说采用的是柏拉图哲学的实在论方式,聚焦于形上学和认识论。我们把我们的哲学活动设想为是研究如何在我们的大脑里客观地反映出实在。与此相反,中国哲学家有关语言的话语采用的则是儒家的实用主义方式,聚焦于用来塑造使行为与道德相符的倾向和情感的社会—心理技艺。Chad Hansen, “Chinese language, Chinese Philosophy, and ‘Truth’,” Journal of Asian Philosophy, Vol. XLIV (1985:3): 495.
中国哲学家不试图去获得符合论意义上的真理,也不试图去援用证明、知识或信念来获得支持,而是试图去保证“名”的可接受性。陈汉生表示,在西方,“语句信念陈述(sentential belief statements)表征的是人与所信的语句之间的关系,[而中文的]词信念陈述(termbelief statements)则把人刻画成具有使用与某一对象有关的特定用词的倾向。在中文中,词信念表征的是一种回应的方式,而非一个命题性内容”Chad Hansen, “Chinese language, Chinese Philosophy, and ‘Truth’,” 501.。
的确,中文从一开始就把定名看作是把对象明确化的行为,是将语言活动放到实践生活情境中去定位,而不是把它当作指称某一事物的方式。汉代许慎在其编著的字典《说文解字》中就表示:
名,自命也,从口从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见,故以口自名。许慎:《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31页。
正是因为功夫认知需要对狭隘地用理智看待事物并仅把语言当作描述的工具这样一种强大的习惯进行制衡,所以佛教禅宗发展出了刻意使用荒诞不经而又振聋发聩的陈述的激发手段,使思想从执着中解脱出来。这种语词的治疗用法亦可见于“后现代”西方哲学,如萨特(JeanPaul Sartre)、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和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著述中。
(二)一种不同的体系
一个笛卡尔式的理性主义者会建立一套线性的理论体系,其成分通过逻辑推理而与一系列的结论联结在一起;而一个功夫大师的学说体系则通常依据修行水平、行为的实践导向以及对环境的特殊回应而建构起来,所有这些都旨在帮助人们在各自的艺术领域中出类拔萃。按照评价一种理论建构的方式去评价功夫体系,就好像要求菜肴要像菜谱那样陈列出来,或者(更糟糕的)像美食杂志文章那样呈现出来。一个人可以用一种线性的、逻辑的方式把一个菜的各种用料成分讲清楚,但菜谱并非菜肴本身。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何诸子(比如孔子)所教授的哲学与典型的哲学话语很不一样。孔子从未以系统的讲学来表述其观点。他的学说大多是通过简短而直接的教导提出的。有时,这些学说是孔子通过自己的生活方式以现身说法的形式提出的。从《论语》可以看出,当弟子向孔子问“仁”时,孔子从未试图去定义“仁”本身。他谈及一个“仁”人会是何样,他们会如何行动,并根据每位弟子的特殊条件给予教导,从而使他们知道他们应当在哪种层次或水平上以及在哪一方面开始或继续他们的实践。这种教学方法确实是功夫大师而非哲学教师的典型方法。倘若孔子仅仅用言语来描述“仁”,他将会误导弟子们进入纯粹的知性理解的歧途中去。在知性理解中,“仁”的真精神是不存在的,这就好比隔靴搔痒一般。
从这一方面来看,我们对中国经典文本中许多看上去前后矛盾不一致之处,也同样开始有了理解。例如,我們发现孔子赞扬他的得意门生颜回时表示,“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论语·子罕》)、“不贰过”(《论语·雍也》)、“其心三月不违仁”(《论语·雍也》)。但我们亦发现孔子还有这样的表示:“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论语·里仁》),他亦哀叹道:“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论语·公冶长》)。在我们责备《论语》文本的内容前后自相矛盾之前,应当认识到孔子很有可能是有意夸大其词,就像中国家长经常对他们的子女做的那样,向他的学生提出挑战,让他们用实际行动来证明他是错的。
又如,功夫路径方法亦让我们理解了为何一位佛教高僧大德会打发他的新弟子去扫地打水,很长时间也不去教授他任何东西。尽管扫地或打水与涅槃之间没有丝毫的线性逻辑联系,但是像这样做一些烦琐的体力劳动有助于使一个人戒骄戒躁。当然,这还是不够的。一个人虽不骄躁,却可能缺乏实现更高的完满境界的抱负。因此,师傅同时亦须在恰当时刻促使其弟子理解到众生皆有佛性、人人皆可成佛。当弟子处在错误地认为这两件事(即扫地和实现涅槃)是完全分离的两个阶段时,师傅就必须进一步教导该弟子去发现通过平常行为亦可以立地成佛。这里的“逻辑”和儒家经典《中庸》里所说的“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是一样的。
(三)对认知主体的培养
功夫之知的这些基本特征对于如何获得功夫之知具有深刻的导向作用。这里的重中之重是实践。陈汉生在描述中国古代的“知识”概念所具有的特征时表示,这里的“知识是在训练的意义上的学习结果,而不是获得所谓概念和事实资料意义上的学习结果。其所学得的范式性的东西,是传统儒家的德性”Chad Hansen, Language and Logic in Ancient China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3), 66.。他的“是此而非彼”的概括受到了何莫邪的挑战。何氏指出,在中国古代,“也同样存在事实和科学范式”Harbsmeier, “Conceptions of Knowledge in Ancient China,” 12.。麦高思(Alexus McLeod)对于早期中国哲学里的真理理论有过更加系统和公正的梳理Alexus McLeod, Theories of Truth in Early Chinese Philosophy: A Comparative Approach(London and New York: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15.。的确,如果命题之知和技能之知如我们先前所希望厘清的那样,是明显不同但又不可分离的话,那么,资讯的获得和训练也应当是不可分离的。不仅所有的训练中都必须包含有资讯的获得,所有的资迅获得亦需要训练。命题之知和技能之知就好比阴阳统一体的两个不同方面。但是,考虑到人们通常倾向于把知识看作是信息的获得,强调训练是获得知识的一种方式是很重要的。
受德性伦理学复兴的启发,当代认识论学者也相应地开拓出了一条所谓“德性认识论”的新路径。诸如公正、清醒、勇敢、勤奋、果断、守纪、好奇、谦逊和坚毅等理智德性(intellectual virtue),由于它们对于获得知识而言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而倍受关注。德性认识论让我们注意到,我们可能需要准备并磨练我们已经具备的能力(例如,去除或避免可能会妨碍我们的能力正常发挥的障碍),同时发展我们学习的能力以及做出适当回应的能力。
就这一点而言,中国哲学已经达到了非常深刻的程度。以众所周知的“思想的开放性”(being openminded)这一理智德性为例,它意味着我们承认自身的可错性,愿意倾听并考察与自己不同的观点,并且如果被说服自己的观点是错的,就愿意改变那些信念。这对于功夫学习来说当然是重要的。但“思想”这一概念本身就非常具有理智主义色彩。具备“思想的开放性”可能导致这样一种倾向,即人们会认为理智是我们认知过程中的唯一相关成分。功夫学习则要求在具备思想开放性的同时,还要使我们内心世界的情感方面——“心”——也具备开放性。有趣的是,与英文单词“mind”大致相当的中文“心”,在词源学上亦有“heart”(心灵)之意。“心”具有“思”与“感”的功能,因而它并不是非物质性的。与笛卡尔哲学中作为与“身”相区别的本体论实体——mind不同,中文的“心”字指的是贯通整个人体的身体器官。这也就是为何大多数学者会把“心”字翻译为“heartmind”的原因所在。虽然这种翻译不那么简练,但它把握住了身与心、思与感之间的联系。诚如《大学》所云:
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此谓修身在正其心。
几乎所有的东方哲学传统都发展出了有关如何“正心”的精致学说。这些传统所使用的一种常见方法,便是“入靜”(meditation)。对于中国哲学家而言,入静不仅与所思想的内容有关,而且也是关于“心”的预备工作,以使其能够作出适当的回应。在佛道两家的哲学中,“心”经常被比作“镜”。镜必须平滑,其自身不可有“成见”或“偏见”,以便能够清晰而准确地反映客观世界(《老子》第十章)。但正如凯伦·卡尔(Karen L. Carr)和艾文贺(Philip J. Ivanhoe)所观察到的,对于中国古人而言,“镜并非只是信息的被动‘反映者’;无论何物在其面前出现,它们都能提供精确而恰当的回应”Karen L. Carr and Philip J. Ivanhoe, The Sense of Antirationalism, the Religious Thought of Zhuangzi and Kierkegaard (New York & London: Seven Bridges Press,2000), 38.。镜样的心不仅能理智地接受,亦能在情感上作出回应,并以恰当的方式作出回应。这种入静不仅需要理智的参与,也涉及到整个人,其中包括调整身体姿势、调整心理状态、调整呼吸、并运用想象力来进入某种存在状态。这种实践是中国古代哲人达致其洞见的方法。庄子所谓“坐忘”(《庄子·大宗师》),朱熹所谓“半日静坐,半日读书”(《朱子语类》卷一一六),《大学》所谓“意诚而后心正”,都是在给予我们这类有关如何转化人生的教导。
主体的预备工作还在另外一个意义上对于“知”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功夫实践者常有这样的体会,在长期勤恳地实践功夫后,恍悟的瞬间会随之而来。一个未经训练的耳朵并不会注意到一段音乐的错综复杂。品酒师需长期的训练以发展出其所需具备的敏感性。“理解一种特定的智力行为所需的知识,恰恰是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做出那种行为的知识。”[英]吉尔伯特·赖尔:《心的概念》,刘建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53页;Gilbert Ryle, The Concept of Mind (London: Hutchinson,1949), 54。译案:译者对照英文原文对译文作了适当改动。如果你不知道如何以可以理解的方式使用一门语言,你就无法理解其他使用该语言的人在说什么Jennifer Hornsby and Jason Stanley, “Semantic Knowledge and Practical Knowledge,” 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 Vol. 79(2005, Supplementary Volumes): 125.。如果你从未练过花样滑冰,你就无法成为一个优秀的花样滑冰裁判。中国有一句俗话说得好——“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
认知主体的训练也牵涉到学习如何协调波兰尼所谓的“集中意识”(focal awareness)和“隐附意识”(subsidiary awareness)Michael Polanyi, Personal Knowledge, Towards a PostCritical Philosophy(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8), 5557.。在演奏一段音乐时,钢琴家须意识到其手指的动作,但他的注意力须集中在音乐上而非集中在手指上。如果他把注意力转移到其手指的感觉上,那么他将会磕磕绊绊甚至不得不停止演奏。这个例证是一个普遍现象而非例外。试想如果你在讲话的时候一直把注意力集中在你嘴唇和舌头的运动以及你声带的振动上,将会发生什么情况?——你很有可能完全无法说话。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对唇舌、声带等的隐附意识,你也无法说话。因此,学习知道如何做某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使你的集中意识从隐附意识的拖累中解脱出来,同时又能够自然而然地以潜意识的方式对这两种意识加以综合并作出反应。这正是道家所谓的“无为”,或曰“为无为”。
与这种认知相关的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自身与外在于我们的事物之间的弹性界线。“通常,我们都认为自己的手脚都是身体的一部分,而不是外在物。这太理所当然了,以致只有在这些部分偶然受到疾病困扰的时候,我们才意识到那只是一种预设。”[英]迈克尔·波兰尼:《个人知识:迈向后批判哲学》,许泽民译,陈维政校,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8页;英文原文见Polanyi, Personal Knowledge, Towards a PostCritical Philosophy, 58。另一方面,外在于我们身体的对象物通过我们的隐附意识亦可以成为我们自身身体的一部分:
事实上,我们运用锤子和盲人使用拐杖的方式都表明,在这两个例子中,我们都把我们与被我们视为处于自己之外的物体相接触的点向外延伸。当我们依赖于一件工具或拐杖时,它们都不被当作外部物体来处理。……我们把自己倾注于它们之中,把它们吸收为自己的存在的一部分。[英]迈克尔·波兰尼:《个人知识:迈向后批判哲学》,许泽民译,陈维政校,第8889页;Polanyi, Personal Knowledge, Towards a PostCritical Philosophy, 59。
我们越是能够吸收外部世界的事物,自我就会变得越发广大,我们也就能够调动更多的外部世界事物。这种培养过程并非是试图涤除主观性,从而使人能够具备纯粹的客观知觉而毫无任何偏见。这种客观性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即便人们能够获得之也是不可取的。毋宁说,这种培养乃是转化我们的主观性使之达到最佳状态,从而使其能够以一种最为和谐且最富建设性的方式与世界产生共鸣。在培养的过程中,人们可以内化其所学到的东西,使其与自身的主观条件相和谐,同时还可以把人的主观性向外拓展乃至与天地同流。
从这层意义上说,培养自我和走向世界就变成了同一个过程。诚如詹启华(Lionel M Jensen)所言,对于宋明新儒家来说,“‘致知格物’并不是一种智力训练,而是对‘神’与‘气’的物理调节,其结果可以消解内与外、今与昔的界线”Lionel M. Jensen, “Dwelling in the Texts: Toward an Ethnopoetics of Zhu Xi and Daoxue,” 未刊稿。。孟旦在评论朱熹“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的观点时指出,“对于无偏者而言,万物皆成一体”——这是儒者修身的一种理想状态,通称“天人合一”Donald J. Munro, Images of Human Nature, A Sung Portrait, 102.。
有记载说,许多宋明儒者、道者和释者在他们静深冥思时,都曾有过达到与万物为一的体验张荣明:《中国古代气功与先秦哲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40243页。。确实,有关这些体验及其相应力量的记述都是神秘玄奥的,它们似乎也与我们的常识及近现代科学相悖,但我们至少可以通过它们来设想,就逻辑的可能性逻辑可能性的范围即所有不违背形式逻辑的范围。而言,我们究竟在多大的程度上可能与客观世界为一 ——这就好像万事万物都变得与盲人手中的拐杖一样!事实上,中文对此有一专名曰“感通”,王怀聿对其含义作出了精辟的概括:
“感通”一词所蕴涵的字面意义即“向对方开放自身,并使自身受到对方的影响”。在中国古代文本中,它常常在非常广泛的含义上使用,用以描述人与人之间或人与神、人与自然事物之间的各种交互作用与交流。Wang Huaiyu,“Ren and Gantong: Openness of Heart and the Root of Confucianism,” Philosophy East & West, 62(2012:4): 464.
王怀聿也指出,儒家的核心概念“仁”與“感通”有着密切的联系。的确,中文对于缺乏敏感性的一种常用表达即“不仁”。“程颢视‘仁’为宇宙内所有事物相融合的基础。因此,成仁就是向周遭世界开放自身,以便参与到世界的运动中并对其作出回应,就好像所有其他存在物和自身都作为一体在发生作用。”Wang Huaiyu, “Ren and Gantong: Openness of Heart and the Root of Confucianism,” 465.他援引牟宗三“仁以感通为性”一语,认为牟氏此言“揭示了程氏这一表述的核心意义”Wang Huaiyu, “Ren and Gantong: Openness of Heart and the Root of Confucianism,”464.。
这一吸收过程是相互渗透的。我们不仅让外在的东西进入到我们之中(犹如盲人的拐杖变成其身体的一部分),亦把我们自身——我们的主观性、价值以及目标——扩展到客观世界中去。
(四)学习楷模与权威
由于功夫之知不只是关乎“真理”,它更关乎“道”,因此学习功夫之知的主要方法不是靠接受言语所传达出来的信息,而是通过摹仿师傅或楷模。这种学习的一个特征,就是在遵循教导和楷模的时候不首先要求甚至永远也不要求要有知性的理解。诚如波兰尼所言:
通过示范学习就是投靠权威。你照师傅的样子做是因为你信任师傅的办事方式,尽管你无法详细分析和解释其效力出自何处。在师傅的示范下通过观察和模仿,徒弟在不知不觉中学会了那种技艺的规则,包括那些连师傅本人也不外显地知道的规则。一个人要想吸收这些隐含的规则,就只能那样毫无批判地降伏于另一个人进行模仿。一个社会要想把个人知识的资产保存下来就得屈从于传统。[英]迈克尔·波兰尼:《个人知识:迈向后批判哲学》,许泽民译,陈维政校,第7980页;Polanyi, Personal Knowledge, Towards a PostCritical Philosophy, 53。
在此,我们会发现与此相关的功夫大师与哲学教师之间的差异,这是一个尚未得到充分关注的有趣而重要的哲学问题。源自理智主义传统的师生关系是建立在这样的假设基础之上,即老师是来训练学生使用其已具备的理性的。其教导方式是使用语词或其他符号来呈现事实,通过言语的厘清及论证来诉诸学生的理性从而说服之。这种教育方式鼓励学生问“为什么?”并寻求其所学到的一切事物的理由或原因(除非它是对理性而言不证自明的)。从具备理性这一点上来说,学生与老师是平等的。
东方的主要哲学传统里的功夫师徒关系则肇始于另一种假设,即一个人的理性必须求助于开发了的直观和通过个人体验方可获得的了悟。学习功夫须先假定修行良好的师傅处在较高的位置,他能够发现未经培养的徒弟所无法察觉到的事物,同时师傅所察觉到的东西是无法单凭语词来传达给徒弟的。因此,徒弟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接受教育——不是主要靠言语陈述和说服的方式,而是通过摹仿典范,接受更多的作为徒弟应当遵循的个性化教导,并落实到相应的实践中去。有时,师傅甚至不允许徒弟问“为什么”,这是因为没有尝试去体验,言语的回答会容易误导学生,使他以为自己已经从语词中理解了答案。面对一位有修行的师傅,最好的立场就是做一名谦诚的学习者;最坏的立场则是自以为已经具备了认知所需要的全部条件,甚或是自以为已经知道了所有能够知道的东西,并且自信有能力去评判师傅。
这就自然而然会导致一连串艰难的问题出现,例如如何选择正确的师傅或模范来摹仿,哪一种教导或传统应当遵循等。如果你不知道师傅引你所走的方向是否正确就盲目跟从,这似乎与理性背道而驰,甚至是很危险的。要是你错选了导师怎么办?要是你接受的教导会使你误入歧途怎么办?驱动整个西方启蒙运动的那种精神,就是要摆脱对权威和传统的盲目信仰,并且只相信人的理性之光。康德著名的《什么是启蒙?》一文开门见山地表示,“启蒙就是人从他自己造成的不成熟状态中挣脱出来。所谓不成熟状态就是指如果没有别人的指引,他就不能应用他自己的悟性”[德]康德:《什么是启蒙?》,盛志德译,伯雅校译,《哲学译丛》1991年第4期。。德国作家戈特霍尔德·埃夫莱姆·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 17291781)亦提出,“如果上帝一手拿着真理,一手拿着寻找真理的能力,任凭选择一个的话,我将选择后者”。这种理性精神告诉我们只能接纳经由我们自身理性批判性评估后的东西。在当代后现代哲人吉亚尼·瓦蒂莫(Gianni Vattimo)那里,这种精神被演绎得淋漓尽致,以致于他声称,“共同体越大,帝国主义越多”引自瓦蒂莫在2006年5月31日在由俄罗斯社会科学院于莫斯科主办的“第二届比较哲学国际会议”上的发言。。对于他和与其志趣相投的西方思想者而言,理想的认知主体是理性的、自主的个体。
在此,我们立马发现我们已经陷入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困境:如果你无法辨识一位导师,或者你无法理解这位导师对你的教导,那么你就没有理由师从他;但如果你能辨识一位导师,并且理解他的教导为何是好的,那么这就意味着你已经知道了什么是好的,然而这种能力应该只能在你已经接受了导师的指引、践行了相关的艺术之后才能开发出来。
不过,这种两难困境不仅存在于功夫认知中,它也同样存在于柏拉图所谓的“研究悖论”(paradox of inquiry)之中——当你不知道你在寻求什么的时候,你如何发现某事物?如果你已经知道它是什么,那么你就无需发现它;但如果你不知道它是什么,你就无法开始你的研究,以至于即便你碰巧遇到了正確的解释,你也可能并不知道这就是正确的解释[古希腊]柏拉图:《柏拉图对话集》,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70171页。。
这对于功夫之知以及有关命题之知的传统认识论而言都是一个难题。我们大多数的信念都有赖于天生的轻信。在我们出生以后到明白什么是谎言和什么是欺骗之前那段时间里,我们不凭借任何证明、而是完全依赖于父母和老师的权威和证词,便接受了大量的信念。笛卡尔会认为这是十分不幸的。然而,正如托马斯·里德(Thomas Reid)所言,轻信是来自造物主的恩赐,否则我们将因为缺乏知识而消亡。
正如在他们(孩子们)能够自食其力之前需要去喂养他们一样,在他们能够根据自身的判断去发现诸多事物之前,必须要让他们接受各种指教。Thomas Reid, Complete Works of Thomas Reid (Two Volumes), ed.by Sir William Hamilton (Edinburgh: Maclachlan and Stewart, 1846), 450.
的确,如果没有轻信,我们甚至就无法和任何人说话,因为言语交流是建立在这样一种信念的基础之上,即对方一定是像我们一样地在使用他们的语词。如果我坚持要找出决定性的证据来证明对方是在与我一样的意义上使用语词,甚至在我和她打招呼之前就先证明她通常不会说谎,那么我怎么可能和她交流呢?
不要以为如果我们防范那些不确定的信念,我们就能成为毫无偏见的独立思想者。事实并非如此。一个人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这种或那种力量的影响,并以某种方式形成这个人的生活态度。这些影响会封锁一些认知的可能性,它们有好有坏。诚如威廉·詹姆斯所正确地指出的那样,对于那些“活的”(live)、“不可避免的”(forced)和“重大的”(momentous)问题,选择不去相信,并不是把自己从犯错误的可能性中拯救出来,而是剥夺了自己正确的可能性大致上说,“一个有生命力的假设,作为一种真实的可能性,对于面对这个假设的人有吸引力”,“它们受思想者行动意愿的检验”([美]詹姆斯著,万俊人、陈亚军编:《詹姆斯文选》,万俊人、陈亚军等译,第438页)。“强制性的”选择是不可避免的,而“重大的”选择是唯一的、举足轻重的和不可逆的。参见James, The Will to Believe and Other Essays in Popular Philosophy, 3。。看来,轻信不仅是不可避免的,它甚至是“知”的必要条件。这就把我们带回到了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即在传统中国,孩子们总是在能够理解经典之前就被教导要背诵经典,正如一名孩子在学弹钢琴的时候,被要求无条件地遵循老师的指导一样。对老师的言辞产生质疑或提出挑战并非是一个选择信念的行为,而是阻碍一个人的成长道路的行为。
在真理认知的认识论领域中,这就意味着走入了绝境。现代认识论和科学哲学的发展都指向了这样一个结论,即不可能有绝对客观的真理,因为没有人能拥有不带任何视角的观点!然而,在功夫认识论中则不同。正如我们先前所讨论的,衡量功夫之知的显著标准,就是其有效性、适宜性以及审美性。其中没有一种标准要求我们超越主观性从而走向物自体或自在之物(dingansich/things in themselves)的领域。这些标准都与人类体验息息相关,而这些标准瞄准的价值也恰恰处于人类体验当中。
楷模学习的另一个困难之处,在于如何既摹仿却又不机械复制楷模孟旦把这种“机械复制”称作“问题解决模型”(problem solving models),不同于“品格楷模模型”(character models)。前者是不顾条件变化地机械复制同一种方法,后者才是楷模学习的适当方法。参见Donald J. Munro, A Chinese Ethics for the New Century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5), 3537。。恰当理解和实践下的模仿应该远非是纯粹的复制。这里的关键在于把摹仿同重复和单纯的形式相似区别开来。摹仿应当理解为获得能力、艺术或功夫的一种过程。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坚持认为摹仿并不是“重复”;相反,摹仿是“跟着做:跟从而来的制作。摹仿在本质上就在于距离,并且就是通过距离来定义的”[德]马丁·海德格尔:《尼采》上卷,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205页;英译本Martin Heidegger, Nietzsche, Vol. 1 (Pfullingen: Neste,1961), 215。译案:引文根据英译本有所改动。。德里达也发现,“真正的摹仿[存在于]两个生产的主体之间,而非两个被生产物之间”Jacques Derrida, “Economimesis,”Mimesisdes articulations(Paris: Flammarion,1975), 67ff.。实际上,摹仿是人获得创造能力的过程本身——这里所说的“创造性”并不是指完全无中生有地制造出某种新东西,而是指把自身的创造力建立在模范的优秀性这一根据之上。例如,在中国武术和书法中,摹仿大师总是作为一项基本功被加以强调,这是因为多半情况下一个全然没有根底的人的创造是毫无价值的,甚至更糟糕的是会成为这个人获得发展其真实创造力机会的障碍。正如任何一种教导都可以被机械地或适当地采用一样,对典范的摹仿本身就是一门艺术。不过必须谨慎、注意的是,在摹仿楷模的时候必须要对文化、历史及其他特定的具体条件,以及某些特定典范所具有的局限性进行反思并保持对它们的敏感度Munro, A Chinese Ethics for the New Century, 3537.。这种危险并不比缺乏适当指导所导致的危险系数小,而且人们在内化了不良影响之后,便会失去成为君子和过上美好生活的自由。
四、结 语
行文至此,笔者希望已经清楚地说明了对认识论进行系统延伸的必要性,以便使其能够把各种被笔者统称为“功夫认知”的那些认知模式(或者借用孟旦的术语“特征簇”[cluster of feature])包括进来。“功夫认知”是依据其有效性和美学价值,而非依据真理价值来加以判断的(虽然真理价值可以作为影响有效性的一种因素)。它虽然与技能之知接近,但却比技能之知更丰富。功夫之知的内容超出了可以用命题表达出来的知识内容。虽然它不能没有命题之知,但却不能归约为命题之知。功夫之知必须体身化,并且必须成为超越对规则或程式加以机械应用的实现能力。认知远比真理认知丰富得多,它甚至包括在实践生活中认识到真理的局限和信念的力量。
功夫认识论要求我们对一些常见的假设提出挑战,例如认为清晰性和逻辑一致性具有绝对的价值。它提醒我们注意语言的行为功能和功夫体系的独特之处。功夫认知更多地要求认知主体的培养与转化,因而它除了认知方面的意义,还具有本体论的意义。获得功夫之知的过程更多地是一种训练而非资料的收集,它更多地涉及到对典范的摹仿。
功夫认识论虽然最初是作为真理认知认识论的补充被提出来的,但它亦可以囊括真理认知。与传统的真理认知认识论忽视了大量的认知领域不同,功夫认识论并不忽视真理认知的合法性。相反,通过承认真理认知与其他认知模式的不可分性,功夫认识论可以说是对真理认知的一大推进。
同实用主义的真理观一样,功夫认识论着眼于信念和思维方式的实践价值。但是,它又不像那种粗糙实用主义的真理观,把真理只视作能产生效果或有利的东西。功夫认识论并不改变我们通常的真理观念——即准确描述实在的陈述。它不否定获得真理的可能性,虽然它并不依赖于对这样一种可能性的认可。它提出了一套不同的问题,诸如一个相关的信念(无论它是真或是伪)是否有助于产生积极的影响或是否有益于生活——而恰恰因此,这种功夫认识论会充分认识到真理对于实现美好人生的重要性及其局限性。功夫认识论亦不同于粗糙版的实用主义认识论,后者把认知主体简单地当作天生给定之物。相反,它把对认知主体的培养置于中心地位。实用主义(pragmatism)这一名词源自希腊文(pragma),意即“行为”或“行动”,它更易于让人关注行为举动及其结果,而不易引人关注到行为的主体。在缺乏“功夫”观念的情况下,实用主义者在谈到实践意义的时候总是容易陷入粗糙的有效性中去,却很难意识到培养主体的必要性。甚至连特别强调教育哲学的约翰·杜威(John Dewey)都称其哲学为“工具主义”(instrumentalism)。工具通常被理解为外在于主体并且只被主体所利用的外在实用手段。一个把“行动”(pragma)和“工具”作为其自我身份认同的关键词的理论,从一开始就把它自身放在一个不利于探讨自我转化这一主题的位置上。此外,与容易被误解为追求有用性的粗糙实用主义不同,功夫视角本身就包含了它所固有的艺术的视角。这种起点上的细微差异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后续影响。例如,功夫认识论很容易产生对“生活风格”(style of life)的重要性的认識,而这一点甚至通常都不会出现在一个实用主义者的词汇中。
同德性认识论一样,功夫视角把认知评价的关注焦点从真伪上转移开来,并更加专注认知德性。然而,当涉及解释为何认知德性有价值时,它们的意见就不同了。德性认识论学者要么退回到真理领域,如“可靠主义者”(reliabilists)认为认知德性的价值在于它们有利于导致真理,“责任主义者”(responsibilists)认为它们的价值在于能使认知主体为获得真理而肩负起道德责任;要么简单地拒绝这个问题,主张认知德性是具有内在价值的,因为这些德性本身就是构成一个良好的理智生活的内容。就这一点而言,功夫视角对德性的看法与亚里士多德看待德性的观点一致——它们有利于实现生命之善,但它们并非生命之善本身。然而,功夫的视角却又不同于亚氏,它并不依赖于目的论的形上学来定义什么是生命之善。它也没有为人类生活设定一个前定的“普遍的善”的观念,而是相反着眼于具体效用——善于做某事(good at)、擅长某方面(good in)、宜于行某事(good to)、对某人或某事有好处(good for),以及善于对待某类对象(good with)。功夫视角承认不确定性,因而对不同的卓越性保持开放态度。就像在对待艺术的时候我们不能说好的艺术形式或风格只有一种一样,功夫亦允许善和创造性的无限可能性。但这却并不同于简单地否认善的标准;相反,它使“善”植根于具体的、可以被感知到的人类体验之中。同德性认识论一样,功夫认识论亦承认需要培养我们对善的鉴赏力。虽然衡量“某人知道如何跳好舞”的标准可能并不像衡量“某人知道桌子上有本书”的标准那样清晰而且“客观”,但基于一个高度发达的善的鉴赏力的标准,我们可以合理地断言某些善的观念意识属于低级趣味,而其他的则好一些。但美德或善的鉴赏力终究是要靠人类体验来衡量的。
[责任编辑 邹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