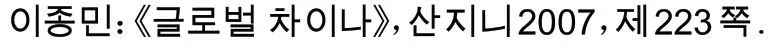金仁淑短篇小说《大海与蝴蝶》中的中国及中国人形象探析
范淑杰 周磊[曲阜师范大学,山东 日照 276826]
金仁淑(1963—)是韩国当代著名女作家,1983年以短篇小说《丧失的季节》入选《朝鲜日报》新春文艺,从此登上文坛。迄今为止,她发表了多部长短篇小说和散文,曾获韩国李箱文学奖、东仁文学奖、现代文学奖等多项文学奖项。金仁淑旅居中国大连(2002—2004)和北京(2006—2007)期间创作出了以中国为背景的《大海与蝴蝶》《监狱的院子》和《走在帝国的后街》等三部优秀文学作品。其中《大海与蝴蝶》是她作为一名陪读妈妈旅居中国大连时期,以自己的生活经历为基础创作的一部短篇小说,并于2003年摘得了韩国文坛最有影响力、最权威的纯文学奖项第27届韩国李箱文学奖桂冠,在韩国引起了极大反响。小说采取了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讲述了一位因婚姻生活失败而带着儿子到中国留学的韩国中年女性,在中国认识了一位即将嫁入韩国的朝鲜族姑娘而经历的一系列故事,涉及国家、民族、社会、婚姻、家庭等各种复杂关系,并深刻地探讨了现代人的孤独、痛苦、生存感丧失及生存的价值等社会问题。金仁淑作为韩国主流女作家,在当代韩国文坛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小说《大海与蝴蝶》是以21世纪初的当代中国为背景展开的,描写了大量有关中国的内容。本文通过对其解读和分析,可以深入地了解韩国人如何认知当代中国、中国社会及中国人。金仁淑是韩国很有影响力的作家,因此这部作品对中国的描述,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到韩国读者对当代中国的印象,从而对未来中韩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与交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小说中的中国形象
法国形象学家巴柔指出:“所有形象都源于一种自我意识,它是对一个与他者相比的我,一个与彼处相比的此在的意识。事实上,形象是对一种文化现实的描述,通过这一描述,制作了它的个人或群体揭示出和说明了他们置身于其间的文化的和意识形态的空间。”也就是说,他者形象的塑造源于形象塑造者对自我身份的建构。从与他者的对比中发现自我,并认同自我身份,反映了形象塑造者所代表的社会或群体对他者的一种集体想象。金仁淑通过《大海与蝴蝶》所塑造的中国形象,不仅揭示了其对中国的认知和看法,而且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自身所处的韩国社会和文化的状况。
(一)从陌生、疏离到熟悉、亲切的“他者”形象
中韩两国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对立和隔阂,使得“我”(女主人公)初到中国时,强烈地感受到异域文化所带来的陌生感和疏离感。首先,在小说的开头部分,“陌生”一词重复出现了十次之多,例如“陌生的异国语言”“陌生的国家”“陌生城市的宾馆”“陌生的食物”“陌生的味道”“陌生的所有一切”“陌生的东西”等。这些词汇的频繁使用,如实地描述了一个外国人初到异国他乡的真实感受,令读者有身处异域之感。其次,对中国人文化和生活习惯的描写也带有强烈的异域色彩,使读者更能直观地感受异国风情,比如红砖房密布的村庄、倒贴着中国式福字的窗户、挂着中国结的墙等。因此,如果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与其他的国家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是语言、习惯、饮食、文化等不同于“自我”的他者而已。
但是,小说中“我”对于中国的认知,显然并没有仅仅停留在“陌生和疏离”上,与陌生感相伴而来的是一种莫名的“熟悉感”,甚至是一种亲切感。“我”因为嫌租住的房子里没有一点生机,从花店买回来一盆在韩国从来没有见过的“金枝玉叶”花,注视着花叶,莫名地产生了一种“从陌生中而来的熟悉感”。随后,在“我”跟随即将嫁往韩国的朝鲜族姑娘李彩琴走进一家麦当劳时,这种熟悉感再次被触发。“除了语言不同,和韩国没有什么区别的麦当劳……熟悉的汉堡味道和炸薯条的味道驱散了在中国的大街上闻到的陌生食物的味道。”
而当“我”去彩琴的父亲所生活的朝鲜族村子里做客时,这种熟悉感则升级为“亲切”。“当感觉到温暖的火炕那一瞬间,啊,我们是同一血脉的想法便涌上心头。”从陌生的“金枝玉叶”花到熟悉的西式快餐,再到十分亲切的朝鲜火炕,金仁淑笔下敏感而细腻的女主人公对中国这个“他者”的感情,很自然地由陌生疏离过渡为熟悉亲切,一步步升级。作者将纤细的心理描写和高超的小说技巧高度融合,其独具匠心的安排也由此窥见一斑。
(二)从“禁忌的极端国家”转变为“培养世界人”的开放国家
小说中女主人公对于亲朋们的“为什么一定要去中国”的疑问,高调地回答:“21世纪是中国的时代,想把孩子培养成世界人。”其实,她是为了逃离因失去进取心而日益无法沟通的丈夫,摆脱窒息的家庭生活。可是,当丈夫也提出同样的疑问时,她不由得想起了他们那青春洋溢的大学时期。“我们只有凭借暗号才能进入密室学习中国革命史,那时,对我们来说,中国既是一个极端的国家,也是一个被禁止的理想。”这句话是冷战时期韩国知识青年对中国认识的真实写照,是当时韩国社会生活的反映。
“我看他者,但他者的形象也传递了我自己的某个形象”,一国文学中的异国形象在言说“他者”的同时,也在言说着“自我”。这里作家对“他者”——中国进行描述的同时,也反映了“自我”存在的社会现实,在本质上是当时韩国自我形象的映照,揭示并表明了作者自身所处的文化、社会、意识形态空间。
20世纪80年代,作家金仁淑正在韩国延世大学新闻广播系学习,作为民众文化联合下的组织成员,她曾经亲自参加过社会运动,对社会运动有着深刻的体会。因此,小说中这段关于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书写,可以说是如实地反映了当时以金仁淑为代表的韩国知识青年渴求了解中国的迫切心理。
韩国学者许世玉指出,“20世纪80年代,韩国年轻人开始摆脱对中国的偏见或教条,出现了通过文学作品来了解中国的一种倾向”。这一时期,在国内民众文学的推动下,韩国知识青年对作为红色革命象征的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掀起了一股阅读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热潮。韩国大学生秘密结社学习中国革命史的场景正是发生在这种背景下。究其原因,“中国现代小说所反映出的,与我们感情基调相似、有着儒教传统的社会通过革命,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形象,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事实上,在这一时期,不仅小说中所提到的有关中国革命史的书籍,而且包括《毛泽东诗词》《青春之歌》《林海雪原》《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反映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精神的红色文学作品也被译介到韩国,可以作为这一现象的有力佐证。总之,由于受冷战意识形态的支配,此时的中国既是韩国官方禁忌的对象,又是民众个体渴求了解的对象。
随着冷战结束,中韩建交,两国进入友好发展的新时期。对于韩国人来说,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不再是“极端的国家”和“被禁止的理想”,而是一个与韩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密切交往和合作的国家,越来越多的韩国人来到中国学习和工作。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令世人瞩目。与留学欧美费用高昂相比,留学中国相对物美价廉,受到了韩国中产阶级家庭的青睐,因此,韩国掀起了一股中小学生来华早期留学的热潮。现实生活中,作家金仁淑2002年陪着身为中学生的女儿来到中国大连学习。尽管小说中女主人公的朋友们背后都说“去美国或加拿大留学费用太高,所以才去中国的嘛”,但不可否认的是,冷战时期曾被韩国视为“极端和禁忌”的中国,早已悄然完成华丽的转型,变成了韩国中产阶层心目中“培养世界人”的开放国家,也成为许多韩国青少年们追逐梦想的舞台。
(三)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转型的中国
小说通过对中国朝鲜族村庄与城市的刻画,展现出一个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中国形象。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来华旅游、学习或工作的韩国人越来越多,一些城市出现了韩人街或韩人社区,而韩国商店和韩式餐馆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中国的大街小巷。韩人街的出现,充分体现了我们对外来文化的包容性,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城市的现代化生活对外国人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小说中,为外国人提供各种服务的相关机构极高的办事效率令女主人公印象十分深刻:“就像韩国留学机构为我打听孩子的中国学校时所承诺的一样,也如在这里见到的向导所承诺的,房子在四天内就找到了,孩子在两天后就入学了……又过了两天,孩子就住进了学校宿舍。”由于韩国人标榜自己做事效率高,崇尚所谓的“快”文化,中韩建交初期,韩国媒体曾经大肆宣扬中国人的“慢”文化,将其视为中国文化的特征,导致韩国人形成了一种刻板的“中国人做事效率低”的负面印象。但小说中所描述的21世纪中国,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高度的开放性、现代化和国际化,生活节奏大大加快,原来的慢文化已经得到了很大改观。当走进与韩国几乎没有差别的麦当劳后,女主人公禁不住发出了“方便、快捷、包装的幻想……麦当劳也存在于中国的大街上”的感叹,认识到了中国已经加入全球经济一体化中的事实。
但朝鲜族姑娘李彩琴和她的父亲所生活的1500户朝鲜族聚居的村庄,则被描绘成一个在现代化浪潮冲击下落后而平和的乡村。当“我”坐着公共汽车,去位于城郊的朝鲜族村庄的时候,“从市中心到城市郊区,开发的景致以十年为单位逐渐落后。公共汽车每经过一站,中间就仿佛隔了十年的岁月。高耸的大厦和宽阔的公路消失了,然后开始看见一些陈旧的房屋,这时候出现了一个与韩人街不同的朝鲜族村的牌子”。公共汽车一站的距离大致介于500至1500米之间,短短千米左右的距离,却给人相隔十年的感觉,城乡基础设施的巨大差距顿时令人产生了巨大的心理落差。从市中心到城郊,从喧嚣到平静,从繁华到落后,从高楼大厦到陈旧房屋,金仁淑敏锐地捕捉到了城市化进程所造成的城乡差异。“村庄里浸染了红色的金黄色田野让人为之倾倒,田野无边无际。大概秋收时节就要到了,每隔一巴掌远的地方就堆放了一堆稻谷……农夫的身后,稻草像童话中的风景,整齐地堆积着。”小说中对朝鲜族村庄里金黄色田野和童话般稻草的描写,则呈现出了一派中国秋收时节温馨而祥和的乡村气象,流露出一丝丝温情,很容易令人产生情感上的共鸣。
二、小说中的中国人形象
《大海与蝴蝶》是以21世纪的中国为背景的,文中自然出现了许多中国人。由于语言文化的同源性,韩国人初到中国,接触最多的便是朝鲜族,在小说中登场的主要有朝鲜族姑娘李彩琴及她的父母、朝鲜族汉语家庭教师等。从作者对于这些人物的描写,我们可以深刻地感知韩国人对中国人,特别是中国朝鲜族的看法。
首先,以李彩琴和家庭教师为代表的中国朝鲜族年轻女性,都以去韩国为梦想,甚至为了达到目的,选择与韩国大龄男性结婚这条捷径。至于她们梦想去韩国的原因,作者借女家庭教师之口,一针见血地道出了答案:“想去韩国的人只相信钱,我不知道我父亲和祖父他们怎么想,但他们已经老了,年轻人相信的是钱。”这段精辟犀利的话,是作家金仁淑对现代社会拜金主义倾向的尖锐批判。对经济利益的过分追逐,不仅改变了个人的价值观,甚至对传统家庭婚姻观都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小说中二十五岁的朝鲜族姑娘李彩琴在非法滞留韩国的母亲的安排下,与一个四十多岁的韩国蔬菜供货员仅见了两次面,就仓促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其速度之快令人瞠目结舌。之所以这样草率地安排女儿的婚事,是因为李母有着“只要女儿一取得韩国国籍,就立刻离婚的打算”。因此,这种“闪电式”的跨国婚姻从一开始就不是建立在牢固的感情基础之上,而是具有极强的目的性和功利性,为以后的婚姻生活埋下极大的隐患。
以这种跨国婚姻方式去往韩国的朝鲜族女性,进入韩国社会之后又会如何呢?对此,小说中也略有涉及。“以这种方式嫁到韩国的朝鲜族女人们,会在某一天抛下自己亲生的孩子,只带一张居民身份证逃跑,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有一段时间里,这种事经常可以在报纸或电视新闻中看到。”正是结婚目的的不纯粹,导致了这种家庭悲剧的发生,给韩国社会带来很大的不稳定因素,使韩国社会对朝鲜族女性的印象大打折扣,嫁到韩国的朝鲜族女性也因此备受非议和指责。
作家金仁淑倾向于对其笔下的女性人物充满人文主义关怀和人道主义同情,因此,在小说中谈到个别朝鲜族女性抛夫弃子离家出走的现象时,她并没有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妄加评议,而是从关怀女性的视角出发,对其产生的深层次社会原因进行了剖析,给我们指出了在韩朝鲜族女性离家出走事件背后不为人关注的一些因素:“一个朝鲜族女人在决定离开、半夜逃走之前,他们夫妻之间发生过什么……男人毒打过女人几次……女人因为朝鲜族身份受到过怎样的侮辱……女人无法忍受的是侮辱,是愤怒,还是思念?……消失的不仅仅是女人的身份证,还有事情的原委。”金仁淑借女主人公的寥寥数语,深刻分析了以跨国婚姻方式进入韩国社会的中国朝鲜族女性,由于两国社会文化的差异,在韩国可能遭受着来自家庭和社会的歧视所导致的双重痛苦,明确表达了自己对女性的关怀和人道主义同情的立场。这段内容也暗含了作者对即将入韩的李彩琴命运的深深担忧。正如“对于她那不娴熟的韩语发音,我并不想特意纠正,毕竟她以后要面对的不仅仅是语言问题,还有很多比语言更深层的东西”所揭示的那样,除了语言沟通障碍外,嫁入韩国的中国朝鲜族女性在生活文化习俗、价值观等许多方面将会经历各种冲突和矛盾。
其次,以李彩琴的母亲为代表的朝鲜族中年女性,以访问就业签证实现去韩国的梦想,后来却成为非法滞留者,只能暗地从事低报酬、重强度的社会底层工作。小说中,在女主人公母亲经营的饭店里打黑工的李母,六年前以给儿子挣大学学费为由,来韩国打工,即使在遭遇因交通事故导致丈夫失去一条腿和儿子死亡的重大家庭变故时,都没有回国。她似乎是一位“极其狠毒”的中年女性,为了让女儿获得韩国国籍,甚至不惜牺牲女儿的婚姻幸福。对此,作者通过女主人公的母亲对李母进行了质疑和批判:“韩国有什么好的,至于让她把女儿卖到这里来?”李母这种无视亲情、急功近利的做法,究其原因还是过度追求物质利益的缘故。金仁淑通过对李母负面形象的刻画,犀利地批判了现代人对物欲的偏执追求,已经对个人的价值观及传统的家庭婚恋观造成严重的冲击,人性被扭曲,亲情在金钱和物质利益面前不堪一击。
再次,以李彩琴的父亲为代表留守国内的朝鲜族中年男性,是在经历妻离子亡等变故后,家庭分崩离析的一位悲剧性人物。李父可谓命运坎坷,幼年时期由于目睹了死刑犯被枪决的场面,心理受到巨大冲击,导致左眼失明,而且这种痛苦的记忆伴随其终生。本来幸福美满的四口之家,随着妻子滞留韩国,儿子遭遇交通事故身亡,自己失去一条腿,最后连唯一的女儿也要嫁去韩国,而彻底瓦解。借用李母的话,李父“以一个死人的魂魄活着”,过着行尸走肉般的生活。可以说,李父作为丈夫、父亲及一家之长的存在感几乎完全丧失,是一个以别人的灵魂活着的、为生活重压之下极度孤独和疲惫的中年男性的缩影。
当然,小说中除了朝鲜族,也出现了一些非朝鲜族的中国人,如精明的花店老板和神秘的文身店老板。初到中国的“我”去小区花店里买花时,一直在“我”身旁悄悄注视着“我”的花店主人,与“我”对视的同时,拍着手大声喊道:“十块钱!”寥寥几笔,一个精明、市侩的小商贩形象便生动而鲜活地跃然纸上,这种小商贩形象跨越了国界,弱化了异域文化所带来的陌生感和隔阂,令人产生了亲近感。女主人公来到中国后,经常会碰到与丈夫身形相仿的男人,她总是下意识地去追寻。有一次,她无意中闯入一家文身店,“文身店老板是一位穿着中国传统服装的老人,坐在一张红色的圆桌后面……老人背后的墙上挂着各种文身用的画,有龙和老虎,还有像红色符咒的蝴蝶”。小说对于文身店老板的穿着及文身店内部的描述充满了神秘色彩,具有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氛围,传递了作者对异质文化别样的感受。
总的来说,比起对中国朝鲜族的细腻描写,金仁淑对非朝鲜族的中国人的刻画比较肤浅与单薄。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由于作者初到中国,受到生活环境和语言障碍等各种因素的制约,主要接触的是中国的朝鲜族人,与非朝鲜族的中国人接触不多,因此在塑造中国人形象方面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主要集中于朝鲜族人物的刻画,没能塑造出中国人完整、系统、直观的整体形象。
三、结语
以21世纪初的当代中国为背景,金仁淑在《大海与蝴蝶》这部短篇小说中塑造了大量的中国及中国人形象,通过这些形象委婉地表达了自己对中国及中国人的认识和看法。由上所述,她所描绘的中国形象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对中国社会生活的了解而一步步深入的。最初,她感知中国是一个陌生与熟悉的“他者”;随着在中国生活的深入,她切身体会到中国已经从一个“禁忌的极端国家”转变为“培养世界人”的开放国家;最后,她还敏锐地认识到,全球经济一体化浪潮中的中国,从传统社会转型为现代社会所带来的城乡巨大差距的深层次问题。在塑造中国人形象方面,虽然由于客观条件的制约,她没能塑造出中国人完整、系统、直观的整体形象,但是小说还是很成功地刻画了中韩两国民间交流频繁的背景下,以朝鲜族为代表的中国人形象,深刻揭示了过度的物质、欲望追求对现代人人性的扭曲和传统家庭生活的冲击。
①③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1页,第12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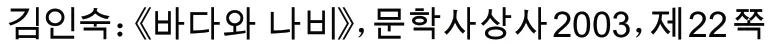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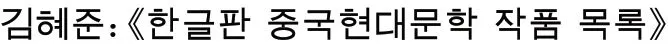
⑦据韩国教育开发院“2002-2003学年初中高留学生出国现况”资料的统计,2002年和2003年韩国早期留学者(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分别为10132和10498人,其中来华的人数仅次于美国和东南亚,位居第三,并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