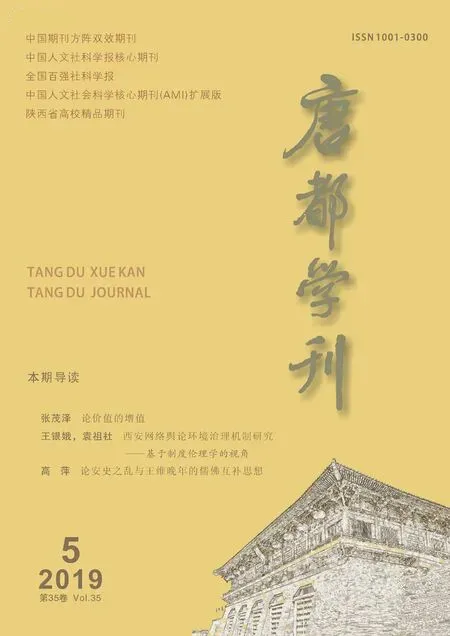家富隋珠 人怀荆玉
——论唐代类书编纂的特点与价值
刘全波
(兰州大学 敦煌学研究所,兰州 730020)
类书是古籍中辑录各种门类或某一门类的资料,按照一定的方法加以编排,以便于寻检、征引的一种知识性的资料汇编[1]。一千多年来,类书作为典籍之荟萃、知识之精华,对文献保存、知识传播和学术研究都产生了重要作用。唐代是类书发展的高潮期,虽然多数典籍没有流传下来,但是,唐代的类书编纂却是繁荣异常的。胡道静《中国古代的类书》言:“唐代自开国到玄宗时代,除了中宗、睿宗两个很短的朝代外,累朝都用封建国家的力量编纂了一些大规模的类书。”[2]贾晋华《隋唐五代类书与诗歌》言:“笔者撰有《隋唐五代类书考》,检得隋唐五代公私所修类书共69部8 477卷。如果考虑到遗佚未经著录者,实际数目可能还要大得多。”[3]由贾晋华先生的统计可见唐代类书之多,其实这个统计也是不完全的,敦煌类书肯定没有统计在内,域外汉籍中的唐代类书也没有统计在内,受唐朝影响依据唐代类书编纂的日本类书《秘府略》等恐怕也没有统计在内,总之,唐代类书的繁荣是超出我们的想象的。
为了展现唐代类书编纂的盛况,我们再次不厌其烦地将《新唐书》所收诸类书做一个集中展示,这是反映唐代类书编纂之盛况的最基本材料。《新唐书》卷59《艺文三》子部“类书类”载:
《文思博要》一千二百卷。《目》十二卷。右仆射高士廉、左仆射房玄龄、特进魏徵、中书令杨师道、兼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颜相时、国子司业朱子奢、博士刘伯庄、太学博士马嘉运、给事中许敬宗、司文郎中崔行功、太常博士吕才、秘书丞李淳风、起居郎褚遂良、晋王友姚思廉、太子舍人司马宅相等奉诏撰,贞观十五年上。
许敬宗《瑶山玉彩》五百卷。孝敬皇帝令太子少师许敬宗、司议郎孟利贞、崇贤馆学士郭瑜,顾胤、右史董思恭等撰。
《累璧》四百卷。又《目录》四卷。许敬宗等撰,龙朔元年上。
《东殿新书》二百卷。许敬宗、李义府奉诏于武德内殿修撰。其书自《史记》至《晋书》,删其繁辞。龙朔元年上,高宗制序。
欧阳询《艺文类聚》一百卷。令狐德棻、袁朗、赵弘智等同修。
虞世南《北堂书钞》一百七十三卷。
张大素《策府》五百八十二卷。
武后《玄览》一百卷。
《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目》十三卷。张昌宗、李峤、崔湜、阎朝隐、徐彦伯、张说、沈佺期、宋之问、富嘉谟、乔侃、员半千、薛曜等撰。开成初改为《海内珠英》,武后所改字并复旧。
孟利贞《碧玉芳林》四百五十卷。
《玉藻琼林》一百卷。
王义方《笔海》十卷。
《玄宗事类》一百三十卷。
又《初学记》三十卷。张说类集要事以教诸王,徐坚、韦述、余钦、施敬本、张烜、李锐、孙季良等分撰。
陆贽《备举文言》二十卷。
刘绮《庄集类》一百卷。
高丘《词集类略》三十卷。
陆羽《警年》十卷。
张仲素《词圃》十卷。字绘之,元和翰林学士、中书舍人。
《元氏类集》三百卷。元稹。
《白氏经史事类》三十卷。白居易。一名《六贴》。
《王氏千门》四十卷。王洛宾。
于立政《类林》十卷。
郭道规《事鉴》五十卷。
马幼昌《穿杨集》四卷。判目。
盛均《十三家贴》。均,字之材,泉州南安人,终昭州刺史。以《白氏六帖》未备而广之,卷亡。
窦蒙《青囊书》十卷。国子司业。
韦稔《瀛类》十卷。
《应用类对》十卷。
高测《韵对》十卷。
温庭筠《学海》三十卷。
王博古《修文海》十七卷。
李途《记室新书》三十卷。
孙翰《锦绣谷》五卷。
张楚金《翰苑》七卷。
皮氏《鹿门家钞》九十卷。皮日休,字袭美,咸通太常博士。
刘扬名《戚苑纂要》十卷。
《戚苑英华》十卷。袁说重修。[4]1562-1564
《新唐书》卷59《艺文三》子部“类书类”所载诸类书共有39部,其中《北堂书钞》应属于隋朝类书,暂且不论,亦有38部之多。试看诸类书之卷帙,总数可达五千多卷,就算《三教珠英》与《文思博要》之间有因袭关系,去掉1 200卷,总数亦有四千余卷,这个数量是巨大的,尤其是在印刷术尚未普及的中古时代。对唐代类书做总体评价,前辈学者已有高论。贾晋华《隋唐五代类书与诗歌》言:“类书在隋唐五代达到高度繁荣,其标志有三:一是数量剧增,公私并举;二是独立成类,蔚为大国;三是体例严密,种类多样。”[3]“从隋炀帝至至唐玄宗开元中,官修类书大量涌现,皇帝、太子、诸王都争先恐后地组织第一流的学者文士编纂类书。开元后,官修类书热潮歇息下来,但私人撰述之风,却自隋至五代,一直持续不衰。”[3]潘冬梅《中晚唐类书研究》亦言:“(一)官修类书渐趋停歇,私修类书迅速发展。(二)中晚唐类书编撰体制多样化。(三)分类体系、类目的设置与排列不如唐初、宋初完善,内容多不完整。(四)编撰的目的由供君主皇室参考向针对科举及民间日用转变。”[5]唐光荣《唐代类书与文学》言:“唐代类书的撰述体式归纳起来一共有九种:书钞体、志人小说体、碎语体、骈语体、对语体、四言对句体、诗体、赋体、问答体。后世类书的所有撰述体式在唐代差不多都可以找到。”[6]115“从部类结构上看,唐代类书虽不如后世类书精密,但已经相当完整、成熟。从撰述体式上看,唐代类书也已经很丰富、全面。很明显,类书编纂发展到唐代已经有很高的水平。”[6]135其实,在诸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对整个唐代类书的编纂情况做一个分析评价还是有些难度的,因为我们所能见到的类书文本是比较少的,故我们只能从目前所知、所见的类书出发,做一些浅显的推断。
第一,一个时间上的认知与判断,这个分界线以安史之乱为界。唐代前期类书编纂的主体是政府,并且此时期多编纂大型类书,而安史之乱之后,唐代类书的编纂开始出现新情况,政府不再主持类书编纂,或者说,官方主导的类书编纂越来越少,而民间私修、私纂类书兴旺发达起来。《唐代官修史籍考》言:“唐代初年历史写作的规范性制度化导致了历史修撰的日益专业化,促使史家努力专注于撰写富有教育意义的历史:不仅在其最广泛的意义上,历史当体现出往昔所应提供给全体士人的道德伦理教训;而且在一个更狭隘的意义上,为那些参与治国的人士提供大量丰富的先例与榜样。”[7]73“在初唐时期,知识的合理化组织与分门别类曾风行一时……他还体现在初唐时期编纂的各式各样的‘百科全书’中,这些书籍在720年的秘书省藏书目录中被归为‘类事’,即‘分类事项’。列入书目的这类书籍不下22种,这类作品中有两种最早的作品流传至今,其一是虞世南主持编纂、完成于隋朝《北堂书钞》160卷,另一种是欧阳询主持编纂、于624年呈于朝廷的《艺文类聚》100卷。第三种流传至今的同类书籍是30卷的《初学记》,由徐坚及其同僚编于集贤院,于727年进呈朝廷。”[7]73-74由此可见,唐代类书编纂的前期与后期之不同是显而易见的,前期与后期的特点也是显而易见的,这是唐代类书编纂的第一个特点,前辈学者亦是已经关注到了这个问题。《唐代前期学术文化研究》言:“唐代前期的类书编纂基本上都由帝王直接发起,因而普遍具有编纂规模大,规格高的特点。在编纂过程中往往汇集了大量饱学之士,这些人一则官居要职,如高士廉、房玄龄、魏徵等都是贞观重臣;学识深广,如令狐德棻、姚思廉、马嘉运、徐坚、张说等都是名重一时的学者鸿儒。这些类书编纂,直接服务于皇室的需要。其主要目标,一是扩充皇家藏书,加强文化建设,完善藏书;二是以史为鉴、施政治国;三是满足皇室文化娱乐的需求,《艺文类聚》等是以辑录诗文词赋为主,直接服务于取事为文的需要;四是促进皇室教育,如《初学记》就是专为诸王皇子的教育和学习而编制。”[8]《中晚唐类书研究》言:“和官修类书的求全求备不同,私人编撰的类书更带有主观性和随意性,可以反映当时知识的定型化和简化,其对知识的分类和介绍,可以透视当时社会一般知识程度。”[5]15总之,唐代前期,修类书与修史一样,在规范性的制度之下,编纂了大量的各式类书,卷帙浩繁,内容多样,而到了后期,私人编纂类书异军突起,并且由于私人编纂类书更有主观性和随意性,于是各式各样且具有鲜明个性的类书大量出现,但是,也不能说唐代前期没有私人编纂类书,只是由于官修类书的光芒太过耀眼,将私纂类书的光芒遮挡了起来。
第二,类书编纂与史书修撰多同时进行,类书编纂者既是史书修撰人员,又是身居要职、官高位尊的宰相名臣,这可见类书编纂之地位,亦可见当时帝王将相对类书编纂等文化事业的重视。杜希德著、黄宝华译《唐代官修史籍考》言:“这些书籍并非我们现代意义上的百科全书。他们的编排与其说是为了汇总知识与资料,还不如说是为了提供有关前人的文学与历史作品的选段摘录的汇编,为作家觅取文学精华与典故的范例打开一条简捷的途径。在他们各个不同的门类中,有许多是涉及‘人事’的各个方面的,由此他们分类汇聚了一大批我们所谓的历史与行政问题的资料。类书与历史写作之间一个饶有趣味的联系是,在这三部类书的编者中,而且事实上也是在唐初其他的那些久已佚失的类书的编者中,有许多学者,他们首先是作为专业的历史学家享誉于世的。其他一些官方史家则在最初三个皇帝的治下参与了范围广泛的法律与礼仪的法典汇编工作。如此大规模地致力于知识的分类与编纂,成了当时的一种流行学风,许多官方史家人也直接参与其中。”[7]74《唐代官修史籍考》又言:“欧阳询从事《陈书》的纂修,被公认为精于前朝历史……徐坚从事《武则天实录》及武后于703年授命编纂的《国史》的撰修:他们两人都是以史官的身份参与了修史。在《艺文类聚》的编纂者中有令狐德棻,他一生大部分的时间都担任史官。在《艺文类聚》的十余位编纂者中,令狐德棻与陈叔达从事《周书》的修撰,而裴矩则致力于撰写《齐书》。合作编纂《初学记》的人士中有著名的专业史家韦述,此书是在张说的主持下编制的,而张说本人此时正参与《今上实录》的撰写,此实录所记即为玄宗即位初年以来的事迹。”[7]74《唐代官修史籍考》言:“这后一种集子编纂之时,正值朝廷的学士们在编制一系列规模宏大的文学选集,其中《文馆词林》1 000卷,完成于658年;《累璧》630卷,完成于661年;《瑶山玉彩》500卷,于663年进呈朝廷。还有一种大型选集,其完成年月已不详,但他的编纂者几乎就是编《瑶山玉彩》的同一批人,此书就是300卷的《芳林要览》。于是包罗万象的学问与规模宏伟的选集一时间风行天下,并享有皇家的慷慨资助。许多参与这类选集编纂的学士同时也是活跃的史家,其中有些人还从事实录与国史的修撰。”[7]86-87总之,不论是前期还是后期,编纂类书的这些文人学士,多半都是担任着修史的任务,他们一方面是史书的编纂人员,一方面还是类书的编纂人员,而在当时,这两项任务皆是大型工程,皆是当时朝廷十分重视的工作,故我们认为类书编纂与修史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进一步说,在古人的眼中,修史与编纂类书是同样重要的事情,并不是后世人眼中的修史之学术地位高,编纂类书之学术地位低,后世的学者总是轻视类书的学术地位,认为类书是“獭祭”“饾饤”,是没有学术性的“摘抄”“抄撮”,皆是偏颇之论,中古时期直至明清,此起彼伏的类书编纂为何不能停歇?不正是类书编纂之地位与重要性的表现吗!
第三,类书编纂体例上的评价。南北朝时期的类书编纂多是类事类书占主导地位,到了《艺文类聚》编纂的时代,“类事类书+类文类书”模式也就是“事文并举”模式,正式出现并得以确立[9]。然而,遍观唐初编纂的大型类书如《文思博要》《三教珠英》等,皆是类事类书,即使是《瑶山玉彩》《碧玉芳林》《玉藻琼林》,仍然是类事类书,当然,这些大型官修类书也是收纳“诗文”的,但是其“诗文”是没有独立性的,仍然是化“诗文”为“类事”,也就是说,此时的“诗文”即“类文类书”是依附于“类事类书”的,所以,我们认为唐初编纂的诸类书,主体模式仍然是类事类书,但受《艺文类聚》的影响,类文部分开始占有更多的篇幅,甚至类文部分有单独独立的倾向与实践。随着官修类书的发展,私人编纂类书开始繁荣起来,私人类书编纂的体例亦是多姿多彩,比官修类书更为自由与热烈,从唐初即不断产生各式新体例的类书编纂此时更是迅速发展,“类事类书+类文类书”模式不再那么受到追捧,因为相对来说,“类事类书+类文类书”模式太过冗杂,知识点也就是要点不集中,而类句类书与类语类书就是更适宜、更合用的体例,当然类句类书之代表作《北堂书钞》,类语类书之代表作《编珠》,在隋炀帝时代已经出现,到了唐初,就是一个如何继续发展的问题。赋体类书也是如此,逐渐受到文人学士更多的青睐,我们怀疑《策府》或许采用了赋体类书的形式,这无疑会拓宽官修类书编纂的新境界,但只是猜测而已。《翰苑》是一部失传已久的赋体类书,幸运的是,日本有古写本重现,这是唐高宗显庆五年(660)张楚金编纂的,原来的学者多认为《事类赋》是赋体类书的开启者,后来,敦煌文献中发现了《兔园策府》,让我们知道唐初就有此类赋体类书出现,而《翰苑》的发现,证明唐初不是只有一个《兔园策府》,还有一个《翰苑》,他们的时代相距不远,也就是说,在唐太宗与唐高宗时代,就出现了较为成熟的赋体类书。晚唐时代还有一部赋体类书,就是《记室新书》[10]。安史之乱之后的唐代类书编纂,还是类句类书与类语类书最受欢迎,《备举文言》《应用类对》是类语体类书,《白氏六帖事类集》是类句类书,而诸如此类的类句类书、类语类书大量出现且流行起来,是类书繁荣兴盛的表现,因为,此时的读书人需要这样的类书,而大量涌现出来的晚唐类书之体例与内容,又染上了藩镇割据的颜色。最后,组合体类书亦是唐代类书编纂的一个特色,《艺文类聚》是类事类书与类文类书的组合,《初学记》是类事类书加类语类书加类文类书的组合,这种组合体类书的编纂,难度是很高的,所以私人编纂类书多不采用这种模式,而只有官方在人才济济的情况下,才可以做出如此经典的文本,《艺文类聚》《初学记》之所以可以流传千年,并成为经典,主要还与他们的编纂体例有关,这是他们不可能被淘汰的质量保障。[11]总之,纵观整个中国类书编纂史,唐代类书之编纂体例最为典型与纯粹,南北朝时期的类书编纂体例尚不丰富,宋及以后的类书编纂体例又多有枝蔓不够纯粹,故概而言之,唐代类书之编纂体例最为经典与纯粹,是研究中国类书编纂史最为可靠的文本。
第四,类书编纂者方面的评价,中古时期也包括唐代,类书的编纂是连绵不绝的,多是父子兄弟交至、师徒交至,同一人编纂多部类书亦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现象。具体到唐代,我们可见到的第一个代表人物是许敬宗,他是唐高宗时代典籍编纂的主要负责人,十几部典籍在其领导下完成,自贞观以来,朝廷所修《五代史》《晋书》《东殿新书》《西域图志》《文馆词林》《累璧》《瑶山玉彩》《姓氏录》《新礼》等书,皆总知其事,而此位许敬宗在唐太宗时代是参与过《文思博要》的编纂,其在后来的《东殿新书》《瑶山玉彩》《累璧》的编纂中究竟是一个什么状况,史书记载不详,但是,毫无疑问的是,早年参与编纂《文思博要》的经验,必然对他领修新书极有帮助,而早年的经验教训必然会指导新的类书编纂,这是促进类书编纂进步、提高类书编纂质量的人才保障。[12]《三教珠英》的编纂者亦是众多,其中起作用最大的是徐坚、张说二人,建议参考《文思博要》编纂《三教珠英》的主意就是他们出的,而《三教珠英》后来也果真是如此编纂了出来,这就是说,徐坚、张说二人对《文思博要》与《三教珠英》皆很熟悉,否则他们也无法完成《三教珠英》的编纂,更为重要的是,到了唐玄宗时代,唐玄宗感觉《修文殿御览》等书,卷帙庞大,不利于王子们学习使用,于是敕令徐坚、张说编纂王子教科书《初学记》,此时的徐坚、张说二人,在两部千卷大类书的基础上,再次编纂类书,难道会不受影响,难道会没有了印象,他们早年编纂《三教珠英》的经验、教训必然会促进《初学记》的编纂,加之唐玄宗的个性化要求,于是一个新的类书体例的践行者《初学记》诞生了,如果没有早年的经验、教训,徐坚、张说二人能够编纂出质量如此高的《初学记》吗!孟利贞是第三个例子,此人早年参与了《瑶山玉彩》的编纂,后来又编纂了《碧玉芳林》《玉藻琼林》,虽然这三部书都散佚了,我们看不出他们之间的联系,但是,通过这文采意蕴十足的题名,孟利贞难道没有受到影响?其早年编纂《瑶山玉彩》的经验教训,肯定会深深的影响《碧玉芳林》《玉藻琼林》的编纂[13]。再者,薛元超曾经参与过《东殿新书》的编纂,而其子薛曜后来又参与了《三教珠英》的编纂,这是父子皆参与编纂类书的代表[14]。王义方编纂有类书《笔海》,而他的弟子,为他服丧三年的员半千,后来参与了《三教珠英》的编纂,早年受学王义方门下的员半千,绝不会不知道《笔海》,而此小小的《笔海》,会不会对《三教珠英》的编纂产生影响,我们不能做出判断,但是,此《笔海》毫无置疑地会影响到员半千。白居易编纂有《白氏六帖事类集》,白居易的好朋友元稹编纂有《元氏类集》,虽然是内容绝无关系的两部类书,但是,两位好友之间、两部类书之间,难道彼此没有交流,难道彼此没有影响?总之,我们认为中古时期的类书编纂皆是如此,皆是前后左右联系紧密,任何学问的养成,任何典籍的编纂,都不可能是孤立的事件,必然都是中国类书发展史、编纂史上的一环,唐代也不能例外,并且唐代的表现更为典型,因为唐代的类书编纂是南北朝以来整个类书编纂链条上的一环,是类书编纂高潮期的延续与发展。
第五,类书的功能即类书在使用范围方面的评价。唐代著名的诗人,如李峤、张说、白居易、元稹、李商隐、温庭筠、皮日休等,皆有类书编纂,其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诗文写作时,类书可以帮助他们迅速地查检捃摭,触类旁通。《文镜秘府论》南卷《论文意》载:“凡作诗之人,皆自抄古人诗语精妙之处,名为随身卷子,以防苦思。作文兴若不来,即须看随身卷子,以发兴也。”[15]《文镜秘府论》这一段经典的论述,经常被引用,因为这就是古人作诗作文的实际情况,我们容易被李白斗酒诗百篇的豪气所误导,我们认为古人作文、作诗就如同长江、黄河水,肆意倾泻而出,其实,这种情况是较少的,更多的情况是“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而如此情况之下,类书就是最合用的随身利器。韩愈《赠崔立之评事》载:“崔侯文章苦捷敏,高浪驾天输不尽。曾从关外来上都,随身卷轴车连轸。朝为百赋犹郁怒,暮作千诗转遒紧。摇毫掷简自不供,顷刻青红浮海蜃。”[16]3796-3797“随身卷轴车连轸”一句,更为清楚地说明了随身卷轴对于读书作文之功用。《隋唐五代类书与诗歌》言:“与前代相比,隋唐五代类书不但数量繁多,而且体例严密,品类丰富,选辑精当,而这些众多的高质量的类书,其主要编纂目的和实际作用,都是供撰写诗文时检索典故事类,采撷美词秀句,构造对偶意象。因此,隋唐五代类书与诗歌发展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微妙而复杂的关系。”“唐代诗歌的日益应酬化和普及化,以诗取士制度的确立,使得许多本来缺乏诗歌天赋的人也必须学会作诗,这就需要把诗歌变成一门可学习的技术,而类书正是促成诗歌技术化的工具之一。”[3]127-132《唐代三部类书对唐诗的影响》言:“现存《艺文类聚》《初学记》《六帖》三部类书与唐诗关系密切,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官修类书为诗歌创作提供了典范,科举考试题目多出于此。帝王用类书编篡的方法提倡文学,导引诗风,从而促进了唐诗的繁荣;其二,类书是唐代文人知识积累过程中重要的童蒙读物;也是唐代诗人创作时‘构思之古书’,是唐诗生成的条件之一。”[17]《温李诗的对仗、声律、用典技巧——兼论类书和骈文对温李诗的影响》言:“温李的诗歌创作受到了类书和骈文的影响,可以称之为‘以骈文为诗’。”[18]总之,文学应该是推动唐代类书编纂与发展乃至繁荣的主要动力,在文学的引领下,大量的文学类书涌现出来,成为文人作诗作文的“随身卷子”;文学的上游是科举,于是针对科举而编纂的科举类书亦大量出现,当然,这个特点在两宋时代更为显著;文学的下游是教育,部分类书随着时间的流逝,进入教育领域,并且部分类书的编纂质量较佳,内容典雅,资料丰富,于是成为童蒙的教科书,如《类林》《兔园策府》;总之,类书迅速占领从低层到高层的整个学术文化空间,成为古代读书人的“终生伴侣”。
欧阳询《艺文类聚序》载:“皇帝命代膺期,抚兹宝运,移浇风于季俗,反淳化于区中,戡乱靖人,无思不服,偃武修文,兴开庠序,欲使家富隋珠,人怀荆玉。”[9]27“家富隋珠,人怀荆玉”是唐代类书编纂的总方针与内在逻辑,并且是在唐初编纂第一部官修类书《艺文类聚》的时候就已经提出来的口号,而这个声明被实际的贯彻到后来的唐代类书编纂之中,经过大唐近三百年的发展,类书之编纂让更多的人较为便捷地获得了知识,逐渐实现了知识文化的传播与下移,这毫无置疑的是唐代类书编纂的功劳,是类书典籍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当然,其他典籍的作用也不能忽视,而这里我们强调的是一直被忽视的类书也是其中之一,也应该受到更多的关注与肯定。
第六,我们有必要补充一下类书与古代读书人之间的关系,因为,今天的很多读书人已经体会不到古代读书人与类书之间的感情,今天的人们做学问也好,编教材也罢,多是用计算机来完成资料的搜索,而往前追30年,甚至更久一点,人们是没有计算机的,当时的学者要完成资料的积累多是利用卡片来完成的,而这些日积月累而来的卡片,如果有个以类相从的体例,不就是简单的专题类书吗?再者,年龄大一些的老先生们也是很重视类书的,一部《太平御览》就会令他们神往,而《太平御览》中的资料就是他们开始研究的基础,故可知古代读书人编纂类书与使用类书是极其常见与频繁的,他们对类书的重视亦是不容置疑的。明清时代,类书家族之中出现了大量的日用类书,这些类书被广大中下层民众所喜爱,成为他们增长见识的“万宝全书”,如《五车拔锦》《三台万用正宗》《万书渊海》《五车万宝全书》《万用正宗不求人》《妙锦万宝全书》等等。这些日用类书与中古时期的典型类书不一样,甚至多被认为是品格低下之书,当然我们这里不再争论品格高下,我们所要借用的仅仅是一个词,即“万宝全书”这个词,为何会有这样的称呼或者叫法,“万宝全书”的提法用在类书身上,到底合适不合适,被人认为是品格不高的类书为何会有如此花哨的称呼,通过不断的思索,我们渐渐明了这个问题,在古代,当然也包括唐代,类书是读书人的“万宝全书”,是古人检索征引、积累知识、开拓视野、处理疑难、了解世界的锦绣万花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