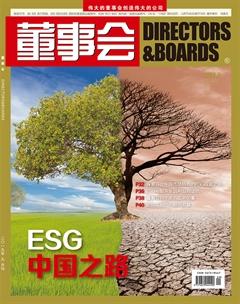不期而遇:我的20年董秘岁月
施卫东

1996年,我从筹备第一家额度审批制的上市公司担任董秘到2016年离开那个岗位,30岁到50岁,正好是我职业生涯最黄金的年龄,整整20年时间。当初,我根本就没想到要进入资本市场,但是进去了以后,它把我的人生都改写了。
从“好上加好”到漂亮的9折
我是1992年走进资本市场的,当时作为毕马威审计团队人员参与了上海石化的A+H改制上市工作。后来,江南造船厂准备上市,那时审批制度是额度制,1996年拿到了六千万的A股发行额度,厂里的领导弄了一个上市筹备班子,大概有七八个人,以年轻人为主,我被任命为筹备组的首席秘书。所以说,从1996年开始,到2016年,我全程参与了资本市场二十年。这里面有意思的是,我把中船集团所有三家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这个职位的工作做了一个遍,两家在上海,一家在广州。现在基本不可能了,没有机缘巧合是没办法做到的,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情。
每个公司都有它的特点。我服务过的第一个上市公司是额度制出来的,自己全程经历,感情很深,尽管规模不大,因为出自江南造船厂,在当时的资本市场上也是有名有姓;第二个就是中国船舶,称得上是资本市场上的一个传奇了。
2007年是迄今为止中国资本市场真正意义上的最大的牛市,上证指数6124点这个点位至今仍需仰望。当時的市场背景是上市公司进行了股权分置改革,股改带来了资金牛;不仅如此,中国加入WTO以后经济发展势头也很好,和资本市场形成了整体共振。跟昙花一现冲到最高点的小股票不一样,造船业是中国比较大的重装备业,有很大规模。我们通过2007年的资产重组,开启了“好上加好”的模式,在这个过程中,身处周期性行业的中国船舶股价也走到了历史的最高点。
2007年以前的资产重组基本上是为了救活一个公司,很多公司都是亏损了甚至要退市了,借助重组装入一个新的产业,把净资产弄得好一点,把这个公司弄成盈利。而我们2007年做的事情是,原来这个公司就很好了,沪东重机当时是国内最大的船用柴油机供应商,加上整个造船业形势相当好,公司业绩非常好。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又加入了优质的造船和修船资产,这就相当于把公司打造为造船、修船、柴油机一体化上市的概念,这就是“好上加好”的模式。
那时候的造船市场火到什么程度?你最终拿到一条船时,从签订合同到建造到最后交船,当中竟然已经换了三四拨船东,真可以说是击鼓传花!就好比你和我签了一个协议,然后我过了两个月加价把协议卖给了张某,张某过了两个月再加个价卖给李某,那个时候船东代表一直在换,最后拿到船的船公司已经不是一开始签合同的人了。
在这个重组案例当中,我们开启了“好上加好”模式,优质资产新老共存,谱写了一曲2007年中国牛市最华美的篇章。
当时超过两百块的股票在我记忆中,似乎只有贵州茅台和中国船舶,但中国船舶股价一直高于贵州茅台。11月中国船舶股价最高达到三百元,茅台最高达好像到了二百八十多元。这是2007年的实际情况,当时公司的市值达到了两千亿,而市值的飙升是有业绩支撑的。当然,炒船也推动了股价飙升。
那个时间段,我一天最多接待投资者八场,从早上到晚上,有的四十五分钟一场,有的一小时一场。那时候大家比较激动,觉得这个公司好得不得了。投资者都希望自己能和上市公司的高管一对一交流,我喉咙沙哑的毛病就是那个时候落下的。有的基金经理甚至还没交流完,就拿起手机下单了。
那个时期是中国船舶,也是我职业生涯当中的一个高点。中国船舶“好上加好”的资产重组做法被上海证券交易所评为当年最佳并购奖案例。并且,这个案例引领了2007年以后一些公司对“好上加好”模式的复制,成为周期性行业不可复制的一个典范,让我们引以为豪。
从我做的三家公司来说,中国船舶创造了不可复制的辉煌,尤其是这个辉煌是真实的。中国船舶当时的动态市盈率三十多倍,并不高,机械行业平均也是三十到四十倍,是非常正常的。尽管受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盛景持续时间只有一年多,但这是制造业的周期性带来的,跟那些主业不正常的公司是不一样的。
我做资产重组并购一共有五六次,有成功也有失败,但记忆深刻的是到了中船防务(广船国际)之后。
2014年,中船集团一纸调令,我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地就去了广州,做广船国际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专门负责广船国际收购一块军工资产。这个案例的一个特殊性在于,公司由此成为H股市场上的军工第一股。以往在香港市场上是没有国内军工的实体资产上市的,后面也没有跟随者,因为我们是(A+H)公司,我们注入的是核心军工资产,据我所知,国防科工局批了我们这一单以后,至今还没有批准其它的公司。
做这件事情,我花了近一年半时间,从2014年五月份开始,之后又花了半年做收尾。当时,我是主持行政工作的副总,主要工作就是负责资本运作项目,没有总经理,这个案例我是全过程的主要参与者,包括和两地交易所的沟通等,这里面的难点就是军工资产和信息披露问题。随着重组的完成,实体型的公司变成一个平台型的上市公司。
2015年5月份之前,这个资本项目就基本完成了。应该说,从时间点的把握上我们做得很漂亮,度也掌握得非常好。这其中有一个细节:证监会批文是2015年3月份拿到的,批文的有效期是半年,而我们只花了2-3周就完成了发行。由于是市场竞价,半年之内完全可以再等一等,等到市场价格更高些发行。但是,我们认为应该抓紧时间弄好,因为市场已经够好了,已经超过我们的想象,这是一个职业判断。
我不能说我不欢迎市场火热,但感觉明显热过头了。原计划我们要做北上广深的全国路演,后来我们当机立断,取消了所有大型路演,代之于定向规模很小的反向路演。最终,我们的股票发行价格和当天的收盘价只相差了10%左右,就是9折——那天收盘40多块,发行价接近38块。
如果在当时心黑一点,等一个高价,价格越高风险也会越大。实际上,两个月以后你就发不了,因为遇到股灾了,天天跌停没法把握了。可见在证券市场上,把握趋势很重要,自己对自己度的把握也是非常重要的。
它就像一种烙印,这辈子拿不掉了
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向来是问题导向的,问题出来了想办法怎么去解决。用这个模式推演开来,可以解决很多复杂琐碎的问题。基于这个逻辑,如果是从对资本市场的贡献角度来说,我觉得有两三件事值得记录。
第一个是我在江南重工工作的时候,当时将车间改造成一个上市公司,所以这里面充满了很多关联交易。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我首创了关联交易的框架协议。当时我和交易所多次沟通,能不能将一年内可能产生的关联交易估一个数值,搞一个额度,在每年一次的年度股东大会一次性通过,这样就不用每次按照规则开这会开那会了,效率提高了很多。现在我们觉得很简单,但在当时是有开创性意义的。

还有就是对内担保的框架协议。担保分对外和对内,我一直认为对内担保的风险跟对外担保的风险是不一样的。对内担保是指自己对全资或控股子公司或者它们之间在业务过程中的一些相互担保。有一天,我在上交所交流时谈到,中国船舶下面有造船厂、修船厂、柴油机厂,他们相互担保,对下的担保,都是内部的,我认为风险没有扩大。对内其实也是对下面的一种把控,有所约束,属于内部控制。企业一旦变为上市公司,很多事情身不由己,要有完全的内控流程,这个和非上市公司完全不一样,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市公司是有它的规范性的,能不担保尽量不担保。但是,光机械地遵守规则,你可能会效率很慢。我们把一年内可能的对内预计担保金额,在股东大会上一次性定下来,一旦发生担保,只需要公告一下,就提高了效率。这件事大概在2008--2009年的时候,我认为是一种既尊重规则又尊重效率的做法。当然,风险非常大的对外担保是不能用这个方式的。
第二个贡献我认为是给初入门的后辈一些经验,集中在我的交流上、讲课上。我和在上交所上市的很多后进同行都交流过,甚至一个公司整个董办都听过我的交流。2012年开始,我给上交所做董秘资格培训的交流,从第44期到现在的120多期,70多期的交流,目前大概已经超过一万五千名学员了。每次培训,我都和他们分享半天的董秘心得,很多人听了以后都觉得,我是真心把他们的疑惑解答了,每一次的评分都是很高的,算是金牌课程了。尽管我离开这个圈子已经两年多了,但上交所还是请我去交流,包括科创板的首期董秘资格培训班,也请我去传道授业,我以为这是对我们这代董秘的肯定。
我们这一代人做事情都是很认真的,来了事情就怕做不好。所以我和他们交流,第一就说要人品好,人品好体现在证券市场上做事要专心专注不敷衍,你的任何一个公告、一段文字都是对着资本市场,一旦粗心了,就可能会给资本市场带来莫名的搅动。比如公告中你写错一个字,一个字可能值一个亿,比如三千万,你写成三个亿了,股票价格不受影响是不可能的。当然人品也体现在我们都是天然的内部信息接受者,我们是要好好交朋友,但不能害朋友,所以要有健康的财富观念,不能觉得什么信息都能和朋友说,常在河边走,一定会湿脚。
刚入行的董秘急需有人带他入门,怎么做好董秘、怎么管理下面的部门,这些都是实战的经验,没有虚的东西。很多你觉得很简单的事情,对他是非常难的,你的经验经历在于可能刚听他半句话,就知道难在什么地方。所以我和他们交流的时候,会设置好多个场景,比如证券监管部门忽然来电话,股东突然指责,调研机构突袭,遭遇不利公司的消息等,你怎么办,应该怎么处理。现在是自媒体时代,纸媒体时代可以把已经印好的报纸都可以买回来,但自媒体时代,一传播出去就收不回来了,我在交流中把它比喻成“一秒就是全世界”。现在政策法规变化很快,一些学员会问到比较难的专业问题,我也不一定回答得了,那大家就一起学习,我用我的人脉再请教交易所的老师或是一些专家,或是上市公司的一线同行,通过这种方式也能保持自己对知识的更新。
第三个是我很奇特的贡献,到了广东以后,短短的两年多时间,粤沪同行之间的交流增多了。我过去了以后,把一些热心董秘组成一个核心的群,再由这些人串出去,像滚雪球一样。每年有一次互访,广州的董秘到上海去,上海也过来广州,这样彼此之间都能有业务提高,我觉得这样做非常好。这都是民间的,比较大的规模,相互在一起的董秘有六七十人,气氛非常融洽。2014年到2016年底,两年半时间,我在广州除了业务上做了一个军工资产注入的重组项目,还做了这样一个无形的东西。我在里面牵线搭桥,不单单要有热情,还要有这个奉獻精神,要带头付出一些,除了精力,还有经济上的。当然我认为都是非常值得的,都是有回报的,大家对你认可,其他方面你有一些问题要讨教的时候,对方就会毫无保留地告诉你。因为广东和上海的董秘群体是不一样的,广东民营的特别多,上海国有的多一些,相互的交流就很有意义。两种不同性质的企业之间的交流,会吸取到不同的工作方式,取长补短。我就像桥梁使者一样,把大家联系在一起,就是天下董秘一家亲的理念。
企业如人,应客观看待上市公司
我一直说,上市公司像人一样,人有点不舒服但并不影响和外界的交流。企业也是这样,一个客观的规律是:企业运转过程中一定会有毛病,但这个毛病不会让企业因此停滞。遇到什么情况不能先找它的毛病,不能因噎废食,而是要容忍这些毛病,想办法怎么解决毛病。所以,问题是靠发展来解决的,一定要用发展的眼光把老毛病克服掉,公司才能不断往前走。实际上,你不可能期待一个企业是完全健康的,这样的上市公司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国有企业有一些弊端可能不符合市场逻辑,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酸甜苦辣,有很多人是不理解的。我以前讲过一句话,每一个公告背后,可能都有一连串的事情。公告出来或许只有几行字,但前面可能做了几个月的努力,有很多和大股东的交流,甚至是交锋,最后出来是风轻云淡,其实公告出来的时候说明一个很大的事情已经解决了。我在第一家公司江南重工做的时候,记得是在1999年,上海证监局来检查,检查以后他们觉得我们很规范,江南重工成了上海证监局巡查以后唯一发文表扬的单位,后面就没有了,因为证监局看到一个个好公司变脸了,这又变成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情。再比如说,我刚到中船防务的时候,整个董办人很少,我去的第一件事是一边做项目一边打造一支队伍,用项目来出队伍,用队伍来出项目,很经典的做法。我花了一年时间把三四个人带出来,淘汰了两个人,但淘汰了的两个人在其他上市公司也做得挺好。从此以后,中船防务在上交所考评都是A,在这之前都是B。
回看我的个人经历,我读的是复旦大学世界经济专业,1989年毕业的时候,中国证券市场还没有起来,压根都没有想到这辈子会与董秘有关联。机缘巧合,我参与筹备了江南重工的上市工作,当初觉得上市公司是一个比较新的领域,没想到进去之后就出不来了,人生的黄金时期都在里面,而且非常投入,人生的成功失败汗水泪水也是这个市场给的。如果要我总结20年董秘生涯的感受,我想用“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八个字形容一点也不为过。我一直觉得,董秘能做好的事都是小事,董秘没做好的事全是大事。董事会秘书实际上是无法改变公司的,但可以影响公司,好的董秘应该是公司董事会的影子。我也一直想写一本回忆录,名字都想好了,就叫《不期而遇》。我想说,一切的不期而遇都是冥冥之中,都是偶然中的必然,有如我与中船集团的不期而遇,是中船成就了我,我心怀感恩;有如我与资本市场、与传奇董秘的不期而遇,从接触市场到职业董秘再到传道授惑,我庆幸我的黄金年代是热忱的、认真的和乐于奉献的。我虽然离开了这个位置,但大部分的社会活动还是和董秘有关,就像一种烙印,拿不掉了。我自己也很认同,我一直是这个圈子里的一份子,应该为这个圈子做贡献,同样,至今还战斗在资本市场第一线的兄弟姐妹们也一直没有忘记我,那么多值得骄傲的同行和朋友是我人生最值得珍贵的财富。
口述整理:谷学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