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再歌唱的巴黎
——阿拉贡《春天的不相识的女子》赏析
钱晓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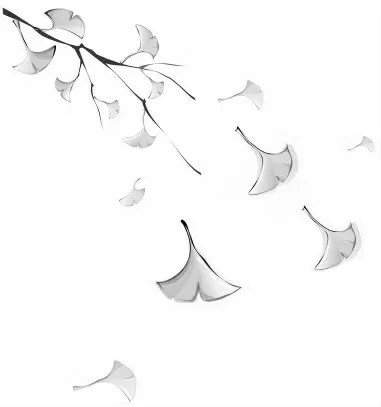
“在市场角落上我遇到一双眼睛/那奇异的凝眸在梦想什么/ /啊雨后巴黎的心在扑扑跳动/下了这么多雨她还觉得快乐吗/ /小溪泉水中间多少花枝/逝去了更无一点颜色/ /我永远望见那昂丹的长堤/和神女躞蹀的帕尔姆人行道/ /黄昏的淡漠者和辚辚车辆/夜色的面纱和无数惊险奇遇/ /人们朝三一教堂走过几步/这犹豫时刻众人纷纷离去/ /在圣拉萨尔火车站的尘嚣中间/为什么这双邂逅的眼睛会流泪呢/ /啊 巴 黎 巴 黎 你 不 再 歌 唱/你 侧过头去脚步踉跄/ /现在是点煤气灯和轻率地行动的时候了/这些街心公园充满了喁喁情话/ /现在是点煤气灯的时候了你还没有点/你还没有点而巴黎却已沉默无言”
(阿拉贡《春天的不相识的女子》,徐知免译)
可以说,能否让读者产生一种“陌生化效果”,是诗与非诗的重要区别。关于巴黎的诗歌实在是太多了,不管有没有去过巴黎,都不妨碍人们对巴黎形成牢固的文化印记。日久天长,一提到巴黎,人们就会说“艺术之都”“浪漫之都”,除此别无新颖真切的感受,这就是感性的钝化。诗人写巴黎如果不能破除读者的“钝化”状态,那写出来的诗只能是庸诗,甚至是非诗。故而,一千个诗人写巴黎,就应当有一千个巴黎,就如海德格尔的著名论断:“诗是给存在的第一次命名,是给万物的第一次命名。”阿拉贡在《春天的不相识的女子》一诗里也写了巴黎,写了一个令人耳目一新、心头跳动的巴黎。

(阿拉贡:形象高于一切)
阿拉贡,全名路易·阿拉贡,生于1897年,逝于1982年,法国著名诗人、小说家、政治活动家,早年与安德烈·布勒东和菲利普·苏波一起,创立了“超现实主义”文学流派,宣扬“形象高于一切”,推崇“纯粹的心理自动作用”“它不受任何理智主宰,摆脱了任何美学或伦理学成见”,不过,后来他加入法国共产党,在文学上趋向现实主义,其作品中的超现实主义痕迹也愈来愈淡。比如《春天不相识的女子》,在诗歌内容层面,有对巴黎的细致描摹和深刻分析;但在写作技法上又闪耀着超现实主义特有的光芒。于是,我们读者很容易产生一个幻觉——巴黎仍是那个巴黎,却又不是那个巴黎。
从表达方式上来看,这首诗属于抒情诗。在春天里遇上一个素不相识的美丽女子,于是男主人公陷入一见钟情的单相思,那感觉甜蜜而又忧愁,幸福而又惆怅。客观来说,就现在的读者的眼光来看,这样的情节还是比较俗滥的;但阿拉贡偏偏可以把这种看似俗滥的题材写出非同一般的感受。这首诗写于二战时法国沦陷的日子,德军在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像样的抵抗的情况下,仅用了四十天就占领了法国全境,当然包括巴黎。对法国来说,这是耻辱;对巴黎来说,则是幸事。巴黎没有遭到战火的焚毁,巴黎似乎仍是那座巴黎,就如鲁迅先生所言“时光依旧流驶,街市依旧太平”。“我”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历史环境下,踽踽独行于巴黎的街道,孤寂的感觉氤氲成一团冷雾,自内向外,也是自外向内地弥漫交汇,直至相融为一。就在这时,“一双眼睛”在“市场角落上”出现,犹如流星划过漆黑的天幕,温暖的光泽在“我”的心底闪烁。于是,“我”想她之所想,“那奇异的凝眸在梦想什么”。真的,这样的情景像极了爱情,很自然地唤醒人们重温各自曾经经历过的那种温馨的感觉。不过,这种“共鸣”的产生,得力于诗人“借代”手法的运用。诗人不直言遇到“女子”,而说遇到“一双眼睛”,那当然是“女子”的眼睛。同样的道理,那“奇异的凝眸”自然也是“女子”的凝眸,直白的表达应是“那女子在梦想什么”,但诗人偏偏说“那奇异的凝眸在梦想什么”。正是因为这种“借代”手法的运用,才使诗歌语言摆脱了平庸的日常交际式的“通讯语言”,从而上升为诗性语言,爱情的“共鸣”也是水到渠成。西方文艺理论家马尔洛夫斯基曾就诗歌的“陌生化”提出过自己的主张,他认为诗的特色就是要选择与日常语言不符合的、破坏标准化了的日常语言规范的语法、词汇和句子,让人产生陌生感。从这个意义上讲,“借代”无疑是诗歌语言“陌生化”的一个有效手段。本诗第二节,“啊雨后巴黎的心在扑扑跳动”,情感是比较容易感知的,就如千千万万恋爱中的人那样,“我”激动的心难以抑制,但诗人不说“我的心”,却说“巴黎的心”,以“巴黎”来替换“我”。运用“换位”手法,我们会获得一种非常陌生而奇妙的体验:“我”激动的心充满整个巴黎,“我的心在扑扑跳动”,也就是“巴黎的心在扑扑跳动”。貌似极度夸大的情感,却恰恰符合真实的人性。“下了这么多雨她还觉得快乐吗”,此句语言形式既无变形,亦不陌生,却是言简意丰。诗句包含了两大主体,一个“她”,一个“我”。“我”关心她快不快乐,因为“下了这么多雨”,也即在“我”的潜意识里,下很多的雨带给别人,至少带给我的是不快乐。换个表达,在遇上这位“女子”之前,“我”的确并不快乐。一个不快乐的“我”关心一个素不相识的“她”快不快乐,这样的爱分明是一种不掺私心的“无我”之爱。
相比一二节,第三节就显得很突兀,无论是意象选择,还是语言形式,都给人强烈的陌生感,甚至带来极大的“审美困惑”。巴黎这座城市里哪来的“小溪”“泉水”“花枝”? 而“花枝”又怎么出现在“小溪泉水中间”? 为什么“逝去了更无一点颜色”?疑问一环套一环。前面我们说过,阿拉贡后来虽然由超现实主义转入现实主义阵营,但其诗歌创作仍然残留着许多超现实主义的印迹。本诗的第三节从一定意义上来审视,应该最能体现这一特点。鲜明的形象,自由的意识,似乎不受理智控制的思维,这些都是“超现实主义”的标签。探究这些意象的现实存在性没有任何意义,追问“花枝”为何在“小溪泉水中间”也无多大价值,因为这些意象本来就属于“想象性的意象”。“小溪”“泉水”与纯真相连,“爱情”与“花枝”自然联系,而“颜色”的渐渐逝去反映出“我”心绪的曲折。当然也可以理解为衬托,“女子”的形象让多少“花枝”般的美丽的人儿黯然失色。
诗歌的四至七节偏向冷静地描摹,以“我”的“望见”这一动作领起后面的一系列描述性意象。第四节中的“昂丹的长堤”和“帕尔姆人行道”具有鲜明的巴黎城市印记和法兰西风情。第五节在“黄昏时分”出现的“淡漠者”和行驶的“车辆”,以及“夜色的面纱”,营造出落寞清冷的氛围。至于“无数惊险奇遇”则是一个个很笼统的概念。接下来第六、七两节的情形只能说是“无数”里的“少数”罢了。“我”望见的那些人原本打算去教堂祈祷,希望得到上帝的庇佑,奇怪的是,“走过几步”后人们就“犹豫”了,然后“众人纷纷离去”。是什么改变了人们的初衷? 是什么使人们虔诚的信仰产生了动摇? 唯一的解释只能是上帝在该出现的时候没有出现。诗人虽然没有指涉时代背景,但不能不让读者联想到巴黎沦陷给人们的生活和精神所带来的浓重阴影。弥漫“尘嚣”的“圣拉萨尔火车站”与“邂逅的流泪的眼睛”,一闹一静,一外一内,形成强烈的对比。流泪的女子与周遭的环境相比,显得如此格格不入。没有人在乎“她”为什么流泪,人们来去匆匆如忙碌的蚁群,只有“我”默默地凝望着她,关注着她。“我”的热情与众人的冷漠同样对比分明。质言之,“我”与“她”就是一类人。从某种意义上讲,前面所有的意象几乎都是为“流泪的眼睛”作铺垫。那双眼睛从“凝眸”到“流泪”,其中经历了怎样的情绪变化,原因成谜。返观第四节“我永远望见”的“永远”一词,瞬间感觉后面那黄昏巴黎的街景、喧嚣的火车站以及那流泪的女子,都随着巴黎的雨丝越拉越长。到了第八节,“我”一反常态,直接宣泄个人的情感。一个“啊”字大开抒情的闸门,“巴黎巴黎”叠加出无尽的感叹意味,“你”第二人称的抒情对象转换犹如面对面的倾诉。“不再歌唱”的巴黎是为何? 巴黎如同悲伤过度的人“侧过头去脚步踉跄”。这样的巴黎是情感浸泡后的巴黎。“邂逅的女子”令我心神荡漾,她的悲伤使本就孤寂落寞的“我”愈发伤感,再加上沦陷中的巴黎了无生机的现状,于是,这雨后的巴黎异化为一个巨大的情感容器。这是一个熟悉的巴黎,也是一个陌生的巴黎。
诗歌的最后两节“煤气灯”的意象颇具古典韵味。巴黎夜晚点灯的传统其来有自,本为驱赶巴黎夜幕下的种种罪恶,由统治者下令推行,后演变成巴黎民众集体自发性的行为。在电力尚未普及的时代,“煤气灯”照耀了巴黎这座“光明之城”的特殊的历史影像。“现在是点煤气灯的时候了”,反复咏叹出迫切的心情,因为这时候是“轻率行动的时候”,年轻男女在“街心公园”彼此说着“喁喁情话”。爱情的光亮可以刺破战乱的乌云,更何况在“浪漫之都”巴黎,还有什么比恋爱更重要更神圣的呢? 我相信很多人,包括诗人在内都不认为这种行为是堕落,而是映射出人性的伟大和民族的坚韧。“我”近乎执念般地渴盼着“她”点燃“煤气灯”,然而“你还没有点”“你还没有点”,反复之中流露出难言的失落和惆怅……在“我”的耳里,在“我”的心里,整个巴黎“却已沉默无言”。诗歌读至此处,人心也变得沉甸甸的了。
这“春天的不相识的女子”竟是让“我”欲罢不能,就如同《春天的不相识的女子》这首诗,又何尝不是让世人读出无穷无尽的深远而动人的意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