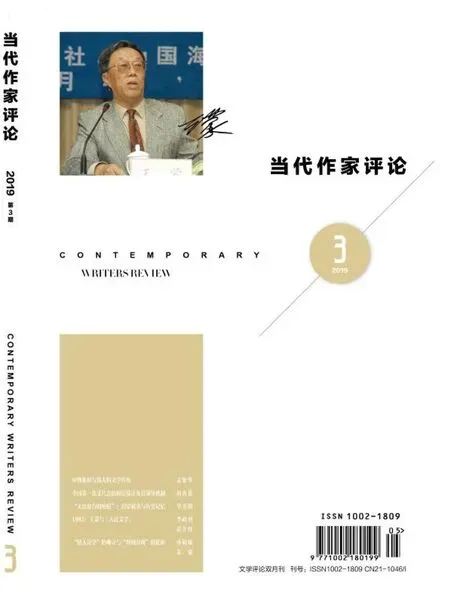轻躁的开端
——“新诗百年”驳论
顾星环
正与近年来中国诗歌的许多命名或命题相似,“新诗百年”历经一度高热的被纪念、被研究后,现今渐被冷落如旧梦,甚至有诗歌媒体急迫地计量“中国新诗第二个百年”。中国诗界眼下的一些行为风格越来越具有新闻界和时尚界的特质。在飞速转变的过程中,“新诗百年”这样的文学工程、文学项目,包含着泥沙俱下的研究结论,真正冷静的诗学反省所占几何?而在所有与之相关的诗学问题中,作为第一前提的“新诗百年”这一概念本身成立与否,首先值得重新推敲。
一、一意孤行的起点
几乎所有关于“新诗百年”的文本和活动,都指认1917年为中国新诗起点,2017年是中国新诗诞辰一百周年。最初由谁如此自信、斩截地落笔已难考证,但显见的事实是,中国当下诗界普遍毫无抵抗地接受了这一结论。然而,开端问题是一切学术史的首要问题,不可能如生活里的纪念日一般单调、明确。作为整个西方文学开端之一的《荷马史诗》,其相关史实始终为历代学者所质疑和探究:“荷马”真是两部史诗的作者吗?“荷马”果有其人吗?如果有,究竟是一人还是多人的合称?诚然,《荷马史诗》引发诸多疑问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该著作年代久远,但西方学者对“开端”的重视和严肃的自我反诘精神没有在纪念中国新诗百年的轰轰烈烈中复现。
1917年在中国诗歌史上的确重要:胡适在《新青年》1917年2月1日第2卷第6号上发表了8首白话诗:《朋友》《赠朱经农》《月》(三首)、《他》《江上》《孔丘》。于是,便有如今的论者据此断言中国新诗正式诞生。暂不论这8首诗是否是真正的新诗,只是转换角度,以诗集出版来说,中国第一部新诗集是1920年1月由上海新诗社出版的《新诗集》,内收胡适、刘半农、沈尹默、周作人、俞平伯、康白情等诗人的百余篇作品,远优于胡适一人区区数首诗这种孤证;若从创作时间讲,姑且认为胡适为中国新诗创作第一人,他的自陈也很清楚:“我的《尝试集》起于民国五年七月”,那么,“新诗百年”自1916年计似又未尝不可。可见,非得指定中国新诗在1917年起步缺乏说服力,实乃胶柱鼓瑟。
而胡适到底是否中国新诗创作第一人?他于1917年发表的8首诗究竟是否真正的新诗?恐怕他自己亦不承认:“我在美洲做的《尝试集》实在不过是能勉强实行了《文学改良刍议》里面的八个条件;实在不过是一些刷洗过的旧诗!”“做到后来的《朋友篇》,《文学篇》,检值又可以进《去国集》了!”《去国集》是《尝试集》内附带的文言诗词集。《尝试集》再版时他还强调:“总结一句话,我自己只承认《老鸦》,《老洛伯》,《你莫忘记》,《关不住了》,《希望》,《应该》,《一颗星儿》,《威权》,《乐观》,《上山》,《周岁》,《一颗遭劫的星》,《许怡荪》,《一笑》,——这十四篇是‘白话新诗’。”其中没有被今人指认为中国新诗开端的8首诗。
胡适的自我判断并非自谦,而是有一代学界宗师的自知之明。彼时同样站在革新立场上却不满于胡适诗歌创作的旁观者与竞争者均不在少数。《尝试集》甫一出版,施蛰存便“以一个暑假期反复地研究它,结果是对于胡适之的新诗表示反对了”,而当他读了《女神》后,“我才承认新诗的发展是应当从《女神》出发的”。成仿吾则干脆说,“《尝试集》里本来没有一首是诗”。穆木天更为武断:“中国的新诗运动,我以为胡适是最大的罪人。”钱杏邨极尽夸张之能事:“《女神》是中国诗坛上仅有的一部诗集,也是中国新诗坛上最先的一部诗集。”胡怀琛也企图以理论和创作实绩与胡适的白话诗分庭抗礼:他称后者为“新体”诗,自己所创白话诗为“新派”诗,认为“新派”诗兼能祛除“旧体”与“新体”“各弊”,是“模范的白话诗”,甚至否认胡适的白话诗满足“诗的条件”。时至当下,依然有学者重新考论胡适与中国新诗起点的关系,如姜涛在其著作《“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中写了整整一章《“新诗集”与新诗历史起点的驳议》。并且,他的研究切入口也恰以新诗集出版而不是期刊发表为主。
二、被遮蔽的先行者
历史在被叙述的过程中总有被压抑的成分,“反记忆”、“反档案”是必要的研究态度。如果说,前述质疑主要围绕胡适、郭沫若、胡怀琛等少数名垂青史的诗人展开,而郭沫若、成仿吾、穆木天等毕竟同为“创造社”成员,胡怀琛又迂阔到妄自尊大的地步,那么鲜为人知、默默无闻却对中国新诗的发生有坚实贡献的新诗人及其作品更应被纳入视野。叶伯和主创的《诗歌集》便是典型一例。
1920年3月,胡适《尝试集》出版。他在此书的自序中信心满满地认为,在《尝试集》最初创作阶段,“白话诗的试验室里只有我一个人”。《新诗集》虽于1920年1月出版,但确难证明其中所收录的其他诗人在1916年便动手试验新诗或胡适所谓“白话诗”。可是1920年5月,《诗歌集》出版。叶伯和在该诗集自序中说,自己在东京留学时“多读了点西洋诗”,尤喜爱伦·坡“言情的”诗,认为比中国古典情诗“更真实些,缠绵些,那时我想用中国的旧体诗,照他那样的写,一句也写不出。后来……想创造一种诗体……‘不用文言,白话可不可以拿来作诗呢?’到了民国三年,……我自己便做了些白描的歌,拿来试一试,居然也受了大家的欢迎。”叶伯和的“试一试”比胡适的“尝试”还早两年,尽管他谦逊地认为这些试验不算什么,“胡适之先生创造的白话诗体传来”后才正式创作新诗,但若比较《尝试集》和《诗歌集》,便会清晰地辨别出后者更为新鲜、现代。
最突出的方面体现在两人对韵律形式的处理差异上。尽管胡适在反思《尝试集》第一编时认定“诗体的大解放”,要求打破“五七言的句法”,用“自然的音节”写诗,“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但在是否祛韵方面仍然保守,他于1917年致信钱玄同,认为白话诗“最自然者,终莫如长短无定之韵文”。钱玄同亦回信同意:“‘长短无定之韵文’,是吾二人对于此事,持论全同,可以不必再辩”,只是稍加反对胡适在旧词曲上的流连。胡适确实爱作“韵文”,即便如《关不住了!》《希望》等译诗也讲究句末用韵。有些诗甚至蹩脚到每句用同一字押韵,朱湘就曾说:“胡君‘了’字的‘韵尾’用得那么多。这十七首诗里面,竟用了三十三个‘了’字的韵尾(有一处是三个‘了’字成一联)。……就是退一步说,不刺耳……也未免令人产生于一种作者艺术力的薄弱的感觉了。”不仅如此,胡适的创作连“长短无定”的理想亦难达成:《尝试集》第一编里的诗固不必说,几乎全按五七言或旧词曲的方式分行;在第二编中,也有《如梦令》《小诗》等作品难逃传统诗词句法的窠臼;直至四版增订的《希望》,非但是如刀切般齐整的五言诗,并且押韵僵硬,乃至后人干脆将之谱曲成流行歌曲《兰花草》。《诗歌集》则不然。它在编辑上分为“诗类”和“歌类”。在1920年5月面世的初版中,“诗类”已经真正做到并超越了胡适所提倡的“诗体的大解放”:完全没有按旧诗词曲的格式分行,行末句尾不显现追求押韵的自觉,更好地成就了“自然音调”之美。它们是散文化的自由诗,而且展现出稚拙的诗艺,文字上时有和谐的对称(并非律诗刻板的对仗),音节上不乏充满余韵的延宕,如:“我和她都换了晚装;携了乐器;牵着孩子们;——/来到蔷薇花的架下,都坐在一把长椅上。//看着月的光明;花的美丽;四面都静悄悄的。”(《我和她》)“歌类”作为叶伯和最早着手的试验,使用尾韵较多,分行略照顾入乐的便利,但同样无一例外跳脱出传统诗词句法的拘囿,实在也比《尝试集》里的许多诗“新”些。更难得者,“歌类”里个别作品竟也作散笔而祛韵,如两首《兰花》中的第一首,与“诗类”的解放无异。
新诗的韵律问题,至今依然为人们所争讼不休。叶伯和已有超前的自觉,他说:“Tagore是诗人而兼音乐家的,他的诗中,含有一种乐曲的趣味,我很愿意学他”,“Tagore说:‘只有乐曲,是美的语言。’其实诗歌中音调好的,也能使人发生同样的美感——,因此我便联想到中国一句古话,郑樵说的:‘诗者,人心之乐也。’和近代文学家说的:‘诗是心琴上弹出来的谐唱。’”同样是诗人而兼音乐家的叶伯和,不仅对新诗的“自然音调”有很深体会,领悟到“按照富有音乐性的词句的先后关联,而不是按照一架节拍器的节拍来写诗”;而且已隐约窥得不可孤立讨论新诗的外在韵律形式、必须感受其与内心情感相谐的堂奥。后一个观点,徐志摩直到1926年、戴望舒直到上世纪30年代才明确提出。
持论至此,并不为让郭沫若、胡怀琛、叶伯和等与胡适争夺中国新诗始祖地位,更不为确定到底何年才是中国新诗元年,而重在展现开端应有的纷繁、多元的开放性质。萨义德说:“人的心智在面对一个遥远的过去时,更愿意去想象一个强大的创始性人物,而不愿在无数解释的文本里细细查究。”“在一般的话语中,提到一个开端(或一般性书写中的多个开端),就意味着有一个具体的日期或时间要被固定下来,这种做法,相比于我对开端怀有的巨大热忱而言限制性太强了。”中国新诗“百年”的计量之所以无稽,正是由于它折射出对权威者的盲目迷信、刻舟求剑的僵化思维和不加深思的草率态度。
三、悖于事实的进化观
“开端”渐渐生长,便理所当然地与物理时间轴上的相关者存在“先后顺序”或“世代更替”的关系吗?萨义德在他的《开端:意图与方法》这部晦涩又蓄积着惊涛骇浪般力量的沉思之作中,不仅否定了这种线性关系,而且认为,“从我所说的开端生发出的秩序,我们甚至无法用一个图像来准确把握”。韦勒克也曾否定进化论文学史观:“并不存在同生物学上的物种相当的文学类型,而进化论正是以物种为基础的。文学中并不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发展和退化这些现象,不存在着一个类型到另一类型的转变。在类型之间也不存在生存竞争。”尊重和勘探开端所带来的“无以名状”的漫漶情形,对中国新诗的理解便可进入更加宏阔、更具启迪性的境地。
很难想象一个完全从无到有的开端。上帝在重新创世之前也选择了诺亚,没有方舟里的旧世界就没有新世界。中国新诗亦然。俞平伯的《冬夜》常被人诟病为旧词曲所束缚太过,胡适的自我批评也正适用于此:“缠过脚的妇人,虽然努力放脚,恐怕终究不能回复那‘天足’的原形了”;但闻一多敏锐地指出文化遗产的双刃性:“词曲的音节,在新诗底国境里并不全体是违禁物,不过要经过一番查验拣择罢了。”他说,《冬夜》中固然不少对旧词曲“生吞活剥”以致“破碎”、“喽唆”、“重复”之作,但也不乏《凄然》这样因“查验拣择”得当而“不滑,不涩,恰到好处,兼有自然和艺术之美”的佳篇。再如,民间的歌谣在中外都是很古老的文体,但胡适、刘半农、周作人、沈尹默、钱玄同等文学革命的闯将们深谙其赋予中国新诗以别样生趣的奇妙魅力,发掘它点铁成金的可能。若从空间视角考察,所谓“横的移植”也激活了中国新诗的关窍。胡适说:“《关不住了》一首是我的‘新诗’成立的纪元。”这句话除了再次印证他本人不认可1917年在《新青年》上发表的8首诗是真正的新诗之外,也有力地说明西方现代主义诗歌对他突破创作瓶颈、乃至对中国新诗质变的重大意义。仅沿此寥寥数例伸展,已可见中国新诗的开端以形态各异的根须扎入词调、民歌、翻译等土壤汲取营养。
如果“查验拣择”得当,中国古典诗歌也同样给予新诗以滋补和灵感。闻一多、戴望舒、何其芳、卞之琳、李广田等的创作和理论都从古典诗歌中获益匪浅。冯文炳对中国新诗的追根溯源特别引人注意。他离开晚清“诗界革命”、胡适起手“尝试”时都曾领受启发的元白流脉或宋诗经纬,认为晚唐温李的诗歌“倒有我们今日新诗的趋势”。尤其李商隐诗中的“典故就是感觉的联串”,“颇难处置,我想从沙子里淘出金子来给大家看罢,而这些沙子又都是金子”,“粒粒沙子都是珠宝”。“他们都是自由表现其诗的感觉与理想,在六朝文章里已有这一派的根苗,这一派的根苗又将在白话新诗里自由生长”。冯文炳对晚唐诗歌的这种体认不但将中国新诗的“前例”远推至六朝,而且接通了西方象征主义的诗歌观:“诗的境界或诗情是由一种新生的感觉、一种感知一个世界或众多关系的完整体系的意愿组成的”。
然而,箭矢再度折返,在已经被新文学史家们公认为中国早期象征主义诗人的王独清、穆木天等的作品里,有学者依然洞见了“陈腐的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的意象”,“象征主义抒情主体与物象之间建立的神秘的暗示关系不见了,冷色调的抒情最终还是沦为一种意象式的说明”。而李金发虽然“醉心于西方象征主义,但……更难改变的则是民族的审美心理结构”,他的“许多‘现代’味是黏上去的”,难掩其“委曲求全”“欲言又惧,如履薄冰,战战兢兢”的处世心态,甚至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常有的“臣妾人格”。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实践者们不少是于老旧的底色上“取舍‘现代体验’的”。更何况,这些“现代体验”还曾被各种非文学的因子长期、多次地阻断和破坏,呈现出愈发支离破碎、往复徘徊的景象。今天,尽管“后学”早已在中国引起关注和思考,但依旧有人张皇地抓住新诗的外在韵律格式不放,依旧有诗作停留于单薄的直抒胸臆或符号化的意象式说明,依旧有抒情主体映照出卑怯的“臣妾人格”。而“现代”,正是中国新诗之“新”的题中之意。从这个角度观察,中国新诗的开端分明又以扭曲、错综的姿态蔓延到现在,乃至可以预见的未来。
因此,开端(特别是现代的开端)意味着“多层次的‘分散的统一’(coherence of dispersion)”,并且,它“是一种行动,和所有其他行动一样,它与一个活动领域、思维习惯、有待实现的条件相联系”。中国新诗并未遵循机械的进化观滚滚向前,目前最需要的不是仪式性的欢呼,而是切实有益的耕耘。
四、急功近利的根底
那么,人们何以会如此轻易地接受“新诗百年”的概念、并心甘情愿为其支付巨大的人力、财力呢?除却受缚于刻板的思维定式之外,是否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上世纪30年代有一场著名的“京派”与“海派”之争。发难者沈从文认为立志投身文学事业者应有“厚重、诚实、带点儿顽固而且也带点儿呆气的性格”,切不可表面“附庸风雅”,实际却沦为“文学的票友与白相人”。其后,鲁迅又将“京派”和“海派”各打五十大板,认为它们的本质乃“官的帮闲”和“商的帮忙”,更是著名的诛心之论。如何评价“京派”和“海派”显然并非本文旨趣,但“新诗百年”成为举国诗界为之劳心劳力的运动,也正反映出其制定者和操办者缺乏一点儿“厚重、诚实”、“顽固”、“呆气”,而太多一点儿玩票和白相态度,甚至难免“假呼群保义之名,成个人事功之私”的嫌疑。对于今天很多生存于政绩指标和市场诱惑之中的文学机构和文学从业者而言,根本不及或不愿深思熟虑中国新诗的开端问题。他们所急需的常常是尽快从半空牵下一两个概念的线头,再迅速填充大量文本和活动,便企图织就文学或文学以外的繁荣锦绣。
有关“新诗百年”的社会实践在客观上有利于大众对中国新诗的认知和传播,在具体问题的研讨中也不乏有价值的思考和写作,但它所激发的参与热潮依然尚不及巴赫金所说的“狂欢”。在“新诗百年”所触发的各类选本和一系列评奖、研讨、朗诵等活动中,人们缺乏追求平等性的自觉,没有充分警惕话语权力在其中的渗透,同时放纵和鼓励着贪婪的入史情结。
只有深入探索和体悟“开端”的究竟,才有可能理性正视中国新诗目前仍然处于漫长而多舛的开端这一事实,从而不再满足于狂热的文学生产所带来的肤浅、虚妄的成就感,明白“静”之于“虚热闹”、“内化”之于“外面的架子”的难得。文学个体不能只是被喧哗与骚动裹挟着推进甚至主动媾和,而必须在生存之基上作为相对独立的清流汇入其中加以抗衡。不妨多咀嚼傅雷对艺术所提出的“往深处去”的要求:“我们需要镇静与忍耐”,“深思默省,锻炼琢磨的功夫尤其应当深刻”。在史料考证方面,保持对现有文学史的质疑精神,重新去扎实地扒一扒一页千钧的故纸堆;在理论、批评方面,“进行新诗文本的考论,从中提取已经由优秀诗作体现出来的文体特征”,清醒地懂得“作为某种‘整体性’而虚拟并描述的新诗‘文体’的历史构架,则成为十分可疑的空中楼阁”;在创作方面,潜心求教于古今中外不同风格之杰作,专注于对世界和自我内部的省思,多产出几位胡适所谓“白话京调高腔之中”的“陶谢李杜”。
开端的魅力还在于“反复不断地经验开端和再开端”。在努力使现有开端成熟的同时,于真正诗学意义上为中国新诗激发层出不穷、独具个性的再开端(而不是轻率浮躁地喊着向“第二个百年”跃进的口号),正是一切诗学行动应有的长远诉求和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