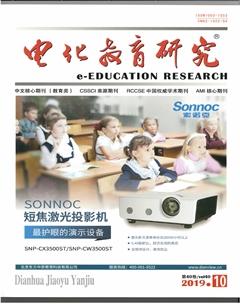基于微信的跨文化网络交流互动深度研究
赵婴 何克抗


[摘 要] 基于微信的跨文化网络互动为外语学习者和母语学习者构建了合作学习的平台。研究从互动数量、活动设计、文化环境等三个维度进行分析,考察微信支持的跨文化交流活动中影响互动深度的因素,探讨推进互动深度的有效途径。研究发现:(1)交互数量与交互深度并无直接关联。有时交互数量多,深度互动的内容反而少。(2)活动设计对交互深度有直接影响。有具体任务的活动为深度交互创造了条件。(3)母语学习者的参与并不能直接深化互动。
[关键词] 微信; 跨文化交流; 交流互动; 互动深度
[中图分类号] G434 [文献标志码] A
一、引 言
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交际式语言教学(Communicative Language Teaching)明确提出,交际能力是语言水平的评价标准之一,而交际能力要通过交流来获得[1]。学习者在交流过程中通过磋商、反馈、评价等方式进行合作学习,实现知识构建。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基于智能手机的教学方式逐渐进入高校课堂,微信等智能手机软件可以达成学习者之间的实时交流。微信在教学中的使用具有多样性,如整合微信聊天、朋友圈分享、公众平台互动等功能搭建独立的学习系统[2-4],或与传统课堂结合构建混合式教学模式等[5-6]。外语课堂中,微信可以把身处异地的外语学习者和母语学习者联系起来,在真实语境中通过合作学习锻炼交际技能。如何搭建微信跨文化合作学习平台,推进微信交流互动深度正逐步成为外语交际教学领域关注的重点。
二、网络交流活动中影响互动深度的因素
学习者通过合作学习平台交流时,互动深度对学习效果和知识构建有直接影响。已有研究表明,网络交流的互动深度与互动数量有关,互动达到一定数量时才有可能产生深度交流,但是,博客等非实时交流中,互动数量与互动深度不一定成正比,大多数交互停留在浅层次[7]。本研究中,中澳学生通过微信实时交流,互动数量的计算方法有别于博客等非实时交流形式,而且表情符号﹑小视频等的大量使用会造成语义模糊。此外,外语学习者与母语学习者交流时,由于语言水平和文化差异等原因,发言数量可能受到限制。跨文化微信实时交流与博客等非实时交流,以及没有母语学习者参加的外语学习者之间的交流有相似之处,但也存在不同。微信辅助的跨文化交流中,交互数量是否影响交互深度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除交互数量外,梁云真等提出,活动设计也是影响网络交流互动深度的因素之一,并不是所有的交互都有助于学习,协作问题解决活动能够促进互动深度,提高学习成效[8]。协作问题解决活动的设计精髓在于促进社会化协作,制造并利用学习者之间的信息沟(Information Gap)生成交流需求,促使学习者主动进行互动。针对问题解决的活动设计应设定具体时间、任务、目标和成果,越具体越好[9]。本研究认为,真实语境下外语学习者和母语学习者之间天然的信息沟为主动互动创造了基础,跨文化微信实时交流符合协作问题解决活动的基本定义,仍需探讨的是,活动设计中任务及目标成果的设计差异是否对互动深度有影响。基于环境论的研究证明,协作学习共同体的活动环境是影响活动效果的因素之一。活动环境包括网络支撑环境和文化环境。崔向平等研究了微信支持的校际协作学习活动,发现学习者之间的深度互动占比超过浅层次互动,证明微信平台环境能够有效支撑深度交流[10]。这项研究没有讨论文化环境因素,如学习者的背景特征等对互动深度的影响。与此项研究不同,任英杰等关注了学习者所构建的文化环境对交流的影响,发现参与者自身知识背景和经验的多样性对群体交流的影响有“双刃剑效应”:多样性引起的差异可能为团队带来创新度和决策质量,但也可能成为深度互动的障碍[11]。可以假设微信交流中,相对于网络支撑环境,母语学习者的参与作为文化环境,对交互的影响更为重要。
因此,本研究尝试利用中外文化差异形成的天然信息沟激发交流兴趣,通过微信支持的协作问题解决式的教学活动,从互动数量、活动设计、文化环境等三个维度分析影响微信交流互动深度的因素,探讨推进互动深度的有效途径。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背景
本研究依托首都师范大学英语教育专业课程“网络辅助国际交流”,该课程通过信息技术搭建跨文化交流平台,锻炼学生在真实语境中使用英语的能力,同时,提升文化意识和交际水平。2017年开始,首都师范大学英语教育专业与澳大利亚某大学教育专业合作,中澳教师共同制订教学计划,双方学生通过微信以文字聊天的形式合作完成学习任务。研究发现,交流者文字聊天时使用的语言更接近口语而非书面语,因此,文字聊天与面对面交流有较高可比性[12]。
(二)研究对象
2017学年选修该课程的中澳学生共67人,且均自愿参加本研究,其中,中方学生45人,澳方学生22人。双方均为大一新生,中方学生的专业是英语(师范),澳方学生的专业是教育学。参照高考英语成绩及入学水平测验成绩,认定中方学生的英语水平为中等;澳方学生均未学习过中文。
中澳学生随机混合編组,共编成11个小组。其中,10个组分别包括中方学生4人,澳方学生2人;另外1个组中方学生5人,澳方学生2人。中澳双方教师2人编入全部11个组,因此,每组总人数为8~9人。
(三)研究过程
1. 活动组织与数据来源
中澳学生小组分别搭建微信群进行组内交流。交流分为无任务和有任务两个阶段:无任务阶段,中澳学生自由交流,教师只对话题选择提出建议;有任务阶段,中澳学生共同设计一次虚拟旅行并完成一篇推送文章发至课程微信公众号。除第一周课程介绍、建群及最后一周中方学生单独上传推送文章外,中澳学生交流活动共进行14周,每次90分钟。中澳双方教师共2人进入所有小组的微信群,但不参与讨论。交流结束后,保存并下载各组文字讨论记录,用于文本分析。
第一周安排“破冰”活动,中澳教师向各自学生介绍教学目标、活动安排及交流主题。中澳学生混合编组,以组为单位搭建微信群并在群内进行自我介绍。建立课程微信公众号,用于发布课程通知。第二至八周为无任务讨论阶段,中澳学生自选话题,自由交流。建议选择与中澳两国文化及社会生活相关的话题,如民风民俗、传统节日、校园生活等。第九至十五周为有任务讨论阶段,中澳学生相互协助对方设计一次以了解对方国家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为目的的虚拟旅行。中方学生目的地为悉尼,澳方学生目的地为北京。全程共3天,需安排5项参观游览活动,且至少一项活动是旅行者之前从未体验过的。此外,还需协助旅行者挑选1~2件具有当地特色的礼物带给家人。交流过程中,各小组内中方学生合作完成一篇微信推送文章,用英语介绍虚拟旅行活动中涉及的中澳两国社会、文化、日常生活等方面的情况。澳方学生不需要制作推送文章,但应协助本组中方学生收集信息。第十六周为活动总结,各组完成推文,并由中方学生上传至课程微信公众平台。
2. 互动深度评价方法
本研究以Gunawardena等提出的五级交互分析模型(Interaction Analysis Model,简称IAM)为文本分析的基本依据,判定微信交流中的互动深度[9]。在五个级别中,前两个级别知识建构水平较低,后三个级别知识建构水平较高,因此,前两个级别归类为浅层次互动,后三个级别为深层次互动。
由于Gunawardena的模型大多应用于非实时交流,其指标更适用于分析网络论坛中的交互知识构建。本研究中,学习者使用微信进行跨文化实时交流,交流内容呈现出与网络论坛不同的一些特点。首先,网络论坛发帖以列表的形式呈现,每个发言帖引发的讨论以回复前帖的形式纵向陈列在“父帖”之后,形成清晰话题链;而微信交流可以多人同时发言,话题相互穿插,难以形成清晰的话题链。其次,论坛发帖人通常直接针对主题表述观点,即便是呼应他人之前的发言,一般也无须闲谈客套。微信交谈则不同,参与者通常相互打招呼并闲谈几句之后,才针对学习内容进行交流。交流过程中话题可能发生自然改变,转向与主题不相关的内容。此外,论坛发帖属于非实时交流,发帖人有时间思考并组织语言,因此,每个帖子的表述相对较完整。微信交谈与面对面交流相似,参与者看到对方发言后实时做出回复,发言呈口语化趋势,碎片化表述多。另外,表情符号、小视频等意义含糊,令话题链不清晰。
基于以上差别,本研究在Gunawardena的五级模型基础上,针对微信交流的特点增加了一项“无关互动”,形成六级编码。第一级(S1)和第二级(S2)为浅层次互动(Surface Interaction/S),交流参与者相互分享、描述并比对信息(S1),通过对比发现概念、描述中不一致之处并加深认识(S2)。第三级(D1)、第四级(D2)和第五级(D3)为深层次互动(Deep Interaction/D),交流者通过意义协商进行知识的群体建构(D1),对新建构的观点进行检验、修正(D2),最终就新建构的观点达成一致并尝试应用新观点(D3)。第六级为无关互动(Theme-Unrelated Interaction/N),互动目的与学习内容不相关,参与者通过互动表达情感、情绪,如吃惊、高兴、道歉、打招呼、道别等。
依据编码方案,从发言频次和发言字数两个角度进行数据统计。微信交流参与人每次陈述结束,点击“发送”键后生成的内容为一条发言。发言人为辅助表达语义所使用的图片﹑短视频﹑文档链接﹑表情符号等若单独成行,则计入发言条数。不同于论坛发言,微信发言中多人、多话题实时交错进行,发言者需要及时相互呼应以保证交流顺畅。来不及输入整段文字时,通常使用多个语言片段或图片、表情符号等快速表达语义,因此,可能出现发言频次高、但字数少的情况。本研究在统计发言频次的同时也对发言字数进行统计,以相互佐证。
四、数据统计与分析
(一)微信支持的跨文化交流互动整体情况统计
活动过程中共收集到2816条发言,共计26798字。全部发言中,浅层次互动S1 、S2两项合计1396条,占总发言条数的49.58%,可见近半数发言处于浅层次互动阶段。浅层次互动中,分享、描述信息的S1阶段发言频次达到1037条,发现并探究冲突的S2阶段发言仅359条,说明大部分交流内容未引发冲突,或交流者未对冲突进行协商进而发现解决冲突的办法,而是把问题搁置了下来。
交流过程中冲突少或交流者搁置冲突,导致深层次互动发言频度和字数相应减少。交流过程中,D1、D2、D3各阶段发言频次之和占总发言频次的29.83%,其中,D1阶段略高于D2 、D3阶段。说明群体建构新观点时的讨论多于对新观点的检验、修正,及应用。
与学习内容无关的交流频次占总频次的20.60%,字数占总字数的25.85%。这部分交流主要是指打招呼和道别、正式开始前的闲谈及交流过程中的情绪、情感表达等。
(二)影响微信支持的跨文化交流互动深度的因素
1. 互动数量
根据各微信群发言频次平均值563条和发言字数平均值5360字,將微信群分为两组,发言频次及字数均高于平均值的群为组1,发言频次及字数均低于平均值的群为组2。互动数量与交互深度的独立样本U检验结果见表1。
发言频次和字数较多的微信群组1虽然比较活跃,但大多数互动属于浅层次互动。与之相比,发言频次和字数较少的微信群组2深层次互动更多。深层次互动与浅层次互动的区别在于对知识的群体构建,包含从提出新观点到应用新观点的全过程。新观点一旦提出,围绕新观点的互动就进入了深层次。没有新观点的互动,而是停留在信息交换阶段,交换过程中因信息不一致产生的冲突没有受到关注,即使参与者发言频繁,这类互动仍是浅层次互动。浅层次互动较多的微信组中,无关互动较少。无关互动是实时交流特有的,目的在于表达情绪、情感及话题维护。
发言量大的组1中,55.34%的互动停留在最浅层S1级,高于发言量少的组2中S1级互动的占比,说明发言量大的微信群中大多数讨论内容属于浅层次互动,未能产生新观点,也非无关互动。这类互动的特点是简单附和他人的发言,缺乏独到的见解,例如:“OK、good、I agree”等。理解困难或看法不一致时,也不能对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并提出有建设性的意见,例如:“I don't know about what you said, but it's fine。”与发言量大的组1相比,组2中深层次D1级互动占比较高,说明发言量较少的微信群构建新知识的讨论较多,而且达到D3层级,即达成并应用新知识的互动也较多。这类互动的特点是讨论中出现的问题及时得到反馈,发言者通过交流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并最终解决问题。例如:中澳学生谈到各自国家的民族构成,对“Nation”和“Nationality”两个概念的理解产生分歧。中方学生认为:“56 nations constitute China, but China is one nation。”澳方学生回复:“It's confusing for outsiders, I think you should say 56 nationalities but not nations。”中方学生并未立即认同,反问“56 nationalities in one nation?”多次往復交流之后,中澳学生逐步梳理清楚“Nation”和“Nationality”两个概念,最终达到了群体构建新知识的深度。之后,双方学生依据共同建构的新知识就各自国家的民族问题展开讨论,没有再发生“Nation”和“Nationality”的认知冲突。
2. 活动设计
根据教学安排,第二至八周为无任务周,学生自由交流;第九至十五周为有任务周,中澳学生相互协助,设计一次到对方国家的虚拟旅行。无任务讨论和有任务讨论两种交流活动中,交互深度的独立样本U检验见表2。
有任务周和无任务周相比,浅层次互动数量的占比无显著差异,不论是否有任务,各微信群的交流均有一半左右属于浅层次互动。有任务时,深层次交互及无关互动的数量多于无任务时。有任务时,D1阶段的占比高于无任务时,说明围绕制定旅行计划这一任务进行讨论时,出现的新观点较多,相关讨论也更频繁。例如:双方学生应在对方国家进行一项从未体验过的活动,设计这项活动引发了较多的深层次互动。有中方学生提出穿着澳大利亚传统服饰(Traditional Clothes)拍照,澳方学生问:“Do you mean traditions or the kind of things Australians wear today?”中方学生回复:“I mean if there's a shop in your neighborhood selling traditional clothes, we can take some pictures from the shop。”澳方学生回答:“We don't really have big traditional clothes store, even in Sydney……You want to look in a museum?”双方学生对什么是传统服饰有不同见解。经过深层次讨论,逐步达成共识,解决了问题。有任务交流中,因深层次交互数量多,无关交互的占比降至8.71%,低于无任务时的37.76%。
3. 文化环境
根据环境论原理,交流参与者搭建的文化环境是影响交流效果的因素之一。跨文化微信交流中,文化环境具有特殊性,外语学习者与母语学习者之间知识背景和经验的多样性为交流增加了难度。学习者外语水平的局限性可能导致母语学习者在交流中占据主导地位,产生过多的语义协商,从而影响交互深度。因此,母语学习者的参与情况是跨文化交流中文化环境的指标因素,也是影响互动深度的重要因素。本研究中,澳大利亚学生在各微信群发言频次均数为247条。把微信群分为2组,澳大利亚学生发言频次高于均数的为组1,低于均数的为组2。对两组进行独立样本U检验,结果见表3。
澳大利亚学生发言较多的微信群中,浅层次互动较多,深层次互动较少;中国学生发言较多的微信群中无关互动较多,主要体现为大量使用表情符号、动图等表达情绪、情感,与讨论主题无关。澳大利亚学生发言较多的微信群中,最低级别的浅层次互动S1的占比达到75.66%,说明超过四分之三的讨论为浅层次互动,没有产出新观点、构建新知识。在与澳大利亚学生交换信息时,中方学生更容易接受澳方学生的观点,使得澳方学生处于主导地位。例如,澳方学生提到茶的口感“Bitter”,中方学生说:“You use bitter to describe tea? We say fragrant。”澳方学生回复并举例说身边的亲友喝茶都要加糖。中方学生说:“I see。”话题结束。这段讨论中,澳方学生发言量超过中方学生,中方学生虽然发现了中澳文化和语言表述的差异,但没有对差异进行探究,而是直接接受了澳方学生的观点。
五、总结与讨论
跨文化微信互动与其他形式的实时或非实时网络交流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本研究通过分析我国外语专业大学生与国外母语大学生的微信交流,发现影响跨文化微信互动深度的因素主要有以下特点:
首先,交互数量与交互深度并无直接关联。从发言频次和字数看,交互数量多时,深度互动的内容反而少,无法实现深层次的知识交流。这不是跨文化互动特有的问题,没有母语学习者参与的学习共同体也存在类似问题。交互数量多但深度互动少也不是微信交流特有的,其他类型的网络交流活动如QQ、博客等也同样存在交互数量虽多、但质量堪忧的现象[8]。
其次,活动设计对交互深度有直接影响。有具体任务目标和成果要求的交流为学生确立了明确的学习方向,围绕如何达成学习目标展开,一旦出现交流障碍,必须通过语义协商解决问题,从而实现学习目标。这个过程为深度互动创造了条件。没有具体任务的交流类似 “闲聊”,虽然可以弥补中外文化差异带来的信息沟,一定程度上促进学生了解对方国家的文化,但无益于推进互动深度。
同时,作为跨文化交流的文化环境因素之一,母语学习者的参与并不能直接深化互动。外语学习者受语言水平等因素影响,与母语学习者交流时即使发现信息冲突,通常也會选择同意母语学习者的观点,放弃对问题进行深度探讨。这种情况下,母语学习者占据了交流的主导地位,不利于学习者平等参与知识构建。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学生更多使用表情符号等微信特有的功能代替语言表达,这种做法生动有趣而且能够增加交互频率,但是有些表情符号语义不明,容易引起母语学习者的误解,甚至使讨论偏离主题,影响学习目标的达成。
外语学习者与母语学习者进行跨文化微信交流在高校外语课堂中尚不多见,目前相关研究仍很有限。本研究根据教学实践做了初步探讨,存在的问题较多,包括研究设计受限于教学方案、周期较短、样本量不够大,特别是澳方学生数量有限等。后续应开展长期教学实践,积累微信使用和跨文化交流等两方面的经验。
[参考文献]
[1] BROWN H D. Principles of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M]. New York:Addison Wesley Longman,2000.
[2] 刘虹,李煜,孙建军.基于微博微信的高校社交网络信息传播特征与效率对比分析[J]. 现代情报,2018(4):3-11.
[3] 王丽,戴建春.基于微信的交互式翻译移动教学模式的构建与应用[J].外语电化教学,2015(3):35-41.
[4] 范文翔,马燕,李凯,邱炳发.移动学习环境下微信支持的翻转课堂实践探究[J].开放教育研究,2015(6):90-97.
[5] 徐梅丹,兰国帅,张一春,孟召坤,张杭.构建基于微信公众平台的混合学习模式[J].中国远程教育,2015(4):36-42.
[6] 涂相华,薛锡雅,曾志平,罗子健,骆晓鹏.“WECO课堂”:基于微信小程序的师生交互系统[J]. 现代教育技术,2018(5):109-114.
[7] 严亚利,黎加厚.教师在线交流与深度互动的能力评估研究[J].远程教育杂志,2010(2):68-71.
[8] 梁云真,朱珂,赵呈领.协作问题解决学习活动促进交互深度的实证研究[J].电化教育研究,2017(10):87-92.
[9] 孟汇海,杨晓宏,崔向平.基于网络的校际协作学习研究现状与趋势分析[J].电化教育研究,2014(12):56-62.
[10] 崔向平,李东辉.促进深度学习的校际协作学习活动设计:理论框架与个案研究[J]. 高等理科教育,2017(4):39-44.
[11] 任英杰,徐晓东.基于差异的校际协作教研的考察与思考[J].中国电化教育,2010(12):99-103.
[12] 赵婴.文字聊天和视频会议对英语口语交谈策略影响的一项对比研究[J].电化教育研究,2011(10):80-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