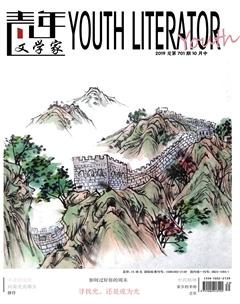朝鲜时期漂流文学作品中的中国江南形象
全银花
摘 要:朝鲜时期漂流文学作品的作者均不是主动对中国行使贡使的行为,被动情况下他们的行为甚至被理解为倭寇。他们眼中的中国形象都是在自己原有印象的基础上,结合自己在中国的所见所闻综合得到的。中国形象的确立是作者基于自身知识的基础上形成的,需要结合燕行录作者们的记录辩证地考察。
关键词:漂流文学;朝鲜时期;江南形象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29--01
从根本上说,漂海录与燕行录最大的不同,一个是民间行为,一个是官方行为,对中国形象就会有所偏差。具体表现在几个方面:首先,明清两朝“恩人”形象。由于朝鲜时期漂流文学作品的作者在中国经历可以说是国际援助的一种。其次,日本侵略者形象。朝鲜时期漂流文学作品时间跨越了15—19世纪,其中16世纪末的壬辰倭乱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再次,对清朝认识的“二重性”。清朝从后金而来,难免会给朝鲜人留下“丙子之乱”的遗患,而事实上,清朝不仅保留了明朝先进优秀的文化,而且有所继承和发扬,这对朝鲜学者的精神世界又是巨大的冲击。
一、对中国江南文化的认同
从中国与朝鲜两国的交往来看,朝鲜对中国文化有着强烈的认同感,“华夷之辨”,到后来的“华夷一也”,其实质就是文化的区别和统一,中国和朝鲜自古以来就有着频繁的友好往来,而在双方文化交流方面亦是如此,朝鲜对中国儒家经典的学习和认同,对中国儒家经典进行重新刊印,将中国一些著名的典籍编进自己国家的书籍当中。这些行为无不反映了朝鲜对中国文化的倾慕。对于崔溥而言,他在中国的行程中,介绍了许多古迹:宁波府贺知章少时所居地;绍兴府娄公埠上天章寺前兰亭王羲之修禊处;杭州吴越国宋高宗南渡迁都之地临安府;栖霞岭口之岳鄂王墓;东坡所撰龙山表忠观碑;司马温公隶书题字之南屏山等。
这些名胜古迹的记载,就是对中国文化重视和认同的重要佐证。由于清朝在后金时与朝鲜有过刀兵相见,所以现存的燕行录中,朝鲜士人对清朝称呼为“清国”、“彼国”、“彼人”等贬低词汇随处可见。而在《乘槎录》中,崔斗灿对于清国不称“清朝”而是“中国”,对于清民不称“清人”而称“华人”,且通篇未见“夷国”、“彼国”等鄙夷字样。这一称呼的变化可以说明,经过了一个半世纪的发展,清朝已经从文化上征服了朝鲜士人,也可以说是朝鲜对中国文化的认同。
二、对中国江南文化的审美偏差
审美是根据不同人的社会背景、文化修养等决定的,去欣赏、品味或者领悟事物本身存在的美感。所以,审美观点是因人而异,因事而异的,每个人的出发点和引起共鸣的点不同,审美结果也会有所不同。作者出身和学识不同,特别是因为每个人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所以,对中国文化的审美领悟也有所不同,也就产生了审美偏差。
崔溥的《漂海录》中这样说道:“我国人物,亲见大江以南者,近古所无。”在房屋的描述中,他这样写道:“江南盖以瓦、铺以砖,阶砌皆用砾石,亦或有建石柱者,皆宏壮华丽。江北草屋,矮小者殆居其半。”对中国此時南北方的建筑做以对比,明显倾向于南方的华美建筑。崔斗灿描写浙江上虞县:“其土地之丰衍,物产之美好,村落之繁华,笔所不能记,画所不能摸。”到了江苏后,又有“良田沃土,连畦接畛”、“诚楼观之第一指也”等记录。语言的描写可以说是入目之处,一片繁华景象,可见江南地区的景象给他的震撼之大。后来,他回到朝鲜,途径练光亭,登亭远眺,发出感慨:“市井之栉比,城郭之壮丽,差不及浙。而江山之形胜,则曲逆洛阳之间也。”可见,这时的朝鲜与中国北方的城镇发展状况基本一致,但是相比江南来说,差距就相对过大。
三、对中国江南社会的崇拜
崔溥的记录很有比较性和代表性,对于文化知识的水平而言,“江南人以读书为业,虽里閈童稚及津夫、水夫皆识文字。臣至其地写以问之,则凡山川古迹、土地沿革,皆晓解详告之。江北则不学者多,故臣欲问之则皆曰:‘我不识字。”张汉喆的《漂海录》中记载了当时的安南大船,十分先进:“船之大异常,所谓如蔽天之山者也。”上船之后,发现各种器物齐全:“见船如巨屋,房室无数,联轩交栊,叠户重闼,器玩什物,屏障书画,俱极精妙,不可殚记。”林氏等人带他各处参观,发现船共四层,用楼梯连接,“船之大,广可百余丈,其长倍焉”。人住在最上面一层,房屋相连。下面三层用来摆放物品。一层养蔬菜和鸡鸭,还有杂物。二层主要放粮食和日用品,也蓄养牛羊猪。最下层为船底,存放张汉喆的小船。船上还有盛水的器皿,“其大若十石缸”,且“盈器之水,用之不竭,添之不溢”。最下另有一层有船舱与海洋相通,可以随意开合,小艇可以随时出入,可见当时东亚的造船技术十分高超,这让张汉喆一行人大开眼界。
朝鲜时期漂流文学作品的作者在中国的经历,也对中国的壮丽河山产生了倾慕之情。崔斗灿在《乘槎录》中对中国江南的富庶极尽描写,路过慈溪县:“树竹之饶,芦荻之胜,诚水国之物色也。”对于中国江南的丰饶,他使用了大量的笔墨和篇幅,却并未对朝鲜的国家的自然景象和社会状况做以记录,可见在记录之时,他被中国社会的壮丽景象所震撼。回到朝鲜后,他的民族情感逐渐占了上峰,发出“差不及浙”的感慨。而事实上,中国江南的繁华的确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常想周游江南”,甚至将自己的草屋命名为“江南亭”。他的这种崇拜心态显露无疑,即使不能再次回到江南,不能拥有那些美好的事物和景色,也假想一下自己的生存环境,聊以自慰。
参考文献:
[1]葛振家,《漂海录》学术价值再探,《韩国学论文集》,1994年第2期,第47页。
[2]戴琳剑,《乘槎录》中对清认识的二重心理管窥,剑南文学,2015年第4期,第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