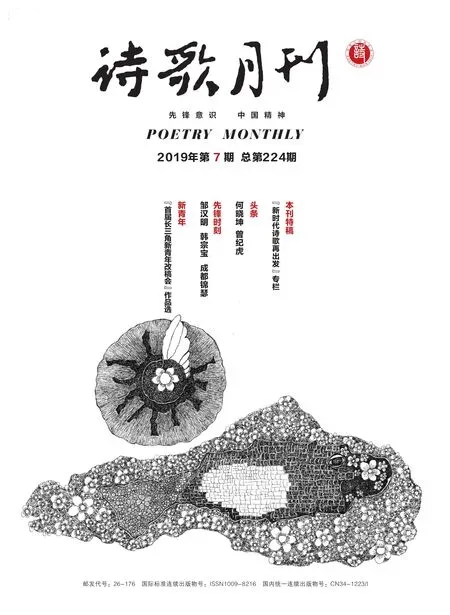星芽的诗
星芽
蜗牛先知
没有谁比蜗牛了解落地的树枝
它们甚至还能闻出树枝是几时落地的
蜗牛开心地爬过去
我就得趁此时机问它
树枝的性别?
树枝能作为维纳斯女神失去的手臂吗?树枝陷入喉咙
我们深埋多年的疾患居然得到了根治
树枝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形态 它们轻易便计算出了古人身体的秘密
蜗牛开始难过起来 泪将地面的树枝浸没
蜗牛不说话 轻轻地浮在上面
没有一点光
花喜鹊
花喜鹊放大了胆子去踢树枝
捉弄它 认为树枝也应该是有羽毛的
要是树枝真长出了羽毛
它会飞得比花喜鹊还要有劲吗
它诏令迫于禁声的树枝都飞离树木的躯干
几只喜鹊也都笔直地射远 一只脚落地
打旋
依然像个大人那样站直
这只能说明橘红色夕光下喜鹊的腿脚
已经奇异般地被拉长了
它不再需要借助树枝的影像来反映
真实的身体
喜鹊拍拍胸脯
“啪”的一声爆开
羽毛上致命的花点散落一地
孙猴子
三百年前 直升机还没有发明
气球被用来套在猴子的屁股上 它们拿糖分稀释寂寞
把动物园及尿液刷成蓝色
想打飞机可以把猴腿驾在人们的脖子后面
有人当马骑 猴子整年都在兴奋得叫唤
抑郁症消失了大半
却忘记了返回动物园的路
猴子野性的脸谱好像在预示着什么
但我从不敢多疑
对蹊跷的事情也得保持缄默
比如 我经常看到高个子的人走路
其实就是猴子与人身体的简单拼合
猴子怀孕了 肚脐眼下坠 它屁股上的气球被钢针戳破
我们由于惯性一下子翻跃到十万八千里外
给暗地里发功的猴子命名为“悟空”
长颈鹿
我扭过头来检查这些长脖子的动物
有没有受过意外的伤害
我修理自行车的时候也是像这样旋转头颅
而接下来的区别是
对于长颈鹿 我的眼睛还得一直沿着脖子
往白云的方向攀爬
它们实在是太长了
抵着这个节气的阴雨天
我的视力不论停留于哪一段斑纹它们都会继续长长
直到成年
自我从家族离去
不断地用卸下镣铐的双手攀登城市的楼层
下面的车水马龙一次次发出长颈鹿的啼啸声
我才怀念起这些曾经哺育过眼睛的巨大动物
灯红酒绿的社会更容易让自己产生来自身体的种种不安
而在小的时候 我并不会怀疑那几只陪伴过我的长颈鹿
即使它们的角把天戳穿了
没有洒下一滴真实疼痛的雨点
刺猬的价值
我揣摩刺猬滚过的地方有没有讨论的价值
它实际滚过的时候我之前的揣摩已经失效了 既然
刺猬现在身居我前端
又朝更远的地方爬行
它便也失去了我想去讨论它的价值
刺猬本来是没有价值的
但是我用边界的视域将过去的它框住了
它就开始与我身体某个部位的疼痛结合起来
它滚动得越厉害我身上密集的痛感就凝聚成愈明显的浮雕
被赋予无趣的历史性
这些皆不能代表刺猬原本的价值
它的有效意志仅仅是在我身体里面形而上地投映出来
而爬远的刺猬对我是不理睬的
鸟类研究中心
鸟类研究专家未必全是飞行能手
他们仅仅爱将鸟类肢解 腿摆入表盘
脖子作为阻断他们交换各自语言的干扰信号
所以至今读懂鸟类全部身体结构的专家也没能发明出
一种可以与麻雀或者鸬鹚对话的工具
这种不存在的工具曾于我们活跃的构思里将鸟分出几条类目:
头呈四十五度仰视树枝的鸟与
借用啤酒铝盖助力弹地起跳的鸟 它们的语言是悬坠于喉骨间
呈迥异形状的飞行器
研究者也尝试按照真鸟的外貌为它们复制配偶 使鸟群生产的后代
可以成批学会人类的表演与造词方式
促使它们领会并接受我们堕落言语的指涉
我们与动物的距离因此获得了解放
变形记
二十岁的时候 我依然懂得用方块计数
咬住牙齿可以防止梦境溜走
皮囊空阔得能够捕住几只像模像样的猴子
只有自己失去了人形
踢一踢墙壁我的思想就会变成倒置的漏斗
动物从外边走进去
一圈圈坐好
不再出来
我依赖它们的形状感到身体的质量变幻莫测
戒掉了养成的规律
传统备受指责只会引发坐骨神经的疼痛
你好
我要模仿鹦鹉说话
把喉咙削得细细的 说“你好”的方式
要处在中关村的深冬使余音封存在体内冰挂子成为叙述的背景
我面对自然的墙壁练习了很多次
“你好”跑到嘴巴的外面
“你好”松脆地弹下来像是我声带以外
独立的部分
它能够自己站直
拍掉耳朵两边的双引号
不怀好意地绑架鹦鹉的舌头
鹦鹉说“你好”
“鹦鹉”柔软地垂下脖子
模仿我
使你好能够舒舒服服地
降落到人类的墙面
“鹦鹉”是构成它们的彩色背景
我们礼貌地相互致意
而语言醒目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