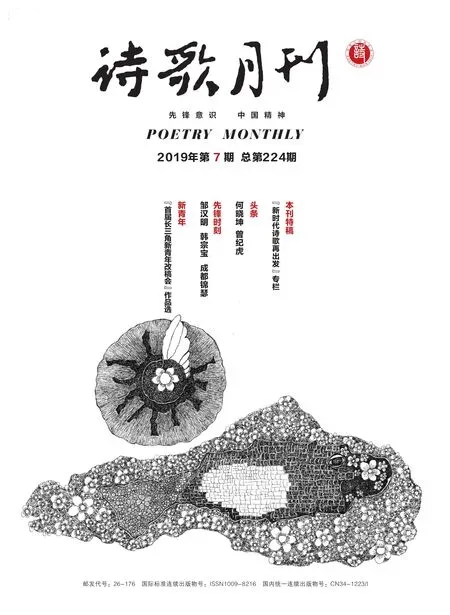新时代诗歌与中国梦写作
杨四平
我在今年《中国文艺评论》第4 期发表的《中国新诗的历史源流、发展态势与诗学反思》里说:“一百多年来,中国诗人除了梦想着‘合众旧诗国为一大新诗国’,还身体力行地创作以中国现代化为主旨的现代诗,以及探究如何艺术地表达中国现代化的意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中国新诗创作和理论探讨也是一个追寻‘中国梦’的艰辛历程。由于不同时代诗人和同时代不同诗人经验之不同,他们的梦想尽管各异其趣但又互为辉映,为我们创作出一个个诗意盎然的梦想世界”,“中国新诗既是‘中国梦’的助力者,也是‘中国梦’的行动者,还是‘中国梦’的有机构成者”。百年中国新诗参与、见证和书写了中国人民追寻现代化的百年历程。中国新诗为中国现代化提供了强有力的文化支撑。中国新诗是中国梦的华彩乐章。
尽管如此,总有那么一些诗人对此缺乏认识,总有那么一些诗人对此熟视无睹。还有一批诗人将中国新诗的中国梦窄化为个人性的诗学梦,换言之,他们把“梦幻诗学”下降为个人潜意识的迷梦,将听从心灵的召唤误读为任由无意识的泛滥,最终把诗写成毫无理性可言的梦呓。他们的失误在于既没有听从良心的召唤,也没有在写作中显示出良好的把控力。申言之,他们没有辩证地看待梦幻与现实、个人与时代、心灵世界与外部世界的和谐共生关系。其实,这种失误及其教训古已有之。比如,针对汉末建安时代以来,诗坛普遍流行的浮华绮丽诗风,李白在《古风》里痛心疾首地指陈道:“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废兴虽万变,宪章亦已沦”。正是由于关乎诗歌创作的法度和规矩已经沦丧,所以具有大雅气度的诗歌正声衰败微茫了。李白当年批评的诗歌流弊,在20 世纪80 年代以来一直延续至今,致使新时期、新世纪、新时代新诗的大雅正声不足而浮华绮丽大兴!因此,重建新时代诗歌的宪章,重提和续写,乃至大写中国新诗的中国梦,就成为新时代诗歌写作的新使命、新担当、新作为,并最终使新时代诗歌与中国梦同频共振、唱响强音。
我们不能把中国梦符号化和本质化。中国梦具有历史性、时代性、个体性和丰富性,但又万变不离其宗:那就是中国梦的基本内涵——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长期以来,中国新诗所追寻的中国梦停留在“凤凰涅槃”式的基础阶段,时至今日,我们已经迈进创造中国梦的发展阶段。也就是说,新时代诗歌的中国梦既与之前新诗的中国梦有着延续性,又具有它自己的时代属性和现实特征。置身于新时代的中国诗人,新时代,对于他们而言,既是同时代,也是异时代。所谓同时代,是指他们共同所处的时代语境而言的;而所谓的异时代,是从每个诗人对此独特的感受、经验和认知及其各异的诗歌表达来说的。申言之,新时代的中国诗人,每个人内心里有着专属自己的新时代,而正是这些丰富多彩的新时代汇成了新时代诗歌里的有机综合的新时代。要写出如此摇曳多姿的新时代,诗人不能置身事外,不能仅仅成为新时代的旁观者,而是要努力使自己成为新时代的一分子。由此可知,在当下中国诗人那里,新时代不止是一种社会结构,更是一种人本意识。唯其如此,新时代诗人方能为新时代培根铸魂。
以往,中国新诗在抒写中国梦时,出现了宁可粗糙也要“用力过猛”的现象;虽然不能武断地说它们是“假大空”,但“大空”之弊是存在的。正是由于此种顽症的存在,时至今日,还有不少人把抒写中国梦的中国新诗一厢情愿地指认为左翼诗歌、革命诗歌和红色诗歌。其实,后者只是抒写中国梦的中国新诗的一个组成部分,两者之间是从属关系。这启示我们:新时代诗歌在大写中国梦时,力戒口号化和机械化,要注重运用特定的意象、生动的细节和场景。
过去,有不少诗人,尤其是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诗人认为,写诗是诗人“分内”之事,诗人只要做好“分内”之事就行,这类走“纯诗”路线的诗人把“诗的现代”生硬地割裂出“中国现代化”这一总体意旨。这提醒我们:新时代诗歌大写中国梦时,要正确处理好所谓的内外关系。其实,对新时代诗人而言,没有纯而又纯的内或者外,内与外是互为表里的有机统一体。我赞赏伊格尔顿在《如何读诗》里说的“形式并不是对历史的偏离,只是达成它的方式。艺术形式的重大危机几乎总与历史激变相伴生”。也就是说,艺术的修辞就是艺术的政治,反之亦然。最纯粹的诗,其形式、修辞与其历史、政治都是相濡以沫的。具体到新时代诗歌抒写中国梦而言,中国梦既是新时代诗歌的形式和修辞,也是新时代诗歌的历史和政治。
从诗歌创作主题而言,以往诗歌在抒写中国梦时,主要是把中国梦作为一个前瞻性的命题予以想象、规划和表达;而进入新时代,诗歌再写中国梦时,一方面继续展望中国梦,一方面也在频频回望这一弥足珍贵的“传统”主题,今昔辉映,传统与现实和鸣,奏响了“多声部”的中国梦,使得中国梦可能会拥有以往此类诗歌所没有的复调。在我的观念里,新时代诗歌抒写中国梦面临的挑战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大;其难度堪比李白笔下的“蜀道难”;仿佛我们诗人与它始终有段距离;也正是有了如此清醒的主观认识和如此难企的客观高度,才永远诱使我们诗人不停地向上奋力攀登。从这个意义上讲,新时代诗歌的中国梦是新时代诗人心中那盏光芒四射的、永不熄灭的明灯。
从诗歌创作的主体层面来看,过去诗歌在抒写中国梦时,出现过理性主体、扩张主体、分裂主体、率性主体,乃至无主体之主体,因而使其中国梦呈现光怪陆离、驳杂难辨之面貌。新时代诗歌抒写中国梦的主体,既与以往诗歌几乎淹没主体的集体主义有别,也与过去那种西式的原子个人主义不同,而是一种把个体性和整体性糅合起来的有机的当代主体。而这种新时代的诗歌主体,首先是诗人,其次还必须是智者。沈德潜说:“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远大的志向和广博的学识,是成就伟大诗人及其伟大诗篇的最重要的两个必备条件。由此我想到,新时代要出现抒写中国梦的伟大诗人及其伟大诗篇,这样的诗歌主体必须具有“第一等襟抱”和“第一等学识”。换言之,新时代,我们如果仅仅满足于做一般意义上的“学者型诗人”已远远不够,还必须大踏步向前走,力争做具有“第一等襟抱”和“第一等学识”的“学者型诗人”。由此再一次彰显了新时代诗歌抒写中国梦的难度和高度。
此外,新时代诗歌抒写中国梦已置身于网络环境和智能写作这样特殊语境中。这是几千年来诗歌写作所遭遇的“未有之大变局”。世界文学史上的每一次文学大发展以及文体大革命,都与其文学书写工具及其书写方式的变化息息相关。新时代网络诗歌抒写中国梦,乃至用人工智能抒写中国梦,完全不同于同时代的硬笔抒写,和之前的毛笔抒写,和再之前的在竹简和龟甲上的刻写。网络写作的即时性、交互性、机读性和自由性,以及智能写作的全息性、重构性、偶合性、游戏性、衍生性、瞬时性、海量性,使得新时代诗歌抒写中国梦好像变得更加容易和快捷了。尤其是人工智能写诗,使原本需要花大力气、花长时间创作的长诗变得分外容易。人类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的所有事物、现象、人物、故事、政治、人文等,只要是网络上所有的,都能轻而易举地根据人们所要求的某个意旨,创作出规模庞大,从理论上讲可以无限长的“智能长诗”。海量的抒写中国梦的网络诗和智能诗,给人造成一种错觉:新时代抒写中国梦的诗不是少了,而是多了。事实上,新时代抒写中国梦的好诗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我常常听到人们在抱怨:网络诗只有网络而少有诗,智能诗只有智能而少有诗。这至少从一个侧面表明,网络诗和智能诗存在诗性不足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网络诗和智能诗写作的时代,既是诗歌写作最好的时代也是诗歌写作的最坏时代。于此,我们暂且不作道德评判,而专注于其诗学建设。如何强化新时代抒写中国梦的网络诗和智能诗的诗性建设,是摆在我们面前亟须解决的时代课题。“传统诗”与网络诗和智能诗只是书写工具、表达方式以及传播方式和接受方式发生了巨变,但万变不离其宗,那就是诗、诗性!而要回归诗、拥抱诗性,最为重要的是,审时度势,智性地回到诗歌写作的弥足珍贵的“朴素”。
“绘事后素!”回到朴素,就是要回到事物的本源,回到语言的源头,回到诗歌的初心。首先我们要重新审视语言和文化对世间万事万物的命名及其意义,而正是这些命名及意义,一方面给了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便利,另一方面也给我们更大限度地创造世界带来了障碍。所以,用诗歌和艺术进行“祛蔽”就显得尤为重要和可贵。但诗歌和艺术在“祛蔽”后对世界的重新命名以及重赋意义,使得世界又一次落入被遮蔽的状态。因此,对诗歌和艺术造成的遮蔽需要后来的诗人进一步“祛蔽”。由此可见,历朝历代的诗歌写作是一次次前赴后继的“祛蔽”与“澄明”的争斗。从这个意义上讲,诗人就是一名战士!而这些“祛蔽”与“澄明”的反反复复,永不停歇,宛如“剥洋葱”,是由外而内,一层层地往里剥,直至见到洁白的“初心”为止。从这个意义上讲,诗人也是一名工作者,具有精雕细刻的“匠心”。而无论是“初心”,还是“匠心”,都是一颗滚烫的“诗心”。当然,回归又不是为回归而回归,而是为了更好地出发,为了更好地抵达诗歌高地,尤其是抵达抒写中国梦的新时代诗歌高地。
“大鹏之动,非一羽之轻也;骐骥之速,非一足之力也。”新时代诗歌大写中国梦,在动能和速度以及在数量和质量等方面,均非一蹴而就;需要新时代中国诗人在厘清中国新诗追寻中国梦和重建新诗抒写中国梦法度的前提下,力求使新时代诗歌抒写出多样化和多声部的中国梦。与此同时,认识到建构具有“第一等”襟怀和学识的诗歌主体的重要性。此外,还要在时代“大变局”的语境中,理性看待网络诗和智能诗的可能及限度,扫荡弥漫诗坛的绮丽诗风和平庸诗风,回到朴素的“初心”“匠心”和“诗心”;唯有如此,才可能登临新时代诗歌抒写中国梦的高峰,完成李白当年所愿:“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