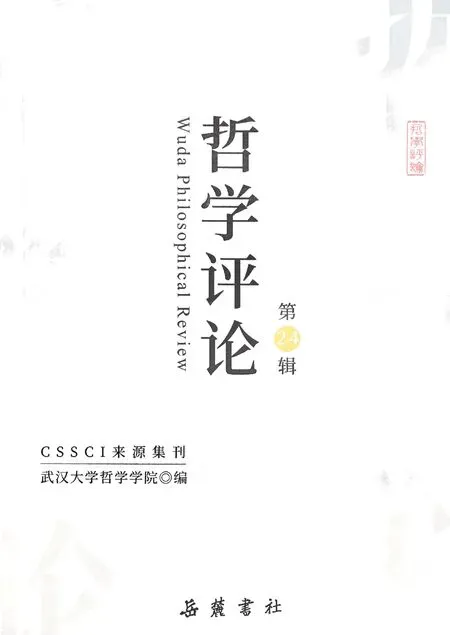论宏智正觉“默照禅”的禅学思想
朱新亮
南宋初年,临济宗杨歧派大慧宗杲(1089—1163)“看话禅”与曹洞宗宏智正觉(1091—1157)“默照禅”禅法相继提出、确立,历经明清,传续至今。大慧宗杲禅法峻切直截、语言明了;宏智正觉禅法绵密宛转、学理性强。宗杲禅法是丛林参禅悟道之主流方式,学界也对宗杲禅法研究青睐有加。宏智正觉禅法研究相对较少,大陆主要有魏道儒、伍先林、张云江、习细平等人从正觉禅学思想角度考察默照禅,皮朝纲、刘方等学者则关注默照禅与美学之关联。台湾阳力、杨惠南、陈荣波、黄青萍、张宽如、郑珍熙,日本武田忠、关口真大、新野光亮、石附胜龙、石井修道等人也对默照禅作了相关研究。相较而言,大陆学者研究方法视点呈现多元化特色,台湾、日本学者则集中讨论正觉禅学思想,日本学者特别注重宏智正觉曹洞禅的性质。然而学界关于宏智正觉禅法的研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故对正觉默照禅的禅学思想还有再探讨的必要。
一、“默照禅”与“文字禅”之关系
汾阳善昭(947—1024)《公案代别百则》《诘问百则》《颂古百则》以文字解说古人公案,推动了临济宗的兴起和文字禅的流行。雪窦重显(980—1052)、圆悟克勤(1063—1135)继而起之,将宋代文字禅推向顶峰。物极必反,文字禅的盛行造成一批“学语之流”掇拾古人言句,不重亲修实证,引起元丰以后禅宗界对文字禅的反省批评。[1]惠洪指出:“禅宗学者,自元丰以来,师法大坏,诸方以拨去文字为禅,以口耳受授为妙。”(《石门文字禅》卷26,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惠洪站在维护文字禅的立场上批判“口耳受授”的禅法,但从这则材料中可知元丰之后禅学界有“拨去文字为禅”的思想倾向。大慧宗杲遂有火烧《碧岩录》之举,宏智正觉则主张默照静坐禅法。学界从大慧宗杲、宏智正觉反对文字禅的行为、语录材料出发,认为宗杲看话禅、正觉默照禅是与文字禅对立的禅学思想,如周裕锴指出“‘文字禅’是作为‘哑禅、魔禅、暗证禅’的对立面而出现的,主张禅教合一,研读佛经,反对纯粹的‘枯骨观’、‘四禅八定’和‘默照禅’”[2]周裕锴:《文字禅与宋代诗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1页。,这其实是对正觉禅学思想的曲解误读。
首先,正觉禅师并没有抛弃文字禅的语言形式。《宏智禅师广录》卷二收录正觉禅师颂古一百则,卷三收录拈古一百则,这是正觉禅师受文字禅影响的直接证明。正觉禅师多关注前辈禅师拈颂过的公案,如颂古第二则:
举梁武帝问达磨大师:“如何是圣谛第一义。”磨云:“廓然无圣。”帝云:“对朕者谁?”磨云不识。帝不契,遂渡江至少林,面壁九年,颂曰:“廓然无圣,来机径挺。得非犯鼻而挥斤,失不回头而堕甑。寥寥冷坐少林,默默全提正令。秋清月转霜轮,河淡斗垂夜柄。绳绳衣钵付儿孙,从此人天成药病。”[1]宏智正觉:《宏智禅师广录》卷2,《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8 册,第18页下。
这则公案即雪窦重显《颂古百则》的首则公案,是禅宗拈颂必举公案,重显颂古做得非常好,直指人心原本具足的佛性。相形之下倒显得正觉颂古稀松平常。正觉颂古影响力虽不及重显,但评唱注解者亦不少,焭绝老人(生卒年不详)作《焭绝老人天奇直注天童觉和尚颂古》,元代万松行秀(1166—1246)曾作《万松老人评唱天童觉和尚颂古从容庵录》《万松老人评唱天童觉和尚拈古请益录》,行秀《寄湛然居士书》云:“吾宗有雪窦、天童,犹孔门之有游、夏,二师之颂古,犹诗坛之李杜。”[2]万松行秀:《万松老人评唱天童觉和尚颂古从容庵录》序,《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8册,第226页下。雪窦重显、天童正觉被视为诗坛李白、杜甫,可见正觉禅师颂古广为流传、浸泽深远,正觉颂古、拈古正以文字禅形式给后世禅人佛理启悟。
其次,正觉禅师开坛说法、小参开示里提举、解说公案具有文字禅性质。如:
复举赵州问僧:“曾到此间么?”僧云曾到。州云:“吃茶去。”又问僧:“曾到此间么?”僧云不曾到。州云:“吃茶去。”师云:“到与不到,吃茶一样。不着机关,殊无伎俩。且非平展家风,岂是随波逐浪。唯嫌拣择没分疏,识得赵州老和尚。”[3]宏智正觉:《宏智禅师广录》卷1,《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8 册,第2页上。
雪窦重显曾颂赵州禅师开示“至道无难,惟嫌拣择”公案,圆悟克勤《碧岩录》指出这句话出自三祖僧璨《信心铭》并依此解释这则公案。[4]佛果圆悟:《佛果圆悟禅师碧岩录》卷1,《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8 册,第140页上。正觉禅师云“唯嫌拣择没分疏,识得赵州老和尚”,将赵州禅师(778—897)开示“至道无难,惟嫌拣择”公案、“吃茶去”公案熔于一炉,以“唯嫌拣择没分疏”解释赵州禅师“吃茶去”的禅学内蕴,可知他深受雪窦重显颂古影响。正觉解说此公案的语言文字整齐,句尾使用韵字,实质与颂古无异。再次,正觉禅师喜用诗语、偈语说法开示。如:
上堂云:“孤筇长作水云游,底事而今放下休。一点破幽明历历,十分合体冷湫湫。暗中须透金针穴,转处还藏玉线头。劫外家风兹日辨,渠侬真与我侬俦。”
上堂云:“菩提无树镜非台,虚净光明不受埃。照处易分雪里粉,转时难辨墨中煤。鸟归无影树头宿,华在不萌枝上开。际会风云底时节,寒梭出蛰一声雷。参!”[1]宏智正觉:《宏智禅师广录》卷4,《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8 册,第36页中、37页下。
两首诗偈完全符合平仄格律,“一点破幽明历历,十分合体冷湫湫”,数字、叠字各自相对,金针穴与玉线头、雪里粉与墨中煤都对得很工巧。正觉禅师以诗歌韵语开示的类似记载不胜枚举。此外,《宏智禅师广录》第七、八、九卷专收赞颂诗偈皆表明禅宗和语言在正觉禅师处并非截然对立。可见,即便是提倡“默照禅”的宏智正觉也是不排除文字语言的,诚如小川隆所说“用文字禅进行表达,是南宋以来的总趋势”。[2]小川隆:《语录的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第189页。
正觉禅师思想上并不排斥文字禅,那他默默无言、休去歇去的默照禅法是否与文字禅冲突抵牾呢?实际上,文字禅、默照禅分属文字般若、观照般若两个层面,分隶闻思与修证两个阶段,二者不能放在一个层面进行非此即彼的比较。文字禅是佛理悟入,[3]惠空法师云:“禅宗理论、祖师的语录著作绝少如论典般的系统思想,但在问答之际仍不脱理论义涵,仔细披寻,仍可看出一些蛛丝马迹。”(慧空法师:《禅宗心要》,台中:慈光寺·慈光禅学院,2013年6月第2 版,第3页)默照禅是实证修行,闻思为修证之助缘,修证为闻思之归趋,二者并行不悖而非扞格难入。文字经典起着指导、印证作用,真修实证才能真正证入,故而正觉禅师不会将文字禅与默照禅对立。
二、宗杲批判“默照禅”的佛法理据
大慧宗杲曾斥默照禅为落空亡底外道、魂不散底死人、黑山下鬼家活计,[1]目前也有人如台湾惠空法师曾怀疑宗杲所批评的默照禅并非针对正觉。此外,闫梦祥《论大慧宗杲批评默照禅的真相》(《河北大学学报》2006年第5 期)指出宗杲批评的“默照禅”与真歇、宏智的“默照禅”有根本不同,宗杲所批评的乃是类于“二乘寂灭”“空亡外道”的一种“禅病”;张云江《南宋禅宗史上的“默照禅公案”探究》(《宗教学研究》2010年增刊)也从不同角度考证宗杲的批评与宏智正觉的禅法不相对应,宗杲所批评的实是古今禅修者最容易走上的一条错误路径。但宗杲口口声声骂“邪师说默照禅”“默照邪师辈”,不能不说跟正觉无关,当然,这很可能是宗杲对默照禅缺乏正确理解造成的结果,却不能说宗杲所指责的不是正觉“默照禅”。指责默照禅“一向闭眉合眼,做死模样,谓之静坐、观心默照,更以此邪见,诱引无识庸流曰:‘静得一日,便是一日工夫。’苦哉!殊不知尽是鬼家活计”。[2]大慧宗杲:《示真如道人》,《大慧普觉禅师语录》卷20,《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7册,第895页中。宗杲对默照禅的批评是与其参学经历和佛法领悟分不开的,宗杲曾跟随曹洞宗芙蓉道楷(1043—1118)弟子瑞州微和尚(生卒年不详)参学且接受过曹洞宗默照禅法,他在《答富枢密》里说:
既未到这个田地,切不可被邪师辈胡说乱道引入鬼窟里,闭眉合眼作妄想。迩来祖道衰微,此流如麻似粟,真是‘一盲引众盲,相牵入火坑。’深可怜愍……宗杲亦尝为此流所误,后来若不遇真善知识,几致空过一生。每每思量,直是叵耐!以故不惜口业,力救此弊。今稍有知非者,若要径截理会,须得这一念子嚗地一破,方了得生死,方名悟入。[3]大慧宗杲:《答富枢密》,《大慧普觉禅师语录》卷26,《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7 册,第921页中。
在宗杲看来,曹洞宗默照禅法虽暂时拘束住身体,心识却纷飞如野马,纵然心识暂停,如石压草而不觉又生,很难真正得到无上菩提、究竟安乐。而且宗杲个性鲜明、直截利落,不喜微和尚将曹洞宗“功勋五位、偏正回互、五王子之类许多家事来传”,认为这种细密绵绵的教授方法违背了佛祖自证自悟之道,故宗杲“始从曹洞诸老宿游,既得其说,叹曰:‘是果佛祖意耶?去之谒准湛堂。’”[4]大慧宗杲:《大慧普觉禅师塔铭》,《大慧普觉禅师语录》卷6,《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7 册,第836页下。转投湛堂文准(1061—1115)、圆悟克勤处参学并因圆悟克勤提举公案而悟入。由此可见,宗杲批判默照禅是在他曾经出入曹洞宗的经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更高角度来看是临济宗对曹洞宗的批判。[1]日本学者武田忠也关注到这个问题,他在《看話禪と默照禪についての一考察—大慧と宏智の立場》(《宗教研究》第36 卷第3 辑,1963年)、《大慧の默照禪批評と曹洞禪》(《宗教研究》第38 卷第2 辑,1965年)两篇文章中对大慧宗杲批评曹洞禅进行了考察。当然,宗杲批判默照禅并非仅因宗派偏见,而是寓含着更为深刻的佛学依据:
首先,宗杲禅法以悟为极则,批评默照禅则执方便为究竟。他说:
而今默照邪师辈,只以无言无说为极则,唤作“威音那畔事”,亦唤作“空劫已前事”,不信有悟门,以悟为诳,以悟为第二头,以悟为方便语,以悟为接引之辞。如此之徒,谩人自谩,误人自误。[2]大慧宗杲:《答宗直阁》,《大慧普觉禅师语录》卷28,《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7 册,第933页下。
昨接来诲,私虑左右必已耽着静胜三昧。及询直阁公,乃知果如所料。大凡涉世有余之士,久胶于尘劳中,忽然得人指令,向静默处做工夫,乍得胸中无事,便认著,以为究竟安乐。殊不知,似石压草,虽暂觉绝消息,奈何根株犹在,宁有证彻寂灭之期?要得真正寂灭现前,必须于炽然生灭之中,蓦地一跳跳出,不动一丝毫,便搅长河为酥酪,变大地作黄金,临机纵夺,杀活自由,利他自利,无施不可,先圣唤作无尽藏陀罗尼门,无尽藏神通游戏门,无尽藏如意解脱门,岂非真大丈夫之能事也![3]大慧宗杲:《答富枢密》,《大慧普觉禅师语录》卷26,《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7 册,第921页下。
宗杲指出,默照禅法只能暂时使胸中无事,却像石头压草,纵然草暂时不能生长,根株还在,并非证彻寂灭。默照禅执静坐方便为究竟、以无言无说为极则、著空滞寂、不求妙悟遂断灭了自心本妙明性,难以开发无漏智慧并实现究竟安乐、如实清净。宗杲认为必须通过悟关才能临机纵夺、杀活自由并得到究竟安乐,故指出“学道无他术,以悟为则”,今生修行最终鹄的就是开悟,不以悟为目的的修行皆不究竟。宗杲认为通过参话头可以实现悟入,其《答陈少卿》云:
今稍有知非者,愿公只向疑情不破处参,行住坐卧不得放舍——僧问赵州:“狗子还有佛性也无?”州云:“无。”这一字子,便是个破生死疑心底刀子也。这刀子杷柄,只在当人手中;教别人下手不得,须是自家下手始得。若舍得性命,方肯自下手。若舍性命不得,且只管在疑不破处崖将去,蓦然自肯舍命,一下便了;那时方信静时便是闹时底,闹时便是静时底,语时便是默时底,默时便是语时底。[1]大慧宗杲:《答陈少卿》,《大慧普觉禅师语录》卷26,《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7 册,第923页上。
悟入别无他法,只能自家下手,等到悟入之时,静闹一如、语默一如、生死心绝,无佛见法见,无众生烦恼,无迷悟、生死、有无等对立分别,无有挂碍。宗杲认为悟入不需要做静中工夫:
若要真个静,须是生死心破,不著做工夫。生死心破,则自静也。先圣所说“寂静方便”,正为此也。[2]大慧宗杲:《答富枢密》,《大慧普觉禅师语录》卷26,《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7 册,第922页上。
宗杲的悟入指破生死心,生死心破就能得到真正的寂静,默照禅正因不以悟为极则,生死心不破,故静坐所得寂静只能维持一时而无法长久。
其次,宗杲认为默照禅离世觅菩提、落入净边。宗杲继承慧能禅学思想,认为世间法即是佛法,佛法即世间法,佛法不可离开世间而寻觅到,若专主静坐、远离世间则是坏世间相而求实相,其《答刘通判》云:
杜撰长老辈,教左右静坐,等作佛,岂非虚妄之本乎?又言,静处无失,闹处有失,岂非坏世间相而求实相乎?若如此修行,如何契得懒融所谓“今说无心处,不与有心殊”?……众生狂乱是病,佛以寂静波罗蜜药治之。病去药存,其病愈甚;拈一放一,何时是了?生死到来,静闹两边,都用一点不得。[3]大慧宗杲:《答刘通判》,《大慧普觉禅师语录》卷27,《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7 册,第926页中。
寂静只是对治众生狂乱之病的药,病去药去、舍筏登岸。若执着静坐则落入净边,依旧没有破除二分对立的模式。离开日用、别有趣向犹如离波求水、离器求金,即自身而求自身,只会愈骛愈远。宗杲认为禅不在静处、不在闹处、不在思量分别处、不在日用应缘处,却不能舍却静处、闹处、日用应缘处、思量分别处参禅,盖大道真体不离声色言语,他甚至说:
正在闹中,不得忘却竹椅、蒲团上事。平昔留心静胜处,正要闹中用;若闹中不得力,却似不曾在静中做工夫一般……若以静处为是,闹处为非,则是坏世间相而求实相,离生灭而求寂灭。好静恶闹时,正好着力,蓦然闹里撞翻静时消息,其力能胜竹椅蒲团上千万亿倍……[1]大慧宗杲:《答曾侍郎》,《大慧普觉禅师语录》卷25,《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7 册,第918页下。
但宗杲只对曾侍郎这样久做静中工夫的人说这些话,只有久做静中工夫才有资格谈闹中工夫。对于初学来说,做静中工夫还是很必要的。
无心是学道的特点,宗杲认为默照禅仅在表面上做到了无心,他说:“所谓无心者,非如土木瓦石顽然无知,谓触境遇缘,心定不动,不取著诸法,一切处荡然无障无碍,无所染污,亦不住在无染污处。观身观心如梦如幻,亦不住在梦幻虚无之境。到得如此境界,方始谓之真无心,且非口头说底无心。”[2]大慧宗杲:《示清净居士》,《大慧普觉禅师语录》卷19,《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7册,第890页下。无心并非如默照禅那样休去歇去、落在净边,真正的无心并不离开日用生活而需在触境遇缘时心定不动、不黏着诸法、无所染污,正如《金刚经》所云“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宗杲认为若心识寂灭、无一动念处即是正觉,拥有正觉则二六时中行住坐卧、语默动静无不湛然清净。宗杲又说:
今时有一种杜撰汉,自己脚跟下不实,只管教人摄心静坐,坐教绝气息。此辈名为真可怜愍。请公只恁么做工夫。山野虽然如此指示公,真不得已耳。若实有恁么做工夫底事,即是污染公矣。此心无有实体,如何硬收摄得住?拟收摄,向甚处安著?既无安著处,则无时无节,无古无今,无凡无圣,无得无失,无静无乱,无生无死,亦无湛然之名,亦无湛然之体,亦无湛然之用,亦无恁么说湛然者,亦无恁么受湛然说者。[1]大慧宗杲:《答许司理》,《大慧普觉禅师语录》卷26,《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7 册,第924页下。
心无实体故无对立、无差别,也无收摄、无安著。宗杲认为默照禅执着于离世间相求实相,违背了慧能所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的教理,这是宗杲批判默照禅的第二个理据。
尽管宗杲批判默照禅,但其实宗杲、正觉禅法还是有不少相同之处。其一,按下妄想之心是宗杲、正觉禅法共同的入手工夫。宗杲《示廓然居士》云:
心意识乃思量分别之窟宅也。决欲荷担此段大事因缘,请猛著精彩,把这个来为先锋、去为殿后底生死魔根一刀斫断,便是彻头时节。正当恁么时,方用得口议心思著。何以故?第八识既除,则生死魔无处栖泊。生死魔无栖泊处,则思量分别底浑是般若妙智,更无毫发许为我作障。[2]大慧宗杲:《示廓然居士》,《大慧普觉禅师语录》卷20,《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7册,第896页上。
众生从本以来念念相续、未曾离念,正是心意识的思量分别造成人的生死轮回,故必须斩断心意识才能将妄念转化成般若妙智。斩断心意识的最好方法是照看话头,以“一念话头”替代万念妄想,从而集中一念直到最后打破话头上的疑情、顿悟本来面目。其二,宗杲并不反对坐禅。客观说来,坐禅是摄心的最好法门,宗杲认为初学尤其应该多静坐,只是不能执静坐方便为究竟。其《示清净居士》云:
学道人,十二时中,心意识常要寂静。无事亦须静坐,令心不放逸,身不动摇,久久习熟,自然身心宁怗,于道有趣向分。寂静波罗蜜,定众生散乱妄觉耳;若执寂静处便为究竟,则被默照邪禅之所摄持矣。[3]大慧宗杲:《示清净居士》,《大慧普觉禅师语录》卷19,《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7册,第891页中。
坐禅能够令心不放逸、身不动摇,久习能使身心宁怗、收摄散乱妄觉,但坐禅不过是对治散乱妄觉的药而已,病去药除,一切扫迹。
三、宏智正觉“默照禅”的佛法理据
学术界对正觉禅师“默照禅”的理解繁多歧异、不相统一。方立天认为默照禅“渊源于菩提达摩的壁观安心法门,以及神秀的长坐不卧禅法,是对菩提达摩和神秀(606—706)坐禅法门的回归。但是在观照的对象与内容方面,默照禅与神秀的禅法又有很大的差别”。[1]方立天:《论文字禅、看话禅、默照禅与念佛禅》,《中国禅学》第1 卷,2002年。伍先林认为“正觉的禅法在理论上继承了曹洞宗综合慧能( —713)南宗与神秀北宗的传统,并与神会、宗密(780—841)一系菏泽宗的灵知说有一定的渊源关系,但在具体的宗教实践上,默照禅则进一步退向神秀北宗的禅法”。[2]伍先林:《正觉的默照禅思想》,《佛学研究》,2000年。魏道儒认为默照禅是“吸取《庄子》入禅的结果”。[3]杜继文、魏道儒:《中国禅宗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 版,第472页。日本学者关口真大认为牛头宗的鹤林玄素才是默照禅实际上的先驱[4]关口真大:《公案禪と印度禪》,《印度学佛教学研究》第16 卷,1968年。……
宏智正觉默照禅自有其禅法渊源。石头希迁弟子大颠禅师(766—779)“应机随照,泠泠自用,穷其用处,了不可得,唤作妙用,乃是本心”[5]大慧宗杲:《正法眼藏》卷3,《卍续藏经》第118 册,第131页下。即着重突出“照”的作用;正觉初参的法成禅师(1071—1128)极为注重坐禅,世称“枯木法成”;正觉之师丹霞子淳(1064—1117)云:“把今时事放尽去,向枯木堂中冷坐去,切须死一遍去,却从死里建立来,一切处谩你不得,一切处转你不得,一切处得自在去。所以道:悬崖撒手,自肯承当。绝后再苏,相欺不得”[6]丹霞子淳:《丹霞子淳禅师语录》卷1,《卍续藏经》第124 册,第487页下。,皆注重休歇妄念、冷坐禅堂的修行方式。曹洞宗枯木死灰般的坐禅传统是正觉默照禅的思想近源,若远溯佛理即可推知正觉默照禅的学理依据及与宗杲禅法相异原因。
首先,默照禅属于“真常唯心论”,与宗杲偏向“性空唯名论”的禅学倾向异途。印顺法师(1906—2005)认为佛教适应众生机感而对“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三法印加以解释发挥,不同发挥各有侧重从而使佛教分成“虚妄唯识论”“性空唯名论”“真常唯心论”三个不同体系。[1]参看印顺法师《印度佛教思想史》(中华书局2010年第1 版)第四、七、八章,《华雨集》(下)(中华书局2011年第1 版)。大慧宗杲秉承慧能“本来无一物”的一派思想,立足诸法性空,宣说一切但有假名,不安立任何自性有或自相有,故应归入“性空唯名论”。正觉禅师则明显受到《大乘起信论》影响而应判归“真常唯心论”。《大乘起信论》提出“真如缘起”说,认为一切世间、出世间法皆是一心所造,真如之性具有生灭、不生不灭两种属性,自性清净的真如随无明风动而生起现象界的生灭变化,故真如亦空亦不空。正如大珠慧海所云:“真如之性,亦空亦不空,何以故?真如妙体,无形无相,不可得也,是名亦空;然于空无相体中,具足恒沙之用,即无事不应,是名亦不空。”[2]大珠慧海:《顿悟入道要门论》,《卍续藏经》第110 册,第850页上。真如又具有觉与不觉两种属性,能够觉照真如自体,真如的寂性与觉性正是默照禅照寂相即的佛理依据。正觉禅师说:
生不为有,动与寂随;灭不为无,处与智共。所以道,如镜照像,像非外缘;如珠发光,光还自照。[3]宏智正觉:《宏智禅师广录》卷4,《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8 册,第47页中。
现象是生灭的,本质为空,故生不为有而常与寂随;真如却非断灭,而具觉性,可以自照真如本体,故灭不为无而处与智共。修行需要先空一切外象,在寂寂中觉照本心、觉照空劫以前含空纳有的真如实相。正觉禅师又说:
尔但只管放,教心地下一切皆空,一切皆尽,个是本来时节。所以道,一切皆从心地生,除去一切生底,还是本来心地。这个心地平等普遍,普遍无有不在,无有不满。既心地上生相,尽十方三世,无有一毫自外而来,俱从个里发现。便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唯性晓。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心无形影,对缘即照,所以假虚空为森罗万象之体,假森罗万象为虚空之用。一切诸法皆是心地上妄想缘影。[4]宏智正觉:《宏智禅师广录》卷5,《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8 册,第60页中。心地放空、一切扫相之后才露出本来风光,这个心地平等周遍、生出万法。默照禅的目的就在于体认本性清净、具足万法。默照禅不同于不净观、数息观等观法,也不同于宗杲看话禅,而是“只管放,教心地下一切皆空,一切皆尽”,“未休休去,未歇歇去。尔若歇得尽、休得稳,千圣不可携。不可携处,是尔自己”。[1]宏智正觉:《宏智禅师广录》卷5,《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8 册,第60页中。即只管静坐,放空身心,不观心看净,也不涉缘对物,所谓“净不涉缘,照不对物。用无去来之相,混无彼我之心”[2]宏智正觉:《宏智禅师广录》卷4,《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8 册,第51页中。,其实相当于天台宗的制心止。默照禅法归根究底是与真如的寂性、觉性相应的。
学术界虽对默照禅的思想渊源提出了不同看法,却没有注意到达摩、圭峰宗密、菏泽神会、永嘉玄觉(665—713)其实都受真常思想浸泽。达摩以《楞伽经》印心,《楞伽经》的“如来藏藏识心”却融合了真常清净(如来藏)心与虚妄生灭(阿赖耶)心,是在如来藏我的基石上融摄唯识学的“真常唯心论”。[3]参看印顺:《印度佛教思想史》(中华书局2010年第1 版)第八章。菏泽神会受《大乘起信论》影响而强调灵知之性,认为“知之一字,众妙之源”,又将本心分为真如之体、真如之相以分别对应《起信论》的心真如门、心生灭门。宗密“禅遇南宗,教逢圆觉”[4][宋]普济著,苏渊雷点校:《五灯会元》,中华书局1984年第1 版,第105页。,《圆觉经》属真常一系,故宗密说:“源者,是一切众生本觉真性,亦名佛性,亦名心地……况此真性,非唯是禅门之源,亦是万法之源,故名法性。亦是众生迷悟之源,故名如来藏藏识。亦是诸佛万德之源,故名佛性。亦是菩萨万行之源,故名心地。”[5][宋]普济著,苏渊雷点校:《五灯会元》,中华书局1984年第1 版,第106页。宗密对本觉真性、如来藏藏识的强调可看出思想渊源所自。永嘉玄觉对禅学的解释更接近默照禅,他在奢摩他颂中说:“必先息缘虑,令心寂寂。次当惺惺,不致昏沉,令心历历……寂寂是药,惺惺亦药。寂寂破乱想,惺惺治无记。寂寂生无记,惺惺生乱想。寂寂虽能治乱想,而复还生无记。惺惺虽能治无记,而复还生乱想。故曰:惺惺寂寂是,无记寂寂非。寂寂惺惺是,乱想惺惺非。”[6]永嘉玄觉:《永嘉禅宗集注》卷2,《卍续藏经》第111 册,第456页上。无记是指坐禅过程中的昏沉、发愣状态,需要惺惺治住。若有妄想则需要寂寂治住,寂寂、惺惺即止观、定慧,二者等持、灵活运用才能有效对治禅病、助长开悟。永嘉玄觉对止观之描述与正觉默照禅佛理相通,默、照也即寂寂、惺惺,也即止观双运、定慧等持。由此可知真常思想才是默照禅与如上禅师禅法相通的佛理依据。
其次,默照禅以离析根尘了脱生死,不同于宗杲以悟入离生死。宗杲禅法进路在于通过话头破生死心,故批评默照禅有导引禅人耽于四禅八定的世间禅定倾向,与大乘禅法了脱生死毫不相干,其实这是对默照禅的误解。正觉说:
参禅一段事,其实要脱生死。若脱生死不得,唤什么作禅。且道,作么生生?作么生死?作么生脱?若一念迷本随情,牵在一切处,纷纷纭纭,胶胶扰扰,既从不自由处生,还从不自由处死。若是分晓汉,本无所从来。明白恁么用,便于一切时一切处脱彻无依,万象中出一头地。[1]宏智正觉:《宏智禅师广录》卷5,《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8 册,第60页中。
从这段材料可知正觉禅法也以了脱生死为目的,生死不是别的,一念迷本随情、牵在一切处即是生死。了生死即是明白本无所从来,断尽心念,便能于一切时一切处脱彻无依、虚静圆明。宗杲看话禅注重禅人自证自悟,并不保证每个禅人悉数开悟、彻见本来面目,故宗杲每宽慰学人即使此世不能开悟也于心地上种下般若种子,后世再出来参禅就能迅速契证本来。正觉默照禅的佛法理据在于只需认清根随尘转造成人的生死轮回,那么离析根尘、能所双亡便能够彻照本源、了脱生死,禅人只需放空一切、照寂相即,即可体证真如本体。故而正觉禅师说:
心是根,法是尘,两种犹如镜上痕,尘垢尽时光始现,心法双忘性即真。到恁么时,一切脱落去始得。正脱落时,彼我俱不着处所。所以道,周遍十方心,不在一切处。个时不是一切心,个时不是一切法,所以遍一切处。[2]宏智正觉:《宏智禅师广录》卷5,《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8 册,第65页上。
尘垢尽尽,根尘离析,心法双忘,便能体会到灵明廓彻、广大虚寂的本来面目,即是成佛作祖之时。
最后,默照禅工夫、功用贯于日用,并非如宗杲所说的离世觅菩提、引人坐在黑山鬼窟里。默照禅虽然偏重坐禅却并非不在日常生活中用功,正觉禅师说:
佛法也无如许多般,只要诸人一切时中放教身心空索索地,条丝不挂,廓落无依,本地灵明,毫发不昧。若恁么履践得到,自然一切时合,一切时应,了无纤尘许作尔障碍处。便能转千圣,向自己背后,方唤作衲僧。[1]宏智正觉:《宏智禅师广录》卷4,《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8 册,第35页上。
所谓“一切时中”即非仅指座上工夫,也包括座下工夫,只有一切时中放教身心空索索地廓落无依才能不昧灵明本性。真正的修行是“也无万行可修,也无三界可出,也无万法可了”[2]宏智正觉:《宏智禅师广录》卷1,《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8 册,第17页下。,是本来光明的透出遍彻。正觉又提到默照禅的功用贯于日常生活之中,他说:
六户不掩,从教万法通同。四衢无踪,祇么一尘不受。所以道眼见色与盲等,耳闻声与响等,便能声色里睡眠,声色里坐卧。[3]宏智正觉:《宏智禅师广录》卷1,《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8 册,第11页上。
修行人心无挂碍,远离妄念,身之所处是一个无差别世界,便能不对色、声起心,便能于声色里睡眠坐卧。如此,修行默照禅的功用就能遍于日常生活。
结 语
文字禅是文字般若,属于闻思阶段;看话禅、默照禅是观照般若,属于修证阶段,二者相辅相成、并不相悖。宗杲、正觉批评文字禅是为破除禅人过分耽溺语言文字、不重真修实证的偏执。二人禅法皆以了脱生死为目的、皆是究竟的,但宗杲更偏向慧能“本来无一物”的“性空唯名论”,偏向慧能及洪州宗在行住坐卧中体道的禅学思想,故更看重日常生活中的修行;正觉更偏向“真常唯心论”,继承曹洞宗盛行的坐禅传统,偏向在静坐中体验照体独立、灵知之性。宗杲并不废弃坐禅,正觉也主张在日常生活中修行。看话禅与默照禅皆只是方便法门,意在待机说法以接引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