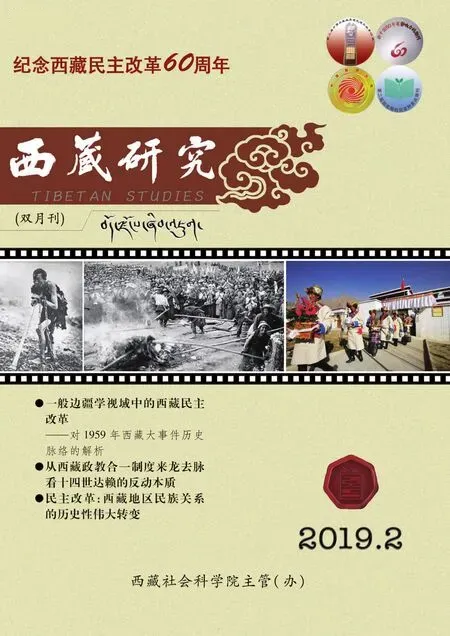“爱国余肝胆”:西藏民主改革前后一位前外交官的学术与舆论战场
冯 翔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北京100081)
一、引言
1959年的西藏民主改革是一场根本性的社会变革,是中国共产党解决我国民族地区问题的又一成功案例。但由于冷战铁幕的降下和西方的固有偏见,西藏民主改革受到西方一些别有用心之人的攻击,这种攻击甚至从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开始就从未停歇。作为一位厌倦了国民党统治的前任外交官,李铁铮在美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便发表了与“西藏问题”相关的学术论文,并出版相关专著;在西藏民主改革后,投书《纽约时报》。他传递了有关西藏地方的正确历史,特别是近代以来的西藏地方与中国中央政府所属关系的历史,以正视听。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提出的“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中做好西藏工作”,在1959年的西藏民主改革前后,作为一位拥有强烈爱国之心的前外交官与学者,李铁铮就已投身于国际的学术与舆论战场之中。
二、李铁铮的生平与外交场
李铁铮1906年出生于湖南长沙一户普通家庭,因其父为人刚正,吃苦耐劳且有信义,李铁铮家的经济状况不错,其父去世时已是湖南染业公司的总经理。宽裕的家庭条件给予李铁铮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也在少年时奠定了他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自尊心。
按照李铁铮的自述,他中学时就读的教会学校和大学之初就读的金陵大学的部分教师给他的印象深刻,感受到了西方人对中国人的轻蔑[1]175—176。受民族自尊心的驱使,李铁铮转学到了东南大学,该校后改名为中央大学[注]即今天的南京大学。。这次转学可以说极大地影响了李铁铮的人生轨迹,李铁铮是青年学生中的积极分子,又保持不错的成绩,自然得到老师们的垂青,其中包括著名的国际法学家、外交史家周鲠生[注]周鲠生(1889—1971年),原名周览,湖南省长沙府长沙县人,著名国际法学家、外交史家、教育家。1900年,入谭延闿创设的湖南省立第一小学。因成绩优秀,1905年被派往日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经济。留学期间,加入中国同盟会。1919年留法期间,“五四运动”爆发,参加在法学生游行。1922年受聘就任北京大学政治系教授。1924年末,参加不平等条约改正运动,出版《不平等条约十讲》。1927年3月,成为国立东南大学(翌年改为国立中央大学)教授、政治系主任。其后,应国民政府之聘,从事宪法制定事务,但因反对蒋介石,数月后辞任。1929年9月,周鲠生应武汉大学招聘担任教授。在武汉大学从事国际法、外交史研究,所著《国际法大纲》《近代欧洲外交史》等书,并在《东方杂志》发表论文。1932年10月,国际联盟所派李顿调查团的报告书发表,周鲠生以《东省事件与国际联盟》为题发表论文。文中称,李顿调查团报告书是英国、法国等强国绥靖的结果,对调查团提出了严厉批判。1935年1月,周鲠生升任武汉大学法科研究所主任,10月任武汉大学法律系主任。1936年,兼任武汉大学教务长。1939年,赴美国从事研究。1945年4月,作为中国代表团顾问,参加了创建联合国的旧金山会议。同年夏,周鲠生归国,被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其后,第二次国共内战爆发,周鲠生反对内战,同情并理解反内战的学生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鲠生出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其后历任外交部顾问、外交学会副会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案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6年,周鲠生加入中国共产党。1971年4月20日,周鲠生在北京病逝。,日后成为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外交部长的王世杰[注]王世杰(1891—1981年),字雪艇,湖北省武昌府崇阳县人。王世杰早年就读于武昌南路高等小学、湖北优级师范、北洋大学。武昌起义爆发后,回到武昌,任革命派的都督府秘书。1913年,赴英国留学,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1917年毕业并获得政治经济学学士学位。此后赴法国巴黎大学,1920年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归国后,出任北京大学教员,创办《现代评论》周刊。1928年10月,被任命为海牙的常设仲裁法院仲裁人。1929年3月,任国立武汉大学校长。1933年4月,升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1938年1月,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1939年11月,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1945年7月,宋子文就任行政院长,王世杰接任外交部长。1946年,同周恩来进行重庆谈判,签署《双十协定》。1948年3月,王世杰成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4月14日,国民大会召开第八次大会,出席代表2717人;9月的第三届联合国大会,王世杰为中国首席代表。12月,王世杰离任外交部长。后随蒋介石逃往台湾,1981年在台北病逝。。
李铁铮毕业之后在周鲠生的帮助下,通过考试成为湖南省南县县长,却因不走官场套路、不请客吃饭送礼,遂因故被撤职。后在王世杰和周鲠生的帮助下在武汉大学担任助教,1931年以第一名的成绩通过外交部的考试[注]戴季陶对李铁铮在口试中的表现甚为满意。参见李铁铮:《敝帚一把:李铁铮的晚年写作和生平》,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06页。,开始了在民国外交界长达19年的工作。
因其在“一二八事变”后的“上海停战会议”中的表现得到肯定,李铁铮后随郭泰祺[注]郭泰祺(1888—1952年),字保元,号复初,湖北省黄州府广济县人。1902年,郭泰祺入张之洞创办的新式学堂武昌湖北省五路高等小学堂。后来,郭泰祺的才识获得张之洞器重,1904年获公费赴美国留学。完成中学教育后,在1908年入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政治学。辛亥革命爆发的消息见报后,郭泰祺在1912年归国,被任命为湖北军政府外交股长。1918年,郭泰祺赴广州,加入孙中山的护法军政府,任参事兼外交次长。1932年1月,汪精卫任行政院长,罗文干任外交部长,郭泰祺任外交次长,同年签订《上海停战协定》,后改任驻英国公使。1941年4月,郭泰祺被召回国,接替王宠惠短暂担任外交部长。1947年4月27日,郭泰祺被任命为联合国特别大会全权代表。1952年在加州病逝。使英,任三等秘书。在英国期间,李铁铮利用业余时间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后由于郭泰祺的不信任[注]郭泰祺怀疑李铁铮泄露了他负面的个人生活情况。,于1936年被调回南京,中断学业,但在伦敦期间的两件事却开启了李铁铮对“西藏问题”的极大兴趣。其一,1935年国民政府在伦敦举办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特将735件故宫文物运至伦敦,结果在说明书的封面地图上却将西藏画至国境线之外,引起风波。其二,也是在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期间,“我见一小老头,貌似汉学学究,对一古画反复观赏,趋与谈,询知是当年统率英军侵入西藏拉萨的司令荣赫鹏[注]荣赫鹏(Francis Younghusband,1863—1942年),生于印度。1887年(光绪十三年)从北京经归化(呼和浩特)进入新疆哈密。曾在印度和喀什米尔等地进行过调查活动。1903—1904年奉英国政府之命率军侵入西藏,占领拉萨后强迫西藏地方签订非法的《拉萨条约》,严重损害中国主权,清中央政府拒绝签字。而荣赫鹏在拉萨的行为同样未取得伦敦的欢心,返回印度后被迫退休。1906年清政府在北京与英国签订《续订藏印条约》,将《拉萨条约》作为附约。1919—1922年任伦敦皇家地理学会会长。著有《大陆的心脏》(1896年)及《英国侵略西藏史》(1912年)等书。他是英国侵略中国西藏地方的急先锋,是屠杀中国西藏军民的英国军官。上校。彼听得我对西藏有兴趣,特邀我去一陈设古老、会员资格限制恭严的俱乐部餐叙,经此一度接触,我未再与之来往,因彼此立场观点不同,既无共同语言,自无接续与谈之必要。”[1]220
调回外交部后,李铁铮得到张群的赏识,受其推荐,出任驻甘肃外交特派员,期间还接待过周恩来总理。1941年郭泰祺出任外交部长后,李铁铮虽不受其信任,却再次受到了王世杰和张群的保举,出任简任秘书。期间,在卸任驻甘肃外交特派员时,恰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设国际事务组,贺耀祖[注]贺耀祖(1889—1961年),号贵严,湖南省长沙府宁乡县人。1905年,湖南新军募兵,他报名参军。后入湖南陆军小学堂。1909年毕业后,先后入武昌陆军中学、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1期毕业后的1911年,赴日本留学,入东京振武学校。同年7月,经刘揆一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贺耀祖到苏州加入江苏的革命军。1926年参加北伐,击败孙传芳,后率军至南京,受蒋介石赏识,成为蒋的心腹。1932年4月,任参谋本部参谋次长。1938年初,贺耀祖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在抗日战争中,贺耀祖同中国共产党开始交流,后对蒋发动内战不满。1949年春,贺耀祖赴香港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同年8月发表起义宣言,赴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交通部部长、民革中央常务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1961年7月16日,贺耀祖在北京病逝。在获得陈布雷[注]陈布雷(1890—1948年),原名陈训恩,字彦及,笔名布雷。民国时期著名评论家,后受蒋介石赏识,弃文从政,被称为“蒋中正之文胆”。1936年,担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副秘书长、侍从室第二处主任、国民党中央宣部副部长、国民党中央委员,成为蒋介石的高级幕僚。1947年在浙江省慈谿县当选为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1948年自杀。的同意后[注]据李铁铮本人回忆,在蒋廷黻组织的一次饭局上,贺耀祖曾说李铁铮在一次训练团会上给蒋介石留下了好印象。所以他判断这次机会可能是他给蒋介石留下的好印象所致。参见李铁铮:《敝帚一把:李铁铮的晚年写作和生平》,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09页。,邀李铁铮担任主任,但衡量利弊之后李铁铮决定放弃。1942年蒋介石亲自兼任外交部长后,李铁铮出使伊朗,在伊朗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后,李铁铮成为民国外交界最年轻的大使。
在伊朗期间,时值滇缅公路被切断中英商讨经西藏修建一条至内地的补给线之时,经过反复磋商,英国方面称西藏地方政府“现在准备允许非军事物资通过”[注]参见英国外交部档案,FO 371/31638,Secretary of State for India to Chungking,July 3,1942。。对此,身处德黑兰的李铁铮致电外交部,提醒注意英国的小动作,“谨建议钧部于发表消息说明该路线及称道英印助我运输时,便嘉许西藏地方政府语,向藉以纠正视听”[注]参见台北“国史馆”馆藏《来电第35098号李铁铮致外交部》,录《藏印驿运线》(三)001-059200-0012,1942年5月7日。,凭借李铁铮在侍从室的关系,李铁铮的建议顺利到达蒋介石处,在该电的左上角,有一行小字“该电已呈蒋委员长”[注]参见台北“国史馆”馆藏《来电第35098号李铁铮致外交部》,录《藏印驿运线》(三)001-059200-0012,1942年5月7日。。
但在出使伊朗期间,却激起了李铁铮对国民政府及国民党治国的极大怀疑。出使伊朗时,李铁铮与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赫尔利(Patrick Hurley)[注]赫尔利(Patrick Jay Hurley,1883—1963年),1883年出生于今奥克拉荷马州,大学时就读于乔治华盛顿大学,曾于胡佛总统任内出任美国战争部长。1945年,任美国驻中国大使,8月赫尔利去延安接毛泽东赴重庆谈判,试图调解国共之间的矛盾,但未能成功。1945年11月辞去大使职位。关系友好,在德黑兰会议期间,赫尔利曾向李铁铮透露了一次丘吉尔与罗斯福的谈话。席间,丘吉尔破口大骂蒋介石,并与罗斯福商定让宋子文出任行政院长,后来宋子文果然上位,赫尔利出任驻华大使[1]223。这使得李铁铮大受刺激,“觉得罗、邱如太上皇,竟商决我之行政院长人选,那还有什么独立自主之可言。”[1]223
李铁铮卸任回国之后,1946年1月受命赴泰国与其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其间却受到美国的干涉,这更使得他意识到,国民政府根本没有实力取得与其名望相符[注]此时国民政府治下的中国表面上已经成为世界五大国之一。的外交地位[2]。1949年夏,李铁铮被任命为大使级代表,出席联合国非自治领土特别委员会。9月时宣布不就任在联合国的新职,转而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1953年李铁铮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的政治学博士学位,1956年获得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哲学博士学位,1962年获得哈德福特大学的终身教授职位。1964年经法国巴黎返回祖国,任外交学院教授。1973年、1976年两次赴美探亲,期间不断反驳外界反华言论。1976年赴美时,还任密西根大学、斯坦福大学高级研究员。1978年2月再度回国,历任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侨联顾问、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顾问、欧美同学会名誉副会长等。1990年在北京逝世。
通过上述事例可见李铁铮的拳拳爱国心,哪怕在对国民政府失望之后,“仍竭所能,做好本职工作,希望对国家对社会能稍有裨益,不完全是一个负债户。”[1]223在民国外交界工作的19年间,李铁铮积累了对“西藏问题”的认识,因此在哥大读博时李铁铮没有把更好入手、更有人脉基础的“中国与联合国”作为选题,而选择了对国家更有裨益的题目——《西藏历史上的法律地位》。
三、出版《西藏历史上的法律地位》以正视听
李铁铮的博士论文《西藏历史上的法律地位》于1956年在纽约出版,这是继沈宗濂和柳陞祺合著的《西藏与西藏人》之后又一本由中国人在西方出版的有关中国西藏地方的专著。而相比《西藏与西藏人》,李铁铮的《西藏历史上的法律地位》显然更专注于捍卫国家主权。在冷战早已拉开帷幕、麦克锡主义盛行的美国20世纪50年代,《西藏历史上的法律地位》得以出版已属不易,而因其材料详实、结构完整、论证逻辑缜密,受到了美国学术界的好评。
亚历克斯·韦曼(Alex Wayman)在写书评时还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在读博士生,但他精通藏语和梵文,指出了李铁铮在前两章错误使用了部分藏语的名称,但依旧认为“事实上,本书的其余部分,从第三章开始,对近代的政治历史作出了重要贡献。简而言之,作者提出了中国人的观点。我认为他在他的文献范围内是公平的。”[3]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舒勒·加曼(Schuyler Cammann)教授是一位以研究东方见长的著名美国人类学家,他对李铁铮著作的评价甚高,且用了大篇幅的内容来书写评论,这在西方学术界并不常见,可见加曼对《西藏历史上的法律地位》的认可。加曼在一开篇就不吝啬对该书的称赞,“这本写得很好,这本引人入胜的书非常详细地讨论了西藏的地位。”并认为:“既然李博士是一位受过学术训练的中国学者,并辅以长期的外交实践经验,他透彻和专业地使用中国历史资料,并用现代的学术标准去检验真相。在这一过程中,他悄悄地、但是专业地揭露了以往关于我国西藏的著作中的错误和缺点,包括审稿人的一些错误,并为那些可能在此领域跟随他的人设置了很高的学术标准。”同时,李铁铮的学术客观性也给加曼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非常值得称道的是,尽管他对祖国的忠诚总是显而易见的……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整个研究都保持了高度的客观性。”最后,加曼总结道:“当他完成这本书时,李博士完全有权说,正如他在结论中所总结的那样,就其地位和与外界的关系而言,西藏并没有什么神秘之处。无论之前在这些方面看起来多么神秘,现在已经被这本令人钦佩的书给梳理过了。作为关于西藏方面的综合历史——特别是对于过去两个世纪的事件——此刻这本书是最权威之作……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太可能被取代,并且如果将来出现有关这个主题的更多书籍,那么李博士的工作也为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应该得到每一位学习西藏历史和文化的学生的感激。”[4]
纵使《西藏历史上的法律地位》在美国学界得到了权威且广泛地认可,但也不必对一些质疑之声感到奇怪,如曾在1938年靠伪装进入拉萨的西北大学教授威廉·麦戈文(William McGovern),虽然面对李铁铮严密的论证,不得不承认此书是“值得推荐的”,却依旧带有强烈偏见地认为李铁铮是“有力的宣传家”[5]。如果我们仔细研读麦戈文的书评就会发现,麦戈文的看法正是典型的、如今称之为“新清史”的观点[注]麦戈文认为“只有当中国自己被外国人(如蒙古人和满族人)统治时,西藏人才会向中国的皇帝付出更多的代价”。这是“新清史”的典型论调,但实际上,这只是他们对中国历史的片面理解。,而讽刺的是,与其他许多“新清史”的代表人物一样,麦戈文教授在最基本的史实方面都没有弄清楚。在面对麦戈文的质疑——“西藏的文化主要来自中国,而较少来自印度”时,李铁铮在《西藏历史上的法律地位》1960年再版时专门予以回应,提出该观点来源于自认为最了解西藏地方的英国官员查尔斯·贝尔(Charles Bell)[注]查尔斯·阿尔弗雷德·贝尔(Sir Charles Alfred Bell,1870—1945年),生于加尔各答。早年,他入温切斯特学院(Winchester College),后成为英属印度政府职员(Indian Civil Service),于1908年被任命为英国驻锡金政治专员。1910年时与出走印度的十三世达赖喇嘛相识。在西姆拉会议期间,英方任命贝尔为西藏助理。1919年,他辞去英国驻锡金政治专员一职,但1920年,他再次出任锡金政治专员,赴拉萨。退休后在牛津大学从事研究。他在西藏拍摄的一些照片至今仍在牛津大学的皮特·里弗斯博物馆内。著有《十三世达赖喇嘛传》(Portrait of a Dalai Lama:The Life and Times of the Great Thirteenth)。他是英国插手中国西藏事务,策划“西藏独立”的主要代表人物。[1]序2。如果说麦戈文的观点还有值得反驳的余地,那么明尼苏达大学的沃纳·列维(Werner Levi)就显得不值一驳了,在简短的书评中,列维完全是在释放自己的情绪,将李铁铮的论述扭曲为“故事”[6]。
一位美国大学教授或许可以对李铁铮及其著作不以为意,但作为当事人的前锡金政治专员古德(Basil Gould)[注]巴兹尔·古德(Basil Gould,1883—1956年),早年在温彻斯特学院和牛津大学接受教育,1907年加入印度文官系统。从1912—1913年任英国驻江孜贸易代表。1913年英属印度政府派古德随同龙厦及4名西藏贵族子弟赴英,并提供“指导”。1926年,古德被派往驻阿富汗喀布尔的英国公使馆。于1933年被派往俾路支省,并与卡罗相识。1936年8月,古德率代表团赴拉萨与西藏地方政府就九世班禅返回西藏的可能性进行讨论,推行卡罗“积极的西藏政策”。1940年,强行到拉萨,试图参与十四世达赖的坐床仪式,但因座次低于吴忠信而未出席1940年2月22日的坐床大典。1945年退休。就不能对其等闲视之了。面对李铁铮就英国反对九世班禅返藏问题揭开的英国人的伪善,这位前英国官员不得不强烈否认,却提不出反对的立足点,只能承认西方读者需要更多中国学者的相关书籍。[7]
无论是好评还是批评,《西藏历史上的法律地位》在当时的西方学界掀起了不小的讨论风潮,这无疑在西方学术界中扎下了中国声音,至此之后如果有人满怀偏见地对中国的在藏主权提出质疑,那么李铁铮及其著作就是一堵不可绕行的墙;而故意忽视,或者无法在关键问题上提出有效论述的行为,其作就将沦为类似范普拉赫之流的宣传品;由此可见,李铁铮在法理论述上有效地捍卫了中国的在藏主权。特别是在1959年西藏地方反动上层叛乱及民主改革开始之后,“西藏问题”再度引发关注,李铁铮的《西藏历史上的法律地位》再版[注]1960年再版时更题名为《西藏今昔》(Tibet:today and yesterday)。,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成为捍卫中国在藏主权的学术论战高地。
四、投书《纽约时报》捍卫中国立场
如果说《西藏历史上的法律地位》是在学术领域为中国的在藏主权进行了缜密地论述,在西方学界产生了积极正面的影响,那么1959年至1960年,李铁铮3次投书《纽约时报》的行为则在意识形态偏见一边倒的舆论环境下,发出了中国声音,捍卫了中国立场。
李铁铮给《纽约时报》的投书第一篇刊登于1959年4月13日,名为《西藏的地位:历史事实说明她是中国的一部分》。李铁铮首先讽刺了印度的政策,“无论英国的西藏政策是否应该成为独立印度的遗产,印度对西藏的情况都有合理的担忧。她与西藏有着密切的宗教和文化联系”,但这正是因为“被称为‘西藏属国’的锡金和不丹……后来成为了英国的保护国,而现已被印度兼并”,并且“如剑桥历史记载,在有争议的克什米尔的拉达克曾属于西藏,而阿萨姆邦沿线从未有一个划定的边界。因此,西藏对印度来说才成为了一个防卫问题”。[8]突出了正是因为独立后的印度继承了英属印度的侵略性遗产,才导致了如今的问题。
面对美国舆论阵地的《纽约时报》,李铁铮也特别举出历史上美国官方的例子,“早在1792年,英国就承认西藏是中国的领土。1904年6月,美国驻英国大使约瑟夫·H·乔特(Joseph H.Choate)被指示让英国外交部了解美国国务院对英国进行的拉萨军事远征的看法。他提醒兰斯顿侯爵(Marquess of Lansdowne)[注]亨利·查理斯·基思·佩蒂·菲茨莫里斯(Henry Charles Keith Petty-Fitzmaurice,1845—1927年),第五世兰斯敦侯爵,英国政治家,先后担任加拿大总督、印度总督、战争大臣和外交大臣。他在自由党和保守党政府中都曾担任要职。,通过英国与中国政府就有关西藏的问题进行过的谈判,英国曾三次承认中国拥有主权,并认为英国‘仍将西藏视为中国统治的一部分’。”[8]
李铁铮还一再提醒美国舆论,西藏地方的自治是来自中国中央政府的授权,“1951年5月23日,在北京签署的‘十七条协议’明确规定了他们的自治权”。而从国际法来看,中国的在藏主权是早已被独立后的印度确认过的,“1954年4月29日,印度与中国签署了一项协议,接受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原则”[8]。
1960年5月2日,李铁铮再次投书《纽约时报》,在这篇名为《中国的主张:用协定的价值来处理印藏边界争议》的文章中,李铁铮提出了一个非常本质的问题,“然而,这里没有人知道麦克马洪线被划到了哪里。”[9]事实上,早在1919年时任英国驻华公使的朱尔典在逼催北洋政府开议“西藏问题”时就曾提出“边界的安排以条约文本为准,而不是地图”[注]参见英国外交部档案,FO 371/3688,Sir J.Jordan to Earl Curzon,Peking,No.253,June1 1919.。显然,在朱尔典看来,所谓的麦克马洪线并不具备什么参考价值。而在英属印度政府中,如果不是以奥拉夫·卡罗(Olaf Caroe)[注]奥拉夫·卡罗(Olaf Caroe,1892—1981年),卡罗早年在温彻斯特就学,后就读于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前往印度服役,从此对“大博弈”(the Great Game)和印度事务产生浓厚兴趣。卡罗于1919年返回英格兰,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文官考试,但他放弃了本可以在财政部和外交部的令人羡慕的工作,要求前往印度任职。卡罗首先被分配到旁遮普,后于1923年进入印度政治部的外交部门(the Foreign Department)工作。1933年,卡罗升任西北边境省的首席大臣(Chief Secretary)。1934年,卡罗再度获得升迁,来到德里,成为外交部门的副大臣。按照兰姆的说法,作为外务副大臣的卡罗对其上司外务大臣麦特卡尔夫爵士(Sir Aubrey Metcalfe)具有极大的影响力,甚至一些重要文件都是由卡罗直接签署的。1939年,卡罗正式成为英属印度政府的对外事务大臣,直到1946年升任西北边境省总督,长期负责对外事务部的卡罗具有相当宽泛的权限,依据对外事务部的传统职能,卡罗实际上成为英属印度边界问题的决策者,甚至白厅(Whitehall)都需要定期征询卡罗的意见。1947年,印度独立,但卡罗仍然担任印度政府的外交顾问。为首的“前进派”在1930年代再度掌握实权,强行将无效的“西姆拉条约”塞进《艾奇逊条约集》[注]对于伪造的1929年《艾奇逊条约集》,李铁铮早年撰写博士论文期间就已发现,甚至将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所藏的真实版本拍照留存。对于这一问题,兰姆和柳陞祺先生也已经进行过精彩的论述,参见柳陞祺:《拉萨旧事(1944—1949)》,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54—199页。以及Alastair Lamb,Tibet,China & lndia,1914-1950,A History of Imperial Diplomacy,Hertingfordbury:Roxford Books,1989:350—373.,那么麦克马洪线早已被世人遗忘。由于知晓麦克马洪线是站不住脚的,李铁铮还特意指出美国国务院对此的态度,“也许这就是国务卿赫脱[注]赫脱(Christian Archibald Herter,1895-1966年):美国政治家,曾任马萨诸塞州州长、第53任美国国务卿和首任美国贸易代表。没有发表意见的原因。”[9]李铁铮还一再提醒美国民众,“无论是帝国时期或共和时期,国民党或共产党,没有一届中国政府接受过所谓的麦克马洪线”,并引用了查尔斯·贝尔的《十三世达赖喇嘛传》(Portrait of a Dalai Lama)来说明十三世达赖喇嘛对于西姆拉会议内容的不满。[9]
对于有印度外交官员认为中国在国际法下受到“西姆拉条约”约束的说法,李铁铮也予以嘲笑并反驳。引用台克满(Eric Teichman)[注]艾瑞克·台克满(Sir Eric Teichman,1884—1944年),英国外交官和东方学者,在剑桥大学的冈维尔和凯斯学院接受教育。在中亚进行过数次旅行。1917—1918年参与调解第一次康藏纠纷。在英国外交界具有一定名气,被形容为“风度翩翩的人物”。台克满去世前曾担任英国驻重庆大使馆顾问,反对英属印度政府的西藏政策。著有《领事官在中国西北的旅行》(Travels of a Consular Officer in North West China)、《领事官在藏东的旅行》(Travels of a Consular Officer in Eastern Tibet)和《中国事务:对中华民国近代历史和现状的考察》(Affairs of China:a Survey of the Recent History and Present Circumstance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等书。的《领事官在藏东的旅行》(Travels of a Consular Officer in Eastern Tibet)中的内容,“西姆拉会议最终在1914年夏天破产了,没有达成任何共识”;并对印度外交官员的无知进行嘲讽,“任何一位国际法专业的学生都会承认‘西姆拉条约’没有作为国际条约的价值”。[9]而正是因为西藏地方不具有签署国际条约的资格,“英国政府才发现有必要与中国签订一项条约,来使在1904年军事占领期间强加给西藏人的《拉萨条约》合法化。”[9]文末,李铁铮再次强调,作为真正的国际条约,1954年的《中印协定》,“明确接受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原则。”[9]
1960年11月19日,李铁铮以《西藏地位概述》第三度投书《纽约时报》,文章主要反驳了在美国的一些印度人的错误观点,一再提醒他们不要忘记1954年的《中印协定》,而“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无论是什么党派或什么宗教的中国人,都如此认为”。[10]对于已经开始的西藏民主改革,认为美国人民不应该盲目听信“那些封建领主和前英国随从”[10]。
五、数十年影响犹存
正如加曼所言:“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太可能被取代”[4],李铁铮的《西藏历史上的法律地位》在其出版后的几十年内成为西方学者在有关西藏的论述中引用率最高的中国视角的著作。如在戈伦夫的《现代西藏的诞生》[11]中,戈伦夫对李铁铮观点的引用几乎贯穿了其著作中对各个标志性事件的论述。
戈尔斯坦的《喇嘛王国的覆灭》[12]在有关近代西藏的著作中是独树一帜的,戈尔斯坦作为一位人类学家,对多达80位相关人物的访谈构成了《喇嘛王国的覆灭》的论述核心。这种研究范式无论在戈尔斯坦成书之时,还是现在,都是新颖且耗费精力的,但其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虽然戈尔斯坦公然标榜自己的“客观”与“中立”,我们也有理由相信这是他的主观意愿,但这种研究方式必然受到被访谈对象立场的制约。戈尔斯坦显然也意识到了这点,因此他在书中引用了不少英国外交部和印度事务部档案,但即便如此,如果没有汉文资料的加入仍会使得论述的视角单一。为弥补这一问题,戈尔斯坦在书中大量引用李铁铮的《西藏历史上的法律地位》,从十三世达赖喇嘛与九世班禅的关系到黄慕松入藏致祭、从灵童的寻找到热振事件、从西藏地方代表出席制宪国民大会到“驱汉事件”,在贯穿近代西藏地方的几乎所有大事件中,戈尔斯坦都引用了李铁铮的说法。特别是在有关十三世达赖喇嘛晚年的内向态度与派遣贡觉仲尼到京、入藏,以及刘曼卿、谢国梁入藏的内容上,几乎是连续引用李铁铮的观点。
相比于戈尔斯坦,兰姆(Alastair Lamb)是一位纯粹的历史学者,其著作《西藏、中国与印度,1914—1950,帝国外交史》(Tibet,China & lndia,1914-1950,A History of Imperial Diplomacy)[13]虽然没有戈尔斯坦的访谈那么鲜活,但兰姆对于历史细节的抓取却更引人入胜。但与戈尔斯坦一样,为弥补汉文资料的不足,兰姆同样大量引用了李铁铮《西藏历史上的法律地位》中的内容,并认为“李铁铮显然曾—度与蒙藏委员会有过联系,他大量利用了蒙藏委员会的档案……这些资料对于无法使用任何汉文资料的人来说是极为有用的”[13]132。在与兰姆接触过的海量英国外交部档案做了对比之后,兰姆得出他的结论,“李铁铮的记述同英国方面的资料并不存在根本冲突”[13]182。甚至在有关吴忠信主持十四世达赖坐床的论述上,兰姆更同意李铁铮的观点,即中国中央政府主导了整个过程;而对古德未能出席仪式的蹩脚借口进行了反驳。[13]297在有关川康局势方面,兰姆同样看重李铁铮的观点[13]200,这对于一般的西方学者或许不足为奇,他们需要通过中国学者来了解那一时期复杂的军阀内斗。但兰姆的父亲蓝来讷爵士(Sir Lionel Henry Lamb)在华32年,1952年成为英国驻北京代办[注]相当于临时大使。,用兰姆的话说便是:“他对20世纪20年代四川盘根错节的政局的了解,对我尤为重要”[13]8。而兰姆在此方面对李铁铮的观点的重视更凸显其在西方的学术地位。
正是由于李铁铮《西藏历史上的法律地位》在西方出版后于法理上无可辩驳地捍卫了中国的在藏主权,自然引得一些帝国主义分子的不满,其中又以英国最后一任驻拉萨官员黎吉生(Hugh Richardson)[注]黎吉生(Hugh Edward Richardson,1905—2000年),早年在牛津大学基布尔学院学习。1930年10月9日进入印度文官系统,之后被派往俾路支省。1936年7月,他被任命为英国驻拉萨贸易代表。1936年至1940年,1946年至1950年,成为英国和独立后的印度驻拉萨代表。他是英国插手中国西藏事务的代表人物之一。为代表。如果说西方学界对于李铁铮的批评更集中于论述用语上的小瑕疵,那么黎吉生则是急不可耐地对李铁铮的几乎所有核心观点进行攻击。当黎吉生还服务于英属印度政府时,他的心腹大患是沈宗濂及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注]沈宗濂及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曾一度在拉萨创造了有利于中央政府的条件,古德本人也认为沈宗濂对英国的利益是一个极大的潜在威胁。参见印度事务部档案IOR L/P&S/12/4217,India to Secretary of State for India,July 8,1944.,但在黎吉生的《西藏简史》[14]中,仅仅提到沈宗濂4次,而对李铁铮的攻击却高达14次[注]根据黎吉生所著的《西藏简史》统计而出。。尽管作为当事人的黎吉生对一些历史细节的掌握程度可能优于李铁铮,但却无法在法理上驳倒李铁铮的《西藏历史上的法律地位》,正如同为英国人的兰姆所说,黎吉生对一些文本的论述,只是为了“令英国人听起来更顺耳一些”[13]237。
从上述的西方研究近代西藏的学者对李铁铮观点的引用,可见其观点及著作《西藏历史上的法律地位》在西方的影响力,至几十年而不衰。李铁铮曾希望工作能对国家稍有裨益、做出对国家有用的题目[1]180,223,在这点上,李铁铮可谓做到了“不忘初心”。
六、结论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的重要论述,西藏的稳定关系中国安全与发展的全局,而这又需要“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中做好西藏工作”。在上个世纪50年代的特殊历史背景下,中国国内的声音,无论是学术还是舆论上的,都很难传递到西方世界。而李铁铮在这样的背景下,自发地扮演了中国观点的发声者。特别是在西藏民主改革前后,由于冷战与地缘政治的关系,“西藏问题”在国际上颇受关注,李铁铮在这一关键时期,有效传递了正确的西藏地方历史,特别是近代以来的西藏地方与中国中央政府所属关系的历史。
改革开放以来,“西藏问题”一直都是国内社科学界关注的热点,也取得非常令人瞩目的成就。但真正将“国际法”与“西藏近代历史”如此有效地结合起来的著作却是凤毛麟角,从这个角度看,李铁铮的《西藏历史上的法律地位》依旧具有时代性,是不过时的。这与李铁铮的职业经历和知识构成是紧密相关的,在其著作中非常善于引用西方例子,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这样的书写模式很容易让西方读者理解,也更容易撕下某些西方人的虚伪面具。
无论李铁铮为了“对国家有所裨益”而作的《西藏历史上的法律地位》,还是3篇投书《纽约时报》的文章,都在致力于维护国家的统一,这样的爱国情怀正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民族精神。而李铁铮所努力捍卫的国家统一,正是西藏民主改革60年来取得各项成就的基础,这些成就反过来又铸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使得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