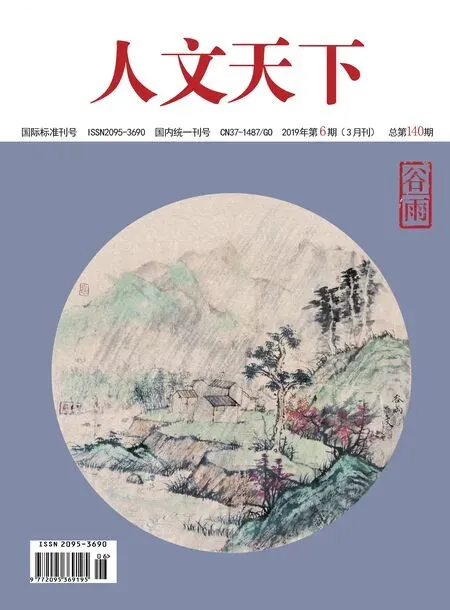非遗在多元格局中需要处理的五种关系
非遗是劳动人民生活、生产实践的积累和结晶,反映了特定时期和区域内人类生产生活的方式和精神状态,具有重要的历史认识价值、文化精神价值、社会经济价值和艺术审美价值。因此,对非遗的挖掘和保护是对人类创造力和生活智慧的尊重与认可。
非遗在20世纪中叶以前长期处于活态传承和自然演变的状态,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各个国家相继订立公约并出台相关法律之后,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非遗自然生存的状态逐渐被打破,其传承与发展也受到各方力量的影响。非遗在享受关注带来的红利同时,也备受各方力量的冲击。
非遗工作由于涵盖面广,业务关联性强,长期处于政府主导、民间配合、学者参与、商业介入和媒体关注的状态之中。工作业务关联者和利益关联者围绕非遗从不同的层面施力,这些作用力都指向非遗项目及其传承人。作为非遗项目的持有者和传承者,传承人需要对业务关联各方施加的力量进行吸收、中和和分解,以确保非遗项目在有效使用外界力量的同时保持良性发展,不被任何一方的力量裹挟,也不错失机会和平台。
一、非遗的文化基因与国家的精神诉求
(一)非遗为国家提供文化元素,满足国家的精神诉求
国家的凝聚力来自民众对文化的认同,国家层面重视文化的挖掘、传承与提炼,并将各类文化塑造为国家精神,不仅可以丰富国家文化的内涵,更有利于增强文化自信,展现国家软实力。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从不同的层面填补正史中民间生活的空缺和不足,反应不同时期国家在文化生活方面的文明程度,佐证和支撑顶层政治文明程度和社会文明程度,也为构筑新时期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提供丰富的文化资源。
(二)国家的主导作用保障了非遗事业的稳步发展
我国自2004年批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和2005年印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开始,国家层面为非遗的发展制定了健全的法律法规,国家的推动让非遗逐步进入民众的视野。随后通过一系列普查、申报、立法等措施规范非遗工作,通过宣传、展演、文化日等措施扩大非遗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国家以强有力的态势进行统筹规划,制定规则,组织实施。非遗项目作为被挖掘和保护的对象,受到了空前的关注,获得了极大的展示平台,非遗工作也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发展态势。
当下,国家的非遗保护工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总书记关于弘扬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重要论述作为主导思想,使非遗保护工作思路更加明确,机制更加健全,措施更加得当,工作更加有序。
国家在非遗工作中起着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作用,让沉寂于民间上千年的遗产快速全面的展示在世人面前,让世界对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有了更加全面和深刻的了解。
(三)非遗保护工作中出现的问题
项兆龙在2018年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政府在非遗保护方面的主要职责,是保护和培育非遗传承发展的文化生态,支持开展非遗的传承实践,使其在当代生活中得到延续和发展,使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成为社会自觉。”这一论述为非遗保护工作者的工作内容和工作方法进行了定位,明确了当下的工作职责和长期的工作目标。
在过去几年的保护实践中,由于中国非遗保护工作起步晚,工作人员的整体素质参差不齐,出现了很多问题。
第一,在思想解读方面不深入,停留在表面,没有深层次理解非遗保护的长远目标和现实意义,出现片面解读甚至误读的现象。思想上的误读导致非遗保护在路径的选择上和工作措施上出现了偏差。
第二,在政策执行方面出现了过度的事业诉求、急功近利和短视的现象,没有掌握文化遗产的内涵及其发展的规律,导致某些项目被破坏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有别于普通的行政工作。普通的行政工作以解决问题为导向,非遗保护工作以建立长效保护机制、营造保护氛围为导向。非遗保护工作不仅仅是解决当下的问题,更需要掌握文化的发展规律,预见未来的发展走向,并为其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因此,非遗保护工作在政策的指引下,需要针对不同的项目类型进行专门化的研究,制定符合其发展规律的保护措施。
第三,在具体工作中实行“一刀切”,没有针对不同的项目类别设计专门的保护策略,也未能及时根据项目的现状及时调整保护措施,造成保护方法不得当、保护不及时、错失保护关键期等不可挽回的后果。非遗项目涉及面广,内涵丰富,不同类型的非遗项目需要专业人士设计保护措施,然而长期进行非遗保护工作的人员固化严重,这导致非遗保护工作出现粗线条式保护,把一种方法使用到所有的项目保护工作中,造成方法不得当,保护效果不明显。
同时,随着非遗保护工作的持续推进,很多非遗项目的存活状态已经得到极大的改变:有些项目的生存环境已经由民间走向国际;有些项目的生存状态已经由濒临灭绝走向繁荣生长;有些项目的传承方式已经由家族、师徒传承走向大众传习;有些项目的功能已经由支持生产生活变为娱乐休闲。在这一系列的变化面前,非遗保护工作者鲜少因时因势而改变工作方式和工作内容。这种程式化的工作方式在非遗保护工作初期曾起到过积极的推动作用,全国上下能够及时形成合力,充分挖掘和保护了散落于民间的非遗。但是当工作推进到一定阶段之后,各种非遗项目就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态势,需要根据项目的类别、现状、自身发展规律和发展阶段有针对性地制定工作路线和方式。
第四,以政府为主导的非遗保护工作,使得民间习惯性以政府的官方认定为圭臬,出现抢报、乱报的现象。调研中发现,原本处于协作关系的项目合作者,为了争抢传承人的资格,出现互相拆台和不再合作的现象。此类现象打破了原有的生存模式,使得原本存活状态良好的非遗项目因为合作者的分裂而无法继续传承。
同时,过分强调政府的作用,也助长了传承人等、靠、要的思想,使原本可以独立存活的非遗项目,失去自力更生的意愿和再创造的动力,坐等政府的扶持和资助。
第五,过度包装使非遗失去了本真。针对一个非遗项目,地方文化主管部门往往会对其进行二次打磨和改造,借传承人的技艺和身份来宣传自己的文化和思想,将其打造成一张张地方文化名片,然后通过一系列研讨会、交流会等进行上色渲染,通过主题文化节、博览会等进行宣传推介。在这个过程中,非遗传承人从现实意义上来说是获益的,因为所有的文化阐释工作和品牌打造与宣传工作都有专业团队在做,而自己只需适时“表演”技艺绝活即可。可能唯一让他们为难的事就是背诵别人写好的发言稿,以应对媒体的采访。但这对非遗项目来说,是灭顶之灾,导致非遗最重要“本真性”和“原汁原味”在逐步被消解、被边缘化、被有意的遗漏,其文化内涵也被强行掠夺或嫁接。
调研中发现,对地方文化事项的宣传与推介,对地方文化精神的挖掘和打造是地方政府文化部门的使命和任务,每一个项目的包装和每一张名片的打造都是自己工作状态和效果的展示。文化主管部门或事业单位会以挖掘到地方尘封已久的文化瑰宝为业绩,如果挖不到就包装一个出来,以此证明工作团队的专业性和工作实施的有效性。
第六,在非遗宣讲教育工作中走精英话语路线,没有把非遗项目作为主体,剥夺了民间的话语权。非遗项目大多来自民间,在民间具有深厚的生存土壤,其生存和传播方式不仅具有极强的民间色彩,也反映了世俗的生活方式。非遗保护工作将非遗从民间“请”到了大众面前,进行跨区域跨阶层的传播,为非遗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舞台。非遗保护工作者在非遗项目宣讲和对外交流的过程中,习惯性按照精英知识体系和思维模式对非遗项目进行包装和宣传,传达出来的仍然是精英阶层的价值观,抑制了民间思想和生活方式的传播,非遗传承人在这里仅作为某种思想的辅助和佐证。
笔者在调研中发现,传承人对话语权的重视程度越来越深。在非遗工作挖掘阶段,传承人希望借助政府力量将自己的项目推荐出去,所以宁愿让渡话语权,来获得被推荐的资格。在非遗项目进入名录、知名度不断提高的情况下,非遗传承人希望有更多的场合和平台展示自己的技艺,传播非遗文化。随着关注度的增加,他们越来越重视文化的本真性,对过度包装的官方话语体系持反感或不配合的态度。而目前话语权的丢失极大地降低了传承人的荣誉获得感和传承热情。
二、非遗的文化元素与学者的理论阐释
(一)非遗为学者研究文化提供了新的视角
国家的行政推动,需要学术界进行理论的构建和学理的阐释。学者以文化专家的身份走进非遗,研究非遗的生存现状、挖掘非遗的文化内涵、提炼非遗的价值、构建非遗理论。在研究非遗的过程中,非遗项目是被观摩和研究的对象,传承人是被访谈的对象。学者除了研究工艺流程、历史沿革、存活现状之外,其主要任务是挖掘隐藏在非遗项目中的文化内涵和价值。
(二)学者对非遗文化的提炼及阐释
对于非遗传承人来说,由于文化程度和工作性质原因,他们最擅长的是技艺展示,而不擅长语言表述和文字表达,如果让他们讲述文化内涵和价值就显得捉襟见肘,词不达意。传承人出于各方面的考虑,为了让自己所持有的项目尽快进入大众视野,跻身高雅文化殿堂,被主流文化认可,会选择让渡自己的话语权,让学者来讲述,接受学者的界定。
学者获得话语权之后,一开始还是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来归纳总结和提炼,但是一段时间之后,这些调研的内容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文化需求了,部分学者开始将一些文化理论、价值体系和社会功能附会到某项非遗之上。在学者的“包装”下,非遗项目逐渐变得丰满,有骨有肉有灵魂,从文化价值、精神价值、审美价值,到社会功能,再到现实的教育价值、经济价值都体现得淋漓精致,完美无缺,不可替代。学者的“包装”让传承人欣喜若狂或是哭笑不得,但又不得不接受,因为“包装”后的项目确实显得更加有内涵。
学者笔下的非遗和传承人持有的非遗有很大的差别,学者挖掘出来的文化色彩是很多非遗传承人在以往的传承过程中没有体现的。这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由于传承人的文化知识欠缺,无法觉察到自己所持项目的文化内涵,即使发现了,也无法用恰当的语言表述出来。第二,学者将文化理论体系套用在非遗项目身上,然后为原本平淡的项目赋予某种文化和功能,而这种文化和功能正好与该项目的表现形式相契合。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很容易产生一些列问题,如很多项目的历史价值和功能未被学者挖掘出来,或者是选择性的遗漏。另外,学者很容易创造性地将当代的主流价值嫁接在传统的非遗项目之上,借传统技艺来宣传主流价值观,或者借非遗项目来阐释自己的文化理论。
非遗是系统的文化现象,其研究工作必须秉持求真务实的态度和方法。正如项兆伦所言:“研究非遗需要有宽厚的知识面和学术素养,需要做扎实的田野调查。在非遗研究领域,特别要提倡求真务实、逻辑严谨,提倡学术性、实践性。非遗研究是与人民大众打交道,与日常生活打交道,与广大传承人群的文化表达权利打交道,尤其要尊重科学,尊重常识,尊重实践,尊重权利,切忌动辄用似是而非的概念和帽子唬人。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不仅要深入研究公约,还要深入研究两个相关文件,一是操作指南,二是伦理原则。”
三、企业的利益诉求与非遗的科学发展
非遗保护工作一开始,很多地方政府和学者即提出开发性保护的概念,就是让企业参与到非遗的保护工作中来,用现代的工艺和方式开发非遗项目。让非遗与企业建立关系,这在概念上是一个互利共赢的设计。一方面通过企业模式,可以让非遗项目尽快融入到现代生活之中,融入到创新体系之中;另一方面,企业可以借助文化的力量发展壮大。但是在实际执行中却造成了非遗文化与非遗产业两张皮,造成非遗产业扭曲非遗文化,非遗文化拉垮非遗产业的局面。
(一)非遗文化对企业的诱与利
近年来,非遗项目成为国家关注的热点,也相应地成为商家招揽生意的道具。企业通过一系列的申报、认定之后,生产产品的某项技艺摇身成为政府非遗保护项目或者注册为“老字号”,然后以此为卖点推广自己的产品,但是真正的传统技艺在其商品中有多少体现,是值得考量的。很多企业在现实生产中已经抛弃了申请为非遗的技艺,仅将非遗作为谋求经济利益的工具,使其成为经济的附庸,传承人甚至沦为虚假宣传的帮凶。
文化认同所产生的共鸣能够汇聚资源,因此企业家乐意借文化项目获取社会的关注,凝聚人气,以此谋取利益的最大化。同时企业家也擅长给经济披上文化的外衣,虽然“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广受文化学者的诟病,但也阻止不了企业和地方政府的逐利共谋。面对质疑声音,很多地方只是在概念和宣传字眼上稍做改动,但实质还是新瓶装旧酒。
(二)产业化对非遗的利与弊
很多非遗项目有走商业路线的历史和传统,比如传统手工艺靠生产产品获取经济利益,传统曲艺靠提供娱乐服务获取经济利益。对于这一类型的非遗项目来说,企业的参与不仅能为其长期的发展提供资金保障,还可以通过商业运作,拓展市场,扩大辐射面,提升影响力,更可以让非遗传承人安心研究自己的技艺,将产品或服务打造好,有利于非遗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但是有很多项目在传统社会中只在特定场合出现,来完成其承担的社会功能,不是走市场路线。如果强行产业化,会导致该类型的非遗项目的文化内涵变质。比如祭祀活动,在传统的社会中有敬畏生命、崇拜祖先、教化后人和睦邻团结的功能,如果将其产业化,用于商业表演,就异化了其社会功能,让当代人对传统社会的仪式产生误解,导致文化的误读,更不利于此类非遗项目的传承与发展。
非遗文化来自于生活和生产,更离不开生活和生产,任何不尊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为和不恰当的保护措施、不合规律的开发措施不仅扭曲了非遗的文化意义和社会功能,更会导致非遗遭到破坏。当然,任何禁锢和扼制非遗传承人的创造性表达权利的保守理念和行为,也会扼杀非遗的生命力,错失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机遇。
四、媒体的热点诉求与非遗的本真性保护
非遗在当代的传承与发展离不开媒体的关注和报道。媒体对非遗技艺与文化的传播起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媒体能让沉寂千年的非遗项目在一夜之间重新绽放光彩,也能让蒸蒸日上的非遗产业在一夜之间声名狼藉。
媒体有追逐热点的行业属性,只有紧抓热点才能走在前沿,保证关注度和点击率。因此,媒体在报道非遗时很少采用平实的方式陈述现实,而是选择从非遗的某一个点入手,选取项目的某一个部分,以夸张的笔法渲染其独特性,进而满足观者的猎奇心理,或是带有某种情绪片面报道非遗的经济效益或传承现状。
媒体对非遗的报道存在片面性,对非遗的解读也有断章取义的现象,它很少关注非遗的整体性,常以显眼的标题抓取读者的眼球。这种报道方式虽然可以引起读者一时的关注,但是对于非遗的整体活态传承却造成了致命的破坏。非遗的“整体性”被媒体肢解,传承人也会在媒体的裹挟下,或者在利益的驱使下只专注于观者喜闻乐见的部分技艺,而不再钻研支撑起非遗项目的其它技艺,甚至在授徒的时候也只是将部分技艺传习,新一代传承人充其量只能算是零碎技艺的持有者,而不能算是某项非遗的传承人,因为零碎的技艺已经不能组合成非遗项目。
五、游客的猎奇心理与传承人的坚守
非遗热改变了传承人以往的生活状态,他们经常被邀请参加旅游文化节、商品博览会、主题文化日等各类活动。在这些活动上,传承人需要一遍遍展示自己的显性技艺,而这些技艺因其独特性和稀有性会吸引很多游客驻步观赏。
传承人原来是一门心思研究自己的技艺,进行技艺的学习和钻研,以习得精湛的技艺为己任。但是在类似于快餐的文化活动中,他们只需要展示既有技艺就可以获得游客的赞赏,获得不菲的收入。
游客的猎奇心理和快餐式文化消费,以及对陌生文化独特性的过分追求,既让传承人走出了非遗项目生存的场域,也破坏了技艺传承的规律。传承人不再长期身处非遗生长的环境,感受和领悟非遗项目的文化内涵,而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展演中消磨自己的意志,不再有毅力和定力去钻研技艺,也不再追求技艺的精进。在这一层面上,不能归责于游客和观者,因为他们仅仅是一个消费者,消费自己喜欢的事和物,以获取感官的满足,传承技艺不是他们的责任和义务。
对于传承人短期逐利的现象,首先,文化主管部门需要针对这一现象及时教育引导传承人,同时制定相应的考核指标,以规范传承人的行为;其次,行业协会需要加大对行业标准的制定与执行,实行行业准入和退出机制,及时清理不守行业规范的个人和团体;最后,传承人需要强化为国家传艺的使命感,传承人的技艺不仅仅是个人安身立命的本领,更是国家文化基因、国家技艺、人民劳动智慧的一部分,所以,传承人必须有为国家传绝学的使命感。
结语
随着技术的发展,大众审美的变化,生活方式的改变,社会流动的加剧,非遗面临着来自内外部的各种挑战,任何因素的改变都会对非遗的传承产生影响。所以,在“非遗热”的盛宴之后,应该让其逐渐回归到原有的状态中。让非遗在国家的倡导中、媒体的正确引导中、学者的护航中、传承人专注中和全社会的呵护中保持本真,活态传承,自然生长。过多的关注和干涉只会破坏其生长的环境,打乱其传承的规律,阻碍其发展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