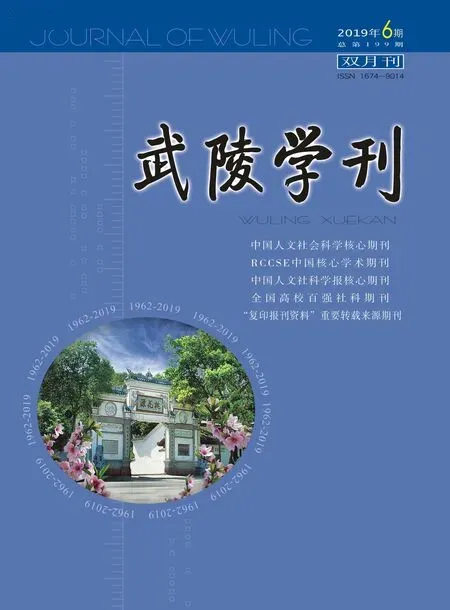论黄宗羲《明儒学案》对明代关学的新建构
甄洪永,李 珂
(山西师范大学 戏剧与影视学院,山西 临汾 041004)
《关学编》是明代冯从吾为识“关中理学之大略”[1]自序而撰写的著作,《明儒学案》也是总结明代学术史的翘楚之作。两者在时间跨度、学者遴选方面都存在交集,因而就有了比较研究的可能。黄宗羲在总结王承裕的学术渊源时称,“冯少墟以为,先生之学,皆本之家庭也”[2]180,意谓王承裕的学术思想来自于其父王恕。冯氏之说见于《关学编》卷三《平川王先生》:“先生著述种种,盖多本之庭训云。”[1]39这表明,黄宗羲在撰写《明儒学案》明代关学部分时参考过《关学编》②。《明儒学案》对《关学编》提供的文献信息进行了大幅删削,并增加了黄宗羲的按语,最终形成了《明儒学案》的相关文本。无论是关学研究,还是黄宗羲《明儒学案》研究,对此问题的探讨尚不深入。利用史源学方法,考察两者之间的异同,将是深化两者研究的有效思路。
一、纳关学入河东之学:《明儒学案》对关中学术脉络的重新厘定
《关学编》是冯从吾为陕西关中学者而撰写,带有鲜明的地域性特征,侯外庐称:“《关学编》,原不过是地志的性质。”[3]135《明儒学案》则是总结有明一代的学术史著作,两者在编纂思想上就有明显的分别。黄宗羲总结明代关中学术时,既要参考《关学编》提供的学术信息,又要完成对明代关中学术脉络的重新厘定。
首先,为了最大程度上勾勒出明代关学的学术脉络,《明儒学案》特地增加了薛瑄、阎禹锡、王鸿儒、王恕4人。通观《河东学案》、《三原学案》所遴选的学者,增加的这4人都不在《关学编》中,薛瑄、阎禹锡、王鸿儒不能入选的原因很简单,他们不是陕西关中人,自然不会出现在《关学编》中。王恕为陕西三原人,《关学编》未其立传,却将王恕之子王承裕视为关学的核心成员之一。黄宗羲推崇王恕对社会有责任有担当,“先生之学,大抵推之事为之际,以得其心安者,故随地可以自见”[2]175。故特意表彰王恕,并将其作为三原学派的开创者。唯有如此,王恕的儿子、弟子也才有学派归属。
其次,《明儒学案》对《关学编》中的明代关中学者进行了更为严格的筛选。《关学编》卷三、四为明代部分,共收录了段坚、张杰、周蕙、王爵、张鼎、张锐、李锦(字在中)、李锦(字仲白)、薛敬之、王承裕、吕柟、马理、何永达、韩邦奇、韩邦靖、南大吉、尚班爵、杨爵、吕潜、张节、李挺、郭郛、王之士等共计23人。《明儒学案》则删除了张锐、李锦(字仲白)、何永达、韩邦靖、尚班爵等5人,只保留了18人。
再次,《明儒学案》将自己重新选择的学者,分别置于不同的学案中,从而梳理出清晰的学术脉络。黄宗羲将段坚、张杰、周蕙、王爵、张鼎、李锦(字在中)、薛敬之、吕柟、吕潜、张节、李挺、郭郛、王之士等12人列入《河东学案》;将王承裕、马理、韩邦奇、杨爵、王之士等5人列入《三原学案》;将南大吉1人列入《北方王门学案》。陈祖武认为这符合明代学术发展事实:“明代理学,当阳明学崛起之前,朱子学在北方得薛瑄恪守,流播秦晋,濡染一方,而有河东之学与关学之谓。黄宗羲认为,其开派宗师当推薛瑄,所以《明儒学案》卷七、八,以《河东学案》述及薛瑄及周蕙、吕柟等十五人学说之传承。随后则于卷九辟为《三原学案》,以述王恕、韩邦奇、杨爵等六位关学大师之学。”[4]陈氏此语诚是。
经过黄宗羲的梳理,明代关学的学术脉络已经基本明朗。阎禹锡、张鼎、张杰就学于薛瑄,段坚就学于阎禹锡,周蕙就学于段坚,薛敬之、李锦就学于周蕙,吕柟师事薛敬之,吕潜、张节、李挺又师事吕柟,郭郛与吕潜又为同学。有了《三原学案》中的王恕,王承裕、马理、韩邦奇、杨爵、王之士等学者也在学术谱系找到了合适的位置。
经过此番梳理之后,黄宗羲也完成了对明代关中学术脉络的重新厘定,也就是将明代关学纳入河东之学。《关学编》则将关学的学术源头追溯到先秦时期的秦子、燕子、石作子、壤驷子,于宋代尤推重张载。两相比较,差别比较明显。
二、“关学”宗薛氏:《明儒学案》强化薛瑄对关中学者的接引价值
由于黄宗羲认为薛瑄是明代关学的理论先导③,也就是所谓的“关学大概宗薛氏”[2]172,所以在《关学编》中并没有出现、也不可能出现的山西籍学者薛瑄,就成为黄宗羲的重点书写对象。表现有二:首先,《关学编》所提供的学者的师承、交游信息比较丰富,某些措辞客观上起到了弱化薛瑄的效果,《明儒学案》却特意提高薛瑄的影响力。例如张杰与薛瑄的交游一节,《关学编》表述为:“一日薛文清公过赵城,与先生论身心性命之学。文清公叹服而去,先生之学由是益深。”[1]29《明儒学案》称:“文清过赵城,先生以所得质之,文清为之证明,由是其学益深。”[2]138在《关学编》中,薛瑄成了张杰学术思想的信服者。在《明儒学案》中,张杰从薛瑄处印证了自己的学术,薛瑄是学术精湛的长者形象。在《关学编》中被弱化了的薛瑄在《明儒学案》得到了强化。
其次,《明儒学案》对关中学者转益多师的情形也进行了选择性处理。此类情况较为复杂,大致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在遇到薛瑄及其弟子之前,往往另有一段求学历程,《关学编》对此交代得比较清楚,《明儒学案》往往会删除这段求学历程。如段坚在正统甲子之前居兰州,“凡当世宿儒宦游于兰者,无不师之”[1]26;李锦为诸生时,“受《易》于乡先生董君德昭之门”[1]34;吕潜“师事蜀进士赵木溪氏,闻木溪氏讲义理之学而悦,于是学甚力”[1]55。这些信息都被《明儒学案》删除掉了,从而达到了强化薛瑄的目的。
第二,某位关中学者虽然转益多师,但如果都来自薛瑄一派,《明儒学案》皆予以全部展示。如周蕙“闻段容思讲学,时往听之……又受学于安邑李昶。李昶者,景泰丙子举人,授清水教谕,文清之门人也”[2]144。周蕙向段坚问学,又向李昶问学。段坚是薛瑄的二传弟子,而李昶则是薛瑄的入室弟子,这样非但不会降低薛瑄的影响,反而会提高薛瑄的影响力。
第三,如果该学者既受学于薛瑄或其后学,又与其他《明儒学案》曾专门立传者有所交往,《明儒学案》也予以全部展示,但这样操作并不会降低薛瑄的影响力。如吕柟师事薛敬之,但又与湛若水、邹守益共主讲席,此时吕柟的身份是讲席老师,其学问已经成型,反而能彰显薛敬之对吕柟的教育之功,故《明儒学案》予以保留。但《关学编》提供的吕柟少时曾师事高俦、孙昂等信息则被黄宗羲删除。
《明儒学案》对明代关中学者师承、交游的选择性处理,其核心目的就是强化薛瑄的学术地位以及对明代关学的接引价值。
三、学术争鸣:《明儒学案》对明代关学学术地位的重新估价
《明儒学案》对明代关学的总体评价为:“其门下多以气节著,风土之厚,而又加之学问者也。”[2]172总体而言,黄宗羲对关学持肯定态度,这应当是黄宗羲站在总结有明一代近三百年学术思想的立场上做出的审慎定位。关学之核心特点为注重“气节”,而“气节”则来自“风土”与“学问”相互夹持。可以说,黄宗羲对关学特点及其成因的总结相对客观、到位。然而,关学毕竟只是地域性学术,若放置到整个明代进行全新观照,黄宗羲仍需对关学进行重新评价。
首先,黄宗羲在一定程度上坚持了关中学者的礼学取向,但远没有达到《关学编》所强调的高度,诚如杨国荣所言,“关注现实,关心治国与平天下,构成了关学的主要特点之一。这一特点体现在学术的取向上,便表现为对礼学的重视”[5]。关中学者对礼法的恪守延伸到政治领域,表现为对君臣之义的坚守;延伸到教育领域,表现为对师道的维护,这部分内容在《明儒学案》中得到了保留,但更多的信息却遭到了黄宗羲的删削。
在《关学编》中,我们可以看到段坚反对乡俗用浮屠法葬人的一贯做法,坚持用儒家礼法安葬祖父。在南阳为官时倡明古礼,民风大化。张杰坚持用古礼葬父;薛敬之以礼葬亲;吕柟以礼哭皇帝,遵古礼为少时老师孙行人服丧,以礼葬父;郭郛居丧守礼;王承裕在武宗南巡期间准备祭品;王之士丁内外艰,几至灭性。这些信息在《明儒学案》中都有一定程度的删减。
其次,批评薛瑄是降低明代关学地位的最有效的方法。由于薛瑄的理气说“最终也无法弥合朱熹关于理气关系的漏洞”[3]123,而黄宗羲最为反对的就是理气为二说,“先儒往往倒说了,理气所以为二也”[6]。职此之故,薛瑄的理气说也遭到了黄宗羲的批评:“羲窃谓,仁人心也,心之所以不得为理者,由于昏也。若反其清明之体,即是理矣。心清而见,则犹二之也。此是先生所言本领,安得起而质之乎?”[2]121
再次,如果说黄宗羲对薛瑄的批评尚停留在形而上的高层次之上,那么对韩邦奇的批评则是集中在音乐这一形而下的低层之上。④对于韩邦奇的《苑洛志乐》,黄宗羲批评得很具体:“声气之元,在黄钟之长短空围,而又不能无疑者。”[2]183理气观是宋明理学的理论基础,黄宗羲站在心学立场上批评薛瑄是可以理解的,但他批评韩邦奇之音乐学观念更多的是一种策略,毕竟韩邦奇的《苑洛志乐》并非如黄宗羲批评的那样不堪,至少在四库馆臣看来,《苑洛志乐》仍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其他若谓凡律空围九分,……虽其说多本前人,然决择颇允。又若考定度量、权衡、乐器、乐舞、乐曲之类,皆能本经据史,具见学术,与不知而妄作者究有迳庭”[7]。黄宗羲对韩邦奇《苑洛志乐》最为不满的是“黄钟之长短空围”,但韩氏的观点虽多本前人,但也决择颇允,黄宗羲的批评则有吹毛求疵的意味了。黄宗羲之所以抓住这一点不放,就在于藉此表明韩邦奇的学术之空疏,既而降低关学的价值和地位。
四、回归平凡:《明儒学案》对明代关中学者的非凡童年、学术称谓的处理
如果说《明儒学案》对薛瑄的理气观提出商榷意见,是一种釜底抽薪式的批评。那么,《明儒学案》全部删除了《关学编》中屡屡提及的学者非凡的童年以及崇高的学术称谓,就成了一种细节处理。
首先,《明儒学案》删掉了《关学编》中关于部分学者未成年时的一些情形,包括出生时的异象、非凡的学术感悟能力等迥异于常人的现象。《关学编》称张杰“生有异质,颖悟过人”[1]29;李锦九岁时“端坐终日,不逐群儿嬉。读书知大义,日见英发”[1]34;杨爵“初诞时,室中如火光起,人咸惊异之”[1]53;王之士“七八岁即知学,教授公授之《毛诗》二《南》辄解,辄为诸弟妹诵之”[1]60。记录杰出历史人物幼时的非凡之举、异常景象是中国史家的一贯传统。司马迁记黄帝“生而神灵,弱而能言”[8];班固记刘邦乃是龙之子,“左股有七十二黑子”[9];相传朱熹出生时,婺源故宅老井中有紫气。
黄宗羲为开宗立派、学术突出的学者撰写传记时,一般也会保留比较奇特的出生情形或者幼年颖悟等信息。如吴与弼出生时“祖梦有藤绕其先墓,一老人指为扳辕藤,故初名梦祥”[2]3;陈献章“右脸有七黑子,如北斗状。自幼警悟绝人,读书一览辄记”[2]80;王阳明“先生娠十四月而生,祖母岑夫人梦神人送儿自云中至,因命名为云。五岁不能言”[2]200;薛瑄出生时,“母梦紫衣人入谒而生,肤理如水晶,五脏皆见,家人怪之。祖闻其啼声,曰:‘非常儿也。’自幼书史过目成诵”[2]119。对于一般的学者则不予保留。关中学者在关中地区自然是杰出人物,但放置到全国范围内,放置到有明近三百年的历史时段中考察,黄宗羲只为薛瑄保留了非凡的记载,对其学术传人的奇异记载就予以删除。
其次,黄宗羲删掉了《关学编》对某些学者过高的类比式学术称谓。《关学编》立意为关中学者立传,在心理上就会有意无意拔高某些学者的学术地位。如称段坚“动作不苟,人以伊川拟之”[1]26;“当时见(周蕙)者,亦翕然以为程、朱复出也”[1]31;“关中学者咸以‘横渠’称之(李锦)”[1]34;吕柟被高朝用视为“颜子”[1]42。平实而论,当地出现一个或数个著名学者,时人很容易将其与更古老、更著名学者进行比附,段坚、周蕙、李锦、吕柟分别被视为明代的程颐、程朱、张载、颜渊,也是对他们学术地位的一种肯定。但是黄宗羲对此并不认可,他肯定的学者要首选陈献章、王阳明,所谓“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其吃紧工夫,全在涵养。喜怒未发而非空,万感交集而不动,至阳明而后大”[2]78。然后是江右王学。因此,对于《关学编》中的某些过高的学术称谓,黄宗羲一律不予采纳。黄宗羲在根本上以阳明学术为宗,但是对南大吉这样亲炙阳明的学者,黄宗羲也不认同《关学编》的定位。《关学编》曾引用王阳明对南氏的评价:“王公报书为论良知,旨甚悉,谓关中学自横渠后,今实自南元善始。”[1]52《关学编》此语不虚,王阳明曾称:“关中自古多豪杰,其忠信沉毅之质,明达英伟之器,四方之士,吾见亦多矣,未有如关中之盛者也。然自横渠之后,此学不讲,或亦与四方无异矣。自此关中之士有所振发兴起,进其文艺于道德之归,变其气节为圣贤之学,将必自吾元善昆季始也。”[10]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关学编》才将南元善塑造成为王门高第。然而,黄宗羲在总结阳明后学时曾专立《北方王门学案》,对山西、山东、陕西、河南的王门弟子都给出了较低的评价,“北方之为王氏学者独少,穆玄庵既无问答,而王道字纯甫者,受业阳明之门,阳明言其‘自以为是,无求益之心’,其后趋向果异,不可列之王门。非二孟嗣响,即有贤者,亦不过迹象闻见之学,而自得者鲜矣”[2]738。南大吉就列在《北方王门学案》的卷末。可见,黄宗羲虽然推崇关中学者的气节,但对其学术地位仍持保留态度。
从表面上看,以上都属于文字上的简单删减,却在客观上将《关学编》中的神异性拉回到了平凡的轨道上来,再次彰显了黄宗羲对《关学编》给予关中学者较高学术地位的不认同。
《明儒学案》纳关学入河东之学,构建了关学的学术谱系。为此《明儒学案》特意强化了薛瑄的影响力,并展开了对薛瑄的批评,甚至删除了《关学编》中的某些非凡书写。在黄宗羲的心学视域下,明代关中学者的学术地位已经不如《关学编》所推许的那样崇高。
注 释:
①《明儒学案》对《关学编》的参考包括两方面:一是黄宗羲对学者学术特点的总结,大多来自《关学编》;二是在撰写学者传记时,大量采用了《关学编》的文献信息,并有删减。前者并没有体现出黄宗羲的学术创新,后者恰恰体现了黄宗羲的学术思想和《明儒学案》的编纂思路。
②关学研究方面,侯外庐等人曾在《宋明理学史》中对《关学编》进行了评价:“所谓‘关学’的始作俑者冯从吾,他所汇编的《关学编》,原不过是地志的性质,一如《金华丛书》、《江西丛书》、《岳麓丛书》之类。而李元春、张骥却从中牵率为承前启后的‘宗传’关系,真可谓是好事者为之,殆无意义。”(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35页)2018年张岂之先生修订版《宋明理学史》仍然坚持此说。黄宗羲《明儒学案》研究方面,尚未见到与关学相关的有影响力的成果。
③根据《明儒学案·师说》,黄宗羲的观点可以追溯到乃师刘宗周。
④音乐有双重属性:一方面属于六艺之一,属于传统儒家经典,列在《四库全书总目》的经部;另一方面,具体的音乐技法等则属于形而下学,列在子部。
——儒学创新发展的趋势与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