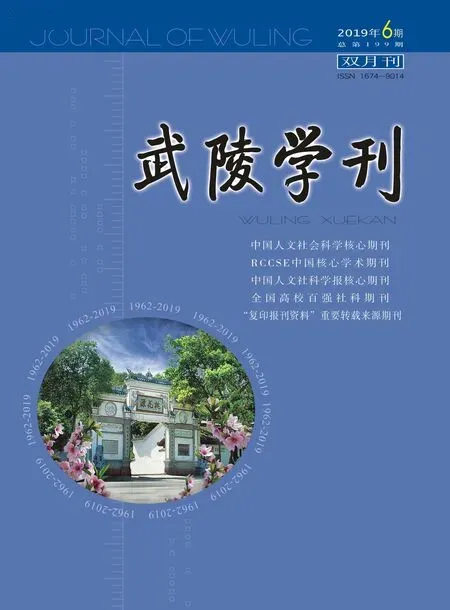清末中国人欧美游记中的灯光书写及其文化意义
张一玮
(中国传媒大学 人文学院,北京100024)
中国人笔下有关欧美国家现代文化的集中描述与呈现,是从晚清时代的旅欧游记作品开始的。19世纪后半期,处于文化、政治和经济等方面危机中的清政府开始逐步引进西方科技,试图以此自强。在这个背景下,由清廷委派的旅欧使臣、驻外公使、随行人员、旅美学童,以及出于其他各种目的的跨国旅行者,都对欧美国家的物质文化给予了相当多的关注。他们留下的关于域外旅行过程、感受、体验和思考的文字,是兼具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的文本。伦敦、巴黎、马赛、纽约等欧美城市,被晚清时代中国旅行者描绘为带有现代奇观色彩的地方。其中最具直观性和代表性的审视对象之一,即是与旅行者的视觉经验密切连接在一起的城市灯光景观。无论斌椿、郭嵩焘、张德彝、曾纪泽、薛福成、黎庶昌等人的公务出访记录或旅外日记,还是王韬、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私人旅行书写,均包含有关煤气灯、电灯或欧美城市灯景的印象和认识。本文试将这些有关域外旅行经历的文字,包括官员或文人围绕书写旅行见闻的日记、笔记、杂记、诗歌等文本形式,纳入广义的“游记”文体框架,借此审视和分析那些关于灯光的书写,并透视灯光、灯景作为物质文化景观的意义。
一、灯光书写的历史文化语境及文本类别
相对于同时代的中国城市,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城市在19世纪的公共设施建设方面具有绝对优势,尤其是夜间照明设备的普及,构成了城市现代化进程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个历史时期的前半段是煤气灯在西欧发达城市普及的时期,后半段则是电灯开始崛起并逐步替代煤气灯的时期。它们作为夜间照明手段的发展,为欧美国家的城市带来了景观、社会、文化、心理等多个领域或维度上的深刻变迁。城市夜晚的黑暗被持续的灯光驱散以后,夜生活即开始成为发达城市中的一种新文化形式。它匹配了资本主义持续发展时期由生产关系引发的劳动与休闲关系的新变,释放了新的消费欲望和商品流通的多重可能。从西方文明史的角度来看,现代夜晚照明手段在欧洲城市公共场所的使用,同样改变了自中世纪以来日常生活的时间格局,以及城市人对城市空间的感知方式。这个具有革命性的因素推动了现代城市生活方式的整体变迁,也催生了有关现代城市之夜的社会想象和文学书写。对于晚清时期初抵欧美的中国旅行者而言,城市的灯光既直接凸显为东西方文化差异的视觉标志,又承担了物质和文化中介。孟悦教授认为:物质文化研究是“一个谈话空间或论坛……不同学科的人聚集到这个空间,不是为了寻找结论,而是为了发现问题和寻求启示,以更深入更有效地理解和描绘我们生存的世界。”[1]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旅人的旅外书写为研究近代中国人的现代文化观念提供了重要的文本。
书写这些灯光景象的晚清中国人旅外游记作品中,多数作者运用了源于传统游记的叙事方式和修辞手法,文体上多以日记或随笔形式出现。其中的大部分作品中,传统文人崇尚山水的审美趣味、闲情逸致与物我之思已让位给不同文化之间互相观照、审视、对话中产生的复杂文化心态。游记原本是对旅行主体在空间中移动过程、感受和经验的书写形式,具有悠久的发展历程和混杂性的文体特征。在近代以来中国遭遇民族危机和文化危机的时期,官员与文人群体心理中的焦虑、隐忧和矛盾开始成为旅外游记的重要主题,当然也不乏旅行者致力于见证文化他者的猎奇心理展示。单以书写者的社会身份来看,相关文本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访外官员、驻外使节及其随从撰写的旅行记录,其中多数带有公务旅行记录或外交备忘录的色彩;另一类是政治流亡者、旅外学童或商人撰写的游记,多数是较侧重个人感悟和独立思考的个体化写作。
第一类作品主要包括斌椿的《乘槎笔记》、张德彝的《航海述奇》《欧美环游记》《随使法国记》《随使英俄记》、郭嵩焘的《伦敦与巴黎日记》、刘锡鸿的《英轺私记》、曾纪泽的《出使英法俄国日记》、黎庶昌的《西洋杂志》、薛福成的《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等。它们记录了纷繁芜杂的外交资料、文化资料、西方现代器物形象。其中,斌椿和张德彝的赴欧旅行开始于1866年,郭嵩焘、刘锡鸿、黎庶昌的旅行始于1877年,曾纪泽于1878年赴欧出任驻英、法大臣,薛福成的欧洲之旅发生在1890年至1894年。这些官方主导下的外交或公务活动的开展,源于1861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成立,以及洋务运动的推进。这一时期中国特使、驻外使臣或其随同人员访问欧美的记录,可进一步具体化为日记、杂论、诗歌等文本形式。此类作品在文体上的混杂性,不仅是其现实功能的标志,有时也可以视作走向西方现代文化的旅行主体充满矛盾性的体现。那些署名为旅欧中国官员所撰写的旅行记录,并非总是出自官员一人之手,有时存在旅欧代表团集体写作的情况。这些文本的一种归宿是带回国内上交朝廷,以便实现资政目的,而张德彝等人的旅行书写还明确具有以个人视角观察别国文化的审美意图。由于此类文本都描写了旅行者的感受、心态和认知,因此形成了同时具有史料价值和文学研究价值的内容。
第二类作品以王韬的《漫游随录》、康有为的《欧洲十一国游记》、梁启超的《新大陆游记》等为代表。王韬的西欧之旅始于1867年,康有为的欧洲十一国旅行始于1904年,梁启超的美洲旅行始于1903年。这些文本中私人写作和思考的色彩更为浓厚,且它们的叙述方式与修辞手法比前一类围绕外交活动的旅行记录更加丰富多样,描写和评论方面也没有太多顾忌。其中有关欧美政治体制和民俗的叙述,匹配了当时中国士绅与民众接触和理解外来文化的现实需求。同时,这些游记中欧美发达国家形象的描写评价,逐步由侧重技术和物质文化方面转向侧重文化机制和社会制度方面。王、康、梁等人的政治流亡者身份,也在清末的政治氛围中为域外文化的传播和接受添加了特殊意义与价值。
无论哪一类文本,创作者们都试图借助具有游记形式的写作,构建有别于中国的海外异域空间。随着此类文本的书写和传播,来自欧美国家的现代文化及其相关的想象也在中国蔓延开来,为中国读者敞开了一个新的世界,并且形成了面对过去、未来及本国、异邦的新感受与新态度。上述两类作品中的大部分作品殊途同归,不同程度呈现出学者型的旅行主体旨在获取和记录地理文化知识的“地学游记”意味[2]。在众多有关欧美国家地理、社会和文化的记载中,煤气灯、电灯和城市之夜的灯光景观,在中国旅行者笔下体现着源于现代性的魅力。而不同时期中国旅行者囿于个性、需要、视野、文化心态、政治立场等复杂的因素,对于游记中灯光景象的描述和理解,也往往具有独特性。这使旅行者面对灯光景象的个别表述,流露出某种可以彼此对照和呼应的整体研讨价值。
二、煤气灯与游记中的城市灯光书写
煤气灯是以煤气为燃料,将可燃气体的能量转换为光能的现代城市照明工具。英国城市于19世纪30年代开始普及煤气灯照明,法国、美国等国家的大城市也随后推广使用煤气灯。至19世纪50年代,大部分欧美发达国家的主要城市已经普遍使用煤气灯作为夜间照明手段。与此相比,上海于1865年年末才开始有煤气灯作为租界街道和住宅的照明设施[3]。在这个背景下,19世纪中后期赴欧洲旅行的大部分中国旅行者,最初并不十分了解煤气灯之于城市的意义及景观价值,这也往往导致他们最初充满惊奇和羡慕的感受。
由于晚清时代乘船前往欧洲的中国人多数选择在法国马赛登陆,这座法国南部港口城市便成为多部中国游记共同提及的第一座欧洲大陆城市。斌椿的游记是近代中国官员第一次欧洲旅行的记录,煤气灯在其中构成了19世纪60年代第一个引人注目的夜晚城市意象:“街市繁盛,楼宇皆六七层,雕栏画槛,高列云霄。至夜以煤气燃灯,光明如昼,夜游无须秉烛。闻居民五十万人,街巷相联,市肆灯火,密如繁星。他处元夕,无此盛且多也。”[4]189这种带有奇观化描述特征的文字,使马赛在中国读者的阅读中被赋予现代文化意义。张德彝对这座城市的观察更为细致,他注意到煤气灯在亮度上的优势——“其光倍于油蜡,其色白于霜雪”[5]480。他还十分关注管道、螺丝等煤气灯的相关装置或技术细节:“如不点时,必以螺狮塞住,否则其气流于满屋,见火即着,实为险事。”[5]480后来,游历里昂的斌椿还刻意以马赛为参照进行叙述:“灯火满街,照耀如昼,繁盛倍于马赛。”[4]180在另一位文人旅行者王韬眼中,马赛的城市风貌也离不开灯光的陪衬:“街衢宽广,车流水,马游龙,往来如织。灯火密于星辰,无异焰摩天上。寓舍供奉之奢,陈设之丽,殆所未有。”[6]以上文字说明,在那个中西文化开始接触的时代,最能代表欧洲城市现代性的主题中,“光”最初吸引了中国旅行者,引发了震惊、艳羡、猎奇、排斥等不同的感受,酝酿着文化认同的全新可能。
这一时期的法国首都巴黎,同样以灯光下的夜景吸引着来自东方的旅行者们。张德彝这样描述巴黎煤气灯的外观和运作方式:“又两树间立一路灯,高约八尺,铁柱内空,暗通城外煤气厂。其上玻璃罩四方,上大下小,状如僧帽。”[5]482黎庶昌笔下的煤气灯被描述为巴黎街道景观整体规划的一部分,它与植被之间形成了富有秩序的关系:“近正中一条处,两边皆植一种野栗树,每树相距不过丈许,枝叶发时最为繁茂,中间间以煤气灯。”[7]471志刚的游记中也有类似的描述:“夹路植树,树间列煤气灯,彻夜以照行人。”[8]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则这样勾勒节庆日的巴黎街头:“经东为蒙勒马儿得大街,并于街两旁树架,连小玻璃盏,引煤气为灯。每值街口,两旁植杆树旗,中聚小玻璃盏,引灯为花围。”[9]635煤气灯参与了节庆气氛的构成,夜间游逛因此成为可能。另外,煤气灯作为室内照明手段的个案,也形之于中国旅人的笔端。1878年,黎庶昌在参观巴黎世界博览会时,注意到了煤气灯在展馆内的应用:“夜则照以煤气灯,华丽宏博,至不可名状。”[7]480持续的夜间照明,为博览会中商品的展示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此外,张德彝在1871年写到了南部城市波尔多戏院中的煤气灯设施:“是园乐工五十名,台上悬煤气灯一百二十盏,台下悬插共三百九十五盏,可容二千一百余人。”[10]当时法国城市夜间购物、休闲活动和文艺演出都需要依赖煤气灯的照明,夜晚文化生活在中国人笔下呈现出繁盛面貌。
赴西欧旅行的中国人多数在游历法国城市之后,再转赴英伦。在《伦敦与巴黎日记》里,郭嵩焘这样谈伦敦的市政建设:伦敦城有“煤气灯公司十八家。水业公司八家,专给伦敦用水。转江水为池面引注水之房,由水管以达各街。”[9]471在郭的眼中,四通八达的煤气管道、给/排水管道是现代城市规划中必备的设施,它们的生产能力是城市文明的重要基础。以今天的视角看来,这也是欧洲城市各区域一体化的现代物质文化标志。同时,城市煤气管网的存在,代表着技术基础已经成熟的煤气灯、煤气生产和输送手段,开始广泛惠及市民家庭的时代状况。张祖翼在漫游伦敦后,写下了《伦敦竹枝词》近百首。其中一首云:“氤氲煤气达纵横,灯火光开不夜城。最是宵深人静后,照他幽会最分明。”[11]18“纵横”“通达”的煤气供给,是伦敦成为不夜之城的基础。煤气灯光驱散了黑暗,也驱散了古代城市夜生活的单一性。他的另一首竹枝词描写了室内交际舞场上的灯光:“一尺圆球百尺竿,电光闪烁月光寒。歌场舞榭浑如昼,世事昏沉普照难。”[11]19这首带有讽世意味的作品中,不夜城的景象引发了作者有关“不夜城”的照明便利与“世事昏沉”的社会认知之间的关联性表述。“普照”这个较多用于东方语境的词汇,更将光线之形象提升至隐喻层面。
政治流亡者王韬对伦敦的书写也很有特点。1867年,他应英国人理雅各邀请游历英国,期间承担起翻译中国文化典籍的工作。王的旅行书写,是中国文士对欧洲文化的思考与文学再现的综合产物,诠释并丰富了国家、现代、文明等概念的意义,同时借助“怀乡”心态的复杂演绎,塑造出一种文人式的现代体验。在这次旅程中,王韬对灯光的描述同样引人注目。如有关伦敦的整体印象描写中,他以灯光烘托出这个强盛的资本主义国家首都的面貌:“从车中望之,万家灯火,密若繁星,洵五大洲中一胜集也。……入暮,灯光辉煌如昼,真如不夜之城,长明之国。”[12]82他还像张德彝那样描述了煤气灯的工作方式和照明效果,为习惯使用灯烛的中国人创造了一个文化他者的新奇生活方式:“每夕灯火,不专假膏烛;亦以铁筒贯于各家壁内,收取煤气,由筒而管,吐达于堂,以火引之即燃,朗耀光明,彻宵达曙,较灯烛之光十倍。”[12]104夜晚室内的灯光还能够勾勒和烘托人的形象,使夜晚的交际活动成为可能:“时有盛集,掌教者大张华筵。来者皆新妆炫服,各袒臂及胸,罗绮之华,珠钻之辉,与灯光相激射,红男绿女,喜气充盈。”[12]149从这类文字可知,既然来自中国的旅行者不单是记录者,而且于文字再现过程中进行着能动的思考,就不能简单地认为他们之于外来文化是一个单向的接受影响的客体。王韬作为观察者的再现和认知当中,即包含了利用传统文言词汇、句式、修辞法等本土文化资源去主动认识和把握其他文明的策略。由于王韬旅欧游记的读者比官员游记更为广泛,因此在中国的社会反响也更显著。旅行者在观察和书写中经历着自我的重新建构,在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中完成自身的确认和再表述。
三、灯光与游记中的现代科技文化思考
晚清时代那些旨在富国强兵的中国旅行者,不但惊讶于欧美城市中照明设施的发达,还试图进一步探究照明技术的基本原理,以期找到煤气灯和夜景背后的现代科技价值。电灯是将电能转化为光能的现代装置,是推动现代文明进步的重大发明。与煤气灯相比,旅行者们对电力及电灯的描述并未停留在表面,而是付出了更多的理性审视与思考。郭嵩焘于1877年即谈论过电灯的问题。他认为当时的电灯技术虽仍需改良,以解决光线强弱和照明范围等技术问题,但它取代煤气灯已显现为历史的必然趋势。同时,郭还描述了电能利用的种种条件,并注意到随着技术条件的进步,电力照明的成本将远低于煤气灯:
潘得尔威得因悟得此法,且言照路煤气灯改用电气,可省费四之三。西洋人皆明此义,而至今未改造,徒以电气光太盛,沿街用之,其光射人恐至损目。又光照处太过,光所不到,不能旁及,思得一法,用镜收之,使其光不至射目,而又能引之使散而四达,至今尚未得其法也。计一二十年后,各国皆当用电气,照路灯无复有用煤气者矣。[9]489-490
郭嵩焘于光绪四年(1878)九月三十日的日记中又一次表达了此种判断①。同年十月十二日的日记中,他记录了刚刚了解的电灯技术发展历史,并重申了电灯替代煤气灯的必然性。文中对人名和国籍的记录虽不免出现讹误,但保留了中国旅人对于现代物质文化展开思考的路径:
俄人丫伯洛廓夫以新法制电气灯,而不能及远,亦仅能以机器发电,连引至十灯。英人爱谛生、威得尔曼又因其法推而求之,以延及百灯以外,亦能及远。故言电气灯者,一时有三家。煤气公司数百万资本,日夜忧惶,莫知为计。数百以后,遍泰西诸国皆为电气灯矣。[9]787
19世纪90年代,电灯作为欧美主要城市的照明手段开始走向普及。另一位赴欧美国家的旅行者薛福成参与见证了这个时代的欧洲社会状况,同时也试图考察电力和电灯之光背后的科学原理。薛习惯使用“电气”“电学”等名字称呼他在欧洲接触的自然光电现象、科学实验及其背后的知识:
昔人见云中电光闪烁,常以此比作事之速,从未有知取而用之者。……然格致家考察电气,已匪朝伊夕。古人始以琥珀摩擦令热,能吸轻物;后人以玻璃、火漆等物摩热,亦能吸轻物。若质巨气足,则见有火星爆出。寻知五金之属,皆善引之。又以瓶内外粘贴锡箔,蓄其气,放之则有光如电,作声如雷,能震人击物。……始知向用玻璃、琥珀等物所出之气,实与雷电无殊,电学由此渐兴。[13]122
天空本有电气,雷亦电气也。是气之为用极光,收之可以镀金银、燃炮火、通文报、代灯烛,皆可以人力制之。[13]407
薛试图深入到电灯背后的“电学”之中,进一步探讨电的起源和被应用的历史。其描绘和探究虽达不到科学叙述的程度,但已经显露了“格物致知”的中国思维方式与欧洲现代文化的交融。在修辞方面,他利用中国古代哲学概念“气”对现代西方科技形态进行表述,又用“湿电”“干电”等词汇区分因摩擦产生和由发电设备产生的电力[13]122。
1893年,薛福成又一次谈论了电灯乃至电力的应用价值:“自电灯盛行,而煤气灯为之黯然减色。如炮台之守御,兵舰之游行,皆用电灯窥伺敌人。……迩来又以电气行车,较之火轮车,无振动、轰炸之患,无风雨迟缓之虞。如日后再用电力以行船,则更妙矣。”[13]761在这段话中,薛立足于电灯的技术优势,从实用的层面评价了电灯和电力的广泛使用价值。在他的游记中,科技知识的实用价值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调。在书写的文体方面,学者张治认为,薛福成有意识地在日记中记录和描写欧洲现代文明,并形成了自己的写作特点,他“标榜一种以传统学术文体来研究西学、时务的著述方法”[14]。薛福成的文字以说明为主,笔法有传统山水游记中地理、地形叙述的格调,其目的是向中国读者尤其是官方决策者进行文化和技术介绍。
至康有为于1899年离开中国流亡海外的时期,电灯已开始在欧美大城市全面取代煤气灯。与煤气灯相比,电灯的亮度更强,安全性也更高。康的游记述及巴黎时写道:“至夕电灯万亿,杂悬道路;林木中马车千百,驰骤过之,若列星照耀,荡炫心目。”[15]灯光衬托了现代都市的流动性,在旅行者面前铺陈出视觉的盛宴。1903年,梁启超在游历美国时,也在文字中曾这样描述纽约:“郎埃仑在布碌仑之西,由纽约乘电车半点钟可达,避暑之地也,游者以夜。余尝一游,未至里许,已见漫天云锦,盖电灯总在数千万盏以上也。层楼杰阁,皆缀华灯,遥望疑为玻璃世界。”[16]梁启超笔下的“朗埃仑”当指纽约的长岛(Long Island),其电灯的普及程度皆形诸文字。其修辞风格与王韬的日记如出一辙,这种写法代表了中国旅行者书写国外生活景象时的特殊格调:以文士使用的传统文言词汇、语句、笔法讲述处于文言文经验之外的欧美现代物质文化。这种写法有时会因“言不尽意”或文化翻译的“不可尽解”造成游记文本的曲解或误译,也可能因为文言辞藻的重复使用形成叙述中的程式化倾向。这种带有自我矛盾性的写法,本身也是文化现代性诸问题的表达。
梁的描述虽并未超出几十年前中国官员旅欧游记中的写法,但梁的美洲之旅核心目的是考察美国的政治及社会制度,观念上已有质的变化。由于19世纪末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剧,有远见的中国文人所写的旅外游记,已开始有意识地将西方器物文化与政治制度的变革需求更为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在这个意义上,梁的旅行本身既是政治流亡,也是了解西方政治文化和组建政治团体的过程。因此,这场由戊戌变法倡导者进行,始于日本,途经加拿大、美国的旅行,可以称作一次“文化与政治之旅”。由无数盏电灯组成的璀璨夜景,与旅行者关于欧美国家先进的社会制度与物质文化的体验结合在一起,具有了文化象征物的意味。旅行者漫游脚步的随意性与不确定性,在灯光和作为现代科技精神代表的“电学”的映衬下,逐步生发出面向现代性的确定性和期待感,最终使现实化为对中国现代性的思考与创造。
如上的游记文本中,中国旅行者在欧美国家见到的煤气灯与夜景,以及围绕电灯、电力和“电学”展开的思考,可以视为推动“开眼看世界”之后中国人心态调整的一个标志物。从那个时代起,来自官员和文人们的帝国情怀渐趋消退,转而开始审视如何使中国成为现代国家的关键问题。中国旅行者初次接触时显得瑰丽而珍贵的灯光及其背后的科技文化,催生了围绕“光”这一主题的文化想象。光的奇观既构成了欧美现代城市的夜景,也映照着夜间消费场所中繁盛的现代商品形象。至少从那时起,欧美城市中具有隐喻价值的城市灯光,同时成为了商品王国的霓虹,它代表着充满诱惑力的现代文明正在召唤中国走向世界。在这个意义上,当时中国人欧美游记中的灯光既代表现代科技的进步和物质文化的发达,也被塑造和表述为西方现代文明本身的一种象征物。
注 释:
①“近年电气灯兴而造煤气厂者为之心惧;炼钢简易之法兴而铁厂皆为之心惧。正虑一二十年后,群用电气为灯而煤气将废,群用钢为制器之用而熟铁亦将废不用矣。”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第774页,岳麓书社198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