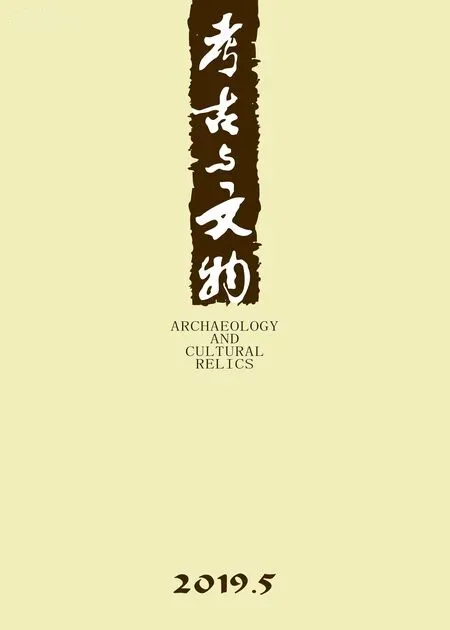关中唐祖陵神道石刻的年代*
田有前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唐祖陵共有四座,分别是唐高祖李渊的高祖李熙的建初陵、曾祖李天赐的启运陵、祖父李虎的永康陵和父亲李昺的兴宁陵。建初陵和启运陵位于河北隆尧,二陵同茔异穴,共用一条神道和石刻;永康陵和兴宁陵分别位于陕西的三原和咸阳,二陵均有独立的陵园和神道石刻,故四座祖陵实际上有三座陵园和三组神道石刻。因陵主追封为帝的时间不同,陵号获得亦有先后,故隆尧祖陵与关中祖陵在陵园布局和神道石刻方面均有着较大的差别,前者更为复杂些,因此本文主要讨论关中唐祖陵神道石刻的年代问题。
近年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先后对永康陵和兴宁陵进行了全面的考古调查和勘探,并对陵园神道石刻和部分建筑遗址进行了发掘,从而搞清了神道石刻的数量、组合和分布规律,对陵园神道石刻的年代也有了新的认识。
一、研究简史
早在1943年,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即对永康陵进行过调查,认为“陵前石刻行列远较其他唐陵为简单,雕刻作风则绝类北魏北周所有,但石马及翁仲则又显出矮小粗劣之形态,颇类晚唐所增立”,“各石刻数量远比其他唐陵为少,且作风不同,疑其中之一部分为后来增补”。对各石刻记录如下:“华表一对均已倒地……形甚小,柱身刻花亦简单,上盖形式亦类晚唐所有”;“石兽一对……造型奇异,头部颇类似骆驼,身长而细,前足有云纹,且与献陵及定陵、桥陵又各不同”;“石马两对,均已倒毁,马形矮小,类晚唐所有”;“石翁仲三对……拙劣无足观”;“石狮一对相对立,均完整存在,造型古朴卓绝,迥异于其他石刻,颇类六朝作品”[1]。
1996年秋及1997年春,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先后两次对永康陵进行了调查。调查有石柱1对,独角兽1对,东侧石马2件,石人1对,石蹲狮1对。调查者认为“永康陵石刻雕凿于初唐武德年间,是唐代陵墓石刻中雕凿最早的一组”[2]。2002年初,陕西文物保护中心又对该陵进行了调查。调查有石柱2件,独角兽(原文天禄)2件,石马仅存东侧2件,石狮1件。认为“陵前石刻排列,是继承了南北朝时期的陵墓石刻制度”,“唐永康陵的石刻处于过渡阶段”[3]。
1977年,咸阳市博物馆对兴宁陵进行了调查。调查有独角兽1对,石马2对,石狮1对。认为“兴宁陵比献陵的石刻品类还要少,但是造型古朴生动”,“这种追求逼真而不作外表装饰的写实手法,是初唐艺术的一大特点”[4]。
员安志对兴宁陵石刻进行了初步的探讨,认为“兴宁陵前的石麒麟等石雕,系唐初武德元年的遗物,是李渊即位后为其父李昺追封为陵的。陵前石刻虽属唐作,但作者实是隋代的工匠,所以石刻群完全是隋代甚至北周时期的造型风格”,“陵前石马二对,东西相对而立,保存完好,雕刻也较古朴浑厚,别具一格”,“兴宁陵前的石狮也与‘唐十八陵’有所区别,造型浑朴,气派雄威,显得其内在的力量特别雄强,是唐陵坐狮中较早的作品之一”。“兴宁陵前的石雕,有它特有风格,又有较高的艺术创作水平,反映了隋至初唐雕刻的高度艺术水平,确为研究唐代石刻艺术珍贵的实物资料。”[5]
林通雁则对永康陵和兴宁陵石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他认为,“初唐期永康、兴宁二陵的蹲狮头小身大,服毛刻饰粗浅,前肱呈椎状,肌肉劲健,较多地保留着北朝和隋代的遗风”[6]。“初唐永康、兴宁二陵的神兽为同一模本刻成,与北朝的有直接承继关系”,“初唐永康、兴宁二陵雕刻作为北朝模式的承启环节,在石人、石兽、石柱三个基本种类组合及其个体造型式样方面,奠定了盛唐五大陵园雕刻的发展方向”[7]。
以上对永康、兴宁二陵石刻的分析,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独角兽、石狮的看法一致,均认为其年代较早,为唐初作品;二是对石柱、石马、石人的看法不一,或认为其年代较早,或认为其年代较晚。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因为之前二陵的许多石刻都埋在地下,研究者无从得见,只能通过保存在地面上的石刻来进行推测,难免出现差错,另一方面也是受惯性思维的影响,认为埋葬时间早的陵园其石刻年代也必然较早,而忽视了某些时候陵园与石刻的年代存在脱节的现象。在此情况下,对石刻具体特征的分析,将是解开二陵石刻年代之谜的一把钥匙。
二、特征分析
根据以往的调查资料及近年来的考古发掘情况,本文首先对永康陵和兴宁陵神道石刻的保存情况做一简单介绍。二陵的陵园石刻均位于神道东西两侧,对称列置。其数量、类别和组合大体相同,经复原研究,推测石刻数量均应为20件,从南向北依次为1对石柱、1对独角兽、2对石马及牵马人、3对石人和1对石狮[8](图一)。

图一 兴宁陵神道石刻分布示意图

图二 兴宁陵西石柱
1.石柱
永康陵石柱均残损,仅东侧保留柱头,现存三原县东里花园。石柱头整体造型为仰、覆莲座上托宝珠。由下向上分为5层,依次为八棱台座、覆莲瓣、宝珠、仰莲瓣、桃形宝珠。柱身八棱,由下至上略有收分,中部纵向阴刻古籀文“唐太祖景皇”。表面阴线刻蔓草禽鸟纹饰,部分漫漶不清。西石柱柱身中部纵向阴刻古籀文“帝永康之陵”。础座为扁方形台座上置素面覆盆造型,为一整块石料雕刻而成。覆盆上部中间刻凿圆形榫眼,扁方形台座四侧面均磨光,残存有部分线刻纹饰。
兴宁陵西石柱完好,东石柱柱头佚失,其造型与永康陵石柱大体相同。不同之处有两点,一是柱身上未刻字,二是仅存的西石柱柱头最下层的八棱台座侧面有浅浮雕的垂幛纹,该纹饰又出现在中晚唐之际的文宗章陵的石柱头上(图二)。
2.独角兽
永康陵东侧独角兽残损严重,仅存头部和躯干部分。西侧独角兽除左后腿残缺外,其余保存完好。石兽呈站立状,立于石座之上,与踏座为一整块石料雕成。石兽昂首平视前方,头顶部较平,中有独角紧贴头上,双耳紧贴头部两侧,眼睛圆睁突起,鼻梁高直。腮部圆鼓,嘴唇紧闭,下颌线条方直。腮后刻画如火焰状鬃毛4缕。前后肢上部侧面浮雕花瓣状或卷云状图案。躯干较长,腰背部平直,腹下有柱状云山造型,增加了石兽的稳定性和协调性。奇蹄粗大,稳固有力。尾部呈柱状,与踏座相连。
兴宁陵两石兽保存完好,与永康陵的造型几乎完全相同。独角均残,仅保留根部突起。后肢上部侧面浮雕漫漶不清,仅存痕迹(图三)。

图三 兴宁陵东独角兽
3.石马
永康陵石马1件佚失,其余3件残损严重,仅存躯干部分。兴宁陵4件石马保存完好,还残存两件牵马人石像。
石马多呈静态站立状,双眼圆睁,平视前方,额前两绺鬃毛分向两侧,中间垂下一杏叶。两耳多残,马面部筋骨突起,以纵向的凹棱表示出肌肉,嘴紧闭。马络头由两纵两横四根皮条组成。缰绳系于马面两侧,系绑于头顶,成一鼓突,缰绳紧贴马的左脸垂下。颈部鬃毛剪成短竖状或三花状。攀胸上一般饰5枚杏叶。马背部有鞍鞯,两侧有障泥垂下,下与马腹平齐。马臀部有鞦带,两侧各有3枚杏叶。马体壮硕,臀部浑圆,四肢粗短,前腿直立,后腿略弯曲。马尾或与踏座相连,或绑成一团(图四)。

图四 兴宁陵东二石马
兴宁陵的两件牵马人身穿翻领或圆领窄袖袍服,两侧开叉。腰系宽带,袍服前襟衣角塞在腰间。双臂屈曲,右手置于胸前,左手位于腰间,作握拳执缰绳状(图五)。

图五 兴宁陵东二牵马人
4.石人
依照石刻排列位置,永康陵石人应为3对,现仅存中间1对,均为武将造型。其中东二石人现存西安碑林博物馆石刻馆。头戴高冠,表情严肃,身着宽袖长袍,宽袖下部边缘残损,双手拄仪刀,脚穿圆头履。站在扁长方形踏座上,石人和踏座为一整块石料雕刻而成。西二石人现残存腿部至踏座,造型应与东侧石人一致,可见仪刀的下半段及下垂的袖胡,袍服前端搭于履上,履前端外露。
兴宁陵石人现存5件。东侧3件均为持笏文臣造型。石人穿宽袖袍服,双手于胸前执笏,腰系宽带。腰带下系短裙,袍服下端垂至踏座,露出双脚,穿高头履(图六)。西侧3件均为双手拄仪刀的武将造型。石人穿宽袖袍服,袍服外穿裲裆,肩部以皮带相连。双手于胸前拄仪刀,圆形仪刀首,梭形刀格,方形刀鞘,直抵踏座。袍服下端垂至踏座,露出双脚,穿圆头小履(图七)。

图六 兴宁陵东二石人

图七 兴宁陵西一石人
5.石狮
两座祖陵除永康陵东石狮残损外,其余3件石狮均保存完好。两陵石狮造型几乎完全相同。
石狮呈蹲踞状,胸部鼓凸,前肢上粗下细,向前蹬直,后肢曲蹲,颈上披毛,颚下有三缕须。两侧脸部为三层卷鬃。头后部狮毛向下披,成三大绺,末梢部略成三角形。前肢肘部两侧刻画翼状或火焰状纹饰,前后爪各四趾。后肢爪侧刻画卷毛。尾部侧弯或从大腿内侧向上贴于背部后呈三缕状,尾尖端弯曲向上(图八)。

图八 兴宁陵西石狮
三、年代推断
通过前面对二陵石刻特征的分析,再对比其前后陵墓石刻的特征,可以初步推断这些石刻的大体年代。
1.石柱
梳理唐陵石柱的造型特征,即可发现从献陵到桥陵之间变化较大,到泰陵逐渐稳定下来,并延续至僖宗的靖陵。献陵石柱柱头为八棱台盘上置带方形踏座的蹲坐石兽,石座则为方形台座上置覆盆式首尾相接的双螭造型[9]。昭陵石柱未发现。乾陵石柱柱头为仰莲瓣上承八棱台盘,上置一桃形宝珠;石座为方形台座上置一周覆莲瓣。定陵石柱已毁。桥陵石柱柱头为八棱台盘上置仰覆莲瓣和球形宝珠;石座为方形台座上置一周覆莲瓣[10]。泰陵及以后诸陵的石柱除一些细部特征外,大体相同,均为方形台座上承仰覆莲瓣,再上置桃形或圆形宝珠,石座则为方形台座上置素面覆盆式造型[11]。
仔细考察两座祖陵与其后唐陵石柱的造型特征,发现它们与泰陵之后石柱的造型相近,而与之前的唐陵差异较大。至于永康陵石柱上的刻字,可能受到了南朝陵墓石柱的影响,当是一个特例。
2.独角兽
唐陵神道石刻从乾陵开始形成定型,以后历代唐陵神道皆有一类瑞兽石刻,不过其造型或认为是獬豸,或认为是翼马,而不见如上述两座祖陵的独角兽造型。与其最为接近的,则是西魏永陵的石兽。永陵石兽头顶亦有独角,不过现存两只石兽的独角均已残缺,头顶可见放置独角的长方形凹槽。不同之处是嘴微张,腹下无假山,前后肢上部侧面的花纹呈火焰状向后飘逸。腹部下方雕凿柱状云山的做法,则见于唐初李寿墓前的石羊,目前该石羊保存于三原县东里花园。因此,二祖陵的独角兽均呈现出了西魏至唐初的较早期的时代特征。
3.石马
唐代以前,帝陵前未见置石马者。唐初献陵未设置石马,昭陵北司马门出现的石马是以石屏形式出现的昭陵六骏。自乾陵以后,5对石马及牵马人才成为唐陵神道石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亦在北门外设置3对石马及牵马人。从造型上看,唐代前后期石马的变化不是太大,但体量、细部刻划及气势上则有区别,从泰陵以后均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二祖陵石马的体量与乾陵、桥陵甚至杨氏顺陵的石马相比,都变小了许多,细部也不如前者丰富,而与泰陵以后石马的特征更为接近。
4.石人
帝陵前置石人以北魏孝庄帝静陵和西魏文帝永陵的石人最早,二陵之前的石人均为拄仪刀的武将。唐初献陵和昭陵未发现神道石人,帝陵前置石人在乾陵时形成定制。乾、定、桥三陵的神道石人均为拄仪刀的武将造型,身穿宽袖袍服。泰陵开始,石人分为左文右武,文臣穿宽袖袍服,武官袍服外加穿裲裆。而永康陵石人均为武将,穿袍服,兴宁陵石人左文右武,武将袍服外出现裲裆,因此二陵石人的时代约在玄宗时期,恰好反映了神道石刻从桥陵至泰陵之间的变化。
5.石狮
唐初的献陵陵园四门设置石虎,昭陵四门未发现石狮,发现于昭陵南侧的2件石狮均为走狮。乾陵之后,各陵陵园四门均设置蹲狮,但其特征与两祖陵石狮有较大差别[12]。与永康陵和兴宁陵石狮特征相近的,其年代都较早,如1965年在洛阳隋唐东都宫城遗址发现的隋代石狮[13],三原县唐李寿墓门砧石狮、西安北郊北周安伽墓门砧石狮等。李毓芳认为:“李虎永康陵和李昺兴宁陵的石狮有明显的隋及北朝作风。”[14]
综上分析,可知永康陵、兴宁陵石刻明显分为两组,即石狮和独角兽为一组,带有北朝和隋代的作风,年代较早,而石柱、石马、石人为一组,年代较晚,约到玄宗时期。
四、结语
为了求得皇权的正统和出身的高贵,按照惯例,王朝建立必会对其先祖进行追封。因此李渊于武德元年五月二十日(618年6月18日)即位,仅一个月之后,便于六月二十二日(7月19日)对其先祖进行了追封。其中追尊其祖父李虎为景皇帝,“葬永康陵”;父亲李昺为元皇帝,“葬兴宁陵”[15]。
兴宁陵所在的咸阳原,自周代以来一直是历代帝王及高等级贵族的集中埋葬区。咸阳原是周、秦时期的一个重要陵区,西汉的9座帝陵、北周武帝孝陵及密戚功臣墓等都位于咸阳原上。西魏永陵位于富平县留古镇,文帝成陵位于富平县宫里镇,因此永康陵位于三原县陵前镇,距离都城也不是太远。另在咸阳发现的北周高等级贵族墓有拓拔虎墓、叱罗协墓、王德衡墓、若干云墓、独孤藏墓、尉迟运墓、王士良墓、侯子钦墓等[16]。
李渊祖父李虎在西魏时为左仆射、柱国大将军,北周时被追封为唐国公;父亲李昺在北周时任安州总管、柱国大将军,袭封唐国公。他们理应埋葬在离都城较近的咸阳至富平一带的渭北土原上。因此,李虎永康陵和李昺兴宁陵均应为二人的原始葬地。他们在李唐建立之前均已去世,初葬时的坟墓应符合其当时的身份地位,故坟墓本身应比较小,陵园范围也不会太大。
随着李渊祖、父封号的增崇,陵号的更改,陵园等级必然提高,范围也必然扩大,神道石刻的数量与组合也随之发生变化。这一时期,应会对陵园进行改造。从目前西魏至唐初的帝陵神道石刻来看,其种类与数量均较少,如西魏永陵前原有独角兽1对、石人1件;北周文帝成陵前原存石狮1件;北周武帝孝陵遵从遗诏“墓而不坟”[17];隋文帝泰陵陵前也未发现石刻;唐初的献陵除了石柱之外,陵前主要有石虎、石犀牛两种石刻。
北周时期的高等级贵族墓也发现有神道石刻,如尉迟运墓神道发现石人、石羊、石虎等,石人均为拄仪刀的武士形象[18]。从目前发现来看,北朝帝陵前已发现石狮、石兽、石人的设置,但因到玄宗泰陵时石人才开始分为文、武形象,所以推测两座祖陵神道石刻的独角兽和石狮年代较早,应为武德元年最初追封为陵时设置的。
开元二十八年七月十八日,玄宗又下令对四代祖陵进行了具体的规定:“伏以八代祖宣皇帝,七代祖光皇帝,六代祖景皇帝,五代祖元皇帝,自昔追尊号谥,稽古有则,而陵寝所奉,须广彝章。其建初、启运二陵,仍准兴宁陵例,置署官及陵户。自今已后,每岁至春秋仲月,宜分命公卿,准诸陵例,分往巡谒。仍命所司,准数造辂,于陵署收掌,以充备礼之用。其建初、启运、兴宁、永康等四陵,年别四时及八节,委所由州县,数与陵署相知,造食进献。”[19]其中“陵寝所奉,须广彝章”,即是对陵寝制度进行扩大、完善,因此可以推测,这一时期不但对陵园的祭祀礼仪进行了修改,还对陵园本身进行了改造和扩建,即新增了神道石刻,主要有石柱、石马、石人。
总之,永康陵和兴宁陵神道石刻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其中独角兽和石狮可能设置于唐初武德时期,而石柱、石马和石人则可能晚至玄宗时期。
[1]何正璜.唐陵考察日记[C]//何正璜考古游记.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0:192.
[2]巩启明.唐永康陵调查记[J].文博,1998(5).
[3]姜宝莲,秦建明.永康陵调查[J].文博,2002(6).
[4]咸阳市博物馆.唐兴宁陵调查记[J].文物,1985(3).
[5]贠安志.兴宁陵石雕艺术[J].美术,1984(4).
[6]林通雁.河北隆尧唐陵雕刻的年代问题[J].美术研究,1992(3).
[7]林通雁.初唐陵园雕刻与汉制及北朝模式[J].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4).
[8]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发掘资料,目前正在整理中。
[9]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唐高祖献陵陵园遗址考古勘探与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2013(5).
[10]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美茵兹罗马—日耳曼中央博物馆.唐睿宗桥陵[M].德国:美茵兹罗马—日耳曼中央博物馆出版社,2002:12-13.
[11]胡春勃.唐代陵墓及陪葬墓神道石柱样式分析[J].文博,2014(2).
[12]曾科.试论唐陵石狮的造型演变[J].文博,2013(3).
[13]该石狮现存洛阳博物馆。黄吉博,黄吉军.黄明兰洛阳考古纪实录[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3:297.
[14]李毓芳.唐陵石刻简论[J].文博,1994(3).
[15]王溥.唐会要:帝号上(第1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1-2.
[16]贠安志.中国北周珍贵文物[M].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3:172.
[17]令狐德棻等.周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1:107.
[18]同[16]:96-97.
[19]王溥.唐会要:公卿巡陵(第20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466-467.
——石界抗疫系列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