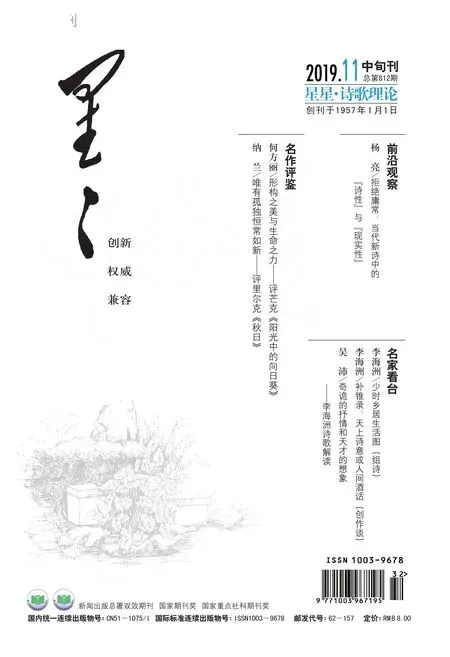拒绝庸常:当代新诗中的“诗性”与“现实性”
■ 杨 亮
谈到新诗中“诗性”与“现实性”的问题,我们很容易联想到“纯诗”与“杂诗”的概念。的确,在中国新诗发展历程中,每当诗学追求游走于“纯诗”脉络之时,都是诗坛“诗味”最浓的时刻,而当推动文学发展的“内因”精致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时,作为诗歌发展的另一因素——“现实”,则成为新诗前进的“外部”推动力量。正是在这内因与外因的交互裹挟下,中国新诗走过了百年的沧桑历程。可以说,诗与现实、诗性与现实性的问题是解读新诗发展的核心所在。尤其在面对当代诗学,面对当下纷繁复杂的诗歌现场之时,我们如何提炼、厘定这四十年来诗歌的发展变化或者说整体成就,如何对平面化的诗歌现场做出有效的诗歌批评、建构当代诗歌的评价标准,如何保有当代诗歌的个性与伦理担当,都是需要我们不断思索的。
一
对于诗性与现实性的统一,20世纪90年代的诗人为我们做出了许多可资借鉴的探索。诗与生活之间是介入还是抽离,一直是缠绕不清的话题。诗歌究竟应该排除一切非诗性因素,编织“纯诗”的乌托邦理想、还是应该拥抱生活,表现出介入的姿态?“为诗而诗”的诗学立场在于维护诗歌“本质的纯正”——穆木天曾说过:“我们要求的是‘纯粹的诗歌’。我们的要求是诗与散文的纯粹的分界。我们的要求是‘诗的世界’。”[1]80年代诗歌始终在“纯诗”的路径中滑动,或表现为对乡土家园农耕庆典式的颂歌调性,诗歌成为诗性的自我迷恋,缺乏同具体可感的历史建立内在的关联;或迷恋于“能指的狂欢”,“第三代”诗人花样翻新地不断表达着对深度写作、历史关怀的公然挑衅,“后现代”作为一个时髦的字眼在诗与现实中筑起了一座高墙,诗歌陷入一场从未经历的价值迷雾中。
冲破这层迷雾的是后来被称作“知识分子写作”的诗人们(在这里使用此概念,只为借用学界约定俗成的概念,并无意陷入“圈子”之争,亦无任何褒贬之意),90年代诗歌在诗学上提炼出很多有效的概念,比如“中年写作”“及物写作”“介入”“叙事性”等等,但涵盖这一切的,我认为应该是“包容”的姿态,建立一种“综合”的诗学,倡导对异质经验的介入,体现为各部件之间相互冲突的综合和平衡,“瑞恰兹的所谓‘综合的诗’——即是,不排斥与其主导情调显然敌对的因素的诗;这种诗,由于能够把无关的和不协调的因素结合起来,本身得到了协调……语境具有了稳定的结构:内部的压力得到平衡而且互相支持。”[2]
诗人的思路和视野纷纷发生转变,对此,西川表示:“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社会以及我个人生活的变故,才使我意识到我从前的写作可能有不道德的成分:当历史强行进入我的视野,我不得不就近观看,我的象征主义的、古典主义的文化立场面临着修正。”[3]“我开始能够理解以前我不喜欢的东西了……有一种人间烟火气,有一种日常生活的美。这种生活是有血有肉的。我觉得我可以和这个世界建立联系了。”[4]诗人们所呼吁的正是透过“纯诗”的迷雾,修正诗歌同现实的关系,以调和“诗性”与“现实性”之间的关联,重新建立诗同历史和人生的联系。
西川早期的诗歌聚焦点是在彼岸世界,其精神向度一直是垂直“向上”的,充满了对绝对神秘的无限向往与敬仰,“有一种神秘你无法驾驭/你只能充当旁观者的角色……”(西川《在哈尔盖仰望星空》),这句诗凝聚着一种属于80年代诗人们的精神气度,诗歌或诗的创作是神秘主义修行,在“词”与“物”的无限挤压和剥离下,现实中的一切对于诗来说,“陌生”得仅剩下旁观者的姿态了。但西川的另一首诗《坏蛋》则充满着对历史或经验世界的关怀和包容:
他的黑话有流行歌曲的魅力
而他的秃脑壳表明他曾在禁区里穿行
他并不比我们更害怕雷电
当然他的大部分罪行从未公诸于众
他对美的直觉令我们妒恨
且看他把绵羊似的姑娘欺负到脏话满嘴
可在他愉快时他也抱怨世界的不公正
且看他把喽罗们派进了大学和歌舞厅
……
在这首诗中,西川的“坏蛋”具有很鲜明的自省式特征,这些“坏蛋”如同被市场经济挤压下的边缘化“诗人”形象,他们口中所谓的诗篇带有“黑话”的流行歌曲魅力,他们穿梭于大学和歌舞厅——孵化出知识分子与“坏蛋”的“温床”,他们总是语出惊人,但却从不信守承诺,更不具备“被雷劈”的慌张,在这幅充满讥讽式“肖像感”的作品中,诗的聚焦点不再是神秘的“天空”,而是生活和现实,且带有俏皮的批判意味。值得留意的是,西川并没有陷入一种经典现实主义诗歌的批判经验或框架中,在处理“诗性”和“现实性”的问题时主动跳出了“主/客”二元对立模式,这也充分体现出二者融合的态势,那就是对现实的关注始终是充满了个人化想象的,是诗歌的外空间与内空间不断融合的过程,而不是剥离或吞噬。“既然生活与历史,现在与过去,善与恶,美与丑,纯粹与污浊处于一种混生的状态”,那么,诗歌作为承载这些混生状态的复杂载体,它柔软的身躯充满了诗性的关怀,但同样也具备了现实的开阔胸怀。“既然诗歌必须向世界敞开,那么经验、矛盾、悖论、噩梦,必须找到一种能够承担反讽的表现形式。”[5]而对这一表现形式所进行的艺术探索,正是90年代诗歌所贡献的又一关键词——叙事性。
二
欧阳江河指出,我们一贯坚持的诗学话语在90年代的时代语境中面临着中断。随着政治热情的不断降温,诗歌日渐被“边缘化”,90年代的诗歌现场是沉寂无名的,但也正因为此,诗歌获得了理性思考的自觉空间。90年代诗歌是在寂寥中不断发展、建构的,“叙事性”诗学话语的提出无疑是最为显著的理论成果,“叙事性”的出现修正了诗歌与现实之间的基本关系。当诗歌经历了80年代的政治狂热以及形式主义高蹈的艺术实验之后,诗歌在90年代呈现出敞开的态势,强调对异质性经验和此在经验的占有,重新恢复了诗歌同现实世界的联系。
将叙事性作为一门综合的诗学我想不会有人对此持异议。“(叙事性)是构成诗歌的手段……不单出现了文体的综合化,还有诸如反讽、戏谑、独白、引文嵌入等等方法亦已作为手段加入到了诗歌的构成中。”“在这里诗歌已经不是单纯地反映人类情感或审美趣味的工具,而是成为了对人类综合性经验的结构性落实。我个人更宁愿将‘叙事’看作是过程,是对一种方法,以及诗人的综合能力的强调。”[6]90年代诗歌的综合体现在其对异质经验的无限包容和占有,从写作题材来看,它涵盖了个人化的历史与现实生活的一切层面,尤其包括对生活的世俗性与日常性的吸纳;从语言风格来说则表现为叙事性所引发的陈述句的渗入,以及口语、方言的充分活跃;有意图地向小说、戏剧等叙事性文体借鉴挖掘诗歌的文体潜力等等。而这一切的综合手段毫无疑问丰富了90年代诗歌多样态的艺术表现与美学层次。
当然,除了以上从微观角度提炼叙事性作为一门综合的诗学以外,我想更高维度的综合则体现在叙事性基本的诗学立场。叙事性具有折衷主义倾向,以调和为基本立场的诗学话语。它可以调和任意处于两个极端的基本元素,在这诸多元素中,对现实的介入以及保持艺术独立的双向承担是叙事性的终极追求。在西川那里,这表现为“当历史强行进入我的视野,我不得不就近观看”,而耿占春则将其表述为“一场诗学与社会学的内心争吵”,欧阳江河将这一场转变概括为“富有洁癖的诗歌开始向现实敞开”,但却永远不会逆转成为“普遍性的话语”,孙文波则将“具体”“结构”和“题材”作为“诗的叙事”所必须面临的三个主要问题,而这里的“题材”显然是面向现实的。
因此,叙事性重新调整了诗歌同经验世界的关联——在诗性与现实性之间搭建了一座浮桥,是在各种介质因素间建立的一种平衡的诗学。叙事性的确强化了诗歌当中的叙事能力,强化了诗歌占有和吞吐现实生活的能力。
陈东东总是在想象的层面构筑艺术的海市蜃楼,甚至带有些许魔幻的意味。他善于在现实的经验之外聆听“神”的旨意,总有一种超乎凡尘的灵气。他对语言的雕琢、结构的精致打磨、意象的考究甚至文本中的空白间隙都试图做到精益求精。但是,这一情形在90年代也发生了转变,现实的介入使陈东东的诗游走于生活与想象、现实与魔幻的中间地带,“在陈东东的诗中,‘超现实’的想象未必是‘非现实’的”[7]。如这首《全装修》,一开篇诗人便营造出一种不同寻常的魔幻氛围:“来自月全食之夜的沙漠/那个色目人驱策忽必烈/一匹为征服加速的追风马”,如此骑士模样的草原枭雄却被护心镜折射出的“落日之光”,拉入了现实生活:“如箭镞,从镶嵌在/卫生间墙上这片瓷砖的/装饰图案里,弹出舌尖去舔//去舔破——客厅里那个人/却正以更为夸张的霓虹腰身/将脑袋顶入液晶显示屏”。原来,诗人所刻意烘托的骑士形象竟然只是浴室瓷砖上的装饰图案,他魔幻般地运用想象在不同世界中穿越,历史记忆、现实生活甚至是虚构的网络世界都被一幅“骑士的图案”串连起来,其中还不乏现实讥讽。诗人的想象天赋游戏般地穿梭于文本间隙所营构的不同世界中,我们在惊呼诗人卓越的文本构思能力之时,诗人却告诉我们这样的真实:“一个逊于现实之魔幻的/魔幻世界是他的现实”。无论是出没于“月全食之夜沙漠”的头戴红缨的中古骑士,还是在“帝国时代”(网络游戏)驰骋疆场的草原英雄,这样的想象却远逊于生活中的荒诞,历史的辉煌仅仅定格于卫生间的墙上,我们正在用生活消解着一切,真正的“魔幻”或“荒诞”存于生活之中,这也是诗人陈东东“真实观”的进一步深入。但无论如何,文本中蕴含了现实生活与想象世界不停穿梭的场面,构筑着现实与艺术双重话语交织的文本结构。此外,张曙光、孙文波、翟永明、臧棣、西川、欧阳江河、萧开愚、于坚等诗人也在90年代纷纷尝试在诗歌中寻求叙事的方式,在诗性的想象中插入带有叙事性的现实元素,形成了意想不到的风格化叙事,拓宽了诗歌的表现能力和疆域,实现了90年代诗歌诗学理想的结构性落成。
三
不可否认的是,90年代诗歌所倡导的“及物写作”以及“叙事性”将事件、故事拉入了诗的视域范畴,加之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写诗、发表诗歌均成为信手拈来之事,这一切所催生出的不良后果既是写诗的难度在不断下降,诗人的准入门槛也在不断下降。在当下诗坛,随处可见广告词、网络段子、口水诗、“散文+回车键”式的伪诗写作。
“一个扛着梯子的人/在大街上走来走去/他在寻找从哪里/可以登上青天”,(缪立士《扛梯子的人》);“学生时代,/我跑得很快,/我以为,/终有一天,/我的速度,/足以追上未来。”(陈子敏《追上未来》);“现在天空有事干了,/现在天空在下雪;/现在我也有事干了,/我在看着天空下雪。”(《天空和我都忙着》);“上午我进了聊天室/里面有两个人/一个是小鱼儿/一个叫所有人/我向所有人打了个招呼/他没有理我/我 就走了……”(小鱼儿《今天我进了聊天室》)等等诸如此类。毫无疑问,在读这些诗句的时候,我们都会感受得到,诗歌在无限度地贴合“现实”层面的同时,“诗性”早已荡然无存了。究竟什么是诗性?难道仅仅是诗歌中随意挥肆的主观情愫,难道是日益僵化的意象情景,又或者是堆砌起的丰富而矫情的词藻?真正的“诗性”,是一个元命题,是一道无解的永恒命题,但是当下诗坛及其精神性与艺术性的双向“走低”态势却均体现出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缺乏“诗性”的写作一定是一种降低甚至无视写作难度的随意行为,这一切并不是90年代诗歌所倡导的介入诗学和叙事诗学的初衷。
与当下诗坛表象相反,90年代诗歌的诗学理想虽面向现实而敞开,却是一种真正有难度的写作。有勇气有担当的诗人们突破既有的写作藩篱,不断以自己的诗歌实践探索着抒情与叙事、诗性与现实性之间的关联。他们让诗歌回归至“写作”的理性创作路径上来,一方面放弃了传统的将诗的发生归结于神秘主义倾向,另一方面也自觉地将诗歌关注的重点从“写什么”(事件/故事)转移至“怎么写”(叙事的过程)上,写诗(写作)更趋理性化,成为一件日臻至美的艺术创作,对细节的打量,对结构的思忖,对风格的营造,这一切恰是当下诗作中那随意充斥着的“事件”与“故事”中最为缺乏的。
就女性主义诗歌而言,与80年代盛行的“内心独白”不同,90年代的女性主义诗歌将叙事文体所擅长的“对话”形式纳入了诗的领域。“独白体”的作品总是围绕“我”而展开,“我是最温柔最懂事的女人”(《独白》),“我被遗弃在世上,只身一人……”“岁月把我放在磨子里,让我亲眼看见自己被碾碎”(《女人》),“内心独白”在叙述者进行深度内心剖析方面的完成度是非常高的。诗的情感极为丰沛,但它的问题就在于诗完全由情绪流所支配,因此属于一种线性的诗体结构,这种结构的诗歌话语模式注定是单调而缺乏变化的,而且它彰显的是写作者对叙述的绝对掌控力,“关键的问题不在话语是内心的,而在于它一上来就摆脱了一切叙述模式,一上场就占据了前台。”[8]但是,翟永明总是对“叙事过程”给予充分的尊重,自觉追求一种难度写作。她将诗从各种观念图解中解放出来,恢复话语自由度,极力抹去叙述主体的印记,让人物自己说话,它的诗体现出了戏剧体对诗体的影响和渗透。并且,诗人们也十分在意“对话”的带入方式,如“母亲说:‘在那黄河边上/在河湾以南,在新种的小麦地旁/在路的尽端,是我们村。’”“她们的爱人都已逝去/‘在黄河上刮来刮去的寒风/每年刮着他们年轻的尸骨’”(《十四首素歌 黄河谣》),后一句引语中诗人主动避开了引导语“某某说”,其实这句话也出自母亲的讲述,但主动避去的做法还是带来效果上的不同,引导语的取消使引用受叙述环境的压迫变小,也就是说,“母亲”的话成为了同时代女性共同的命运写照。可见,任意一处细节都不应是“笔随心至”的草率行为,叙事过程的每一个设想都应该是面向可能性的谨慎之举。
由此可见,当下诗坛大量充斥着的崇尚官能化、快餐化、平面化的日常主义诗作,它们是21世纪诗歌的“流行诗”,而造成这一局面的恰恰是企图与现实同构的“媚俗”倾向。它们所追求的反历史、反价值、反文化、反深度等种种“后现代”任意妄为,在“炫酷”的外表下掩盖着的是一种艺术上的“无为”,而不是真正的“无畏”。在今天,我们重新思考当代诗歌的“诗性”与“现实性”问题,应该放弃二者作为不可调和之两极的对立思路,回到90年代诗歌所奠定的艺术路向上来:在保有诗性关怀的前提下,充分探索诗对现实的介入与敞开。
注 释
[1] 穆木天:《谭诗——给沫若的一封信》,《创造月刊》,第1卷第1期。
[2] 克利斯安·布鲁克斯:《反讽——一种结构原则》,袁可嘉译,赵毅衡编选《<新批评>文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382页。
[3] 西川:《大意如此》,湖南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
[4] 西川:《当代诗歌承担了什么》,《诗潮》2004年第4期。
[5] 西川:《大意如此》,湖南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24页。
[6] 孙文波:《我理解的90年代:个人写作、叙事及其他》,《诗探索》1999年第5期。
[7] 姜涛:《一首诗又究竟在哪儿——陈东东<全装修>解读》,《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2期。
[8] 申丹、王丽亚:《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版,第1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