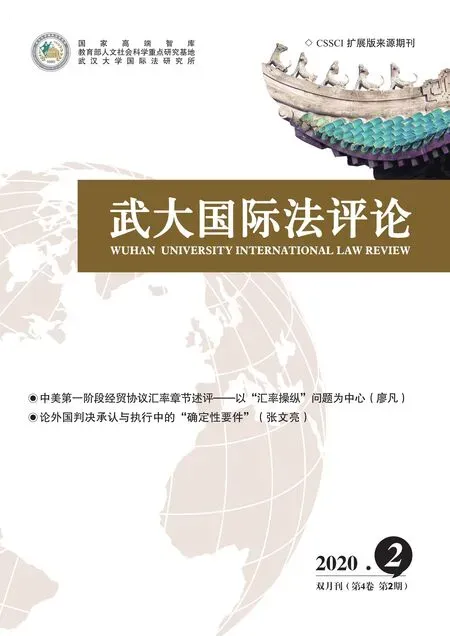ICSID与内国执法机关间反腐协作机制的构建:缘起、法律基础与策略
银红武
在外国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事项上,自21 世纪初期起,东道国在仲裁程序中所援用的腐败抗辩议题日益引发特别关切。毋庸置疑,“腐败”因素的介入使得国际投资争端的解决变得更为复杂(如仲裁庭的管辖权问题等)。反腐法治问题已逐渐成为新近国际投资仲裁的焦点议题。
一、构建ICSID与内国执法机关间反腐协作机制的现实缘起
尽管就目前而言,鉴于其身处内国控制范围之外,投资仲裁庭总体上可为打击国际投资腐败行为提供有效机制:确保投资者免受可能腐败的内国司法系统的裁判,仲裁庭(尤其ICSID 仲裁庭)所作裁决相对透明公开且可执行性强。①See Michaela Halpern, Corruption as a Complete Defense in Investment Arbitration or Part of a Balance, 23 Willamett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 Dispute Resolution 297-317 (2016).但是,基于国际投资腐败行为的跨国性与复杂性等原因,国际投资仲裁庭在单独应对涉腐国际投资争端时经常表现得较为被动。
(一)国际投资仲裁庭反腐调查与裁决执行职权的先天不足
毋庸置疑,诸如2007年Siemens AG仲裁案裁决②See Siemens AG v. Argentine Republic, ICSID Case No.ARB/02/8, Award.事后被证实为错误裁判事件的发生从侧面揭示了投资仲裁庭缺乏足够的手段与工具从事腐败刑事调查的无奈现实。从传统意义上讲,仲裁(包括投资仲裁)并不被视为对贿赂乃至腐败诉请进行裁判的一个理想场所。不难理解,对腐败诉请的可裁决性不予认可虽然主要是基于主张对仲裁庭管辖权予以限制的观点,但其中当然也包含了对仲裁庭在强制要求争端方提供证据方面权力有限的担忧——尤其是将其与对腐败行为强有力的调查乃至起诉权的内国监管职权部门进行比较,更是相形见绌——况且,投资仲裁庭还缺乏强制执行刑事处罚的职权。③See Andreas Kulick & Carsten Wendler, A Corrupt Way To Handle Corruption?:Thoughts on the Recent ICSID Case Law on Corruption, 37 Legal Issues Economics Integration 61, 83 (2010).事实上,根据ICSID公约第54条第1款④ICSID 公约第54 条第1 款规定:每一缔约国应承认依照本公约作出的裁决具有约束力,并在其领土内履行该裁决所加的财政义务,正如该裁决是该国法院的最后判决一样。具有联邦宪法的缔约国可以在联邦法院或通过该法院执行裁决,并可规定联邦法院应把该裁决视为组成联邦的某一邦的法院作出的最后判决。,针对ICSID“裁决所加的财政义务”的强制执行,亦必须依靠缔约国法院得以最终实现。此外,在仲裁庭为东道国成功援引投资腐败抗辩所设置先决条件(如要求东道国已对同时涉嫌腐败的本国政府官员提起了公诉或承诺将提起公诉等)的执行方面都离不开内国反腐执法机关的监督与配合。
(二)跨国投资腐败本质剖析中的ICSID与内国执法机关的联动必要
国际投资腐败既可发生于外国投资进入东道国市场之前阶段(如通过伪造资格许可证或采取欺诈性陈述骗取市场准入资格),亦可发生于进入东道国市场之后阶段(即在外国投资经营过程中从事腐败行为)。无论处于哪一阶段与采纳何种形式,东道国内国反腐执法机关均对跨国投资腐败行为享有管辖权(前者基于保护性管辖权,后者基于属地管辖权)。此外,国际投资腐败行为还可细分为单边腐败行为(即外国投资者单方面涉嫌腐败违法)与双边腐败行为(如贿赂涉及投资者行贿与东道国政府官员受贿两方面)。在对投资腐败进行本质剖析时,鉴于投资腐败行为大多发生于东道国境内,依据国家主权独立原则,在投资腐败行为的调查取证方面,国际投资仲裁庭难以抛开内国反腐执法机关的协作与配合。
(三)仲裁庭证据采纳标准不明确的现实困境与内国反腐机关的辅助取证解决
ICSID 仲裁庭本来在其据以作出支持东道国腐败抗辩的三大法律理由①这三大法律理由是:国际(或跨国)公共政策原则;投资必须“遵照东道国法律”作出的要求;当事方诚信行事的义务。除了Inceysa案仲裁庭表现为将“诚信原则”与“国际公共政策”并入至“投资必须‘遵照东道国法律’作出的要求”中之外,其他ICSID 仲裁“判例法”表明前两项为独立的可援引法律理由——即便缺乏“遵照法律”条款的支撑,仲裁庭依然可以对两项法律理由进行援引。方面就已存在一些技术细节的不确定性②依照Michael A. Losco.的观点,第一个不确定性是投资者必须遵守哪些法律法规,以及怎样才能称得上“遵照法律”?第二个不确定性在于,“遵照东道国法律”条款是否对投资者施加了一种持续义务,要求其对具体投资的守法情况实行全程监管,抑或该条款仅适用于投资作出之前的阶段范围?第三个不确定性是,在裁定投资者违反适用法的责任时,是否存在一些能主张减轻责任的裁量因素?See Michael A. Losco, Note: Streamlining the Corruption Defense: A Proposed Framework for FCPA-ICSID Interaction, 63 Duke Law Journal 1201-1241 (2014).,更何况在争端方到底应承担何种证据责任问题上,仲裁庭的裁决法理可谓更是“令人费解”③See Michael A. Losco, Note: Streamlining the Corruption Defense: A Proposed Framework for FCPA-ICSIDInteraction, 63 Duke Law Journal 1201-1241 (2014).。就目前而言,仅有极少数涉腐投资案的仲裁庭明确了裁判的证据标准(如Siag v. Arab Republic of Egypt 案④See ICSID Case No.ARB/05/15, Award, p.326.适用了“清晰且令人信服的”证据标准),大多数案件均未确定明确的证据标准。未来投资仲裁庭究竟应适用何种证据规则不得而知。案件审理过程中,仲裁庭似乎对事关腐败的种种主张不愿进行深入探询(即便能获取进一步的证据)。
1.个别仲裁庭适用“清晰且令人信服的”证据标准
Siag v. Arab Republic of Egypt 案仲裁庭适用了美国法意义上的、介于传统民法“优势证据”标准⑤美国民事诉讼中所适用的“优势证据规则”是指当诉讼一方提供的证据所证明事实的概然性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所证明的事实时,前者的证据优先得以采纳。(亦称“概然性权衡规则”)与刑法“排除合理怀疑”标准之间的“清晰且令人信服的”证据标准。仲裁庭认为,无论从申请方已经援引大量初步证据证明自己并未涉嫌欺诈的角度分析,还是从严重违法行为(如欺诈等)的控诉要求较高的证据标准方面来看,该标准都是适当的。⑥See Siag v. Arab Republic of Egypt, ICSID Case No.ARB/05/15, Award,pp.324-326, http://italaw.com/sites/default/files/casedocuments/ ita0786_0.pdf, visited on 20 December 2019.
2.绝大部分仲裁庭主张采纳的证据标准不确切
绝大部分仲裁庭在应对东道国所提出的腐败抗辩时,一方面认为后者援引的证据不足以支撑其抗辩,另一方面却未能对自身应予适用的确切证据标准。⑦个中原因以Wena Hotels Ltd. v. Arab Republic of Egypt 案为代表。该案中,申诉方“非常可疑地”定时向其位于东道国的代理人支付了总共5.2 万英镑的款项。本来仅向中间人支付“可疑”款项这一事实并不足以认定为构成“欺诈行为”,但仲裁庭依然不愿划出一条明确的分界线。可以说,“准确区分合法与非法合同、非法贿赂与合法佣金间的分界线”对于仲裁庭而言,依旧是一个略显微妙的棘手问题。See Florian Haugeneder & Christoph Liebscher, Corruption and Investment Arbitration: Substantive Standards and Proof, in Christian Klausegger et al., Austrian Arbitration Yearbook (2009) 539, 549-550 (Manz Publ.2009).事实上,尽管各仲裁庭在确切证据标准上存在分歧,但在证据标准方面普遍趋向于主张高标准要求——“对贿赂行为的控诉需要承担最严厉的举证责任”。也即对腐败行为的控告必须证明其具有非常高的盖然性。①See Douglas Thomson, How to Deal with Corruption Allegations. Global Arbitration Review,http://globalarbitrationreview.com/news/article/32055/how-deal-corruptionallegations,visited on 14 October 2019.当然,投资仲裁实践中也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如在Siag 案中,一位持不同意见的仲裁员就主张采纳较低的证据标准,允许仲裁庭基于“一致的间接证据(concordant circumstantial evidence)”自主进行推论。但截至目前没有仲裁庭适用该仲裁员所主张的这一标准。
3.内国反腐机关的辅助取证解决
鉴于目前ICSID 仲裁庭遭遇跨国投资腐败证据采纳标准不明确的现实困境,仲裁庭理应非常乐意将内国反腐执法机构列为“私家侦探”,以此保障仲裁裁决是基于“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法律原则而作出。反过来说,内国反腐执法机关也应提供信息帮助,理由在于:建立在准确信息基础上的ICSID 裁决一方面将对诚实的投资者提供嘉奖,另一方面将对从事腐败投资活动的投资者实施惩罚,这也是内国反腐执法机关所肩负的国际责任“使然”。②参见银红武:《ICSID 仲裁庭应对东道国腐败抗辩的困境及其解决——以仲裁庭对涉腐投资主张无管辖权为切入点》,《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9年第4期,第80页。故而,实践中部分投资仲裁庭明知涉腐行为正处于内国调查进程中却未等到调查结果出炉便先行裁判③See Fraport AG Frankfurt Airport Servs. Worldwide v. 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 ICSID Case No.ARB/03/25, Award, p.47.的做法非但不值得提倡,反而应予以批判并坚决摒弃。
综上,尽管仲裁庭所面临的现实困境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这并非意味着以ICSID为首的投资仲裁庭在打击国际投资活动中的腐败行为方面不应该或不能有所作为,毕竟仲裁庭对最终公平公正地解决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间争端是留有余地且拥有杠杆手段的。面对投资争端方日益援用腐败抗辩(其范围有扩大的趋势)的国际投资仲裁现状,考虑到国际投资仲裁机构与国内反腐执法机关的职能重合特征和功能贯通现实,若能成功创设两者间的反腐法治合作机制,那么就能更好地确保国际反腐功效的实现,切实保护国际投资活动的全球公共利益,并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国际投资共同体构建的目标。
二、构建ICSID与内国执法机关间反腐协作机制的跨国投资国际合作反腐立法
历经过去二十余年的巨大发展变化后,表现为国际规范和国家措施的全球反腐法治标准方兴未艾。
(一)国际经贸反腐专门条约与腐败治理条款中的跨国投资国际合作反腐规定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于1997 年制定《禁止在国际商业交易中贿赂外国公职人员公约》(下称《公约》)对“贿赂”①事实上,该公约第1 条第1 款所定义的“贿赂”主要指的是“行贿”行为,并未规范“受贿”行为。议题予以了调整。②实践证明,在国际投资仲裁语境下,经合组织《公约》其的直接影响力有限,主要原因在于:其一,尽管绝大多数资本输出国已签署《ICSID 公约》,但仅有少数《ICSID》公约缔约国同时亦为经合组织《公约》缔约国;其二,经合组织《公约》只要求对投资者母国境内的行贿行为实施刑罚。但众所周知的是,国际投资争端却主要聚焦于东道国对投资者的待遇问题。因而可以说,经合组织《公约》的重要性在于它向国际社会传递了一个信号,即对国际公共政策所关切的腐败问题应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并设法应对。欧洲委员会《反腐败刑法公约》(1999 年)随后面世。相较于经合组织《公约》,《反腐败刑法公约》的调整范围更广:缔约国有义务对贿赂(包括国内和国外)、洗钱和会计犯罪等腐败行为实施刑罚(第12~15 条)。此外,《反腐败刑法公约》规制的对象除了内国政府官员外,还涵盖国际组织机构中的行政官员、法官及立法成员,即便是私营部门的腐败行为也纳入刑罚范畴(第2~11条)。③与经合组织《公约》一样,欧洲委员会《反腐败刑法公约》仅要求成员国设法在其内国法中对各种腐败行为方式实施刑罚,并未能在东道国与投资者的国际关系方面就腐败问题创设直接的条约义务。2005通过的、堪称“方法意义深远,许多条款具有强制性,为全面解决全球反腐败问题提供了独特蓝本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三章“定罪和执法”全面列举了11 种腐败(犯罪)行为(第15~25 条):贿赂本国公职人员;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公职人员贪污、挪用或者以其他类似方式侵犯财产;影响力交易;滥用职权;资产非法增加;私营部门内的贿赂;私营部门内的侵吞财产;对犯罪所得的洗钱行为;窝赃;妨害司法。
值得注意的是,《美墨加协定》(USMCA,2018 年)“反腐败”篇第27 章专门从“定义”“范围”“打击腐败措施”“公共官员的廉洁促进”“私营部门与社会的参与”“反腐败法律的适用与执行”“与其他协议的关系”“争端解决”“合作”九个方面强调缔约各方的反腐败集体应对以及与其他国际组织的反腐合作义务等。
(二)内国国际经贸反腐立法中的跨国投资国际合作反腐规定
当然,规制国际经贸活动中的腐败行为的法律规范还体现于内国的刑法、行政法与民法体系之中。美国在1977 年即颁布了《海外腐败行为法》。国际范围内,自21 世纪初以来,打击国际投资腐败行为的内国强制执行法的数量呈现大幅增长的态势。④单在2004 年至2009 年期间,国际范围内的反腐败内国强制执行法从最初的五部上升至40 多部。 See Lauren Ann Ross, Using Foreign Relations Law To Limit Extraterritorial Application of the 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 62 Duke Law Journal 460(2012).美国《海外腐败行为法》由两部分内容构成:一是反贿赂规定;二是财务制度条款。其中,反贿赂条款禁止公司(包括代理与雇员)向外国官员支付钱财或赠送礼物。该法采纳供给侧路径对腐败进行惩治与预防——尝试通过惩罚行贿的公司来减少对外国官员的贿赂供给,而不是试图对受贿的官员予以惩治而实现减少贿赂需求的目的。①See David C. Weiss, Note: The 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 SEC Disgorgement of Profits, and the Evolving International Bribery Regime: Weighing Proportionality,Retribution, and Deterrence, 30 Michig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471-477 (2009).在《海外腐败行为法》框架下,司法部和证券交易委员会还可以对被告进行民事处罚,处以罚金,勒令被告停止其违法活动,也可以禁止被告入市。1998年修订的《海外腐败行为法》通过属地管辖权将执法范围扩展至外国公司或外国自然人:外国企业或个人在美国境内直接或间接的违法行为将受到《海外腐败行为法》的制裁,不论该行为是否使用美国邮政系统或者其他转移支付工具。
相较于美国《海外腐败行为法》,英国的《反贿赂法案》(2010 年)覆盖面更广、执法更为严厉(前者仅规定对公共官员的行贿入刑,而后者将刑事惩治扩展适用于向私人或私营部门间的贿赂行为,并且几乎所有与“英国”有关联的个人或者公司都在该法案的约束之下;前者将出于“推动或确保政府例行履职”目的而支付的“便利费”规定为例外情形,后者却没有这样的例外规定)。②See Sharifa G. Hunter,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 and the U.K. Bribery Act, and the Practical Implications of Both o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18 ILS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 Comparative Law 89-109 (2011). 根据Hunter教授的观点,英国《反贿赂法案》的实际影响取决于英国“反严重欺诈办公室”的“监察胃口”。
部分国家已开始重视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国内立法,2018 年10 月26 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以下称《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就是较好的示例。该法第67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有关国际组织开展刑事司法协助,参照本法规定”为ICSID 与中国执法机关间的反腐刑事司法合作机制构建提供了明文法律依据。
事实上,依照《ICSID 公约》第42 条第1 款的规定,投资仲裁庭“应依照双方可能同意的法律规则对争端作出裁决。如无此种协议,仲裁庭应适用作为争端一方的缔约国的法律(包括其冲突法规则)以及可能适用的国际法规则”。这也意味着,ICSID仲裁庭裁判案件时可适用的法律既包括国际法渊源亦包括内国法渊源。在选择适用内国法渊源的情形下,仲裁庭对法律的解释与适用有可能需借助内国执法机关的力量(比如法律查明、判例查找与法律意见咨询等),以此彻底解决内国法反腐规定的实际适用方面的不确定性问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ICSID与内国执法机关间反腐协作机制的构建是跨国投资国际合作反腐法治的必然结果。
三、ICSID仲裁庭与内国执法机关间的反腐协作策略
下文基于ICSID 仲裁与内国反腐执法程序的启动时间顺序分别对两者间的互动协作策略予以探讨。
(一)ICSID仲裁程序先于内国反腐执法程序
1. 仲裁庭对东道国成功主张腐败抗辩进行条件设置
考虑到ICSID 仲裁庭反腐裁决法理与实践易造成外国投资者和东道国权益保护的失衡,有必要对后者成功主张腐败抗辩预设条件:投资仲裁庭可要求东道国举证其已对本国涉嫌共同腐败的官员启动了公诉程序;或者东道国应表明在其法律框架下已然贯彻施行了所要求的反腐败标准;或者已经采取强有力的遏制措施对腐败予以了打击。此外,仲裁庭还应考量东道国在投资者腐败行为中的责任,东道国仅能在其无罪的范围内援引腐败抗辩等。①参见银红武:《ICSID 仲裁庭应对东道国腐败抗辩的困境及其解决——以仲裁庭对涉腐投资主张无管辖权为切入点》,《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9年第4期,第77页。在投资争端的实际解决过程中,腐败抗辩的成功采纳可导致内国相应的反腐调查;反过来,内国的反腐调查结果亦可作为成功提起腐败抗辩的依据。
2. ICSID向内国提出反腐司法协助请求
鉴于投资者从事腐败的证据一般处于东道国境内,再加上在腐败证据收集方面仲裁庭职权存在“先天不足”,因而面对东道国针对外国投资所提起的腐败抗辩,仲裁庭略显“心有余而力不足”。就仲裁庭而言,一方面,应要求东道国遵守“清晰且令人信服的”证据标准而承担举证责任;另一方面,在必要时仍需寻求内国反腐执法机关的司法协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第13条,ICSID“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提出刑事司法协助请求的,应当依照刑事司法协助条约的规定提出请求书。没有条约或者条约没有规定的,应当在请求书中载明下列事项并附相关材料:(一)请求机关的名称;(二)案件性质、涉案人员基本信息及犯罪事实;(三)本案适用的法律规定;(四)请求的事项和目的;(五)请求的事项与案件之间的关联性;(六)希望请求得以执行的期限;(七)其他必要的信息或者附加的要求……请求书及所附材料应当附有中文译文。”考虑到ICSID 与中国政府间并未缔结刑事司法协助条约的情况,ICSID应向中国政府作出互惠承诺。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第5条第2、3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等对外联系机关负责提出、接收和转递刑事司法协助请求,处理其他与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相关的事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外国之间没有刑事司法协助条约的,通过外交途径联系。”按照该条规定,ICSID 只能通过中国外交部向我国政府提出反腐司法协助请求。依照《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第6 条,我国国家监察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等部门是开展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主管机关,按照职责分工,审核向外国或国际组织(如ICSID 等)提出的刑事司法协助请求,审查处理对外联系机关转递的外国或国际组织提出的刑事司法协助请求,承担其他与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相关的工作。
3. ICSID向内国请求安排证人作证或者协助反腐调查
ICSID 在解决涉腐国际投资争端过程中,若有必要,还可以请求外国政府(主要为东道国政府)协助安排证人、鉴定人赴外国作证或者通过视频、音频作证,或者协助调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第32 条规定,ICSID 向中华人民共和国请求安排证人、鉴定人作证或者协助调查的,请求书及所附材料应当根据需要载明“(一)证人、鉴定人的姓名、性别、住址、身份信息、联系方式和有助于确认证人、鉴定人的其他资料;(二)作证或者协助调查的目的、必要性、时间和地点等;(三)证人、鉴定人的权利和义务;(四)对证人、鉴定人的保护措施;(五)对证人、鉴定人的补助;(六)有助于执行请求的其他材料”诸事项。
(二)ICSID仲裁程序与内国反腐执法程序同步进行
1.仲裁庭意图借助内国反腐调查结果主动暂缓案件审理
Fraport 仲裁案称得上是ICSID 仲裁程序与内国反腐调查程序同步进行的一个典型案例。就本案而言,菲律宾内国执法机关启动反腐调查程序所取得的相关文件对于ICSID 仲裁庭来说应该是非常有用的。但遗憾的是,这些材料未能转交至该案仲裁庭。被诉的菲律宾政府在内国反腐调查结果未出来之前曾向仲裁庭提出中止仲裁程序的请求。但仲裁庭并未同意中止审理。仲裁庭的这一做法着实令人费解,估计未来ICSID 仲裁庭极有可能仍将延续这一做法。尽管作为东道国的菲律宾最终在仲裁案中胜出(裁判法理是Fraport公司方面的投资未能遵照菲律宾法律作出)——但事实上,该案内国反腐调查所查明的信息本来已经为菲律宾获胜提供了可行路径。无疑,ICSID仲裁庭不愿等待内国反腐调查结果出炉而中止仲裁程序的做法使得内国反腐调查执法机关在证据收集方面相较于ICSID所具有的优势大打折扣——虽然ICSID仲裁庭在要求投资争端方提交证据问题上的确拥有一定的强制权力,但是此种职权与内国反腐执法机关被授予的调查权(如美国《海外腐败行为法》框架下美国司法部、证券交易委员会与联邦调查局被赋予的调查权力)相比,还是有较大差距的。因而,出于利用内国反腐机关所能获取的调查资源的目的,ICSID仲裁庭应先向内国反腐机关征询在内国反腐调查结果未出前是否暂缓仲裁程序的建议,并将这种做法作为一项政策予以遵守——当然,内国反腐机关也应该积极准备提供建议。
就目前而言,部分ICSID 仲裁庭基于案件审理时间、成本与效率方面的考量不会轻易作出中止仲裁程序的决定。但是出于避免重蹈2007年Siemens AG仲裁案之覆辙的目的,接受争端方所提请的暂缓案件审理的申请是完全有必要的。
2. 外国投资者申请方应内国反腐执行机关要求申请暂缓仲裁案件审理
无疑,内国反腐执法机关有能力找寻那些完全可能逃脱仲裁庭注意的证据。正是基于内国执法机关的反腐调查优势,对于投资仲裁与内国反腐执法同步进行的案件,内国反腐机关也应鼓励投资者申请方向仲裁庭提交中止仲裁请求。这一方面能给内国反腐执法机关进行全面调查创造比较宽缓的外部条件;另一方面,内国反腐调查结果亦可对ICSID 仲裁庭的审理提供裁判依据,仲裁程序可在内国反腐调查结果落定后得以继续进行。投资仲裁庭本应争取尽可能多的、能胜任的内国反腐执法机关,以此来确保自身仲裁裁决建立在准确、全面的事实上。就内国反腐执法机关而言,其亦会十分乐意提供协助——毕竟,建立在准确信息基础上作出的ICSID 裁决既可以对诚实守信的外国投资者施以嘉奖,亦能使真正进行腐败行为的不诚信投资者难逃法律惩罚。
3. 内国反腐执法机关向ICSID仲裁庭告知腐败调查结果
内国反腐执法机关根据反腐调查结果可采取不同策略与ICSID 仲裁庭对接。如内国反腐调查未发现任何外国投资者涉嫌腐败的证据,则内国主管职能部门可向仲裁庭作如实告知。当然在这一情形下,作为被诉方的东道国政府无法主张腐败抗辩,自知理亏的东道国会表现出不情愿轻易将“投资者清白”的调查结果交付ICSID 仲裁庭。因此,内国反腐执法机关的通力协助配合,需要在如ICSID 的国际仲裁组织与东道国政府间缔结有司法协助条约;或内国机关依据国内法承担法定义务;抑或两者间根据互惠原则相互提供司法协助。
若东道国反腐执法机关确实掌握了外国投资者涉嫌腐败的确凿证据,一方面,在现行投资仲裁法理下东道国一般会选择向仲裁庭披露这一信息,从而极有可能收获仲裁庭拒绝行使管辖权的结果(外国投资者变得投诉无门);另一方面,东道国反腐执法机关也可寻求向外国投资者摊牌,要求对方撤回投资仲裁请求,并将这作为内国起诉协议书的部分内容。如此一来,外国投资者基本丧失其在相关双边投资条约下受保护的权益。但以Siemens 公司为鉴,投资者基本也会接受东道国所开列的条件——毕竟不配合的话,外国投资者在遭遇牢狱之灾与钱财两空的同时,还极有可能落得身败名裂。
(三)内国反腐执法程序先于ICSID仲裁程序
1. 内国反腐执法程序:以美国为例
(1)美国反腐执法机关
在美国,强制执行《海外腐败行为法》的重任主要由美国司法部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配合完成:前者调查、起诉刑事犯罪;后者则负责对违法者提起民事诉讼。证券交易委员会传统上基本负责应对违反《海外腐败行为法》财务条款的行为,但是,如今该机构在执行有关受贿条款方面变得越来越主动。就目前而言,这两大部门表现为“联手对违法者提起刑事或民事诉讼”。①David C. Weiss, Note: The 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 SEC Disgorgement of Profits, and the Evolving International Bribery Regime: Weighing Proportionality, Retribution, and Deterrence, 30 Michig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471-477 (2009). See Thomas McSorley, 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 48 American Criminal Law Review 749-780 (2011). 美国司法部报道,联邦调查局在2011 年的行动中逮捕了22 名涉嫌违反《海外腐败行为法》的自然人。此外,该局据报道仅2011 年一年就介入了至少六起未公开的《海外腐败行为法》调查案。值得一提的是,美国联邦调查局近些年来亦开始在《海外腐败行为法》的违法调查中充当重要角色。①David C. Weiss, Note: The 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 SEC Disgorgement of Profits, and the Evolving International Bribery Regime: Weighing Proportionality, Retribution, and Deterrence, 30 Michig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471-477 (2009). See Thomas McSorley, 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 48 American Criminal Law Review 749-780 (2011). 美国司法部报道,联邦调查局在2011 年的行动中逮捕了22 名涉嫌违反《海外腐败行为法》的自然人。此外,该局据报道仅2011 年一年就介入了至少六起未公开的《海外腐败行为法》调查案。
(2)美国内国执法机关的反腐处罚
在美国,触犯《海外腐败行为法》主要可遭致刑事处罚与利润回吐处罚。“利润回吐”作为旨在防止不当得利的衡平救济对于《海外腐败行为法》的施行而言实属一种创新。事实上,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将此种处罚运用于《海外腐败行为法》的执法过程也仅仅是2002 年《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通过后的事情。在将该处罚适用于《海外腐败行为法》的违反者时,证券交易委员会对合法获取的利润与非法获取的利润予以区分(非法获取的利润即通过违反《海外腐败行为法》的行为而获得的利润)。一旦在违法行为与所获利润间成就了因果关系,证券交易委员会可要求违反者放弃其通过违法举动而赚取的相当金额利益(附加算上利息),除非该公司能证明在因果关系链条上存在断裂情形。②See Michael A. Losco, Note: Streamlining the Corruption Defense: A Proposed Framework for FCPA-ICSIDInteraction, 63 Duke Law Journal 1201-1241 (2014).
考虑到《海外腐败行为法》处罚的严厉性,该法授权美国总检察长可向各公司发放非正式的咨询意见书,对商事组织内部的潜在违法行为进行问询。一旦咨询意见书得以通过,也就初步(但可逆转地)肯定了公司的经营未违反《海外腐败行为法》。咨询意见书亦可向公众散发,其结果不具有法律效力且不构成须遵循的先例。2012 年11 月,美国司法部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曾联合发布了一份长达120 页的行动指南,对两大机构强制执行《海外腐败行为法》的“路径与侧重点”予以列明。
(3)美国反腐执法行政协议书
美国司法部对《海外腐败行为法》的执行主要依赖两类法庭外解决协议书:不予起诉协议书和延缓起诉协议书。两者十分相似,均囊括大量的标准要求:承诺合作、承认行为失当、接受罚金、实施公司改革、接受独立监管以及其他处罚等。不同之处在于,不予起诉协议书下,检察官根据公司对协议条款的履行情况可放弃提交起诉文件。而就延缓起诉协议书来说,检察官虽已提交了起诉书,但却同意只要延缓起诉协议的条件得到满足则撤回起诉。不难看出,尽管两类协议书所附的条件可能同样严格,但前者传递的信号显然不如后者严厉。在美国,人们将这两类起诉协议书视为《海外腐败行为法》执法机制中的基本工具。改变《海外腐败行为法》适用的任何建议都必须纳入这两种协议书内。
伴随着反腐执法形式的增多,美国司法部对这两类协议书的运用也更为广泛①1993 年至2002 年期间,美国司法部订立了16 份起诉协议。但自2002 年开始,起诉协议书的数量急剧增长,2007—2010 年,每年均有39 份协议书被提交。2012 年提交的协议书数目为37份。——其中包括不通过法院审理而对刑事案件予以解决的方法。尽管这一法庭外解决方法在短期内可能有利于公司,但其毕竟不能构成先例,因而对公司几乎不能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②美国司法部于1997 年在《美国检察官手册》中首次就延缓起诉协议书的运用制定了行为指南。自此,司法部在《海外腐败行为法》执法中对不予起诉协议书和延缓起诉协议书的运用一直受1999 年至2008 年期间所颁布的四个备忘录系列文件的指引。See Allen R.Brooks, A Corporate Catch-22: How Deferred and Non-Prosecution Agreements Impede the Full Development of the 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 (Note), 7 Journal of Law & Economics & Policy 137-158 (2010).有鉴于此,部分学者对起诉协议书的负面作用进行抨击,认为此类协议书阻碍了《海外腐败行为法》执法框架下的诉讼规则体系的发展。③譬如Allen R. Brooks 指出,美国司法部对不予起诉协议书和延缓起诉协议书的运用已直接影响《海外腐败行为法》下判例法的发展,原因在于相关先例不能诞生于法院之外的争端解决方式……这样的执法政策增加了市场成本,从而导致效率低下。See Allen R.Brooks, A Corporate Catch-22: How Deferred and Non-Prosecution Agreements Impede the Full Development of the 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 (Note), 7 Journal of Law & Economics& Policy 137-158 (2010).
2. 外国投资者接受内国反腐执法处罚后启动ICSID仲裁程序
实际上,无论内国对外国投资者所发起的反腐调查结果如何,都不影响投资者向ICSID 申请仲裁的权利:假若调查结果显示投资者为“清白”,投资者可就东道国的具体行政监管措施依据后者所作的同意仲裁要约而申请投资仲裁;即便反腐调查得出肯定性结论,亦不能阻碍投资者就东道国所造成的损害发起投资仲裁申请(除非投资者与内国反腐机关已达成不递交仲裁的合意)。原因有三:
其一,依据内国行政法领域的“一事不再罚”法律原则,在接受东道国相应反腐处罚后,外国投资者基于东道国其他侵害事实而享有的仲裁请求权不应一概被剥夺。
其二,根据“回复原状”法律原理,投资者的腐败行为自始无效,应使相关方的法律状况回复到腐败发生前的状态(包括东道国官员的受贿应予没收充公——当然,投资者的行贿不能退回)。在实践中,投资者的腐败行为表现为外国投资本身涉嫌腐败或经营投资涉嫌腐败。前一种情形通常发生在外国投资的设立阶段(如通过伪造文书或印章获取东道国市场准入资格等),即外国投资的设立本身为非法。后一种形式表现为外国投资合法成立后,在其具体经营过程中投资者涉嫌腐败(如通过欺诈或行贿获取业务合同等)。投资者在接受了相应反腐处罚后,其法律状态应“回复”至“未违法”状态——就第一种情形而言,事实上可进一步细分为两种次类型:(1)假若外国投资者在进入东道国市场后成功获取了市场准入资格(比如在投资的后续实际运营过程中拿到了真实有效的文件或许可,从而使得先前“通过腐败行为设立的外国投资”成为了“形式上真正合法的外国投资”),外国投资者自然作为“合格投资者”享有仲裁申请权利。(2)外国投资自始至终不符合东道国法律所规定的“外资准入条件”。对于这些“真正不适格”的外国投资,依然有望受到国际法律框架①应该注意到,《ICSID 公约》的全名为《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投资争端公约》,该公约的名称中并未使用“投资者”的概念。事实上,外国“投资者”可依据相关双边投资条约以“他国国民”身份寻求提起国际投资仲裁申请。与内国法②针对“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贿赂单位或者个人,以谋取交易机会或者竞争优势”的外国投资者,1993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下称《反不正当竞争法》)并未作出“吊销执照”的法律规定。但2017年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9条规定:“经营者违反本法第七条规定贿赂他人的,由监督检查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处十万元以上三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对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生效前所做的中国境内外国投资,其“外国投资者(或投资)”的身份根据“不溯及既往”法律原则不能被剥夺——因为外国投资虽然从事了腐败行为,但其经营执照并未被吊销。的保护。更何况,基于“禁止反言”法律原则,东道国必须就其先前已给外国投资者颁发了市场准入许可的事实承担责任(特别是负责审核市场准入事项的东道国政府官员在收受了贿赂后“心知肚明地忽视”投资者的不合法行为,最终还是提供了市场准入许可③See Fraport AG Frankfurt Airport Servs. Worldwide, ICSID Case No.ARB/03/25,Award, p.346.)。而在第二种情形下,外国投资者在履行了东道国内国反腐执法机关所施加的惩罚后,其“合格投资者”的身份应回复至正常。
其三,依照内国反腐法律规范,外国投资者的腐败行为如果触犯刑律,刑罚形式一般为“有期徒刑”或“并处罚金”,并不必然遭致被“没收财产”。④如我国《刑法》第390 条规定:“对犯行贿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因行贿谋取不正当利益,情节严重的,或者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或者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东道国不能借口外国投资者涉嫌腐败犯罪即对其财产施以等同于“没收财产”的征收或类似征收措施。投资者的相关投资仲裁请求权理应得到保护。
四、结论
面对东道国会更热衷于将腐败抗辩作为一项挫败投资者诉请的应诉策略(乃至技巧)加以运用的现实(投资仲裁庭的仲裁法理“漏洞”与拒绝行使管辖权的“错误决定”难辞其咎),投资仲裁庭正遭遇腐败抗辩范围扩大与涉腐案件数量增加的双重压力。伴随着世界范围内国际经贸反腐专门条约与腐败治理条款的发展,以美国《海外腐败行为法》为代表的打击国际投资腐败行为的内国强制执行法的数量亦呈现大幅增长的态势。鉴于国际投资仲裁庭在反腐调查职权方面的先天不足,现行仲裁庭证据采纳标准不明确亦饱受诟病,再加上诸如2007 年Siemens AG仲裁案事后被证实为错误裁判的个案事件的发生,以ICSID 为首的国际投资仲裁机构在应对涉腐国际投资争端案件时表现得较为被动。构建ICSID 与内国执法机关间的反腐协作机制无疑对于目前投资仲裁庭所面临的反腐困境解决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ICSID与内国执法机关间反腐协作机制的构建是跨国投资国际合作反腐法治的必然结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为创设内国反腐执法机关与ICSID 等国际组织间的反腐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机制提供了国内法依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