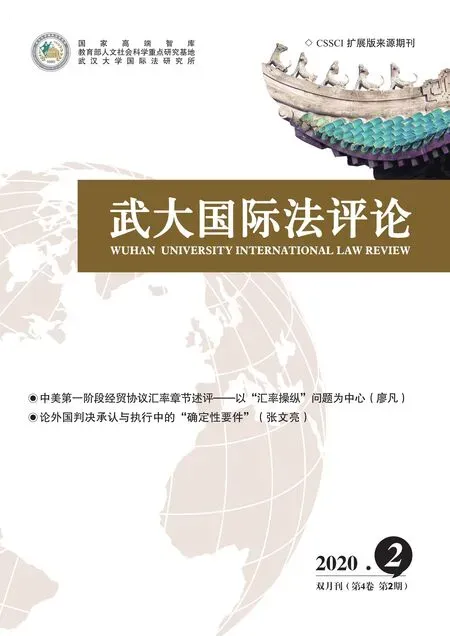论外国判决承认与执行中的“确定性要件”
张文亮
一、引言
任何判决都具有一定的状态;根据判决作出地法律,某一判决所处的状态可能是“最终的”、“再审中的”或“临时的”,抑或是“可执行的”,甚或是“处于上诉中的”或“存在上诉可能性的”等。通常来说,一国判决若要发生其国内法所规定的完全效力,其必须具有“确定性”状态。类似地,在外国判决的承认与执行语境下,被请求国亦通常要求外国判决应具备适宜的状态——“确定性”或“适宜”外国判决。①对于外国判决寻求承认与执行时应具有的确定状态,冯麦伦教授用“适宜”(ripeness)来概括。See A. T. von Mehren,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Foreign Judgments-General Theory and the Role of Jurisdictional Requirements, 167 Collected Courses of the Hague 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Law 47-49 (1980).我国学者多采取“终局性”来表述“确定性要件”,如乔雄兵:《论外国法院判决承认与执行中的终局性问题》,《武大国际法评论》2017年第1期,第76页等。对外国判决已经“确定”或“适宜”的要求便是外国判决承认与执行中的“确定性要件”。具体来说,外国判决的“确定性要件”是指由被请求国的国内法或有关国际性法律文件所规定的,外国判决寻求承认与执行时应具有“适宜”的拘束力或确定性状态,该要件旨在确保已被承认或执行的外国判决不因其状态在原审国之变化而被撤销承认以及执行回转。
虽然“确定性要件”是外国判决承认与执行的普遍条件,但是在没有条约保障的情形下,各国通常诉诸其自有的“确定性要件”判断外国判决的状态且彼此之间对该要件尚不存在一致性表述及理解,②常见的表述方式有:外国判决是“最终的”(final),“最终的和确凿的”(final and conclusive)以及“可执行的”(enforceable)等。参见下文第二部分“确定性要件”的国别差异及协调。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国家间判决的承认与执行。不仅如此,围绕“确定性要件”产生的国别差异亦为当事人滥用相关诉讼机制创造了空间,比如利用“确定性要件”的国别差异,通过上诉或再审,破坏判决的确定性,阻碍判决在域外承认与执行。总而言之,外国判决的“确定性要件”深刻影响着判决承认与执行,是一项充满诉讼策略的关键问题,其因此成为国际社会在协调或统一外国判决承认与执行中关注的重要事项。③参见下文二(三)“确定性要件”的协调或统一。本文意在从“确定性要件”的国别实践出发,梳理其中的问题并剖析国际社会围绕该要件的主流协调或统一方案,进而评析我国的相关立法和实践并提出若干完善建议。
二、“确定性要件”的国别差异及协调
从比较法的视角来看,各国内法或有关的国际性法律文件虽然大多明确规定了“确定性要件”,但是在该要件的表达及内涵等方面均存在显著不同,尤其是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对该要件的理解极为不同。一方面,不同法系之间对“确定性要件”的规定差异较大;另一方面,同一法系内不同国家之间对该要件的规定亦存在或大或小的差异。这种差异的存在充分地体现在相关国际组织就该要件的协调或统一之中,而相关国际组织折中方案的采纳即是对该差异性的回应和弥合。
(一)大陆法系的代表性国家
《瑞士关于国际私法的联邦法》第25 条规定:“某一外国裁判将在瑞士获得承认:a.……b.如果不存在针对该裁判的普通司法救济或该裁判是最终的;c.……”该条款仅对外国判决承认中的“确定性要件”作了规定;不过在有关执行外国判决的章节中,该法典第28 条又明确指出,“依据第25 条至第27 条予以承认的裁判,应有关利害当事人申请将被声明可予执行。”据此,外国判决的执行须以承认为前提,且应满足相同的“确定性要件”:不存在针对外国判决的“普通司法救济”或该裁定是“最终的”。“普通的司法救济”或是“最终的”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同义反复。作为规定外国判决“确定性要件”的另一替代性根据,术语“最终的”包含了术语“不再受制于普通的司法救济”所未包含的含义。透过该法典的立法历史可知,采纳术语——“最终的”是为了将那些不再受普通的司法救济约束的裁定也纳入到外国判决“确定性要件”的考虑范围之内。①See Adrian U. Dorig, The Finality of U.S. Judgments in Civil Matters as a Prerequisite for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in Switzerland, 32 Texas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271, 280 (1997).具体来说,当提起上诉或其他司法救济的期间已过且未提起上诉或其他救济,或不允许上诉或其他司法救济机制时,在瑞士寻求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意义上的“确定性要件”方可满足。②See Martin Bernet & Nicolas C. Ulmer,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Foreign Civil Judgments in Switzerland, 27 The International Lawyer 317 (1993).对于不恰当送达是否影响普通救济的起算时间问题,瑞士联邦法院在一起承认和执行美国判决的案件中裁定③Judgment of 18 December 1990, BGE 116 II 625, 630-1.认为,在裁判地法院并不要求判决予以送达的情形下,判决送达的缺失并不能阻止执行。④Martin Bernet & Nicolas C. Ulmer,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Foreign Civil Judgments in Switzerland, 27 The International Lawyer 325 (1993).当外国程序法载明了特殊救济措施必须实施的期间时,外国判决的“确定性要件”不能成立。作为执行外国判决时的一般原则,瑞士法院仅仅在特殊的救济措施并不存在某一法定的行使期间时才会忽略这些特殊救济措施。⑤See Martin Bernet & Nicolas C. Ulmer,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Foreign Civil Judgments in Switzerland, 27 The International Lawyer 317 (1993).
依据《德国民事诉讼法》,若外国法院判决依据适用于该法院的法律尚未最终且确凿,(德国法院)不会对该判决予以执行。⑥See The German Code of Civil Procedure (ZPO), §723.对于外国判决的承认,《德国民事诉讼法》并没有明确规定“确定性要件”;相反,其仅仅规定了不予承认外国判决的理由,但其中并不包括外国判决欠缺“确定性”。⑦See The German Code of Civil Procedure (ZPO), §328.不过,德国主流学者认为,针对外国判决执行所规定的“确定性要件”通常亦应延伸至外国判决的承认。⑧See Dieter Martiny,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Foreign Judgments in Germany and Europe, in Jürgen Basedow, Harald Baum & Yuko Nishitani, Mohr Siebeck, Japanese and Europea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391 (Tübingen 2008).据此,外国判决若要在德国承认与执行,其应“最终且确凿”。“最终且确凿”,意指判决不再受制于通常形式的上诉或审查。而对于案件在原审国独立的诉讼程序中被重新审理的可能性并不能阻止判决的承认。①See Dieter Martiny,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Foreign Judgments in Germany and Europe, in Jürgen Basedow, Harald Baum & Yuko Nishitani, Mohr Siebeck, Japanese and Europea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391 (Tübingen 2008).诸如抚养裁判,尽管其通常会因情形的变化而被变更,但这不影响该类裁判的确定性。②W. Wurmnest,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U.S. Money Judgments in Germany, 23 Berkele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83-184 (2005).对于外国判决是否“最终且确凿”,其判断依据在于原审国法律,对此,《德国民事诉讼法》予以明确规定③See The German Code of Civil Procedure (ZPO), §723.。在一起承认与执行美国判决的案件中,德国最高法院认可美国法院作出的其判决未被上诉或撤销的证明,并裁断美国判决“最终且确凿”。④Judgment of the Bundesgerichtshof, IXth Civil Senate, of 4 June 1992, Docket No.IXZR 149/91[1992]. See also Peter Hay,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American Money Judgments in Germany-The 1992 Decision of the German Supreme Court, 40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729 (1992); Joachim Zekoll, The Enforceability of American Money Judgments Abroad: A Landmark Decision by the German Federal Court of Justice, 30 Columbia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Law 645 (1992).
对于外国判决的“确定性”,法国一直以来都持甚为宽松的态度。在1964 年之前,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法国不会承认在原审国不是“可执行的”外国判决。但是,不同于很多大陆法系国家将外国判决的承认与执行限定在外国判决不再受制于普通上诉程序的情形,法国法院采取了更为宽松的立场,其在外国判决的上诉程序尚未结束时仍承认外国判决。除此之外,法国法院也愿意承认临时或中间裁决。⑤See J. K. Grodecki, Enforcement of Foreign Maintenance Orders: French and English Practice, 8 The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32-33 (1959).从目前来看,外国判决若要获得承认与执行,其没有必要是“最终的”;通常意义上来说,“确定性要件”并不是外国判决获得承认与执行的前提条件。⑥法国最高法院确立了外国判决在法国寻求承认与执行须满足的五个要件:原审法院有管辖权;外国法院所遵循的程序是充分的;外国法院适用了法国法所指引的法律;符合法国公共政策;不存在与另一判决或未决的法国诉讼程序相冲突的情形。See Norel Rosner, Cross-border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Foreign Money Judgments in Civil and Commercial Matters, 2004, pp.230-231; Paul Hopkins, International Enforcement of Foreign Judgments 194 (Yorkhill Law Publishing 2006).若要在法国获得执行,外国判决只需要在原审国是“可执行的”即可。⑦See Norel Rosner, Cross-border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Foreign Money Judgments in Civil and Commercial Matters, 2004, p.254.
综上,代表性大陆法系国家均保留了外国判决承认与执行中的“确定性要件”,但是它们在这一要件的表述上仍存在着一定差异。如前所述,大陆法系国家对“确定性要件”的表述主要有:“不存在普通的司法救济”“最终的”“最终且确凿”“可执行的”。一方面,尽管“确定性要件”在大陆法系国家立法中存在不同的表述,然而该要件的内涵却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即它们均要求通常形式的救济机制已经用尽,而不管该救济机制是来自原审法院还是上诉法院。尤为突出的一点是,上诉可能性的存在或悬而未决的上诉都会使得判决的“确定性要件”不能满足。①See Volker Behr, Enforcement of United States Money Judgments in Germany,13 Journal of Law and Commerce 218 (1994).另一方面,“确定性要件”本身是由被请求承认与执行国法律所规定的外国判决寻求承认与执行的前提条件之一;依据大陆法系主要国家的立法及司法实践,对于外国判决是否满足该要件,则要根据原审国有关法律来判断其判决是否符合被请求承认与执行国的“确定性要件”。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大陆法系国家如法国、荷兰、比利时等国,在外国判决的“确定性要件”上的态度甚为宽松;其并非要求外国判决具备其他国家通常要求的“确定性要件”,而只是强调外国判决在原审国是“可执行的”即可,这与欧盟在外国判决承认与执行中“确定性要件”的立场一致。
(二)英美法系的代表性国家
在英国,若要使得某一外国判决成立普通法上的有效诉由,该判决必须是“最终的和确凿的”,即当事人之间的所有争议已经裁断。②See James Fawcett, Janeen Carruthers & Peter North, Cheshire, North & Fawcett: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536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在这里,术语“最终的和确凿的”是同义反复,③See Lawrence Collins, Dicey & Morris on the Conflict of Laws 476 (Sweet &Maxwell 2000).即该要件指的是外国判决是最终的裁断。在早期有关该要件的最具代表性案件Nouvion v. Freeman④See Nouvion v. Freeman, [1889] 15 APP Cas 1.中,英国上诉法院作出判决认为:西班牙法院Remate 判决不能确立英国普通法上的有效诉由。上议院维持了英国上诉法院的这一判决。Remate 判决是在简易程序中作出的;在该程序下,当事人的主张尤其是被告的抗辩事由并不能完全提出;更为重要的是,该判决的存在并不影响当事人就其争议另行提起完整诉讼,而且该完整诉讼的提起完全不受Remate 判决的影响,相反,Remate 判决却因相应的完整诉讼的提起而不再具有拘束力。故Remate 判决对于当事人的任何一方来说均非已决事项,也没有消除原始诉由。⑤See Nouvion v. Freeman, [1889] 15 APP Cas 1.在Blohn v. Desser 案⑥See Blohn v. Desser [1962] 2 Q.B. 116.中,奥地利法院作出了一项针对某一公司A 的判决,Blohn请求英国法院执行案外人Desser 的财产。根据奥地利法,该判决对案外人Desser具有拘束力,但需要另行提起针对该案外人的诉讼;不过,案外人Desser在另行提起的诉讼中可主张针对公司A案中未提出的抗辩。因此,虽然奥地利判决可以视为针对Desser的判决,但是该判决不具有终局性。①See Paul Torremans (ed.), Cheshire, North & Fawcett: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1081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英国普通法对外国判决所要求的“确定性要件”并非指已不存在针对该判决的上诉权利。外国判决可能会在上诉中被推翻的事实,以及在原审国正在进行的针对该判决的上诉这一更为有力的事实均不能成为在英国提起承认与执行之诉的障碍。②See James Fawcett, Janeen Carruthers & Peter North, Cheshire, North & Fawcett,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538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不过,如果存在悬而未决的上诉,英国法院通常会依据衡平法上的管辖权中止对该判决内容的执行。此外,很重要的一点是,如果依据外国法该悬而未决的上诉将发生中止该判决执行的效力,该判决似乎在英国是不可诉的。③See James Fawcett, Janeen Carruthers & Peter North, Cheshire, North & Fawcett,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538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在美国,尽管外国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属于州法事项,大多数州在制定有关外国判决的承认与执行时依循了全国统一州法委员会会议1962 年通过的《统一外国金钱判决承认法》。④已有31 个州已经采纳了该法。See Nellie Veronika Binder, Making Foreign Judgment Law Great Again: The Aftermath of Chevron v. Donziger, 51 Suffolk University Law Review 42 (2018).该法第二节载明了寻求承认与执行的外国判决应具有的“确定性要件”,即“该法适用于在原审国是‘最终的、确凿的且具有执行力的’外国判决,尽管存在针对该判决的悬而未决的上诉或该判决的上诉期未满。”美国《第四次对外关系法重述》因循了“最终的、确凿的且具有执行力的”这些“确定性要件”,并指出判断标准是外国判决作出地法律,上诉可能性之存在并不必然影响外国判决的确定性。⑤See Restatement 4th of the Foreign Relations Law of the U.S., §481.另外,在全国统一州法委员会于2005 年讨论通过的《统一外国金钱判决承认法》中,对外国判决的“确定性要件”规定如下:“根据原审国法律,外国判决是‘最终的、确凿的且具有执行力的’”。⑥See Uniform Foreign-Country Money Judgments Recognition Act, Section 3 (a)(2).
可见,美国法律对外国判决的“确定性要件”表述为:“外国判决应是‘最终的、确凿的且具有执行力的’”。这里的“最终的”和“确凿的”是一种同义反复。对于“最终的”含义,《第三次对外关系法重述》曾在其评注中定义为:“最终的”判决是指在原审法院不再受制于除了执行程序以外的额外程序拘束的判决。在决定某一判决是否为承认与执行意义上“最终的”判决时,美国法院通常会依据原审国的法律。①See American Law Institute, Restatement of the Law, 4th, Foreign Relations Law of the United States: : Jurisdiction, Sovereign Immunity, and Treaties, 2018, p.438.另外,即使仍然存在针对外国判决的上诉可能性或上诉悬而未决,该外国判决也被认为是“最终的”。至少有一个美国州法院,其在外国判决被撤销之后拒绝重新考虑其已经作出了承认判决的案件。②See DSQ Property Co., Ltd., Plaintiff, v. John Z. DeLorean, Defendant, 1990 U.S. Dist. LEXIS 11880.在该案件中,英国法院撤销了其作出的但已经被美国密歇根法院承认的判决;但美国拒绝就该判决的承认问题再行考虑。另外,至少有一个美国法院主张:仍然受制于原审国法院更改的判决也不缺乏“最终性”,只要请求执行的部分为该外国判决已经积累的数额部分。③See Coulborn et al. v. Joseph, 1943 Ga. LEXIS 284. Cf. Ronald A. Brand, Enforcement of Foreign Money-Judgm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Search of Uniformity and International Acceptance, 67 Notre Dame Law Review 253, 270 (1991).不仅如此,美国法院给予缺席判决与对席判决以同样的法律效力;④See Restatement 3d of the Foreign Relations Law of the U.S., §481. Cf. Voileta I. Balan,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Foreign Judgm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Need for Federal Legislation, 37 The John Marshall Law Review 229, 248-249 (2003).也就是说,判决的“确定性”并不因判决是被告缺席情形下作出而受影响。与英国的做法一致,若上诉期间尚未经过或上诉悬而未决,美国法院也可以中止判决的承认与执行程序。
英美法系国家在外国判决“确定性要件”上的表述相对一致;它们所采用的术语主要是“最终的、确凿的”以及“最终的、确凿的且具有执行力的”。然而,相较于大陆法系国家对外国判决“确定性要件”所赋予的内涵,英美法系国家对外国判决“确定性要件”的理解要复杂得多。从一般意义上来讲,英美法系主要国家对外国判决“确定性要件”的理解为原审法院已经就案件的所有争议事项予以裁决,当事人不可能在原审法院寻求针对该裁决的新的普通程序;对于上诉或其他的救济措施并不能否定外国判决的“确定性”。英美法系国家在评断外国判决是否符合其所规定的“确定性要件”时的做法和大陆法系国家的做法一致:根据原审国的有关法律予以判断,而上诉状态的存在会使被请求法院中止外国判决的承认与执行程序。但是在英美法系国家,外国判决“确定性要件”内涵的确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有关判例;尤其是在英国,对该要件的理解必须借助于复杂的案例体系,这增加了适用该要件的困难与不确定性。同时,英美法系国家或地区在评判外国判决的确定性时也受其本身对“确定性”理解的影响,
(三)“确定性要件”的协调或统一
“确定性要件”标准的差异导致判决承认与执行要件的不一致,影响或阻碍外国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因此,围绕该要件的国家间协调或统一具有突出价值。各国“确定性要件”国内法机制存在诸多差异,因此国际组织的协调或统一便显得十分必要,而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和欧盟在该领域的实践最具代表性。
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在1971 年通过的《外国民商事判决承认与执行公约》(以下称“1971 年公约”)将外国判决的“确定性要件”明确规定为判决在缔约国之间承认与执行的前提条件之一:外国判决“不再受制于原审国普通形式的审查”;如果要使外国判决在被请求国是“可执行的”,其必须在原审国是“可执行的”。①See HCCH, Convention of 1 February 1971 on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Foreign Judgments in Civil and Commercial Matters, Article 4(2).1971 年公约未能得到广泛接受,亦未得以签署适用。②Ronald A. Brand & Paul M. Herrup, The 2005 Hague Convention on Choice of Court Agreements Chapter 1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Ronald A. Br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Electronic Commerce and the Preliminary Draft Hague Jurisdiction and Judgments Convention, 62 Universityof Pittsburgh Law Review 582 (2001).因而,该公约的“确定性要件”方案未能成为普遍标准。1992 年海牙判决计划重启之后,构架为各国认可的国际公约再次提上议程。1999 年《外国民商事判决承认与执行临时草案公约》(以下称“1999 年草案公约”)③See https://www.hcch.net/en/projects/legislative-projects/judgments/preparation-of-a-pr eliminary-draft-convention-1997-1999-,visited on 9 August 2019.规定,“要获得承认……判决须在原审国具有既判力(res judicata)”“……判决在原审国须具有执行力。”然而,“如果判决在原审国处于审查之中或寻求该审查的时效未过,可以暂停承认或执行”。④Preliminary Draft Outline to Assist in the Preparation of a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Jurisdiction and the Effects of Foreign Judgments in Civil and Commercial Matters, Article 25(2)-(4).1999 年草案公约未能为各国接受,因此其确立的“确定性要件”规则亦未被确立为普遍标准。
作为海牙判决计划的一项“小公约”,海牙国际私法会议2005 年通过的《选择法院协议公约》(以下称“2005 年公约”)规定:只要判决在原审国“具有效力”,其应被承认;只要判决在原审国是“可执行的”,其应被执行。⑤See HCCH, Convention of 30 June 2005 on Choice of Court Agreements, Article 8(3).海牙国际私法会议2019 年公约采取的立场与2005 年《选择法院协议公约》一致。⑥See HCCH, Convention of 2 July 2019 on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Foreign Judgements in Civil Commercial Matters, Article 4(3).从历史发展来看,在协调外国判决承认与执行中的“确定性要件”问题上,海牙国际私法会议自1971 年公约以来的立场并非完全一致,而其当前采纳的立场亦未沿袭大陆法系或英美法系常用的表述,如“最终的”或“最终的和确凿的”,亦未因循其传统的关于判断判决确定性的标准——“不再受制于原审国普通形式的审查”或“既判力”等;而是采用了“具有效力”以及“可执行的”等一般性概念。这一最新立场已经偏离了海牙国际私法会议的传统立场,亦不同于大陆法系或英美法系关于“确定性要件”之规定。应当说,传统的“不再受制于原审国普通形式的审查”与大陆法系在外国判决承认与执行问题上所规定的“确定性要件”内涵有着诸多重合之处,因为它们都将判决的“确定性”聚焦于原审国是否存在针对该判决的普通救济,即上诉程序;但是其与英美法所规定的“确定性要件”的内涵相差较远,因为英美法系判决“确定性要件”主要侧重于原审法院已经解决了案件的所有纠纷,这也解释了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在其晚近的公约中,放弃了其传统的“确定性要件”,引入更为开放、中立且具有包容性的标准。
一些区域性国际公约或文件在外国判决承认和执行的“确定性要件”方面有着不同的规定和立场,最具代表性的是欧盟布鲁塞尔判决体系的相关实践。1968年《布鲁塞尔公约》①See EC, The 1968 Brussels Convention on Jurisdiction and the Enforcement of Judgments in Civil and Commercial Matters, Offical Journal of European Union C27,26.1.1998, Article 31.、取代该公约的2001 年《布鲁塞尔条例I》②See EC,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44/2001 of 22 December 2000 on Jurisdiction and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Judgments in Civil and Commercial Matters,Offical Journal of European Union L12, 16.1.2001, Article 38.以及最新修订的《布鲁塞尔条例Ⅱ》③EU, Regulation (EU) No.1215/2012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12 December 2012 on Jurisdiction and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Judgments in Civil and Commercial Matters (Recast), Offical Journalof European Union L 351/1, 20.12.2012, Article 39.等构架起布鲁塞尔判决体系,其在外国判决“确定性要件”的规定和立场一致。该体系区分外国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判决的承认无须满足任何“确定性要件”,这主要是考虑到在临时救济以及单方诉讼等程序中作出的判决仍需要承认,尽管该类判决并不总是具有既判力等确定性。④See P. Jenard, Report on the Convention on Jurisdiction and the Enforcement of Judgments in Civil and Commercial Matters,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5.3.79, No.C 59/43.值得特别提及的是,欧盟2013 年《关于相互承认民事保护措施的条例》统一了欧盟内临时救济在特定领域的承认和执行规则。⑤EU, Regulation (EU) No.606/2013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12 June 2013 on Mutual Recognition of Protection Measures in Civil Matters,Offical Journal of European Union, L181/4, 29.6.2013.这样以来,可被承认的判决既包括全部或部分裁决,也包括受到上诉或其他挑战以及仅仅具有临时可执行性的裁决、中间裁决等。⑥See Peter Mankowski & Ulrich Magnus, Brussels I Regulation 627 ( Sellier European Law Publishers 2012).尽管布鲁塞尔判决体系并未对判决的承认引入明确、一致的“确定性要件”,然而其赋予被请求国在外国判决处于普通上诉状态时可以暂缓承认的权力。⑦See, e.g., the 1968 Brussels Convention, Article 30; Brussels I Regulation, Articles 37 & 46 and Brussels I Regulation Recast, Articles 36 & 39.对于判决的执行来说,相关判决在原审国应为“可执行的”。⑧See 1968 Brussels Convention, Articles 26 and 31; Brussels I Regulation, Articles 33 and 38.此外,1988 年《卢加诺公约》和2007 年新《卢加诺公约》①EU, Convention on Jurisdiction and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Judgments in Civil and Commercial Matters, Offical Journal of European Union L339,21.12.2007, pp.3-41.在外国判决的“确定性要件”方面采取了与布鲁塞尔判决体系同样的立场。除布鲁塞尔判决体系之外,1928 年《布斯塔曼特法典》中,外国判决的“确定性要件”也被规定为“可执行的”。②参见《布斯塔曼特法典》第423(4)条。
这些区域性的国际公约或文件旨在最大程度地在可容许的范围内简化判决的承认与执行条件,减少拒绝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的理由;而降低外国判决“确定性要件”的门槛是加速判决流动的重要途径之一,同时也有助于防止被申请人蓄意破坏外国判决的承认与执行进程。因此,上述区域性判决公约或文件在“确定性要件”方面的规定较为宽松,布鲁塞尔判决体系下诸公约或条例甚至在判决的承认方面并不引入“确定性要件”。另外,无论是2001 年《布鲁塞尔条例I》(包括其修改版)还是1988 年的《卢加诺公约》,其调整范围均包含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之间判决的承认与执行问题;因此,两大法系在外国判决“确定性要件”方面的不同是可以弥合的,或者说存在可以公共认可的标准。术语“可执行的”作为判决的“确定性要件”得到了广泛的采用,而这更多的是针对外国判决的执行而非承认本身引入的“确定性要件”。
三、海牙判决公约体系的方案
前文已经述及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在其1971 年公约中引入的有关“确定性要件”的立场,并梳理、阐释了海牙国际私法会议重启海牙判决计划后的诸项公约或草案公约中关于“确定性要件”的相关规定和历史沿袭。本部分主要围绕海牙判决计划下的2005 年公约与2019 年公约,就海牙国际私法会议晚近以来的基本立场予以阐释,剖析这一主流国际组织在协调或统一国家间判决承认与执行的“确定性要件”中的态度及历史演变,并就其立场予以评析。这两项公约是海牙国际私法会议1992 年启动“海牙判决计划”以来最为重要的成果,该公约有关“确定性要件”的规则代表着海牙国际私法会议成员国的共识。
(一)2005年《选择法院协议公约》
2005 年公约调整排他性选择法院协议基础之上的外国判决承认与执行,在“确定性要件”方面,其要求“外国判决在原审国具有效力,且只有当该判决在原审国具有执行力时方可获得执行”。③See HCCH, Convention of 30 June 2005 on Choice of Court Agreements, Article 8(3).具体来说,“具有效力”指的是所涉外国判决“合法有效”且处于生效之中。①See Trevor Hartley & Masato Dogauchi, Explanatory Report on the 2005 Hague Choice of Court Agreements Convention (Hartley/Dogauchi Report), para.171.在该公约的起草过程中,曾存在较大争议,因考虑到各国的差异性规定,故采行该立场。②参见何其生:《中国加入海牙〈选择法院协议公约〉的规则差异与考量》,《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4 期,第84 页;乔雄兵:《论外国法院判决承认与执行中的终局性问题》,《武大国际法评论》2017 年第1 期,第76 页;王吉文:《判决终局性:外国判决承认与执行上一道难以逾越的坎》,《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11年第4期,第141页。该公约考虑到不同法系或国家在“确定性要件”中的不同立场,在“确定性要件”的规定中诉诸“具有效力”和“执行力”等更为中性的表达,以求摒除该要件解释可能产生的困难。
值得注意的是,该公约对“确定性要件”的规定区分外国判决的“承认”与“执行”;“承认”意味着赋予外国法院作出的权利和义务裁断以效力,而执行则意味着被请求法院通过采取措施强迫被告遵守原审法院的判决。依据该公约,承认和执行须满足的“确定性要件”并不一致,即前者要求“发生效力”,而后者需要“具有执行力”。鉴于执行通常须以承认为前提,③See Trevor Hartley & Masato Dogauchi, Explanatory Report on the 2005 Hague Choice of Court Agreements Convention (Hartley/Dogauchi Report), para.170.故具有“执行力”的外国判决亦应“发生效力”。在外国判决确定性的法律适用标准方面,2005 年公约指明:判断判决是否“具有效力”或“执行力”的标准在于原审国法律,而非被请求国法律。④See HCCH, Convention of 30 June 2005 on Choice of Court Agreements, Article 8(3).该公约区分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并规定不同的“确定性要件”,判决的执行之“执行力”要件等均与布鲁塞尔判决体系中的“确定性要件”一致,亦表明该公约的“确定性要件”受欧盟实践的影响较大。
对于在原审国发生效力与具有执行力的外国判决,如果该判决尚处于某种特殊状态之下,被请求国可以暂缓承认与执行或附条件地不予承认与执行。具体来说,若外国判决在原审国尚处于审查之中,或寻求“普通审查”的时限未过,那么对该外国判决的承认或执行可予推延或拒绝;然而,该类情形下的拒绝承认或执行不阻碍后续判决承认与执行的再次申请,⑤See HCCH, Convention of 30 June 2005 on Choice of Court Agreements, Article 8(4).且不应对后续申请形成偏见。⑥See Trevor Hartley & Masato Dogauchi, Explanatory Report on the 2005 Hague Choice of Court Agreements Convention (Hartley/Dogauchi Report), para.174.对那些在原审国尚处于审查之中或“普通审查”期限未过的外国判决,被请求国虽无义务但可以承认或执行该类判决,或者要求申请人提供担保。⑦See Trevor Hartley & Masato Dogauchi, Explanatory Report on the 2005 Hague Choice of Court Agreements Convention (Hartley/Dogauchi Report), para.173.这是2005 年公约在引入“确定性”要件的同时,设置有利于外国判决承认和执行的矫正机制,以软化“确定性要件”的适用。基于此,2005 年公约在形式上提供了较为明确的“确定性要件”标准,并在实质上引入了灵活的、有利于外国判决有效承认、执行的规则和矫正机制,是一种折中、值得肯定的“确定性要件”构建路径。
(二)2019年《承认与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公约》
2019 年公约确立了广泛领域的民商事判决承认与执行原则,①See HCCH, Convention of 30 June 2005 on Choice of Court Agreements, Article 4.其在“确定性要件”上的规范完全因袭了2005 年公约的做法。在原审国“具有效力”的判决应予承认,且在原审国具有“执行力”时方可在被请求国执行。公约区分“承认”和“执行”,分别规定不同的“确定性要件”。同样地,在对“确定性要件”的界定上,2019 年公约亦回避了因循大陆法系或英美法系对“确定性要件”的惯常界定,而是在对两大法系“确定性要件”予以折中考虑后作出选择。此外,《公约草案临时解释报告》(以下称“解释报告”)将“具有效力”解释为:合法有效且处于生效之中。②See Francisco J. Alférez,F. Garcimartín & Geneviève Saumier, Judgments Convention: Revised Preliminary Explanatory Report 2018, para.102.在“确定性要件”的判断标准上,判断判决是否“具有效力”的标准在于原审国法律,而非被请求国法律。③See HCCH, Convention of 2 July 2019 on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Foreign Judgements in Civil Commercial Matters, Article 4(3).
2019 年公约充分考虑到不同法系对判决确定性的不同认识,尤其是关于外国判决既判力与执行力的不同理解,并完全因循了2005 年公约有关“确定性要件”的矫正机制。有鉴于此,对于即使满足“确定性要件”的判决,被请求国仍可根据外国判决的特殊状态采取不同的措施:如果具备公约“确定性要件”的外国判决在原审国处于被审查状态,或寻求“普通”审查的时限未过,被请求法院可以承认或执行,或推迟承认或执行,或拒绝承认或执行,但这并不影响后续重新提请承认或执行。对于核心概念——“普通审查”与“特别审查”之区分,解释报告着重考虑相关审查是否为正常诉讼程序的一部分、是否为当事人所合理预见以及是否受到合理的时限期间所限制。④See Francisco J. Alférez,F. Garcimartín & Geneviève Saumier, Judgments Convention: Revised Preliminary Explanatory Report 2018, paras.106-112.
(三)方案的优点与不足
海牙判决公约体系“确定性要件”的现行方案充分考虑到不同国家、法系在“确定性要件”上的差异性,借鉴了海牙国际私法会议的传统经验与欧盟在该方面的有益实践,其协调或统一之努力成为各国合作的重要起点,可成为各国广泛接受的基本方案。其在形式上引入了较为明晰的“确定性要件”,区分判决的“承认”和“执行”,并在实质上确立了有利于认定外国判决具备确定性的标准和矫正机制,从而有利于增进国家间判决的承认与执行,这符合外国判决承认与执行的总体趋势。
然而,海牙判决公约体系的现行方案就“确定性要件”方面的规定仍然存在一些不甚清晰的方面。比如,其应进一步明确判断外国判决是否“具有效力”的依据在于原审国法律,厘清其与被请求国标准的界限;海牙判决公约的现行方案尚未触及被承认的外国判决在被请求国将产生何种效力,已属“确定的”外国判决被承认后将在被请求国产生的效力范围等问题亦应澄清。此外,由于各国围绕判决的确定性进行“普通审查”①See HCCH, Convention of 30 June 2005 on Choice of Court Agreements, Article 8(4).的类型及范围各异,各国提交其国内法中符合公约目的的“普通审查”清单,可避免适用该公约的过程中产生的诸多分歧,且将来相关公约解释报告亦可对“普通审查”作进一步阐释和界定。而对于“具有效力”的各国判决的范围,亦应成为海牙判决公约体系应解决的重要事项。
四、我国立法及司法实践
(一)立法概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称《民事诉讼法》),外国判决要在我国承认与执行,其应“发生法律效力”,②参见2017 年《民事诉讼法》第265 条。虽然《民事诉讼法》在2017 年被修订,但是有关外国判决的承认与执行条款没有任何改动。因此,对于外国判决的“确定性要件”来说,“发生法律效力”这一术语从《民事诉讼法》1991年颁行至今仍延续适用。该表述在形式上类似于海牙判决公约体系中的“产生效力”之标准。在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语境下,“发生法律效力”指的是判决已经产生了拘束力、确定力以及执行力。具体来说,下列判决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以及依法不准上诉或者超过上诉期没有上诉的判决、裁定。③参见2017年《民事诉讼法》第155条。然而,对于依据哪一国法律确定外国判决是否“发生法律效力”,我国《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民事诉讼法》中的“确定性要件”未区分外国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因此该要件同等适用于外国判决在我国的“承认”和“执行”。
除《民事诉讼法》外,《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等法律规范④参见乔雄兵:《论外国法院判决承认与执行中的终局性问题》,《武大国际法评论》2017年第1期,第78-79页。亦规定了特殊类型的外国判决,如破产判决在我国寻求承认与执行时的“确定性要件”即是“发生法律效力”。⑤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5条。对于外国离婚判决的承认与执行,我国法律规定的“确定性要件”也是“发生法律效力”。⑥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国公民申请承认外国法院离婚判决程序问题的规定》第12(1)条。总的来看,我国法律中的“确定性要件”是外国判决“发生法律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民商事判决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稿)》在“确定性要件”的表述上亦采用了“发生法律效力”之表述。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民商事判决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稿)》第15(3)条。对于“确定性要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称《民诉法解释》)要求申请人提交申请书,并附外国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②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543条。但是对于何为“发生法律效力”并无相关解释。
在我国与诸多国家所缔结的双边司法协助条约③我国已缔结39项中外民商事双边司法协助协定,37项已经生效。关于中外民商事司法协助条约缔约情况,参见外交部网站,https://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tytj_674911/tyfg_674913/t1215630.shtml,2019年8月1日访问。中,外国判决“确定性要件”的表述不同于《民事诉讼法》等国内法之规定;④参见乔雄兵:《论外国法院判决承认与执行中的终局性问题》,《武大国际法评论》2017年第1期,第80-81页。相反,绝大多数表述为“已经确定”⑤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法兰西共和国关于民事、商事司法协助的协定》第22(3)条。,或“已经生效”⑥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意大利共和国关于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第21(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秘鲁共和国关于民事和商事司法协助的条约》第23(1)条。,或“已经生效和可以执行”⑦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波兰人民共和国关于民事和刑事司法协助的协定》第20(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立陶宛共和国关于民事和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第17(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关于民事和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第21(1)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希腊共和国关于民事和刑事司法协助的协定》第22(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民事和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第17(2)条。,或“终局的和可以执行的”⑧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巴西联邦共和国关于民事和商事司法协助的条约》第23(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科威特国关于民事和商事司法协助的协定》第24(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关于民事和商事司法协助的条约》第24(1)条。,以及“终局和具有执行力的”⑨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关于民事和商事司法协助的协定》第24(2)条。。一方面,对于这些双边条约采取相互之间差异较大的“确定性要件”之表述,并不存在显在的合理理由;另一方面,对于这些双边条约采取与我国《民事诉讼法》等国内法中“确定性要件”相去甚远的表述,亦难以解释。在我国现行法律框架下,尚不存在相关法律对这些差别予以区分和阐明,这容易引起条约适用中的不确定性。对于这些双边条约中的“确定性要件”,最基本的一个问题是所采用的术语“已经确定”“已经生效和可以执行”“终局的和可以执行的”等是否等同于我国《民事诉讼法》中的“发生法律效力”。关于确定性的判断标准,我国现有双边条约均规定应依据“作出裁决的缔约一方的法律”①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法兰西共和国关于民事、商事司法协助的协定》第22(3)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意大利共和国关于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第21(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巴西联邦共和国关于民事和商事司法协助的条约》第23(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关于民事和商事司法协助的条约》第23(1)条。,该规定符合国际社会的一般实践。值得注意的是,2019 年《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民商事案件判决的安排》将承认和执行的范围限定于“生效”判决②参见《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民商事案件判决的安排》第1条。,并就“生效”的判决给予了列举式载明③参见《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民商事案件判决的安排》第4条。。该安排将“确定性要件”界定为“生效”判决,因循了2019 年公约的“确定性要件”之表述;不仅如此,该安排详细列举了内地及香港可作出“生效”判决的法院清单或情形④该安排所称“生效判决”:(1)在内地,是指第二审判决,依法不准上诉或者超过法定期限没有上诉的第一审判决,以及依照审判监督程序作出的上述判决;(2)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是指终审法院、高等法院、上诉法庭及原讼法庭、区域法院以及劳资审裁处、土地审裁处、小额钱债审裁处、竞争事务审裁处作出的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这似乎可为解决围绕“确定性要件”的诸多难题,提供可取的“确定性要件”之缔约方案。
(二)司法实践
本部分意在梳理我国近13 年来具有代表性的外国判决承认与执行案件,分析“确定性要件”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适用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在早期的外国判决承认与执行案中,如具有代表性的安托瓦纳·蒙杰尔2005 年提起的申请承认与执行法国破产判决案⑤参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5〕穗中法民三初字第146号民事裁定。中,申请人提交了一份由法国瓦提艾市商业法院的书记官皮埃尔·奥利维埃·于朗于2004 年7 月28 日出具的证明,意在证明该申请人申请承认的法国判决已经生效。据此,在并未分析该法国判决是否以及如何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法兰西共和国关于民事、商事司法协助的协定》中的“确定性要件”的情况下,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径直认定该判决已生效。而在一些案件中,如在2016 年法国K.C.C 有限责任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法兰西共和国贡比涅商业法院RG2013F00048 号商事判决案⑥参见〔2016〕湘10协外认1号。,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其裁判文书中并未对“确定性要件”予以任何裁定。早期具有重大影响的1994 年五味晃案⑦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6年第1期,第29页。,2003 年明斯克自动线生产联合公司申请承认及执行白俄罗斯共和国最高经济法庭判决案⑧参见〔2003〕民四他字第4号。,2003 年受理的意大利B & T Ceramic 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意大利法院破产判决等案件中,我国法院亦未对“确定性要件”作出任何裁定。值得注意的是,在2010年胡克拉床垫和软垫家具厂有限公司(以下称“胡克拉公司”)申请承认及执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奥芬堡州法院第20460/07判决案①参见〔2010〕民四他字第81号。中,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申请承认(及执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奥芬堡州法院第20460/07判决一案的请示的复函》中,不认可德国奥芬堡州法院向北京富克拉家具销售有限公司邮寄德国判决书的送达方式,故认定该判决尚未对北京富克拉家具销售有限公司“发生法律效力”。在本案中,相关法院依据送达非法而认定德国判决对被申请人未“发生法律效力”。
2005 年施耐德电气工业公司申请承认与执行法国巴黎大审法院判决案②参见〔2005〕温民三初字第155号。是少数我国被请求法院较为详尽地阐释“确定性要件”的案例。为证明所涉判决的确定性,申请人施耐德电气工业公司向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称“温州中院”)提交了巴黎上诉法院出具的涉案判决已经生效的证明书副本及中文译本。温州中院认为法国判决书本身没有明确指出判决已经确定,上诉法院的证明仅表明巴黎上诉法院无任何关于所涉案件对席判决的上诉记录,故其依据《法国新民事诉讼法典》的规定签发民事判决生效书。然而,《法国新民事诉讼法典》规定了在判决书签发当年可允许取消逾期导致失去上诉的权利,故温州中院认定涉案判决尚未确定。此案中,温州中院对确定性的适用依据模糊不清,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法兰西共和国关于民事、商事司法协助的协定》中载明的按照作出判决的缔约一方的法律判断确定性之规定。③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法兰西共和国关于民事、商事司法协助的协定》第22(3)条。从措辞来看,其更多地是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有关上诉导致判决不能发生效力之规定判断法国判决的确定性,进而否定法国判决的确定性。
在近几年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的案件中,我国法院亦未对外国判决的“确定性要件”予以明确审查。比如,在申请人刘某与被申请人陶某、童某申请承认和执行美国法院民事判决案④参见〔2015〕鄂武汉中民商外初字第00026号。中,受诉法院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未对美国判决的确定性予以裁断,被申请人亦未针对该要件提出异议。在法国K.C.C 有限责任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法兰西共和国贡比涅商业法院RG2013F00048号商事判决案⑤参见〔2016〕湘10协外认1号。中,受诉法院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及被申请人均未提及法国裁判的确定性问题。同样地,在Kolmar Group AG 与江苏省纺织工业(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民事判决案⑥参见〔2016〕苏01协外认3号。中,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并未就新加坡法院判决确定性问题予以裁判,而是径直承认和执行了该判决。在纳尔科公司有限责任公司申请承认与执行美国伊利诺伊州北部东区分庭判决案⑦参见〔2017〕沪01协外认16号。中,美国判决的确定性问题未成为当事人争辩的焦点,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据申请人提交的判决副本及中文译本认定美国判决为最终判决且已生效,并最终承认与执行了该美国判决。
基于上文的考察,可以大致得知我国一些法院对“确定性要件”的适用未给予充分重视和关注,未对外国判决是否确定的标准或法律适用等问题作出明确、有说服力的裁判。对此,最高人民法院亦无关于该要件的统一解释。囿于现行外国判决承认与执行法律之限制,我国一些法院通常聚焦于“互惠”的存在以及“送达”的合法,而对外国判决的确定性、外国法院管辖权、公共政策等诸要件鲜有触及或阐释。①See, e.g., Wenliang Zhang,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Foreign Judgments in China: A Call for Special Attention to Both the Due Service Requirement and the Principle of Reciprocity, 12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43 (2013); 张文亮:《外国判决承认与执行语境下“送达抗辩”研究》,《当代法学》2019年第2期,第150页。一方面,这与我国《民事诉讼法》的原则性规定存在重要关系;另一方面,我国一些法院可能尚未在实践中厘清或架构外国判决承认与执行的要件体系。从形式上说,我国《民事诉讼法》引入了“确定性要件”,尽管较为框架化和原则性,但这在原则上并不妨碍我国法院在实践中对该要件予以适用,并加以丰富和发展。即便是在存在双边条约的情形下,司法实践亦未充分关注“确定性要件”。除此之外,在前述案件中,鲜有被执行人围绕“确定性要件”对外国判决的承认和执行加以抗辩,这亦是我国司法实践中该要件尚未凸显的另一缘由。
(三)若干建议及完善进路
针对当前外国判决承认与执行现状,一方面,我国应改变立法及司法实践不重视“确定性要件”的做法,确立“确定性要件”的合理地位。“确定性要件”已是各国普遍确立的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的重要条件,重要的国际性和区域性法律文件均将该要件置于凸显的位置,外国判决确定与否决定着该判决能否得到顺利承认或执行。我国在立法上应确立体系化的外国判决承认与执行法律框架,其中,“确定性要件”的合理与体系化是重要内容。伴随体系化的外国判决承认与执行之立法体系,司法实践亦应摆脱以往片面关注部分承认与执行要件而忽视包括“确定性要件”等诸要件的实践做法。由于我国目前缔结的双边司法协助条约的数量有限,因此,有必要完善《民事诉讼法》等法律中有关“确定性要件”的相关规定。鉴于《民事诉讼法》有关外国判决承认与执行立法的较为滞后,②我国《民事诉讼法》自1991 年颁布以来,有关“确定性要件”在内的外国判决承认和执行之规定还未曾有过修改。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实践突出并完善“确定性要件”适用的思路可能可取。
另一方面,我国“确定性要件”的架构应遵循合理的思路。首先,应明确“确定性要件”的标准或法律适用。尽管在原审国已属确定的判决未必依被请求国的相关标准亦属确定,然而依据原审国法律判断外国判决确定性的思路是可取的。这可以避免不同国家依据各自标准对同一判决认定为不同的效力状态,因而成为目前国际主流标准。由于外国判决在被请求国的效力不应大于其在本国的效力,①参见张文亮:《论外国判决在内国的效力——兼析外国判决在我国的效力》,《国际法研究》2013年第9卷,第76页。依据原审国法律判定外国判决的效力可以避免被请求国赋予不具有效力的外国判决以本地效力。再者,有关“确定性要件”适用中的适度矫正或制衡成为必要。对于依据原审国法律已属确定的外国判决,可以参照2005 年公约或2019 年公约的立场,尽管其在原审国尚处于审查之中或寻求“普通审查”的时限未过,被请求国仍然可以在申请人提供担保的情形下承认和执行,或者暂停承认和执行程序,而非径直予以拒绝承认和执行,以保障和创造有利于外国判决承认与执行的环境。
处于上诉或再审状态的判决是判决具有的两种典型状态,其确定性应予明确。外国判决处于“上诉”状态只是外国判决的一种状态,该状态下的判决依据原审国法律可能是确定的,亦可能是不确定的;如上文所述,应以原审国法院而非被请求国的法律加以判断,并借鉴2005年公约或2019年公约予以适度矫正,是适用外国判决承认与执行中的“确定性要件”的合理路径。再审是原审法院针对其自己在先作出的判决的一种重新审理程序,该程序通常会破坏在先判决的确定性。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和当事人均可启动再审程序并从证据、回避、程序以及枉法裁判等方面规定了13 种当事人可申请再审的情形。《民诉法解释》确认了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发生新的事实,当事人再次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正因为如此,有学者认为我国的再审程序易被启动且适用条件不太严格,所以判决不符合普通法系要求的“确定性要件”;②See LIU Nanping, A Vulnerable Justice: Finality of Civil Judgments in China,13 Columbia Journal of Asian Law 35-98 (1999).显然,该主张诉诸被请求国的法律判定外国判决并不合理。然而,即便再审程序是我国诉讼中的“非常态”诉讼程序,但是若该程序的适用条件较为宽松且易于启动,那么会阻止判决的确定性,一方当事人从诉讼或纠纷解决策略的角度启动该程序,则容易为被请求国认定为相关判决欠缺确定性。从1991《民事诉讼法》颁行以来,我国《民事诉讼法》对再审条件及启动时限等多有修改,使其朝着更为严格适用的方向发展,凸显其“非常程序”的特质,③比如,在启动再审程序的时限方面,我国《民事诉讼法》经历了从无时间限制到有时间限制,以及两年时限到六个月时限的过程。参见2007 年《民事诉讼法》第184 条和2012年、2017年《民事诉讼法》第205条。回应那些对我国判决确定性存疑的主张。
欠缺确定状态的判决亦非全然不能获得承认与执行,尤其是对跨国纠纷解决及国际民商事诉讼意义日渐凸显的临时救济而言,其跨境承认与执行之意义更加突出。④参见张文亮:《论临时救济中的第三人——以我国涉诉民商事临时救济为视角》,《现代法学》2016年第1期,第165页。在欧盟现行布鲁塞尔判决体系下,对案件实体有管辖权的欧盟成员国法院作出的临时救济可以在其他成员国得到承认与执行,①See, e.g., EU, Preamble (33), Regulation (EU) No.1215/2012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12 December 2012 on Jurisdiction and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Judgments in Civil and Commercial Matters (Recast), 20.12.2012,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Union L351/1.尽管这种临时措施并不具备传统意义上的“确定性”。而布鲁尔塞尔判决体系传统上并不要求外国判决的“承认”应以外国判决具有确定性为前提,也是考虑到特殊性的判决虽然并不具有确定性,但其仍然需要得到域外的承认或执行。欧盟2013 年《关于相互承认民事保护措施的条例》致力于欧盟内临时救济的自由流动,亦提供了各国在临时救济领域承认和执行的典范。②参见张文亮:《涉外临时救济的三重困境及应对分析——兼评我国现行涉外临时救济体系》,《现代法学》2017年第6期,第164页。我国现行司法实践中未出现外国临时救济的承认和执行,然而,随着该类救济在涉外纠纷解决中重要性日益凸显,其跨境承认与执行亦应成为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规范的对象。
我国已缔结若干双边司法协助条约,其大多就“确定性要件”作了相对明确的规定,我国司法实践应充分关注并适用其中的“确定性要件”。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应根据双边条约的规定切实适用依原审国法律确定外国判决的“确定性”,并对差异较大的“确定性要件”予以统一解释,以有效避免司法实践的混乱。对将来我国拟缔结的双边司法协助条约,可借鉴2019 年公约就“确定性要件”引入的主流标准,确立更加合理且有利于判决承认与执行的“确定性要件”。
五、结语
随着外国判决承认与执行事项的重要性日益凸显,③参见张文亮:《外国判决在中国的承认与执行:现状及未来》,《武大国际法评论》2016年第2期,第48页。围绕外国判决诸要件的拟定、适用以及协调或统一成为迫切问题,而外国判决承认与执行的“确定性要件”已成为广泛关注的问题。各法域或法系之间在该要件上的立法与实践多有差异,这造成了协调或统一的困难,也使得当事人在外国判决承认与执行中可能遭遇诸多困境,被执行人也可能围绕“确定性”恶意破坏或阻碍外国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在协调或统一“确定性要件”中,海牙判决公约体系的方案具有代表性,其意在调和诸法系或国家之间在“确定性要件”上的分歧,引领了国际社会架构合理的“确定性要件”。欧盟对外国判决的承认,原则上并不要求“确定性”,其代表了“确定性要件”协调或统一的更高目标。
我国国内法确立了“发生法律效力”之“确定性要件”,双边民商事司法协助协定引入的确定性标准并不统一,尚不能为司法实践提供有效引导。在我国现行司法实践中,有关“确定性要件”的适用亦未引起我国法院足够重视,且已有实践相对混乱。引入合理的“确定性要件”并保障我国法院恰当适用该要件应成为我国有关外国判决承认与执行之立法改革与司法完善的重要方面。以海牙判决公约体系的协调与统一为蓝本,我国有关“确定性要件”的立法应脱离传统立法对判决确定性的固有认识,从比较法的视域出发,确立原审国法律作为判断“确定性要件”的依据,并对处于特殊状态下的外国判决予以适度制衡。我国未来缔结的双边司法协助条约,亦应确立相对一致的确定性标准,海牙国际私法会议的协调和统一方案同样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