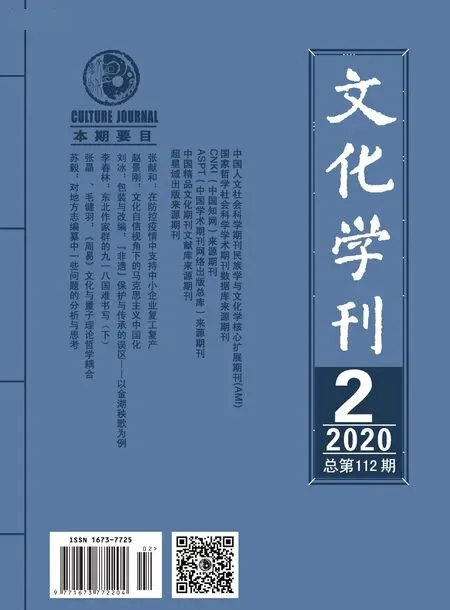论郭启宏的“传神史剧论”及其时代价值
郭 歌
郭启宏是新时期具有重要影响的戏剧作家之一,在历史剧创作方面剧作多、质量高、水平高,形成了独特的创作理论和艺术风格,对我国戏剧艺术的繁荣和发展有着重要贡献。他提出的“传神史剧”理论主张建立了一种新型的强调作家主体意识和戏剧艺术本位的史剧观念,继郭沫若之后,进一步推动了我国史剧理论的发展,成为历史剧创作过程中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生动范例和典型。
一、“历史剧”性质的争鸣与史剧创作理论的探讨
“历史剧”是以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典型的历史人物为题材的戏剧,最初命名时是相对于“时事剧”提出来的。关于历史剧的性质和作用,理论家有着不同的理解,西方文学史上已经争论很久,国内论坛上也是见仁见智。就国内学界的争论来看,一部分学者认为历史剧是艺术但也是历史,提倡历史剧要完全根据史料的真实性来构思,不容虚构;一部分学者则认为,作为戏剧艺术的历史剧,剧作家可以根据塑造典型人物的实际需要,对历史事件及其他非主要人物进行艺术加工,甚至还可以进行局部的虚构。
关于历史剧创作的理论很早就受到理论家和剧作家的重视。“五四”启蒙运动时期,应时代精神的需要,历史剧创作方面表现出个性解放、追求自由和爱国主义的时代主题,并明显地带有主观抒情性特征。郭沫若的《卓文君》《王昭君》《三个叛逆的女性》和王独清的《杨贵妃之死》《貂蝉》等就是这一时期历史剧创作的典型代表。可见,我国现代历史剧在创作初期就表现出具有时代内涵的史剧观念和戏剧主张,体现出史剧作家关于历史剧创作的重要理论见解。
抗日战争时期,民族主义情绪异常高涨。鉴于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高压和言论自由的限制,宣传抗战的戏剧演出频频遭禁,剧作家们把创作内容放到了从历史上挖掘那些反抗侵略、主张爱国和追求光明进步的题材,从而激发和鼓舞人民群众救亡图存的抗战斗志。郭沫若作为旗手和主将,连续创作出《棠棣之花》《屈原》《虎符》《孔雀胆》等多部浪漫主义的历史剧。其他一些剧作家也积极行动,写出了一大批历史剧作品,如杨(阳)翰笙的话剧《李秀成之死》《草莽英雄》、欧阳予倩的京剧《梁玉红》《桃花扇》、于伶的话剧《大明英烈传》等,迎来了历史剧创作的一个高潮。
这一时期历史剧的创作与繁荣,在史剧创作方法上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剧作家们都强调历史剧创作应该尊重历史,也承认历史剧有服务现实的功能,但在历史剧是否能够反映现实,以及“史”与“剧”,“虚”与“实”谁主谁从的关系问题上有着较大的分歧。对此,许多剧作家发表了大量意见,对历史剧创作中的问题进行争论。重庆的《戏剧月报》在1943年第4期特别刊载了《历史剧问题特辑》。作为抗战时期历史剧创作实践和理论研究的主要代表,郭沫若大力强调和宣传古为今用的主张,旗帜鲜明地捍卫史剧作家自由创作的权利。郭沫若还把这一时期历史剧争论的内容作了概括,对自己提倡的史剧理论进行了总结和阐述。他指出:历史研究是“实事求是”,史剧创作是“失事求似”;“史学家是发掘历史的精神,史剧家是发展历史的精神”。郭沫若[1]认为,历史剧的创作不在于历史本身的体现和完全依靠史实,而在于历史观的正确与科学,以及能在现实斗争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这一理论提倡史剧创作应运用各种表现手法,尽量使戏剧作品具有生动性和艺术性,使剧中人物形象具有丰富性和典型性。史剧不是要教条化地再现历史,而是要体现充沛的现实精神。但是,现实精神也不能是机械的说教,不能是脱离历史人物形象的标签,而是在充分尊重历史人物形象的基础上表达出来的、体现现实斗争需要的一个辩证的统一体。这是郭沫若对历史剧创作理论的重大贡献。
20世纪50年代中期兴起的改编神话剧、新编历史剧如何为现实服务问题的讨论,同时引发了一场关于历史剧性质问题的论争。20世纪60年代初,剧作家围绕吴晗发表的《论历史剧》一文又引起了关于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古为今用等问题的激烈争论。但这两次关于历史剧问题的讨论和争辩的结果并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和意义,而是更多体现出复杂的政治氛围及文学与政治的紧张关系。“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以人为本”的观念成为历史剧作家创作的核心,取得了一定成就,出现了一大批具有鲜活艺术生命力的史剧作品。郭启宏“传神史剧论”正是贯彻这一新的创作观念的重要体现,是新时期历史剧创作在理论建设方面的一个重要突破。
二、郭启宏的“传神史剧论”及其要义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郭启宏相继创作了京剧《司马迁》《王安石》《卓文君别传》和昆剧《南唐遗事》等,塑造了一系列独特而深刻、复杂而丰富的古代知识分子形象。《司马迁》获得国家文化部庆祝建国30周年献礼演出创作二等奖,《王安石》获得1980年文化部创作奖,《南唐遗事》1988年获第三届全国戏曲电视剧“金三角奖”一等奖、第四届全国优秀剧本奖,《南唐遗事》还在1989年获北京市新创剧目优秀编剧奖。这些成果的社会影响与良好的声誉奠定了郭启宏在新时期优秀历史剧作家的地位。
在史剧创作的艺术实践中取得一系列丰硕成果并获得重要社会影响和声誉,郭启宏在历史剧创作的理论方面也有着自觉的探索。1988年《剧本》月刊1月号,发表了郭启宏的被誉为“新时期中国史剧作家的创作宣言”的《传神史剧论》[2]。接着,他还发表了《史剧四题》《历史剧旨在传神》《再论传神史剧》等系列论文。在这些文章中,郭启宏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他的“传神史剧论”主张,实现了现代以来关于历史剧性质争论中“史”与“剧”关系问题的突破。郭启宏“传神史剧论”的要义是他提出的“传神三义”,即传历史之神、传人物之神、传作者之神。
传历史之神,就是用当代意识观照历史。郭启宏认为:“传历史之神就是要把历史看作有生命的实体。人们不应该误解,历史不是发黄的故纸堆。在一个有血有肉的剧作家来看,历史是另一形态的现实人生,写历史依然是反映生活。”[3]同时他指出:“历史的魅力就在于我们现实中的人总可以在历史中照见自我,历史之神韵便是寻求历史与现实的连接点,用当代意识激活历史。要以审美为终结,依神写貌。”[4]当然,郭启宏强调以当代意识审视历史并非要随意更改历史,或率性而为、随意增删。郭启宏的史剧观历来非常明确,那就是要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对历史精神加以分析和艺术加工。
传人物之神,指剧作家在创作中要特别注重传达人物的精神世界,通过体悟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来塑造人物的形象。郭启宏指出:“要写人的内心,而不满足于写人的外部行为。”他还指出“要透过人物身后的厚重的帷幕去触摸社会的、文化的、传统的大背景”,用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去考察历史人物所处时代的政治制度、经济状况、人文环境以及典章文物等,发掘历史人物本身所蕴含的人生哲理。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传人物之神。
传作者之神,指史剧创作要注重表达剧作家的主体意识。郭启宏认为:“史剧家的主体意识与创作而俱来,与史剧而同在……作家在创作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将自己的理想、情操、趣味、学识。连同自身精赤条条的人性,融汇于自己笔下的历史人物形象之中。”[5]在郭启宏看来,剧作家的主体意识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通过历史感悟,从丰富的历史素材中寻找沟通古今的哲理意蕴;二是进行现实体验,在深刻地认识历史过程中,把握历史人物的独具个性与真性情;三是体现审美理想,充分表达剧作家的创作个性与艺术风格,张扬其独特的审美情趣。
上述郭启宏“传神史剧论”中的传神三义是史剧创作过程的完整和系统表达,其中,以传历史之神为基础,以传人物之神为核心,以传作者之神为归宿,三者是一个辩证统一的整体。这一体现新时期史剧创作精神的理论原则是我国史剧理论创新的重要成果,也是现当代史剧创作理论发展的重要体现。
三、郭启宏“传神史剧论”的时代价值
郭启宏的“传神史剧论”形成于改革开放之初,在文学艺术创新发展的历史潮流中呼应了时代的召唤,同时把我国史剧创作的理论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时代价值。
第一,“传神史剧论”提倡剧作家的主体意识、尊重史剧创作的基本规律、回归史剧创作的艺术本体论,这是对史剧创作中客观性原则的运用,具有思想解放与文化启蒙的价值意义。
“五四”以来,我国历史剧的创作和演出历经了“演义史剧”和“写真史剧”的较长时期,剧作家的创作只是局限于传统的写实戏剧观,所追求的是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去创作,衡量戏剧创作成败的唯一标准也只看戏剧是否忠实于客观事实、是否揭示了社会生活的本质与规律。剧作家主体意识的体现、心灵的思考、主观理想的表现和艺术的感受,往往成为戏剧评论者被忽视的问题。新时期的到来,“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时代潮流的推动使社会主体意识得以觉醒,并诞生了强烈的文化启蒙精神和精英意识。作为一名有理想、有抱负的戏剧作家,郭启宏有着敏锐的时代感和迫切的使命感,他提倡的“传神史剧论”恢复了史剧创作中艺术的本体性地位,使剧作家对社会、人生、命运的思考成为戏剧创作的主体意识。这种对史剧创作理论的探索与开拓创新,对改变中国当代史剧多年来僵化教条的创作思维和单一贫乏的舞台观念,起了重大作用,对新时期文化艺术领域中的思想解放和精神启蒙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传神史剧论”充分尊重戏剧文学的独立性和审美特征、从人性的视角解读历史、从不同角度挖掘人物性格的多重特点,主张戏剧艺术应当建立在人性的基础之上,体现了新时期戏剧创作的新趋势,为史剧创作提供了理性思辨与艺术实践的双重参照系。
改革开放之前的一段时间,我国戏剧虽然被称之为“人民的戏剧”,但这里的“人民”只能是一种政治的符号。在“左”倾思潮冲击和影响下,人性成为资产阶级的代名词。受到忽略人性、排斥人性、批判人性史剧观的驱使,历史剧成为空洞无味的政治说教。新时期的到来,我国的戏剧创作和戏剧理论也发生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历史剧的创作视野、价值观念、精神内涵、艺术范式等出现了一系列新变化,剧作家的主体意识普遍加强。人的解放与人性的展现成为一种强烈的时代意识,渗透到了历史剧的创作之中,使新时期戏剧舞台的面貌焕然一新。
提倡“传神史剧论”的郭启宏是戏剧文学创新中时代潮流的代表,在史剧创作中凭借剧作家的现实亲历和创作体验,不断地激活历史,赋予历史人物鲜明的个性特征,展现出历史人物独特的精神风貌。郭启宏创作的话剧《李白》《天之骄子》、京剧《司马迁》《王安石》、昆曲《司马相如》等,对传统文人仕途命运的艰辛和心灵冲突重新进行了历史的阐释。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作品透过历史人物身后的帷幕去揭示封建体制下传统文人的艰难处境和曲折人生。郭启宏认为,历史剧最高的审美境界,就是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和内在哲理性,从而体现出剧作的思想深度与艺术韵味。可以看出,挖掘人性、深层次地思考人性和张扬人性是郭启宏史剧创作的主题之一,也是新时期“人学”回归历史剧创作的重要体现。
第三,“传神史剧论”从“史”与“剧”的关系出发,积极寻求解决“史”与“剧”矛盾冲突的方法和途径,找到了文学与历史相融的最佳契合点,使史剧创作的当代意识与传统史论得以沟通,促进了剧作内容和形式的同步发展,实现了新时期史剧理论的创新。
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现代历史剧的创作一直都是随同时代发展的脉搏共振,跟踪时代潮流的政治使命感造成了长期以来史剧创作中重“史”而轻“剧”的倾向,“剧”成为现时意识形态传播的工具。新时期到来,史剧创作中“史”的霸权话语被不断解构,“剧”的本体地位得以回归,逐渐摆脱“史”对“剧”的束缚、不断拓宽“剧”的解放之路。郭启宏的“传神史剧论”一改过去色彩浓厚的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相统一的原则,肯定了“史”与“剧”结合的重要性,确立了“剧”在历史剧创作中的本体地位。以“剧”的神似来传达“史”的神韵,将“剧”的神似与“史”的神韵相融合,成为“传神史剧论”的鲜明特点,体现着贯穿历史与历史人物相融通的剧作者的主体意识和时代精神。正如郭启宏所指出的:“传神史剧指的是这样的历史剧:内容上熔铸剧作家的现代意识和主体意识,形式上则寻求‘剧’的彻底解放。”[6]
四、结语
在新的历史时期,历史剧同其他文学艺术作品一样,在思想解放和文化启蒙的过程中积极地发挥着自身应有作用,在探索中确立了自己独立的身份和地位,并呈现出丰硕的成果。郭启宏关于“传神史剧论”主张的提出是改革开放时期戏剧改革的现实需要,历史剧作为“剧”的艺术本体地位的确立也是这一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郭启宏呼应时代的召唤,在历史剧创作的理论与实践方面同时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并为新时期历史剧的创作开拓了新的途径与可以遵循的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