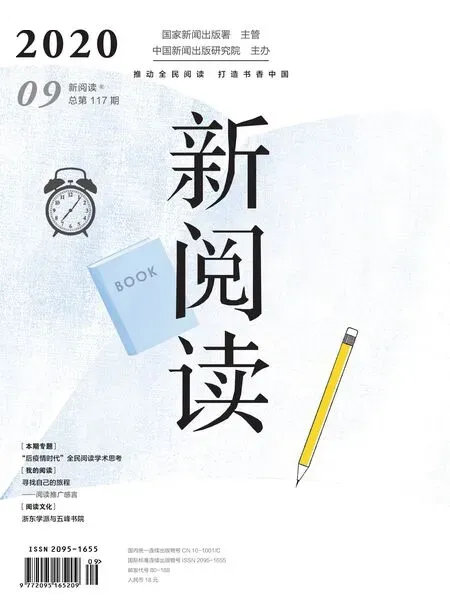《白鹿原》展现的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
文/ 王曼利
《白鹿原》是陈忠实20 世纪80 年代在国内寻根文学、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以及“文化心理结构”影响下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的一颗文学果实。文学思考与人生经历使陈忠实最终将目光聚焦到了熟悉的西北农村,以现实而又不失诗意的手法构筑了一个个白鹿原为核心的文化空间,展现了文化之间的复杂联系。
坚守:白鹿原上的儒家文化
《白鹿原》开篇谈到了白嘉轩娶妻七房的奇闻,这几任妻子分别来自白鹿原东南西北四个方位,六个无名女性从父家来到夫家,却以不同方式纷纷殒命,这是中国男性社会中女性命运向男性威严的俯首,又是民间文化场向白嘉轩代表的儒家文化场的投诚。仙草诞下儿子白孝文后,白嘉轩完成了传宗接代的人生大计,主要活动空间从家庭转向祠堂。
“祠堂是中国古代宗法制社会皇家祭祀权世俗化和民间化的结果……对凝聚族群、培植和塑造族群文化,乃至同化族人思想都具有不可否认的深刻作用。”白嘉轩在祠堂中行使宗法制族长的权力,对族人进行规训与惩罚。黑娃与田小娥的结合在白嘉轩看来“非法”的,因此他拒绝二人进祠堂祭拜。黑娃甚至一度也认同白嘉轩的做法,可见儒家文化影响白鹿原之深。白嘉轩在祠堂中惩治过狗蛋、小娥、白孝文及烟鬼和赌徒,“祠堂由惩罚而衍生了示众、拷问、鞭笞、监禁、集体唾骂和边缘化等一系列规训和排除异己的手段,目的是要塑造儒家文化谦卑的顺民。”
“如果说儒家思想理念的实践者是白嘉轩,那么朱先生则是白鹿原的精神领袖。”朱先生一生恪守关学派的处世准则,是白鹿原上人人信仰的一尊神,他为村民占卜、铲除鸦片、编写县志、投笔从戎、墓室留下的谶言……无一不是凡人能为的奇迹。“朱先生以文化权威凌驾于白鹿原精神文化世界的至高地位……朱先生以白嘉轩为中介,通过祠堂的群聚效应实现了儒家文化思想对白鹿原的精神控制。”
叛逃:白鹿原内外的政治文化
鹿兆鹏曾在朱先生处求学,后联合黑娃风搅雪,以国民党和共产党身份在白鹿原上创办农讲所,策划渭北运动,他的一生反映了国共两党从合作到破裂,红色革命活动从公开到隐蔽的过程。鹿兆鹏一直反叛旧文化的束缚,数次革命的对象都是白鹿原,但却屡遭失败,这源于儒家文化的根深蒂固。白灵一生经历了求学、自由恋爱、参加革命、与鹿兆鹏结合和最后被活埋,与鹿兆鹏相比,她更加疏离于白鹿原,她奔向外面世界是一个与白鹿原渐行渐远的过程。红色革命文化以白鹿原的儒家传统为反叛对象,却始终离不开这个可恨又可亲的故乡。
白孝文是白鹿原族长的继承人,家族的严格教育使他成为“被规训的产物,儒家思想化为他的集体无意识,塑造了他老成沉稳外表,”在与小娥私通、卖祖宅、抽鸦片和几乎为野狗分食后,白孝文最终走上仕途,不断的升迁使白孝文日益冷漠、残忍,最终为攫取新政府的权力而葬送黑娃性命。当白孝文与第二任妻子回家祭拜先祖及母亲时,看似回归儒家文化的他“情感已经回不到当初。”
田福贤重新回到白鹿原,在原上戏楼前杀鸡儆猴,白嘉轩因此将戏楼称为“烙锅盔的鏊子”。白鹿原是田福贤的根据点,他在原上利用权力残杀异己,镇压进步力量。白嘉轩的硬措施是重修乡约,此举被朱先生誉为“治本之策”。重修的祠堂和乡约引发了乡人的感叹和痛哭,重修乡约不仅是白嘉轩在儒家文化熏陶下本能应对外来异质权力话语的途径,更是他重新凝聚人心的重要举措。
“鏊子”是不同政治力量在白鹿原消长和演替的形象隐喻,白嘉轩一直试图独立于政治外,却始终被卷扰其中,当政治力量与族群文化发生交锋时,白鹿原的儒家文化就显得脆弱不堪。
反抗与皈依:白鹿原的民间文化
土匪是近代中国极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匪帮往往罔顾法律,无视人类道德底线,价值观模糊,遵循民间的道德法则,往往与近代中国各种政治力量保持一种微妙的联系。黑娃砸过祠堂,闹过风搅雪,为国民革命军习旅长做过警卫,之后落草为寇,因脾气硬、手段硬、枪法准,被土匪推举为二拇指。入匪前,黑娃跟随鹿兆鹏闹革命,但此时他在隐约反抗的是白嘉轩及祠堂文化,有泄私愤的嫌疑。后在白孝文的招降下,黑娃进入保安团,西安解放后被白孝文陷害杀死。田小娥被杀后,黑娃深夜潜入白家,“他悲哀地发觉,儿时给白家割草那阵儿每次进入这个院子的紧张和卑怯又从心底浮泛起来,无法克制。”这种紧张和卑怯在来自黑娃对白家所象征的儒家文化的卑微和怯懦,黑娃砸断白嘉轩的腰隐藏着他对白嘉轩象征的儒家文化威压的反抗。
黑娃后来的妻子高玉凤知书达理,“聪明过人,没上过一天学却能熟背四书”。从小耳濡目染儒学经典的玉凤与黑娃结合,是黑娃回归儒家文化的象征。之后,黑娃更是拜师朱先生,成为朱先生最后一个弟子。黑娃先闯世事后求学问的经历,使他比朱先生所有的学生顿悟更快也更深,以至于朱先生慨叹:“想不到我的弟子中真求学问的竟是个土匪胚子!”自此,黑娃“真正开始了自觉的脱胎换骨的修身……强硬地迫使自己接受并养成一个好人所应具备的素质,中国古代先圣先贤们的刻骨铭心的哲理,一层一层自外至里陶冶着这个桀骜不驯的土匪胚子。”黑娃回原上祠堂祭祖,受到了白鹿村最高规格的欢迎仪式,离开祠堂时,黑娃回头看到断裂的乡约石碑,晚上执意睡在母亲的炕上时,黑娃说:“我这会儿真想叫一声‘妈’。”显然,白鹿原祠堂对黑娃来说“是一种‘精神'故土。是一个人的精神家园。‘魂归故里’‘浪子回头’,实质上是一种精神的漂泊者对‘家园’的回归,是一种子精神对母精神的依恋和融合。”
《白鹿原》还大量展现了陕西关中地区的农事活动、婚丧嫁娶和巫术传说等民间文化。白鹿原上每逢“忙罢会”,人们便穿新衣,携花馍,走亲访友,演大戏演灯影耍木偶。作为农民的白嘉轩,一生首先关注的是稼穑、纺织、圈养牲畜、娶妻生子,他过年放鞭炮,爱听秦腔爱敲锣鼓。白孝文与田小娥因私通被白嘉轩在祠堂惩罚后,白鹿原上相继出现了旱灾和饥馑。身为族长的白嘉轩心急如焚,他带领族人伐神取水的描写颇具传奇色彩。此外,《白鹿原》中还有相当篇幅的生殖文化和鬼神文化的描述。对棒槌神的民间崇拜,目的是维持儒家文化“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族群传统。鬼神文化则集中体现在田小娥附身鹿三复仇的片段,对此,我们另行撰文再论。
民间文化看似远离白鹿原的儒家文化场和交锋的政治文化场,实则始终构成了这两种文化的地平面,构成《白鹿原》浓烈的地域文化底色。
结语
空间是权力运作的基础。儒家文化通过祠堂和乡约对白鹿原进行规训与惩罚,鹿兆鹏和白孝文作为白鹿原儒家文化的反叛者,分别走上了一正一邪的道路,鹿兆鹏革命成功后不知所踪,政治反动派白孝文却功成名就,先匪后文的黑娃则在皈依儒家文化后被牺牲,族长白嘉轩超然于世事之外……在不同文化的关系中,传统的儒家文化究竟如何完成现代性的转型?这是《白鹿原》的深刻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