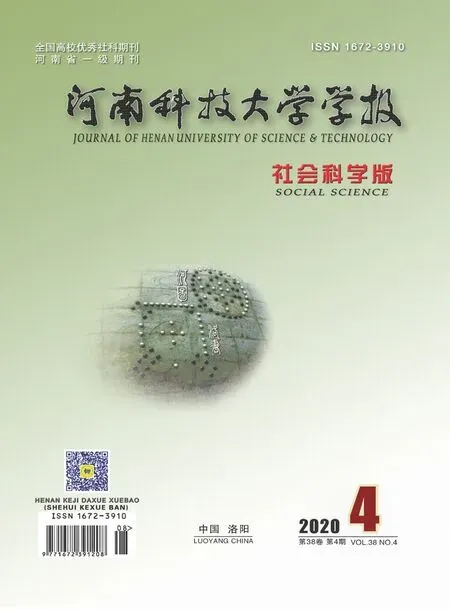《海上花列传》中的空间书写及其文化意义
张 震
(河南大学 文学院, 河南 开封 475001)
关于青楼/欢场的文学性书写,兴盛于唐。这一时期,产生了大量歌、诗、小说等体裁的文学作品,“不少严肃的作家和民间艺人在面向严酷的生活时,总是怀着一种神圣的道德感,深情地关心着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命运”[1]2。这种理解的悲悯一直延续至明清之前。明代青楼体制的变革(1)明洪武二十七年(公元1394年),朱元璋于金陵设十六酒楼以安置官妓;宣德年间,宣宗因群臣沉迷狭邪,取消官妓制度,自此,南京诸烟花之地回归民间。将多情撒向民间,资本主义萌芽的初潮席卷东南,四民阶级之辨不断被稀释,士与商共同狎妓征色、醉生梦死,同情与恻隐褪色成昨日风景,女子化身为某种可资品评之“物”[2],或是成为士子富商标榜风骨、风月加身的名片。清中叶,文字狱大兴,青楼文学多以前朝故事编织风花雪月,至乾隆时侈靡之风炙盛,但早年间“禁妓”的文化政策、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使妓院梨园行当不再须含英咀华以飨顾客,诗酒唱和、辞歌酬答不再成为青楼宴饮中的主要娱乐方式[3],鸦片、肉欲的满足反而成为头等大事。在此时期,书写妓优士绅交往的章回体小说,鲁迅名之为“狭邪小说”[4]。
《海上花列传》出版于1892年,“从来说部所未有”的“穿插藏闪”的结构技巧,书写社会的空间意义,吴语创作的“文学革命”自觉[5]使其不仅被视为“狭邪小说”中的翘楚,甚或成为中国文学跨至“现代”的界标[6]。从此出发,我们将视点单独聚焦于《海上花列传》的空间特征上: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交织的上海租界,作为现代都市欲望书写背景的上海的前身,新型都市文化催生下的长三书寓和公馆功能性上的此消彼长,不断现代化的都市对传统乡村环境无声的压制。空间是“一种人物及故事赖以生存的逻辑边界”[7],相对于占领文本主要篇幅的长三书寓空间,公子贾人们租住的公馆成为文本的夹缝地带,而在公馆中幽居的夫人们化身“阁楼上的疯女人”。她们被动地失去了自己的生活、地位,旧日里霍小玉们暴风雨般的郁愤唏嘘易位,一堂缔约多年以后,夫人们的痛苦只能若隐若现在文本的边角中。与此同时,处于现代性进程中不断野蛮生长的上海,其所包含的属于未来的经济特质,更使它本身成为清末民初具有代表意义的“孤岛”,商品经济和城市娱乐的强势渗入打破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平衡,进入城市的人只能选择重塑自我以适应新的社区习惯,此消彼长,硬币的另一面则是对于传统乡村空间的脱离。
一、 生成方式的空间上海及其现代性
当下学界对于“现代性”的阐释尚没有公认的确定概念。在《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一书中,卡林内斯库以线性时间顺序对“现代性”的概念进行梳理,将之分为“现代性”“先锋派”“颓废”“媚俗艺术”及“后现代主义”5个部分,恰恰说明了以时间为名的“现代性”概念在不同时期实指的不确定性,正如他在文中所说:“现代性因而是一个时间/历史概念,我们用它来指在独一无二的历史现时性中对于现时的理解”。出于术语的模糊性和变动性,“现代性”和另一个略有不同的术语“近代性”并没有得到科学的分辨(事实上由于两个术语的来源都是英文modern,也很难得到彻底地分解)[8],有鉴于此,我们将两个概念取其大略,不再述说它们之间的细节分歧,而统一以“现代性”的社会意义为理论出发点(2)事实上,存在两种两辅相成的“现代性”:即社会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审美现代性倾向于激进的反资产阶级态度。参见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上海:译林出版社2015年版,第42-47页。,也即叶中强所言:“世界工业革命以来,一整套器物、制度与观念的同构与演化。”[9]24
沪城襟江带湖,是天然良港,《南京条约》签订后率先开启了现代化进程——租界空间挤满了西方列强所带来的工业资本,各种物质资料纷至沓来,“声光化电、饮食日用、交通通讯、市政建设、文化娱乐、居住方式等这些西方物质文明,影响到人们的生活方式”[10]。1845年租界正式设立,1854年小刀会起义使租界由华洋分居变为华洋杂居,中国军队禁止驻扎租界,此时上海租界某种意义上已成为“孤岛”。租界因战时中立、市政服务完善、求职机会多,超过一半的上海市民居住其中,劳动力、资本、技术、交通区位的综合效应使上海一跃而成为全国内外贸易中心、金融中心、航运中心和工业中心[11]。经济的骤然腾飞带来的是消费模式及生活方式的改变,当时的四马路已成为上海消费文化的聚合点,而妓业也成为最能代表四马路消费特征的消费方式之一[9]26-30。清代青楼“自乾隆时复苏,愈演愈烈,而南盛于北,东胜于西”[1]207。尤其是到了晚清同光年间,沪上后来居上,更加华糜,“上海青楼之盛,甲于天下。十里洋场,钗光鬓影,几如过江之鲫。每逢国家有变故,而海上北里繁盛,益倍于从前”[12]。太平天国时期刀兵四起,海禁大开,扬州、广东等昔年的风流胜地再不复往日。与此同时,上海开埠后北部租界在1854年由工部局对妓院实行登记并且征税[13],妓院获得了法律意义上的管理和保护。此时妓院本身的职能和性质也已发生了变化:一方面,城市工商业繁荣的背后是农民的破产,因此妓女的来源不再单单是扬州瘦马,而大多是生活所迫者——妓家云集绮颜列肆,吐属俊雅风流隽爽者却鲜有人在,女妓与乐籍制度传统自此完全断开;另一方面,随着封建制度的渐渐坍台,金钱与资本使青楼女子不必承担文人墨客的风骚雅兴,她们更多地承担起作为“商人”而非“商品”的角色定位,也就是说,妓女们就此具有了一定程度的自主性——她们行走于社会伦理秩序、世俗闺阁法度之外,具有相对“自由”的特殊地位。
《海上花列传》是“第一部以19世纪末上海租界的狭邪事迹为故事的长篇说部”[14]。小说近乎真实的书写特点使它与上海构成互文关系:《海上花列传》是想象上海的一种方法,上海又是解读《海上花列传》的基本门径之一。小说以吴语画地为城,上海因此在文本中浮出水面,它的现代意味并不仅仅指涉现代化的器物、建筑,更多地关涉到生活和谋生在兹的人们。成为空间的上海遂被符号化,在她的隐喻下的一切都指向碰撞中的社会文化属性。而租界上海既是韩邦庆创作时的写作环境,同时也是《海上花列传》的文本背景。对于作为文本生成方法的彼时期上海的了解正是产生《海上花列传》“平淡近自然”叙事生成的基础,也是解读它的重要依循。
二、长三书寓与公馆的空间对立
《海上花列传》在描写妓女恩客生活琐事时,一方面是一个明确建构女妓主体性的过程,在书中,妓女奔波于各个欢场,和恩客交往过程中具有相对自由的行动意愿,女性拥有了初步的自我选择权利。另一方面,尽管韩邦庆在创作《海上花列传》的时候并没有刻意勾勒陆家桥附近娼楼花薮的空间景观图像,但是潜藏在文本空间中的上海的记忆、情感等诸多表现物的附着依然熠熠生辉。通过对文本空间煞费苦心的筹划,文中出现过恩客们的工作地点,洪善卿的永昌参店、管账胡竹山的中祥发吕宋票店、账房吴松桥的义大洋行等等;当恩客们走马观花滑过不同书寓时,空间地点转换的描写几达到锱铢必较的地步:“四人离了聚秀堂,出西棋盘街北口,至斜角对过保和楼”[15]9,“出了公羊里,就对门进同安里,穿至西荟芳里口”[15]78,“朴斋听了出来,遂由兆贵里对过同庆里进去,便自直通尚仁里”[15]112,等等。文本空间的划分是一个划界的过程。凭借韩邦庆独特的文本建构方式,我们可以轻易顶针续麻地复述出每一所长三书寓的空间方位,每所建筑之间的位置关系立在文本的显要位置上,但那些坠鞭公子、走马王孙租住的公馆却掩盖在阴影中:通过对后者空间的遮蔽,定位出上海租界在空间分布上的权力关系格局。这种空间结构所指涉的权力关系、意识形态变化是不言而喻的,而在文本中,二者有两次清晰的交叉,对此的分析有助于廓清前述内容。
第一次碰撞出现在第二十三回姚季莼的正室夫人姚奶奶与尚仁里卫霞仙的交锋。姚季莼惧内,叫局后总要提前回公馆(第二十一回),尽管如此,姚奶奶还是搭轿前往尚仁里找姚季莼做的卫霞仙兴师问罪。奶奶是一个“半老佳人,举止大方,装饰入古”[15]186。她首先发难,试图以大妇身份压卫霞仙一头,强迫她不再勾引姚季莼。“霞仙见如此情形,倒不禁哑然失笑”,“正色向姚奶奶朗朗说道”[15]187。卫霞仙的话表明了两个意思:一是“倪开仔堂子做生意,走得进来,总是客人,阿管俚是啥人个家主公”[15]187,即姚卫二人是姚季莼占据主动权,个中责任自当由姚季莼和姚奶奶管不住丈夫来承担;二是“来里该搭堂子里,耐再要想拉得去,耐去问声看,上海夷场阿有该号规矩”[15]187。同前所述,彼时期的上海租界中欢场受法律保护,是一种正当营生,姚奶奶的闹事反倒不合规矩,所以刚好路过的翟掌柜如此言讲:“故是姚奶奶失斟酌哉!倪搭季莼兄也同过几转台面,总算是朋友。姚奶奶到该搭来,季莼兄面浪好像勿好看相。”[15]188这就连姚季莼的脸面也搭进去了,所以姚奶奶最终呜呜咽咽大放悲声,落荒而逃。在这场争锋中,卫霞仙始终气定神闲,姚奶奶则由最初的色厉内荏到大惊失色再到败北而归,讲述人的声音、文中人物的反馈无不充满了王德威所言的“自然主义成分”[16]34:自始至终,在实用主义、拜金主义的光环中,女妓仿佛理所当然地拥有超然地位。其后当卫霞仙和姚季莼再次相遇提及此事,姚季莼无奈承认了自己确实处于两头说好话的境地,这间接说明了一个问题:妓女和自己夫人的地位至少在此时是相同的。在公馆已被剥夺了大部分职能,而只有惧内的人才会回公馆睡觉的租界上海(在文中,同样惧内的只有在一笠园当师爷的马龙池),往日婚姻的家族功能、夫妻之间同荣共辱的关系[17]被金钱彻底击溃。夫人们被困在名为“公馆”的幽闭场所(3)对于“幽闭”这个词,孔颖达疏引《尚书正义》为:“妇人幽闭,闭于宫使不得出也。”,被困在封建伦理道德规训下的陈规戒律中,妓女和嫖客在马路、茶楼等公共场合里渐趋步入“现代”社会,在幽闭的酷刑中夫人们化身为干枯的、不能反抗的符号,在这样纸醉金迷的十里洋场中身负枷锁,沉默地注视一切。
较之,第二次相遇则表现为妥协。姚季莼被迫不能做卫霞仙的生意,“但季莼要巴结生意”,姚奶奶于是代他找了幺二马桂生。第五十六、五十七回姚季莼第一次酒后失检,在马桂生家住了一宿,第二日马桂生就被姚奶奶叫局,下一回书目叫做“甜蜜蜜骗过醋瓶头”。尽管风格完全不同,卫霞仙和马桂生都达到了目的——往日的诗酒唱和已然不再,转化为逢场作戏的绝妙口才。一方面,马桂生看似始终没有掌握主导权,她唯唯诺诺、处处忍让,她明白这位公馆里的夫人需要的无非是一个面子,所以在姚奶奶面前马桂生构建出姚奶奶希望看到的场面:一切都还是传统中国的样子,女妓始终都须仰人鼻息,而她,则代表了宗法制下中国的家族文化正统[18]。另一方面,姚奶奶的选择只能是妥协,“青楼名妓,与当时社会名流和文人绅士有更多的交往自由,其营造的闲暇空间,已建构起明清社会生活史的一个重要侧面”[19],士绅子弟、富贾豪商的都市生活在青楼,他们在此处诗酒唱和、娱乐消闲,进行商业活动、信息交互,“他们见面、恋爱、争吵、分手或重聚的方式一如普通的情人”[16]30。当青楼取代了公馆的所有功能之后,文明进一步被压抑,只有公馆和公馆里的女人,在方寸之地闪转腾挪出往日的故事。
姚奶奶在《海上花列传》中被描述为一个“醋瓶头”,自始至终围绕于她的话语环境都是戏谑和嘲笑。而恰恰又因为她是一个悍妇,在小说文本中诸多男主人公里,她是唯一出现在读者视野中的夫人,至于其他的夫人们呢?选择接受、自暴自弃、就此堕落,不论何种结果,她们也分明已经不再适应极速走在近代化进程中的租界上海,只好以公馆为界,既是牢笼也是庇护所,湮没于时代之中。“妓女比之家庭妇女则比较上反觉得受教育为高,他们比较上较能独立生活,更较为熟悉于男子社会。其实在古代中国社会中,她们才可算是唯一的自由女性。”[20]毫无疑问,上海裹挟而至的中西观念的共同体中,现代性的文化输入确实使女妓建构起较之正妻大妇更为健全的人格关系,但当林语堂先生在《妓女与妾》中轻描淡写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只看到了社会-观念意义上的所谓进化,并没有怀着人文主义情怀看待被压抑的、被禁锢的彼岸世界。或许是无心插柳,韩邦庆在《海上花列传》中微带恶意地描写出这样一个小人物,结果姚奶奶形象极尽锋芒地指向了衰颓文明的实质。
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往日文人骚客于青楼邀客侑觞、尊罍丝管,在彼时期文化交织、众声喧哗的上海,文化的变故与更迭时时发生的19世纪末的上海,公子贾人唯知挥金而风月不再。与其说公馆与书寓间的关系是此消彼长,毋宁说是公馆在时代变更下的迅速坍塌。代表了传统文化某些侧面的公馆陷落、资本重构下的青楼平地而起,当我们将眼光指征向整个时代,彼时中国风月繁华之所无不在资本控制下,依旧沉醉于月夕花朝鬓影流香的人们似乎还未感觉到时代车轮滚滚而来的轰鸣,上海作为古老中国的某种指征,公馆和书寓也有了非同寻常的历史意义——当前浪已经奔腾而来,波涛也将即刻席卷而至。我们在慢慢成为社会边缘、淡出观者视角的幽闭之地,才得以瞥见文明在此时已经开始了让步。
三、现代性空间下的文化认同
《海上花列传》中分别出现了三个主线人物,他们出入于租界上海之中,而被上海截然不同地对待。针对这三个人物的分析有助于我们了解沐浴在现代性荣光下的上海与旧中国版图其他地域截然不同的空间气质。
首先是赵朴斋一家人,他们是全书旗帜鲜明书写乡下人进城之后主动依附都市的典型。赵朴斋是一个以消费性为导向的迷失自我的城市贫民形象,这个形象的不断上场使我们注意到两个有趣的细节。第一个细节是,与文本时间相对应,在线性的叙事时间中身无分文的赵朴斋的行踪。《海上花列传》中,赵朴斋第一回即已登场,由他舅舅引入了上海的狭邪大潮,而后,每次舅舅遇到他或得知他的消息都变得更加不堪,做不起陆秀宝(幺二),去王阿二(野鸡),又被流氓打伤(第十七回),再次偶遇时,洪善卿发觉他长衫都当了,于是派人送他回家,赵朴斋逃掉,开始做拉车生意(第二十八回)。这是在赵二宝携母来沪之前赵朴斋的经历。作者意味深长地不断描写赵朴斋每况愈下的着装,从最初“穿着月白竹布箭衣”[15]3到“只穿一件稀破的二蓝洋布短袄”[15]199,再到“脸上沾染几搭乌煤,两边鬓发长至寸许,身穿七拼八补的短衫裤,……俨然像乞丐一般”[15]241,显然此时赵朴斋在上海接近于走途无路,上海已经不再能给他带来任何物质享受,他所贪恋的不是女妓、鸦片或是饭局,而是这座城市以及城市空间繁华奢靡的现代气息。作者借赵二宝的话说出了赵朴斋不愿回乡下的原因:“我说俚定归是舍勿得上海,拉仔个东洋车,东望望,西望望,开心得来!”[15]241(第二十九回)第二个细节则是赵母洪氏的宽容和赵二宝的迅速归附。第二十九回中,赵二宝同赵母初次到沪,面对衣衫褴褛的赵朴斋,母女俩似乎全然没有责备的意思。赵母先是心疼,“洪氏猛吃一惊,顿足大哭道:‘我倪子为啥实概个嘎!’刚哭出一声,气哽喉咙,几乎仰跌”,“洪氏、二宝着实埋冤一顿”[15]241。紧接着“洪氏忽有些怜惜之心,不复责备,转向秀英、二宝计议回家”[15]241。紧接着二宝被施瑞生撩拨,全家搬至清和坊,以至于赵二宝主动开始贴条子做生意,洪氏都表示了默许——洪善卿赶去清和坊叱问洪氏这一情节(第三十一回)中,尽管洪氏柔懦无能,可也并非毫无主见。洪氏的言行说明她是希望留在上海的:“洪氏顿住口,踌躇道:‘转去是最好哉;不过有仔盘费末,……到仔乡下,屋里向大半年个柴木油盐一点点无拨,故末搭啥人去商量嘎?’”[15]257同时,赵二宝开书寓之后,也迅速融入了职业生涯中:“赵二宝一落堂子,生意兴隆,接二连三的碰和吃酒,做得十分兴头。”[15]290(第三十五回)“其实赵二宝时髦已甚,每晚碰和吃酒,不止一台,……”[15]312(第三十七回)方式不同,但他们的目的都很一致:不论从事什么行业,都要留在都市里。我们从洪善卿训斥洪氏一节中可以看出,女妓这个行业在当时依旧是有损名声的。尽管如此,一家三口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了惊人的默契。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论及的乡下人珍视泥土被现代化都市轻而易举化解,在乡土/都市而非狭邪/都市的二元对立中,乡农所饱有的回归田土的古老信仰遂跌落进尘埃里。
可与赵朴斋一家人构成对比关系的还有张小村。赵朴斋的身影贯穿《海上花列传》始终,可说是小说结构所有故事的一个重大线索,而张小村的存在则贯穿赵朴斋始终,扮演了同赵朴斋相反的角色。他最初同赵朴斋一同自苏州来沪寻生意,赵朴斋迷上幺二陆秀宝,张小村则流连花烟间,赵朴斋衣食无着干了东洋车,张小村则一直在米行顺风顺水。在张小村身上,作者寄予了他从乡下“逆袭”都市、被都市接纳的重任:生活不好不坏,却也没有堕入最底层,在上海这样节奏快速的现代化都市里,凭借一己之力站稳脚跟,而不是同赵朴斋一样被动地沉沦其中。但在细节中,我们依旧可以看出副作用来:赵朴斋落魄之时,他曾出语奚落,到第三十七回赵朴斋衣着光鲜再次出现,张小村的反应是“有心依附,举手招呼”[15]311,俨然成为一个势利鬼。赵朴斋和张小村之间境况强烈的对照之下,他们不约而同被现代社会侵蚀。显然,不论生存方式好坏,乡下人进城都表现出了不同程度的不耐受。当逐利成为生存环境的最显著界标,乡土伦理秩序也即不堪承受生活之重。以往依靠宗法制链接而生的亲密的人际关系被极端个人主义、极端商品拜物教的物质关系取代。不管主动被动,他们都成功建构起对现代都市的文化认同,与之对应的则是对之前所服膺的传统伦理观念的放弃。
两个乡下人境遇截然相反,在他们不同程度地对都市依附、又被都市排斥的过程中,他们身处其中,不断被规训。不难发现,韩邦庆正是用赵朴斋和张小村给出了城乡对立下小人物生存的极限阈值,他们平行生存却同声唱和,通过亲历的感受性接橥现代上海的城市品格。
四、 结语
韩邦庆声言他的创作目的为“此书为劝戒而作,其形容尽致处,如见其人,如闻其声。阅者深味其言,更返观风月场中,自当厌弃嫉恶之不暇矣”[15]1。时过境迁,我们已远离彼时期的社会语境,无法判断其是否是文人惯用的“劝百讽一”模式,在他意味深长的春秋笔法之下,我们透过文本,足以发现其中巨大的阐释可能性。不论是书寓功能性的极大生长还是乡下人进城无奈地妥协,我们都能发现小说已脱离了传统狭邪小说指征的乡土/狭邪之间的对立,而深入到了现代性都市对人的改造。商品经济的急速发展造成了金钱本位价值观的兴起,基于小农经济和乡土中国的道德观念在金钱面前土崩瓦解,而以儒家教化伦理为主导的正统社会传统也在与西方资本主义接触之后逐渐成为同王朝没落同期迸发的悠远余音。这种对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双重统治无疑也是我们“借镜”以观当下的一条路径。这正是《海上花列传》在都市空间书写层面上的现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