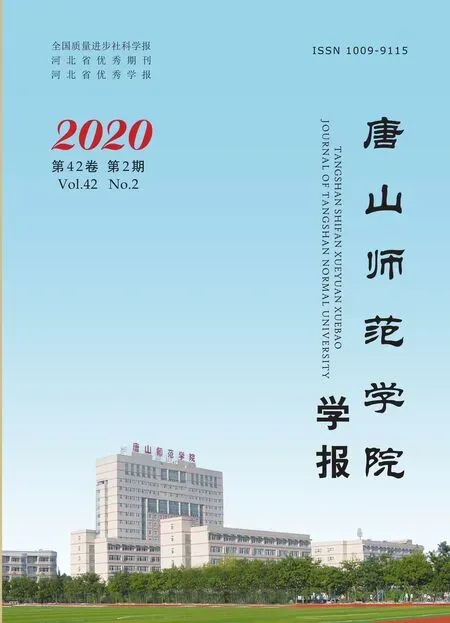论当代女作家的“超性别意识”写作观
刘志慧
论当代女作家的“超性别意识”写作观
刘志慧
(阜阳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阜阳 236037)
“超性别意识”只是一种理论预设,目前来讲是不可能实现的。然而,当代女作家在接受写作观调查时依然表示向往“超性别意识”写作。究其原因,可以看到现实处境迫使大多数的女性作家不一定向往站在男性角度进行写作,却不希望被读者认出自己的女性作者身份,甚至有些女作家会刻意利用男性化写作来遮掩自己的女性意识。
女性作家;“超性别意识”;写作观
尽管女性写作(这里指女性作家的创作)自古就有,然而对于女性写作的研究却严重落后于作家创作。我国女性文学的研究是伴随着五四运动中女性意识的觉醒,以及国外女权主义思想的西渐东入才发展起来的。在20世纪70年代末,由于改革开放的提出涉及女性解放问题,故女性写作蓬勃发展,女性文学研究也因此成为我国文学研究中的重要论题。但是,相对于20世纪女性作家的被关注度及研究成果而言,学界对当代女性作家的性别观及写作观的理解较为薄弱与片面。同时,在“最近四五年,人们开始用非常认真的态度重新讨论中国社会的性别不平等的问题或性别观念的问题,可以称为当代中国继前两次之后关注性别问题的第三次热潮”[1]。因此,张莉的《当代六十七位新锐女作家的女性写作观调查》[2](以下简称为《调查》)将当代文坛最为活跃、新锐的67位女性作家作为特殊而重要的群体,以问卷调查的形式对她们展开性别观及写作观的大讨论,并且得到诸多读者与学者的关注以及众多微信公众号的转载,也是时势使然。在《调查》中,多位女作家流露出对“超性别意识”写作观的向往,她们几乎都倾向于不分性别、忘记性别、超越性别的写作姿态,认为女性首先是“人”,然后才是“女人”。“超性别意识”被提出于20世纪末期,学术界对此展开过广泛讨论。本文以当代女作家的写作观为切入点,对这一概念及相关问题做进一步的分析。
一、关于“超性别意识”
在讨论“超性别意识”之前,有必要了解一下性别意识。“性别意识是自我意识的重要内容之一”[3],它应该包括男性意识和女性意识。但在仍是父权与夫权当道的当代社会,性别意识常常指的是女性意识,因为“男性意识是显在的,而女性意识却是被压抑的,不存在需要张扬男性意识的问题”[4]。可能就像男作家张楚所猜测的一般,“女作家们……的性别意识就像‘红字’般烙在她们的灵魂里”[5]。所以,可以合理猜测《调查》中女性作家回答里的“性别意识”即“女性意识”。
“超性别意识”的提出最早见于60后作家陈染的《超性别意识与我的创作》,她在其中指出:无论是对于爱情、看待一个人还是回到艺术上的写作,都应该采取“超性别意识”的观念[6]。在她看来,真正的爱情是超越性别之上的,异性爱掺杂着虚伪、诡计、繁衍等复杂的目的,超性别的爱情才是无功利的艺术;在看待一个人时应该脱离性别去欣赏别人,这样才不至于肤浅;在写作方面,更是要贯穿超性别意识,一个优秀的作家是不会被性别所迷惑的。从陈染的表达中可以看到,所谓“超性别意识”就是超越个体的性别视角来关注社会、对待生活[7]。也就是说,20多年前的“超性别意识”应该是“在保留现有看法的基础上,萌生出更多的性别意识观念,作为传统性别意识的一个补充”[8],是指同时拥有男性意识和女性意识的“双性意识”观。
从《调查》中可以看到,“超性别意识”这一说法至今仍被沿用,但是其涵义是否一致却是值得商榷的。从她们“遮掩性别”“无性别写作”“走出小女子的‘小’”“中性色彩匿名写作”“超越单一性别”“走出女性性别”“去性别化”“模糊化性别”“不分性别”“忘记性别”“跨越性别”这些语词中似乎可以窥得,在当代女作家这里,“超性别意识”不再是追求“双性意识”,而是力求躲避、忘记自己的“女性意识”。正如蒋方舟在回答“理想的女性写作是什么样子”时提出的:“我向往女性的写作是人性的。她们走出女性性别,也走出性别压迫。”[2]其实很好理解,因为当代社会中“性别压迫”似乎更多地发生在女性身上。比如,彭思萌在《调查》中提到的“Me Too”运动席卷中国时,蒋方舟、易小荷、春树、王敖等人曝光的性骚扰、性侵事件[2]。性别不平等的现象依然暗流涌现,创作界如是。以至于当代女作家在意识到自身的性别意识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她们的创作,天然地出现在她们作品的各个方面时,她们出于趋利避害的心理,会选择遮掩、模糊、忘记、逃避自己的女性意识。她们不一定向往站在男性的角度进行创作,但她们大多数不希望被读者看出自己作品中的女性意识,甚至有些女作家会刻意利用男性化写作来遮掩自己的女性意识。
因此,当代女作家向往的“超性别意识”写作观是希望在自己的写作中超越、隐藏自己的女性意识。
二、“超性别意识”写作是否可能
“超性别意识”写作真的可能吗?它的现实可操作性又有多大?其实,这一概念甫一提出,就激发文学界的热烈讨论。有学者从男女双向共建、和谐发展的角度出发对此表示肯定,有学者则针对陈染的言论表示质疑。丁帆就曾撰文讨论“超性别意识”观,他在文中斥责了陈染的观点。陈染认为:“人类有权利按自身的心理倾向和构造来选择自己的爱情。这才是真正的人道主义!这才是真正符合人性的东西!异性爱霸权地位终将崩溃,从废墟上将升起超性别意识!”[6]丁帆将此称为“女权主义歧路的悲哀”[9,p125]。可以看出,丁帆主要是就陈染在爱情这一层面上的“超性别意识”做出反击的,他认为“五四妇女解放的回声虽然响彻20世纪,却远远没有使得女性获得在爱情中的平等地位”。同时,无论是男性作家还是女性作家笔下的女性都没有真正获得话语权的解放,只不过是男性作家毫不遮掩地直接以同情的笔触描写女性,女性作家是一种隐性的男权视角下的女权意识罢了。因此,在这样一个封建情绪浓烈的男权主导的国家中,不去唤醒女性该有的性别意识和权力,却奢谈什么“超性别意识”的情感,无疑是女权主义运动的倒退,起着完全相反的作用[9,p126]。
1997年,降红燕在思考“超性别意识”时就探讨过这个问题。她认为陈染提出和铁凝践行的所谓“超性别意识”观“似乎是超越男性性别和女性性别,但实际上主要是偏重超越女性性别”。因为这是女性作家提出,为女性研究者肯定,并针对女性文学而言的。同时,她指出在中国目前的社会环境中,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物质的解放和经济权益的保障并不意味着女性意识的高涨和文化心理的提高,相反,当前而言女性意识不是张扬得超越了,而是觉醒得远远不足。在很多人的女性意识还没被唤醒时就谈论超越女性意识有些太过匆忙和简单[7]。降红燕的这一说法和丁帆的责问有异曲同工之处,将丁帆对于爱情中“超性别意识”的看法对等到写作这一层面上来也是如此。在大多数女性读者还不知女性意识为何物,还在精神上附庸男人生活时,作家就在写作中贯穿“超性别意识”是不是有些行将过急?另一方面,降红燕提出在男女关系不和谐的今天,应该倡导“双性文化”和“超性别意识”,至少在女性文学甚至整个文学未来的发展中,“超性别意识”应该拥有姓名。
2010年,吴春直接以“超性别意识写作的现实可能性”为题深入分析“超性别意识”写作的现实可操作性。她在阐释“超性别意识”概念、分析其提出的背景的基础上,表明:“无论是创作还是批评,‘超性别意识’都处于纯理论层面,其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可操作性还待进一步探讨。”[10]就拿当代女作家来说,她们在自我写作中真的能完全剥离出自己作为一个女性的现实存在吗?在这一问题上,乔叶的态度可能更加诚恳。她在重新浏览自己的小说之前坚称她在写作时“不从性别来考虑人物”,但之后她意识到“号称不从性别来考虑人物”竟然是她“试图自欺欺人的谎言”。“生而为女人,这就是我的命。我的写作,也必定在这个命里面。”[2]
关于“超性别意识”写作是否可能,丁帆和降红燕从性别状况的视角出发,认为在传统力量过于强大的今天,这一提法不合时宜,并且在有用性和实效性上对其进行了批评。学者吴春并没有批评“超性别意识”观念,只是在实践层面上对其表示质疑。笔者认为,“超性别意识”只是一种理论预设,是当代女作家对性别和谐的一种渴望。就实际情况而言,“超性别意识”写作目前来讲是不可能的。正如桑德拉·吉尔伯特所说:一个作者最后书写成的,无论是有意识地还是无意识地,都构成他个人的整体,如果女性作家是受到作为女性的文化教育成长起来的,那么她的性别特征是不可能同她的文学创作能力分离开的。同时,他认为这世上只有很小一部分生理异常的女性没有被作为女性教育成人[11]。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当代女作家大概也是明白“超性别意识”写作的不现实性,不然也不会用“向往”“理想”这样带有愿景式的语言。既是如此,那她们又为何提出“超性别意识”写作,渴望拥有“超性别意识”写作观呢?
三、“超性别意识”写作提出的缘由
“超性别意识”提出的20余年里,即使在实践层面上没有太大发展,也有众多当代女性作家对此表示渴望。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首先,孙频的自白或许能为我们提供一种解释:“这个社会整体上表现出对女性主义的一种压制和歧视……有时候你表达的东西越真实越会被诟病,一个女性作家的写作尤其容易被诟病,你写疼痛会被诟病是狭隘,你写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自我分裂会被诟病为黑化女性,不美不善不是正常人的生活。有些女作家倘若敢写得私人化一点,那便需要很大的勇气和强大的内心……这就是为什么几乎所有的女作家都不愿意被扣上女性主义的帽子,因为在目前的价值体系中,这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甚至代表着可笑与羞耻。”[12]她提出自己在最初写作的时候的确拥有一种自觉的女性意识,但在之后的写作中会有意压抑这种意识,使之变淡,变成了无性别写作,不让读者看出自己的女性意识。现实社会中的处境让女作家们不敢肆意释放自己的女性意识,面对众人的诟病和揣测,她们只能选择隐藏、搁置自己的性别意识,“超性别意识”写作观的向往或许是她们突破困境的一种努力。
其次,当代新锐女作家大多是独生子女政策的产物,她们从小接受的是男女平等的思想教育,“自小经受的性别教育,是男生女生的无差别教育:你们就该毫无区别长大成毫无区别的独立个体……男的能做的女的也能做”[2]。她们和男性作家一样,获得开放且持续的学习资源,并在其中形成认知与思考世界的方式。也就是说,大多数当代女作家从小被灌输的是“性别无差别意识”,她们抱着这样的女性认知进入社会,投入创作。但现实社会是怎样的呢,它是否也对女性如此宽容与看重?周李立的个人经历或许是这一部分女作家的真实写照。“社会对女性从不平等也不宽容,这让我有不明真相跌入陷阱的惶惑。所幸年岁渐长,对家庭或工作中女性跨越不了的性别藩篱也被动接受了。开始写作后,这被动接受的心态却很难平和。”[2]当她们发现从小接受的“性别无差别意识”这套规则在社会无法畅通时,逃避、忘记、渴望超越自己的女性意识自然就成了她们写作时的一种选择了。
再次,在写作中“一些写作特质,比如细腻、繁复、幽微,很多时候可能会被人不假思索地归为‘女性化’,而与之相反,粗犷、简练、宽阔,似乎就专属于男性”[2]。这其实是一种将男性女性对立的粗暴分裂,它将性别概括为分离的两面,却忽视了其中复杂丰富的个人。即使细腻、婉约、精巧是对女性写作的一种赞美,“但同时也让女性作家警惕,‘这是否在说我的写作,格局不够大,稍欠力量?’”[12]因为在男权社会的今天,男性标准仍然是主流追求,一些女作家不可避免地将女性天然具备的细腻、柔软、善感等能力认同为一把双刃剑。马金莲就认为:“女性的敏锐以及细腻,限制了女性对更为辽阔外界的想象和感知,女性文字难免缺乏剑气和豪气,恰如绣花功夫足够,却鲜有仗剑天涯的豪气和大开大合的杀伐决断。”所以,她“尽量让自己走出小女子的‘小’,学习借鉴男性作家普遍拥有的那种‘大’,大眼光,大境界,大情怀”[2]。身处于男性权力的社会中,“超越女性意识”去迎合大众即主流的追求,可能是一部分女作家无奈的潜意识之举。毕竟在“女性写作”概念盛行而“男性写作”并不与之对等的现今,有几个女作家愿意被标签化呢?
四、结语
当代女作家“超性别意识”写作观的本质其实就是超越自己的女性意识,在男性主导的现今社会,即使知道超越自身的性别意识是不太可能实现的,通过遮掩自己的性别也可以使她们规避伤害、拒绝窥视、保护自己。这也许能够解决当代女性作家一时的问题,可是性别公正问题会一直存在,要如何正视呢?在张莉另一篇关于男性作家性别观调查的文章中,提出相比于女性作家在面对两性差异时向往搁置、不解决的“超性别意识”观,男性作家则更坦诚面对两性差异,努力寻求尊重、平等的解决方法。我们承认正视性别公正问题对于在两性关系中处于优势地位的男性来说稍显容易,但是“性别观念上的自觉是同时针对男人和女人的,而性别公正的可能性也需要女人和男人的共同努力”[1]。如果当代女作家一直以逃避、遮掩、忘记的态度选择“超性别意识”写作的话,性别公正这个问题的解决可能遥遥无期。
[1] 贺桂梅.性,性别与文学创作中的观念观自觉[J].天涯, 2019,(4):13-20.
[2]张莉.当代六十七位新锐女作家的女性写作观调查[J].南方文坛,2019,(2):109-127.
[3] 百度百科.性别意识[EB/OL].https://baike.baidu.com/ Item/性别意识/5724902?fr=aladdin,2019-04-16.
[4] 陈骏涛.关于女性写作悖论的话题[J].山花,1999,(4): 90-94.
[5]张莉.当代六十位新锐男作家的性别观调查[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2):19-64.
[6]陈染.超性别意识与我的创作[J].钟山,1994,(6):105- 107.
[7]降红燕.关于“超性别意识”的思考[J].文艺争鸣,1997, (5):25-31.
[8]郑艳蓉.现代性与性别再定义——关于超性别意识的思考[J].青年与社会,2014,(25):304-305.
[9]丁帆.“女权主义”的悲哀——与陈染商榷“超性别意识”[A].张清华.中国新时期女性文学研究资料[C].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
[10]吴春.超性别意识写作的现实可能性[J].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0,(3):58-60.
[11] Gilbert Sandra. Feminist Criticism in the University[A]. Gerald Graff & Gibbons, Reginald eds. Criticism in the University[C].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85.
[12] 张莉.她们与我们时代的女性写作——三十四位中国当代新锐女作家的同题回答[J].青年文学,2018,(11): 5-30.
On the Writing View of "Super Gender Consciousness" of Contemporary Female Writers
LIU Zhi-hui
(College of Arts, Fuyang Normal University, Fuyang 236037, China)
“Super gender consciousness” is only a theoretical presupposition, which is impossible to realize at present. However, contemporary female writers still yearn for “super gender consciousness” writing in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ir writing view. The reason is that the real situation forces most female writers to write from a male point of view which they do not want to. And they do not want to be recognized by readers as female authors either. Even some female writers will deliberately take advantage of masculinity to cover their female consciousness.
female writers; “super gender consciousness”; writing view
I206.7
A
1009-9115(2020)02-0041-04
10.3969/j.issn.1009-9115.2020.02.008
阜阳师范大学、阜阳市校地合作平台提升项目(xdhzpt201705)
2019-10-11
2019-12-07
刘志慧(1994-),女,安徽马鞍山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责任编辑、校对:任海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