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壶祭祀类自名简论
赵谚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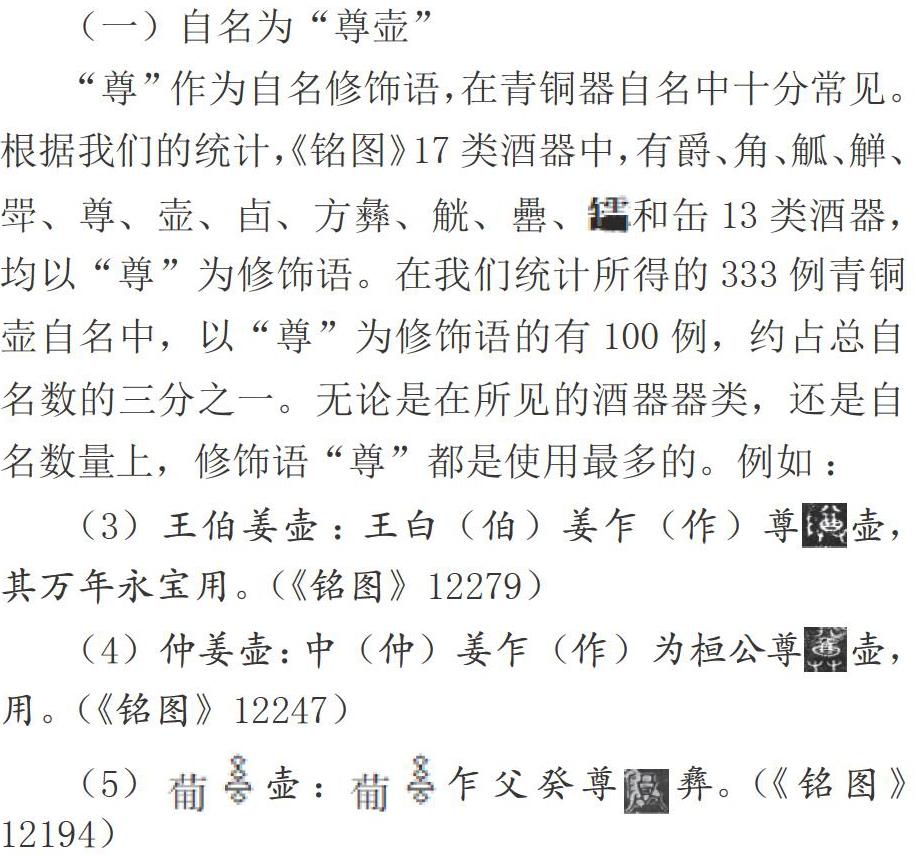


摘 要:青铜器的自名即器物在铭文中的自称,可以分析为修饰语和器名两部分。青铜器自名,尤其是自名修饰语,反映了有关器物功用、质地、形制等方面的关键信息。青铜壶是商周时期用于宗庙祭祀的重要礼器。其铭文中的自名“尊壶”“宗壶”“禋壶”“祠壶”和“旅壶”,反映了青铜壶的主要功用是在于祭祀。修饰语“尊”常与表示祭祀相关的青铜器共名“彝”组合,而“宗”则与“宗庙”“宗法制”相关。“禋壶”即“禋祀”之壶。“祠”作为修饰语,修饰共名“器”,义同“祭”和“祀”,泛指祭祀。青铜壶自名为“旅壶”,且铭文中有明确的祭祀对象,可知此器为祭祀祖先所作。
关键词:青铜壶;祭祀类自名;自名修饰语
一、引言
青铜器的自名,即青铜器铭文所记录的该器的自称。青铜器的自名可以分析为两部分:修饰语和器名。例如:
(1)彭伯壶铭文:彭白(伯)自乍(作)醴壶,其子子孙孙永宝用之。(《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12321)①
(2)仲南父壶铭文:中(仲)南父乍(作)尊壶,其迈(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12329)
彭伯壶自称为“醴壶”,则其以“醴壶”为自名,其中,“醴”是自名修饰语,“壶”是自名器名。同理,仲南父壶自名为“尊壶”,“尊”为修饰语,“壶”为器名。“器名”又有共名和专名之别。王国维在《说彝》一文中指出:“尊、彝皆礼器之总名也。古人作器,皆云‘作宝尊彝,或云‘作宝尊,或云‘作宝彝。然尊有大共名之尊(礼器全部),有小共名之尊(壶、卣、罍等总称),又有专名之尊(盛酒器之侈口者)。彝则为共名,而非专名。”[1](P73)简言之,“共名”即不同形制的器类所共享的名称。如共名“彝”并不特指某一种器类,不同器类如壶、卣、罍、尊、斝等,皆自称为“彝”。许慎《说文解字·糸部》:“彝,宗庙常器也。”可见,彝是古代青铜祭器的通称。“专名”是相对于共名而言的,它是具体某一种器类的专称,如“壶”“卣”“锺”等都是青铜器器类专名。
青铜器自名中的修饰语或说明器物特征,如宝卣(《铭图》12741)自名“小郁彝”之“小”;或提示器物用途,如彭伯壶(《铭图》12321)自名“醴壶”之“醴”;或强调器物价值,如伯卣(《铭图》12887)自名“宝彝”之“宝”等。而同一类器物的器名也并非全然一致,多有异称、连用等现象。青铜器自名从不同的方面补充了有关器物的多种相关信息,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据此,我们对吴镇烽先生的《商周青銅器铭文暨图像集成》[2](以下简称《铭图》)及《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续编》[3](以下简称《铭续》)中所收录的551件商周青铜壶的自名情况进行了整理和统计。根据我们的统计,在551件青铜壶中,333件有自名,282件有修饰语。这333件青铜壶的自名形式丰富多样。其中,反映器物祭祀功用的自名主要有“尊壶”“宗壶”“禋壶”“祠壶”和“旅壶”。下面,我们就对青铜壶祭祀类的自名现象进行具体分析。
二、“尊壶”和“宗壶”
(一)自名为“尊壶”
“尊”作为自名修饰语,在青铜器自名中十分常见。根据我们的统计,《铭图》17类酒器中,有爵、角、觚、觯、斝、尊、壶、卣、方彝、觥、罍、和缶13类酒器,均以“尊”为修饰语。在我们统计所得的333例青铜壶自名中,以“尊”为修饰语的有100例,约占总自名数的三分之一。无论是在所见的酒器器类,还是自名数量上,修饰语“尊”都是使用最多的。例如:
(3)王伯姜壶:王白(伯)姜乍(作)尊壶,其万年永宝用。(《铭图》12279)
(4)仲姜壶:中(仲)姜乍(作)为桓公尊壶,用。(《铭图》12247)
(5)壶:乍父癸尊彝。(《铭图》12194)
关于“尊”作为修饰语的意义,学界众说纷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
1.释为“宗”
清人徐同柏认为:“尊当读为宗。宗,尊也。”[4](P290)
2.表示“陈列”
唐兰先生指出,凡称为“尊”的器,是指在行礼时放置在一定的位置的器。如“尊鼎”意为陈设用的鼎[5](P7)。黄盛璋同意“陈列说”,并认为不搬动的尊器即等于宝器,后来“不移动”义逐渐弱化,转变为表示“尊贵”[6](P78)。屈万里也认同这一观点:“尊,陈酒或置酒祭祀也。”[7](P433)
3.表示“尊贵”
张亚初认为:“(尊)字义与宝相近,是尊贵、高贵的意思。‘尊字作双手捧抬酒尊之形,从字形结构讲,就有‘尊‘高之意。尊彝之‘尊往往有作从‘阜的。从‘阜的‘尊字‘升高之义更为明显。”[8](P275)
4.表示“祭祀、荐献”
徐正考认为,青铜器器名前的“尊”是充当动词性修饰语,有奉献、登进之意[9](P75)。陈英杰则指出,“尊”不仅表示陈酒祭祀,也同样有荐献义:“‘尊之意义有二:置酒而祭;荐献。”[10](P316)
《说文解字·酋部》:“尊,酒器也。从酋、廾以奉之。《周礼》六尊:牺尊、象尊、著尊、壶尊、太尊、山尊,以待祭祀宾客之礼。”在甲骨文、金文中,修饰语“尊”的字形从廾从酉,或省或增“阜”。从字形来看,像两手抬高酒罐进献之形。此外,在金文铭文中,“尊”就有“祭祀”义。比如,四祀邲其卣铭文:“尊文武帝乙宜,才(在)召大厅。”(《铭图》12429)再如,作册夨令簋铭文:“用乍(作)丁公宝尊簋,用尊事于皇宗,用卿(飨)王逆复。”(《铭图》05353)因此,我们认为,陈英杰先生的观点可从,“尊”首先应从字形出发解释其初始义。作为修饰语,“尊”常与表祭祀相关的青铜器共名“彝”组合,强调了作器者所铸之器用于祭祀的功能。所谓“尊壶”,即用为祭祀之壶。
(二)自名为“宗壶”
根据我们的统计,修饰语“宗”见于爵、觚、觯、尊、壶、卣、方彝、觥、罍、10类青铜酒器的自名中。“宗”往往单独或与“宝”“尊”等修饰词组合,共同修饰共名“彝”。在青铜壶中,“宗”作为修饰语的共有5例,具体信息如表1所示:
可以看出,表1中的五例青铜壶均自名为“宗彝”。曾姬无卹壶甲、乙两例又称“尊壶”。从形制来看,这五例情铜器均为方壶,而且同属于春秋战国时期。
《说文解字·宀部》:“宗,尊祖庙也。从宀从示。”在甲骨文中,“宗”作“”(《殷虚书契前编》卷一·四五·四),已作“宗庙”解,“宀像屋宇,示为祭事,屋下设祭,是必宗庙然矣”[11](P865)。李孝定指出:“示象神主,宀象宗庙,宗即藏主之地也。”[12](P2479)传世文献中也有释“宗”为宗庙的辞例。《周礼·春官·肆师》:“凡师甸,用牲于社宗,则为位。”杜子春云:“宗谓宗庙。”
商周壶自名中的“宗”修饰共名“彝”,组成自名格式“宗彝”。关于“宗彝”的释义,学界也曾有过讨论。龚自珍云:“宗者,宗庙也……宗彝也者,宗庙之器……宗彝者何?古之祭器也。”[13](P261)龚氏将“宗彝”之“宗”释为“宗庙”,将“宗彝”释为宗庙之器。陈梦家指出,共名“彝”或器名前的修饰语“宗”和“将”均表示一定意义,“宗彝”和“将彝”作为“有限度的共名”,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组合:“宗彝”是盛酒器的卣、尊、方彝和壶;金文中的“将彝”之“将”从“鼎”,“将彝”多指烹饪器[14](P70)。杜廼松认为,“宗”为“宗庙”义,并指出金文自名中的宗彝,“应与统治阶级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和祖先崇拜观念而建立的宗法制度联系起来。”[15](P44)陈英杰先生进一步论述说:“修饰器名的‘宗是指大宗和大宗之庙……祭器都会放在宗庙里使用,标明的原因是这些器物要放在大宗之庙里使用。”[10](P288)
甲骨文和金文中的“宗”为会意字,从宀从示,其字形和意义也一直沿袭下来。因此,将青铜酒器自名中的修饰语“宗”释为“宗庙”是颇有道理的,“宗彝”即用于宗庙之彝器。在先秦时期,以血缘亲疏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制度具有很大影响力,“宗子(嫡长子)”和“庶子”有别,“小宗”和“大宗(有始祖者)”亦有别。青铜器壶自名特以修饰词“宗”修饰和强调器名,我们也可以根据其自名推断出该器物是与古代宗法宗庙祭祀有着密切关联的。
三、“禋壶”和“祠器”
(一)自名为“禋壶”
修饰语“禋”仅有一例,见于“陈喜壶”,如下:
(6)陈喜壶:陈喜再立(涖)事岁,月己酉,为左(佐)大族,台(以)寺(持)民选,宗词客敬为壶九。(《铭图》12400)
例(6)中的修饰语“”字迹模糊。马承源先生的摹本为“”,并将其释为“尊”:“当为的别体,即尊字”[16](P45)。于省吾等改释为“”:“即陻之繁文,从阜从又垔声,典籍中也作堙,与形不同。陻为禋之借字,汉华岳碑以‘堙埋为‘禋埋……壶之称‘禋壶,犹蔡侯盘称‘禋盘。‘宗祠客敢为禋壶九者,是说陈氏宗祠之客籍铸工敢为禋祭之壶九器也。”[17](P35)张颔则认同马承源的观点,将其释为“”,他指出,该字字形左半“”为阜不可割裂,隶定的时候不能转移到字形“”的下面,而“”为卣字,与“酉”音通而意近,可通假[18](P40)。我们认为,张颔先生的解释略显牵强,“”字与金文中常见的“”的字形并不相近。因此,于省吾先生释“禋”可从。
《说文解字·示部》:“禋,洁祀也。一曰精意以享为禋。从示垔声。”《周礼·春官·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郑玄注:“禋之言烟。周人尚臭,烟气之臭闻者。”可见,“禋”为祭名,是一种烧火升烟以祭天的祭祀方式。此外,“禋”字亦可泛指祭祀。《诗经·大雅·生民》:“克禋克祀,以弗无子。”《广韵·真韵》:“禋,祭也。”史墙盘铭文:“义(宜)其禋祀。”(《铭图》14541)由此看来,陈喜壶自名为“禋壶”,也应是泛指“用于祭祀之壶”。
(二)自名为“祠器”
自名修饰语“祠”修饰共名“器”的情况,仅见于两例,皆出自春秋晚期的“赵孟庎壶”:
(7)赵孟庎壶:禺(遇)邗王于黄池,为赵孟庎(介)邗王之惕(锡)金,台(以)为祠器。(《铭图》12365)
(8)赵孟庎壶:禺(遇)邗王于黄池,为赵孟庎(介)邗王之惕(锡)金,台(以)为祠器。(《铭图》12366)
《尔雅·释天》:“春祭曰祠。”《说文解字·示部》:“祠,春祭曰祠。品物少,多文辞也。从示,司声。仲春之月,祠不用牺牲,用圭璧及皮币。”《诗经·小雅·天保》:“禴祠烝尝,于公先王。”毛传:“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尝,冬曰烝。”《周礼·春官·宗伯》:“以肆献祼享先王,以馈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礿夏享先王,以尝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可见,上述文献中的“祠”均为祭名,特指春祭。
在古代文献中,“祠”亦可释为“祭”或“祀”。《尔雅·释诂》:“祠,祭也。”《尚书·伊训》:“伊尹祠于先王。”唐代陆德明释文:“祠,祭也。”《诗经·大雅·生民》:“克禋克祀,以弗无子。”毛传:“以大牢祠于郊禖。”陆德明释文:“祠,本亦作祀。”同时,这里的“禋”与“祀”对举。
罗振玉云:“《尔雅·释天》:‘商曰祀……是商称年曰祀,又曰司也。司即祠字……在商时始殆以祠与祀为祭之总名。周始以祠为春祭之名。”[19](P53)在金文中,“祠”又作动词,义同“祀”。如战国中期壶铭文:“卿(飨)祀先王……敬明新坠(地),雨(雩)祠先王。”(《铭图》12454)其中的“祀”和“祠”,辞例结构和词性完全相同,均表“祭祀”义。“祠”作为修饰语修饰共名“器”,义同“祭”和“祀”,泛指祭祀而言,“祠器”即“祭祀之器”,用以说明其祭祀之功能。
四、旅壶
修饰语“旅”大量见于青铜器各个器类的自名中。仅商周青铜酒器自名中的修饰词“旅”就出现在爵、觯、鍴、杯、尊、壶、锺、卣、方彝、罍、?、瓶等十多
种器类中。我们对吴镇烽先生《铭图》中的17类青铜酒器进行了统计,其中,带修饰词“旅”的自名有111例。这些用例多见于西周时期,殷商时代和东周时期数量相对较少。就青銅壶而言,自名以“旅”为修饰语的有23例。关于青铜器器名前的“旅”,到底是什么含义,宋代金石学者就对此展开了讨论,迄今为止,仍然没有定论。其中,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
[11]古文字诂林编纂委员会.古文字诂林(第6册)[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12]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0.
[13]龚自珍.说宗彝[A].龚自珍全集[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14]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三)[J].考古学报,1956,(1).
[15]杜迺松.金文中的鼎名简释——兼释尊彝、宗彝、宝彝[J].考古与文物,1988,(4).
[16]马承源.陈喜壶[J].文物,1961,(2).
[17]于省吾,陈邦怀,黄盛璋,石志廉.关于《陈喜壶》的讨论[J].文物,1961,(10).
[18]张颔.陈喜壶辨[J].文物,1964,(9).
[19]罗振玉.增订殷虚书契考释(下)[M].东方学会,1927.
[20][宋]王黼等.博古图[A].刘庆柱,段志洪,冯时编.金文文献集成(第一册)[C].北京:线装书局,2005.
[21][宋]董逌.广川书跋[A].刘庆柱,段志洪,冯时编.金文文献集成(第十六册)[C].北京:线装书局,2005.
[22][清]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A].刘庆柱,段志洪,冯时编.金文文献集成(第十册)[C].北京:线装书局,2005.
[23][清]吴荣光.筠清馆金文[A].刘庆柱,段志洪,冯时编.金文文献集成(第十二册).北京:线装书局,2005.
[24]郭沫若.金文丛考[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
[25][宋]吕大临.考古图[A].刘庆柱,段志洪,冯时编.金文文献集成(第一册)[C].北京:线装书局,2005.
[26]马衡.凡将斋金石丛稿[A].刘庆柱,段志洪,冯时编.金文文獻集成(第三十七册)[C].北京:线装书局,2005.
[27]容庚.殷周礼乐器考略[J].燕京学报,1927,(1).
[28]唐兰.陕西省岐山县董家村新出西周重要铜器铭辞的译文和注释[J].文物,1976,(5).
[29]黄盛璋.释旅彝——铜器中“旅彝”问题的一个全面考察[A].黄盛璋.历史地理与考古论丛[C].济南:齐鲁书社,19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