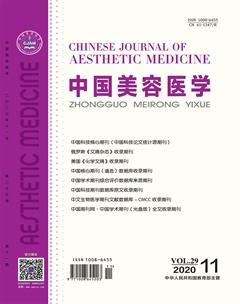痤疮中医诊治源流考
郝英利
[关键词]痤疮;中医;源流;病名;病因病机;治疗;预防调护
痤疮(Acne)是一种好发于青春期并主要累及面部的毛囊皮脂腺单位慢性炎症性皮肤病[1]。皮疹初起多为粉刺、丘疹和脓疱,严重时伴有结节、囊肿、瘢痕及色素沉着,易反复发作[2]。流行病学研究显示,痤疮患病率为88%~94%[3],且青春期后痤疮患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从中医角度出发,痤疮的病名记述、病因病机及预防调护的认知,已有深远历史,且中医治疗痤疮已经成为临床上一大特色。研习古籍,结合当代医家论述,从以下四个方面整理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对痤疮的认识,以兹为临床创新提供理论依据。
1 痤疮之“名”、“义”渊源
1.1 战国至秦汉,病名之始,痤之源流:“痤疮”一词由来非现代医学所创,在中医学古籍中早有记载。早期《说文解字》[4]:“疕,头疡也,从疒匕声”中“疕”字代指疮疡和头疮,而“疡”在《周礼·天官》中被记述为皮肤表面之肿物,将“痤疮”归属于“疕”的范畴。首次记载“痤”于书内的是《素问·生气通天论》[5],载 “汗出见湿,乃生痤痱”、“劳汗当风,寒薄为皶,郁乃痤”开辟了后世论述痤疮和粉刺的先河。
1.2 晋隋时期,据之病位,以形定名:晋隋时期多因本病好发于头面,依据病位命名为“面皰”“面疱”“嗣面"等,如晋代《肘后方》[6]载“年少气充,面生皰疮”。隋代逐渐开始描述其皮损形态,《诸病源候论》[7]中:“面疮者,谓面上有风热气生疮,头如米大,亦如谷大,白色者是”。
1.3 唐宋时期,直接命名,谓之粉刺:沿前代皮损形态的记述,唐·王冰在《黄帝内经·素问》注释:“隳,刺长于皮中,形如米,或如针。俗曰粉刺”,将本病直接命名为“粉刺”。宋代《圣济总录》中:“论曰面疮者,是粉刺也”亦有相关直接命名的记载。
1.4 明清时期,命名繁多,普于粉刺:明《外科启玄》、清《洞天奥旨·粉花疮》中均记载,若窠?生在人面,而作痒,都可命名“粉花疮”,并强调“粉花疮”好发于妇女。顾世澄《疡医大全》载:“粉刺即粉疵……”,后续又提出“酒刺俗名谷嘴疮”的说法。《医宗金鉴外科心法要诀》[8]等书籍又将肺风与粉刺结合命痤疮为“肺风粉刺”。《古今医统大全》中将其称之为“风刺”……虽“粉花疮”“粉疵”“酒刺”“谷嘴疮”“肺风粉刺”等这类命名繁多,但概念相似,当代医家仍延续前人记载,普遍以“粉刺”命名。
1.5 近现代,深于病机,以因命名:随研究进展逐深,近现代中医皮肤病学和相关学科以及临床工作中均采纳“粉刺”、“肺风粉刺”之病名。并传承晋代葛洪“年少气充,面生皰疮”之观点,加之当代生存环境的改变及诸多致病因素的产生,将发于青春期人群的头面、胸背部皮疹,又名为“青春痘”、“青春疙瘩”。
综上,中医自古本有痤疮之“名”,再论其“义”,早于《内经》“寒薄为皶,郁乃痤”中已有痤疮与粉刺有别之说。基于前者,《类经》中“形劳汗出……液凝为皶,即粉刺也。若郁而稍大,乃成小疖,是名曰痤。”已有明确记述。归纳古籍可见,“粉刺”“酒刺”“粉花疮”等病名之义多指近代痤疮中较轻的皮损形态,如黑头、白头粉刺等,而古籍之“痤”类等同于近代痤疮中结节、囊肿等较为严重的皮损形态。现代医学已将粉刺作为痤疮的阶段性表现,而“痤”已成为粉刺症状的后续发展。
2 痤疮之病因病机
辨析其病因病机,意义在于传承中医辨证体系。自《内经》起,对痤疮病因的认识呈现出一个由浅入深、逐渐发展的过程。近现代医家更是扬前辈之效验,弃墨守成规之定律,辅以长期临床经验,据患者不同病情施以辨证,由此出现一人多证、证病结合的综合诊治思路,展现了中医的继承与发展。
2.1 外感侵袭,肺经郁热:“汗出见湿,乃生痤痱”,“劳汗当风,寒薄为皶,郁乃痤”,此为古代医家对痤疮发病的最初认识,两句均出自我国现存最早、影响最深的医學典籍《黄帝内经》,都记述了汗出致使毛孔舒张,湿邪入侵或感受风寒,毛窍壅闭而发,轻为粉刺,重者郁而化热生痤的思想。认为其发病赖于“湿”、“寒”之交杂,郁于肌表,成为中医学对痤疮病因认识的理论源头。
除寒湿致病外,外感阳邪亦会发病,如《万病回春》“肺风粉刺,上焦火热也”、《石室秘录》“粉刺之症,乃肺热而风吹之”中的“风”“火”都为阳邪,侵袭肌表发于本病。又因肺为娇脏,不耐寒热,外感侵袭,肺脏首当其冲,久则化热生痤,故已成为痤疮发病的基本病因。在明清多将本病以“肺”论治,在《外科启玄》、《外科正宗》等多部古书中都谈及由“肺受风热”郁滞不散而化为粉刺的说法,当代医家少有与之相佐之处,当代医家在临床上仍将“肺经风热证”作为痤疮基本证型,在此基础上施以论治。
2.2 脾胃湿热,上熏于肺:脾主运化,升清降浊。与胃相表里,五行与肺母子相称,且脾喜燥恶湿,湿困脾则母病及子犯于肺,发于肌表而致病。古时魏晋战乱频繁,玄学兴起,社会多尚纵乐饮酒之风,加之继承西汉《养生方》“饮酒热未解……轻者皶疱”的说法,隋代巢氏总结了“饮酒当风”、“饮酒以冷水洗面”致使风热之气上乘于头面致病。然除风热外因,酒亦为辛热之品,多饮伤及脾胃,湿热尤生发病。后清代医家认识逐广,在前人之上,补充“好饮者,胃中糟粕之味,熏蒸肺脏”的理论。可见若饮食多辛辣厚味及酒辛之品,易生湿热,致病脾肺,乃生痤痱。
中医是理论与经验并重的学科,即便言传身教,也未悉数传承,加之临床病情多变,每位医家的临证经验都各具特色。赵炳南[9]作为现代中医皮外学科的奠基人,认为肺胃湿热之上,外感毒邪而发,在肯定前辈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看法。其弟子陈彤云[10]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主张本病与饮食不节有关,并从湿热毒瘀入手论治。2.3 肝郁化火,痰瘀互结:肝主疏泄,性喜条达。若肝气不舒,侮脾生湿,日久肝郁化火,湿热交杂上犯头面;或肝郁气滞,致使血瘀,肝火过旺,炼液生痰,久则痰瘀相结。均可诱发本病。宋《圣济总录》中载:“目眜眦疡疮痤痈,病本于肝”;清《外科大成》云:“燥淫所胜,民病疮疡痤痈,病本于肝是也。”可见古代医家逐渐重视以肝论治痤疮。
當代生存环境的变更,动则急躁、静则忧郁的情绪因素,压力的施加与日趋重视容貌的心理,现代医家治疗时多在清肺胃之热的基础上,辅以疏肝、调肝之法。如王行宽教授“从肝肺脾多脏调变”论治痤疮;金香淑、崔鸿峥等诸位医家都认为肝郁化火致青年痤疮,谈及与当代因素密切相关。
2.4 肝肾亏虚,致病冲任:清代有“八脉隶乎肝肾”之说,重视冲任与脏腑之间的关系,不可单独而论,为以肝肾致病冲任论治痤疮提供了理论基础。肾阴不足,虚火燔灼冲任;肾阳虚衰,寒于冲任;肝阴亏虚,冲任失养。加以肝肾同源,肝阴亏虚乃肾阴不足,致使冲任之本不足而失调,致病痤疮,尤以女性经期前后皮疹加重多见。
近代禤国维[11]认为具有时代表现的因素(睡眠、饮食、压力、生活节奏等)所致病的痤疮多由肾阴不足、相火过妄所致;陆德铭认为病因以阴虚火旺为本,重在养阴清热;韩冰[12]依据朱丹溪的“相火学说”,从肝肾不足、冲任失调致相火妄动论治痤疮等。
2.5 其他:痤疮的发病与心有关,《素问·至真要大论》云:“诸痛痒疮,皆属于心”;亦有“虫”作祟,《石室秘录》云:“粉刺……然皆气血不和,故虫得而生焉”;体虚受邪乃为常因,以《内经》:“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为理论基础,宋《圣济总录》提出“粉刺……因虚而作”的理论;痤疮与年龄相关,气血盛者好发,《肘后方》云:“年少气充,面生皰疮”;外在致病因素“胡粉”为多,隋代巢元方认为“因敷胡粉……粉气入腠理化生之也”,近代朱仁康[13]强调涂擦劣质化妆品会加重女性痤疮;王琦[14]从体质论治痤疮,调理“湿热体质”治其本。
3 痤疮之治疗方法
3.1 内治法:早于晋代《肘后方》首次记载痤疮方剂,如去面上粉刺方、面生疱疮方等。《内经》“有诸于内必形诸于外”意指发于外在的皮疹皆由内在脏腑功能失调而发,为后代医家从内论治痤疮提供思想依据。翻阅古籍可见,唐宋之前多以外治为主,内服方剂较为单一且内容零散,含苞待放,正处于萌芽阶段,明清以后内治法才逐渐丰富。
3.1.1 损其有余,除肺经风热:自明清以来,内外治法紧密结合,众多医家普以肺经有热作为主要致病因素,皮疹多为粉刺,伴有痒痛,热重于湿,治则以疏风清热为主,如明《寿世保元》的清肺饮、《外科正宗》[15]的枇杷叶丸和黄芩清肺饮,以及《医宗金鉴》所载的枇杷清肺饮,运用枇杷叶药性入肺、胃二经,并具清泄肺热的作用,将其作为君药加以辨证,对现代治疗痤疮的影响颇大,现代研究药理作用显示枇杷叶具抗氧化、消炎之功,致使临床上更加重用枇杷叶与其他药物配伍,故现代医学一直将枇杷清肺饮作为粉刺轻症的代表方剂,已被录入《中医外科学》教材中。近代赵炳南教授运用枇杷清肺饮,加苦参、野菊花等药物,在清肺胃蕴热之上佐以解毒;朱仁康、张志礼等近代名老中医也多在此方上进行随证加减;徐宜厚[16]清泻肺胃常应用枇杷清肺饮合白虎汤。
3.1.2 护其脾胃,清中焦湿热:患处皮肤多油腻,多见脓疱、且皮疹红肿疼痛明显,常伴口臭、便秘及溲黄等表现,湿热并重,多以清热除湿解毒为主。常用《伤寒杂病论》茵陈蒿汤加减,因三味药为苦寒之品,利用苦能泄湿、寒能泄热的特点,清中焦湿热。当代研究推测茵陈蒿汤可能具有抑制寻常痤疮的炎症发展,降低体液免疫应答的作用。又有药理研究车前草、生薏苡具有抗炎、解热作用,喻文球[17]在茵陈蒿汤之上加此二味以助清热之功;此外,《医宗金鉴》除湿胃苓汤具有健脾燥湿之力,也常应用于此。
3.1.3 降其肝火,化痰兼散瘀:皮疹多见结节、囊肿,甚者出现瘢痕色素沉着等损害。若伴口苦易怒等肝郁表现,或妇女经血不调伴经期前后加重者,多疏肝解郁为主,常用《太平惠民和剂局方》逍遥散加减,后《内科摘要》在逍遥散中加丹皮、栀子组成加味逍遥散(又称丹栀逍遥散)[18],增加清肝热、和营血之力,如徐宜厚常用丹栀逍遥散加减以疏肝清热,疗效显著;若皮损严重且病程长、久治难愈者,多化痰散瘀为主,如朱仁康应用化瘀散结丸加减、陈彤云应用内消瘰疬丸、张志礼[19]方用海藻玉壶汤加减等已达到化瘀消痰,软坚散结的功效。
3.1.4 补其不足,滋肝肾之阴:明代对虚证痤疮,多以补虚,如《万病回春》中六味地黄丸为滋肾补阴的名方,现仍应用于临床治疗肾阴亏虚之痤疮;近代禤国维提出痤疮应从肾来论治,平调阴阳,予以知柏地黄丸合二至丸加减消痤汤进行滋肾清热;陆德铭常应用生地、麦冬等滋阴药以养阴清热为治本之法,配合祛邪治标临证治之;韩冰以滋补肝肾、清热凉血为治则,以知柏地黄丸作为基础方辨证论治,应手辄效。肝肾阴虚,日久冲任失调,张志礼运用金菊香方加减、徐宜厚运用益母胜金丹合二仙汤调理冲任等。
3.1.5 其他治法:现代内治多分型而论,多元化的认识发病机理,以致分型种类众多,方药应用上,或主方加减,或古方新用,或临床经验方、自拟方等。除上焦湿热,亦有心火而论,马绍尧言心火亢盛亦会生热,方用泻心汤加减以泻火解毒;王琦引用清代《温病条辨》中“三仁汤”,自拟“湿热调体方”从体质论治以达清热利湿之功;许连霈注重从三焦而论,清火毒为主;余方根据脏象学基础,认为面部各个区域均与五脏相对应,可辅助皮损特点辨证施治等。
3.2 外治法:早于战国,《五十二病方》在美容护理章节里已有关于“痤”的治疗,但以外治为主,记载用含蛋白、纤维等成分的大豆煮液洗患处,达到抗氧化作用来预防本病,可见中医外用药治疗痤疮早于内服。后《内经》:“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指出了随其病位驱邪的思想,为外治法提供了思想基础。
3.2.1 粉膏熏洗,直达于病所:我国现存最早外科专著《刘涓子鬼遗方》[20]有记载外用木兰膏方治疗粉刺的讨论。随后,晋代《肘后方》白蔹散和连牡散、唐代《古今录验方》木兰皮散和苏合煎、宋代《圣济总录》赤膏方和丹砂散、《太平圣惠方》牵牛膏、明代《普济方》使君子膏和黄连膏、清代《医宗金鉴》颠倒散等诸多外用药的记载,仍被现代所沿用。尤其唐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中记载白膏等对现代影响颇大,三十年后为补充前书不足,又成书于《千金翼方》,从之前单纯治疗痤疮,到后书研讨痤疮瘢痕的治疗,丰富了治痤经验,并指导后人且据此留下了“灭瘢痕方”,从美容角度讲,又促使了中医美容医学事业的发展。近现代医家,如赵炳南老先生将颠倒散外涂患处治痤的疗法发扬光大;朱仁康提倡将大黄蛰虫丸配以凉茶水调制糊状敷于患处等等,可见近现代粉剂、膏剂已成为外治主流,被众多医者受用。另有《外科启玄》“凡治疮肿......宜药煎汤洗浴熏蒸,不过取其开通腠理,血脉调和。”指出中药熏洗法治疗痤疮的记载。
3.2.2 刺络行针,通经且活络:战国《灵枢·经别》载“十二经脉,人之所以生,病之所以起”,当疾病产生时,经络在体表有所反应,针刺通过刺激相关部位,可使经络通畅,气血调达,可见从经络论治痤疮也是中医疗法的一大特色。刺络放血疗法依据《素问·针解》“宛陈则除之者,出恶血也”在针刺基础上达到推陈出新的作用;耳穴贴压循经施穴,辅助刺络放血大大提高治愈率;火针、刺络拔罐、刮痧等多种疗法都运用经络走行,刺激人体穴位起到活血祛瘀、泄热排浊的作用。现代研究发现,针灸不仅治疗痤疮显效,在改善皮损症状、降低复发率方面同时具有明显优势,疏通经络以达调理气血之功,辅助治痤,成为外治法中的一大特色。
3.2.3 其他剂型,沿袭与创新:前人之上,近现代医家抓住外治法毒副作用小、简便易行、价格低廉的特点,注重对不同类型痤疮进行分类施治,研制不同剂型,在中医疗法中成为临床一大特色。中药面膜是近年来较为创新的外治方法,不仅提供治痤疗效,又具有美容养颜作用,禤国维运用中药加日常食材做成面膜以发挥清热解毒散结之功,被广大患者受用。又有研究显示,中药面膜贴敷法干预痤疮的循证技术操作的临床适用性等方面均具有较高一致率,可进一步试用于国内各级医院并推广[21];倒模是在面膜基础上加石膏在其上,达到清热泻火、消肿止痛作用。中药凝胶制剂是在传统软膏基础上发展而来,具有清爽、易清洗的特点,有更高前景;酊剂是利用酒精透皮作用,使中药药性发挥到极致作用于皮肤的一种方法;此外,另有穴位埋线、中药负离子喷雾法等众多特效疗法,针对不同时期皮疹,在前人之上使痤疮诊治更具针对性。众多剂型,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促进异物排出,气血运行通畅,达到治愈痤疮的效果。
综上,古今中外各有当代治疗特点。《医宗金鉴》载:“内服枇杷清肺饮,外敷颠倒散”、《理瀹骈文》曰:“外治之理,即内治之理,外治之药,即内治之药,所异者法耳。”又强调了内外结合的重要性。于内,应深入研究古人医案,在此之上加以创新,着重因人辨证以解病之源头;于外,应将传统医学经验与现代医学技术相结合,深入追溯药理作用,运用外用药物安全、高效、零刺激的特点直达患处,缓解症状。在前人的理论上灵活变通,在现代的科技上大胆创新。
4 痤疮之预防与调护
4.1 传统医学初探:古代医家在皮肤清洁上,《普济方》肥皂丸、《杨氏家藏方》洗面方等类似当代洁面产品功效;饮食上建议多素少荤,调和五味,依《素问·生气通天论》“膏粱之变,足生疔疮”之论;又因“劳汗当风、寒薄为皶”“谓面上有风热之气生”,嘱患病者应避风寒暑热、防日暴晒;起居上,《素问·上古天真论》“起居有常,饮食有节,不忘劳作,能度百年”,意指注重合理起居,充足睡眠,干预痤疮发生;情志上,《素问·汤液醪醴论》“精神不进,意志不治,故病不可愈”,指出疾病重在精神调护,调畅情志,使痤随郁而解。
4.2 现代医学承袭:近现代治痤疮的特点,除内调外用,愈来愈重视痤疮的预防与调护。生活习性、饮食偏嗜及精神压力等诸多因素的改变,使痤疮发病率逐年增加。生活习惯上,更加强调“子午觉”的重要性,应坚持午睡、23点前入睡的生活规律,并指出吸烟饮酒已成为高危因素;情志上,现代研究显示精神紧张会引发内分泌失调增加发病几率;饮食上,除禁忌高糖、辛辣、油腻等品,也应避免其他可疑因素(咖啡、奶茶、海鲜等)的摄入;面部护理上,随化妆产品的多样化,以及产品使用不当、清洁不佳等都会诱发加重痤疮,形成“化妆品性痤疮”。
5 小结
从以上四个方面的阐述,可见传统医学的开创挖掘,現代医学的引经据典,日趋完善。论病名,虽古今命名繁多,但临床证候特征均为一致;论病因病机,因医家众多思路各异,临床证型尚不规范,虽名略不同,实际大都相近,现已将“肺经风热”、“肠胃湿热“和“痰湿瘀滞“此三个基本证型编制于《中医外科学》[22]教材中;论治疗方法,内治法辨证施治,为求其本;外治法直达病所,形式多样。当代更加注重内外相结合的治疗措施;论预防调护,日趋被重视,注重饮食、情志、生活习惯及面部护理等方面的调护,可干预痤疮发生,大大提高治愈率。本文结合古今医籍,初步探析各医家对痤疮不同的学术见解,归纳临床思维与宝贵经验,在体现传承与发展的同时,希望对痤疮的临床治疗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