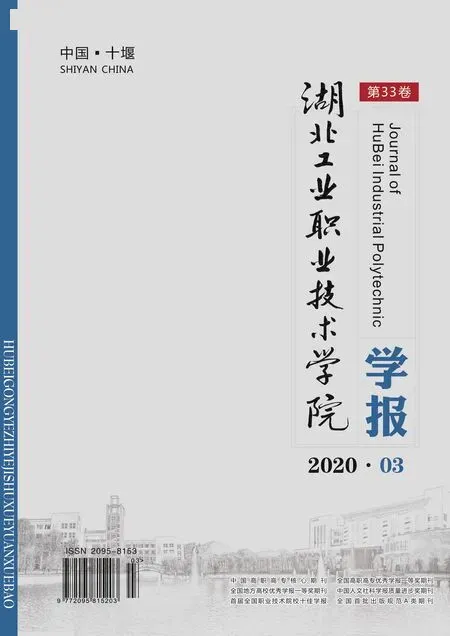论黄庭坚茶词艺术及其人生情怀
李志明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据统计,《全宋词》[1]中咏及茶的词作约有256首,其中可断为茶词的有52首,这些茶词一般会在题目中标注“茶词”“茶”“咏茶”“送茶”等语。苏轼最早将茶纳入词境,但苏轼只有两首茶词,其他两宋名家大多只有一两首。而黄庭坚创作了10首茶词,在数量上居两宋词人之最。在这些词作中,茶不再只是作为文人生活的点缀出现,而是真正成为词人笔下的审美对象,真正寄托着文人的内心情怀。黄庭坚这些茶词几乎首首皆精品,极大地丰富了两宋词坛的艺术实践。
目前学界对于黄庭坚茶词的研究并不多。以往对茶词的研究,大多通过对宋人词作整体面貌的分析,来探究风行于宋的茶文化。如于巧《舌尖上的咏茶词——宋代咏茶词研究》、李亚静《浅论宋代茶事茶词与文人生活》、刘学忠《宋代茶词研究》等;或者通过探究茶词的创作情况来揭示两宋文人的整体精神面貌,如吴启桐《宋代咏茶词研究——以咏茶词中所蕴含的情感为中心》、王璇《宋代茶文化与宋代士大夫意识》、付以琼《宋代茶词与宋代文人日常生活审美化》等;而仅有的涉及黄庭坚茶词的几篇论文也多是从这两个角度展开论述的,如余悦《黄庭坚与中国茶文化》、施由明《论茶与黄庭坚的人生情怀》,以及陈永娟和郑培凯的同题论文《黄庭坚的茶词》等。
在这里我们采取微观解读的方式,对前人研究尚不充分的黄庭坚茶词的艺术魅力及其所折射出的黄庭坚的文人心态进行分析阐释。
一、黄庭坚的一生茶缘
饮茶之事极盛于宋,《铁围山丛谈》记载:“茶之尚,盖自唐人始,至本朝为盛;而本朝又至祜陵时益穷极新出,而无以加矣[2]。”茶以其清凉降火、醒酒解醉的功用,以其平和淡泊、香远益清的品性,不仅赢得了士大夫阶层的青睐,更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普通市民也不可缺少的饮品。南宋吴自枚《梦梁录》就曾记载:“人家每日不可缺者,柴、米、油、盐、酒、酱、醋、茶[3]。”
茶既有其高雅性,又有其世俗性,因而能够被宋代社会各阶层广为接纳。茶事活动是宋代文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宴饮、社交都能看到茶的身影。黄庭坚一生嗜茶,其家乡江西修水县是著名的茶乡,盛产一种名为“双井”的茶叶。而双井茶的声名远播离不开黄庭坚向欧阳修、苏轼等文化名流的大力推荐。黄庭坚以茶相赠亲友,并大量创作诗歌加以宣传,如《双井茶送子瞻》《以双井茶送孔常父》等,极大地提高了双井茶的知名度。欧阳修的《归田录》就曾将双井茶推为“草茶第一”[4],而宋周辉的《清波杂志》卷四也记载:“双井因山谷而重[5]。”
黄庭坚心性超然淡定,其身处逆境之时,常能够以达观的心态泰然处之。这固然与宋人在思想上往往出入佛老,擅长自我解脱、以圆融自适的态度面对人生磨难的整体心态有关系,但对于黄庭坚来说,这份平静淡泊、不执著的人生态度的养成,还有赖一份茶香的滋润和涵养,其超然淡定的人格特征,与茶道中所蕴含的平和恬淡、和敬清寂的精神是相契合的。
茶是至清至洁之物,韦应物在《喜园中茶生》中咏到:“洁性不可污,为饮涤尘烦。此物信灵味,本自出山原[6]。”黄庭坚生于双井茶之乡,高洁脱俗的茶文化想必会滋养黄庭坚的少年心性,并使得他将这份不俗的高洁情性作为自己一生的人格追求。相传黄庭坚七岁时就曾写下《牧童》诗:“骑牛远远过前村,吹笛风斜隔垅闻。多少长安名利客,机关用尽不如君”[7]1416以表达自己对于官场名利争夺的厌恶。当与黄庭坚亦师亦友的苏轼在仕途上蒸蒸日上时,黄庭坚却用一首茶诗这样劝谏苏轼:“人间风日不到处,天上玉堂森宝书。想见东坡旧居士,挥毫百斛泻明珠。我家江南摘云腴,落硙霏霏雪不如。为君唤起黄州梦,独载扁舟向五湖[7]219。”这首诗中的“为君唤起黄州梦,独载扁舟向五湖”,与其说是黄庭坚对苏轼的劝谏,倒不如说是黄庭坚自我人格追求的体现。他不像苏轼“奋历有当世志”,面对激烈的党派斗争,相比较政治理想,他更渴望的是自由自在的田园生活,是“但使愿无违”的心灵安顿。因此当他晚年被贬为涪州别驾、黔州安置时,尽管生活困顿,但对他而言又未尝不是一种解脱。当他发现黔州竟也如他的家乡一般盛产香茗时,他怀着喜悦的心情写下一首清新流丽的词作《阮郎归》:
“黔中桃李可寻芳。摘茶人自忙。月团犀胯斗圆方。研膏入焙香。
青箬裹,绛纱囊。品高闻外江。酒阑传盌舞红裳。都濡春味长[8]178。”
黄庭坚对茶的热爱不仅仅是因为茶身上承载着他的乡土情怀,也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情性与茶的品性有暗合之处,还因为在思想精神上黄庭坚与茶亦有灵犀相通之处。“禅茶一味”是茶文化的核心命题,这一命题似乎最早是由与黄庭坚同时代的临济宗禅师圆悟克勤提炼概括出的,其手书墨宝“禅茶一味”四字真诀送给来宋参学的日本弟子,并对日本的茶道形成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茶味与禅味是浑融一体的,茶事活动的每一步都蕴含着禅机。吴立民在《中国的茶禅文化与中国佛教的茶道》中写道:“茶不仅为助修之资、养生之术,而且成为悟禅之机,显道表法之具。盖水为天下至清之物,茶为水中至清之味,其‘本色滋味’,与禅家之淡泊自然,远离执著之‘平常心境’相契相符。一啜一饮,甘露润心,一酬一和,心心相印[9]。”
黄庭坚有很深的禅学修养,他经常阅读佛典、参悟禅机,与僧侣交游,并与当时著名的法秀禅师、晦堂祖心禅师、五祖法演禅师等参禅学道。《五灯会元》将黄庭坚列入黄龙派法嗣中[10],而黄龙派是由马祖道一洪州禅的后世临济宗传人慧南所创,因此黄庭坚与圆悟克勤算是同宗。黄庭坚在品茶的过程中是很能够从中领悟禅味的,他在《了了庵颂》中写道:“方广庵名了了,聊聊更著庵遮……若问只今了未,更须侍者煎茶[11]。”以平常心看待世间万物,不再对个人得失耿耿于怀、斤斤计较,因此黄庭坚才能在仕途蹭蹬之时以从容洒脱的心境泰然处之。当他被贬黔州,亲友都为其投身遥远荒僻之地而担忧不已时,他却投床酣然大睡、鼾声如雷;当他再次被贬途经长沙,全家十六口人只能挤在一只小船内时,他却对友人说:“烟波万顷,水宿小舟,与大厦千楹,醉眠一塌,何所异?道人谬矣[12]。”这是黄庭坚的平常心境,是禅境也是茶境,黄庭坚对于禅意人生的追求,使他自然而然的在精神境界上与体现着禅意的茶相亲近,使得茶能够成为与黄庭坚一生相伴的绝世好友。
二、黄庭坚茶词的艺术特色
宋代诗歌创作的特征是向日常生活的倾斜,黄庭坚一生与茶为伴,茶自然也会进入他的创作视野。而词这一文学样式在经过苏轼等人对词境的开拓以后,也具备了描摹刻画日常生活的能力,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在此基础上黄庭坚也创作出了众多的茶词,这些茶词几乎首首皆佳,从而成为宋代茶词艺术中一道最为亮丽的风景线。
黄庭坚茶词的艺术魅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形象的比喻
黄庭坚擅长通过巧妙的联想、形象的比喻,来对整个烹泉煮茗的过程进行生动的刻画。如《看花回·茶词》:
“夜永兰堂醺饮,半倚颓玉。烂熳坠钿堕履,是醉时风景,花暗烛残,欢意未阑,舞燕歌珠成断续。催茗饮、旋煮寒泉,露井瓶窦响飞瀑。
纤指缓、连环动触。渐泛起、满瓯银粟。香引春风在手,似粤岭闽溪,初采盈掬。暗想当时,探春连云寻篁竹。怎归得,鬓将老,付与杯中绿”[8]6
茶汤从壶具中倾泻而出,在空中划出一道美丽的弧线,流水冲撞杯壁,词人以飞瀑作比,使得茶汤圆润而不乏力度的流动轨迹如在目前,飞湍瀑流般的声响如在耳畔。“飞瀑”一语,同时着眼于视觉与听觉,可谓摄茶汤之魂魄。词人除了“飞瀑”之语外,还以“波怒涛翻”(《满庭芳·咏茶》)、“汤响松风”(《品令·茶》)等语来对茶汤做拟诸形容,都可谓曲尽其妙。
烹泉煮茗时,茶汤的表面往往有白沫漂浮,称之为茶乳。陆羽在《茶经》中记载:“凡酌置诸碗,令沫饽均,沫饽,汤之华也[13]。”由于沫饽是由一个一个的细小气泡聚集而成,词人将其喻为“银粟”,如此一来,茶乳晶莹剔透的质感也就跃然纸上。除此之外,词人还将其喻为“蟹眼”(《满庭芳·咏茶》)、“浮蚁”(《西江月·茶词》)、“雪浪”(《西江月·茶词》)、“露珠”(《阮郎归·茶词》)等等,每一种比喻都形象生动,也避免了同一意象反复出现所带来的审美疲劳,具有陌生化的效果。
词人还常常以“春风”喻茶,在《踏莎行·茶词》中词人也有“碾破春风”之语。茶是迎着春天的和风细雨长成的,当淡淡的茶香扑鼻而来,自然使人唤起那番融融春日的记忆。以春风喻茶,是化抽象为具体,看似无理,实则巧妙。词人也时常以酒喻茶,如本词中的“杯中绿”就属酒名,李白曾有“子猷闻风动窗竹,相邀共醉杯中绿”[14]之句。饮茶亦足以使人沉醉,茶以其沁透心脾的芳香,给人带来精神上的愉悦。词人以酒喻茶,正旨在说明茶之醉人的独特韵味。
形象的比喻是黄庭坚茶词最为显著的一个特征,不仅展现了词人细致入微的观察力,别开生面的联想力,更显示出词人高超的语言表现力。
2.多层次的感官描摹
黄庭坚在对茶事活动进行描写的过程中,常常注意调动读者的多重感官,给人带来一种立体的审美感受。如上文列举的《看花回》一词中,“露井瓶窦响飞瀑”为听觉描写,“纤指缓、连环动触”为触觉描写,“香引春风在手”为嗅觉描写,多重感官的联动拉近了读者与文本的距离,使读者对整个烹泉煮茶、饮茶品茗的过程有更加具体而微的感性认识,对整个茶事活动有一种更加丰富饱满的审美体验。
这种多层次的感官描摹手法在黄庭坚的茶词中并非孤例,如《品令·茶词》:
“凤舞团团饼。恨分破、教孤令。金渠体净,只轮慢碾,玉尘光莹。汤响松风,早减了、二分酒病。
味浓香永。醉乡路、成佳境。恰如灯下,故人万里,归来对影。口不能言,心下快活自省。”[8]73
这里的“金渠体净,只轮慢碾,玉尘光莹”是视觉描写,“汤响松风”为听觉描写,“味浓香永”是味觉描写。应当说这种着眼于多种感官的描写方式是黄庭坚的自觉追求,再如《西江月·茶词》:
“龙焙头纲春早,谷帘第一泉香。已醺浮蚁嫩鹅黄。想见翻成雪浪。
兔褐金丝宝碗,松风蟹眼新汤。无因更发次公狂。甘露来从仙掌。”[8]165
“谷帘第一泉香”为味觉描写,“已醺浮蚁嫩鹅黄”为视觉描写,“松风蟹眼新汤”既是视觉描写,又是听觉描写。这样的例子在黄庭坚的茶词中不胜枚举,不同的感官描写极大地丰富了读者的审美体验,这是黄庭坚的茶词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的重要原因。
3.虚实结合的表现手法
对咏物词而言,只刻画所咏之物的外在形象会显得板滞和肤浅,难以为读者创造出审美想象的空间,营造出韵味无穷的词境。因此对于作家来说,必须既有形象之实境描写,又有想象之虚境描写,由实入虚、虚实结合,才能显得含蓄不尽、韵味无穷。在黄庭坚的一些茶词中,虚实结合的表现手法同样是普遍的,以下仅举两例:其一为上文所引的《品令·茶词》。
这首词的下阕即为虚实结合之笔,“味浓香永。醉乡路、成佳境”,茶之浓香,是着眼于味觉和嗅觉的实写,饮此香茗,便觉摇摇晃晃,如入醉乡。由实入虚,给人以飘飘摇摇,如离尘世之感,这样就将茶之如何“味浓香永”、如何“茶不醉人而人自醉”给生动的展现出来了。而下句“恰如灯下,故人万里,归来对影”则历来评家赞不绝口。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六评论道:“鲁直诸茶词,余谓品令一词最佳,能道人所不能言,尤在结尾三四句[15]。”清黄苏在《蓼园词选》中对该词评论道:“凡着物题,止言其形象则满,止言其味则粗。必言其功用及性情,方有清新刻入处。苕溪称结末三四句,良是。以茶比故人,奇而确。细味过,大有清气往来[16]。”茶如故人,这故人想必是有着如茶般高洁恬静品性的谦谦君子。词人与好友相隔万里,今日灯下品茗,如见老友之春风一面,心中自然快活非常了。词人落想天外,又与前文之“恨分破、教孤令”形成呼应,因此该词最为后人所激赏。
再如《满庭芳·咏茶》下阕:
“相如方病酒,银瓶蟹眼,波怒涛翻。为扶起,樽前醉玉颓山。饮罢风生两腋,醒魂到、明月轮边。归来晚,文君未寝,相对小窗前[8]19。”
下阕纯为想象,词人思接千载,竟联想到风流倜傥的司马相如在饮罢名茶后,风生两腋,魂魄伴着茶香,悠悠荡荡的飘回到家乡,与妻子卓文君对影窗前。这既写出了茶香之醉人心魄,使人如遁入逍遥之境,又使得该词带有了一定的浪漫色彩。
虚实结合的笔法是词境之灵气所在,这一笔法的广泛使用,是黄庭坚茶词之所以富有韵味的原因之一。
4.清新流丽、恬淡雅致的词风
黄庭坚的茶词具有清新流丽、恬淡雅致之美,这与人们脑海中黄庭坚惯用口语、大写俗词的刻板印象迥然不同。以下从两个方面进行论述。
黄庭坚的茶词之所以具有清新流丽的风格,一个显著的特征在于他擅长将风土人情纳入词境的创作,如他的《踏莎行·茶词》:
“画鼓催春,蛮歌走饷。火前一焙争春长。低株摘尽到高株,高株别是闽溪样。
碾破春风,香凝午帐。银瓶雪滚翻成浪。今宵无睡酒醒时,摩围影在秋江上。”[8]100
这首茶词是黄庭坚被贬黔州时所作,他在这首词中生动的描写了黔州的地方风土人情:伴随着隆隆的画鼓声响,春日的晴光拂过大地,又到了农忙采茶之时,人们唱着欢快的民歌,在田野间辛勤的劳作——他们要在寒食禁火之前将茶叶采摘完毕,因为这时正是品茗的最佳时节。词中所使用的意象清新自然,带有深厚的乡土风味。
再如他的《阮郎归·黔中桃李可寻芳》(见上文),同样以生动的笔触,刻画了黔中的茶农趁着时令采茶制茶的忙碌生活,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而词中一系列明亮色调意象的使用,如“月团”“研膏”“红裳”“青箬裹”“绛纱囊”等,也使得该词带有了清新流丽之美。
黄庭坚的茶词之所以具有恬淡雅致的风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对人物动作的刻画都是曼妙轻柔、小心翼翼的。例如“纤指缓、连环动触”(《看花回·茶词》)“碾轻罗细,琼蕊暖生烟”(《满庭芳·咏茶》)“纤纤捧”(《满庭芳·咏茶》)“金渠体净,只轮慢碾”(《品令·茶词》)等等,整个煮茶品茗的过程,没有一丝的莽撞、鲁莽,给人以恬静祥和之感。
其次,整个茶事活动中,一切物象都是品格不俗的。例如这茶须是品质极佳的“龙焙茶”、“鹰爪茶”,茶饼的包装上需要以“金缕”为饰,喝茶的杯子须是“冰瓷莹玉”,用来煮茶的泉水须是“谷帘”泉等等。这些格调不俗的意象,为黄庭坚的茶词带来了一种清丽雅致之美。
最后,典故的运用也使得黄庭坚的茶词别具雅味。典故往往言简意赅但是却浓缩着深厚的文化内涵,用典的修辞格能够以较少的词汇来传达尽量多的历史信息,从而能够让词境韵味悠长。例如《满庭芳·咏茶》中的“相如病酒”就化用了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浪漫爱情故事;再如《西江月·茶词》中的“无因更发次公狂,甘露来从仙掌”就同时化用了汉代宽次公“无多酌我,我乃酒狂”的典故和汉武帝铸造铜仙人以其仙人掌中玉杯承云表之露的典故,这些典故的运用既说明了茶之味美醉人、超凡脱俗,又使得黄庭坚的词更加典雅。
三、茶词与黄庭坚的文人心态
任何文学作品都是作者思想感情的体现,都包含着作者的意趣旨归。词作为中国文学史上抒情意味极强、自我抒写极其鲜明的文学样式,自然能够更加生动地体现出作者的内心情怀和人生态度。黄庭坚创作的不少茶词寄托着他的人生追求、体现着他的精神面貌。这部分茶词所折射出的黄庭坚的文人心态既有其个人的独特性,又有其时代的共性,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珍惜韶华、及时享乐的世俗情怀
由于宋代优待文臣的国策再加上内忧外患背景下正直文臣的事功无望,北宋社会以其表面的畸形繁荣更促进了文人士大夫阶层之间及时享乐的世俗情怀的盛行。词这一文学样式最开始是在酒筵歌席场所用来演唱的,以发挥“用资羽盖之欢”的功用。因此在大量诞生于文人雅聚环境下的文学作品中,词往往更能够体现出宋代文人的享乐心态。黄庭坚的茶词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这样的心态,这与茶本身所具有的社交属性是密不可分的。
宋代文人亲朋好友之间常常以茶相赠,这一点在上文已有所提及。实际上文人雅聚之际,茶是必不可少的角色,甚至发挥着重要的功用。宋代文人在酒筵歌席结束以后,并不会促然离席使聚会戛然而止,而是设茶款待,一为醒酒之用,二为留客之用,三为尽余欢之用。在宋代这成了一种仪式和礼节,黄庭坚的茶词对此也有鲜明的体现。例如他在《惜余欢·茶词》中写到“相将扶上、金鞍騕褭,碾春焙、愿少延欢洽”,在《看花回·茶词》中写到“欢意未阑,舞燕歌珠成断续。催茗饮、旋煮寒泉,露井瓶窦响飞瀑”,再如《阮郎归·茶词》中写到“烹茶留客驻雕鞍,有人愁远山”等等,都揭示了茶在文人聚会时的重要作用。
茶的这三点功用都围绕着一个核心,那就是试图延长生命的欢乐、试图完全耗尽此一时刻的生命热情、试图进一步舒展生命的活力与欲望。由于宋代文人大多能够意识到社会繁华掩盖下尖锐的社会矛盾,因此他们对于盛宴难常、宾朋难聚有着深深的体会,他们毫不迟疑的抓住每一次欢乐的时光,以尽情地享受,尽情地释放生命的欲望。酒席上推杯换盏还不够,更要待醒酒之时以尽余欢,在这种环境下,茶之“少延欢洽”的功用就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宋代文人珍惜韶华、及时享乐的深层文化心理。只是极致的享乐过后,人们的内心又未尝不包含着一种深深的怅惘,毕竟时光终难挽留,盛宴终将散去,在黄庭坚的茶词中,同样能够见到这种对于人生的悲剧性体验的深刻关照。如在他的《看花回·茶词》中,上片才写到“欢意未阑,舞燕歌珠成断续”,下片就写到“怎归得,鬓将老,付与杯中绿”,在感情的抒发上是先扬后抑,由喜入悲,充满了自省精神。黄庭坚的茶词创作,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了宋代文人的整体的精神气质。
2.乐天知命、随遇而安的达观心境
黄庭坚对于功名利禄并没有多么深的执念,当他在仕途上遭遇打击,被贬荒僻之地时,常常能够以乐天知命、随遇而安的达观心境泰然处之,较快地从人生逆旅的悲苦境遇中超脱出来。
黄庭坚在被贬黔州时,曾有《定风波》一词:
“万里黔中一漏天,屋居终日似乘船。及至重阳天也霁,催醉,鬼门关近蜀江前。 莫笑老翁犹气岸,君看,几人白发上华颠。戏马台前追两谢,驰射,风情犹拍古人肩。”[8]87
在这首词中,上片写黔中环境之艰苦,下片写乐观潇洒之心情,为黄庭坚那高蹈脱俗、乐天知命、随遇而安的达观心境做了一个生动的注脚。但如果说黄庭坚在这首词中对于“屋居终日似乘船”的恶劣环境还有所介意的话,那么在他的《阮郎归·茶词》中,则是彻底的与黔中的环境达成和解,真正地体味到了黔中生活的美丽动人之处,于是他写下了“黔中桃李可寻芳”这样的词句。这里风光秀美,民风淳朴,不正是他所一心向往的田园生活吗,更何况这里盛产香茗——他的精神之友,他大可安居此处,凭茶香一抹,静味春意之悠长。因此黄庭坚的这首茶词《阮郎归》同样折射了他乐天知命、随遇而安的达观心境。
对于黄庭坚而言,遭贬的际遇反而让他更加贴近了生活的本来面目,让他脱离了官场的虚伪,以及名缰利锁对于心灵的束缚。他看到了黔中的茶农,看到了他们尽管辛苦却不乏惬意安适的生活,这正是黄庭坚所向往的,是真正的生活美学。越贴近淳朴本真的生活,心灵就越是自由无碍,越能保持心灵的澄澈清净,这也是茶道中所蕴含的至清至洁的精神,也是黄庭坚之所以身处荒僻之贬所却能够保持达观一个重要原因。
3.平和淡远、和敬清寂的悠悠禅思
诗歌的意境创造与禅境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意境作为中国古典美学的核心范畴,在其形成发展的过程中曾有赖于禅境的启发。禅语的思之隽永与禅悟的洞然开朗,均部分地为意境美学所吸收,成为意境之美的重要特质,这一点前人多有论述,这里不再敷赘。黄庭坚有着很深的佛家思想,对于禅宗的精深研修也有助于他创造出意境非凡的文学作品,可以这样认为,当他把禅宗中不可言说的禅悟借助文学形象而不是枯燥说理的方式成功的加以暗示表述出来时,文学作品也就具有了意境之美。这也是黄庭坚的茶词之所以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相比较他在一些词作中生硬地夹杂一两句禅语,他的茶词则完全是把禅思不留痕迹地融化在诗歌的意境创造中了。茶道中所蕴含的禅意在唐代陆羽的《茶经》中就开始有所体现,到黄庭坚的时代,“禅茶一味”的命题已经被提炼概括出来。黄庭坚生于茶乡,爱好品茗,又精修禅宗思想,他在茶词中本也可以像在其他的一些词作中一样大谈禅理,甚至还有着先天的优势,然而他并没有这么做。在他的茶词中,禅境之哲思与意境之韵味已经完全妙合无亘,例如他的《踏莎行·茶词》。词的上片写黔中茶农响应时令、勤劳采茶过程,带有浓郁的地方风土人情色彩;词的下片写词人烹泉煎茶,临江眺望的场景。词人今宵无睡,又是醉酒方醒,想必心中有所郁结,然郁结所为何事,词人又未点破,只是举目望去,只见冷清的月光下,摩围山的影子长长地倒映在辽阔的江面上。摩围山是一座有着浓郁佛教文化气息的宗教之山,“摩围影在秋江上”一句如同禅宗中引人顿悟的一句偈语,词人可曾借这摩围山影,借这澄江如练,顿悟到人生的真谛?心中的那份愁绪可曾得到消解?一切尽在不言之中,夜色是如此静谧,雪沫乳花的翻滚声响似乎更加衬托了夜的安详,空气中弥漫着的不仅仅是茶的清香,还有寄寓于茶香中的悠悠禅意。下片寥寥数语,最后以景结情,这几句景语,是词人平和淡远心境的投射,词人用简约的几笔,为我们描绘了一个禅意盎然的美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