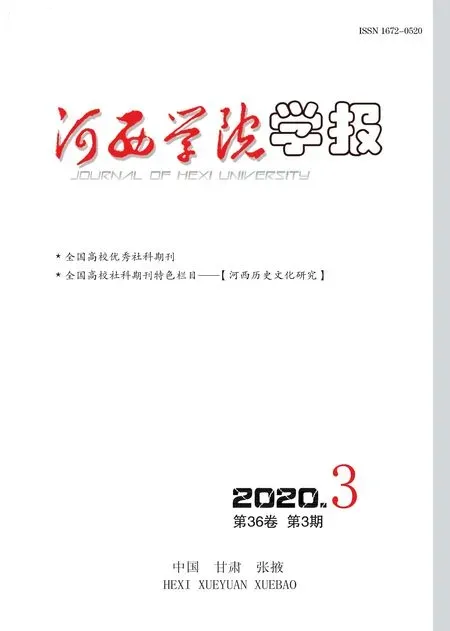明诗中的河西风貌与明人的河西认知
高璐 王钰洁
(兰州大学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河西地区系指今甘肃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等地,因位于黄河以西,自古称为河西,又因其地处祁连山与合黎山之间的狭长地带,亦称河西走廊,是中原地区通往西域的咽喉要道。该区域原为大月氏部族的领地,后为匈奴占领。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汉朝驱逐匈奴,控制了河西地区,打开了通往西域的道路。中央政府在此设置武威郡和酒泉郡,后增设张掖郡、敦煌郡,“河西四郡”之称由此而来。其设置为汉朝起到了连通西域,隔绝匈奴与西羌的重要作用。明代国力不及汉唐,但并未放松对河西地区的经营。据陈洪谟《继世纪闻》卷六载:“国朝于张掖设甘州五卫,于酒泉设肃州卫,命将屯兵拒守。肃州外为嘉峪关,关外蛮夷各因其种类建卫,曰赤斤、曰苦峪、曰蒙古、曰安定、曰沙州、曰曲先、曰罕东左,降给印信,命其酋长管束夷众,内附肃州,外捍达贼。……自古据有河西,修饰武备,羁縻羌戎之法,惟本朝最为精密。守臣相继抚驭,诸夷一遵旧规,不敢坐视启衅,所以百五十年来,西陲晏然无事。”[1]110在明王朝着意经营河西的同时,文学表达中亦出现了紧密关涉河西的态势,主要表现为对河西走廊的地理位置与地域风貌的描摹,具体则涉及自然环境、军备活动与地方物产等诸多方面,在明代边塞文学书写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目前学界围绕明代河西文学展开的研究主要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就明代边塞文学作品展开的整体性考察,如周啸天《略论明代的边防诗》[2]论文,指出明代边防诗产生与边塞战争频繁密切相关,分别讨论了描写西北边防与东南边防的诗作风格,重点分析了于谦、谢榛、戚继光等人的诗作风格。吕靖波《明代布衣文人的边塞之游与诗歌创作》[3]论文关注在明代游边之风盛行、布衣文人入边塞幕府的背景下,南方之士边塞诗风貌表现的独特地域特征。胡静书《明代边塞词刍议》[4]论文论述了明代边塞词丰富多变的风格及情感,并关注到了女词人的创作情况。蒋培卓《明代边塞词研究》[5]论文对西北、西南、东部边塞词进行分析,以时间为轴线,认为明代各阶段边塞词作呈现的特点各不相同,指出明代开创了追和词、幛词等词作新形式,明确了时代特色、地域风貌对词作情感的影响。二是以河西地区文学样貌为中心展开的地域性、专门性研究,如龚喜平《甘肃历代文学作品与历代咏陇篇章简论》[6]论文梳理自汉代以来咏陇作品的创作概况,其中对李梦阳、解缙等诗人的作品特点及形成背景进行了分析,扼要论述了甘肃历代本土及旅陇作家的创作成就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朱瑜章《河西走廊地域文学叙论》[7]论文,点明荒凉的西北边陲有陶谐、姜道渊、刘大夏等词翰名流聚集创作,兼论河西自上古至明清各阶段发展态势,指出描写河西地区的文学作品中诗歌占主流,诗风以苍凉悲壮、豪放阔大著称。朱瑜章、吴浩军《陶谐〈西行稿〉述评》[8]论文指出,陶谐的西行诗在创作主体的境遇、诗歌格调、反映生活的广度深度等方面拓展了唐代河西边塞诗的内涵和外延。肃州是明代西部贬谪文学和边塞文学创作的中心,应当重视河西贬谪、边塞、纪行文学在明清文学史中的地位。以上研究均从不同角度对明代边塞文学样式,乃至河西地域文学特征展开了探讨,对后续相关研究具有启发性意义。就目前研究情况来看,与河西地区相关的明代诗歌一般作为边塞文学或地域文学的分支予以提及。事实上,河西地区具有难以忽视的地理意义与特殊的军事地位,当地的自然环境与社会风貌亦迥异于中原地区,考察明诗中的河西图景与明人的河西的认知既有助于丰富明代西北区域文学研究类型,亦能够加深对丝绸之路沿线社会文化心理形成的了解。
一、明诗中的河西风貌
所谓“风貌”,除关涉客观对象之形态、特征、风采之外,还包括书写者主观思维评价与判断的成分。明代语涉河西的诗作中往往包括对当地自然环境、军备活动与地方物产的叙述,必须指出的是,文学书写中包含夸张与想象的成分,其性质与目的亦有别于史志文献。如果说亲身行边者笔下的摹景状物尚有所依傍的话,寄赠类诗作中对河西的叙写往往并非出于亲眼所见,“想当然耳”的情况屡见不鲜,故而文学书写不能等同于历史实录。然而从社会心理角度观之,则均可作为一手资料,由此窥见明人头脑中的河西景象。
(一)内陆气候与多样地貌:明诗中的河西自然特征
河西走廊深居内陆,四周又有祁连山、合黎山、乌鞘岭等山脉阻隔,携有暖湿气流的海洋季风难以深入,使得河西走廊降雨量小,气候干燥,年温差大。当地的气候特征首先被纳入明代诗歌书写当中。张九一曾在嘉靖时期任职甘州,写有《春暮自甘州回署见杏花有作》诗:“晚霞遥逗杏花生,微绿风前柳色轻。独把一杯身万里,不知今已过清明。”[9]暮春时节,始见杏花柳芽,这样的描写突出了河西春天姗姗来迟的气候特征。与这种叙写相类,正德年间谪戍肃州的陶谐作有《暮春之初》诗:“塞草初舒颈,林花尚束胎。酒泉春更湿,怀抱郁谁开?”[10]369直到暮春,酒泉才草舒花发,比同时期的中原要晚许多。然而一旦春草萌发,春花吐蕊,甘州、肃州也是一派塞上江南的景象。晚明时期,蒲秉权出任肃州副使,其《酒泉即事寄王游戎》其三诗中描摹了边地冰雪消融,柳树刚抽出嫩芽,草长莺飞的春景:“边城雪霁柳条新,极目关河淑气匀,浪说玉门春不度,如何塞草绿如茵。”[11]676衬托出作者畅快愉悦的心境。
尽管如此,由于深居内陆,降雨量小,明代的河西走廊时常面临旱灾的威胁。王越《赠朱都宪巡抚甘州》诗称:“闻道酒泉忧旱久,墨池春水是甘霖。”[12]198一语道出酒泉一带时常遭受旱灾的情况。降雨量小除引发旱灾外,还会导致当地植被减少,土地沙化。何庆元《送侯碧塘按甘肃》诗曰:“甘州广塞大河阴,漠漠风开绣斧临,白简賸添朝着色,黄沙不起暮笳音。”[13]与之相类,顾梦圭在《送宋太仆赴甘肃》诗中写道:“酒泉张掖古边州,节钺西行是壮游,羌管胡笳千碛月,黄沙白草万山秋。”[14]黄沙四起,衰草连天,羌笛与胡笳的乐声使人倍感凄凉。以上几首诗作虽属寄赠,但如果将其与亲身行边者的作品放在一起对比,则会发现,两类“构图”均距实景不远。初明时期,陈诚曾经数次出使西域,对于河西风貌有切身的体验。其《宿嘉峪山》诗称:“朔风抢白草,严霜冽朱顔,流沙远漠漠,野水空潺潺。”[15]337勾勒出嘉峪山附近流沙遍地、寒风凛冽、植被稀疏的画面。联系到其他同类叙写,无论是“惊心沙碛起烽烟,若个投荒万里天”[11]676,还是“炖煌张掖接氐羌,杀气连云万里黄”[16]143,均对明代河西一带平沙无垠的图景进行了描摹。可以说,明人对于该地区荒漠景象的认知是清晰而突出的。
河西地区地貌多样,既有沙漠戈壁,亦不乏水草丰美、土壤肥沃的山地与平原。这是由于河西走廊群山环绕,春夏时节大量冰雪融水进入河流,不仅满足植物生长需要,而且有利于农业灌溉。据杨慎《升菴集》载:“甘州本月支国,汉匈奴转得上所居,后魏为张掖郡,改为甘州,以甘峻山名之。山有松柏五木,美水茂草,冬温夏凉,又有仙人树,人行山中,饥即食之饱,不得持去,平居时亦不得见也。”[17]据《明史·地理三》载:“(甘州)又有张掖河,流合弱水,其支流曰黑水,仍合于张掖河。”[18]1014又司马迁《史记》卷二《夏本纪》“弱水既西”条集解曰:“孔安国曰:导之西流至于合黎。郑玄曰:众水皆东,此独西流也。”索隐《水经》云:“弱水出张掖删丹县,西北至酒泉会水县入合黎山腹。”[19]21明代诸多行至河西的文士对弱水进行了题咏。陶谐《弱水》诗云:“少闻弱水名,今见父老语。源出合黎阳,西流十千里。”[10]357蒲秉权《弱水》诗云:“谁知彼岸是瀛洲,不信飞仙乃可浮,莫道流沙无禹迹,如何此水独西流?”[11]677这些书写均指出弱水流向的特异性。水源在西北边地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同时又作为地标性区域景观,自然而然进入了明诗书写当中。
当然,除了贴近现实情况的描写,也有不少诗歌内容因创作者并未亲身赴边而与现实稍有出入,例如胡缵宗《送甘肃宋太仆二首》诗云:“大宛通张掖,黄河傍酒泉,云霄应九万,騋牝自三千。”[20]充分地勾勒出了作者想象中的河西走廊绵延千里的宏阔样貌。而具体到“黄河傍酒泉”这一句,其摹写与实情略有出入。盖因黄河并不流经酒泉,二者地理位置相距实远,然则作为文学中的夸张以体现作者的豪迈情志亦未尝不可。这种情况也为我们揭示了明诗中边塞书写的一个特征:因送赠酬答等人事往来而促生的作品中,送赠者无须亲身赴边,他们对于河西地区的认知是概念化的、符号化的。落实到书写中,对于河西地理环境的实际考量和描摹往往不够精准,变形、位移的诗景由此产生,以配合主观情感的抒发。
明代诗歌中的河西自然面貌丰富多样,整体来看深居内陆,降水较少的客观因素促使河西出现了面积广大的沙漠戈壁。当地水资源主要来自高山冰雪融水,河流沿岸植被覆盖较好,而远离河流的干旱地区则衰草连天,黄沙漫地。这种边塞景色给诗人苍凉孤寂之感,并投注于文学表达中。相关书写多塑造辽阔宏大的景象,其中或多或少添加作者的想象,亲身游历至河西的文人,其创作相对而言更加贴近河西真实情况。还有一些诗作是寄赠给去往河西的友人,诗人并未亲身体验河西的自然环境,依靠想象及转述创造了文学图景,因此内容相比实际有偏差。但无论是亲身行边环境下产生的作品还是想象类作品,作品所表现的河西样貌均是作者头脑中的主观构图,是客观现实在诗人笔下的主观反映,即使贴近现实,也是加上情感“滤镜”之后的呈现,而无法百分之百复刻现实,我们对待此类作品应当考虑这一因素,不可将文学想象完全等同于客观历史。而这些描摹的真正意义其实在于,它使我们从中观察到了在明代社会背景下,以士人群体为主的创作者对河西地区所产生的各类丰富认知,这种认知既包括自然环境方面,也包括社会文化方面,为我们呈现了前现代社会丝绸之路沿线社会文化视角的形成过程。
(二)修筑边防与屯田实兵:明诗中的河西军备活动
现存与河西地区相关的明诗中,有不少是围绕关隘修筑与军事屯田展开的,嘉峪关的修建就是其中一个典型。河西走廊是中原通往西域各国的咽喉要道,嘉峪关则是这条咽喉要道上的锁钥,它东连酒泉、西接玉门、背靠黑山、南临祁连,据《秦边纪略》载:“初有水而后置(嘉峪)关,有关而后建楼,有楼而后筑长城,长城筑而后可守也。”[21]嘉峪关设有多层防线,戒备森严,与长城及沿边堡垒共同构成完整坚固的军事防御工程。其城楼称镇西楼,谈迁《国榷》卷四十二“甲寅弘治七年正月”条载:“辛亥,改作肃州嘉峪关甃之额,曰镇西楼。”[22]刘大夏《和冯汝阳端阳日巡嘉峪关回韵四首》其二诗云:“边关新构镇西楼,此日劳君送远眸。万里华夷如指掌,百年人物几抬头,高低屯垦增前日,远近人家望有秋,漫诵希文忧乐记,一生志愿拟同俦。”[23]524诗中的“边关新构镇西楼”谓整修城楼以加强对外防御力量,而“高低屯垦增前日”则指的是大力垦荒以屯田实兵。《明史·宋讷传》称:“备边在乎实兵,实兵在乎屯田。”[18]3953河西是“据三秦之上流,控全陕之扼塞”的边防前沿,常年重兵驻守,由于远离中原,军粮转运耗时费力,不利于统兵备战,屯田就成为了当地的重要举措。屯田有民屯、商屯、军屯之别,民屯即政府招募百姓开垦荒地,是元末明初应对战乱、缺粮和流民的自然之举。商屯指的是“募盐商于各边开中”[18]1885。为解决边镇储粮问题,洪武三年(1370)实行开中法,让商人运输粮食到边镇,然后给予商人盐引,但商人远地运输成本过高,就在边地招募游民开垦,所产粮食就近缴归仓库。商屯不仅使政府节省军粮运输费用,而且使边疆的荒地得以开垦。军屯即以兵养兵,是屯田中的重点工作,朱元璋早在建国前就组织军屯:
兴国之本,在于强兵足食,昔汉武以屯由定西戎,魏武以务农足军食定伯兴王,莫不由此。自兵兴以来,民无宁居,连年饥谨,田地荒芜。若兵食尽资于民,则民力重囤,故令尔将士屯田,且耕且战。[24]
《明史·食货一》称:“太祖初立民兵万户府,寓兵于农,其法最善。”[18]1883军屯对促进军队自给自足,减轻当地的负担起到积极的作用。在政策指导下,军民积极响应,辛勤耕作,在诗中都有体现。陶谐《喜酒泉秋收用姜太守道渊韵》诗中对屯田景象作出描写:“流澌入浍疏耕易,沃壤连原入望多。穮蓘有秋真乐事,饔飱堪办亦恩波。”[10]378军民辛勤耕耘,喜应秋收,沉浸在农事的欢乐之中。罗洪先《答同年杨虞坡》诗称:“酒泉戎出塞,瓯脱地屯田。”[25]刘大夏《谪肃回次韵柬复莆田林二二首》其一诗云:“塞下屯田正力耕,风光翻转促归程。”[23]528胡奎《送百戸徐叔平之甘州》诗云:“吾闻李牧今守边,边庭四境俱晏然,椎牛飨士开屯田,星河远近同一天。”[26]488均在诗歌中构建了边塞力耕以足食足兵作的和劳作景象。
这类作品中,刘大夏《和汝阳经理屯田写怀二首》组诗较有代表性,细致地表现了行边者参与屯田,躬耕边塞的生活状况,并指出该时期的屯田举措充实了仓廪,加强了备边实力,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其一诗曰:“年来随处说民穷,经济宁教累圣躬?足食欲储边地粟,分忧因遣内台骢。”[23]524其二诗曰:“一鞭谁着在君前,盘错今裁塞下田。制度已看加汉地,疲癃今欲乐尧天。”[23]524明朝贯彻以军屯为主,民屯、商屯为辅的屯田政策在一段时间里效果显著,既巩固了中央对河西的统治,又解决了边地军队缺粮的难题,成为边地百姓安居乐业、军队保境安民的坚实保障。具体到诗歌书写当中,春种秋收的场面欢喜热闹,创作者更多地表现对贴近自然的农事劳动的喜爱,风格轻快,与前线严肃、紧张的气氛对比鲜明。
(三)葡萄、苜蓿与枸杞:明诗中的河西代表性物产
河西走廊独特的自然环境孕育了诸多物产,当地出产的葡萄、苜蓿、枸杞等作物在明诗中不仅被屡屡提及,而且作为不可或缺的物象,参与到了诗歌整体意境构建当中。李时珍《本草纲目》认为,甘肃种植葡萄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张骞通西域之前,即“汉前陇西旧有,但未入关耳。”[27]1406葡萄喜光照,巨大的昼夜温差有利于其糖分积累,另外根系的生长发育对土壤通透性要求较高。河西地区作为葡萄种植的“黄金地带”,出产的葡萄乃至以其酿造的葡萄酒久负盛名。谢肇淛《送纳言于文若迁太仆北上二首》其二中有“酒泉亭障蒲桃熟,赢得新诗醉里题”[28]396句,正是对葡萄酒醉人场景的描写。何庆元《送侯碧塘按甘肃》诗亦称“回首天街神欲醉,葡萄美酒若为斟”[13],表明河西出产的葡萄酒实属酒中佳品,享有盛誉。
与葡萄相类,苜蓿也是河西地区的代表性作物。苜蓿喜光耐旱,生命力强。河西地区光照充足,有利于苜蓿生长。苜蓿是优良的马饲料,河西作为重要的军事区域,战马必不可少。用苜蓿喂养的马匹体格健壮,有利于军队整体战斗力的提升。《史记》记载:“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观旁尽种蒲陶,苜蓿极望。”[19]803唐龙《塞上曲八首为邃翁先生赋》其五诗云:“阵云黯淡塞沙平,苜蓿槽边万马鸣,立雪不忘征战意,因风时听鼓鼙声。”[29]提到边地以苜蓿饲养战马的情况。联系到河西地区,赵南星《送助甫自徽宁再镇甘州》诗云:“宛马骄嘶肥苜蓿,胡儿清泪尽燕支。”[30]谢肇淛《送牟侍御按甘州》诗云:“日落塞垣低度鸟,秋高猎火远连天。寒乌晓散燕支月,骢马闲嘶苜蓿烟。”[28]565都指出甘州一带苜蓿长势良好且十分丰美,是上好的牧草。
除葡萄、苜蓿外,枸杞也是当地特产。李时珍《本草纲目》载:“古者枸杞、地骨取常山者为上,其他丘陵阪岸者皆可用。后世惟取陕西者良,而又以甘州者为绝品。”[27]1578“河西及甘州者,其子圆如樱桃,暴干紧小少核,干亦红润甘美,味如葡萄,可作果食,异于他处者。”[27]1578“则入药大抵以河西者为上也。”[27]1578指出甘州枸杞质量上乘,果肉饱满,色泽鲜艳,口感甘甜,不论食用还是药用,皆为佳品。枸杞根系发达,耐寒、耐旱能力强,多长在碱性沙质土壤中,喜光照,低洼积水地区易造成烂根和死亡,因此在干旱的河西能广泛种植。这些特质在明诗中有所记录,如吴宽《谢顾良弼送甘州枸杞》诗云:“畦间此种看来无,绿叶尖长也自殊。似取珊瑚沉銕网,空将薏苡作明珠。菊苗同摘凭谁赋,药品兼收正尔须。曾是老人宜服食,只今衰病莫如吾。”[31]指出枸杞叶片尖长,果实饱满如明珠,能入药,具有保健功用。
除物产之外,河西一带的美食也被记录在了明诗当中,阮大铖《答梅长公书讯兼送其开府酒泉》诗言:“杯前杏酪听笳管,马上隃麋扫檄文。”[32]就指出当地有饮用杏酪的习惯。杏酪即杏仁磨碎加入牛羊奶制成的乳制品。杏适应性强,耐旱,耐寒,耐瘠薄,能够在河西地区生长。此外,当地畜牧业发达,牛羊产奶量丰富,这些都是促使杏酪成为当地特产的先决条件。
二、明人对河西地区的认知
文学书写中的“表达”在某种层面上可视为社会文化心理的外显方式。谁的表达、表达什么、为何表达以及如何表达,这些问题反映了人们头脑中对书写对象所持的既定观念与认知。就明诗中的表达来看,明人眼中的河西主要作为中西往来的通道、建立功业的疆场及离家去国的戍地而存在。从文本出发梳理这些认知,则有利于从细部观察明代士人群体对于作为丝绸之路重要一环的河西地区所持的基本态度。
(一)使节初从万里还:中西往来的通道
西汉建元二年(前139),张骞从长安出发,由此打开了一条绵延七千多公里的中外通道,河西走廊则是其中重要的交通枢纽。此后,张骞的历史功绩为后人所乐道,而河西走廊作为中西往来通道的意义则深入人心。这种认知明确地体现在了明人的书写当中。张光孝《送让野张侯之甘肃》诗云:“陆海当年开治化,抡才西域使张骞,阳关此去三千里,知共谁人泛酒泉。”[33]在点明张骞凿空之绩的同时,指出酒泉就位于张骞出使西域的路线上。刘伯爕《寄助甫兼呈本宁四首》其一诗云:“怀人万里意凄然,回首秦中到酒泉,百战入关知李广,片槎出塞尚张骞。”[34]不仅指出张骞出使西域经过酒泉一带,也借用张骞事迹传达对友人于边关能有所建树的殷切期望。李舜臣《送陈介泉中丞赴河西》诗云:“张掖国西门,中丞山甫论。从天下节钺,绝塞驻戎轩。蛮赋千邦入,威名万里存。空传汉出使,此路去河源。”[35]直接指出张掖是明王朝的西北重要门户,而河西地区则是张骞通往西域的必经之路。
值得一书的是,明初陈诚曾五使西域,极大地扩展了当时中原对西域的认知。谢国桢在《明清笔记谈丛》中称赞道:“世徒知郑和之乘槎南洋,而不知陈诚、李暹之奉使西域,其功不减于和。”[36]陈诚路过河西一带时以诗记事,在《宿嘉峪山》中写道:“朝离酒泉郡,暮宿嘉峪山,孤城枕山曲,突兀霄汉间。戍卒夜振铎,鸡鸣角声残。朔风抢白草,严霜冽朱顔,流沙远漠漠,野水空潺潺,借问经行人,相传古榆关,西游几万里,一去何时还?”[15]337此地远离中原故土,景致大不相同,西行道路遥远漫长,流沙漠漠,风霜凛冽,使得陈诚发出了不知何时才能完成使命平安归家的感叹,可见西行之路并不顺利。然而,陈诚的西行之举历史意义重大,不仅促进了明王朝与帖木儿帝国的往来,而且将这一路见闻写成《西域行程记》与《西域番国志》。河西走廊作为中西往来的咽喉要道,见证着使节在文化交流中付出的努力,同时参与文化交融过程,从中受益。馆阁重臣杨荣曾称赞陈诚“炜皇华于绝域,宣圣德于遐漠。其出也,有同张骞之秉节,其归也,远胜陆贾之分橐。”[15]382认为陈诚出使西域起到了宣扬皇威、巩固政权的作用,其坚贞不屈的气节可与张骞相提并论。
在陈诚出使的践行场合中产生过诸多诗作,呈现出明人对河西走廊作为通道的认知。曾棨诗言:“曾驱宛马入神京,持节重为万里行,河陇壶浆还出候,伊西部落总知名。天连白草寒沙远,路绕黄云古碛平,欲忆汉家劳战伐,道傍空筑受降城”[15]365褒扬陈诚万里西行、不辞劳苦的精神。其途经地区或是“天连白草”或是“路绕黄云”,正是河西走廊一带的地域风貌。王英诗云:“乘轺西去度河源,望尽满山接塞垣,诸部讴歌迎使节,一时雨露降天恩。黄沙白草烽烟静,斜日寒云鼓角喧,知有番王随入侍,远将龙马贡中原。”[15]363强调了陈诚出行对于中外文化交流所起到的推动作用。无论是“诸部讴歌迎使节”还是“知有番王随入侍”,均以热情洋溢的笔调描摹出陈诚带领的使节队伍所受到的欢迎景象。陈彝训诗称:“前旌遥度玉门西,万里山河入马蹄,紫塞寒沙云漠漠,赤亭斜日草萋萋。晨吹筚栗霜华重,夜醉葡萄月影低,宛马归时秋正早,西风苜蓿满郊齐。”[15]363不仅指出陈诚的队伍经过河西地区,还将当地独特的物产民情,包括筚栗、葡萄酒、苜蓿、良马等物象纳入到诗歌书写中。陈敬宗诗云:“使节初从万里还,东风又度玉门关。重承凤诏安番落,曾见龙媒进御闲。”[15]365则在强调陈诚数次出关,担负着连通明王朝与西域的重任。胡广诗言:“使节重持出玉门,西行万里访河源。水泉泛处经疏勒,冰雪消时过大宛。马上看山逢汉使,帐前切字学番言。朝廷重在敷声教,好尽忠贞报国恩。”[15]365“疏勒”、“大宛”分别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里木盆地西缘喀什噶尔绿洲中部和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一带,“水泉泛处”“冰雪消时”则暗示出使西域历时长久。诗中特别提到陈诚此行着力学习少数民族语言,以达到与对外交流沟通,传播中原文化的目的。
(二)未知何日勒燕然:建立功业的疆场
河西地区作为中原与西域来往的咽喉要道,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历史上诸多将领在此树立勋业,为明人所乐道。同时也成为积极进取的典范,进入了他们的书写中。刘伯燮《寄助甫兼呈本宁四首》其一诗云:“百战入关知李广,片槎出塞尚张骞。”[34]唐之淳《从军行》诗云:“都护书传羽箭中,班生掷笔酒泉东。”[37]指出河西一带是班超立下赫赫战功的地方。与前述诸作稍异,吕㦂《挽伏羌侯毛公》诗赞颂的是本朝河西名将毛忠,称其“二十灵州拥胜兵,四朝身任一长城,中原每惜廉颇老,西域犹尊定远名。日昃挥戈分大战,星芒随矢堕前营,堂堂追宠河山誓,庙食丹青炳若生。”[12]629毛忠在英宗朝任都督同知,同西宁侯宋诚出镇甘凉,期间“兵出凉州,三战三捷[38]。后在平叛战役中为流矢所中,壮烈牺牲。
前贤可追,因此在写给赴任河西的友人的明诗中往往含有许多殷切期许,希望友人建功边陲,有所成就。胡奎《送百户徐叔之甘州》诗云:“万里无烽燧,功归定远侯。”[26]424王世贞《送助甫使君赴河西》诗云:“但使酒泉长似酒,不须金谷徧成金,鱼肠唤汝终投笔,燕颔封侯始称心。”[39]545这些诗歌赠给即将赴任河西的好友,诗中引用班超的典故,寄托了好友能建功立业的祝愿。杨士奇《送曹都御史赴甘州》诗云:“绣衣骢马引双旌,手捧纶章出帝城,满路桃花飞乳燕,夹堤杨柳带流莺。关西旧识霜威肃,塞上今传氛祲清,昭代有才当显用,会看竹简记勋名。”[40]表明诗人坚信友人德才兼备,处事严谨,日后定会大有作为。岳正《送定西蒋侯出镇甘肃二首》诗称:“重镇雄藩最上游,三边西去是甘州,封疆出塞犹千里,人物中兴第一流。公暇含毫吟蟋蟀,日长麾羽练貔貅,泾阳部曲今犹在,应说风流似祖侯。”[41]“吟蟋蟀”“练貔貅”是对友人洒脱自由生活作风的刻画,同时赞美友人出类拔萃,性格豪放豁达,其成就可与先祖相提并论。
这种实现自我价值的诉求和以身许国的情怀,使得相关作品增添了豪壮的气格和动人的力量。王越《赠朱都宪巡抚甘州》诗云:“十年不作还家梦,一饭难忘报国心,闻道酒泉忧旱久,墨池春水是甘霖。”[12]198赞扬友人戍守甘州期间勤勉恳悃,“墨池春水”指代友人竭尽所能为国效力的政举,传达了尽忠职守的精神。更多的类似表达出现在了歌行体等拟作当中,沈炼《邯郸少年行》诗云:“黄金只为酬知已,赤骥将来猎酒泉。席上弦歌教出塞,室中图画尽三边。鸣笳每愤边戎入,折戟常轻汉将权。安得一悬金印出,长驱万里勒燕然。”[42]王廷陈《少年行六首》其六诗称:“应募去幽燕,长驱出酒泉。楼烦既已破,休屠亦复残。耻隶骠骑部,岂屑轻车官。归来见天子,长缨牵左贤。”[43]于慎行《阁试征西将军出塞歌》诗云:“酒泉亭障接乌孙,辎重如山入塞门。五云阙下报天子,万里封侯安足论。”[44]这些作品背后饱含着诗人征战边塞、浴血杀敌的强烈愿望。
然而明代国力远不及汉唐,尤其明代中期以后国势渐衰,在与外族对抗的战争中往往落败,反映在诗歌书写当中表现为警醒、悲愤之音。李梦阳《赠赵将军》诗云:“大同反刃血未干,甘州累卵人心寒。”[45]康海《赠王显之》诗称:“壬申以来兵事烦,甘州一带如痺肘。”[46]唐龙《塞上曲八首为邃翁先生赋》诗称:“前年回子围甘州,杀人如麻飞鸟愁。”[29]均提到游牧民族屡次入侵,甘州一带岌岌可危的情状。明王朝实力不济的客观情况导致明人建功边陲的志向逐渐消沉,或流于应酬中的客套之言,明人对河西的认知也产生了新的变化。王世贞《咏戍卒》诗中写道:“岁岁从军出酒泉,未知何日勒燕然,相逢莫更嫌衰贱,多少黄沙掩少年。”[39]601屡屡战败使得无数士兵暴骨沙场,所谓“勒功燕然”则遥不可及,使得诗歌书写中苦痛之词频频出现。边境民不聊生,军队士气低落,深陷屡战屡败的困境,郑善夫《侠客行》诗云:“落日吹杨柳,沙场恨未穷,莫收张掖北,复失酒泉东。”[47]一语道出彼时明王朝军队首尾难顾,疲于奔命之窘迫。所谓“闺中莫道腰围减,塞上难辞鬂发丝”[48],此时像明代初期《挽伏羌侯毛公》诗中的铿锵之音已不多见。
尽管河西地区在明人眼中仍被视为建功立业的场所,但具体到不同历史阶段,书写倾向则各有侧重。中晚明以后国力渐衰,表现在书写中涉及对外战争时普遍持消极态度,多表达边警时闻、边民流离的哀痛之情,使诗歌被蒙上了阴郁的色调。
(三)天涯多少思乡客:离家去国的戍地
明代河西地区远离中原,行旅至此的各色人等中,有一类较为特殊,他们是谪戍边关的罪臣,其中以刘大夏较为典型。据《明史·刘大夏传》载:
大夏忠诚恳笃,遇知孝宗,忘身徇国,于权幸多所裁抑。尝请严核勇士,为刘瑾所恶。刘宇亦憾大夏,遂与焦芳谮于瑾曰:“籍大夏家,可当边费十二。”三年九月,假田州岑猛事,逮系诏狱。瑾欲坐以激变律死,都御史屠滽持不可,瑾谩骂曰:“即不死,可无戍耶?”李东阳为婉解,且瑾诇大夏家实贫,乃坐戍极边。初拟广西,芳曰:“是送若归也”,遂改肃州。大夏年已七十三,布衣徒步过大明门下,叩首而去。观者叹息泣下,父老携筐送食,所至为罢市、焚香祝刘尚书生还。比至戍所,诸司惮瑾,绝馈问,儒学生徒传食之。遇团操,辄荷戈就伍。所司固辞,大夏曰:“军,固当役也。”所携止一仆。或问何不挈子姓,曰:“吾宦时,不为子孙乞恩泽。今垂老得罪,忍令同死戍所耶?”大夏既遣戍,瑾犹摭他事罚米输塞上者再。[18]4847-4849
刘大夏因触怒宦官刘瑾入狱,出狱后流放肃州,年事已高,白发辞京。其《谪戍肃州故旧无敢来见者独严仲洪赠诗和答之》其一诗云:“老冒风霜万里行,蒲轮今日出都城,独怜陌上王孙草,一任寒霜不世情。”[23]528过去的交好因担心受到连累都避而不见,离京之日送行者寥寥无几,不禁使人自慨身世,宛若野草飘摇。其二诗云:“都门杨柳管人行,树底无人唱渭城,惟听崇文桥下水,激流如诉不平情。”[23]528寒风中柳枝飘摇,崇文桥下水流激荡,刘大夏联想到自身的处境,将被贬的孤苦无依之感与郁愤不平之情都融入书写中。其三诗云:“敝裘羸蹇向西行,西望阳关是肃城,回首泰陵犹未远,烟笼泪眼岂胜情?”[23]528“泰陵”指弘治皇帝陵寝。刘大夏回首京师,追忆先王,泪眼模糊。抚昔思今,幽愤之情跃然纸上。《明史》述其离京情景,仅称“大夏年已七十三,布衣徒步过大明门下,叩首而去”[18]4848,一派刚毅,但从当事人诗歌的表达中,我们能够体察到在史料记载之外的,更为生动真实、复杂可感的刘大夏。
刘大夏抵达抵达肃州后,孤苦伶仃,思乡心切,复杂的内心活动被记录在诗里。其《答同谪李侍御自俾》诗曰:“心恋故园频北望,身犹黑水此西流,感时无限悲秋意,醉后黄花插满头。”[23]526其《送李生还虞城盖尊绣衣时谪肃来省又以母老东归》诗云:“满路风尘迷顾看,连墩烟火促归程,天涯多少思乡客,惆怅椿庭送子行。”[23]526在《和冯汝阳端阳日巡嘉峪关回韵四首》其三诗中,他写道:“公事闻君尽日忙,忧勤何止佐都堂,清时共让才猷美,边地争传姓字香,汉将屯田新国计,明妃岀塞旧宫妆。端阳佳节荒凉过,独泻蒲醪倍感伤。”[23]524诗人在热闹非凡端阳佳节孤身一人,与周遭的欢乐气氛格格不入,倍感悲伤。被贬远地的苦闷与思家不得归的无奈成为了这类诗歌的主要情感基调。
除了流放河西的谪戍之人外,在此任职的朝廷官员也是诗歌创作的重要力量。他们的生活境遇和社会身份虽优于罪臣,然而常年久居边境、远离中原的客观生存境遇,使其不免涌起逐臣之感。蒲秉权《酒泉即事寄王游戎》诗称:“关山难锁天涯梦,一夜飞身一到家。”[11]676与之相类,欧大任在《重阳后一日同古比部黎秘书集张民部宅》诗中写道:“班生宁望酒泉封?旅食重阳已再逢。紫闼梦悬金涧月,白云心寄石闾松。故人薄禄多官酿,狂客酣歌待禁钟。手把茱萸还强饮,明年何地忆追从?”[49]这类书写均表达了行边者多年远离故土,羁留异乡的苦痛。王恭在其《书王明府家庆》诗中写道:“几年戎马怅分飞,此日君恩赐独归,张掖寒云行处满,鲁城霜雁别来稀。西江买棹寻花县,南国趋庭换绿衣,官满他年应昼绣,吴门乡树碧依依。”[50]其中的思乡之情浓烈沉重,使人动容。像如“一去三年边月苦,归到家时消百忧”[51]之类的摹写在明代语涉河西的诗作中屡见不鲜,既是对行边者情感的写照,也反映出明人对河西诸多认知当中包括有“远戍”的意指。
三、结语
在明王朝着意经营河西的同时,明诗中亦出现了紧密关涉河西的书写态势,并由此呈现出多样的河西风貌:就自然特征而言,相关诗作鲜明地突出了河西走廊一带年温差大的气候特征与复杂多样的地理面貌;在军备活动方面,则较为生动地记录了河西地区修筑边防工程、屯田备战的场面;就地方物产而言,相关诗歌对河西一带出产的作物,如葡萄、苜蓿、枸杞等进行了细致地描摹与吟咏。值得注意的是,明诗中所呈现的河西风貌是杂糅了作者主观思维的二次呈现,有的笔触能够与现实贴合,而有的笔触则掺入了作者的艺术想象与夸张,因此它并不完全等同于明代河西的客观历史样貌。
借助明诗中所构建的河西风貌,可以窥见明人头脑中对于河西地区的基本认知:首先,它是中西往来的交通要道,无论是汉博望侯张骞,还是明代著名使节陈诚,均经由河西走廊出使西域。是河西走廊连通了中原和西域,对于明人而言,其作为通往域外世界的“通道”意义非常明确。其次,作为建立功业的场所,河西地区凝聚了明人对于保卫国家、实现自我价值的期待,在书写中被投注了不同寻常的热情。而这种热情随着明代中期以后国势渐衰逐渐消歇,反映在诗作中,表现为警醒、哀痛之音。最后,作为明代官员贬谪的戍地,河西地区远离中原,“远戍者”在对河西地区进行文学表现的同时,往往对其附着以悲苦意蕴。
尽管在艺术水准与题材开拓上,明诗中的河西书写难以与前代、尤其是唐代边塞诗比肩,但就身赴河西者如刘大夏、陶谐而言,其诗歌在书写的纪实性与细致程度上较前代有所加强和推进。例如前述对旅途见闻的记载,对河西地区风土人情的书写、对边塞屯田备兵场面描摹、对个体遭际的喟叹等,这些方面均有力地增强了作品的纪实性与细致度。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书写特征在明代边塞文学创作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许多明代赴边文士乃至僧侣,均具有自觉记录个人行边、居边生涯中日常活动的意识,例如唐龙《渔石集》、马中锡《东田漫稿》、释昙英《昙英集》等文集,均体现出非常明确的纪实观念。可以说,这种对个体历程的细致记录,或许由明人的书写习惯所致,但客观上导致其已成为明诗边塞书写区别于前代的一个重要特征。而明诗中所呈现出的河西认知,则揭示了在明代社会文化环境中,以士人群体为主的创作者对河西地区所产生的各类丰富的印象,使我们得以从细部观察明代士人群体对于作为丝绸之路重要一环的河西地区所持的基本态度。
——徐诗云素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