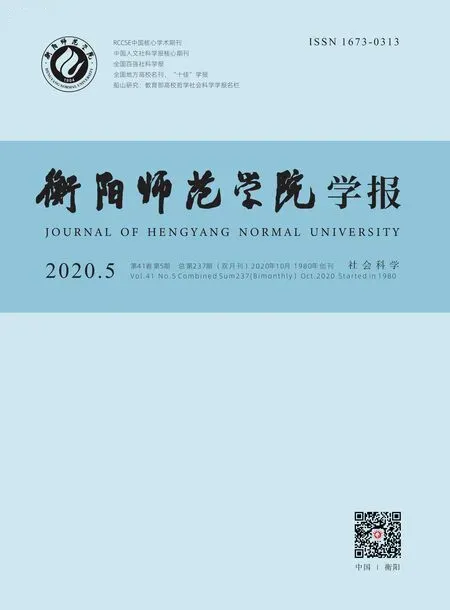传统村落的祠庙及其公共空间功能探析
——以江永上甘棠古村为例
徐红
(湖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公共空间”这一概念源自德国学者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他认为公共领域是一个“公众的领域”,“就基本上已经属于私人,但仍然具有公共性质的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中的一般交换规则等问题同公共权力机关展开讨论”[1]的场所,泛指公众讨论公共事务的场所。传统村落的公共空间是指村民们能够自由进出的场所,如村内街巷、井旁、祠庙等,这些公共空间承载着村民们的各项公共活动。在这些传统村落公共空间中,最核心的公共空间就是祠庙。祠庙是传统村落村民崇奉各类神祇的地方,具体包括寺庙、道观、祠堂等。由于中国传统社会民间信仰的多样性,导致村落中往往先后或同时出现多座祠庙,其中上甘棠古村就是如此。上甘棠古村位于湖南省江永县,历时千年,村人皆姓周,与北宋著名思想家周敦颐同祖。古村不仅保留着大量的古代民居,还先后拥有多座寺、观、庙、阁等宗教建筑,反映了各个历史时期上甘棠村民信仰的多样性特征。梁启超曾言:“某地方供祀某种神最多,可以研究各地方的心理;某时代供祀某种神最多,可以研究各时代的心理。”[2]也就是说,作为民间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供祀、信仰活动既对研究人们的观念、心理有一定的价值,也为探讨当时的社会生活、文化风俗等提供了重要依据。当我们将祠庙看作传统村落的公共空间时,它对村民生活和村落文化的影响也就非常值得探究。本文以上甘棠古村的祠庙为例,分析传统村落祠庙的公共空间功能,以期揭示祠庙对于传统村落的重要作用。
一、祠庙类型及供祀对象
依据上甘棠古村现存碑刻、遗址、周氏族谱等资料及村中老人的回忆,可以得知上甘棠古村在历史上曾先后存在过大约30 余座祠庙。由于时间的流逝及战乱的破坏,现在绝大部分祠庙的遗址已无从查考,有的仅留于村民的口耳相传中。但不可否认的是,祠庙几乎与上甘棠的历史相始终,且在古村的历史演进过程及村民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现根据祠庙供祀对象的不同,我们将祠庙大致分为以下四类:
第一类,供祀原始自然之神的祠庙。此类祠庙有广德庙、白岩庙、龙源庙、栎山庙、社庙、水神庙、竹神庙、米庙、牛庙等,它们供祀的原始自然之神种类繁多,包括土地神、山神、水神(河神)、竹神、米神、龙王、牛神等。
自然崇拜属典型的泛神崇拜,源于史前时期人们对赖以生存的自然界的敬畏心理。当先民们面对强大的、神秘莫测的自然力量束手无策时,他们就会想像各种自然物和自然现象的背后皆有神灵,如天地、山河、日月、星辰、风雨、雷电等,无不有神。先民们认为,这些神灵主宰着自然界,也主宰着人间的祸福,于是,他们通过虔诚地膜拜这些神灵,祈福避灾。自然崇拜是中国古代社会民间信仰的来源之一,其中有一些崇祀对象是绝大多数农业村落所共享的,如土地神、水神(河神)、山神等。此外,不同地域的人们在选择供祀的自然之神时,还表现出一定的地域特征,倾向于选择与其生活环境密切相关的自然物和自然现象神灵。上甘棠古村三面环山,面河而居,村子东北是昂山,东南是滑油山,西南是将军山,山上长满了竹子,西北是由沐河和谢河汇流而成的谢沐河,古村的经济形态为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因此上甘棠村民对山、水、土地及与农业有关的自然物非常重视,除了具有普遍性的对山神、水神(河神)、龙王、土地神等的崇拜外,还对竹神、米神也非常崇拜。慢慢地,传统村落的村民们对这些神祇的祭祀已不仅仅出于敬畏,还带有明显的实用目的,自然神灵的社会功利功能进一步突出。例如,清朝重修的白岩庙,最早建庙于昂山之麓,是因为昂山“钟灵毓秀……为灵秘所隐”[3]174。村民们在此庙祭拜山神,目的十分明确,就是为了祈求祛病驱邪。村民们对龙王的崇祀亦是如此。由于“叩求雨泽,大沛甘霖”[3]174,求雨灵验,故重修庙宇以奉祀龙王。可见,自然神灵由史前时期控制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主宰者,逐渐演变为满足人们现实愿望的工具:求福求吉、消灾弥难、惩恶扬善等。
第二类,供祀历史人物之神的祠庙。上甘棠古村崇奉的历史人物包括舜帝、孔子及其弟子、李靖、关羽等,一般皆属圣帝明王、古代圣贤、忠臣烈士等有功于民者,只是他们已脱离了原来的社会身份,成了超自然力的、神化的人物。此类祠庙有虞舜庙、忠厚堂、广德庙等。
舜帝是古代传说中著名的有德之君,司马迁对其评价较高:“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4]同时,舜帝对于中国传统儒学亦具有特殊的意义。在文献记载中,舜以孝行闻名于天下,虽然“父顽,母嚚,象傲”,但他却能“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汉代孔安国言舜“能以至孝和谐顽嚚昏傲,使进进以善自治,不至于奸恶”[5]。如此至孝之德,又与中国古代专制王朝所奉行的稳定天下秩序、控制基层社会的伦理观念相吻合,因此,在百姓尊崇高尚道德及官方倡导两方面力量的推动下,民间往往以舜帝作为祭祀的对象。孔子及其弟子是儒学的创始人及传播者,他们受到百姓的顶礼膜拜,是儒学世俗化、民间化的结果。上甘棠周姓与宋代大儒周敦颐同宗共祖,他们的祖先来自孔子故里山东,尊儒是家族传统,所以他们崇奉孔子及其弟子也就是理所当然了。
唐朝名将李靖,因辅佐唐太宗平定叛乱、战功卓著而受封卫国公[6]2475-2481,后人亦称其为李卫公。在民间故事中,李靖的形象与道教神灵杂糅在一起,被认为是托塔李天王,任天宫护卫,具有强大的神力,而且民间传说李靖去世后经常显灵,救民于水火之中,故民间为其立祠,将其神化。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北宋时潞城县(今山西潞城县)曾有一李靖祠,崇宁四年(1105),宋徽宗赐额“广德”[7];又,上甘棠古村《广德庙碑记》云:“庙主广惠大王世居京兆,受业河汾,藏文武才能,身作邦家巨石,荡扫漠南而安汉土,廓清江左以挽天河,功高唐朝,名标青史……祈求有感,赐福无疆。”《重修广德庙碑记》亦云:“奉李卫公为庙主。”[3]141综合上述史料,我们基本可以确定上甘棠古村的广德庙是为崇奉李靖所建的。上甘棠村民将李靖看作本村的保护神,是因为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下,祈求其护卫上甘棠不受外界袭扰,“赐福无疆”。
上甘棠古村广德庙中供奉的神灵,除主神李卫公外,还有关公。这是民间信仰的特点之一,即每座祠庙有一位主神,同时不排斥其他神灵进入同一祠庙接受村民祭拜。关公即三国时期的关羽,作为中国民间信仰的重要对象之一,关羽的形象一直处于变动之中,从有神迹、能显灵的普通神,到护佑胜利的战神,再到忠义兼备的完美形象,其传承、演进、升华的过程十分明显。上甘棠村民将关公与李卫公共同奉祀于广德庙中,一方面是将他们看作传统道德的化身而予以崇拜,另一方面则取其护村之意。 万历四十二年(1614),明神宗加封关羽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8]。这是官方第一次正式敕封关羽为“帝”,从此“关圣”“关帝”之类的称呼开始出现。到明朝末年,这样的称呼广泛存在于各地对关公的崇奉中。而且,由于此时社会秩序混乱,明王朝面临内外交困的两难境地,内有农民起义的打击,外有满清的威胁,因此明末民间信仰中的关羽,基本是以一种护国佑民的“国家神”形象出现的。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上甘棠古村难免也会受到战乱的影响,广德庙中加入对关公的崇祀,应与对李卫公的祭祀目的类似,即祈求关公卫护村庄。
可见,上甘棠村民崇奉的历史人物之神主要体现了村民两个方面的现实诉求:一是崇尚先贤往哲的高尚道德,希冀以此引领、教化村民,维护古村的伦理秩序,这是古村得以长久延续的思想文化基础;二是将历史上功绩突出之人看作本村的守护神,期望他们能够御灾捍患,护佑古村平平安安。
第三类,供祀佛教道教中的神的祠庙。此类祠庙有鱼赛庙、云归观、前芳寺、文昌阁等,供祀的有佛祖、弥勒佛、十八罗汉、观音菩萨、文殊菩萨、三清尊神、赤松子等在佛教、道教中常见的神祇。
佛教在汉代传入中国后,其内容和体系不断中国化、世俗化,几乎所有的人都可以以一种较为松散的方式参与佛教活动,这就使得佛教诸神能较为迅速地进入到民间信仰之中。不过,百姓崇奉佛教诸神与佛教徒的信仰不同,他们并不关心神灵背后佛教经典、教义的含义,他们只需要灵验的神灵,如此,佛教诸神所具有的某些特质就被无限放大了,其中最为典型的是观音菩萨。在上甘棠古村,村民对佛教的信仰也反映了这一点。菩萨在佛教体系中的定位是“道众生”“觉有情”,即求道求大觉之人,帮助佛祖普度众生。一方面,相较于佛祖的威严、至高无上,观音菩萨的仁慈形象更易于为百姓所接受,其解救众生于苦难的职能与普通百姓的功利性诉求恰好吻合;另一方面,观音菩萨在民间信仰中的“送子”功能,也使其在追求人丁兴旺的中国古代民间社会香火鼎盛。
道教是中国的本土宗教,与民间信仰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道教的某些神仙在民间有崇高的地位,如三清尊神、城隍等;另一方面,道教在很大程度上也汲取了民间信仰的因素,有着广泛的受众基础。因此,道教的传布范围更广,可谓无时不有、无处不在。道教中的部分神仙是百姓时常供奉的对象,其中以三清尊神为代表。三清尊神是道教的三位至高神,即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太清道德天尊。上甘棠的云归观中即供奉着三清尊神,镌刻于月陂亭的《云归观重塑圣像舍钱题名记》载:“圣像固坏,迨我圣朝宣德间,桃川官舍钱福捐财,塑妆三清至圣。其诸圣像盖未有焉,泰乙亥叔父周麒等化缘,毛珏等塑妆,列品圣像,慈幸完成,命予以记之。”[9]村民供祀三清尊神的目的在于驱鬼辟邪、祈求平安。赤松子本为古代传说中的仙人,“神农时雨师也,服水玉以教神农,能入火自烧……至高辛时复为雨师”[10],后来进入道教仙谱中,成为掌管下雨的神仙,上甘棠古村的鱼赛庙庙主即为赤松子。在干旱年景,村民至此进香祷告者络绎不绝。与祈求龙王的目的一样,村民们期望雨师能够普降甘霖,解除旱情,保佑农业丰收。
第四类,供祀周氏祖先神的祠庙。上甘棠古村的宗族文化始自唐代,唐宪宗时期,征南大元帅周如锡的孙辈周通璧从宁远大阳洞迁居到上甘棠境内[3]4。此后的一千多年间,上甘棠古村始终保持着单一的周氏血脉,所以村民们时常举行祭拜周氏宗族祖先的活动。祭拜祖先的地方即上甘棠的周氏宗祠,建于明末清初。祖先崇拜是早期人类对自身由来的一种神秘化理解,当时人们敬畏先祖神灵如同敬畏自然神灵一样。随着历史的演进,祖先崇拜的意义也开始发生变化,成为蕴含家族文化、联系家族成员的重要纽带,其敬宗收族的作用更加突出。
由前揭内容可知,传统村落村民们进行祭祀活动源自对未知世界的敬畏。当他们遇到各种无法解释的现象时,只能寄希望于各类神灵,以期得到神灵的保护或者帮助,由此使得村落祠庙的供奉对象较为繁杂,既有自然神、祖先神,亦有历史人物神和佛教道教中的神。不过,一以贯之的原则是不变的,即供祀的实用性和功利性,凡是对村民有用的神祇,无论出自于哪里,皆能得到村民的认可,成为他们崇祀的对象。
二、祠庙的祭祀空间功能
传统村落最基本的特征就是人的活动,而人的活动总是在一定的区域内进行的。根据活动区域的属性,我们可将其划分为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两大类。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是属于现代社会学的两个概念,把它应用于本文所论传统村落的议题中,那么私人空间主要是指村民各家各户的居所,是他们个人或者小家庭的活动空间,具有明显的排他性和私密性;公共空间则是指村民们能够自由进出、自由活动、参与公共事务的场所,承载着村民们的各项公共活动,如村内街巷、井旁、祠庙等。本文主要讨论祠庙作为传统村落公共空间的功能。既然是祠庙,其最突出的公共空间功能就是祭祀。
上甘棠古村曾先后存在过30 余座祠庙,其核心活动就是对各方神祇的祭拜。这些超自然的神灵,一方面存在于村民们的观念中,另一方面以具象化的形态被尊奉于祠庙的神台之上。通常而言,这些具象化的形态往往是神灵的一尊塑像,或者一幅画像,说明民间信仰中的神灵发展到后来,拥有更具体的人格化的特征。塑像一般以陶、木等原料塑绘而成,放置于祠庙内砖砌、石垒或木构的神台之上。村民们举行的祭祀仪式,就是面对神灵的塑像或者画像进行祭拜,因此,传统村落的祭祀活动主要在祠庙内部进行,如每年春季和秋季的社日,上甘棠古村均会举行祭祀土地神的活动,其主要程序就是在社庙内面对土地神的塑像跪拜,烧香化纸,祈求土地神保佑风调雨顺,农业生产能够获得丰收[3]142。
在祠庙中举行的这些祭祀活动,突显了祠庙作为传统村落祭祀场所的作用,体现出其公共空间的功能。总体看来,祠庙的公共祭祀功能具有神圣性、社会性、多样性、整齐性四方面的突出特征。
神圣性是祠庙公共功能的首要特征。关于上甘棠古村公共祭祀活动的神圣性表现,已无直接资料的记载,不过我们可利用间接资料说明这一点。从前揭祠庙的供奉对象来看,儒、释、道三家以及对自然神、祖先神的崇拜,共同构建起了上甘棠村民的精神世界。村民们之所以接受或者创造出这些神祇,无非就是希望这些神祇能够帮助他们理解神秘的、未知的周边世界,诠释不可预知的生命和变化莫测的生活的意义,因此,村民们始终怀着非常虔诚的心理参与到对神祇的崇祀活动中,他们认为神祇有一种神秘的力量,能够回应并满足他们的祈求。如周氏族人周标奇所撰《重修龙源庙碑记》载,龙源庙本无此庙额,是因为壬寅年,即康熙元年(1662)秋季大旱,村民们“叩求雨泽,大沛甘霖,故更其额曰‘龙源庙’”,为了报答祠庙的灵贶,村民们捐资重修祠庙[3]174。显然,对于普通百姓来说,他们总是愿意相信如此神奇的灵应故事,因为这样的故事能够给他们带来心理的慰藉,在面临无法应对的艰难境况时看到希望。
流传于上甘棠古村的一些传说亦可从侧面说明祠庙公共供奉活动的神圣性。古村路旁石壁上有一形似拳头冲击而成的穹洞,栎山庙即依穹洞而建。关于栎山庙的来源,有这样一个传说:雷公奉玉帝之命捉拿害人的蜈蚣精,可是蜈蚣精躲藏起来了,雷公找不到,所以就问栎山庙神,但庙神却言不知情,引得雷公发怒,挥拳打向庙神,庙神侧身躲过,雷公的这一拳就落到石壁上,留下了这个穹洞,于是村民们就在这里建造了栎山庙[3]142-143。从现代科学的角度而言,这个故事纯属无稽之谈,但在其出现之时,村民们更愿意信其有,或者说创造这个故事的人希望村民们信其有,这种现象反映了村民们神化祠庙的复杂心理。也就是说,他们试图用这样的神化故事告诉大家,不可疏忽供奉祠庙之神的活动,因为这些神祇均与上天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如果崇祀不当,将会遭到惩罚。可见,附会于祠庙及神祇上的神话故事,使村民们的公共祭祀活动具有较为突出的神圣性。
除特殊情况外,祠庙的祭祀活动均要求村民们必须参加,这体现了祠庙公共活动的社会性特征。在村民们看来,祈求神祇护佑、风调雨顺或者驱邪避凶等事务,皆与古村所有村民的利害相关,若拒绝参加,则会受到他们的抵制和藐视,这样的人也就无法在古村立足。一般说来,传统村落公共祭祀活动的主持者或者发起者,往往是村落中的士绅、族长或者宗教人士。其中士绅应该是组织祠庙公共活动最主要而持久的群体,他们基本都是读书人,有的还曾通过科举考试或其他途径出任朝廷官员,在地方上有较强的影响力。就上甘棠古村而言,张官妹等人曾对出自上甘棠的官宦人士做过统计,发现由唐至清上甘棠周氏族人为官者约有60 余人[11]60-66,而且从后人所写小诗看,绝大多数官宦具备两个共同的特点:一是通儒经,有学问;二是德行高尚,声名远播。他们与古代中国绝大多数外出为官者一样,在辞官或者致仕之后回到家乡,因贤能而成为当地的精英,拥有较高的威望,对本村事务有很强的话语权,自然就成为祠庙公共祭祀活动的组织者。他们以乡村贤达的身份组织祭祀活动,要求所有村民参加,就是希望达到教化百姓、稳定古村秩序的目的。
上甘棠古村祠庙祭祀的神灵,既有佛教道教之神,也有民间信仰的神祇,既有全国性的观音菩萨、三清尊神、土地神等神明,也有地方性较强的竹神、米神、牛神等神祇,因此,祠庙公共活动还具有多样性特征。上甘棠地处湖湘腹地,与外界的沟通并不是十分方便,自给自足的经济生活又使他们与外界的交往较少,因此,一些土生土长的地方神存留于古村中,受到村民们的崇祀。此类地域特征突出的地方神的存在,亦与宋代以后礼制观念的下移有一定关系。《礼记》曰:“有天下者祭百神。诸侯在其地则祭之,亡其地则不祭”[12]1787,“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无福”[12]204。受其影响,民间普遍认为,只有祭祀本地的神灵才会灵验,若祭祀“非其所祭”的神灵,则无法达到祈福的目的。这是地方神存在的思想基础,所以竹神、米神、牛神之类的神祇就成为具有上甘棠特色的祭祀对象。
值得注意的是,传统村落祠庙的祭祀对象也不排除全国性或外地的神祇。由于宋以后经济的发展及科举制度的推行,人口流动较之前频繁,加之上甘棠周姓本身就是从外地迁居而来的宗族,因此,在民间信仰上也就出现了祭祀越界之神的现象。当然,更重要的还是基于这些外来神祇灵应故事的传播。前已述及,自唐至清,从上甘棠古村走出了不少读书人,其中的优秀分子通过科举考试入仕为官,当他们置身于中央或其他地方时,某位神祇的灵验恰好能够满足他们的需求,于是对这一神祇的信仰很可能就经由他们传入上甘棠。而上甘棠周姓本身就与大儒周敦颐同族同宗,有崇尚儒学的传统,因此对自小读圣贤之书的士人、官员十分敬重和信任,再加这些神祇的灵验故事也很符合村民的心理,所以他们很自然就接受了这些经由读书人传播而来的外来神祇。
可见,对于传统村落的村民们而言,祀神的原则就是有用,为此不惜内外神灵通祭,这样就导致古村祠庙的公共祭祀活动比较多样,在一年中的任何时候,只要有需要,都可以举行祭祀活动。为了祭祀的方便,村民们还将数个神祇置于同一祠庙之中,即每一座祠庙都有一个主神及其他神灵,这些神灵共同接受村民们的祭拜,如广德庙庙主为李卫公,同时还有关帝、土地神[3]141。不同的神灵主管的事务不一样,所以村民们一般会根据所要祈求的内容,选择合适的神灵进行祭祀。
祠庙公共祭祀活动的整齐性特征亦较为突出。所谓整齐性,是指举行祭祀活动时秩序井然,讲究上下尊卑的宗法等级。虽然祠庙是传统村落的公共祭祀活动场所,全体村民皆可自由进出,很多公共祭祀活动也要求相关村民共同参与,但是这样的公共祭祀并不是随意为之。为了获得神灵的福报,也是为了体现传统村落的宗族权威,维护宗族内部的礼制秩序,使得祭祀活动具有了整齐性的特点,这在祭祀祖先的活动中得到了较为完整的体现。
上甘棠古村周氏族人祭祖的场所是周氏宗祠。宗祠为一座两进的建筑,大堂内的神台上放置周氏先祖牌位,且按照昭穆之序,由中间向两边,由前到后,依次排列。在每年清明、中元或其他约定的时间,族长带领周氏成年男性在祠堂举行敬供祖宗的活动,祈祷祖宗保佑全族人安康。祭祀祖宗之时,必须“衣冠整齐,行列翼如,言笑不苟”[11]55,如果祭祀不及时,或者不恭敬,则“祖宗虽灵必不默为呵护汝曹”[11]57。可见祭祖仪式包含两个方面的严格要求:一是适时祭祖,不可荒废;二是要对祖宗保持恭敬、谨慎态度,即参加者衣冠整齐,队列有序,不苟言笑。族谱用到“翼如”一词,“翼”有两种解释,《诗经·采薇》言:“四牡翼翼,象弭鱼服。”[13]841“翼翼”指军列整齐,训练有素。另《诗经·大明》言:“维此文王,小心翼翼。”[13]1391这里的“翼翼”则指恭敬、谨慎。结合前后文,族谱中的“翼如”可以理解为祭祖时同族成年男性按照长幼、辈分顺序列队于祖宗牌位前,以恭敬的态度进行祭祀,这最能体现祭祖的整齐性。
对祖宗的崇拜有利于增强宗族的凝聚力,起到敬宗收族的作用。上甘棠古村能够在上千年的历史中始终保持周氏血脉的高纯性,并形成独特的文化传统,与村民们对祖宗的崇拜有密切关联。祖宗牌位的昭穆有序,祭祖队列的长幼、辈分次序分明,是祭祖活动的重要表现形式,这种整齐性的示范作用不可低估,它对明确宗族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规范古村秩序有着重要意义。
三、祠庙的其他公共空间功能
传统村落的祠庙除了作为公共祭祀场所外,还承担了其他一些公共空间功能。
首先,充当古村的学堂。上甘棠古村的传统包括农业传统和儒学传统两个方面。周氏族人从唐朝始祖周弘本起,就一直有人在朝中为官,且世代耕读传家,儒风浓郁,可谓“诗礼相传千载盛,家兴丕振万年芳”[11]48。古村建筑亦处处显示出对儒学文化的推崇,如位于谢沐河上的步赢桥,建于宋代,《步赢桥记》云:“大唐十八学士,居天子儒宫,备顾问,时况以登瀛洲焉。其意亦谓仕宦而至华近者,诚在于能修德而阴有以陟之尔……周氏于此修瀛洲之德欤……遂名之曰步赢桥。”[14]696可见步赢桥命名即取“步入瀛洲”“步步高升”之意。《步赢桥记》部分内容源自《旧唐书》的记载,其言唐太宗因“留意儒学,乃于宫城西起文学馆,以待四方文士”,并选拔杜如晦、房玄龄、虞世南、褚亮等十八人入馆,时称“十八学士”。“每军国务静,参谒归休,即便引见,讨论坟籍,商略前载”,体现出唐太宗对儒学人才的重视,当时的儒学士大夫们皆以能入馆为荣,“预入馆者,时所倾慕,谓之‘登瀛洲’”[6]2582-2583。上甘棠村民将新修之桥命名为“步赢”,其寓意非常清楚,就是希望周氏子弟能够通过勤奋读书,科举及第,平步青云,光宗耀祖。受这一观念的影响,上甘棠古村除重视劳动耕作外,也特别关注族人子弟的读书入仕,规定学龄儿童都应该去学堂读书。有时候由于学生人数太多或者其他原因,学堂不足以容纳子弟学习,就利用村中的祠庙充当子弟的学堂,如修建于唐代的虞舜庙及周氏宗祠,都曾是古村的学堂。
其次,祠庙及其周边还是上甘棠村民们进行休闲娱乐活动的公共场所。随着历史的演进,社会经济逐渐发展,一些神灵的身份亦随之向世俗化方向转化,在不影响其神秘性、灵验性的前提下掺入了世俗、娱乐的内涵,这就使某些原先严肃的公共祭祀活动演化为兼具祭祀、娱乐等功能的公共集会活动,活动的场所也越出祠庙内部的范围,开始扩展到祠庙前的空旷地带。据《光绪永明县志》记载,在每年的秋季,县城都会举办所谓“报赛”活动,即民众为了祈求、报谢神祇而举行的、以抬神出巡为核心的定期集会。“出巡之日,神舆前后仪仗具备,绅耆拈香步行,杂以巫觋,爆竹喧填。神过之处,沿途居人、铺户筵祭诚肃,巫觋则至人家跳鼓吹笙,口中邪许相和,以为祓除”,且“庙中灯烛辉煌,歌台剧早登场”,这样的活动要持续五日或者七日[14]301-302。秋天正是农业收获的季节,这时举行的报赛活动反映了报谢神灵时喜庆、热烈的景象,对于普通百姓而言,不啻是一个节日。上甘棠古村的报赛活动是在天井庙前的空旷地带举行,“先于庙前辟广场,架横木。择牛之色纯而壮健者,以绳曳牛首于横木,以猛勇者一人操大刀,将牛项一刀决之”,与县城的报赛活动一样,也有仪仗,只是“略减而已”,亦是持续数天时间,观礼之人除本村村民外,还有附近十里八乡的民众,可谓“观者如堵”[14]302。可见,上甘棠古村报赛的对象是自身奉祀之神,其渊源是民间最普遍的祈福避灾、谢神感恩的心理,其集会的地点、时间相对固定,参加者以上甘棠村民为主,同时包括附近乡村的民众,其影响范围不限于本村。而且,这样的活动已演化为围绕祠神报谢举行的民众集会,祠庙及其附近就是人们娱乐、集会的公共场所。村民们热衷于参加报赛活动,除了报答神祇、祈求来年的好收成外,越来越多地是为了休闲、娱乐的目的。村民们在祠庙及其附近共同分享祭品,饮酒作乐,聊天谈笑,报赛的仪仗也演化为一种表演,为文化生活相对匮乏的乡村带来欢乐,数日的报赛活动也就因此而成为村民们狂欢的节日。不过,即使是这样的休闲娱乐活动,也包含着教化的目的,如抬神报谢的宗教内容、仪仗表演的整齐有序,无不指向儒学所推崇的伦理规范。这类活动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维持乡村秩序、凝聚族人思想的基础。
上甘棠古村周氏祖先与大儒周敦颐的亲族关系以及儒学传家的传统,使得上甘棠的文化氛围较为浓郁,因此,除了本村的娱乐活动外,上甘棠的祠庙建筑也吸引了远近的文人墨客前来游览,成为文人雅集的盛地。周氏族人周仁泽曾言,村内的寺、观等祠庙自修建以来,“非独有以崇奉佛教,而实使之蔚起人文”,文人游览于祠庙之间,“往往于兹怀雅兴焉”[3]137。村中月陂亭的摩崖石刻即保留有文人的诗作,为上甘棠的历史文化增加了浓郁的人文气息。例如,南宋永明县令傅圣泉曾与友人共同造访上甘棠,在遍游上甘棠的亭台楼观庙之后,留下了这样的诗句:“月波楼扁认初寮,万仞依山作小楼。险石罅边沿曲径,响波声里济清流。千章古木参天密,百顷香粳趁日收。地步已高人更杰,看君接武上瀛洲。”①傅圣泉的这次游历是否为周氏族人所邀已无从查考,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与其同游者皆为崇尚儒学的文人,应该还有诗酒唱和,只是可惜年代久远,仅傅圣泉一诗得以保存,不过从傅诗的内容我们还是可以感受到傅圣泉及其文友,因身处与周敦颐有联系的上甘棠而生发出来的感慨。诗中谈及月陂亭上有初寮的作品,初寮即王安中,北宋末南宋初人,文才十分出众,“为文丰润敏拔,尤工四六之制”[15],颇得宋徽宗赏识,因有《初寮集》而号“初寮”。王安中在宋高宗时曾任职于道州,很可能来过上甘棠或者为上甘棠写过诗文,故月陂亭的摩崖石刻中曾经有王安中的诗。可见,上甘棠的亭台楼观庙及其周边的公共空间也是古代文人的聚会之处,他们往往因仰慕周敦颐或受邀于周氏族人而来,三五文友,七八同僚,徜徉于祠庙间,吟诗唱和,留下了不少作品,为上甘棠古村的文化生活增加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文人儒士雅集本身,亦受到村民们的钦羡,借由文人的这种身份和影响,儒学所推行的伦理道德也就潜移默化地成为村民们认同的观念和习俗。
四、结语
祠庙是传统村落的灵魂,更是村落的公共活动空间。在这个空间举行的以祭祀为核心的公共活动,体现了村民们信仰的实用性和功利性原则,因为他们似乎并不在意崇祀的对象出自哪里,也不太能够分清哪些是佛教的神灵,哪些是道教、抑或民间宗教的神灵,他们只需要有用的神祇。村民们这样的诉求使得祠庙的公共祭祀功能表现出神圣性、社会性、多样性、整齐性等特征,由此形成一种集体话语和共识,即公共祭祀活动能够维护古村的社会秩序,团结宗亲,并保证古村得以绵延不绝。同时,随着历史演进,祠庙的公共空间功能又衍生出了新的内涵——儒学传承和休闲娱乐。儒学传统是中国大多数传统村落的共同特点,其中某些村落,如上甘棠古村表现得更为突出,这种以祠庙作为传承儒学的公共场所显然是儒学渗透的必然结果。休闲娱乐是祠庙公共祭祀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以报谢、祈福为中心的祠庙公共娱乐活动一方面满足村民们的精神需求,为他们单调的生活带来乐趣,另一方面也是村民们接受伦理教化的方式之一。由于上甘棠特殊的崇文传统,祠庙及其周围还是文人墨客吟诗唱和的交友之所,他们的活动使古村的文化氛围更为浓郁,也更有利于推行儒学的伦理道德。可见,传统村落的祠庙及其祭祀、休闲、文化等公共空间功能是村民们精神生活的重要表现,亦是村落历史记忆得以传承的主要方式,它们构成了传统村落精神世界的根基,并从伦理教化、规范秩序、凝聚族众等更深的层面,影响到了村民们的观念意识和日常行为。
注释:
①月陂亭摩崖石刻的个别字词已模糊不清,难以辨认,故以《光绪永明县志》卷五○《傅圣泉月波楼诗有跋》校之,参见万发元修、周诜诒纂《光绪永明县志》,南京:凤凰出版社,2002 年,第701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