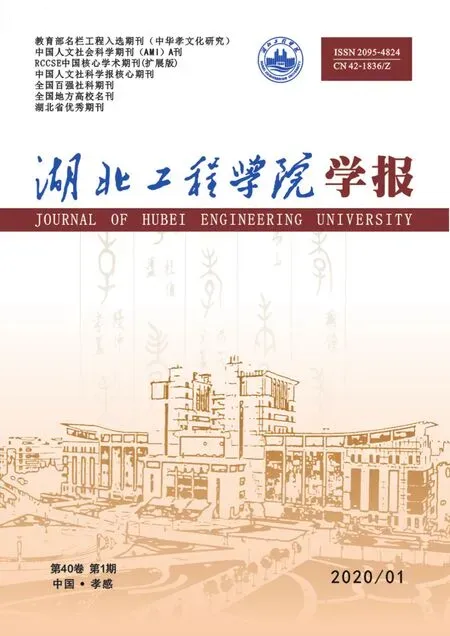金驲孙与韩愈孝道思想之比较
——以金驲孙《非鄠人对》和韩愈《鄠人对》为例
娄玉敏
(曲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曲阜 273165)
“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论语》中就记载了孟懿子、孟武伯、子游、子夏分别问孝于孔子的事,以后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重视对“孝”的弘扬,唐朝时期还专门设有“孝廉”,对那些孝行突出的人授予官职,以此旌表。自隋朝陈杲仁的“割股疗母”受到政府旌表后,唐朝也出现了割股为父母治病的现象,并为时人所推崇。据《新史孝友传》记载:“唐时陈藏器注《本草拾遗》,谓人肉治羸疾,自是民间以父母疾,多刲股肉以进,或给帛,或旌门阊。”[1]韩愈极力反对这种做法,写了《鄠人对》这篇文章,对这种“愚孝”行为予以批判。几百年后,在海东朝鲜,有“东国之昌黎”称号的金驲孙写了《非鄠人对》来反驳韩愈,申明了自己的孝道观。下面以这两篇文章为例,进一步论述韩愈和金驲孙孝道思想的异同及成因。
一、 “愚孝”、“至孝”之争
金驲孙(1464-1498),字季云,号濯缨,是朝鲜李氏王朝著名的文人,性理学家,在当时社会中有很高的名气和声望,南孝温曾说他“德器似韩魏公,学术似董广川,才识似蔡西山,文章似韩昌黎”[2]。他的文章气势豪迈,奔放雄博,“为文章,下笔千百言,奔放雄博,读者皆呿舌,华人目之曰:‘此韩子也’”。[3]世人由此称其为“东国之昌黎”。
《非鄠人对》是金驲孙读了韩愈的《鄠人对》之后有感而发的作品,由于说理透彻,理论性很强,成为当时的名篇,“濯缨子非鄠人对,南秋江鬼神论,李晦斋与曹忘机论无极太极数书,皆足以为发明道理之文,而示于上国之名儒者也”[4]。韩愈在《鄠人对》中,极力批判鄠人“割股救母”的“愚孝”行为,认为这是时人沽名钓誉的手段,是大不孝的做法,“其为不孝,得无甚乎”[5]758,甚至进一步批判了旌表这种鼓励孝行的政策,认为对于这样的人,“不腰于市,而已黩于政,况复旌其门”[5]759。金驲孙在《非鄠人对》中对韩愈的观点表示强烈反对,他认为鄠人“割股救母”的行为是其“至孝”思想的体现,并用种种例证,据理力争,来阐明自己的孝道观。
《非鄠人对》全文如下:
唐之时,鄠人有母疾,剔股以奉之瘳,令尹以闻,旌其门,使勿输赋。愈曰:“母疾则止于烹粉药石,未闻有毁伤支体以为养,其为不孝,得无甚乎!苟有合于孝道,不当旌门,生人之所宜为,曷足为异。”愚窃非之,凡为人子,父母有疾,千方万药,必获一效,至于迎巫祝祷鬼神,虽揣其妖妄,亦将无所不为矣。就令善医者引方书,以为非人肉合药,无良云尔,将以彼为诞,坐视其母之死而不从耶?万一冀其复生,而不惜支体耶?吾之支体,即亲之遗体,古人以全归为孝,则伤其支体,固伤于孝,然吾惜吾之支体,则他人亦自惜其支体,谁肯毁其支体,为他人母哉?然则药终不可得,而疾终不可愈。就令退之,不幸而处此,当如何?君子未尝不惜其身,然此身有时惜不得者,常出于不得已之变。于是而子死于孝,臣死于忠,即退之所谓死于逆乱者也。临逆乱,不惜身命,固也,当危疾,吾不至于死,而顾惜一块肉乎?当危疾,顾惜块肉者,其临逆乱,不苟生乎?退之又以陷危难,能固其忠孝而不苟生,然后旌表爵名,斯为劝已。如是则为子为臣,当平居,无尽孝尽忠之地矣。如是则朝家非危难,亦不得忠臣孝子之用矣,况性分内事,莫非生人之所宜为,常人不能充其性,惟圣人能尽其性。剔股一事,初非尽性者之所为,推其言之弊而断之,则将以尽其性者,生人之所宜为,而夷圣人于常人,不异之地耶?噫,古今天下,谁无父母?谁非人子?能尽子道而孝于父母者盖寡,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者比比,夫货财外物,妻子虽一体,视吾身有分而尚私之,况于其身乎。世之知有其身,而不知有父母者何限,杯羹汉祖,截裾温峤,虽以盛帝名臣,到头一念,犹不知有父母矣!若鄠人者,虽谓知有其母而不知有其身,可矣!所患世之诡异者,残忍果敢,为不经之行,要一时之赏者或有之,是诚可罪也,如曰以一人为孝,是辨一邑皆无孝者,尤非古之圣贤,因所遇不同道,故时之人后之人,循其迹举其盛。圣贤为学,莫不于孝悌上立本,而自生民以来,独称舜为大孝,曾参养志,其余无凭,圣贤皆非孝者耶。愈说若行,媢嫉者得志,将忌人修而蔽其行,阻天下之孝,骇众人之听,其为害不既多乎!或曰:“退之立言,是也!平生好古道,为理胜之文,岂鄠人非诚于孝,内外殊观而攻之迫耶,退之攻鄠人诚迫,而子攻退之又何迫耶?大朴散而巧拙形,大素文而黑白分,夫不表一人之孝于一邑者,待一邑之人咸孝也,其意浑矣。尝见新唐史书,以人肉治羸疾,父母疾多,刲股肉以进,或给帛,或旌门,当时已不胜滥矣,以此为劝,则将尽刖天下之人,不可以身教,而方尽子职之常者,将不得为孝矣,退之岂无所见而言非耶?对曰:“先王为民立教,非不浑且厚矣,乃曰旌别淑慝,未尝曰以一人为淑,是辨一邑无善也,阴阳判而善恶分,善恶既分,不能无过不及之差,故律之以中庸。中庸之道,民鲜能久矣,故曰观人,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剔股虽过,斯亦孝之党也,断以不孝,不亦过乎!生其养,病其忧,殁其哀,至于所属之发肤,不敢毁伤,敬以终身,伤足不出,启手知免,乃孝子之常经也。或不得已而以一身致于君父,则轻甚鸿毛者有之,况于股肉哉!股不剔而药有别种,可治母疾,则吾不必矫情以剔股也,药无别种,而股不可不剔,则虽得罪于中庸之君子,吾亦为鄠人矣。夫立言者,要于中庸,垂之不朽,通万世而无弊,吾观鄠人对,其言多弊,吾又疑其杜撰,而非出于退之也,不然,鄠人之行,既非中庸,而退之之对,亦非中庸也。[6]
朝鲜王朝固有“子孝于父”的孝道思想,与儒学伦理理论相结合,进而提出了子女对父母尽孝是天经地义的事,将孝道列为人伦的最高原则,这就使得孝道入民间,成为人们事亲的行为规范。[7]金驲孙也深受这种观念的影响,在这篇文章中,他首先从人情方面极力反驳韩愈,认为鄠人割股救母是人之常情,“凡为人子,父母有疾,千方万药,必获一效,至于迎巫祝祷鬼神,虽揣其妖妄,亦将无所不为矣”。无论用什么方法,只要是有利于治愈父母疾病的,都要不遗余力地去尝试,不能因为顾惜一块肉就让父母死于疾病。韩愈则遵循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8]的正统儒家孝道观,认为这种做法不仅为义理所不容,而且是大不孝的,“苟不伤于义,则贤圣当先众而为之也,是不幸因而致死,则毁伤绝灭之罪有归矣。其为不孝,得无甚乎”。但金驲孙又从“忠孝”两个方面反驳韩愈,认为如果只有那些面对危乱不顾惜性命的人才被认为是忠孝之人的话,那么大家都会一样平庸无为,如果国家没有遭遇危难,忠臣孝子将无用武之地,“如是则为子为臣,当平居,无尽孝尽忠之地矣;如是则朝家非危难,亦不得忠臣孝子之用矣”。随后,金驲孙提出了自己对鄠人“割股救母”行为的看法,他认为这种做法是“至孝”行为的极好展现,并不是只有圣人才能做到,而是有情有义之人皆能做到的,况且“古今天下,谁无父母,谁非人子,能尽子道而孝于父母者盖寡,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者比比”。鉴于此,金驲孙认为鄠人的做法是应该被表彰的,如果因为害怕有人用这种方法沽名钓誉而对这种至孝行为全盘否定,那就是“因噎废食”了。最后,金驲孙站在儒家“中庸之道”的立场上对韩愈的观点进行了批判,认为韩愈“以一人为淑,是辨一邑无善”的观点太过于绝对化,不符合儒家的“中庸”之道,由此甚至对韩愈这篇文章的真实性进行质疑:“夫立言者,要于中庸,垂之不朽,通万世而无弊。吾观鄠人对,其言多弊,吾又疑其杜撰,而非出于退之也,不然,鄠人之行,既非中庸,而退之之对,亦非中庸也。”
由以上分析可知,金驲孙通过《非鄠人对》对韩愈在《鄠人对》中提出的观点予以反驳,论证严密,层层推进。正是因为这篇文章,金驲孙才在当时获得了“足以为发明道理之文,而示于上国之名儒者”的盛誉,这也奠定了金驲孙性理学大家的正统地位。
面对同样的孝行,金驲孙和韩愈给出了不同的看法,鄠人“割股救母”的行为到底是“愚孝”还是“至孝”。金驲孙表示自己虽然赞同官方表彰鄠人“割股救母”的做法,但有人用这种方法“沽名钓誉”,他还是深恶痛绝的,这又和韩愈的观点不谋而合。
二、孝道观分歧的原因
金驲孙与韩愈虽然都是儒家思想的传承者,但面对同样的孝行时,他们却给出了不同的看法与评价,这是不同的早年经历和相异的社会环境造成的。
1.成长经历。
(1)金驲孙的成长经历。第一,家风熏陶。金驲孙生于儒学世家,其祖父金克一以孝行闻名于当时,世称“节孝先生”,金克一曾为其母吮血吸毒,为其父尝痢观病,尽心奉养父母,在父母去世之后悲痛欲绝。权鳖在《海东杂录·孝子》篇中说他“性至孝,为母吮疽,为父尝痢”。母亲去世后,金克一“勺水不入口,几至灭性”,卜葬于距家三十里地,因庐其侧,每朝夕奠后,必草以屡徒步来省父,虽隆冬暑雨,终不少懈。[9]可见,金克一的孝行在当时是十分突出的,并为世人传颂,人们把他和曾子、黔娄相提并论,其事迹被载入朝鲜王朝当时的至孝读本《三纲行实》之中:“亦粤持平臣克一,幼有至行,事亲极孝。母疽吮血,父病尝痢,前后丁忧,庐于墓侧,晨夕号哭,若在始殡,诚感殊类,至有虎驯之异,事闻, 光庙特命旌闾,事在三纲行实。”[10]
“近朱者赤”,在这样的至孝家风环境中长大的金驲孙必然耳濡目染,将这种至孝观念潜移默化地融入其日常行为之中。他在做官期间,为了方便照顾母亲,曾以病为由辞官:“明年,出补晋州学官,时仲氏乞养监昌宁县,公为便省母计也,戊申,病辞。”[11]由此可见,家风的影响力是巨大的。
另外,金克一就如鄠人一样,因其孝行而使整个家族得到旌表,虽然他无心于外在的盛名荣誉,在父母去世之后仍潜心研习性理之学,但愈是这样,他的声名就愈大,被世人称为“节孝先生”。无论如何,金克一是这种“至孝”行为的既得利益者,所以,金驲孙在看到韩愈对鄠人的批判时,就予以反驳,来肯定鄠人的至孝行为以及官方的旌表,其实也是从侧面捍卫其祖父金克一的孝行,维护家族利益。这或许是其“至孝”思想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师长教育。金驲孙的老师金宗直也是一个节孝之人,金宗直在其母生病期间,尽心侍奉,昼夜不离,晨昏定省,奉养有勤,夜设衾,朝敛枕,躬自为之,妻孥欲代之,先生曰:“母今老矣,后日,虽欲为母为此,不可得也。”[12]484其父去世时,他极度悲伤,为父守灵,孝行感动乡里,三月日,丁先公忧,饘粥哭泣,绝而复苏,行葬礼于密阳府西六里高岩山粉底谷,从先志也,先生与伯仲氏庐墓,纯至,乡闾感化。[12]484在安葬了母亲以后,金宗直便无心仕途,开始了隐居生涯,潜心研究性理之学,金驲孙与其兄金骥孙便是在这个时候开始跟随金宗直研习性理之学的。在学习过程中,金宗直把《孝经》放在首要地位进行传授,在四书和诸子百家之前,初授童蒙须知,幼学字说,正俗篇,皆背诵然后令入小学,次孝经,次大学,次语孟,次中庸,次诗,次书,次春秋,次易,次礼记,然后令读通鉴及诸史百家[13],由这种课程的设置就可看出金宗直对孝的重视。
孔子在推行其教育方法时曾经说过:“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14]可见,老师的言传身教对学生的影响之大。金驲孙跟随金宗直学习时正是其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期,金宗直的为人处世方式及价值观念对金驲孙产生了巨大影响。
在尊礼重孝环境的熏陶下,金驲孙耳濡目染,也对“孝”十分看重,对儒家传统的孝道观念深信不疑,甚至达到了“愚孝”的地步,所以,他在《非鄠人对》中极力反对韩愈的观点,并用儒家的“中庸之道”来反驳韩愈。
(2)韩愈的成长经历。韩愈三岁丧父,其母或改嫁,或沦为乳母[15]30,韩愈从小便跟随其兄韩会和其嫂郑氏生活,由他们抚养长大,韩愈在文章中也只提到其三岁丧父,而对其生母并未提及。他在《祭郑夫人文》中说:“我生不辰,三岁而孤,蒙幼未知,鞠我者兄,在死在生,实维嫂恩”[5]376;《祭十二郎文》云:“吾少孤,及长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5]379。这都说明韩愈是在父母缺失的情况下由兄嫂抚养长大的,他对父母的感情自然就不会太深。综观韩愈诗文,谈及父母的也很少,这种幼年父爱母爱缺失的经历对韩愈孝道观的形成有着深远影响。所以当鄠人父母有疾“割股救母”时,韩愈无法感同身受,这也是金驲孙反驳他的一个重要原因——古人以全归为孝,则伤其支体,固伤于孝,然吾惜吾之支体,则他人亦自惜其支体,谁肯毁其支体,为他人母哉?然则药终不可得,而疾终不可愈,就令退之,不幸而处此,当如何。
2.社会环境。
(1)金驲孙所处社会环境。古代中国特别是唐朝以来,国力强盛,政治制度完备,文化事业发达,以其强大的辐射力影响着周边国家。这其中,与中国山水相连、地处中国东方的近邻朝鲜,在其历史发展的各个时期,与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往来不断,经济贸易交流频繁,始终保持了密切的藩属关系,即一贯奉行“事大”外交政策。[16]从箕子朝鲜开始,其就对中国有着强烈的“尊周”意识,到了三国时期,新罗借助唐朝帮助统一了朝鲜半岛,后来的高丽王朝与李氏朝鲜都继承了“事大”的外交政策,保证了自身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尤其是朝鲜王朝,常常以“小中华”自居。中华文化对朝鲜半岛的影响还体现在其把汉字当作官方文字上,汉字最初传入朝鲜半岛的时间尚不可考,但依据《史记·朝鲜列传》及朝鲜半岛文献《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中的相关文字记载,可确定在公元前1 世纪,朝鲜半岛国家已能熟练使用汉字,将汉语文言(以下简称汉文)作为其官方书面语来书写邦交文书、记载本国历史。[17]52汉字在朝鲜半岛的历史地位就如同欧洲中世纪的拉丁文,朝鲜半岛文人通过汉字学习中国文化,聆听圣人教诲,并进行文学创作。此后,朝鲜人在汉字基础上不断进行改造,创造出了本国文字,可以说,汉字承载了其国家民族的文化根基,使用汉字的历史也是其民族文字诞生的前提基础。没有与汉字磨合过程中失败的经验和知识的累积,就没有朝鲜民族新文字的最终创制,汉字永远是朝鲜半岛文化中不可去除的部分。[17]52除汉字外,影响了中国社会几千年的传统儒家政治伦理思想也为朝鲜朝所吸收借鉴,并在国内大力推行,尤其是儒家的纲常伦理对朝鲜社会的影响更大。
“三纲五常”是儒学提倡的人与人之间的道德规范,朝鲜历代王朝的国王都利用儒学的伦理理论来维护和巩固其统治地位,完善国家的道德秩序。[7]56新罗真平王时期,僧人圆光曾入中国求法,归国后开始传播儒家伦理,称为“世俗五戒”:“一曰事君以忠,二曰事亲以孝,三曰交友以信,四曰临战无退,五曰杀生有择”[18]111,圆光所传授的“世俗五戒”颇为时人所看重。新罗花郎的起源也与儒家伦理有关:当时有号“风月主”的,都是容仪端正的少年,他们相互切磋道义学问,择其善者荐之于朝,故金大问花郞世记曰忠佐贤臣,从此而秀,良将勇卒由是而生。[19]他们奉行的正是儒家“入则孝于家,出则忠于国”的思想。高丽王朝也大力推行儒家名教,维护纲常伦理。据《高丽史》卷三《成宗世家》记载,成宗曾下令访求孝子、顺孙,给予旌表,并免除徭役。李朝对儒学的尊崇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太祖即位之初,就颁发诏令,褒奖忠孝节义之人:“忠臣孝子,义夫节妇,关系风俗,在所奖劝。令所在官司,询访申闻,优加擢用,旌表门闾。”[20]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儒家的纲常伦理对朝鲜有着深远影响,而且这种影响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深化。
到金驲孙生活的成宗时期,国家更是优待儒臣文人,儒家思想在朝鲜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统治者对“忠孝节义”的推崇也达到了鼎盛,不容许对儒家思想有半点质疑。成宗继承祖父以来的治权,创建弘文馆、湖堂等读书场所,并且优待儒者文人。[18]288同时,私学里所教授的也是儒家传统书籍《孝经》和“四书五经”等,传授的是忠孝节义等儒家传统思想。在这样一个有着深厚儒家纲常伦理之风的国家,金驲孙不可能不受影响,而且,他本身就是性理学家,是儒家思想文化的学习者、传承者,所以,其自身的儒家纲常伦理意识就更加浓厚。
(2)韩愈所处社会环境。韩愈虽然也生活在儒家思想浓厚的国家,但他生于中国的唐朝时期,唐朝是一个开放的王朝,提倡对各种思想文化兼容并包,对社会政治实行宽容政策,包括以仁义治天下、重视人才、君臣共治、爱华夷如一等,因此,唐朝的社会风气呈现出自由开放和平等重人两大特点。[21]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统治阶级对人们的思想控制相对宽松,所以才会容忍韩愈这样具有“异端”思想的人存在,而对比明清具有“异端”思想的李贽、黄宗羲等人,其下场要比韩愈惨得多。
唐朝自由开放、兼容并包的社会环境为韩愈革新儒家思想提供了有利条件,韩愈对鄠人“割股救母”做法的质疑与批判,正是其对儒家思想革新的体现,他虽然也是正统儒家思想的维护者,但面对日益腐朽、落后的思想文化,他大胆地对官方所倡导的行为提出批评,敢于发声,这也正是其“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决心的真实写照。
三、儒家孝道思想的一脉相承
综观金驲孙对韩愈的评价,会发现他其实对韩愈是十分敬佩的,他自幼便学习韩愈的诗文,对韩愈的异端思想也十分称赞,他在《赠山人智楫序》中写道:“古今儒者,不为不多,而平生以辟异端自任者,韩也,其论道也,必欲人其人而庐其居,其为浮屠作词,必欲冠其颠,楫乎尔学韩,得无戾于尔浮屠之教乎,使尔学韩者,必出于启卿之意,而遣尔就余者,亦心有存焉。噫!韩疏佛骨而谪潮阳,其疏也乃在其位,其谪也犹带刺史。”[22]228
从金驲孙《非鄠人对》和韩愈《鄠人对》这两篇文章本身来看,他们各自表达的孝道观并非是针锋相对、水火不容的,而是一脉相承的。虽然金驲孙在《非鄠人对》中多次反驳、批判韩愈,但是,他并未对韩愈的观点全盘否定。他也承认鄠人的做法有不得当之处,而且,对利用这种表彰政策沽名钓誉的人深恶痛绝,他说:“若鄠人者,虽谓知有其母而不知有其身,可矣!所患世之诡异者,残忍果敢,为不经之行,要一时之赏者或有之,是诚可罪也。”而且他在文章的最后也表示,虽然鄠人的做法是不对的,但其是出于“孝道”才这样做的,这应该是可以被理解和宽容的,其云:“中庸之道,民鲜能久矣,故曰观人,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剔股虽过,斯亦孝之党也。”这说明,金驲孙对韩愈的观点是部分赞同,只是觉得韩愈太过于激进,违反了儒家的中庸之道。
韩愈和金驲孙都是儒家思想的维护者,这一点毋庸置疑。综观韩愈一生,无论是其哲学思想,还是其政治、经济、伦理、文学、教育等思想,都是以儒家正统为己任的,尤其是他的“建立道统,传道以治国”[15]274的政治主张,更是正统儒家思想的体现。韩愈所传之“道”,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孔孟之道。他在《原道》里说:“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5]20可见,韩愈将自己当作孔孟思想的直接继承人,他所奉守的是正统儒家思想。但是,韩愈毕竟和孔孟相距一千多年,他在宣扬孔孟思想的同时,必定会根据当时的社会情况作出相应的调整, “变则可久,通则不乏”的道理韩愈不会不知道。如果仔细考究,则不难发现,韩愈所领导的古文运动并不是全盘复古,更多的带有“旧瓶装新酒”的意味,而且,他极力辟佛,在维护儒家思想的实践中不断吸收新的东西,锐意创新。《鄠人对》也是韩愈对儒家思想创新的成果,他以其激进的思想对鄠人“割股救母”的做法提出了批评,进而根据时代背景,对整个社会存在的沽名钓誉乱象予以揭露,这正是其儒家卫道思想革新的体现。
金驲孙是朝鲜王朝著名性理学家,而性理学则是儒学发展到宋明理学阶段在域外的分支,这样看来,他也是儒家传统学说的继承者。金驲孙曾到过中国,求学于当时的理学大师程愈门下,后将小学传入朝鲜:“仆昔年到京师,切切求有道之士,而一解陋方之惑,卒未见,匆匆将还。因伴送刘钺,得礼部程员外愈求学焉,程以手撰集说小学及晦翁书一帖与之,观其序述,抑其人也。仆初不知程深浅,试质俚语,而持小学相与以付,范公劝张载中庸不许谈兵之意也,然未承一日之雅,忽忽反国。”[22]227由此可见,金驲孙也是传统儒家思想的传承者,只不过他所传承的是儒学发展到理学阶段的思想。
儒学发展到宋明理学阶段,其本身已经僵化,很多弊端逐渐暴露,尤其是到了明代,理学已经大大束缚了人们的思想甚至是人身自由。明代解缙编写的《永乐大典》,对“忠、孝、节、义”的推崇达到了极致,其中“割股救母”的记载比比皆是:《夷坚志》中记载祁酥儿,割股救母而死;《清明集》中记载江应,割股救母,母愈之后得到表彰;《宋史》中记载樊谭,割股救母,母愈后得到官职;《金史》中记载王震,虽割股救母,母未能愈,而后其眼疾不治而愈,传为孝感所致。[23]这些都是由宋至明间的孝子孝女故事,这些人都因为至孝行为而被统治者极力赞扬,得以名垂青史,而且最后大都得到了好的结果。
明清以前,从公元739年陈藏器在《本草拾遗》中提出“用人肉治羸疾”,到公元907年唐朝灭亡,社会上对这种做法的认同感一直很低,当时的大文学家韩愈更是对这种愚孝行为极力批判;宋代钱易在《南部新书》中也指责:“开元二十七年,明州人陈藏器撰《本草拾遗》,云人肉治赢疾。自是闾阎相效割股,于今尚之。”[24];明初杨维桢写有《杨佛子行》与《陈孝童》两篇文章,都写到了割股疗亲,但一成一败,深刻揭露了当时人以这种方式获得旌表,以达到规避赋税的目的。试想,为什么要用人肉才能救命呢?而且,人肉本身也不是灵丹妙药,为什么父母吃了之后疾病就能痊愈呢?细思之后便会发现,这些都是统治者为了加强其统治的手段,是统治者宣扬传统孝道思想而故意大肆渲染、极力吹捧的结果。
在宋明“割股救母”之风盛行的情况下,其理学思想的东传势必也会对朝鲜王朝这一时期的社会思想产生影响,正如洪大容所说:“东儒之崇奉朱子,实非中国之所及,虽然惟知崇奉之为贵,其于经义之可疑可议,望风雷同,一味掩护,以箝一世之口焉。”[25]金驲孙不仅是性理学思想的直接继承者,而且又到过中国,接触过中国的理学大家,所以,这种传统的忠孝节烈思想更加根深蒂固,对于“孝”的坚守有时近乎“愚”。反观韩愈,上面已经提到,他在维护儒家传统思想的实践中不断锐意创新,剔除腐朽过时的、阻碍社会发展的思想。统治者大肆宣扬“割股救母”正是为了愚化百姓,便于统治,而韩愈对这种行为大胆地提出质疑,是对儒家思想的扬弃。但其所秉承的还是儒家正统的孝道思想,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
总体来看,金驲孙和韩愈所秉承的都是儒家传统的孝道思想,只不过是儒学不同发展阶段的孝道思想而已,韩愈直接从传统儒家思想出发,来申明自己的孝道观,而金驲孙所继承的则是儒学发展到理学阶段的孝道思想。
综上所述,金驲孙和韩愈的孝道思想都是从儒家思想出发的,有着一脉相承的文化渊源,由于不同的早年经历及其所处的文化环境差异使得他们各自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变化,以至于他们在面对同样的孝行时,给出了截然不同的评价,但这并不影响他们正统儒学维护者的身份和地位。金驲孙对韩愈的孝道思想也不是全盘否定,而是辩证看待,这说明,朝鲜文人在吸收借鉴中国古代文人的思想时,并不是不加区分,而是有所甄别的,其对中国文化的借鉴和吸收亦是如此。由此可以看出,早年经历和生活环境对个人思想观念的形成有重大作用,朝鲜文人独特的思想受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较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