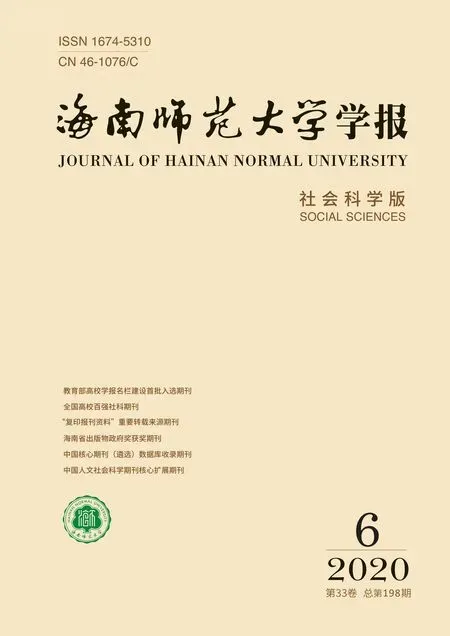自由的悖论
——对丁玲早期小说中女性主体自由的再思考
丰 杰
(湘潭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莎菲女士的日记》一直以来被认为是塑造了“‘五四’退潮后小资产阶级叛逆、苦闷的知识女性中最重要的典型”,并且她带有“一部分知识青年身上的时代阴影——使反抗带有病态但仍是反抗——表现出莎菲形象的全部矛盾性”。(1)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31页。研究者极为重视20世纪20年代丁玲小说中“灵肉冲突”这一主题,并且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角度认可其在同时代作品中的先锋性。阐释者又以丁玲对女性身体和情欲的大胆书写为证据,赋予其反传统的社会意义。典型如认为,《莎菲女士的日记》“因其独特的女性体验与现代意识而成为了世界文学的经典”,莎菲是一个“向男权文化传统宣战的叛逆者……解构男性神话的现代女性”。(2)邹永常:《莎菲形象与现代气息——解读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名作欣赏》2005年第5期。可以说,正是由于“五四”启蒙的大背景与“灵肉冲突”主题的强行粘连,使莎菲被认定为女性解放的楷模。然而,当我们重读丁玲《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韦护》等作品时,却产生了一些困惑:梦珂、莎菲、丽嘉到底在反抗什么?她们缘何苦闷?她们的出路何在?这些问题最终归结为一个核心命题:莎菲式形象究竟是以启蒙理性主导的现代女性、反传统英雄,还是处于青春叛逆期的感性少女?重新思考这些问题,对于我们重估丁玲笔下莎菲式女性形象的文学史价值应该说是有所裨益的。
一、“莎菲”反抗什么?
为完成辛亥革命所未完成的思想启蒙之重任,“五四”语境下诞生的现代小说天然地肩负着反封建的文化使命。陈独秀在《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中说:“三纲之根本义,阶级制度是也。所谓名教,所谓礼教,皆以拥护此别尊卑、明贵贱制度者也。近世西洋之道德政治,乃以自由、平等、独立之说为大原,与阶级制度极端相反。”(3)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青年杂志》第2卷第4号。基于这种逻辑,现代生活与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形成了难以调和的对立关系。《狂人日记》正因为狂人读出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短篇小说,而“反抗带有病态但仍是反抗”,也是莎菲形象的先锋性所在。但是,莎菲与狂人的反抗是否可以等同?
莎菲形象和狂人形象有两个重要的区别,值得我们注意。其一,狂人的反抗有清晰的对象——即村民思想中的吃人欲望,而莎菲的反抗没有一个可以抽象出来的明确对象。其二,狂人有一个很明显的启蒙举动——他试图“劝转”吃人的人,而莎菲没有启蒙动作。我们可以这样解释:莎菲是用自己的身体完成自我意识的现代化,是在进行自我启蒙。这种自我启蒙的意义并不逊色于狂人对他者的启蒙。在发展心理学看来,女性在青春期发育过程中发现自我身体与男性的不同,然后经历一系列的心理过程从而确认并接受“自己是女人”这个事实。如果对身体的自我发现这一心理过程,不能促进莎菲形成与社会民主进程相关的理性认识,即获得真正的“反叛传统”的意义,那么莎菲自我启蒙的时代价值就值得商榷。
实际上,无论是从马克思主义,还是从民主主义的理论出发,经济因素都是个体获得自由的前提。陈独秀用以驳斥康有为的便是:“西洋个人独立主义,乃兼伦理、经济二者而言,尤以经济上个人独立主义为之根本也。”(4)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青年杂志》第2卷第4号。将“个人独立主义”中的“独立”二字抽离,而单独谈论“个人主义”,显然是把“经济”这一根本问题给浪漫地忽略了。如果我们对现代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做一个梳理,便可以发现女性如未获得经济上的独立,那么所有的“解放”都是空谈。例如,老舍笔下的小福子(《骆驼祥子》)、月牙儿(《月牙儿》)都因为走投无路而卖身为娼,最后悲惨死去;叶绍钧笔下的“伊”(《这也是一个人》)因丈夫病死而不得不从帮佣的主人家离开后,像一头牛似的被夫家所卖,“把伊的身价充伊丈夫的殓费,便是伊最后的义务”(5)叶圣陶:《这也是一个人》,《叶圣陶集》第1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102页。,成为了旧道德的牺牲品;而许地山笔下的春桃(《春桃》)在逃难进城后成了一名拾荒者,拥有了足以养活一个家庭的经济实力,故而可以不顾舆论非议,拥有“两个丈夫”,成为家庭的核心。鲁迅针对风靡一时的娜拉热,也曾表示担忧:“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6)鲁迅:《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67页。由此,我们可以对丁玲作品中具有“反叛性”的女性进行细微辨析。梦珂(《梦珂》)、莎菲(《莎菲女士的日记》)、丽嘉(《韦护》)这三位女性形象和《母亲》中的于曼贞相比,在经济上的独立性是截然不同的。于曼贞离开农村去城里读书,因为钱财花光了而不得不卖地,于是切断了自己与传统大家庭的联系,即不再依靠父家或夫家的经济资助。这在客观上促成了她向独立自主的现代女性转型,其收入所得不仅养活了自己,还抚养了女儿。而年轻一辈的女性——梦珂、莎菲和丽嘉,却并没有表现出超越“母亲”于曼贞的现代性。梦珂、莎菲和丽嘉这些“大学生”(这个身份也是不确定的),理应是于曼贞在学堂里所羡慕的“大脚同学”,但在她们随性自由的背后,依靠的仍然是父家的经济供养,这并不能使她们成为真正独立的个体。因此,她们思想上的“反叛性”是可疑的,而她们身上体现出来的青春期叛逆却是明显的。
我们来看几个证据。梦珂本来在学校学习绘画,却因为一件小事而“厌倦了学校生活”,“无论如何我不回学校去”(7)丁玲:《梦珂》,《丁玲全集》第3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8页。,于是先在朋友家借住,而后又长时间寄居在姑母家。她不仅在课业上如此随意,在生活上也近乎奢侈。看到表姊们都穿上了斗篷,她也想做件皮袍。“凑巧,父亲在这天竟一次汇来三百元,是知道她住在姑母家里,要用钱,赶忙把谷卖了一大半,凑足了寄来的,并说等第二年菜油出脱时才能再有钱来,但决不会多……”(8)丁玲:《梦珂》,《丁玲全集》第3卷,第21页。,梦珂用这些钱做了什么呢?“买了一件貂皮大氅,两件衣料,和帽子,皮鞋,丝袜零星东西,一共便去了两百四十五元”,“一看钱所剩不多,便请姑母等吃了一顿大餐”(9)丁玲:《梦珂》,《丁玲全集》第3卷,第22页。,请客吃饭大约就是“五十五元”。那么这“三百元”在当时的实际购买力又是怎样呢?《梦珂》的发表时间是1927年底,与其相近的1928年,一担(100斤(10)“担,全称市担。市制中的重量单位。一担=100斤=50千克。”参见夏征农、陈至立主编:《辞海:第六版彩图本》,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第397页。)华米的价格是7.08国币元(11)参见刘克祥、吴太昌主编,刘兰兮等著:《中国近代经济史(1927—1937)》,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82页,表2-4。。可以看到,梦珂购买貂皮大氅等衣物的价格约等于购买3460斤华米,而请客吃饭的钱相当于购买约777斤华米。再看一例,鲁迅于1927年10月2日到达上海,其在1927年12月18日的日记中记载:“收大学院聘书并本月分薪水泉三百”(12)鲁迅:《鲁迅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2页。;同月23日,又记:“买书柜一个,泉十元五角”(13)鲁迅:《鲁迅全集》第16卷,第53页。。可见,梦珂父亲汇给她的这“三百元”,在当时是鲁迅这样级别的学者、作家在国家级学术机关里才能拿到的月薪;同时,一个书柜的价钱也说明了当时“十元五角”的购买力并不算低。因此,不能不说,梦珂毫不犹豫地把“父亲卖谷一大半”所得的“三百元”用于购买衣物和请客吃饭,实在是过于奢侈。当梦珂穿了貂皮大氅去看匀珍,“匀珍总不转过她的脸色。单为那一件大衣,她(梦珂)忍受了四五次的犀锐的眼锋和尖利的笑声,使她觉到曾经轻视过和还不曾用过的许多装饰都是好的”(14)丁玲:《梦珂》,《丁玲全集》第3卷,第23-24页。。匀珍父母早已在城市立足,但梦珂如此挥霍的大手笔连匀珍都震惊了。对于同辈人的嘲讽,梦珂的心理活动是:“为什么一个人不应当把自己弄得好看点?享受点自己的美,总不该是不对吧!”(15)丁玲:《梦珂》,《丁玲全集》第3卷,第24页。“爱美”“攀比”“享受”,对于一个青春期少女而言并非值得批判,但如果要给这些建立在依靠家庭基础上的价值追求冠以“现代”“启蒙”之名,未免有些牵强。
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中,莎菲同样是从原生家庭走出来到城市里读书的女孩,租住在一个单人公寓里。莎菲与梦珂相比,更清晰地展现了青春期少女的心理状态。小说前四段将这个女孩在城市的学习生活娓娓道来。开首第一句便是:“今天又刮风!”(16)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丁玲全集》第3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1页。这句带着惊叹号的天气描述,奠定了小说“气闷”的基调。让莎菲如此气闷的并不是与国家命运、个人前途有关的问题,而是“风”。为什么呢?因为这“风”让莎菲“睡不着”“又不能出去玩”,所以“只是每天都在等着,挨着”(17)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丁玲全集》第3卷,第41页。。因无事可做,她先是把牛奶煨了三四次也不喝,再把一叠厚厚的报纸(甚至于广告)都看完。她既没有固定的学习任务,更无需工作,为了接近和追求凌吉士还另外租房。和梦珂一样,她花的自然也是父母的钱。莎菲理直气壮地恃宠而骄:“偏偏我的父亲,我的姊姊,我的朋友都如此盲目的爱惜我,我真不知他们爱惜我的什么;爱我的骄纵,爱我的脾气,爱我的肺病吗?有时我为这些生气,伤心,但他们却都更容让我,更爱我”(18)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丁玲全集》第3卷,第43页。。从这种描述不难看出,莎菲不仅接受着原生家庭的经济供养,而且还和家人有着极为亲密的情感关系。对一个肺病患者,医生不建议住院治疗,也未开西药中药,而是让她“多睡,多吃,莫看书,莫想事”(19)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丁玲全集》第3卷,第41页。。这个治疗方案无疑切中了莎菲之病的要害,因为这是“精神上的肺病”,无需物理上的疗救。这病有两大特征:一是无聊;二是生无名火。莎菲对自己的症结有这样的概括:“我却宁肯能找到些新的不快活,不满足;只是新的,无论好坏,似乎都隔我太远了”(20)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丁玲全集》第3卷,第42页。。《莎菲日记第二部(未完稿)》中,丁玲实际上对莎菲形象已经有了较为清晰的评价:
“我读了我几年前的东西,没有一点感伤和留恋……我是还在一个极旧式,比我过去还可能到更堕落的地步去的。……同时我得审判我自己,克服我自己,改进我自己,因为我已经不是一个可以只知愁烦的少女了。”(21)丁玲:《莎菲日记第二部(未完稿)》,《丁玲全集》第4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8页。(注:着重号为笔者加)
“堕落的”“只知烦愁的少女”,便是丁玲对莎菲的形象定位。莎菲“为赋新词强说愁”的身心状态,与其说具有反传统的意义,倒不如说是极为传神地表现了青春期少女的叛逆心理。
《韦护》的女性主角从一个变为了两个:丽嘉与珊珊,这两个形象似乎是莎菲形象的一分为二。丽嘉保持着莎菲骄纵任性的青春期个性,而珊珊则显现出理性稳重等趋于成熟的特点。丽嘉有着典型的莎菲式苦闷:“厌倦了学生生活,无耐心念书,然而又无事给她做,她又不愿闲呆着……她所想的都是梦,她知道行不通,所以苦恼”(22)丁玲:《韦护》,《丁玲全集》第1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3页。。丽嘉这时候是女生团体中的“精神领袖”。薇英原本到南京来是想学体育的,因为经济不宽裕,想通过读书找一份踏实的工作。但她的想法“却为丽嘉和珊珊反对,说她不适宜,强迫她一同呆下来学音乐,学绘画,看小说的玩过去了,她的成绩都不好,只在思想上,个性上受了很大的同化,她从前是一个拘谨守旧的人。……正是因为她受了她们的影响,她很爱自由,又爱艺术,但她觉得若不能将自己的经济地位弄得宽裕些,那一切只全是美梦。”(23)丁玲:《韦护》,《丁玲全集》第1卷,第26-27页。小团体对于个体的“道德绑架”,本来就是一种青春期女孩的典型交往规则。微妙之处在于,叙事者这样评价丽嘉对女孩们不要各奔前程的建议:“她说了五打以上的梦想,说得像真有其事一样来蛊惑她的朋友们。”(24)丁玲:《韦护》,《丁玲全集》第1卷,第27页。“蛊惑”而非“启蒙”的措辞,很显然表现出了叙事者对丽嘉之价值观的警惕。当然,无论多强的“道德绑架”,最终还是会被经济理性冲垮。这个群体并没有支撑多久,最后大部分女孩还是去铸造经济基础了。丽嘉向往法国的生活,但她后来既没有去法国留学,也没有在国内学习或工作,而是走进了同居的小家庭。
我们从这三部小说中,可以看到丁玲对这些女性形象逐渐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韦护》中的珊珊,这个同样有着丁玲意志影射的人物,象征着理性精神已经从梦珂、莎菲形象中分离并成长起来,构成了对莎菲式人生观与价值观的反思姿态。珊珊始终“坚持她的意见,她要纠正那错误”(25)丁玲:《韦护》,《丁玲全集》第1卷,第55页。。“错误”是什么?一是玩弄小聪明,因无知而无畏——“处处我们都显得很聪明……但是,到底我们思想的依据在哪里,我们到底懂了那些没有?没有呀!我们没有潜心读过几本书,我们懂的全是皮毛。”(26)丁玲:《韦护》,《丁玲全集》第1卷,第54页。二是懒惰,纵情挥霍青春——“我们都太年轻了。所以我们的懒惰总是胜过我们别的方面,它将害得我们一无成就。”(27)丁玲:《韦护》,《丁玲全集》第1卷,第27页。归根结底,“错误”是因为“幼稚”与“年轻”。正如丁玲借几年后的莎菲之口说的,“那时完全是小孩”(28)丁玲:《莎菲日记第二部(未完稿)》,《丁玲全集》第4卷,第12页。。青春叛逆和启蒙反叛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历时性的可以自我修正,与荷尔蒙的分泌有关;后者则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长期的抗争过程。青春叛逆展现于人发展中的一个时期。绝大部分人过了这一时期又会向家庭回归。而反叛行为的主体尽管可以被打败,但他的精神始终是难以战胜的。如鲁迅笔下的狂人、孤独者、过客等形象。总而言之,莎菲式女性既未在经济上建立独立性,又未在思想上理性地反对传统文化。如“把‘随意’和‘自由’混为一谈”(29)[德]叔本华:《叔本华论道德与自由》,韦启昌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61页。,说莎菲们已经拥有了一个具有现代性的自我,也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二、“莎菲”缘何苦闷?
在由中华书局于1937年出版的美籍华人何林华撰写的《发展心理学》中,“鲁钝期—青春期”一章开首就谈及了青春期在各种文艺和学科中的形象:
浪漫文学则以描写青春期为其特色。诗歌、小说、教育学及半科学的记载,其写青年生活,都以放浪不羁的热情为其特征。诗与小说,其旨趣在热情之狂炽。教育学与《心理卫生》的论调则以为青春期好像一种病,或像一种有机与精神的激变,儿童经过这种激变,其进程遂可达于成熟期。(30)[美]何林华:《发展心理学》,王介平、蒋梦鸿译,上海:中华书局,1937年,第207页。
可以看到,“放浪不羁的热情”几乎是青春期的代名词。也许我们可以说,从传统女性“进化”到现代女性,也如个体生命发展过程中必须要经历青春期一样。女性在这个阶段里发育成熟,并伴随着身体成熟而形成一种主体自由意识,但这种说法同时也是不完全准确的,因为这是把女性孤立对待,而没有将其放在一个男女共存的社会中去看。波伏瓦认为:“女人并非为其所是,而是作为男人所确定的那样认识自己和做出选择。因此我们必须首先按照男人所想象的那样描绘女人,因为‘她为了男人而存在’是她的具体境况的基本要素之一。”(31)[法]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第1卷,郑克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第196页。因此,从男性视角来评价“五四”时期女性解放的进展程度,或许更具说服力。高长虹在20世纪20年代发表了一篇鼓吹女性解放之檄文——《论杂交》。他在文中列举了婚姻制度的十大罪状,认为“家庭或婚姻的束缚尤其是女子的致命伤,不革除这些困难,除退回原路之外女子解放很不容易有别的结果”,最后推导出“杂交之与女子的关系,就是解放的唯一的途径”(32)高长虹:《论杂交》,《高长虹全集》第1卷,北京:中国编译出版社,2010年,第482页。的结论。高长虹的宏论并没有太多反驳的价值,但我们可以从中窥见,“五四”时期男性心目中所谓“新女性”的理想面貌,其最大的新质乃是性观念的开放。
丁玲小说所描写的男性对新女性的幻想也可构成一条证据链。在《韦护》中,柯君因结识了一群新女性而十分得意。他对自己的男性友人吹嘘:“我有几个女朋友,都是些不凡的人呵!她们懂音乐!懂文学,爱自由!她们还是诗!……”。末了,还做出了这样的总结陈词:“而且……她们都是新型的女性!”(33)丁玲:《韦护》,《丁玲全集》第1卷,第6页。这段描述的滑稽之处在于,依据后来的情节发展,男性友人们对新女性之文艺天才评价颇少,而对新女性的身体发育却投以全身心的关注。初来乍到的韦护“望过去,连丽嘉有五个,都在十七、八、九上下,是些身体发育得很好的姑娘,没有过分瘦小的或痴肥的。血动着,在皮肤里;眼睛动着,望在他身上。他知道柯君要来这里的缘故了。”(34)丁玲:《韦护》,《丁玲全集》第1卷,第11页。这“缘故”显然不是文艺天才。又如已婚的浮生和丽嘉散步时,“不断地拍着她的手,只觉得她天真活泼有趣,而且美丽可爱。唉,那白嫩、丰润的小手,不就正被他那强健有力的手捻着吗?”(35)丁玲:《韦护》,《丁玲全集》第1卷,第19页。当丽嘉来到韦护的住所时,韦护看着丽嘉剥橘子就有这样的心理活动:“她那又软、又润、又尖的手,在那鲜红的橘皮上灵巧的转着。他不由的想起一句‘……纤手试新橙……’的古词来。”(36)丁玲:《韦护》,《丁玲全集》第1卷,第74页。在确定恋爱关系后,韦护高谈“我为我们爱情的享受而生活”,于是抛弃了理性,和丽嘉在公共场所忘情地接吻。旁边的办事员被他们骇得直摇头,心里想:“大约这便是所谓新人物吧!”(37)丁玲:《韦护》,《丁玲全集》第1卷,第97页。韦护还直白地这样评价丽嘉:
她是那末善于会意的笑,那末会用眼向你表白她的心,一个处女的心。她一点不呆板,不畏缩,她没有中国女人惯有的羞涩和忸怩,又不粗鲁不低级。他早先对于她的印象,只以为是有点美好和聪明而放浪的新型女性。(38)丁玲:《韦护》,《丁玲全集》第1卷,第73页。
在《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韦护》三篇小说中,男性对新女性之“自由”的认识,也都以“放浪”为关键内核。正是“太崇拜了自由”的缘故,她们较传统女性而言,挣脱了原生家庭的管束,又无需得到男友在经济上的供养(此刻供养新女性的是她们的父母)。在某种程度上,韦护等男性与丽嘉等女性在交往过程中印证了,或者说兑现了高长虹的“女子解放”理想。
杜威认为:“一个社会制度是能够继续存在下去的,只要它满足了人性中某些在过去得不到表达的因素。”(39)[美]杜威:《自由与文化》,傅统先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32页。“灵肉冲突”这个主题被赋予启蒙意义,正是因为它大胆坦率地表达了人的身体与欲望。但“灵肉冲突”的时代苦闷在男性作家和女性作家笔下,并不能等而同之。“五四”时期以郁达夫《沉沦》为代表的自叙传抒情小说在表现“灵肉冲突”时,实质上表现了人性自由的绝对主义思想影响下,欲望奔涌而出又无法尽情施展的躁动之苦闷。20世纪40年代,钱钟书在《围城》中幽默地谈及了这一问题:方鸿渐羡慕校园里男女同学的新式恋爱,所以鼓起勇气给家里写信要解除包办婚约。父亲方遯翁明察秋毫,直接揭穿了方鸿渐的用心:“汝校男女同学,汝赌色起意,见异思迁;汝托词悲秋,吾知汝实为怀春……”!(40)钱钟书:《围城》,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第8页。方遯翁对新式恋爱“怀春”实质的点评可以说是犀利见血的。
应该说,丁玲创作《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韦护》这三篇小说最大的价值并不仅仅是塑造了“反抗的女性”,从更深层次来说,或许还在于其对女性启蒙的理性反思。笔者认为,丁玲所表现的苦闷之内涵,并不是郁达夫《沉沦》所表现的“灵肉冲突”这么简单。因为即使在赤裸的“灵肉冲突”中,也不得不承认这一事实——女性解放是在男权文化的主导下进行的。这是更深层的文化苦闷。梦珂和莎菲玩弄小伎俩,都是为了让男性欣赏并爱上自己,这和《围城》中苏文纨、孙柔嘉的爱情套路异曲同工,似乎唯有得到男性的肯定,才显出女性自由之彻底,解放之到位。丁玲在小说中还多次将妓女作为女性解放的参照对象。《梦珂》中,一向“谦和、温雅、小心”的表嫂,忽然对梦珂说:“愿意把自己的命运弄得更坏些,更不可收拾些,现在,一个妓女也比我好!也值得我去羡慕!”(41)丁玲:《梦珂》,《丁玲全集》第3卷,第29页。梦珂听了这“大胆的,浪漫的表白”,一时被骇住了。表嫂接着说:“这不过是幻想,有什么奇怪!你慢慢就会知道的……”(42)丁玲:《梦珂》,《丁玲全集》第3卷,第29页。。表嫂这句话潜台词就是她认为向往妓女的自由是女性心理成长的必经阶段。将妓女与自由联系在一起无疑是对两者的双重误解,而同时为了自由而羡慕妓女、并且连妓女那种有限的“自由”也不可得,这才是中国女性最大的悲哀。当梦珂见到“中国的苏菲亚女士”(43)丁玲:《梦珂》,《丁玲全集》第3卷,第23页。时,却因为她是“斜眼”而对其不屑一顾。“妓女”与“中国苏菲亚”一高一低的心理位置,其实质无外乎是其对于男性的吸引力有天壤之别。因此,丁玲小说并未停留于表现女性的“灵肉冲突”,而是更深层次地呈现了在“灵肉冲突”中女性的他者地位,道出了女性以自由解放之名,实为取悦于男性的悲哀处境!
众所周知,所谓“启蒙道德”正义性的根基是反传统,那么“女性解放”的题中之义自然是反对包办婚姻。于是,表嫂攻击旧式婚姻,认为“嫁人等于卖淫”(44)丁玲:《梦珂》,《丁玲全集》第3卷,第28页。,但丁玲借梦珂之口反驳表嫂:“新式恋爱,如若只为了金钱,名位,不也是一样吗?并且还是自己出卖自己,不好横赖给父母了。”(45)丁玲:《梦珂》,《丁玲全集》第3卷,第28页。这一反问,揭示了“消灭家庭不一定能解放女性”(46)[法]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第1卷,郑克鲁译,第81页。这个残酷的事实。女权主义在辛亥革命前后被广泛宣传,助力于社会整体的反封建运动。易卜生塑造的“娜拉”成为了全中国女性的精神偶像和时代神话。然而“直接依附于国家,女人并不会少受男性的压迫。真正社会主义的伦理学,就是说寻求正义,而不取消自由,给个体负担但不消灭个体性,由于女性的状况问题,它处于非常尴尬的局面。”(47)[法]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第1卷,郑克鲁译,第81页。反抗包办婚姻,往往只能通过一种报复性的堕落来实现。这个过程被简化成了从家庭妇女走向妓女的道路。如在《梦珂》中,表嫂以“卖淫”来抨击包办婚姻,又反过来羡慕“妓女”的现代性。这一逻辑悖论,正揭示着女性解放的尴尬境地。鲁迅认为:“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48)[法]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第1卷,郑克鲁译,第165页。波伏瓦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在社会解体时,女人获得解放;但当她不再是男人的臣属时,却失去了她的采邑;她只有一种否定的自由,只通过放荡和挥霍表现出来。”(49)[法]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第1卷,郑克鲁译,第188页。从结果来看,所谓“女性解放”之路,让男性获得“自由乱爱”的合理借口的同时,并没有因为取消包办婚姻而让女性获得真正的自由,反而可能将其推入一个更痛苦的深渊。
无论是同居也好,“杂交”也好,生理学早就告诉过我们,女性因天然的生理特点而成为了苦难的承受者。澹明、凌吉士、韦护等男性形象对女性的身体消费,和高长虹对于新女性的人生设计一样,是实践着男性视角的女权主义运动,而女性对此从无意识到认识其悲剧性,需要一个拐点和仪式。我们从这三篇小说中,可以梳理出梦珂、莎菲、丽嘉三个女性角色对自我形象的“破却”过程,即她们冲破自己建构的自我形象幻影,站到自我之外,借由男性视角甚或社会视角来反观作为他者的自我。也唯有如此,女性才真正形成对自我的完整认知。梦珂自以为得到了表哥和澹明的爱,还纠结于如何选择,心生愧疚,但她偶然在花园里却听到了表哥与澹明正在议论自己。原来,自己在两个男性眼中,不过是个猎物。澹明说“我们七八年的交情,难道为一个女人而生隔阂!”(50)丁玲:《梦珂》,:《丁玲全集》第3卷,第32页。表哥则得意于他在女性面前的“假劲”之效用。梦珂在两性交往中的自信与骄傲瞬间崩塌。莎菲一方面因将苇弟控于股掌之中而自得,另一方面又精心设计着俘获凌吉士的爱情圈套。但当她终于打算为了凌吉士美丽的皮囊而“献身”时,却得知凌吉士是一个已婚人士,且在和自己的交往中不过是顺水推舟、乐得其所罢了。莎菲的“成熟老练”在凌吉士看来不过是“幼稚可怜”。韦护与丽嘉经过了一段昏天暗地的同居生活后,终于感到革命事业之于自己的重要了。读完分手信后,丽嘉才幡然醒悟,原来,韦护并不是她的战利品。梦珂、莎菲、丽嘉都经历了“幻想自己是爱情高手”到“明白自己才是情欲猎物”的情感体验。她们在响应“五四”启蒙呼声而成为“新女性”时,实际上就开启了这个荒谬而残酷的情爱故事的开关。在男女交往中,女性无从建构起一个真正的主体,并获得超脱男性文化的自由,这才是梦珂、莎菲、丽嘉之苦闷的根源。
三、“莎菲”出路何在?
爱情理想破灭后,小说中这些女性形象的人生选择耐人寻味。梦珂逃离了姑母家,打算去实现自己的明星梦。当她改名林琅并走红后,却发出了“这样的去委屈自己,等于卖身卖灵魂似的”(51)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丁玲全集》第3卷,第40页。的自我拷问;莎菲受情伤后“陷到极深的悲境里”(52)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丁玲全集》第3卷,第78页。,于是南下疗伤去了。前者麻木,后者消沉,同样都是悲哀的。那么,莎菲式女性的出路究竟在哪里?这也是困惑着丁玲的问题。
对女性启蒙悲剧的体验与反思,客观上推动了丁玲的“左转”。直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的“左转”才最终定型。而在此之前,《莎菲日记第二部(未完稿)》《母亲》《我在霞村的时候》《夜》《在医院中》等小说都表现出了一种过渡期的特征,为莎菲式形象设计了投身革命的理性路径。《莎菲日记第二部(未完稿)》虽然仅有两篇日记,但已经交代了丁玲对莎菲出路的初步设计。“五月四日”的日记,交代后来莎菲并没有“跑到无人认识的地方,浪费她生命的余剩”(53)丁玲:《莎菲日记第二部(未完稿)》,《丁玲全集》第4卷,第9页。。几年后的莎菲减持了浪漫和幻想,变得很理性,认为是“到了要读书,开始做事,开始重新做人的时候了”(54)丁玲:《莎菲日记第二部(未完稿)》,《丁玲全集》第4卷,第10页。。莎菲遇到了一个十九岁的男孩,并与之一同向着光明靠拢。在丈夫去世后,莎菲也没有消沉下去。可以说,是革命理性将莎菲拯救了。“五月五日”一篇则感性许多,谈到她为一个爱情的纪念日而特意去找一朵牡丹花。这种浪漫的行为,让莎菲马上警觉起来。她感到:“这意识真可怕”(55)丁玲:《莎菲日记第二部(未完稿)》,《丁玲全集》第4卷,第12页。。这部残篇本身意味着丁玲日记体叙事的终结,以感伤情调为基础的日记体叙事,已经不再符合她对人物形象的心理预期了。这也恰恰预示着丁玲在创作上的理性“左转”趋势。从理论上来说,投身革命之所以能够实现对女性的救赎,是因为它预期将女性拔离出传统道德的评价体系,让她告别性别所带来的天然弱势。《我在霞村的时候》将两个评价体系非常清晰地建构起来。其一是传统道德评价体系,其二是革命道德评价体系。贞贞在前者中是个“缺德的婆娘”(56)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丁玲全集》第4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19页。,而在后者中则是一个意志顽强的革命战士。贞贞拒绝了夏大宝的求婚“施舍”,实质上就是拒绝了第一个评价体系的灵魂“救赎”。她说:“我还可以再重新作一个人,人也不一定就只是爹娘的,或自己的。”(57)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丁玲全集》第4卷,第232页。贞贞这一宣言既意味着女性告别了青春期,也告别了个人主义的女性自我,归入了社会性的大我。通过转换评价体系来改变女性命运,在一定时期内有会有明显的正面效果。
女性投身集体革命,需要进行一系列的自我改造,建构一个“去女性化”的自我形象。首先要做到的就是精神上的禁欲。“灵肉冲突”让我们认识到力比多的存在,并赋予它反封建的意义,但人在这途中实际上又沦为了力比多的俘虏。为了反拨个性过度自由而带来的不自由,叔本华说:“要获得解救,就必须否定意欲”(58)[德]叔本华:《叔本华论道德与自由》,韦启昌译,第224页。。具体到创作中,丁玲开始用政治理性来控制人物的欲望。在设定陆萍这个人物时,丁玲认为“不须把她的外型写得很美丽或妩媚,因为她不是使用自己的性别或青春去取得微薄的满足的人物。不要恋爱故事,也不应该感伤。”(59)王增如、李向东:《读丁玲〈关于〈在医院中〉(草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年第6期。在《夜》中可以看到在两性碰触将要产生火花时,理性的控制力:
他感到一个可怕的东西在自己身上生长出来了,他几乎要去做一件吓人的事,他可以什么都不怕的,但忽然另一个东西压住了他,他截断了她说道:
“不行的,侯桂英,你快要做议员了,咱们都是干部,要受批评的。”于是推开了她……(60)丁玲:《夜》,《丁玲全集》第4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60页。
曾经作为启蒙动力去抗击传统道德的力比多,此时地位被反转,成为了政治理性所压制的对象。作为启蒙者的男性革命者,不断地向女性灌输着这样的逻辑:“不行的……你快要做议员了”,“为恋爱而妨碍工作是不行的”(61)丁玲:《在医院中》,《丁玲全集》第4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52页。。在政治理性中,女性对于爱情的需求成为了她们追求新生的累赘。从这个层面来看,贞贞拒绝夏大宝是一种理性的必然。其次,是审美上的雄化。《母亲》将女性雄化的审美趋势,写得最为具体和细腻。于曼贞羡慕农妇和同学们的大脚,于是把自己的小脚慢慢放大。那双畸形丑陋的小脚,曾经是传统社会中女性引以为傲的取悦男性的身体标志,被三太太当作是最可宝贵的财富。当于曼贞终于把脚放大了,同学们对她的评价是“雄多了!”(62)丁玲:《母亲》,《丁玲全集》第1卷,第188页。曼贞不仅在身体上克服了传统社会对女性的歧视,还变得更加勇敢,更有担当,成为了家庭中的经济与精神支柱。丁玲在早期小说中曾用很多笔墨来描绘梦珂、莎菲、丽嘉的身体魅力,而在《我在霞村的时候》中写贞贞和侯桂英的出场时,却刻意回避了对“女性之美”的描摹,显示出一种“无性化”的叙事追求。例如贞贞的外貌:“阴影把她的眼睛画得很长,下巴很尖。虽在很浓厚的阴影之下的眼睛,那眼珠却被灯光和火光照得很明亮”(63)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丁玲全集》第4卷,第223页。。小说中这唯一一句对贞贞的面部描写有着很强的理性寓意。丁玲在写侯桂英时就更简洁——“一个人影横过来”(64)丁玲:《夜》,《丁玲全集》第4卷,第259页。。以上这两处外貌描写显然都缺乏性别特点。《在医院中》的陆萍室友则更是一个典型的雄化形象,她“仿佛没有感情,既不温柔,也不凶暴”(65)丁玲:《在医院中》,《丁玲全集》第4卷,第238页。,走路时风云叱咤,还会熟练地骂脏话。
革命事业帮助年轻女性告别了青春感性的叛逆,从而走向政治理性的成熟。丁玲的《在医院中》就试图把莎菲式女性直接放入第二个评价体系,期待她成长。“她们都富有理想,缺少客观精神,所以容易失望,失望会使人消极冷淡,锐气消磨了,精力退化了,不是感伤,便会麻木。”(66)王增如、李向东:《读丁玲〈关于〈在医院中〉(草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年第6期。从失望而陷入感伤或麻木,正是莎菲和梦珂的人生注解。但很快丁玲就意识到,两个评价体系不可能截然分开。第二个评价体系不可避免地与男权文化发生着交叠。热情、理想主义的陆萍很快便被舆论扣上了“小资产阶级意识,知识分子的英雄主义、自由主义等等的帽子”(67)丁玲:《在医院中》,《丁玲全集》第4卷,第251页。。她再度成为和环境格格不入的“异类”。杜威认为,人们容易把“个人性”和“社会性”互相孤立起来,“一方面是把人性中的某一个东西当作最高的动机,另一方面是把社会活动的某一种形式当作是最高的。”(68)[美]杜威:《自由与文化》,傅统先译,第19页。莎菲女士正是在男权文化下感受到不自由,所以去到革命文化中寻找自由。然而,她又需要面对一个新的自由悖论:“个人只有跟大规模的组织联系起来,才能得到自由,而这样的组织又成为自由的限制,这两方面都有使人信服的论据。”(69)[美]杜威:《自由与文化》,傅统先译,第56页。丁玲在写作《在医院中》时感受到了这种矛盾:“我所肯定的那个人走了样,这个人物是我所熟悉的,但不是我理想的,而我却把她做为一个理想的人物给了她太多的同情,我很自然的这样做了,却又不愿意。”(70)王增如、李向东:《读丁玲〈关于〈在医院中〉(草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年第6期。最后,丁玲为小说设计了陆萍被双腿残疾的革命党精神启蒙的结局。陆萍获得了理性的力量,从而振作起来迈开步子前去。《在医院中》客观上建立了这样一种耐人寻味的叙事结构。初来乍到的陆萍想成为改造医院的“启蒙者”,但她的启蒙理想和行为将她推向了精神的绝境,最后她又以“被启蒙者”的形象而获救。这就具体演绎了革命启蒙对“五四”启蒙的覆盖,革命拯救启蒙的逻辑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在丁玲早期以莎菲式形象为主人公的作品中,始终存在着一种女孩与母亲的精神呼应关系。丁玲多次在《梦珂》《韦护》《在医院中》《莎菲日记第二部(未完稿)》中用“孩子”来定义女主人公,当她们在现实生活中遭遇挫折心灰意冷时,往往有一个明显的精神还乡的举动。例如,梦珂的精神还乡是这样的:
像喝醉酒那样来领略这些从未梦想过的物质享受,以及这一些所谓的朋友情谊。但,实实在在这新的环境却只扰乱了她,拘束了她……真的,想起那自由的,坦白的,真情的,毫无虚饰的生活,除非再跳转到童时。(71)丁玲:《梦珂》,《丁玲全集》第3卷,第11-12页。
这种精神回归也出现在陆萍身上:
她想着南方的长着绿草的原野,想着那些溪流,村落,各种不知名的大树。想着家里的庭院,想着母亲和弟弟妹妹,家里屋顶上的炊烟还有么?屋还有么?人到何处去了?想着幼小时的伴侣,那些年轻人跑出来没有呢?听说有些人到了游击队……她梦想到有一天她回到那地方,她呼吸那带着野花、草木气息的空气,被故乡的老人们拥抱着;她总希望还能看见母亲。她离家快三年了,她刚强了许多,但在什么秘密的地方,却仍需要母亲的爱抚啊!……(72)丁玲:《在医院中》,《丁玲全集》第4卷,第247页。
莎菲们通过精神还乡达到与原生家庭的情感和解,让在现实生活中受挫的灵魂得到慰藉。唯有到了这个时候,她们才度过了青春叛逆期,进入成年期。而《母亲》又何尝不是丁玲在现实困境中怀念母亲、怀念童年的精神还乡之作?还应指出的是,当丁玲从母亲的人生轨迹中寻求新生的动力时,她发现自己对母亲的精神传承与她对革命的信仰产生了合流效应。换句话说,推动丁玲走向无产阶级革命的精神力量,不仅是女性解放的现实困境,还有她在梳理母亲和其故乡的历史时所意识到的革命必然性。
1932年6月,丁玲在一封信中谈到《母亲》的创作预想:“这书里包括的时代,是从宣统末年写起,经过辛亥革命,一九二七年之大革命,以至最近普遍于农村的土地骚动。”(73)丁玲:《致〈大陆新闻〉编者》,《丁玲全集》第12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8页。在《母亲》第三部提纲手稿的第一章中,我们可以大致梳理出母亲与时代之互动:
革命失败后,小城市之黑暗腐败。对革命之压迫,母亲生活之感寂寞悲苦。……母亲之消沉痛苦寂寞……革命虽然失败,母亲并不灰心……母亲不能活动,孤独无援……母亲只有对革命心向往之。(74)王增如:《丁玲〈母亲〉第三部写作提纲初探》,《现代中文学刊》2014年第6期。
在这段话中,前两个“革命”指的是国民大革命,最后一个“革命”指的是无产阶级革命。大革命失败所造成国人精神上的严重创伤,客观上推动着鲁迅和丁玲等一批独立作家向时在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靠拢。丁玲所列的这份提纲,既是对其母亲人生的纪实,实际上也投射了她自我人生的理性选择。也就是说,从莎菲到于曼贞再到陆萍,丁玲清醒地认识到:只有投身无产阶级革命才是中国女性的唯一归途。尽管在这个革命语境中,丁玲也将感受到苦恼和困惑,但是她清楚不能再回去,事实上也没有再回去,她决心用革命理性来战胜青春感性,坚持“人是在艰苦中成长”(75)丁玲:《在医院中》,《丁玲全集》第4卷,第253页。。丁玲对莎菲式女性形象的建构和对其出路的预设,深刻描绘了“五四”启蒙与革命文学的内在逻辑关联:大革命之后,“五四”启蒙的个性主义走入了绝境。“无产阶级革命”从“革命”这一词汇中挣脱而出,替代了原来意指“民主革命”的“革命”,开启了新的政治启蒙机制。因此,我们可以说,不是“启蒙”选择了“革命”,而是“革命”拯救了“启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