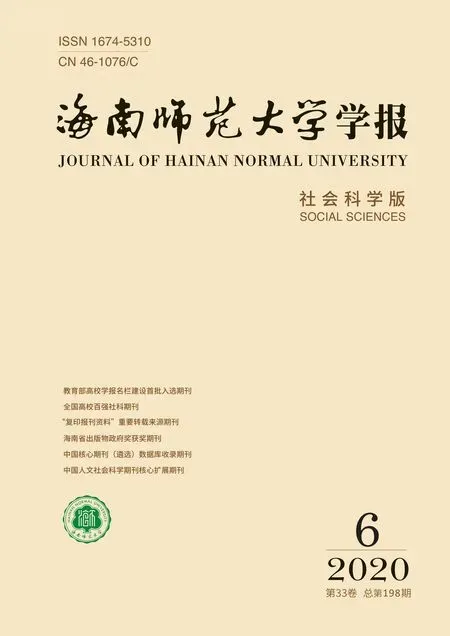“族”的经济性理解
——重读施蛰存《将军底头》
郭文瑞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5)
施蛰存小说《将军底头》中少女形象塑造的前后断裂,令敏锐的读者稍感不适。少女先前虽毅然拒绝了将军的表白,告诫其不可为军法之例外;同时却也机巧地推脱甚至许诺了将军,“像将军这样的人,想起来哥哥也不会得再替我另外拣选的”(1)施蛰存:《将军底头》,初刊于《小说月报》1930年第21卷第10号,第1447页。。但当故事结尾将军的头被砍掉,丧失了普通为人资格,更无法成为英雄时,少女则一改先前的镇定、善良与羞涩等正面形象,变得绝情乃至刻薄起来,“喂!打了败仗了吗?头也给人家砍掉了,还要洗什么呢?还不快快的死了,想干什么呢?无头鬼还想做人么?呸!”(2)施蛰存:《将军底头》,《小说月报》1930年第21卷第10号,第1450页。这一唾骂,而不仅是嘲笑,使得将军失掉首级却仍驾马狂奔寻找少女的行为显得纵情浪漫却又可怜,或至少为读者同情于将军提供了可能,颠覆了作者在全篇中对猛将的解构意图。
少女形象的这一断裂集中体现出历史小说的创作限制。据施蛰存自陈,花卿故事出自清张英(1636—1708)所纂《渊鉴类函》,其“头四”中有“下马沃盥花敬定”之条目,其中提到“适浣女云无头何以盥为”(3)[清]张英、王士祯等纂:《御定渊鉴类函》卷二五九,《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988册,第527页。一句。可见,浣纱女质问将军之事乃出于史载,施蛰存的创作保留了传奇故事本身的框架。这看似印证了郁达夫以来对其“以史实来写小说”(4)郁达夫:《在热波里喘息》,《现代》1932年第1卷第5期。的赞赏,却同时提示了一个研究方向,即花卿之事的本事如何,施蛰存又对花卿本事做了何种改动。从本事改编出发,稽考花卿本事,提炼施蛰存对本事再创作的虚与实,本是历史小说研究的题中之义,却往往被现有研究者忽略。
现有研究侧重施蛰存对精神分析理论的运用,却对其本事改编尤其是其虚构吐蕃族身份或语焉不详(5)如李欧梵在介绍此篇小说时径直写道,“主人公,那个唐朝将军,是汉藏的混血人种”,“二人都不是纯汉人,所以血统中都有异域”;史书美虽意识到施蛰存写花将军事是出于对种族问题的观照,但也如是介绍道,“这篇小说的素材取自《旧唐书》和杜甫有关名将花惊定的诗歌”。参见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毛尖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73页;李欧梵:《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性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63页;[美]史书美:《现代的诱惑:书写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主义(1917—1937)》,何恬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12页。,或只字不提。目力所及,仅有周允中近来明确写出,“施蛰存先生将花敬定写成是吐蕃的后裔”(6)周允中:《施蛰存、花敬定和〈将军的头〉》,《文史杂志》2018年第3期。。周允中之父周楞伽早年曾与施蛰存有一面之缘,晚年亦曾鱼雁往来,周允中对吐蕃身份无史可据的判断即出自其父。本文以小说《将军底头》为中心,希望探讨的正是在历史故事再创作中,施蛰存如何以新引入的“种族”主题,表达自己对时代语境中种族观念的理解。
一、 作为文化符号的“花卿”及其意涵
细读《将军底头》可知,施蛰存此作以杜甫《戏作花卿歌》为引,以唐史记载为表,其内里则是无头猛将的民间传奇,小说将杜诗、正史与传奇故事同时入文,揭示了文学经典与正史提供文化符号、稗说依附其上并与之渐合为一的过程,在历史故事再创作中颇具典型性。是以,对花卿本事的稽考不应局限于单一的杜诗唐史起源,而应同时观照传奇故事一线,考虑多条脉络的各自流变与互融共生,着力探讨其中罅隙与转捩点,以呈现花卿故事的更新概貌与核心要素。这正是本文第一小节试图完成的任务,也是理解施蛰存匠心独运的起点。杜诗向有“诗史”之名,花卿随之名留青史,历代杜诗研究者的争议焦点多在于探讨作者意图是赞花卿、讽花卿抑或讽天子,但若意在考证花卿故事的形态流变,则应转换视角,重在考察花卿何以得名花惊定,又何以成为无头猛将。考以相关文献可见,花卿得名具神直至丧元而生的过程本身是多重冲突的力共同作用的结果,此中有家国情怀与地方意气,有文人之怨与市井之趣,亦有种种偶然与误置。
(一)花卿得名“惊定”
首先,杜甫原诗并未记载花卿其名,后世注杜诗者常据《旧唐书》中“崔光远传”与“高适传”补之。但考之早期文献可见,花卿得名“惊定”的逻辑未必严密,本文试以宋人吴曾(1112?—1184?(7)孙赫南:《吴曾生平仕履考补》,《历史教学》2013年第2期。)的一条文献为引线,辨析其与前人文献记载之冲突悖谬处以证之,希与方家探讨。
吴曾笔记《能改斋漫录》较早完整转引《旧唐书》中的花惊定条目,为了解彼时《旧唐书》相关记载提供可能,吴曾以此反驳前人鲍彪(1091?—1160?(8)吴怀东、徐昕:《宋代杜诗注家鲍彪考》,《杜甫研究学刊》2014年第1期。)的质疑。鲍彪质疑旧注花卿名惊定无史可据,吴曾则称《旧唐书》中“崔光远传”与“高适传”有花惊定之名(9)[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73页。,并引旧史原文以驳之,其引文与今日得见基本相同。但细究可知,鲍未在正史中未见花惊定之名的可能性有二,一是如吴曾所言鲍彪未读《旧唐书》,但鲍彪言“新旧史无其人”,可见其曾读旧史;二则是鲍彪所见旧史版本或具体行文与吴所见者相异,鲍彪生年约早于吴曾二十年,生活地域亦不相同,现有文献尚无法排除这一可能。
将新旧两部唐书中相关记载对比阅读亦可见出,花惊定其人其事与上下文联系并不密切,无法排除时人笔录舛误乃至刻意篡改的可能。《旧唐书·光远传》称,“及段子璋反,东川节度使李奂败走,投光远,率将花惊定等讨平之。”(10)[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一一一,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319页。《新唐书》中同一处原文则为,“会段子璋反,东川李奂败走成都,光远进讨平之。”(11)[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四一,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655页。两相对比,“花惊定”之名并无功能意义。旧史《高适传》亦以子璋反叛开篇,以高适代崔光远之职作结,中云:“西川牙将花惊定者,恃勇,既诛子璋,大掠东蜀”(12)[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一一一,第3331页。,并称这是崔光远被罢职的直接原因,这与《将军底头》的设定是一致的,新史则全无此句。
除吴曾所引《旧唐书》外,花惊定之名还较早出现在邵伯温(1056?—1134?)所著《邵氏闻见录》中。邵伯温生年约早于吴曾半个世纪,其所据为嘉州当地花将军庙中的庙史而非正史,其中云“庙史以匣藏,唐至德元年十月(756年),郑丞相告云:‘花惊定,将军也。是岁吐蕃陷嶲州,将军与丞相岂同功者耶?’”(13)[宋]邵伯温:《闻见录》卷十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3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815页。但必须指出的是,此段文字在明刻津逯秘书本与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出现,位于卷十七末,但在现今《邵氏闻见录》通行版本,即中华书局点校本与上海书店本中均未出现。中华书局点校本“以夏校本为底本,诸宋、元、明本俱从夏校本转校,又补校以津逮本及学津本,以及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所引者,比勘异同,择善而从”,其中“夏校本”指民国涵芬楼夏敬观校印本,是公认《邵氏闻见录》旧校各本中最完备者。上海书店本即此涵芬楼旧本之影印本。由此可见,夏敬观考以旧本后并不认可此段花惊定事。参见《邵氏闻见录》中华书局点校本“点校说明”,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6页。。庙史并未记载花卿官列何职,也未交待其后下落,但这一记载已与旧史记载略有冲突。按庙史所载,花惊定立功于至德元年(756年),敌方是吐蕃,功高至与丞相同功。若此言与旧史记载皆非虚,何以花惊定立高功五年后(即上元二年,761年)仍只是西川节度使手下之牙将?何以专咏其功德的庙史只包含战吐蕃事而未含平子璋事?可见,将花将军庙之花将军等同于杜诗之花卿,逻辑并不严密,遑论此段记载乃至《邵氏闻见录》全书之真伪亦受质疑。由邵伯温上溯至黄庭坚(1045—1105)处,花卿之名直接不见。黄庭坚作《书花卿歌后》曾提及花卿庙,并未记载花卿其名,“杨明叔为余言,花卿家(14)注:另作“冢”。在丹稜之东馆镇,至今有英气血食其乡云”(15)[宋]黄庭坚:《黄庭坚全集》,刘琳、李勇先等点校,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404页。。杨明叔指黄庭坚知交杨皓,黄庭坚谪居黔州期间与其来往甚密,杨皓是眉州丹棱本地人(16)[宋]任渊:《山谷内集诗注·再次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8页。,想必对故乡风土传说颇为了解,黄庭坚亦素重视字句来历,但仍未记载花卿其名。
综上所述,若以时间为序稽考花卿得名的早期文献可见,距杜甫最近的黄庭坚未记花卿其名,稍远的邵伯温虽记花卿其名,但依据来自地方庙史而非官修正史,复远的鲍彪据所见正史质疑花惊定其名,反而是距其最远的吴曾以旧史确认花卿其名。这表明花卿名“惊定”并非历史定论,或至少彰显了文献考古的局限性。
(二)花卿符号的意涵增衍与传奇附会
花卿得名“惊定”的逻辑严密与否,并不影响花将军得名后逐渐成为重要文化符号,并由杜诗之意延伸出丰富意涵,形象愈趋立体,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忠勇爱国的程度上升,怀才不遇之怨被确立,影响范围波及全国;二是其人其事被传奇故事附会。
南宋是花卿形象上升的重要节点,这由爱国名臣吴泳(1181—1252?)为花卿加封所制碑文中可见一斑。吴泳认为花卿精神重在忠义,与之相比,平叛之举“特其细也”。更重要的是,吴泳将花卿本身“成都牙将”的地方英雄身份,上升至匡扶社稷的国家层面,碑文虽以咏地方“金马碧鸡”传统起首,却未停留于此,而是进一步上升,“使高祖当此时,必不兴猛士之叹;孝文当此时,必不起良将之思”(17)[宋]吴泳:《鹤林集》卷一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6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09页。。显然,吴泳对花卿的高度评价是对时代困局的想象性解决,其处南宋末造,“权奸在位,国势日蹙”(18)[清]纪昀等:《鹤林集·提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6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2页。,边防废弛;吴泳为蜀人,深知蜀地是南宋后户。他对蜀地名将花卿的赞美,意在赓续传统、激扬士气,思猛士良将以纾国难,其对花卿符号的使用颇具代表性。
对花卿之忠勇爱国的赞美与对其不为所用的哀叹向来为一体两面,后世文人多由“天子何不唤取守京都”(19)[唐]杜甫:《戏作花卿歌》,曾祥波:《杜诗考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378页。一句生发,以之寄托怀才不遇之怨,花卿之名遂广泛出现在元杂剧及明清戏曲中。如汤显祖在改编蒋昉《霍小玉传》作《紫箫记》时,将李、霍二人的引见人由“故薛驸马家青衣也”(20)[唐]蒋昉:《霍小玉传》,[明]汤显祖:《紫箫记》,黄仁忠、陈壭耀评注,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5年,第340页。的鲍十一娘,改为花卿伎妾鲍四娘,花卿则被设置为李益故旧,汤显祖借花卿之口叹怀才不遇,亦颇能体现花卿在后世文人心目中的核心意涵。
花卿得名具神、形象意涵渐趋立体的过程,亦同时是其逐渐成为文化符号并被组合利用的过程,这突出表现在明清两代民间传奇故事对此符号的“附身”上。明清笔记杂俎小说中反复出现的花卿丧元故事,有助于概览民间“丧元勇士”故事类型的形态流变,表明花卿丧元故事其来有自。如明人谢肇淛(1567—1624)称花惊定将军在闻浣纱女无头之言后,并未立即倒地僵仆,而是“乃作贾雍至营问‘将佐有头佳乎?无头佳乎?’咸泣言有头佳”(21)[明]谢肇淛:《五杂组》卷五,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98页。,这提示了无头猛将故事的可能原型。“贾雍无头”典故在《搜神记》《幽明录》《录异传》中皆有记载,鲁迅《古小说钩沉》在辑录《幽明录》《录异传》时亦收之,可见在花卿之前,无头猛将的故事已广为流传,只是人名不一。再如晚于张英的清代藏书家吴骞(1733—1813)曾据其私藏的残本《元一统志》补齐花卿生平,但在吴骞笔下,花卿故事并未止于花卿之死,而是与新的故事类型“立戈发生”组合,“因植戈于冢,祝曰:‘若戈发生,当为立庙。’乙已而戈果生,遂立庙。”(22)[清]方薰:《山静居诗话及其他一种》,[清]吴骞纂,王云五主编:《拜经楼诗话》卷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26页。吴骞另在其杂俎小说集《桃溪客语》中另载明季卢象贞与顺治年间周启琦两位丧元勇士之事,与之相类。
可见,在这一故事类型中,丧元未死是不变轴心,姓甚名谁则是边缘信息,较轻易改变附会。这一故事与比干剖心事相类,成形于明中期,风行于明清两代,表明时人对生命状态与身体器官关系的思考;借路人之口宣布生死,也凸显了语言的述行功能,民众意识与民间趣味借传说形态进入文学文本,花将军之名不过是其载体。
通过以上对花卿得名惊定,成为“文化符号—符号意涵不断扩大—符号被传奇故事‘附身’”等三阶段的梳理可见,施蛰存所面对的花卿“本事”自身已是史实、文学创作、历史记载、民间传说和文人再创作等多重因素纠缠互动的结果,杜诗并非其唯一起源,《将军底头》则可被视为隶属这一脉络的新时代演绎。以上梳理同时表明,花将军的忠勇、贪掠、怀才不遇与丧元仍生等都并非施蛰存虚构,但前者吐蕃血统则毫无根据,属后者主观创作。
二、“将种族作经济(饭碗)问题解”
施蛰存彼时所见材料未必与今日相同,但至少由以上梳理可见,属作者生造的反而是花将军的吐蕃族身份。同时,恰恰是这一吐蕃血统构成故事的核心冲突与叙事发展的绝对动力,进而解构了花卿忠勇善战却怀才不遇的经典形象,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作者的初始解构意图,但吐蕃血统之虚构性却甚少被以往研究者论及。
《将军底头》的现有研究偏重于施蛰存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文学运用,此偏重与施蛰存的创作论自陈及现代文学的现代性诉求密不可分。本节即试图首先简要澄清此一偏重的缘由所在,继而稍作纠偏,探讨施蛰存对“种族”观念的经济性理解。
既往研究对其精神分析技巧的偏重,盖可从以下三方面予以解释。其一,就作者的创作动机自陈与创作论追认而言,施蛰存曾反复提及阅读显尼志勒、弗洛伊德与霭理士之作对彼时文学创作影响甚巨,作者意图向来是文学研究的重点,偏重精神分析是对作者的充分尊重。其二,就美学效果而论,真正赋予《将军底头》“超现实主义”与“色情—怪诞”之跨时空艺术魅力的,是断头猛将溯溪寻爱故事本身具有的“阴森而奇丽”(23)佚名:《书评:〈将军底头〉》,《现代》1932年第1卷第5期。的色彩,而非种族冲突的主题。主题并非决定文艺创作成功与否的关键,仅以施蛰存为例,《鸠摩罗什》的成功开阔了施蛰存的创作雄心与视野,曾想沿此方向写《达摩》《释迦牟尼》,搜集大量材料后却“一句也不敢落笔”(24)施蛰存:《我的创作生活之历程》,《施蛰存七十年文选》,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56页。,这表明叙事的真正完成与艺术魅力的建立常有赖于作者一字一句的具体填补,缘主题以析艺术效果极易南辕北辙。而精神分析理论中爱欲本能与死亡本能间的复杂张力,确乎为花将军的丧元仍生提供了爱欲升华的迷人解释。其三,就现代文学的现代性渴望来说,现代文学的创作与接受中始终萦绕着个性解放与求新求变的诉求,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与建构亦相应地重在新声而非旧物,呈现为线性进步叙事。施蛰存及“新感觉派”的研究者们偏重强调外来的精神分析理论,强调艺术独创性,相对忽视其对传统的承接,即与这一现代性渴望息息相关。《将军底头》自诞生之初,其血统设定便被现代文学读者们径直接受,极少见对其真假虚实的争议,可见其读者并不以之为问题,甚至赞其为纯粹的古事小说。
但正如精神分析理论自身阐明的那样,无意识并非不重要,甚至更重要。如果说施蛰存对精神分析理论与性心理学的刻意运用,体现出其个人及现代文学的现代性诉求,隶属意识层面,那么,其对汉族/吐蕃族叙事框架的设定及种族主题的引入,则属于长期被忽视的政治无意识。故此,在此篇小说发表近一个世纪后,挖掘并重审文本蕴藏的政治无意识,极有必要,也将对深入理解施蛰存个人及其时代大有裨益。
鉴于种族主题历史小说在彼时为数甚少,在施蛰存的创作中也堪称异数,这一问题更值得考察。就时代而言,问世于《鸠摩罗什》之前的现代历史小说篇目较少,更极少涉及种族问题(25)在《鸠摩罗什》之前问世且较有影响的现代历史小说,除鲁迅《补天》《奔月》与《铸剑》外,仅有郁达夫《采石矶》(1922年)、郭沫若《鹓鶵》(1923年)与《函谷关》(1923年)、许钦文《牛头山》(1928年)、王独清《子畏于匡》(1928年)、孟超《陈涉吴广》(1929年)与《查伊璜与吴六奇》(1929年)、冯乃超《傀儡美人》(1929年)、冯至《伯牛有疾》(1929年)等数篇。这些小说除《查伊璜与吴六奇》触及明清易代与异族统治外,其余均与种族问题无涉。参见上海社会科学院编:《中国现代作家历史小说选》,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其后,历史小说勃兴,但种族主题小说依然几近于无,遑论如《将军底头》一样行文处处强调“种族”二字者。就施蛰存创作而言,他对历史故事的关注贯穿始终,始于《鸠摩罗什》(1929年),基本终结于《黄心大师》(1937年),从未放弃旧事新研之乐,《将军底头》正处其创作旺盛期,但《将军底头》与紧随其后的《阿褴公主》(26)此作原名为《孔雀胆》,首发于《文艺月刊》1931年第2卷第10期。是其作品中仅有的两个关注种族问题的小说,其后亦不再涉及。更需注意的是,施蛰存在1931年10月为同名小说集出版作序言时,曾特地反驳时人的过度阐释,其反驳观点之一便是“有人说我是目的在倡议民族主义”(27)施蛰存:《将军底头》,上海:新中国书局,1932年,第2页,序言末尾识曰“民国二十年十月二十五日施蛰存记”。,这与此作诞生之初读者们的径直接受相左,表明种族问题在一年内变得相当敏感,而非无人问津,敏感到作者要多此一举自我辩白。
1930年并非中国现代史上种族危机格外加剧的特殊年份,模糊地将其创作灵感解释为种族危机加剧并不充分,有将创作史与接受史混同之嫌。笔者以为,讨论施蛰存选择种族主题加以敷演的直接原因,更应考虑20世纪20年代后期中国社会学与民族学的初创状况,尤其是潘光旦所引介的种族论与优生论思想的影响。异于清末民初的“黄种”之争或“排满”之说,潘光旦此时引介的种族论思想更为具体。在其《近代种族主义史略》(1925年)一文结尾,潘光旦指出彼时种族问题之争按范围大小可分为两派,“第一派以种为单位,即白种与黄黑二种之对待问题。第二派以族为单位,即白种内部各族之相待问题”(28)潘光旦:《潘光旦文集》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83页。。这一划分有助于细致理解施蛰存笔下的“种族”。由《将军底头》或《阿褴公主》可见,行文中处处可见备受强调的种族或血统之语,其实质是在小“族”而非以往大“种”的尺度上展开讨论,且与潘光旦一致,施蛰存更强调后天因素而非先天血统之作用,“族”即隶属于这一新建立的社会学与民族学脉络与概念系统。
潘光旦1926年归国后,积极传道授业、著书立说、担任编辑(29)潘光旦自1926年回国起,先后在政治大学、暨南大学、东吴大学、大夏大学、光华大学、吴淞中国公学等学校任教,在复旦大学、沪江大学兼职,在《时事新报》“学灯”副刊、《中国评论周报》、《新月》月刊、《优生》月刊、《华年》周刊等报刊杂志任编辑或主编。具体参见吕文浩:《潘光旦图传》,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8-71页。,传播其民族优生论思想;更热衷参与讨论乃至辩论,影响颇广。胡适曾在日记中载其在“平社”讨论的发言,潘光旦称中国民族就数量质量等方面看有大危险,得胡适激赏(30)胡适:《胡适日记全编》“十八,五,十九(S.)”,曹伯言整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20-421页。;其1927年与周建人围绕《中国之优生问题》论辩,1929年与社会学家孙本文围绕《文化与优生学》论辩,来往间更引发诸多关注。如此广泛的社会活动,对沪上学界,尤其年轻学子学术兴趣、学术视野的影响可想而知。学者谭其骧在暨南大学就读时,就曾深受潘光旦社会学基础和种族问题两门课程的启发,热衷向潘光旦求教,讨论范围皆直接关涉谭其骧日后的研究重点,其影响可见一斑。
“族”而非“种”的问题不仅关涉到种族理论的细化,也关涉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中国民族学科的建立。学界普遍认为,20世纪20年代至抗日战争爆发,是中国民族学科的初创期,其中尤为重要的是,中国民族学科于1928年开始开展独立规范的田野调查,这标志着中国民族学科在方法与实践上的充分自觉与独立。此期开展的民族学田野调查主要包括:1928年夏,杨成志等人的川滇交界彝族、苗族考察,颜复礼等人对广西凌云瑶族、苗族的考察;同年8月,黎光明等人对川北羌族、土家族的民族学调查;1929年,凌纯声等人对松花江赫哲族的田野调查等。(31)杨圣敏:《中国民族学的百年回顾与新时代的总结》,《西北民族研究》2009年第2期。这些民族学调查及其调查成果使社会科学意义上的“族”之概念广为人知。施蛰存自1923年起长期寓居沪上,兴趣广泛,热衷参与社会活动,于此时随手拈来风行一时的“族”之概念以为灵感来源,并不意外。但同时由《将军底头》可知,施蛰存在这一时期对“族”的理解相对片面,他试图对其作纯粹经济性的理解,完全剥除种族观念携带的意识形态色彩,以此完成对“族”观念的解构与超越。这一解构意图同时表现在小说叙事与遣词造句两方面。
就叙事而言,施蛰存的经济性理解凸显于《将军底头》前半部分的行文中,即文章起首至将军微醺并被武士告知对其颇为失望的段落,讲述的是一个异族将军因倍感怀才不遇而决意“归国”的故事,字数占据全文近一半,且完全未曾出现“美丽少女”;此后的故事,才是施蛰存所谓“种族与爱的冲突”。在叙事的前半部分,花将军浪漫歌颂吐蕃精神,施蛰存却以全知口吻上翻一层,指出汉族与吐蕃族的区别仅在于汉人无法克服其贪掠本性,“独于要训练他底武士不爱财货,那是绝对地不可能的”(32)施蛰存:《将军底头》,《小说月报》1930年第21卷第10号,第1432页。。花将军口口声声的“种族”精神仅是“出路”或生计问题的一个表征或借口。动摇花将军作战意志的根本原因是其未能升职,而非自小听祖父对吐蕃荣光的渲染,亦非行军路上体会到的艰辛或兵士的无义。自小接受熏陶并不影响花将军“三日之前”仍有作战意志,手下兵士之厌战也只是表面原因,真正原因是兵士奸淫掳掠的不检行径连累了崔光远,更连累了花将军自己的升职,“将军自己也因了这个缘故,只得将功赎罪,依旧守着原来的官职,这是将军在平定东川之后朝夕烦恼着的事情”(33)施蛰存:《将军底头》,《小说月报》1930年第21卷第10号,第1433页。。未能升职的政治失意,更进一步说是为生存所计,同其祖父当年定居成都一样,只是一个中下层武士试图谋生寻找出路的无奈选择,“但我是,如果没有新的出路,将永远被埋混在这些贪鄙者的人群中了”(34)施蛰存:《将军底头》,《小说月报》1930年第21卷第10号,第1438页。。政治与经济失意方使花将军突然产生“异族”身份的自觉,并借“归国”之思完成了精神上从边缘向中心的转化:“在卑贱的汉族里做一个将军,还是在英雄的祖国的行伍里做一个吹号兵为更有光荣些”(35)施蛰存:《将军底头》,《小说月报》1930年第21卷第10号,第1435页。。
施蛰存特意将故事设定在广德元年(763年)或广德二年(764年),而非历史记载的“上元二年(761年)”或“至德元年(756年)”,盖因是岁吐蕃攻入长安,花将军个人世界中的强弱对比恰与整体局势强弱之别形成同构。吐蕃在边境大肆劫掠市镇,是强势的非正义者,大唐则是弱势的正义者,花将军精神上的回归故国亦与客观强弱形势一致,偏向于强者与“中心”。既然如此,全篇故事主旨也随之发生偏移,由通常理解的爱欲消磨集体纪律与作战意志使之堕落,转变为爱欲升华促使花将军超越功名利禄之心,试图成为英雄。这与《鸠摩罗什》中色欲具有的破坏力及其解构倾向背道而驰,却与施蛰存一贯的非政治价值观相符,史书美称其为“用经济(饭碗)问题取代帝国主义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36)此语出自史书美1990年采访施蛰存后的总结。参见[美]史书美:《现代的诱惑:书写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主义(1917—1937)》,何恬译,第390页。。施蛰存对血统种族观的消解,不仅表现在将种族区别作经济问题理解这一核心观念上,更充溢在字里行间,小说以说书人的调侃口吻开篇,“是在广德元年呢,还是广德二年?那可记不起了”(37)施蛰存:《将军底头》,《小说月报》1930年第21卷第10号,第1431页。,野史而非正史的传奇笔调跃然纸上。
三、沈从文《龙朱》中的“你们民族”
施蛰存对“族”的这一经济性理解在与时人沈从文相关创作的对比阅读中更为明显,之所以选择沈从文作为参照对象,原因有二。一是如前所述,彼时关涉种族主题的现代小说本就为数甚少,沈从文又是其中佼佼者,其由苗族传说改编而成的《龙朱》《媚金·豹子·与那羊》作于1928年冬,早于施蛰存作《将军底头》,两者共同早于其后的“九·一八”事变与“一·二八”事变,及其所标志的民族危机之加剧,且二人同在沪上。这保证了二人创作之时外部语境的相对同质化,为细辨施蛰存的种族观念提供参照光谱,尽管这一光谱不得不相当狭窄。二是因为沈从文祖母是苗族人,这与小说中花将军祖父是吐蕃人的情节,似有关联。这一表面上的牵强,却因沈从文对自我苗族血统的(未)公开书写乃至讳莫如深,成为值得深入读解的症候。
《龙朱》之前言《写在“龙朱”一文之前》,是沈从文小说中为数不多的直抒胸臆之语,其中多有对都市生活的激愤与哀痛。这一篇作于其生日的文章是“送与那供给我生命,父亲的妈、与祖父的妈、以及其同族中仅存的人一点薄礼”,沈从文自矜血管中明明流着“你们民族的健康的血液”,自愤因都市生活而变得虚伪庸懦,种种优良品质消失殆尽,以至于“生的光荣早随你们死去了”(38)沈从文:《龙朱:写在“龙朱”一文之前》,《红黑》1929年第1期,第13页。。可见,与血液或血统相比,沈从文更重视“高贵”“热情”等精神文化品质,并以此为拯救都市生活之颠沛与失意的精神武库,但行文始终并未直接说明何为“你们民族”。尽管沈从文在1922年离湘进京时已被其父告知其苗族血统,作于1932年的《从文自传》曾多次修订再版(39)具体修改情况参见彭林祥:《〈从文自传〉的版本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第3期。,但他却始终对此三缄其口。直至半个世纪后,沈从文方才公开书写自己的苗族血统,使“你们民族”的含义更为显豁。在《从文自传》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修订版本中,沈从文首次写道,其父是其叔祖父与青年苗族姑娘所生,而后被过继给其祖父一脉。换言之,沈从文的生身祖母是苗族人。具体而言,这一未公开书写除个人心理外,更有时代印痕:一是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民族学科刚处起步期,民族识别工作尚未展开;二是民族学科始终处于“造国民”与“造民族”两种旨归的漩涡间,20世纪30年代民族危机的加剧使得小“族”差异成为次要矛盾。
首先,就中国民族学科的建立状况而言。1933年,凌纯声、芮逸夫赴湘西开展苗族人类学调查,其成果《湘西苗族调查报告》迟至1937年方写成,此时距沈从文进京已逾十年。可知,在沈从文作《龙朱》至《从文自传》时,“苗族”尤其湘西苗族仍是一个历代相传的文化意义上的能指,而非社会科学意义上的严格理论概念。实际上,直至新中国建立之初,“苗”名还同时是区域泛称、历史泛称乃至服饰或生活习惯等文化泛称,所指并不精确。
其次,民族学科自建立之初便处于“造民族”与“造国民”的冲突中(40)马戎:《民国时期的造“国民”与造“民族”——由王明珂〈民族与国民在边疆:以历史语言研究所早期民族考察为例的探讨〉一文说起》,《开放时代》2020年第1期。,现代学科建立与民族国家建立的冲突纽结于“种”内“族”的识别问题上,“九·一八”事变与次年“一·二八”事变更促使沈从文直接体会到“族”之上“国”的更大尺度的、非观念性的实在差异,创作出《泥途》等与“一·二八事变”直接相关的作品,《从文自传》正是作于这一时期,这也部分解释了沈从文彼时对自身苗族血统的避而不谈。
与沈从文歌颂苗族精神却又隔绝概念认同的暧昧书写相比,施蛰存更为挥洒自如。在《将军底头》中,施蛰存纵情书写着花将军对吐蕃人与吐蕃精神的赞美,“在他底失望的幻念中,涌现起来的是祖父嘴里的正直的,骁勇的,除了战死之外的一点都不要的吐蕃国的武士”(41)施蛰存:《将军底头》,《小说月报》1930年第21卷第10号,第1433页。,与之相比,自己的兵士不过是“一群不成材的汉族的奴才”(42)施蛰存:《将军底头》,《小说月报》1930年第21卷第10号,第1434-1435页。。花将军对正直、骁勇之灵魂与力量的赞美,与沈从文笔下的“高贵”“热情”“勇敢”而痛恨“虚伪庸懦”的字句颇为相似,乃至于前者可被视为对后者的重写。但异于沈从文早期完全服膺于对种族精神的浪漫想象,施蛰存以说书人的全知叙事口吻,进一步将此浪漫想象解构为经济出路问题,从而弃置乃至超越了种族观念携带的文化与意识形态色彩。花将军所感叹的原来汉族武士中也有少女哥哥这样英勇庄重的人,也暗合了潘光旦所谓,“宜以严格的个体差别作选择之根据,而不宜根据笼统的统计的团体间之差别”(43)潘光旦:《潘光旦文集》第1卷,第387页。作优劣判断之语,彰显其对种族集体概念的解构意图。
概言之,施蛰存此时对种族的经济性、个人性与超意识形态性理解,与沈从文对种族的文化标举形成对照,某种程度上甚至可将此篇小说视为对沈从文苗族小说的回应,毕竟《龙朱》直接为沈从文引来“天才”(44)沈从文在复程朱溪信中说“有人在我《龙朱》一文上又称我为天才”,转引自吴世勇:《沈从文年谱》,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72页。赞誉,在文坛颇得好评。那么,沈从文又如何评价花将军四分之一的吐蕃血统设定及施蛰存的经济种族观?沈从文未曾直接评价《将军底头》,无由得知其态度,只可对二人彼时交往状况稍作敷演。沈、施二人相识源于1928至1929年,彼时沈从文与丁玲、胡也频同住沪上,施看沈是“一个温文尔雅到有些羞怯的青年”(45)施蛰存:《滇云浦雨话从文》,《沙上的脚迹》,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32页。,两人相见寥寥,仅在后来施蛰存编《现代》杂志向沈索稿后,方才相对熟络。但沈看施却并不这么疏淡,其发表于1930年11月的评论文章《论施蛰存与罗黑芷》,恰在《将军底头》问世一月之后,批评对象主要是小说集《上元灯》,并未论及《将军底头》。其中虽盛赞施蛰存文体纤细,风格优美,技巧完美;却同时借施、罗对比,指出施蛰存囿于其诗人人格,缺乏对广阔生活世界的有力书写,笔力难及“那所谓宽泛的人生,下流的,肮脏的,各特殊世界,北方的荒凉,南方的强悍”(46)沈从文:《论施蛰存与罗黑芷》,《现代学生》1930年第1卷第2期。,而这“宽泛的人生”恰为沈从文所擅长且偏爱,其对施蛰存的不认同可见一斑。但“捕风捉影”也只能止步于此而已。讽刺的是,本文开篇提及的《将军底头》中的叙事罅隙,即少女形象前后的强烈反差,还是在事实上推翻了施蛰存对种族观念的经济性与非意识形态性理解。如果说施蛰存认为种族精神的核心只是经济问题,并作此文以讽之,那么文本客观叙事效果则恰好走向其反面,即以少女为代表的整个外部世界都宣布超越意识形态并不可能,将军以自己的空虚与死亡证明个体的超种族或非种族之念在时代现实中并无容身之地。
差异是叙事的动力,种族差异亦不例外。但叙事差异一旦超出文本限度走向实践,又必将作为客观历史沉积,在实践与思想层面不断创造新的差异,乃至与作者主观意图及时代诉求相悖,这便是行文处处消解种族观念却依旧被评价为“提倡民族主义”的施蛰存个人所面临的困境。“族”之识别所纽结的多重冲突,使作者无力应对,只好趋于沉默,这也是20世纪30年代历史小说勃兴与种族观念普及时期,种族主题创作却依然寥寥无几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