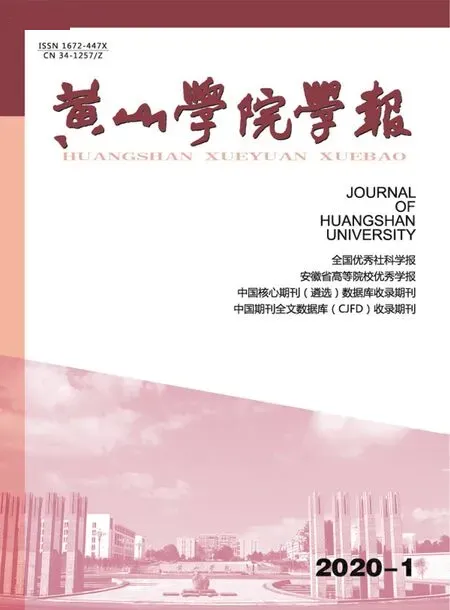托妮·莫里森小说《秀拉》的空间解析
濮志敏
(黄山学院 外国语学院,安徽 黄山245041)
引 言
美国非裔女作家托妮·莫里森第二部小说《秀拉》主要讲述了生活在俄亥俄州梅德林小镇上黑人女孩奈尔和秀拉的成长历程。文本中反复出现的社区、街道、房屋不仅对情节的发展和主题深化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构建起小说人物成长的存在空间。黑人社区包罗万象的情怀搭建起具有一定社区价值的社会空间。黑人女性在追求自我的过程中利用身体的力量对世界做出解释和透视,演绎出独特的身体空间。整篇小说虽然以时间为章节标题,但是在显性的时间节点下从隐形空间角度对小说进行解析,一定意义上拓展了小说的深度,更有助于提升读者对小说的理解力。
20世纪末,文化研究和社会理论领域出现了引人注目的空间转向,成为研究社会的一种新视角。1974年列斐弗尔出版了《空间的生产》,引起了社会理论对空间概念的系统关注。在物理空间、精神空间之余,他创造性地指出了空间的社会生产性:即社会关系的重组与社会秩序实践性建构过程。空间不是抽象的逻辑结构,而是一个动态的实践过程。在他看来,空间不仅是物质的存在,也是形式的存在,是社会关系的容器。他认为思考空间的每一种方式,人类每一个空间性“领域”——物质的、精神的、社会的——都要同时被看作是真实的和想象的。他提出有着辩证关联的三元组合:空间实践(感知的空间)、空间的再现(构想的空间)、再现的空间(实际的空间)。同时,列斐弗尔指出“空间的生产,开端于身体的生产。”他强调身体和空间有着物质上的直接同构关系,二者追求着共同的解放。[1]结合列斐弗尔空间理论的观点,从存在空间、社会空间、身体空间三个方面及其相关表征意义来解读《秀拉》。
一、存在空间与政治表征
挪威建筑理论家诺伯格·舒尔兹认为存在空间是比较稳定的知觉图式体系,亦即环境的“形象”(image)。它从大量现象的类似性中抽象出来,具有“作为对象的性质”。[2]空间对存在结构具有两个方面意义:一方面是“抽象”的,它属于拓扑学或几何学范畴,由一般图式而成立;另一方面是“具体”的,它指对自然景观、城市景观、建筑物、物理事物一类的“环境诸要素”的掌握。其中存在空间结构分为以下几个阶段:地理、景观、城市、住房和用具。莫里森在接受来访时称:“写《秀拉》时,我对小说背景中的城镇、社区和街坊都很感兴趣,尽我所能地也把他们塑造成强有力的角色。”[3]为此,从存在空间中的景观、社区、住房、用具这几个阶段解读《秀拉》,能够更好地了解作者意图。
1.景观和社区
所谓景观阶段(landscape),一般是指存在空间的轮廓作为“图”时所表现出来的“地”的阶段。景观阶段的图式是通过人的行为与地形、植物分布、气候等的相互作用而形成。[2]40
小说开篇展现出梅德林社区被改造成高尔夫球场的景观:他们连根拔起龙葵和黑莓,山毛榉不复存在,梨树也不见了,杂乱无章、衰微破败的建筑物夷为平地,横跨小河的人行桥已经不见了。随后,通过一个有关黑鬼的笑话还原了“底部”与“山谷”的由来并介绍了二者所形成的独特景观:黑奴得到了山上的一块地,那里水土流失严重,种子都会被冲掉,冬天寒风呼啸不已。白人住在富饶谷地里的那座河滨城镇上。黑人只能从每天都能真的低头看着白人这件事上得到微不足道的安慰。[4]景观具有自身的结构,“底部”与“山谷”显示出空间格局上的二元对立。黑人在谈论“底部”来源时,从其略带自嘲的口吻得出白人在明知“顶部”生存条件之后,根据自己的意愿改变事实,凸显出种族掌控体现在空间占有上。长久以来,空间上的隔离是奴隶制度下种族歧视空间表征的最主要形式。这一景观的建构让读者强烈感受到在白人主宰的社会中,白人在空间上的优越感,而处于社会边缘的黑人丧失话语权。空间是白人阶层行使权力的主要媒介,而黑人抗争的历史可以浓缩为空间融入的斗争。通过蓄意制造出地理上的“底部”和“顶端”,白人成功地划分出空间表征,再现了白人对空间的掌控,逼迫黑人从理念上接受黑人永远不可以居住在肥沃的峡谷里这一观念。随着资本的注入,“底部”解体,人们逐渐入住山谷。这二元对立的景观的改变不仅意味着随着民权解放运动的兴起,黑人处在社会边缘的存在空间正在逐渐发生变化,同时也表达了莫里森对消除不平等的空间对立的希冀。
梅德林社区的出现本身承载着白人阶层设计的空间表征。河底隧道工程将雇佣黑人的传闻变成了告示,然而一场冰冻摧毁了一切,也标志着夏德拉克一直挂在嘴边的预言应验开始。人们似乎开始意识到好运不会青睐于他们,于是大家异乎寻常地加入夏德拉克一年一度的“自杀节”。尽管隧道的坍塌夺去了大多人的生命,但是这一空间实践表明了黑人反对白人的空间表征的决心。小说最后展示了社区变迁的面貌。有钱的黑人搬入谷底,白人走进高地。至此,白人规划的原始空间表征标准改变为另一种尺度——贫穷与富有。空间反映了动态的社会构成以及权力关系。“底部”的建构真实地再现了1920年到1960年的美国。一方面,白人通过空间表征实施对美裔黑人的压迫;另一方面,黑人通过自身的空间实践改变着表征空间。[5]
2.住宅和用具
住房始终是存在的中心场所。人正是在自己的住房中看到自己的统一性。住房的结构首先是一个场所的结构。它包含着由自己统一各种二次场所的路线所划分的内部结构。在住房中进行各种活动,表现生活的一个形态。[2]46
在《秀拉》中,莫里森曾多次对人物居住的房屋进行详细的描述。奈尔的母亲海伦娜出生在一个殷实的黑人家庭中,这点从对塞西尔·萨巴特住宅的描写中可以看出:法国式的盒式住宅、宽阔的花园、锻铁栏杆。可是在海伦娜和她的母亲罗谢尔简单的对话之后,就带着奈尔迅速地离开了这栋房子回到自己在梅德林的家。并且一个劲地说:“总算过去了,顺顺当当地过去了。”[4]30海伦娜这种迅速逃离自己家乡的行为可以理解为想对过去的彻底遗忘。在海伦娜嫁给威利之后,他们住在一座门外有砖砌的前廊、窗上挂着真正的蕾丝窗帘的漂亮房子里。[4]19她把自己的家布置得干净而又整洁,把自己装扮得端庄而又优雅,可以看出她努力过上上等人的生活。她试图用自己的方式改变既定的表征空间,事实上,她也是在不断地模仿她一直逃离的表征空间。
而与之并置的是秀拉那个粗犷朴实的家。各式各样的人生活在这又大又旧的房子里:收养的三个杜威、退伍回来的李子、浪荡的柏油娃娃。伊娃住在顶层,俯瞰着房子里发生的一切。伊娃家庭的社会性与资本主义的核心家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与此同时,伊娃还在不断地增建房屋:今天加一条楼梯,明天盖一个房间,东开一座门,西修一条廊。[4]33可见,在白人统治的社会中,伊娃正用她自己的空间实践对抗白人预设的空间表征。
存在空间的最底层阶段停留在用具之间。床是一个极其有意义的场所。布鲁诺指出,是人“为了休息而制造出来的”。也是人的运动找到最后目标的场所。[2]48
《秀拉》中的李子从战场归来之后,萎靡不振。伊娃不忍心看到他这样颓废下去,趁他在睡觉之余,一把火结束了他的生命。伊娃在和汉娜解释为什么要杀死李子时是这么说的:他一声不响地摸到床上,想分开我的腿,重新爬回我的子宫里去。[4]76布鲁诺指出:床所体现的中心,是人从那里开始一天,夜里又返回那里的场所。[2]49伊娃在床上给予了李子生命,又在同一空间终结了他的生命,这也是以另一种方式让他获得重生。床对秀拉而言也是获得存在的场所。通过在床上与其它男性暧昧,然后像橘子皮一样把他们抛弃,她从中找到了存在的意义。所以床对于秀拉而言是一个寻求自我的场所。
景观、社区、住宅、用具这些存在空间相互作用,多重穿插,构成一个复合作用的场。黑人女性,他们既不是白人,也不是男人,在小说中通过最基本的用具——床,寻求自我价值。社区、街道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体现。景观的形成又体现出一定的空间政治。所以,正如海德格尔所说:每逢一个世界,都发现属于它的空间的空间性。一切行为都意味着“在某个场所”。[6]
二、社会空间与价值表征
列斐弗尔创造性地将日常生活视为比生产更重要的主导性的位置空间是富含社会性的,它是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的脉络,同时叠加着社会、历史、空间的三重辩证。社会空间是在物质性和精神性的基础上,基于人的活动开展的社会关系的展现。
莫里森对个人与社区的关系给予了高度的关注,人物与社区的命运紧密相连。她的每一部作品基本都存在一个核心社区。《秀拉》中梅德林小镇是生养秀拉和奈尔的地方,它促成女孩们个性形成,又与她们个性相抵,成为了相互补充的“角色”。《最蓝的眼睛》里佩科拉遭到社区的唾弃,走向毁灭。《所罗门之歌》和《柏油娃娃》里的奶人、雅丹和森与社区的关系虽然没有完全弥合,但进了一步。《宠儿》里的赛丝在社区的帮助下,治愈了萦绕在她心头多年的心灵创伤。历史三部曲中的社区尽管有毁灭性,但是有给人疗伤的作用。《家》中的特洛斯小镇更是给了弗兰克和茜家庭式的温暖。社区价值在社区的日常生活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列斐弗尔的无限“阿莱夫”是无所不包的同时性空间,既具有各种可能性也包含着危险。它是彻底开放的空间,也是社会斗争的空间。
博特姆是一个在地理位置、经济和种族诸方面都遭受压迫、孤立与歧视的黑人居住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个在苦难中挣扎、在苦行中煎熬的黑人社区渐渐形成了界定人们生活的传统。在环境恶劣的山上自给自足地生活,人们大多拥有救人危难的善良之心。莫里森认为这就是社区存在的价值之所在。这种价值观在小说中无处不在。在一战中受到惊吓的夏德拉克回到社区后,决定将死亡规定在特定时间以求得内心的平静,随即创造了“全国自杀节”。这种怪异、荒诞的行为逐渐被人们当作生活中的一部分接受。这是黑人们面对压迫求生存时合情合理的态度。他们从自己能忍受各类打击,能相互帮助的行为上看到了某种成功,并产生出与日常生活相匹配的带点黑色的幽默感。由此,他们才有心调侃自己居住区的名称。
秀拉对祖母不孝,在已婚男人中选择性伙伴,甚至连朋友的丈夫也不放过。她的各种行为与社区“法规”相抵触,成为不折不扣的“妖魔”。在黑人社区中,人们对恶采取一种“接受态度”:“他们让恶随意蔓延,逞凶得势,从不设法改变它、消除它,或是防止其再度发生。他们待人也是如此。”他们对外界环境造成的艰难、压迫、死亡习以为常,表现出一种包容和坚韧。社区中的人们虽然厌恶她,但都遵从自己的原则,不伤害、驱逐她。秀拉从本质上讲是社区不可或缺的内在组成部分。社区对秀拉的需要也许超过秀拉对社区的需要。秀拉的“恶行”起到使社区向善的功能。人们更多的担负其母亲的责任、妻子的责任。从一定意义上,秀拉去世后,博特姆黑人社区开始了解体的进程。
三、身体空间与权利表征
列斐弗尔认为:空间的生产,开端于身体的生产。“空间的生产”理论所推崇的“生产”主要指的是具有尼采式的“生命的(身体)生产。”他的空间观与身体理论密不可分。身体是空间性的,而空间也是身体性的。他倡导用身体体验想象空间,用身体实践去体现构成空间。尼采认为权力意志构成了一切存在者的基本属性,作为权力意志的动物性当然就是人存在的根本规定性。这样,在人的定义中,身体取代了形而上学中理性的位置。
生活以身体为目标,身体的力量和意志创造了生活,生活与身体的关系就此发生了置换:生活成为身体的结果,生活被身体的权力意志锻造和锤炼,在身体的激发下,生活成为一件艺术品。生活、身体、自我处于无限的可能性之中,它们永远处于即刻性状态,永远在创造,永远在无休无止地进行艺术生产。[7]
伊娃通过对自身身体的毁灭,换来了金钱,建造了一栋房子,让全家人安居乐业。汉娜有意让男人们注意到她的臀部、她纤细的足踝、她那露水般光滑的皮肤和长得出奇的脖子,还有她那含笑的眼睛。[8]通过性感的身材和挑逗的举止,与很多男人亲近,所以造就了与女人少见而短暂的友谊。通过身体,构筑起来的是男人的欲望,女人的敌意,自身的满足。
战场归来的李子整天无所事事。他的头发几个月没有理或梳过,衣衫褴褛,脚上没穿袜子。[4]48头发是人身上最具可塑性的东西,也是最具象征性和表现性的东西。它和身体只是溶解在同一个自我之中,它虽然是身体的一个模糊能指,但却是自我的一个明确所指。对身体形象的不屑一顾,影射出经历了一战后的李子已经形同躯壳,人存活的意义已经消失殆尽。所以伊娃决定行使母亲的权力,一把火了结儿子的生命。
在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双重压迫下,黑人女性除了自己的身体之外一无所有,肉体成了她们表达自己思想的方式之一。秀拉与尽可能多的男人偷欢,然后将他们抛弃。她的举动摆脱了女人被挑选、被支配的地位,彻底颠覆了黑人社区的法规。[8]238秀拉通过构建自身的身体空间,向人们彰显出女性权利的主体性。也正是通过对床伴的自主选择,来确认自己作为黑人女性的主体性存在。
结 语
文学作品中所构造的空间不仅仅只是一个环境的因素或者说是地理学上的特定点,它还有着特定的意识形态的内涵。[9]莫里森不但在她的小说中呈现了丰富的空间书写,而且把这些空间书写与空间叙事模式结合起来,共同表现她小说创作的主题。同时,空间的生产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作家以及一代人的现实或者理想。从空间角度解读《秀拉》,不仅是对处在社会边缘的黑人女性的生活现状的真实写照,也表达出莫里森身为黑人女作家对美国黑人和女性的深切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