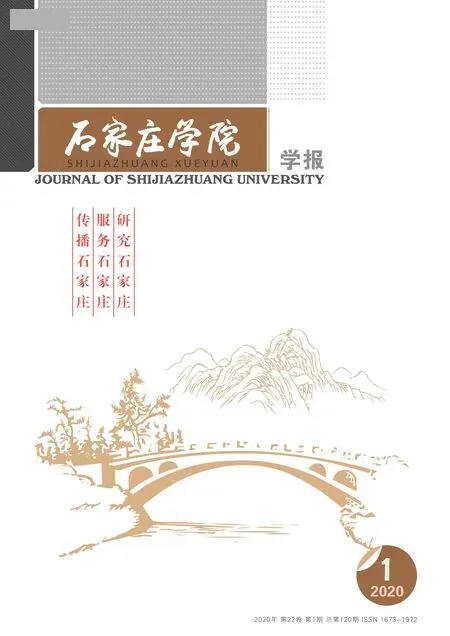恩格斯晚年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研究
赵庆元
(河北地质大学 社会科学部,河北 石家庄 050031)
在马克思与恩格斯对立论的理论语境中,恩格斯晚年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始终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研究视点,而自然辩证法与恩格斯晚年哲学研究重心的偏移、恩格斯晚年历史唯物主义通信对所谓经济决定论的修正以及自然辩证法研究的深层理论意涵则是这一研究视点中极具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的问题。加强对恩格斯晚年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相关理论问题的研究,对于我们深刻理解恩格斯与马克思之间的思想与理论关系,准确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精髓与精神实质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
一
如果将1870年停止在曼彻斯特的欧门—恩格斯公司的工作并迁居伦敦作为恩格斯晚年时期的开始,那么在从1870年到1895年总共25年的晚年岁月中,恩格斯哲学研究的重心到底是什么,是以自在自然或自然科学为基础的自然辩证法还是以人类社会及其历史发展为核心的历史唯物主义呢?在这一问题上,从我国现今马克思哲学研究的现状来看,认为以自在自然或自然科学为基础的自然辩证法构成恩格斯晚年哲学研究的重心是一个不仅在实践唯物主义的非传统模式中,甚至也在辩证唯物主义的正统模式中普遍流行且占主流地位的观点。当然在我们看来,这种观点之所以会成为占主流地位的观点,并不单是因为恩格斯有一个他自己也承认的在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脱毛”时期,也不单是因为恩格斯有一部在其晚年哲学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的《自然辩证法》,而且还因为在许多人看来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然观,而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真正建构恰是从恩格斯晚年的自然辩证法研究开始的。因此,如果没有恩格斯晚年的自然辩证法研究,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构建,从而以这种自然观为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解释模式的产生就是难以想象的。例如,安启念在《通向自由之路》中谈及恩格斯与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差别时就明确地表达了这种观点。安启念指出,恩格斯在早期曾与马克思合作从事哲学研究,但他本人的主要哲学著作写于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主要是《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晚年有关唯物史观的通信以及《自然辩证法》,在这些著作中影响最大的是《反杜林论》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而这两部著作所依据的哲学思想基本上来自《自然辩证法》。因此,恩格斯主要哲学著作的研究对象是自然界,它所关注的主要是存在于人之外的自然界。[1]6安启念还进一步分析了恩格斯晚年哲学研究重心形成的历史根源。安启念指出,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刺激下,自然科学在17、18世纪获得飞速发展并从19世纪开始进入到恩格斯所说的整理材料阶段,而正是在这一阶段出现了细胞学说、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以及达尔文的进化论三大自然科学发现,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自然观)不过是对19世纪以三大发现为标志的自然科学成就的概括总结,正如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是对18世纪自然科学发展的概括总结一样。[1]6-7那么,应该如何看待这种关于恩格斯晚年哲学研究重心的观点呢?单从表象上来看我们或许会认同这种观点,但如果深入到历史事实的深层,问题的结论似乎就没有这么简单了。
如前所述,认为自然辩证法构成恩格斯晚年哲学研究重心的决定性论据来自于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研究,那么,这一研究在恩格斯从1870-1895年25年的晚年岁月中到底占有多大比重呢?在1885年9月为《反杜林论》所写的二版序言中,恩格斯指出:“当我退出商界,从而有时间进行研究的时候,我尽可能地使自己在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来一次彻底的——像李比希所说的——‘脱毛’,八年当中,我把大部分的时间用在这上面。”[2]349这就是说,从恩格斯自己的说法来看,自然辩证法研究耗费了他8年左右的时间,而按照我们通常的说法,恩格斯晚年的自然辩证法研究是在1873-1882年间进行的,那么,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研究大约有9年左右的时间。但是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在8年当中他是将大部分时间花费在“脱毛”上面,这也就是说还有小部分的时间并没有花费在自然辩证法的研究方面。例如,在1876-1878年间恩格斯耗费了2年左右的时间撰写了《反杜林论》的鸿篇巨制;在1874年5月到1875年4月间花费了将近1年的时间研究波兰、法国和俄国等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特点,撰写了由5篇论文组成的《流亡者文献》;在1880年应保尔·拉法格的请求将《反杜林论》中引论的第1章、第三编的第1章和第2章改写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77年6月应威·白拉克的请求为《人民历书》撰写了关于马克思生平与思想的《卡尔·马克思》,等等。如果将所有这些研究所占用的时间除去,那么在恩格斯晚年真正用于自然辩证法研究的时间大概只有5年左右。显然,如果说8年或9年在恩格斯25年的晚年岁月中还算是一个比较长的时间的话,那么这5年左右的时间则无论如何都不能算是比较长的时间了。可是,如果单从形式上来看自然辩证法的研究都没有占用恩格斯晚年的大部分时间,自然辩证法又如何能够成为恩格斯晚年哲学研究的重心呢?当然,对于恩格斯晚年哲学研究的重心是不能单凭时间的长短来作推断的,还要根据恩格斯晚年的研究与著作情况来作具体分析。
虽然恩格斯晚年花费了比较长的时间进行自然科学与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并最终形成了《自然辩证法》这部重要的哲学著作,但他不仅在整个晚年时期进行了大量并非是自然辩证法而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而且正如前面所指出的,就是在进行自然辩证法研究的过程中还进行了许多属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并为此撰写了大量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著。例如,为了遏制杜林主义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内部的泛滥,恩格斯撰写了《反杜林论》这部系统批判杜林主义的著作;为了系统评述作为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间环节的费尔巴哈哲学,恩格斯撰写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按照恩格斯的说法,他正是在这两部书里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到“目前最为详尽的阐述”[3]698。在1884年,为了实现和完成马克思的遗愿,恩格斯撰写《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系统阐释摩尔根关于古代社会研究的深刻意义,为历史唯物主义奠定了一直延伸到原始社会的历史科学基础。在1890-1894年间,恩格斯通过致施密特、布洛赫、梅林以及博尔吉乌斯等人的书信,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作了重要的补充与修正。当然,在这里我们没有提到恩格斯从1883年开始直到1895年所进行的《资本论》第2、3卷的编辑与出版工作,而实际上,按照现在马克思哲学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路向的逻辑,对《资本论》的编辑整理所体现出来的某些研究也应该归属到历史唯物主义的范畴,至少相对于自然辩证法的研究来说是更加接近于关于人类社会及其历史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
这里并没有列出恩格斯晚年的所有重要论著,但单是这些对于理解历史唯物主义来说极其重要的研究成果就足以说明恩格斯晚年哲学研究的重心究竟在何处。那么,在这些重要研究成果中,恩格斯到底在怎样的意义上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呢?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通过对历史唯物主义与德国古代哲学之间历史联系的深刻分析,系统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新的历史观产生的历史必然性。恩格斯指出,近代德国哲学在黑格尔那里完成了,而黑格尔哲学的伟大功绩就在于,它第一次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2]736-737但是,黑格尔哲学包含着一个不可救药的内在矛盾,这就是,一方面它以历史的观点作为基本前提,即把人类的历史看作一个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按其本性来说在认识上是不能由于所谓绝对真理的发现而结束的;而另一方面,它又硬说它自己就是这种绝对真理的全部内容。黑格尔哲学的深刻矛盾最终导致了黑格尔哲学的破产和黑格尔学派的解体。[2]737恩格斯指出,在黑格尔学派的解体过程中还产生了另一个派别,这就是与马克思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现代唯物主义,这种现代唯物主义“第一次对唯物主义采取了真正严肃的态度,把这个世界观彻底地(至少在主要方面)运用到所研究的一切知识领域里去了”[3]242。当然,在恩格斯看来,由于费尔巴哈在唯物主义自然观方面所实现的进展,这种现代唯物主义所谓“运用到一切知识领域去”主要是运用到人类历史的领域里去,而恰恰是在这个领域里,由于对人本身的抽象的理解,费尔巴哈最终没有能够将唯物主义原则彻底地贯彻到人类历史的领域,从而造成了自然与历史的对立;而马克思的现代唯物主义之所以能够将唯物主义原则彻底贯彻到人类历史的领域,正是由于他实现了费尔巴哈没有能够实现的从抽象的人到现实的、活生生的人的转化。通过对以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关系的历史分析,恩格斯清晰地勾勒出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产生的理论逻辑。
第二,通过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系统分析,全面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新的历史观的基本原理。恩格斯指出,无论历史的结局如何,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但是在历史上活动的许多单个愿望在大多数场合下所得到的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往往是恰恰相反的结果,这样就产生了一个旧的唯物主义从来没有给自己提出过的问题,这就是在这些动机背后隐藏着的又是什么样的动力?在行动者头脑中以这种动机的形式出现的历史原因又是什么?[3]246恩格斯指出,如果说在以前的各个时期对历史的动因的探究几乎是不可能的话,那么,“在现代的历史中却至少已经证明,一切政治斗争都是阶级斗争,而一切争取解放的阶级斗争,尽管它必然地具有政治的形式,(因为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归根到底都是围绕经济解放进行的。因此,至少在这里,国家,政治制度是从属的东西,而市民社会,经济关系的领域是决定的因素”[3]251。但是恩格斯指出,不仅国家这一政治上层建筑是由一定社会的经济关系决定的,社会的思想上层建筑,无论是处于下层的法律还是远离物质基础的哲学、宗教等意识形态,也如同国家政权一样归根到底应该从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中得到说明。因此,尽管在历史领域内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但无数的单个愿望和单个行动的冲突,在历史领域内所造成的却仍然是一个同没有意识的自然界中占统治地位的状况完全相似的状况。[3]247
第三,通过对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与本质问题的深刻分析,系统论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史前史基础。作为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理论,历史唯物主义不能只研究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而必须同时研究包括原始社会和资本主义以前的阶级社会在内的前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这样才能在全面研究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上揭示关于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形成涵盖人类社会一切历史发展阶段的普适性历史理论。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恩格斯在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的基础上撰写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部重要著作,从而极大地拓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证科学基础。恩格斯指出:“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缔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种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劳动越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越受限制,社会制度就在较大的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3]2但是,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逐渐提高,特别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导致私有制和阶级产生以后,人自身的生产对社会制度的支配就越来越小,而各种新的社会关系特别是社会的经济关系对社会制度的支配作用越来越大,这种支配作用的日益扩大最终使以血族关系为基础的旧社会被组成为国家的新社会所取代。因此,无论是在原始社会还是以后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政治社会,物质生产都始终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而在原始社会中血缘关系对社会制度起支配作用的情形,归根到底也还是由物质生产不发达的状况造成的,因而在根本上仍然是经济关系决定作用的一种表现。
我们无意反驳安启念关于恩格斯晚年的主要著作“所依据的哲学思想基本来自《自然辩证法》”的观点,这里想说的是,如果说马克思仅仅是在1845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他与恩格斯共同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作了唯一一次系统的阐释,并且我们知道这唯一一次的系统阐释其实也没有完成,那么,恩格斯晚年对历史唯物主义所作的上述阐释显然就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了,这就是它第一次使历史唯物主义成为一个相对完整且逻辑自洽的科学与哲学理论。但是,如果不是将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晚年哲学研究的重心或从来就没有离开过青年时期作为重心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我们如何能够想象恩格斯有对历史唯物主义从理论到历史的系统阐释呢?因此,那种认为恩格斯晚年哲学研究的重心是以自在自然或自然科学为基础的自然辩证法或以自然辩证法为核心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是根本不能成立的。
在上面对恩格斯晚年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概括中,一方面,我们并没有提及历史唯物主义通信的丰富内涵及其所承载的理论意义,这正是下面要着力展开分析的问题。另一方面,对恩格斯晚年哲学研究重心的分析中,我们也并没有提及这一问题以及引发的争论所承载的理论意涵,这将是本文第三部分重点分析的问题。
二
19世纪90年代,针对资产阶级学者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歪曲以及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的青年党员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误解,恩格斯在1890-1894年间通过致施密特、布洛赫、梅林以及博尔吉乌斯等人的书信,对政治以及意识形态因素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进行了深入阐释,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进行了重要的补充与修正,这些补充与修正如上面所作概括的那样,同样是恩格斯晚年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众所周知的是,正是恩格斯晚年书信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补充与修正引发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从第二国际开始一直持续到今天的激烈争论。那么,恩格斯晚年的历史唯物主义通信到底引发了怎样的争论,这种争论又到底承载了怎样的理论内涵呢?
众所周知,在1845年《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主要是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作了经典的概括。时光转到20世纪初的第二国际时期,第二国际理论家伯恩施坦在1908年出版了他全面修正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公开对马克思1859年的经典概括提出批评。伯恩施坦指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概括使用的是“独断论的措辞”,把意识和存在截然对立了起来,“人的意识和意愿表现为非常从属于物质运动的因素”,以致“把人仅仅看成历史力量的活的代理人,他几乎是违反着自己的意志而执行历史力量的任务”[4]51。但是,恩格斯在19世纪90年代的书信以及其他著作中却“对生产关系的决定力作了限制”,其结果是,唯物史观被扩大了,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纯粹唯物主义的,更谈不上是纯粹经济的了”。[4]59伯恩施坦认为,正是通过恩格斯的修正与补充,历史唯物主义从马克思的不成熟的“最初的形态”提高到了“成熟的形态”,[4]53社会民主党制定革命政策不应该从马克思早年具有独断论倾向的唯物史观出发,而应该以恩格斯晚年成熟形态的唯物史观为根据。
从伯恩施坦对马克思经典概括的批判来看,其批判的核心质点在于经典概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决定论解读,而批判的基本依据则是恩格斯晚年通信对经济决定论的修正。从伯恩施坦的批判开始,历史唯物主义是否是历史观上的经济决定论,恩格斯的晚年通信是否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决定论作了修正就成了人们长久争论的话题。应该看到,虽然现在的人一般并不认同至少在表象上并不认同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立场,但其对马克思的经典概括以及对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书信的解读却是不折不扣地承续了伯恩施坦的观点,不同的地方主要在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所谓经济决定论到底是谁提出来的,如果说伯恩施坦倾向于认为马克思是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决定论的始作俑者,那么现在的人们则大多将其归咎于以拉法格为代表的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甚至恩格斯。那么,恩格斯的晚年通信到底是否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决定论作了修正呢?我们先来看恩格斯的晚年通信到底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怎样的补充与修正。
在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通信中,恩格斯在检讨他和马克思在阐释历史唯物主义中的“过错”的基础上,系统地阐述了政治以及意识形态因素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恩格斯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是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政治形式及其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确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的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里表现出一切因素的相互作用。”[3]695-696在1890年10月致施密特的信中,恩格斯具体地分析了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的作用。恩格斯指出,社会产生它不能缺少的某些共同职能。被指定执行这种职能的人,形成社会内部分工的一个新部门。这样,他们也获得了同授权给他们的人相对立的特殊利益,他们同这些人相对立而独立起来,于是就出现了国家这一“新的独立力量”,这个“新的独立力量总的说来固然应当尾随生产的运动,然而由于它本身具有的、即它一经获得便逐渐向前发展的相对独立性,它又对生产的条件和进程发生反作用”;“总的说来,经济运动会为自己开辟道路,但是它必定也要经受它自己所确立的并且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即国家权力以及和它同时产生的反对派的运动的反作用”[3]700-701。恩格斯指出:“法也与此相似,产生了职业法学家的新分工一旦成为必要,就又开辟了一个新的独立领域,这个领域虽然一般地依赖于生产和贸易,但是它仍然具有对这两个领域起反作用的特殊能力。”[3]702至于那些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意识形态领域,即宗教、哲学等,例如拿哲学来说,它和那个时代的普遍的学术繁荣一样,也是经济高涨的结果,但是由于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因而“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小提琴”[3]703-704。因此,如果认为我们否认经济运动的政治等等的反映对这个运动本身的任何反作用,那他就简直是跟风车作斗争了。[3]704那么,恩格斯的这些论述是否修正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呢?
对于表1中的这些电路,无论是动态功耗还是静态功耗,算法1的结果均与算法2相同.针对每一个基准电路做进一步分析,对于每一个极性值相同的MPRM电路,算法1均能得到与算法2相同的动态功耗和静态功耗计算结果(因空间关系,这里不再给出每一个MPRM电路的功耗计算结果),这验证了算法1功耗计算结果的准确性.
这里首先需要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决定论解读作一点说明。如前所述,除去伯恩施坦之外现在的几乎所有人都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决定论解读归咎于恩格斯或第二国际的正统理论家,严格说来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我们这里不去探究伯恩施坦所提到的马克思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而只举出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决定论解读及其运用。按照恩格斯的说法,《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是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说明一段现代历史的初次尝试”[3]506,那么马克思是如何说明法兰西的阶级斗争的呢?在分析1848年6月无产阶级起义问题的时候马克思指出,七月革命之后,法国政府陷入严重的财政困难,这种财政困难使七月王朝一开始就依赖于资产阶级上层,但对资产阶级上层的依赖又不断造成日益加剧的财政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又有两起世界性的经济事件加速了普遍不满的爆发并最终演变为无产阶级的起义,这就是1845年和1846年的马铃薯病害和歉收以及英国普遍的工商业危机。因此,在马克思看来,法国1848年6月的无产阶级起义纯粹是由于经济的原因所引起的。但是我们知道,1848年6月的无产阶级起义最终以失败而告终,那么起义的失败是否说明经济因素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源呢?马克思在起义之后通过对最近10年法国经济发展状况的分析发现,虽然1847年的世界贸易危机孕育了二月革命和三月革命,但从1848年开始法国工商业转入复兴并在1849年和1850年达到全盛。这就说明,法国当时的经济状况还没有发展到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程度,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整个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所能达到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5]470显然,马克思对法国革命的基于法国经济状况的分析所运用的不仅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且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决定论。
但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决定论解读绝不是马克思的偶尔萌发而是其一以贯之的思想。例如,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内部,产生出一些交往关系和生产关系,它们同时又是炸毁这个社会的地雷。……如果我们在现在这样的社会中没有发现隐蔽地存在着的无阶级社会所必需的物质生产条件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关系,那么,一切炸毁的尝试都是堂吉诃德式的荒唐行为。”[6]106在1867年的《资本论》回应巴师夏所谓古代人和罗马人专靠掠夺为生的观点时,马克思指出:“如果人们几百年来都靠掠夺为生,那就得经常有可供掠夺的东西,或者说,被掠夺的对象应当不断地被再生产出来。可见,希腊人和罗马人看来也要有某种生产过程,从而有某种经济,这种经济构成他们的世界的物质基础,就像资产阶级经济构成现今世界的物质基础一样。”[7]98-99因此,真正说来马克思才是对历史唯物主义作经济决定论解读的始作俑者。
现在我们来看恩格斯晚年通信是否修正并最终抛弃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决定论。
的确,恩格斯晚年的历史唯物主义通信充分肯定了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政治以及意识形态因素的重要作用,但是,如果不是片面地而是全面地理解恩格斯的相关论述我们就会发现,虽然恩格斯充分肯定了政治以及意识形态因素的重要作用,但几乎在每一次阐释政治以及意识形态因素作用的时候,恩格斯都不忘强调经济因素或经济关系在“归根到底”意义上的决定作用。例如,在1890年致布洛赫的信中,恩格斯指出,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而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归根到底还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向前发展”[3]696。在1894年致博尔吉乌斯的信中,恩格斯指出:“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相互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并非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归根到底总是得到实现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相互作用。”[3]732但是,在某些人看来,恩格斯的“归根到底”恰恰是弱化了并因而否定了经济因素或经济关系的唯一决定作用。这里,我们先不说经济因素“归根到底”意义上的决定作用应该作何种解释,而是先看一下政治以及意识形态因素与经济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到底应该作怎样的理解。许多人纠结于经济决定论将经济因素或经济关系作为社会历史发展的唯一决定因素的观点,认为经济决定论的根本错误就在这里,因为在他们看来,政治以及其他意识形态的因素同样对社会历史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如果将经济因素或经济关系的作用不是看作唯一的,那就一定是认为政治以及其他意识形态的因素同样对社会历史发展具有决定作用。可是,这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吗?否,这是历史观上典型的二元论或多元论,或者按照某些论者的说法叫做多因素论。那么,怎样的解读才是历史观上真正的唯物主义呢?不可否认,政治以及意识形态因素同样对人类社会及其历史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在承认它们对人类社会及其历史发展重要作用的同时,一定要进一步追问它们又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正如恩格斯在讲到思想动机的作用时所追问的那样,我们不能像恩格斯所批判的旧唯物主义那样“从来没有给自己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以至于在“历史领域内自己背叛了自己”。[3]248而当进一步追问政治以及意识形态的决定因素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它们在根本上又是由经济因素或经济关系决定的,正如恩格斯晚年在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系列论述中一再强调的。可是,也许有人会质疑,这难道不正是恩格斯所说经济因素或经济关系在“归根到底”意义上的决定作用的实际含义吗?但是,如果说在初始的时候就将政治以及意识形态因素看作是同经济因素或经济关系一样的决定因素,哪里还有追问它们又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必要与可能呢?实际上,可以而且也应该对政治以及意识形态作决定因素的进一步追问本身就说明它们根本就不是也不可能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既不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唯一决定因素,甚至也不是同经济因素或经济关系相并列的多元决定因素。这也就是说,政治以及意识形态因素即使在直接的意义上也不构成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而既然政治以及意识形态因素在直接的意义上都不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当然它们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就更加不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那么“归根到底”在这里还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吗?因此在我们看来,那种认为恩格斯的晚年通信因强调经济因素或经济关系在“归根到底”意义上的作用而否定经济决定论的观点是根本不能成立的。
其实,如果不是局限于历史唯物主义通信,而是联系恩格斯晚年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系统论述,我们就会发现,恩格斯并没有而且也不可能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决定论作什么修正。例如,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的第二编用三节的篇幅,借对杜林唯心主义暴力论的批判,深入阐述了经济状况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第四节,恩格斯借对费尔巴哈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批判,系统分析了经济动因或经济关系对阶级、国家以及意识形态因素的决定作用;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通过对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的深刻解读,进一步论述了物质生产或经济关系对家庭形式的演化以及阶级和国家起源的决定作用。所有这些论述,尽管存在着某些争议,在总体上都不存在对经济因素决定作用的弱化以及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决定论的修正;而且除了晚年的历史唯物主义通信之外,似乎也没有人提出过恩格斯其他论著修正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决定论的问题,相反地倒是有一些传统的观点对恩格斯的晚年著作提出过弱化经济因素决定作用的质疑,并认为这种弱化背离了马克思的思想。因此,除非认为恩格斯晚年的历史唯物主义通信与其晚年的其他论著之间存在着显见的逻辑上的矛盾,否则认为恩格斯晚年通信修正了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决定论的观点就是不能成立的。
这里我们或许还应该对恩格斯在给梅林的信中所提到的他与马克思的“过错”作一点解释,因为似乎有太多的人把这种“过错”理解为恩格斯和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决定论解读。恩格斯指出:“只有一点还没有谈到,这点在马克思和我的著作中通常也强调的不够,在这方面我们大家都有同样的过错。”[3]726那么恩格斯所说的“过错”是指什么呢?恩格斯指出:“我们大家首先是把重点放在从基本的经济事实引出政治的、法和其他意识形态的观念以及以这些观念为中介的行动,而且必须这样做。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为了内容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这些观念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这就给了敌人以称心的理由来进行曲解和歪曲。”[3]726显然,从恩格斯的说明来看,他所说的“过错”主要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形式方面而非内容方面,即并不是在是否能够从基本的经济事实引出政治的、法和其他意识形态的观念方面,而是在如何从经济事实中引出这些观念方面。这显然并不涉及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问题,而仅仅涉及决定作用的形式问题;而既然不涉及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问题,恩格斯又怎么可能对这种决定作用作出修正呢?因此,那种借所谓的“过错”来作为恩格斯修正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决定论的理由同样是不能成立的。
三
现在我们来看恩格斯晚年哲学研究的重心问题及其引发的争论所承载的理论意涵。
为什么以实践唯物主义为代表的许多人一再地指责恩格斯晚年以自然辩证法为重心的哲学研究呢?其根本原因在于,在他们看来,恩格斯晚年的自然辩证法研究偏离了马克思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改变世界的主题。在这方面,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卢卡奇无疑是最典型的代表。卢卡奇认为,对于辩证方法来说,中心问题乃是改变现实,而要使辩证法的中心问题真正转向改变现实,就必须把最根本的相互作用,即历史过程中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置于与它的方法论相称的中心地位。但是,作为“辩证法的决定性因素,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在作为范畴基础的现实中的历史变化是思想中的变化的根本原因等等,并不存在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认识中”[8]51。因此,把辩证方法“限定在历史和社会的领域,极为重要”[8]51。但是,恩格斯在对辩证法的理解中却“错误地跟着黑格尔把这种方法也扩大到对自然界的认识上”[8]51,其结果是,“辩证法不再是革命的方法,不管如何想(终归是妄想)保持‘流动的’概念”[8]50。实际上,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我国此后大多数讨论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关系并强调两者差异的思想家“都遵循了卢卡奇的思路”[1]240。其实,卢卡奇的思路说起来并不复杂,这就是,马克思哲学的根本问题在于改变现实,而改变现实要依赖于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其核心是依赖于由作为主体的人所发起的自觉实践活动,但是在恩格斯晚年研究的自然辩证法中却根本看不到人的实践活动的踪迹,这不仅忽略了马克思哲学改变世界所倚重的主体性实践,更由于这种忽略而将马克思哲学引向了与改变世界的主题完全无关的方向。
那么,恩格斯晚年真的由于转向自然辩证法研究而偏离了马克思哲学改变世界的主题吗?答案是否定的。的确,从恩格斯最初萌生自然辩证法研究的意向来看是具有某些偶然性的,因为他只是1873年5月30日早晨躺在床上时脑子里出现了一些“关于自然科学的辩证思想”之后才开始较系统的自然辩证法研究,尽管这种偶然性如果脱离了当时自然科学的巨大发展以及由此提出的一系列哲学问题也是无法理解的,但是随着自然辩证法研究的不断深入,这种由外在刺激所引发的自发研究就逐渐被自觉的研究所取代,而到最后,自然辩证法研究所具有的对于马克思哲学的深层理论意涵便充分地展现了出来。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1882年德文第一版序言中,恩格斯指出:“这样的读者也会感到奇怪,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发展史的简述中提到康德—拉普拉斯的天体演化学,提到现代自然科学和达尔文,提到德国的古典哲学和黑格尔。”[2]691恩格斯指出:“科学社会主义本质上就是德国的产物,而且也只能产生在古典哲学还生气勃勃地保存着自觉辩证法的国家,即在德国”,因为“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在现代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上的特别应用,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2]691-692在1883年德文版中借修正“在德国”这一笔误的机会,恩格斯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解释。恩格斯指出:“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一方面必须有德国的辩证法,同样也必须有英国和法国的发达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德国的落后的——40年代初比现在还落后得多——经济和政治的发展阶段,最多只能产生社会主义的讽刺画。只有在英国和法国所产生的经济和政治状况受到辩证法的批判以后,才能产生真正的结果,因而,从这方面看来,科学社会主义并不完全是德国的产物,而同样是国际的产物。”[2]691因此,在恩格斯看来,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不仅不像我们现在的某些人所理解的那样远离了马克思哲学改变世界的主题,而恰恰是与这一主题深刻关联着的。但是,在德国这样一个按照有些人的说法具有深长辩证法传统,并且还产生了作为辩证法集大成者黑格尔的国度里,为什么还需要进行一种作为辩证法部门形式的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呢?这就要说到德国辩证法在黑格尔之后的历史境遇了。
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德国资产阶级的学究们已经把关于德国伟大的哲学家及其创立的辩证法的记忆淹没在一种无聊的折衷主义的泥沼里,这甚至使我们不得不援引现代自然科学来证明辩证法在现实中已经得到证明。[2]692恩格斯的话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在黑格尔去世以后,而特别是在费尔巴哈宣布废弃思辨概念以后,德国民族就“坚决摒弃了在柏林老年黑格尔派中陷入困境的德国古典哲学”[9]40,这也正是马克思所说的德国知识界发号施令的、愤懑的、自负的、平庸的模仿者像莱辛时代大胆的莫泽斯·门德尔松对待斯宾诺莎那样对待黑格尔,即把它当作一条“死狗”的时期。[7]24由于黑格尔及其辩证法当作“死狗”被抛弃,旧的形而上学及其固定不变的范畴就在科学中又重新开始了它的统治,[9]40“从此以后,在公众当中流行起来的一方面是叔本华的、而后甚至是哈特曼的迎合庸人的浅薄思想,另一方面是福格特和毕希纳之流的庸俗的巡回传教士的唯物主义。在大学里,各种各样的折衷主义互相展开竞争,不过在一点上它们是一致的,这就是它们全都是由过时哲学的十足的残渣拼凑而成的,并且全都同样地是形而上学的”[3]692。恩格斯分析指出,这种现象的出现是有它的自然原因的:黑格尔学派的狄亚多希的统治在空谈中结束以后,自然就出现一个科学的实证内容重新胜过其形式方面的时代。同时,德国以异乎寻常的精力致力于自然科学,这是与1848年以来资产阶级的强大的发展相适应的;在这种科学中思辨倾向从来没有多大地位,随着这种科学的时兴,旧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直到沃尔弗式的极端浅薄为止,也就重新流行了起来。黑格尔被遗忘了,新的自然科学唯物主义发展了,这种唯物主义在理论上同18世纪的唯物主义几乎没有差别,它胜于后者的地方主要只是拥有较丰富的自然科学的材料,特别是化学和生理学的材料。[9]40-41因此,如果不了解德国辩证法在黑格尔之后的历史境遇,那就根本无法理解恩格斯晚年何以要进行一种自然辩证法的研究。
可是,正如我们知道的,实践唯物主义似乎也不否认辩证法对于马克思哲学改变世界的主题所具有的意义,而且事实上,他们也正是以此为据展开对恩格斯晚年自然辩证法研究的批判的,这样就产生了一个似乎是矛盾的现象:坚持只有辩证法才能体现和实现马克思哲学改变世界的主题的实践唯物主义却起劲地批判恩格斯晚年的自然辩证法研究。这里实际上隐含着一个到底什么样的辩证法才契合于马克思哲学改变世界的主题的问题。那么,到底哪一种辩证法才更契合于马克思哲学改变世界的主题呢?
如前所述,卢卡奇与实践唯物主义之所以强调实践辩证法是因为看中了人的主体性,它试图通过直接体现在人身上的自觉意图以及由这种意图所支配的自觉实践实现改变世界的愿望,毕竟这里还有第二国际将理论与实践看作相互分离的两极所造成的后果的鉴戒。但是,这里存在着两个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一是世界能否被改变,二是世界如何被改变。就世界能否被改变的问题来说,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任何对于世界的改变活动都必然要预设世界的可改变性,如果世界是不可改变的则谈论改变世界就没有任何意义了;[10]363就世界如何被改变的问题来说,任何改变世界的活动都必须设定改变世界的自觉目的,如果没有明确而自觉的目的,所谓改变世界就成了一种毫无目的的本能盲动。其实,从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来看,这两个问题其实又是一个问题,所谓世界的可改变性就是世界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支配之下的运动、变化与发展过程,而所谓改变世界的目的性,则不过是世界本身的客观规律及其逻辑指向在人们头脑中的自觉表现形式,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失掉了单纯外在自然必然性外观”而“被看做是人自己提出的目的”的“外在目的”而已。但是,如果我们作认真的反思就会发现,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论逻辑在这里遇到了困难:一方面,虽然实践唯物主义高举马克思哲学改变世界的旗帜,但是他们似乎从来就没有认真思考过世界可改变性的问题,似乎只要人的意志希望、愿意并且需要改变世界,世界就一定能够在人们的自由意志以及自由意志支配之下的实践活动中被改变。这难道不是一厢情愿的左倾幻想吗?现在,倒是有人提出了世界可改变性的问题,但却不仅没有把这种可改变性理解为世界在自身规律支配之下的变化与发展过程,反而走向了完全否定世界本身客观规律的非决定论立场,这就不仅没有真正解决世界可改变性的问题,反而又消除了基于世界本身的客观规律设定改变世界自觉目的的可能。这样一来,如何改变世界这个在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模式中远非烦难的问题在这里就实实在在成了问题。对此,实践唯物主义往往是依据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人的类特性的思想来消解这种困难。在实践唯物主义看来,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自由自觉的活动的人的类特性实际上就是一种未被异化的人的理想状态,这种未被异化的人的理想状态正是马克思实现对现实不合理状态的理论上的批判与实践上的改造的依据,这实际上是将某种永恒真理与正义的观念作为马克思哲学改变世界的目的论依据。但是,如果把马克思哲学改变世界的目的性看作是某种永恒真理与正义的观念,那就不仅中了资产阶级思想家们的圈套,而且根本上就是在为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们做嫁衣裳,因为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们早在马克思哲学之前就据以永恒真理与正义的观念提出过理性王国的理想,并且认为这种理想早已在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得到了实现。
然而问题远不止此,如果我们作进一步的分析就会发现,马克思哲学改变世界主题的不仅不是以这种未被异化的永恒的理想状态为前提,而恰恰是以对这种状态的彻底批判与否定为起点的,无论这种状态是理想性的还是在现实中已经实现了的。例如,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永恒化的错误。马克思指出,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这个事实出发,却不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它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的过程套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又把这些公式奉为规律,但是它没有理解这些规律,没有指明这些规律是怎样从私有财产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这样就将私有财产以及以私有财产为社会形式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永恒化了。而如果马克思批判这种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永恒化的理解,他也就必然批判作为这种永恒化的观念表现的关于人类永恒真理与正义的观念。例如,在1877年给佐尔格的信中,马克思就曾经严厉批判过德国无产阶级政党内部的这种倾向。马克思指出:“在德国,在我们党内流行着一种腐败的风气,在群众中有,在领导中尤为强烈。……这些人想使社会主义有一个‘更高的、理想的’转变,就是说,想用关于正义、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女神的现代神话来代替它的唯物主义基础。……几十年来我们做了许多工作和花了许多精力才把空想社会主义,把对未来社会结构的一整套幻想从德国工人的头脑中清除出去,从而使他们在理论上(因而也在实践上)比法国人和英国人优越,但是,现在这些东西又流行起来,而且其形式之空虚,不仅更甚于伟大的法国和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也更甚于魏特林。”马克思指出:“在唯物主义的批判的社会主义时代以前,空想社会主义本身包含着这种社会主义的萌芽,可是现在,在这个时代以后它又出现,就只能是愚蠢的——愚蠢的、无聊的和根本反动的。”[3]627-628
如果说马克思不仅不承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某种真理与正义观念的永恒性与绝对性,反而是以对这种永恒性与绝对性的批判与否定为起点的,那么到底哪一种辩证法才最契合于马克思哲学改变世界的主题的问题事实上就已不言自明了:如果说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论逻辑不仅不否认这种永恒性与绝对性的存在,反而是以这种永恒性与绝对性为前提的,那就只有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辩证法才最契合于马克思哲学改变世界的主题,因为这种唯物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7]24的。而正是因为只有唯物辩证法从暂时性方面去理解事物的本性,最终否定并彻底抛弃了一切形式的永恒真理与正义的观念,并藉此为马克思哲学改变世界的主题提供了逻辑的基础,恩格斯不仅在对唯物辩证法的一般阐述中,而且在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具体阐述中一再地提到并指明这一点。恩格斯指出:“辩证法在考察事物及其在观念上的反映时,本质上是从它们的联系、它们的联结、它们的运动、它们的产生和消逝方面去考察的。”[2]736而黑格尔辩证哲学的真实意义和革命性质正是在于,它“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绝对的人类状态的观念。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东西、绝对的东西、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生成和灭亡的不断过程、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过程,什么都不存在。它本身就是这个过程在思维着的头脑中的反映”[3]217。如前所述,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恩格斯曾经将科学社会主义看作是在英国和法国的发达的经济关系受到德国辩证法批判之后的结果,当然这里的辩证法只能是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并用于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可是,如果恩格斯的意思不是说,科学社会主义只有借助于唯物辩证法才能彻底否定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那里被永恒化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并据此为马克思改变世界的主题提供了逻辑的基础,则显然是非常奇怪的。因此,如果在马克思哲学改变世界的主题中确实蕴含着一种辩证法的思想,这种辩证法也只能是恩格斯晚年通过自然辩证法研究雄辩地证明出来的唯物辩证法。当然,有鉴于现在许多人对唯物辩证法从暂时性方面理解事物的误视与曲解,我们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唯物辩证法从暂时性方面来理解事物绝不是现代西方历史哲学那种完全非决定论的东西,否则,马克思恩格斯终其一生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运行规律以及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就显得匪夷所思了。
总之,正如青年时代的恩格斯与马克思一样,改变世界仍然是恩格斯晚年哲学研究的重心,如果说恩格斯在晚年进行了一种形式上好似“闲棋冷子”的自然辩证法研究,那也不过是以改变世界为主题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不仅丝毫无损于马克思哲学改变世界的主题,而且恰是与这一主题深刻关联的,无论这一研究在初始阶段具有怎样的偶然性质。这应该是我们对恩格斯晚年哲学研究的不带有任何偏见与误解的正确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