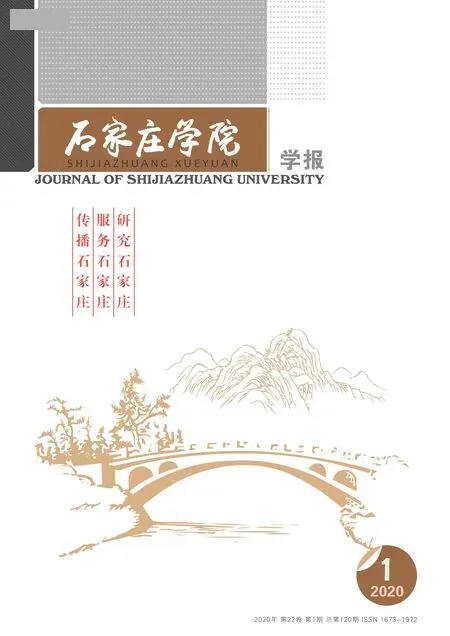电影的审美形而上
——中国传统美学下克拉考尔理论分析
王逸飞
(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0715)
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cauer)在《电影的本性》中描绘了电影与生活之间构造的意境。人们在审美观照中走进了这种电影意境,获得了一种复杂的体验。克拉考尔看到了电影的独特性,看到了它给观众带来的主客之间的交流和交融感。叶朗先生曾在《现代美学体系》中把美学研究的对象设定为“审美活动”,以便结合多学科、从多角度突破以往研究立场的限制。依靠审美活动实现中西美学的贯通,以审美活动作为研究对象切入克拉考尔的电影理论,可以有效地在中国语境之下讨论电影的意境。必须强调,西方对电影的研究是分析式的,缺乏对电影整体的观照,而中国传统美学的研究是整一的,在于把握整体的意象。
一、电影之“道”
将克拉考尔的电影理论放入中国美学体系中讨论时,我们必须为之寻找一个合适的位置。在克拉考尔眼中,电影是对生活中不确定、意外和偶然事件的集合,他在强调电影本性时注意到了电影与现实的关系。为了追求真实,他将电影引向对无限生活表达的可能之中,这是一种“有”“无”的交融、一种从影像向生活流的流动。道家“道”的思想具有从有限到无限的韵味。生活作为一个融贯一切的大熔炉,是克拉考尔眼中一切的本源、电影的起点。电影的起点——生活,就是万物的本源——道。
电影是虚与实的结合,而虚实、有无融成“道”,电影承载了“道”。《老子》中有:“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道”是原始混沌,存在于天地产生之前,包含形成万物的可能性,没有具体形象,不能通过知觉感受其无限和无规定性。同时作为万物之母,“道”又是“有”,是“实”。人们可以在这种“有无结合”“虚实相生”中看到事物的本质。“道”既存在于现实世界里,又反映在电影意识中。抽象的生活无形无影,看不到实体和边界,是虚无。但它却孕育了无数的电影,赋予影片灵魂,是实在。在电影的审美活动中,人们可以看出被掩盖和隔离的生活本身。摄影机前有限的“实”和镜头外无限的“虚”共同构成了电影中的“道”。
“玄鉴”是对“道”的观照。玄鉴电影,便是观照自然,抛开形式,透过影像表面看到背后的生活流。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电影由“道”所生,每一部电影都是万物的一次表达。电影描述摄影机前的现实,但意义不停留于描绘现实本身,而是让观众看到偶然性事件背后的无限可能,将观众引入生活本源。
“只有无头无尾的情境;既无开始,又无中段,也无结尾。”[1]78电影就是用有限的形式展现生活的无穷意境。克拉考尔表示电影只是对生活流的截取,目的在于将观众引入生活本身。银幕形式倾向于反映出自然物象中含义模糊的本性,即路西安·塞弗所谓的“现实的无名状态”。这种模糊之感,与用线条勾勒出来的中国山水画有异曲同工之妙,都可以在隐现的印象中勾勒出虚幻的境界。电影与现实的关系颇似绘画中的留白,没有着实的填满只有淡淡的勾勒。老子讲的“无”在书画上便是空白。电影应该和水墨画一样“同自然之妙有”[2]197。不求与现实相匹配,只求欣赏者能从片段和插曲中看到空白部分,看到生活流本身的意境,通过镜头来展示无穷尽生活流的品味。画将不再是画本身、电影也不是电影自身,画与自然、电影与现实生活达到完美交融。
“电影对‘街道’的永不衰竭的兴趣最鲜明地证实了它对偶然事物的近亲性。”[1]87克拉考尔特别强调“街道”类场景的重要意义。这类场景受到许多电影作者的喜爱,吸引人的地方就在于它们对意外的偏爱。如在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偷自行车的人》中,透过维托里奥·德·西卡的摄影机,观众看到了战后罗马的街道、广场和工厂——一幅落寞的城市图景。这种场景制造了一种不确定性,也就是说无数个故事的孕育、无限种可能的“自然流露”在这里产生,电影在有限的形式中蕴藏了无限的生活流。
现实性目的的记录往往侧重于人群而不是个人。在经验这种图景时,人们能产生芸芸众生和人生无涯的渺茫感,一种“沧海一粟”的沧桑。这种不确定的可能性会使人们产生不同的人生感悟,将人们从有时间概念的影片本身带到永恒静止的现实之中。有无、虚实的结合可以引导观众进入人生本原和人生境界的思考之中,这也恰恰体现出了追求“道”的“超脱”精神。克拉考尔意识到现实本身的意境,生活流可以将观众带入现实之中,在抽象化的影响下寻找物质的本质。从“道”出发,人们可以探索观照电影时进入的一个世界——意象世界。
二、电影的意象
电影意象的意蕴是一种人生感、宇宙感和历史感,是一种“物我两忘”、一种“超脱”。谈到意象,有必要先简单论述中国思维方式的独特性。中国采取“一分为三”的思维方式,依照庞朴对中国传统思想的考释,在“物”和“意”之间存在“象”。他说:“象之为物,不在形之上,亦不在形之下。它可以是道或意的具象,也可以是物的抽象。”[3]235因此,中国思想便形成了“道—象—器”或“意—象—物”的图示。“象”是一种类似主客观融合的度物境界,不是主客二分的状态。对于电影而言,在电影作品和主体之间存在一种交融状态。解读克拉考尔理论所打造的这种“意象”,必须从其对于电影和现实关系的讨论入手。克拉考尔强调电影对于生活——也许就是生活流的图解的亲近。观众对电影的观照会被引入无限的生活图景之中。意境由此而生,一种人生感裹挟而出。一部部作品就像生活的一个个图示。
“诗不是诗人的创造,而是‘神的诏语’;诗人只不过是神的代言人,在陷入迷狂时替神说话而已。”[4]20在柏拉图眼中,诗人创作时的神灵附体,颇似祭祀时产生的迷狂状态。观影是一种仪式,电影打开了观众通往电影意象的大门。对于现实世界的超越并不是消极避世,“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5]83-84。酒后的张旭悟到人生的洒脱,进入迷狂的“高峰体验”。而观看电影时,人们也同样达到这样一种“忘乎山水之间”的状态,陷入电影的“深渊”,一时意识不到自己的存在。
迷狂背后蕴藏的是一种超脱。中国传统中的道家思想对超脱有独到的见解。庄子曾说:“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睨于万物。”这种超脱背后是自然与精神的交流。超越电影的形式而进入意象世界,人们可以实现与世界和生活精神的直接对话,甚至会感觉到自己就是精神本身。电影审美带来的超越绝对有别于宗教和理性的超越,是一种电影自身的超越。品读这种超越的意味,被满足和愉悦填满,意象本体向观众显现。
意象的基本结构是情景统一,这种统一不是两者的累加,而是两者交融形成的一种东西。就电影而言,审美意象需要观众和影片本身的主动参与,在两者中间形成一种意向性的结构。单独的情和单独的景都不能形成意象,只有两者的交融才能形成整一。在电影之中,意象统治一切,从导演创作影片到观众观赏影片都是在追求意象。意象是电影的本体,在克拉考尔那里就是对无限生活流的感悟,它统治着整个的感兴过程。
中国传统美学理论经常关注到这种“超脱”问题,这是一种从有限尘世到无限意境的实现。电影引导观众进入一种迷狂。古代信仰随着尼采眼中的“双希”文化的衰落而倒塌,人类的思想大厦需要被完整的新意识形态重新建筑,电影此后接起信仰之刃,让生活变得可以接受。在中国美学家眼里,艺术替代宗教来实现超脱。蔡元培说:“我的提倡美育,便是使人类能在音乐、雕刻、图画、文学里又找见他们遗失了的情感。”[6]215审美逐渐代替了宗教,艺术鉴赏的态度颇似宗教下的那种迷狂状态。电影作为一种大众文化的载体,具有最广阔的受众和文化适应性。因此,这种新的迷狂必将由电影引起。电影的审美意象便是一种超脱。
电影打开了人们生活意象的大门。但每个人的生活图景是有差异的,所以每个观众在电影面前各显其情,进入了不同的意象世界。电影的意境是专属的,具有特性的,也就是说,具有多样性和主体性。作为自然的完美载体,影像为“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的审美体验提供了可能。审美主体在欣赏时自然是有选择的,会依照自己的喜好和品味来选择,而电影为不同品味的人提供了无数种可能。
虽然每个观众的意象世界是不同的,但是却存在一种相同的状态——审美感兴。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在下文中还会详细讨论。对于电影的观照可以将观众引入意象世界,用中国美学来讲,是一种“物我两忘”的状态,这种交融和忘我的状态抛开了功利和目的。
电影的意象在观众的审美活动之中产生,克拉考尔强调在现实化影片的背后看到生活的意象。笔者认为,进入的电影意象世界是一种境界,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挖掘电影意象背后蕴藏的精神状态,即挖掘电影意象的发生机制——电影审美感兴。
三、电影的审美感兴
审美感兴是一个过程,是心灵与客体间的一种接触。关于“感兴”的含义,学者们曾有过十分详尽的阐释。叶朗教授提出:“‘感兴’是一种感性的直接性(直觉),是人的精神在总体上所起的一种感发、兴发,是人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的升腾洋溢,是人的感性的充实和完满,是人的精神的自由和解放。”[7]160-161感兴的过程是一种状态的转变和持续,绝不停留于对物的一般欣赏,而是进入意象的世界,直观主客交融后整体的“象”。“感兴”是中国古典美学中的概念,笔者将它纳入对电影的讨论中以探求电影的审美心理学的问题。电影的感兴自然是主动参与的一种发抒行为和发抒方式,了解感兴的过程和形态才能深化对审美活动的认识。
电影的审美感兴是一个自发和持续的过程,观众在审美活动中完成从日常态度向审美态度的转换。不妨回想一下,在观照电影时,人们完成了一个“进入”的过程。当人们不再意识到自己在看电影时,审美的感兴便发生了。起初这是一种模糊的状态,但随着主体意识在意象世界中的慢慢淡化,一种深层次的愉悦和刺激产生。克拉考尔眼中的电影是需要依靠审美感兴过程的,他强调通过看电影去看生活本身。这种视觉方式需要观众忽略媒介而产生对电影自身的模糊感。在“进入”的过程中实现对电影的感兴,走进无限的生活流当中,感悟意象世界。
审美感兴存在一个准备状态和阶段,这个阶段引发观众的注意,引导观众走进审美状态。在谈论电影之前,我们不妨看一个中国传统中的例子。“《关雎》兴于鸟,《鹿鸣》兴于兽。”[8]675《诗经》中的诗大多以自然鸟兽花木起头。在中国传统诗歌的创作之中蕴藏着对“感兴”的思想,诗人兴发的创作状态需要自然来引导,颇有触景生情之韵。鸟兽花木属于自然,属于现实。克拉考尔认为电影是对自然现实的再现,那电影便有“起情”的作用。“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诗人的状态、创作的狂热由鸟兽所引,触景以起情。克拉考尔所言的电影成为了自然的载体,甚至就是自然本身。感兴兴于电影画面,电影成为观众审美活动的一个起点。在这种“兴发”的作用之中,观众达到一种迷狂,实现尘世的超越。电影的这种感染力不仅控制了观众的眼睛和耳朵,更控制了观众的内心世界。这不是一场梦,电影带来的真实感甚至超过现实本身。观众在这种迷狂中忘乎自我。这种迷狂效果,绝对是其他艺术形式所不可能拥有的。
电影是一种视觉文化,但是电影给观众带来的感受不只停留于眼中或耳中,而是刻在心中。影像带来的体验在感官之间自由游走,各种感官被打通了,这种现象就是“通感”。通感是审美感兴中的重要因素,在电影中,为了意象的产生,通感的作用不容忽视。克拉考尔看到了电影影像深层的现实内涵,为了达到深层生命精神的感悟,必须实现“感觉挪移”来品读生活中图景的“响亮”和声音的“灿烂”。如观看完《星际穿越》时,笔者想用“振聋发聩”一词来形容观影感受。观看过《星际穿越》的人不会质疑这个形容声音的成语所意欲表达的意思,因为大家都有和笔者同样的体验。因此可以说,在文化的历史进程中,人们形成了某种“通感”。电影是打开通感之门的一把钥匙,为审美感兴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艺术的重要性更在于它把我们带出那种秩序,并把我们置于静观永恒事物的境地。”[9]12叔本华看到了艺术将人从现实世界因果秩序中的剥离。克拉考尔意识到在抽象化思维的影响之下人类意识的分离。电影,起到恢复观众感性思维的作用,促进感兴的发生。康德理论中提出的无功利性(disinterested)意在激发审美思维,这种思维帮助观众脱离功利和效用的囚牢。电影背后的生活本身,在感兴的作用中帮助观众超越有限生命时间和凡世无尽的痛苦,进而静观无限的生活意境。
审美的感兴需要一种诗性智慧。按照维科的观点,诗性思维是每个民族幼年时期都天然拥有的。然而在成长过程中,西方人的诗性思维逐渐被哲学取代,“成了历史的遗物”[10]99。相反,中国人的诗性思维与哲学并驾齐驱,成为互补的精神形式。就电影而言,一种从图像到经验的知觉过程更多依靠这种智慧。对于电影的诗性解读和感悟是受中国传统影响的我们所擅长的,中国的传统美学本身就有一种诗性的韵味。中国人对电影具有更佳的敏感度,意识在画面中自由游走,像克拉考尔说的那样,通过电影看到无限的生活流,在镜头中看到无限生活的感染力。
电影将现实生活本身生动地展现在观众面前,余味悠长。观众在愉悦和感悟背后,无意识地发生了审美活动,走进意象世界。电影带给人们的是看世界的方式,在电影结束后,人们依然可以感受这种意象,一种历史感、人生感和宇宙感便油然而生。在审美活动中,人们完成了感兴的过程而进入了平静和安宁的状态。在这种着色的状态背后,人们进入了一种思考,一种对世界本源的静观。
四、电影的审美心胸
中国的传统美学中形成了关于审美心胸的理论体系,从老子的“涤除玄鉴”到庄子的“心斋”“坐忘”,再到宗炳的“澄怀味象”,关于审美心胸的讨论就是挖掘观众的审美态度。①中国传统美学中关于审美心胸的讨论,参见叶朗的《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审美意象的大门需要审美心胸作钥匙。笔者在上文对审美感兴的论述中提到过一种兴发机制,这种兴发不仅需要电影的激发,也需要主体作好准备,这种准备便是拥有审美心胸。人们将审美心胸理论投射到电影的观照中,可以清楚阐释观众在电影审美活动中的一种主体境界和态度,也为打开电影意象的大门作解释。传统美学在意一种“心境”,在克拉考尔的理论中,人们对于电影的审美需要这种心境。观众观看电影,目的不仅在于理解其本身,更要去追求影片外无穷的生活现实,体会生活的意象。
彭锋先生曾经提到的一个例子十分有趣。在演出《哈姆雷特》的时候,有一位激动的英国老太太从座位上站起来,提醒扮演哈姆雷特的演员,对手的剑上有毒。不难看到,这种观剧方式不能引入审美的意境。究其原因,“艺术和他们的实际人生之间简直没有距离”[11]53。拥有审美心胸才能进入审美活动,这种心胸要求观众自身具有一种境界。观众在观看电影时,必须走进电影内容却又不束缚于情节之中,需要在象与心之间“游”,进入电影的意象世界,进入无限的生活流来实现一种超脱。
审美心胸要求“涤除”和“澄怀”。放下心中对于实用利益的追求,才能达到一种审美的境界。一种适当的状态是必要的,在电影观照中,如果缺乏审美心胸,克拉考尔所言的电影价值将不再存在。重新挖掘“澄怀”和“涤除”的意义就要求人们用“虚空”的精神状态对待电影,清除内心的杂念,抛开利益去欣赏电影。人们只有完成牧牛十图中从“忘牛存人”到“人牛俱忘”的跨越,才能达到最后“返本归源”的境界。这种“开悟”是一种审美的心胸,这种状态之后便可以带着审美的眼光来寻找电影的本源——生活,人们在这种境界下得到的是一种审美愉悦。
审美心胸是需要抛开功利和实用目的的。也许有人会反驳说,审美心胸与克拉考尔对生活流的追求存在矛盾。但在克拉考尔眼中,生活绝对不是一种实用的追求,他认为,电影的本性是生活,是向生活的延展,是对生活的观照。这种活动是审美的,也只有审美心胸才能体悟克拉考尔所言的电影背后的无限生活流。
苏轼曾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自)缘身在此山中。”电影展示了繁杂的物象,而观众很容易陷入这种混乱之中,难以探求背后的“道”。老子对“涤除玄鉴”和庄子对“澄怀观道”的阐释背后体现了一种对人生艺术化观念的思考。对电影的观照需要一种审美的眼光,审美感兴的准备过程决定了观众观看电影的态度。审美心胸可以将主体从实用态度向审美态度引导——走向电影背后的生活流,可以涤除杂念,透彻地感悟影像背后的自然,将电影的价值还原到对于“山水”的欣赏。“观照”是打开电影意象的一把钥匙,使观众和电影作品融为一体。
依照克拉考尔的论述,抽象化使人身体悬空,使双手和物质脱离,割裂了人和自然。人类在繁杂的物质现象中迷失自我,重新建立主客的联系,创造“意象”尤为重要。电影成为这种回归的最好方式。电影的审美活动追求一种境界,这种境界可以说是观众的“故乡”,对于电影而言,现实生活就是它的故乡。张世英先生说:“审美意识是人与世界的交融,用中国哲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天人合一’。”[12]199人们对电影的感兴就是为了回到这种“物我两忘”的状态。
“电影可以说是一种特别擅长于恢复物质现实的原貌的手段。”[1]380电影对现实的近亲性,可以实现物质现实的复原。克拉考尔说的原貌或原始材料是生活的真实样子,是物质在被抽象和分离之前的整体,是人和自然亲密接触的起始状态。对于审美的把握可引申到一切事物的源头。审美经验是人生在世的原初经验,其他的经验依它而生长。因此,只有对审美经验的把握,才能引导人类在现象世界中找寻社会和生活经验的本源,回归到克拉考尔眼中的生活。可以看出,电影所具有的独特魅力在于它未经消化,是“故乡”的引路人,人们观赏电影的过程就是归乡的过程。
人类被隐藏在物质的氛围之中,抱以审美心胸来面对意向性的电影可以看到电影世界背后生活的本来面目。“审美活动可以使我们从日常生活中超越出来……是向一种本然的生存状态的超越。”[13]104对于这种状态的追求,可以使人进入主客体交融的状态,也就是“意象”之中。电影成为回归自然的必要手段,那么抱以审美的胸怀来对待电影,便可以发挥电影的最大价值。
中国的美学理论重视审美活动,追求“意象”的打造。克拉考尔看到了电影作为手段使观众达到从有限到无限的超脱,其电影理论背后蕴藏着无限的意象,打造了一种心与物、电影与生活流交融的意象世界,激发了观众对于电影的审美活动。人们对于电影的审美从审美感兴开始,进入一种审美状态,进而进入意象世界,在这种状态和过程之中感受电影的本体——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