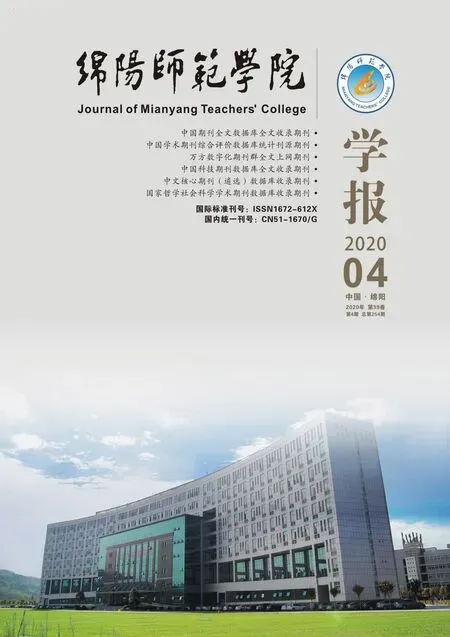自恋、文学、身份
——论菲茨杰拉德的自恋倾向在其四部长篇小说中的再现
王 潇,戚 涛
(安徽大学外语学院,安徽合肥 230601)
一、引言
弗朗西斯·司科特·基·菲茨杰拉德(以下简称菲氏)以深刻、凄婉的笔调真实、生动地再现了美国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诸多社会特征,被称作 “爵士时代”的代言人。他著有《人间天堂》(1920)、《美与孽》(1922)、《了不起的盖茨比》(1925)、《夜色温柔》(1934)、《末代大亨的情缘》(1941,未完成)5部长篇小说,近200篇短篇小说,16部剧本和1部散文集。菲氏高度戏剧化地表现了自己的成功和失败,也具体入微地浓缩了一代人的欢乐与悲哀。他的一生历程诠释了他的作品,他的作品又为他谜一般的生平做出了恰当地注解[1]3-4。贯穿菲氏一生的四部已完成的长篇小说更是具有高度的自传性,凝聚了他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他的人格倾向。
目前我国学界关于菲茨杰拉德的研究成果丰硕,前辈学者从存在主义、美国梦、女性主义、象征主义、人物形象等诸多视角对菲氏的长篇小说进行了研究论述,也有学者用科胡特的心理学理论阐释了菲氏自恋型人格的成因、菲氏的自恋型人格对《了不起的盖茨比》及《夜色温柔》中男主人公人物形象塑造的影响,然而研究的理论与文本的结合较少,更多的是根据菲氏的人生经历对他的小说进行推测,得出的结论多为研究者的主观理解,缺乏客观的理论依据。用卡伦·霍妮的人格理论动态地研究,建构其理想化自我身份则有效弥补了前辈学者的理论缺陷,达到了理论与作者的生平、文学文本的融合。文章用卡伦·霍妮的人格理论,分析菲氏人格中的自恋倾向及防御策略在其四部已完成长篇小说中的再现,揭示其人格中的自恋倾向与其文学创作及身份认同间的关系,以便我们更好地理解作者性格与其文学作品中人物形象、行为和命运之间的联系。
二、卡伦·霍妮的人格理论
卡伦·霍妮作为新精神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有别于弗洛伊德的生物决定论和泛性论,强调家庭环境及社会文化环境对人性格最终形成所起的重要作用,在应对基本焦虑时,正常人可以在多种不同的人格策略中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切换,而神经症人格的人则只能无意识的在一种策略上走入极端[2]2。霍妮将人的人格策略分为自恋型、夸张型、攻击型、超然型、顺从型五类。自恋型人格的成因一是补偿型的,即由于幼儿、少年时期遭受虐待或有心理创伤,个体会压抑自发的自我,失去衡量自身价值的能力,依赖于别人对自己的看法。也会由于悲伤和恐惧而失去爱的能力。内心的激烈冲突引发心理失衡,自恋型人格的个体会在别的方面弥补内心的亏空或年长之后弥补年幼时的心理创伤。成因二是处境优越、存在一定的过人之处。这类人幼时或被溺爱或在赞扬中长大,无法接受打击和正确认识逆境,多逃避真实和现实的自我,在理想的自我中越走越远。自恋型人格分为智慧型与身体型,具有强迫性的神经症需求,一是获得他人赞美的需求,过分夸大自己的形象;想要他人称赞讨好自己,这只是为了幻想中的自己,而并非所具有的或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自己;根据与这个形象相符以及他人对这个形象的称赞来进行自我评估;担心这种称赞不再属于自己。二是追求个人成就的野心,自恋型人格的人,想要凭借自己的行动比别人强;自我评估有赖于变成最优秀的人,还要成为他人眼中最不可缺少的那个人,大家都不讨厌他;即使满怀焦虑还是固执地想要获得更大的成就;害怕不成功。三是想要得到社会认可和名望的需求,害怕没有社会地位;凭借名望的价值对所有东西进行评价。四是对完美、无懈可击的需求。自恋型人格的人固执地追求完美无缺,不敢正视自己身上的缺点,害怕做错事,担心遭到批判或反抗[3]43-44。
这些强迫性的人格需求决定了自恋者具有聪明、分析能力强、富有独创性、足智多谋;勤奋、事业心强;取悦他人;好竞争、野心大;傲慢、武断;理想主义、完美主义;焦虑、自恨、虚无等性格特征。
因为家中前两个姐姐的早夭,菲氏的父母,尤其是其母亲对他百般溺爱,过度的娇惯影响了菲氏性格的健康成长。加之菲氏长相英俊,又有运动、写作、演讲等方面的非凡才华,他从小到大的成长环境使得他人格中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自恋倾向。正如他所做的自我评价:“我拥有英俊的相貌和非凡的才智。所以,我总是能赢得最漂亮的姑娘的芳心。”[4]7菲氏大学时期的女朋友,富家女吉妮芙娜·金回忆菲氏说:“他很自负,自命不凡,却又遮遮掩掩,缩手缩脚。”[1]15在他自己及他人对他的评价中也可以看出他明显的自恋倾向。他人格中的自恋倾向决定着菲氏具有自恋型人格的神经症需求,会无意识地采取相应的防御策略。
而人的性格是人的需求动态适应某一特定社会的特定存在状态的结果,是在人类与环境的互动过程中,发展出来的替代本能的策略系统,是社会因素和生理因素共同作用形成的。人的人格形成之后会决定个体价值观的好恶与取向,成为塑造意识形态的重要力量,而文学话语作为一种审美意识形态,它的建构更是会受到作者人格的调节和影响[5]。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在建构、推销不同的身份。菲氏人格中的自恋倾向在其五部长篇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塑造、人物行为和命运的安排等方面得到了全面的再现,其自恋倾向在调节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之间的巨大差距时,无意识地采取了愤世嫉俗、自我贬斥、幻想与内投射等策略群,暂时抚平作者的内心冲突,为作者赢得声誉与财富,建构“有史以来最伟大小说家之一”的自我身份及“伟大英雄”这一理想化自我形象。
三、菲氏人格中自恋倾向的文本表现
(一)夸大自我形象
人格中具有自恋倾向最外在的表现就是过分夸大自己的形象,包括外表样貌、才智品德等,并根据自己是否与这个形象相符以及他人对这个形象的评判来进行自我评估。小商人家庭的出身以及家庭经济条件平平,都给从小在贵族学校上学的菲氏带来了不小的心理创伤,他在新人学校读书期间因为自己“是一个在富家子弟学校就读的穷孩子”而感到自卑和苦痛,“金钱意识这么早就开始侵蚀他幼小的心灵”[1]8。他曾自我评价道“我不具备强大的对异性的吸引力或无数的金钱,但我拥有英俊的相貌和非凡的才智”[4]7。他纵情参与了“爵士时代”的酒食征逐,但他在追名逐利的同时却能用严峻的道德标准来审视和衡量现实生活[1]3。因此在菲氏的五部长篇小说中,他夸大出身高贵且富有、相貌英俊、才智非凡、道德高尚这些形象,所塑造的主人翁们的这些品质都无一例外地被放大和强化。
在主人公们的出身上,阿莫瑞的父亲史蒂芬·布莱恩虽然碌碌无为,却因继承了早逝亲人的巨额财产变得富有,母亲比阿特丽斯是出身显赫之家的名流,“她从小受到的教育培养出了她日后独特的高雅气质、完美的艺术造诣”[6]6。阿莫瑞正是出身于这样一个父亲富有、母亲富贵的上流家族,“他赖以生存的准则就是一种贵族唯我主义”[6]25。“安东尼对自己的身份和地位感觉良好,半是因为他是亚当·J·派奇的孙子,半是因为他的家世可以跨洋过海一直追溯到参加过十字军东征的骑士。”他的爷爷亚当·派奇“从战场上回来的时候已经是少校了,随即又杀入华尔街……挣下了大约七千五百万美元的家产”[7]4。安东尼·派奇同样出身古老的欧洲贵族,又因为爷爷积累的万贯家财而兼备高贵与富有。尼克·卡罗威“三代以来都是中西部城市家道殷实的头面人物。姓卡罗威的也可算是个世家,传说我们是布克娄奇公爵的后裔”[8]11-12,盖茨比通过贩卖私酒和非法倒卖证券发家致富,拥有了财富的盖茨比仍然要处心积虑地伪造高贵的出身,合法化他的财富来源,他对尼克说“我是中西部一个有钱人家的儿子。我是在美国长大的,可是在牛津接受的教育,因为我家祖祖辈辈都在牛津受教育的。这是个家庭传统……我家里人都死光了,因此我继承了很多钱”[8]61。狄克·戴弗“是像我自己这样的一个男子,出生在一个由中上层资产阶级落入小资产阶级的家庭,但所受到的教育仍然花费不菲”[9]2。
在对主人公外形的塑造上,阿莫瑞“顶着一头赤褐色的头发,长着一双漂亮的大眼睛”[6]7,他是个“英俊帅气的男孩”[6]20。安东尼·派奇“举止优雅,对聪明的男人和所有的女人极具吸引力”,“他那双蓝色的眼睛始终充满了迷人的魅力……他长得英俊潇洒——更重要的是他非常干净,这既是指他的五官样貌,也指他的家世身份,他还有着那种特别的、得自于美的洁净感觉”[7]3-10。盖茨比“的笑容含有永久的善意表情……是一个风度翩翩的年轻汉子,说起话来文质彬彬”且“一表人才”[8]48-67。狄克·戴弗“身形壮实,相貌俊秀”[9]4,“长得非常帅,一头赤发”[10]15,“他有一种讨人喜欢的气质”[10]108。
菲氏反复强调主人公们的天赋和才智。阿莫瑞“拥有完美的人格、迷人的个人魅力,他有着统领所有同龄男子的能力,同时还有博得所有女性青睐的天赋”,“足球场上他勇往直前”,他热衷于文学创作,“为拿骚文学写作……成为《普林斯顿日报》委员会的一员让他受益良多”[6]26-64。盖茨比身上“有一种瑰丽的异彩……异乎寻常的永葆希望的天赋,一种富于浪漫色彩的敏捷,这是我在别人身上从未发现过的,也是我今后不大可能会再发现的”[8]11。盖茨比头脑灵活,聪明能干,自己没有任何家世背景,白手起家赚取了巨额财富,在战争中由于 “英勇过人,被提升为少校,每一个同盟国政府都给我发一枚勋章”[8]62-63。狄克·戴弗“他拥有一切天赋,在耶鲁度过的岁月相当成功”,他“也非常聪慧,博览群书——事实上他才华横溢,有着极其强大的个人魅力……他是具有无限潜力的超人”[9]2-4。狄克的同事弗朗兹认为狄克“绝对是个认真的人,是个才华出众的人。在所有最近在苏黎世取得神经病理学学位的人当中,人们认为狄克最有才华”,作为医学博士,狄克的医学著作《精神病医生的心理学》,“在那一类书里仍是标准作品”[10]304。
菲氏同样强调其小说主人公们的高贵品德。“阿莫瑞是个有着清教徒般良知的人”[6]26。盖茨比是个“好人,人品极好……非常有教养……在女人方面非常规矩。朋友的太太他连看也不看”[8]67-68。狄克“他对人很认真,冷漠时宁愿不露面”[10]108,狄克不仅热忱待人,懂得尊重他人,而且善良正直,他“以为人永远精力充沛,人性本善”[10]146。在拜金主义的“爵士时代”,人们变得越发势利冷漠,眼里只有金钱利益,为了一己私利可以不择手段,高尚的道德良知显得尤为珍贵,菲氏的小说主人公们在纷繁复杂的金钱社会始终保持着善良正直和人性良知。菲氏通过对其所塑造的主人公们形象的强化,加强自我在现实生活中的身份认同。通过世人对这些完美形象的赞许获得内心的归属感。
(二)追求个人成就的雄心
人格中的自恋倾向促使个体总是力争第一、达到最好,他们必然具有追求个人成就的雄心勃勃的性格特征。自恋者通常自视甚高,给自己的定位虚高不下,他们的人生目标不是立足于现实而是立足于想象,目标宏大,野心勃勃。菲氏追求成功的雄心壮志体现在他所塑造的每一个主人公身上。
阿莫瑞想“将来成为伟大的剧作家……成为普林斯顿引以为傲的大人物……我渴望被崇拜”[6]67。安东尼则一直怀揣写一本中世纪历史书的宏图大志,“写那本书的念头在他的脑子里生了根。在其后的岁月里,他开列过几次这方面的权威著作的清单,甚至还尝试着写出了各章节的标题,把他的著作分好了几个时期”[7]16。盖茨比更是自认为“他是上帝的儿子”[8]89,他从小就给自己制定精英计划,他一定要娶像黛西那样出身高贵的女子,虽然出身贫寒却由内而外散发着贵族的气质,他的父亲感叹道“杰米是注定了要出人头地的。他总是订出一些诸如此类的决心……他在这方面一向是了不起的”[8]150。狄克·戴弗为了和妮珂结婚,照顾妮珂而放弃了自己前程似锦的科研事业,但这并不意味着狄克没有追求,相反,他一直“最想成为勇敢而仁慈的人,更要为人所爱”[10]383。得到他人和社会的尊重与爱戴是狄克一生的追求,这也正是仅凭善良和热情难以达到的宏伟目标。
菲氏人格中的自恋倾向使得他具有夸大自我形象和追求个人成就的雄心,这些自恋需求及性格特征在他自传性很强的文学作品主人公身上得到了全方位的再现。
四、菲氏防御策略的文本再现与身份建构
为解决由内心冲突引起的焦虑情绪,不同的人格倾向会选择不同的防御机制,维持内心与外界的平衡。菲氏解决自我内心冲突、维持自恋需求的方法更是多措并举,自成体系,在其四部已完成的长篇小说中主要有愤世嫉俗、自我贬斥、幻想与内投射。
(一)愤世嫉俗
愤世嫉俗是通过否定和嘲讽价值观念来避免冲突,有些人可能是无意识的愤世嫉俗,他们有意识地接受社会的价值观但是却不能发自内心的苟同这些价值观,因此较容易采取愤世嫉俗的策略来发泄。菲氏渴望跻身美国上流社会,他跟自己的妻子一道全情投入于“爵士时代”的纸醉金迷中,想融入上流社会人们的生活,然而出身不高始终是遭人诟病的硬伤,加之菲氏靠写作的收入在1931之后就不是很稳定,经济基础的薄弱,使得菲氏在生前没能实现他的成功之梦。他努力地想要在上流社会找寻身份认同,然而性格中的自恋倾向让他自视甚高,感觉自己孤傲脱俗,他看不上拜金、自私贪婪的中产阶级,发自内心的无法苟同上流社会的价值观,因此他愤世嫉俗地批判他人、批判社会。《人间天堂》和《美与孽》中菲氏间接谴责罗莎琳德和她的妈妈,她们的婚姻观是只讲物质不论真爱。安东尼的悲剧虽然有自身懒惰和酗酒的毛病,但作者更多地谴责世态的炎凉,谴责社会上的人们把友情和爱情建立在金钱的基础上,才造成了安东尼的疯癫。盖茨比生前在他的豪宅里夜夜笙歌,宾朋满座,在他被无辜枪杀后,无论是他昔日全心全意真爱着的恋人黛西,还是生意上密切的合作伙伴迈耶·沃尔夫山姆,没有一个人来参加盖茨比的葬礼,那些曾经喝足了盖茨比酒的宾客们不但不为盖茨比的死表示一点哀悼,还觉得盖茨比死有余辜,害怕和盖茨比沾一点边[8]147。菲氏或委婉地谴责他人的人性泯灭或直接愤世嫉俗道:“是女人毁了我,是酒毁了我,这段婚姻毁了我。”[9]1性格中的自恋倾向使菲氏对周围世界过分期待,总认为别人欠他、别人耽误和毁灭了他,自恋者本人是完美的,错的都是别人,是社会,作者借助愤世嫉俗的防御策略发泄心中的郁结,同时创作出优秀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作品。
(二)自我贬斥
自恋型神经症患者心目中的自我形象或者自我要求是很理想主义的,加之人的欲望是无穷的,他们理想中的自我是不可能存在或实现的,患者又有不懈的追求以达到理想中自我的强迫性需求,这种现实自我与理想中自我的鸿沟让他们产生了延绵不绝的焦虑,《人间天堂》《美与孽》《夜色温柔》中的男主人公们都和现实中的菲氏一样借酒浇愁,用酗酒麻痹自我、排解焦虑。自恋者因为自己的过人之处而自负,又因为自己无法达到理想中的自我而深深地自恨着,同时他们又对外界的评价、别人的看法极度敏感,与其从他人嘴里听到对自己的批评,不如以退为进,主动地自我嘲讽、自我贬斥,而贬斥自己可能是一种有意识的作用,仅仅是实践中的一种权宜之计,被贬斥的能力通常是个人最迫切渴望超越的能力,人们可以通过自我贬斥的焦点来猜测他最大的野心是什么[11]147-149。阿莫瑞觉得“为拿骚文学杂志写作让他一无所获……新的欲望和报复在他的头脑里涌动”[6]64,《美与孽》里的作家迪克·卡拉梅尔的第一步长篇小说《恶魔恋人》一炮打响之后,便很少出佳作,写了很多挣快钱却质量欠佳的短篇小说,菲氏在该小说中以迪克·卡拉梅尔的口吻来调侃自己:“你知道,这些新派小说让我感到厌倦。我的上帝啊!无论我走到哪里,都会有傻乎乎的姑娘跑来问我有没有读过《人间天堂》。难道我们的姑娘们真的会喜欢那样的作品吗?如果这样的小说忠于生活的话,对此我是不相信的,那么下一代人肯定要堕落了。我对所有这些劣等的现实主义感到恶心。”[7]425当《了不起的盖茨比》即将完成付梓前夕,菲氏的妻子姗尔达由于耐不住寂寞,和一位年轻英俊的法国军人尤多亚德·约桑发生婚外恋,这一打击严重干扰了菲氏的文学创作,极大延宕了《夜色温柔》的创作进度,在《夜色温柔》中菲氏塑造了蹩脚作家麦吉斯哥,借麦吉斯哥夫人的口嘲讽道“我丈夫正在完成他的第一部小说,你知道。只不过人家用二十四小时写出来,我丈夫却用了一百年之久”[8]12。主人公狄克·戴弗同样在完成了一部著作之后就一直未能再出版计划要完成的作品。菲氏的这种对写作的自我贬斥并不是真的自谦或自嘲,而是自己做出自谦的姿态,实则渴望他人对自己写作才华的赞美与肯定,而菲氏最常常贬斥的写作则是自恋者最在意、最给予厚望和最大的野心所在。
(三)幻想与内投射
人格中的自恋倾向使个体向往完美的自我,通过幻想、做白日梦逃离现实的自我,在幻想中将矛盾的情感分割成绝对好和完全坏的两部分,只放大好的部分,对好的部分作过高评价。内投射是把客体或客体的一部分包含为主体的自我过程。即客体(主体)吸收外界事物(客体,如他人的性格特质、行为方式等),而将他们内化为自己人格的一部分。菲氏的经济收入在1931年之后开始走下坡路,妻子精神病发作耗费了巨额的医疗开销,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经济危机时期,菲氏的后三部长篇小说没有引起太多社会关注,菲氏生命的后期,他的财富和作家声望都与理想中的自我相去甚远,为了消解现实自我与理想化自我的巨大差距,幻想与内投射是常用的防御策略。《了不起的盖茨比》对完美英雄人物的塑造,较集中体现了菲氏的幻想与内投射这一防御策略。杰伊·盖茨比在冷漠的大环境下保持着热忱、善良,在受过打击与轻视之后仍然保持着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在实用主义、拜金主义的话语霸权下保持着浪漫主义情怀,保持着对已经嫁为人妇的昔日恋人黛西至纯至真的爱恋,甚至在黛西开车失误撞死人之后,盖茨比还为她掩饰,担心黛西并且在黛西的窗下守候了一个晚上。菲氏渴望自己专注于写作事业并有所成就,渴望拥有真心相爱的恋人与和谐幸福的婚姻,渴望自己有身份地位和足够的财富维系体面的生活,相信与他人相比自己是善良正直、顶天立地的人,而不是物质的奴隶、无情的机器等,盖茨比的人设是菲氏幻想的理想的自我形象,菲氏通过将盖茨比身上的伟大投射到自己身上,抹平现实自我与理想化自我的鸿沟,平抚内心的焦虑和冲突,建构“伟大英雄”的身份认同。
五、结语
综上所述,菲茨杰拉德在进行文学话语的创作过程中,极大地受到其自恋型人格的制约与影响。他夸大自我形象、追求个人成就的雄心和渴望他人、社会认可的自恋需求全面影响着他长篇小说人物形象的塑造、人物的行为及他们的悲剧命运,为了满足人格中自恋倾向的需求、维持自恋者的完美形象,菲氏在调节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之间的巨大差距时,无意识地采取了愤世嫉俗、乞求怜悯、投射与内投射等防御策略来缓解焦虑与冲突,同时为作者赢得声誉与财富,建构“有史以来最伟大小说家之一”的自我身份认同,及“伟大英雄”这一理想化的自我形象。菲氏通过这些自传体小说的创作不仅抒发着内心的冲突,也探索生活经历对个人的意义,不断完成对自我身份的现实意义上的建构及理想化自我英雄形象的双重建构。通过对菲氏人格中的自恋倾向与内心冲突对其长篇小说创作巨大影响的探讨,为我们深入理解其小说人物的性格和形象塑造、人物命运等提供了一个人格分析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