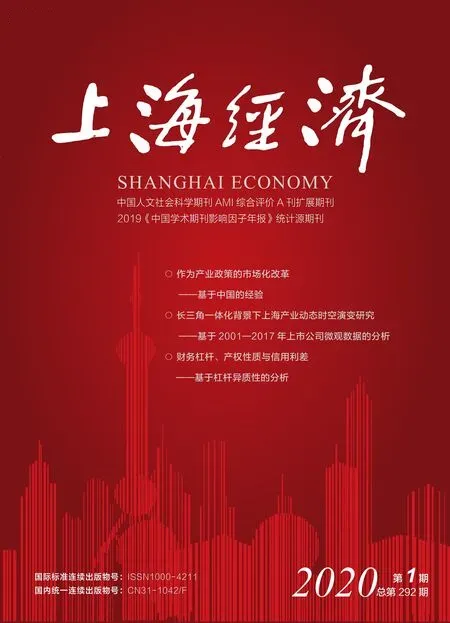企业异质性市场势力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分析
——基于我国制造业企业数据
文春艳
(上海社会科学院应用经济研究所,上海,200020)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经济转轨过程中,在市场体制机制很不健全的情况下,经济呈现井喷式高速发展,制造业体量和规模不断扩大。根据宏观经济增长理论,众多学者从劳动、物质资本以及技术水平变化的角度解读经济增长和效率变革的源泉。然而,除了要素投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市场竞争的引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Homels et al.,2010)。简泽(2011)从市场竞争机制视角,指出转轨时期我国制造业各行业逐渐呈现出可竞争性特征,市场竞争机制的引入,改善了企业之间的资源配置效率,提高了在位企业创新研发激励,促进了企业和总量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我国将长期处于经济体制渐近转轨的过程中,秉持开放和塑造“竞争中性”的市场环境是我国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基本要义。因此,明确市场竞争机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微观影响机制是什么?对不同类型的企业影响是否存在差异?有助于从不同的视角对高质量发展阶段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机制给出解释。
市场势力(markup=P/MC,即产品的价格加成率)是衡量市场竞争程度的主要指标之一,在产业组织文献中,市场势力反映的是企业在产品市场的定价权或竞争地位。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企业垄断形成的原因既可能源于政府通过行政命令给予企业特殊的保护,也可能源于企业通过提升技术水平、产品质量等方式获得的相对竞争力。随着经济改制进程,后者在市场资源流动和企业优胜劣汰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林梨奎,2019)。在同一个市场行业中,两个具有相同市场势力水平的企业之间不会造成资源的再流动效应,企业之间的相对势力差异才是导致市场竞争地位差异以及资源流动倾向的原因。在产品市场拥有市场势力的企业是否能够促进自身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同行业不同企业之间的绝对市场势力和相对市场势力对企业的竞争促进效应是否存在差异?仍然需要进一步从微观数据入手,分析企业市场势力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微观作用机制。
制造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本文依托于市场势力指标,从产品市场竞争视角分析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微观机制,以期对现有全要素生产率的相关研究理论给予一定的补充。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包括两个方面:首先从经济性市场势力视角分析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微观机制,对现有市场竞争机制和全要素生产率变动机制的研究做出一定补充;其次,本文对企业市场势力和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进行剥离,分析市场势力的同质性部分和异质性部分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差异,为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一定的实证支撑。
二、相关理论文献
(一)竞争机制和全要素生产率理论分析
已有研究关于竞争对市场效率的争论呈现出支持竞争和限制竞争两种观点。认为竞争能够促进市场效率提高的学者认为,竞争能够激励企业经理人提高企业效益、促进改革开放、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等。例如,Tybout(2000)指出长期受到国家保护缺乏竞争的制造业,容易造成生产率分化程度高、垄断企业利用市场势力获取暴利以及由于小企业的发展受到抑制无法形成规模效应等结果。Sekkat et al.(2009)以埃及、约旦和墨西哥为样本,发现这些发展中国家的低生产率主要是由于缺乏竞争造成的,且国有企业的存在阻碍了竞争性市场的形成。Boitani.et al(2013)通过分析欧洲交通领域的77家企业,发现私有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和公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依次递减,而通过良好的竞争选择机制能有效地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Holmes et al.(2010)通过梳理竞争和生产率研究的文献,指出竞争对生产率作用的微观机制在于促进了企业投资的增加。高生产率企业的进入,会通过竞争促进效应提高整体行业生产率的水平。Matsa(2011)研究美国零售业行业时,发现高生产率的沃尔玛的进入,极大地促进了零售超市之间的竞争,使得大型连锁超市减少了高达三分之一的亏空。
而认为竞争抑制市场效率提升的文献指出市场竞争的增加会降低企业的投资回报率和收益率,从而降低企业创新投资的动力,抑制生产率的提高。Aghion et al.(2001)认为创新作为内生性结果,为了促进企业进行创新投资,需要限制市场竞争。Singh(2003)指出在较为完备的市场经济中,竞争通过促进投资会促进生产率的提高,但是发展中国家为了提高国民生活水平,需要较高的投资回报率,高投资回报率和激烈的产品市场竞争理念是相悖的。Masahito(2013)对日本经济进行研究时,发现竞争主要促进了制造行业生产率的提高,而对服务业的促进作用有限。Amri et al.(2013)以突尼斯制造业为例,发现以低竞争水平为基准,竞争程度的增加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加,而以高竞争水平为基准时竞争程度的再提高对生产率产生了抑制作用。
(二)产品市场竞争和全要素生产率
传统理论认为,垄断厂商会以降低产量、提高价格的形式获取超额垄断利润,此时市场势力和市场竞争是负相关关系。例如,加拿大经济学家海默(Hymer)提出的垄断优势理论,大型跨国公司凭借其垄断优势,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跨国公司凭借其在产品市场、要素市场、规模经济、货币等方面的垄断优势影响市场竞争行为,获取高额垄断利润。拥有市场势力的企业还可能会提高市场进入门槛或产品门槛,减少市场中参与竞争的企业绝对数量(Campbell&Hopenhayn,2005)。同时,从动机看,竞争性企业和垄断性企业之间存在“替代效应”(Arrow,1962),即在竞争性市场中的企业相比垄断企业更具备进行技术进步、降低成本的动机。竞争性企业希望通过创新达到垄断者的地位,从而获得垄断利润。而垄断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之后,在市场中的地位仍然保持不变,因此技术创新激励不足。
张维迎(2018)指出完全竞争市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只有水平效应,没有增长效应,竞争均衡理论所谓造成市场失灵的市场势力恰恰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在转轨经济中,政府干预性政策和市场主导性规则对市场环境中的资源流动是逆向作用的,过程中不仅存在着传统的行政性垄断问题,还出现了经济性垄断特征,前者是政策强制性干预的结果,导致资源逆市场趋势流动,而后者则是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力提升的结果,反映市场优胜劣汰的动态变化(林梨奎,2019)。尽管垄断厂商会扭曲市场要素配置效率,但异质性市场势力代表的企业产品差异能够促进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Epifani et al.,2011)。从社会效应上,垄断势力对市场良性发展起阻碍作用,而市场势力在市场经济中长期存在,并且能促进市场有效竞争的形成(杨晓玲,2005)。其中,经济性市场势力能够反映企业在市场中的比较竞争优势,Peters(2013)通过构建产品质量阶梯模型,发现企业市场势力能够用于衡量领导者相对于追随者的生产率优势。
企业市场势力水平与其创新研发决策进而与企业全要生产率密切相关(郁培丽等,2013),其中,拥有市场势力的企业能够凭借高质量产品定价获得高利润,而研发创新是投入资金量大、投入周期长的过程,因此市场势力是决定企业是否有能力进行研发创新的直接因素。从间接影响看,企业市场势力通过影响市场竞争环境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在竞争性市场运营的企业效率没有在市场更集中的企业效率高,即拥有垄断势力是企业进行技术进步和创新的基础(Schumpeter,1942)。市场势力反映了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地位,会促使企业进行创新研发提高产品质量(以便定制高价)或者提高技术水平降低边际生产成本,即市场势力促进了市场创新竞争效应(Aghion et al.,2005;简泽,2011等)。Aghion et al.(2005)从理论上证实了创新和市场竞争之间呈现倒“U”形关系,即指出创新同时存在逃离竞争效应和熊彼特创新效应,前者指行业中状态相似的企业通过技术创新逃避和对手之间的直接竞争,后者则指竞争抑制了不同水平的企业创新,因为存在创新的租金消散作用。一方面,竞争促使资源流向高效率企业,使得低效率企业退出并且新进入企业的生产率进入门槛不断提高,另一方面竞争通过促使企业增加提高生产率的成本投入,防止被淘汰出市场(Syverson,2011)。简泽等(2017)的研究也证实在经济转轨过程中,我国制造业同时存在竞争创造性和竞争的破坏性特征。王贵东(2017)对我国制造业垄断势力进行分析时将市场势力和全要素生产率正相关的企业识别为创新型垄断企业,将市场势力和全要素生产率负相关的企业识别为寻租型垄断企业,通过分析发现我国制造业企业主要呈现创新性垄断,所谓的生产率悖论现象并不显著。
小结评述:通过梳理文献,目前多数文献从竞争影响资源配置效率、影响R&D投入水平等间接方面进行研究,较少对市场竞争关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影响机制进行分析。指标度量方面,在经济转轨阶段,市场中不仅有行政干预导致的企业垄断势力,还有随市场化进程催生的经济性市场势力,已有研究主要从行政干预导致的企业垄断势力视角分析垄断造成的市场失灵,较少对经济性市场势力的竞争促进效应进行研究。此外,在一般均衡框架下,市场势力往往取决于相对价格水平而非绝对价格水平(Lerner,1934),这也暗含着市场中资源的流动取决于之间的相对水平而非个体的绝对水平。现有研究主要以市场势力的绝对水平为度量衡,忽略了相对水平的重要影响。
因此,本文在异质性垄断竞争框架下,着重研究我国制造业企业市场势力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微观影响机制。首先,基于De Loecker& Warzynski(2012)异质性市场势力测度框架和Ackerberg et al.(2015)微观生产函数的半参数估计方法,对企业市场势力和全要素生产率分别进行测度。其次,通过构建一阶差分模型,分析市场势力和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作用机制。随后,考虑现实市场经济中相对竞争水平是导致市场中资源流动的基本因素,因而,进一步对企业市场势力和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同质性和异质性解构,分析市场势力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深层次原因。根据上述基本研究思路,下文首先对基础理论模型进行设定,在模型设定的基础上采用工业企业数据库1998—2007年制造业企业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明晰转轨时期市场势力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微观作用机制。
三、模型设定和数据整理
(一)理论模型设定
市场势力、市场集中度等指标都是产业组织经济学中衡量市场竞争程度的常用指标,但是在动态市场环境中,一方面市场集中度的变化会滞后于经济发展的变化,即敏感度较低;另一方面市场集中度指标只能反映由于企业数量增加导致的古诺数量竞争,而不能反映企业数量减少和激烈竞争并存情况下的伯川德价格竞争(Arai,2005),而以价格加成率(markup=P/MC)衡量的市场势力水平取决于价格和边际成本两个方面,能够综合反映企业在市场需求优势和成本优势的权衡(李世刚等,2016)。本文基于De Loecker& Warzynski(2012)异质性市场势力测算框架和微观生产函数的ACF半参数估计方法(Ackerberg et al.,2015)分别对市场势力和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度,并分析市场势力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同时,本文进一步对核心变量进行分解,分析市场势力的同质性部分和异质性部分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差异。
1.企业异质性市场势力估计方法
设企业i在时期t的生产函数为


对成本最小化函数关于可变要素求一阶导数


2.核心变量的同质性和异质性解构
将企业市场势力和全要素生产率进行重新解构,即对任意行业中企业有

3.企业市场势力和全要素生产率回归模型设定
首先,考虑生产率的滞后性以及变量之间可能的内生性问题,基准回归模型设定如下:

下面基于对核心变量的分解,拓展模型设定如下:

(二) 数据整理
本文采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1998—2007年的样本,参照Brandt et al.(2012)、聂辉华等(2012),对主要投入产出变量进行整理。此外,本文主要致力于市场竞争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剔除烟草制造业(行业代码16)和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企业样本(行业代码42),共得27个两位数行业样本。
本文用到的主要变量如下:
工业增加值(VA):由于2004年增加值数据缺失,借鉴刘小玄、李双杰(2008)的处理方式,即工业增加值 =产品销售额-期初存货+期末存货-工业中间投入 +增值税,对2004年企业增加值进行估算。采用1998年为基期的各行业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进行平减。
劳动投入(L):采用年末从业人口衡量。
资本存量(K):根据会计统计规则,固定资产年平均余额是企业层面报告的已经考虑过折旧的资本存量数据,且考虑到较多样本存在折旧率数据缺失,因此本文采用固定资产年平均余额作为企业资本存量。由于固定资产平减价格指数没有分行业的数据,因此按照年度固定资产平减指数对资本存量进行平减,基期调整为1998年。
中间投入(M):根据企业报告的中间投入数据,采用制造业分行业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进行平减,基期调整为1998年。
企业所有权性质(ownership):借鉴聂辉华等(2012),按照国有资本、外资资本和私营资本在企业实收资本的比例,将企业划分为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
企业年龄(age):根据企业开业年份数据(st)和样本企业出现的年度(year),则age=year-st。
资产负债率(leveldebt):等于总负债/总资产,用于反映企业经营状态。
企业工资绩效(wage):采用本年应付工资总额衡量。
资本密度(percapital):人均资本,即K/L,用于反映企业要素密集度。
企业规模(hhi):基于增加值计算的市场集中指标衡量企业相对规模,计算公式为
四、实证分析
(一)企业异质性市场势力测度结果
根据De Loecker &Warzynski(2012),在成本最小化目标下,企业市场势力与生产函数中可变要素的弹性和要素支出份额有关,即要素弹性份额的估计目前文献中较常采用的是OPLPACF等方法,由于ACF方法既能够解决OP方法对投资数据的依赖问题,还能缓解LP方法忽略的变量联立性问题,因此本文采用ACF方法对要素弹性及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估计,采用中间投入要素作为控制函数。针对要素支出份额,借鉴白重恩(2008)计算要素支出成本的方法,即劳动支出份额=劳动支出成本/(劳动支出成本+资本支出成本)。
表1列示了我国制造业企业市场势力的分布情况。首先从全样本看,1998—2007年,我国制造业企业市场势力总体呈现上升趋势,表明企业定价空间较为充足。从不同所有制企业市场势力数量分布统计结果(即markup>1的企业占比),外资企业中高市场势力企业数量占比最高(40.13%),其次是民营企业(37.71%),国有企业数量占比最低(22.07%),即市场势力高的企业更集中分布在外资和民营企业。
从三类企业市场势力的平均数值分布特征看,2000年之前,民营企业的市场势力均值高于外资企业和国有企业,2000年及以后,外资企业的平均市场势力水平更高。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由于面临的体制机制障碍不同,在市场中的表现也存在差异。针对外资企业进入对东道国企业的影响,Edmond et al.(2015)指出如果同一行业的跨国企业生产率不存在明显差异,则贸易开放促使国内外生产者之间直接进行竞争。然而,如果同一行业的跨国生产率存在明显差距,则贸易开放的促进竞争效应是负向的,会使得生产率占优势的一方生产者市场份额不断扩张,市场势力分化加剧。从国有企业的市场势力分布看,可以认为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主要是由于行政干预造成的,而不是基于企业产品质量或生产成本的优势。此外,从不同所有制企业市场势力的离散程度结果看,国有企业尽管市场势力均值较低,但是离散程度最大,这也从侧面表明国有企业内部良莠不齐。

表1 企业市场势力分布(均值)及离散程度
(二)异质性市场势力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分析
1.按规模分类的市场势力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为了控制企业规模效应的影响,按照增加值将企业划分为五个等级(scale=1,2,3,4,5),数值越大表明企业规模越大。按照式(7)进行回归,结果见表2。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全样本和不同企业规模市场势力关于企业生产率的影响都为正。经典产业组织理论指出企业在竞争市场环境下的创新激励大于处于垄断市场环境下的创新激励,即市场势力和全要素生产率应该是负向关系。然而,根据熊彼特“破坏式创新”理论,拥有市场势力是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基础。经济性市场势力反映的是企业在产品市场的价格加成率,企业通过对质量高的产品收取高价,同时将获得的利润投入创新研发,形成良性循环机制。从企业规模分类看,市场势力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呈现两头大中间小的特征,即大规模企业和最小规模企业市场势力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效应更高,可以解释为企业规模越大,越能够通过规模效应实现技术创新、降低成本,而最小规模企业要想融入市场,必须通过干中学和技术外溢效应进行模型创新、改进创新,即小型企业的创新激励高于中等规模的企业。
从控制变量看,主要变量都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有显著影响。企业的规模异质性能够有效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反映出同行业规模越大的企业越有能力进行资源整合,优化资源的配置方式。企业资本负债率系数为正,可以解释为相比传统物质投入要素,研发创新所需的投入成本更大、周期更长,因此大多数企业是通过向金融机构融资进行生产和研发,能够有效利用资本杠杆的企业能够维持企业长远发展。企业资本密度系数为负,表明样本期间粗放式的劳动资本投入无法有效转化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企业规模较小时,年限对全要素生产率无显著影响,随着企业规模的增大,经营年限越长的企业能够凭借以往的经验和干中学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工资绩效系数为正,工资绩效越高表明企业的人力资本结构水平越高,优质的人力资本投入是进行研发创新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基本要素。

表2 按企业规模划分异质性市场势力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2.按企业所有制分类的市场势力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分析
不同所有制企业面临的市场和行政约束不同,导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轨迹有所差异。下面按照企业所有制对样本进行回归,结果见表3。从回归结果看,首先,不同所有制企业异质性市场势力关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都显著为正。其次,从不同所有制样本企业看,外资企业市场势力对生产率的促进效应最高(0.186),略高于民营企业,而市场势力对国有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最小(0.108)。外资企业产品的技术水平和管理经验相较于本土企业都具备比较优势,根据Melitz(2003)异质性企业选择效应理论,生产率水平高的企业倾向于出口,为了降低边际成本,出口企业会定制更高的产品定价。外资企业进入我国市场,会对高质量产品收取更高定价,同时为了保持绝对的竞争优势,外资企业的创新激励更强,以避免本土企业的竞争追赶效应。国有企业长期受到政府的偏向政策扶持,且国有企业所得收益主要以税收形式上缴给政府,创新研发投入激励较低。此外,行政干预导致创新资源的配置扭曲,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变化影响相对较低。

表3 按企业所有制划分的异质性市场势力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三)市场势力的同质性和异质性部分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分析
1.市场势力分解项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分析
根据上述结果,垄断竞争市场中,只有异质性的市场势力能够有效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同质性的市场势力则无益于生产率的增长。结合我国制造业发展的实际情况,样本期间是制造业高速增长阶段,市场开放程度的不断增强和企业进入率高于退出率的事实都表示市场竞争程度越来越强。不论是市场环境变化导致的高生产率企业竞争逃离效应还是生产率水平相当企业之间的“熊彼特式”的创新过程,企业会致力于获取区别于同行业企业的同质性市场势力,以获得市场竞争优势。

表4 企业市场势力和全要素生产率分析
2.按市场势力分组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分析
为了控制企业拥有市场势力本身对模型可能的内生性,按照市场势力水平对企业进行重新分组。根据企业数量统计结果,有34.49%的企业市场势力大于1,即在产品市场具有绝对市场势力;62.39%的企业市场势力介于[0,1]之间,表明我国制造业在高速发展阶段可能存在大量低价低质竞争的情况;还有3.13%的企业市场势力小于0,可能源于长期亏损企业(如僵尸企业)或者是新进企业前期投入周期较长,短期未实现产品盈利。
下面分别按照市场势力大于1和市场势力小于1对企业进行样本划分,验证市场势力的同质性和异质性部分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同质性和异质性部分的影响,结果见表5。从分样本模型回归结果看,市场势力大于1的样本集合回归结果和表4结果基本一致,即主要是市场势力的异质项部分而非同质项部分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而市场势力小于1为样本和前述模型结论一致,差异主要体现在表格第六列上,即市场势力小于1的样本中,市场势力均值和市场势力异质项对生产率平均项均是负向关系,表明企业不具备市场势力时,市场势力水平抑制企业水平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表5 市场势力分组时企业市场势力和生产率的相对关系
3.按企业所有制分组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分析
下面按照企业所有制对企业进行分组回归,结果见下表6-表8(为了方便直接比较分析,下表未直接列出个体控制变量结果)。
首先,从三个表格的第二列结果看,市场势力的同质性部分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显著为负,异质性部分则显著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针对市场势力的同质性部分,私营企业平均市场势力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向作用最显著,对外资企业作用相对最小。而针对异质性部分的系数大小,外资企业异质性市场势力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程度高于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表明外资企业在产品市场更具备产品竞争力,且获得市场势力的外资企业能够促进自身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被解释变量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异质性部分时,系数分布情况和第二列结果保持一致,并且可以看出,市场势力的同质化部分不利于企业异质性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最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关于同质性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回归结果一致,但是与第二列和第四列结果相反,表明市场势力的同质性部分是促进共同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因素,而异质性生产率对同质性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很小。与此相反,对于外资企业,平均市场势力和异质性市场势力都与企业同质全要素生产率负相关,从侧面表明全要素生产率的异质性部分是促进外资企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部分。相较于市场共同技术水平,外资企业在前沿技术和高附加值产品方面更具竞争优势。

表6 国有企业市场势力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回归结果

表7 外资企业市场势力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回归结果

表8 民营企业市场势力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回归结果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从市场竞争机制视角,分析了企业市场势力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微观机制,根据上述结果,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模型回归结果表明,企业市场势力和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表明企业在产品市场上拥有市场势力能够显著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这符合熊彼特式创新的理论基础,即拥有市场势力是企业进行创新进而提升技术和生产率的基础。其次,市场势力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程度按企业规模划分具有“两头大中间小”的特征,即小规模和大规模企业市场势力的竞争促进效应强于中等规模企业。大规模企业资源获取能力和技术转化能力都较强,为了保持行业领先地位,会不断通过创新投入维持市场竞争地位。小规模企业需要突破市场份额封锁,提升市场竞争力,需要进行差异化产品和技术创新,竞争激励效应较强。中等规模企业即面临大企业的技术门槛,又面临小企业的追赶,易陷入中等规模陷阱。此外,从企业所有制视角,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市场势力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强于国有企业。相对于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受到政府的关注和行政干预更强,导致广泛存在市场化竞争不足的现象,同时由于兼顾社会福利目标,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低效企业往往选择低价竞争策略,不利于市场价格机制发挥资源导向性作用。最后,通过进一步对市场势力和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同质性和异质性解构,本文发现市场势力的异质性部分是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主要因素,而市场势力的同质性部分则不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异质性部分反映的是企业相对于其他企业的差异性和独特性,在垄断竞争市场中,只有进行差异化创新和经营的企业才能够提高生产率,提高在市场中的竞争地位。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本文给出以下建议:(1)政策法规方面,反垄断法对企业进行管制时,需要对行政干预导致的企业垄断势力和市场化条件下企业通过提高产品质量和技术水平获得的市场势力进行区分,后者能通过市场竞争机制促进经济整体效率的增长,因此需要避免“一刀切”的管制方法;(2)国有企业改制改革仍然是我国现阶段经济工作的重点,适当引入竞争机制,特别是对商业类国有企业更多的通过市场竞争实现优胜劣汰,对深化国有企业要素配置、市场化运作和管理的体制改革有积极的引导作用,有助于形成有效的约束激励机制,激发企业生产创新活力;(3)由于我国区域经济复杂,地方保护主义或行业行政壁垒仍然存在,应加快构建“竞争中性”的市场体制机制,让不同所有制企业公平公正竞争,更多的让市场机制解决市场问题,防止政府和市场相互作用导致资源逆向流动;(4)市场势力作为反映企业定价空间的指标,异质性势力反映了企业在技术和产品质量上的差异或者创新能力的差异,是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关键,应鼓励和支持企业在市场需求引导下,营造市场创新激励机制,鼓励和支持企业特别是中小型企业进行差异化创新竞争和产品质量竞争,防止对企业进行过度补贴和倾斜性政策指导,避免企业陷入同质化低效竞争困境。通过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构建“竞争中性”市场竞争机制,能够为我国制造业从中国制造向高质量发展奠定良好的制度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