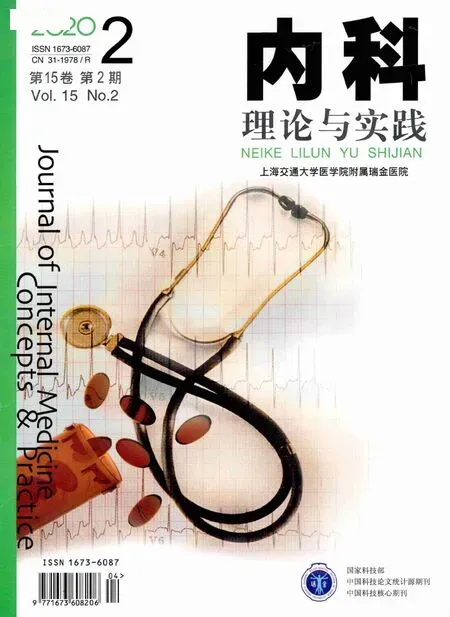生物制剂和小分子药物治疗炎症性肠病的研究进展
孙培君, 谢梦凡, 王 蕾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消化内科,上海 200025)
炎症性肠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IBD)是一种慢性、进展性肠道非特异炎症,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包括克罗恩病(Crohn’s disease, CD)和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 UC)[1]。 传统治疗药物包括氨基水杨酸类、免疫抑制剂类及肾上腺糖皮质激素类等,但由于服药时间久、不良反应多、对于重症IBD 疗效不佳,患者依从性较差。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IBD 不断认识, 其治疗策略逐渐从控制症状过渡到达标治疗[2],传统药物愈显不足。 另一方面,随着免疫学的发展,抗体类药物的出现极大弥补了传统药物的不足[3],自首个抗肿瘤坏死因子 (tumor necrosis factor, TNF) 单抗类药物——英夫利昔单抗(infliximab, IFX)上市以来,IBD 的临床缓解率得到了极大提升,IFX 也在临床广泛使用, 其他靶向TNFα 的抗体也逐渐在临床使用, 包括阿达木单抗(adalimumab)、培 化 舍 单 抗(certolizumab pegol)以 及 戈 利 木 单 抗(golimumab),但问题随之出现:约1/3 的患者会出现初次使用无应答,以及每年约20%的患者IFX 继发治疗失效[4-5]。因此, 研发靶向其他炎症因子或炎症相关信号通路的药物至关重要。
虽然IBD 的发病机制不明, 但多种异常的下游细胞因子已被检测到,并被证明与疾病的严重程度密切相关。 除了TNFα 异常升高之外,白介素(interleukin, IL)12、IL-23、白细胞黏附因子表达升高也常见于疾病活动期[6]。 阻断以上细胞因子可有效阻止下游炎症反应以及白细胞趋化运动导致的肠黏膜损伤。 针对这些靶因子的药物可有效控制症状,延缓病程。 本文就近年来新型生物制剂在IBD 中的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抗细胞因子抗体
辅助T(T-helper, Th)细胞在不同的细胞因子作用下可向Th1、Th2 和Th17 细胞亚群分化。 其中Th1 细胞被认为与CD 病情较为相关。 IL-12 作为促进Th1 免疫应答的重要细胞因子,由p40 和p35 亚基组成。 在临床中也发现,CD 患者在肠固有层中IL-12 表达增加[7]。
除IL-12 外,在结肠炎动物模型中的研究发现,炎症的发生、发展与IL-23 更为相关[8]。 IL-23 是由p40 和p19 亚基组成的异二聚体细胞因子, 与促进IL-17 和干扰素(interferen,IFN)-γ 释放有关。对IL-23 的研究提示,IL-12 在IL-23 不表达的情况下能引起肠道炎症, 而在IL-23 表达的情况下,IL-12 能促进肠道炎症。 这些现象说明肠道中免疫调节相互作用可能促进肠道炎症的发生、发展,并提示IL-12 和IL-23在控制慢性肠道炎症中具有多重作用。 因此,开发靶向p40亚基的中和性抗体可同时阻断IL-12 及IL-23, 有望控制肠道炎症[7]。
IL-17A 被认为是IL-23 的下游调节细胞因子,积极参与调节肠道炎症反应。 活动性CD 患者肠固有层中同时表达IL-17A 和IL-23 的细胞增加, 提示IL-23/IL-17A 途径对于IBD 发病具有重要调节作用。在银屑病及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治疗中,IL-17A 的中和性抗体可有效缓解病情, 而在一项CD 的2 期临床试验中, 抗IL-17A 抗体治疗无明显疗效,并且与安慰剂组相对比, 抗IL-17A 抗体治疗组的不良事件发生率更高,并且直接导致试验中断[10]。 这提示了抗IL-17A 抗体对于IBD 的治疗作用需要进一步研究。
一、乌司奴单抗(ustekinumab)
2016 年11 月, 乌司奴单抗被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 批准 可用于CD 的治疗,是首个针对IL-12 和IL-23 细胞因子的IgG1 型单克隆抗体, 通过阻断IL-12 和IL-23 的p40 亚基来阻止其介导的免疫反应以及下游炎症因子激活[11]。 在治疗中、重度CD 的2 期及3 期临床试验中, 乌司奴单抗治疗组较安慰剂组疗效更好。 在一项用于评估乌司奴单抗诱导疗法在中度至严重活动性的TNF 拮抗剂不耐受或治疗失败的CD 患者中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的3 期、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多中心临床试验(a phase 3, randomized, double-blind, placebo-controlled,parallel-group, multicenter study to evaluate the safety and efficacy of ustekinumab induction therapy in subjects with moderately to severely active Crohn’s disease who have failed or are intolerant to TNF antagonist therapy,UNITI-1)和UNITI-2中,患者被随机分配接受单次静脉输注乌司奴单抗130 mg或6 mg/kg 体重和安慰剂治疗。 诱导治疗有效的患者进入维持治疗试验(IM-UNITI),即每8 或12 周皮下注射90 mg 药物或安慰剂治疗。 观测终点是临床缓解,治疗组的缓解率为34%~58%,安慰剂组缓解率为20%~30%,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在第44 周维持缓解的患者中,治疗组占的比例显著高于安慰剂组,并且C 反应蛋白(C-reactive protein, CRP)和粪钙防卫蛋白(fecal calprotectin, FC)降低水平显著高于安慰剂组,乌司奴单抗的用药安全性尚可接受[12-13]。
乌司奴单抗是抗TNFα 抗体治疗无效或者具有禁忌证CD 患者的一种新选择。 但对于已经有并发症、术后的难治性CD 患者,尚需要更多的临床数据及随访资料来判别乌司奴单抗能否作为一线治疗用药。
在一项用于评估乌司奴单抗诱导和维持疗法用于中至重度活动性UC 患者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的3 期、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 平行组、 多中心研究 (a phase 3, randomized,double-blind, placebo-controlled, parallel-group, multicenter protocol to evaluate the safety and efficacy of ustekinumab induction and maintenance therapy in subjects with moderately to severely active ulcerative colitis,UNIFI)中,也给予患者单次静脉输注乌司奴单抗130 mg 或6 mg/kg 体重和安慰剂治疗。 8 周后, 15.6%、15.5%和5.3%的患者处于临床缓解期。接受乌司奴单抗的患者中也观察到FC 显著降低[40]。
二、Risankizumab
Risankizumab 是靶向IL-23 亚基p19 的人源性单克隆抗体。 与靶向p40 的单克隆抗体相比,risankizumab 并不影响IL-12 参与的免疫反应。 而由于IL-12 被认为是参与肿瘤免疫的重要细胞因子[14],risankizumab 并不会影响患者的肿瘤免疫。最近一项多中心、2 期临床研究共纳入121 例中、重度难治性CD 患者, 分配到3 组中进行疗效比较 (安慰剂组、risankizumab 200 mg 组和risankizumab 600 mg 组), 治疗终点为临床缓解。 结果显示,在第12 周,600 mg 组、200 mg 组和安慰剂组达到治疗终点的比例分别为37%、24%和15%。此外3 组临床应答率分别为42%、37%和21%,缓解率和抗TNFα 抗体获得的益处相当。 高剂量组的内镜缓解率(20%、15%、3%)及内镜深度缓解率(12%、2%、0)亦高于低剂量组和安慰剂组,IBD 问卷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questionnaire, IBDQ) 的改善也更见于高剂量组。 在本项研究中,risankizumab 的用药安全性尚可接受,大多数不良反应与疾病恶化相关,且患者耐受性良好[15]。
Risankizumab 用于UC 的2 期和3 期临床评估正在几个国家进行,其结果可为治疗收益及安全性提供更多资料。
三、Brazikumab(Medi 2070)
Brazikumab 是一种人源性IgG2 型单克隆抗体, 通过选择性结合p19 亚基靶向阻断IL-23。 最近的一项前瞻性研究旨在评估这种新药在治疗活动性CD 患者中的有效性及安全性[16],共有121 例CD 患者纳入随机分组,据既往是否使用过抗TNFα 药物进行分层,分别在第0 周和第4 周进行静脉注射brazikumab 700 mg 或安慰剂治疗。用药后第8 周,治疗组和安慰剂组的临床应答率分别为49.2%和26.7%,临床缓解率分别为27.1%和15.0%。 另外,分别有42.4%的治疗组患者和10.0%的安慰剂组患者的CRP 和FC 水平较基线水平下降50%或以上。 在药物的安全性及耐受性方面,brazikumab 治疗的患者未出现严重的并发症,头痛和鼻咽炎是最常见的不良事件[16]。
一项针对UC 患者的Ⅱ期试验正在进行中, 试验中brazikumab 将与维多组单抗(vedolizumab)进行比较。
四、Mirikizumab
Mirikizumab 也是针对IL-23 的p19 亚基的单克隆抗体。最近一项针对中至重度UC 患者的Ⅱ期随机、对照试验证实了mirikizumab 在该群患者诱导治疗中的疗效[41]。 患者被随机分为接受安慰剂或mirikizumab 50、200 和600 mg 组。 接受安慰剂治疗的患者中4.8%达到临床缓解, 而mirikizumab 50、200 和600 mg 组的患者临床缓解率分别为15.9%、22.6%和11.5%。 所有治疗组的不良事件发生率相似。 针对CD 患者的Ⅱ期试验正在进行, 并且已开始针对UC 的Ⅲ期计划。
抗白细胞迁移、黏附类药物
整合素是一类介导细胞外介质和细胞之间相互连接的跨膜受体,在炎症性疾病中扮有重要角色。 白细胞迁移到炎症肠组织中是IBD 发病机制中必不可少的一环[17]。促炎细胞因子,包括TNFα 和IL-1,能激活白细胞膜表面整合素,并且能上调细胞内黏附分子-1 (intercellular adhesion molecule-1,ICAM-1)、黏膜地址素细胞黏附分子(mucosal addressin cell adhesion molecule,MAdCAM)以及E-选择素的表达,导致炎症组织的血管内皮对于表达α4 整合素的白细胞具有更高的黏附性,一方面加强免疫防御反应,另一方面也扩大组织破坏。 因此,阻断整合素介导的下游炎症反应可减轻肠道炎症负荷,是治疗的重要靶点。
需要说明的是, 抗整合素抗体可引起严重的脑部病变。那他组单抗(natalizumab)是靶向整合素α4 亚基的中和性抗体, 可同时阻断中枢神经系统和肠淋巴系统的α4β1 和α4β7 整合素,可用于多发性硬化和IBD 的一线治疗,然而由于其非特异性, 那他组单抗的使用和进行性多灶性脑白质病(progressive multifocal leukoencephalopathy,PML)有 关[18],其严重的不良反应限制了其在临床上的运用。
一、维多组单抗
维多组单抗是人源性抗α4β7 整合素的IgG1 型单克隆抗体,选择性阻断胃肠道α4β7 整合素,而不影响全身免疫反应。 在一项评估MLN0002 在中至重度UC 患者中诱导和维持临床应答及缓解的3 期多中心、随机、安慰剂对照、双盲研究 (a phase 3, randomized, placebo-controlled, blinded,multicenter study of the induction and maintenance of clinical response and remission by MLN0002 in patients with moderate to severe ulcerative colitis,GEMINI 1)中[19],共 将374 例UC患者纳入诱导期治疗试验中, 其中维多组单抗治疗组较安慰剂组的临床应答率(47%比25.5%)、临床缓解率(17%比5%)及黏膜愈合率(41%比25%)更高。 在维持期治疗中,每4 周或每8 周连续输注维多组单抗较安慰剂治疗更有效,临床应答率为52%、57%对24%,临床缓解率为20.5%、24%对9%,52 周黏膜缓解率为56%、52%对20%。 在GEMINI 2试验中[20],共纳入368 例CD 诱导期治疗患者和461 例CD维持期治疗患者,最终结果不如UC 那样乐观,但也能有效改善CD 症状。 诱导期治疗中,更多治疗组患者有临床应答(31%比26%)和临床缓解(14.5%比7%)。 CD 患者维持期治疗到第52 周,每4 周和每8 周接受维多组单抗治疗者临床应答率较高(45.5%、43.5%对30%),临床缓解率较高(36%、39%对22%)。此外,无发生PML 的报道。GEMINI 研究表明,维多组单抗对CD 及UC 均有疗效,并且安全度较高,患者可耐受。
一项评估2 种剂量的维多组单抗治疗瘘管性CD 的安全性和瘘管修复者比例的4 期随机双盲研究[a randomized double-blind phase 4 study to evaluate the safety and proportion of subjects with fistula healing in 2 dose regimens of entyvio (vedolizumab Ⅳ) in the treatment of fistulizing Crohn’s disease,ENTERPRISE]中,受试者被分配到治疗组,即在第0、2、6、10、14、22 周静脉输注维多组单抗300 mg,或在第0、2、6、14、22 周静脉输注维多组单抗300 mg,第10 周注射安慰剂治疗,目前仍在招募受试者。 此外,一项评估维多组单抗用于术后CD 患者的2 期临床试验也正在进行中,主要观测结局为内镜缓解和病理组织学缓解, 受试者分别在第0、2、6 周,此后每间隔8 周,直到第52 周用药结束,接受维多组单抗或安慰剂治疗。
随着达标治疗的提出,衡量达标的生物标志物显得尤为重要。一项正在招募患者的探寻维多组单抗用于UC 患者中功效生物标志物的研究[development of a biomarker of efficacy of vedolizumab (EnTyvio®) in patients with ulcerative colitis,DETECT]中,通过使用共聚焦内镜技术来观察体外荧光标记治疗性抗体 [异硫氰酸荧光素 (fluorescein isothiocyanate,FITC) 标记维多组单抗和AF647 标记阿达木单抗]特异性结合肠道免疫细胞情况,结合患者临床、内镜及组织学表现,找到生物标志物来判定维多组单抗疗效。
二、依曲利组单抗(etrolizumab)
依曲利组单抗是靶向β7 整合素亚单位的人源性IgG型抗体, 可以同时阻断αEβ7 和α4β7 整合素与MAdCAM1和E-钙黏蛋白的相互作用。白细胞表面的α4β7 整合素和血管内皮细胞表面的MAdCAM1 分子相互作用,介导白细胞迁移出血管。 而αEβ7 整合素主要表达于黏膜上皮间T 细胞,通过和上皮细胞表面的E-钙黏蛋白介导白细胞滞留于上皮内[21]。 由于αEβ7 整合素的表达在活动性UC 和CD 中均增加, 且已有研究表明阻断该整联蛋白在动物实验中可减轻结肠炎, 可能机制是通过阻断α4β7 和αEβ7 整合素的β7亚基,可以减少淋巴细胞归巢到胃肠道黏膜,从而减轻肠道炎症。
在依曲利组单抗治疗中、重度UC 的1 期临床试验中,12 例(66%)治疗组患者和4 例(80%)安慰剂组患者治疗后监测到临床应答,3 例(16%)治疗组患者和1 例(20%)安慰剂组患者治疗后监测到临床缓解。 在药物的免疫原性检测中2 例(5%)治疗组患者检测到抗依曲利组单抗抗体,无严重不良事件发生[22]。 2 期临床试验中共纳入119 例中、重度UC 患者, 旨在研究依曲利组单抗能否有效诱导缓解炎症,在第10 周,100 mg 依曲利组单抗治疗组达临床缓解8 例(21%),300 mg 依曲利组单抗治疗组达临床缓解4 例(10%),安慰剂组无临床缓解[23]。 观察期内安全性尚可,5 例(12%)100 mg 治 疗 组、2 例 (5%)300 mg 治 疗 组 和5 例(12%)安慰剂组患者出现不良反应。
在UC 患者的组织标本中发现表达整合素αE 亚单位(integrin subunit alpha E , ITGAE)、 颗粒酶A (granzyme A,GZMA)的T 细胞数量增加。与对照组相比,UC 和CD 患者的肠道中ITGAE 阳性T 细胞比例更高, 并具有促炎细胞因子表型,且同时表达穿孔素和GZMA。在结肠炎动物模型中,抗αE 治疗可有效改善小鼠结肠炎症状[21]。 一项110 例患者的队列研究发现,对依曲利组单抗有应答的UC 患者,结肠组织的T 细胞水平显著高于不应答患者。 在使用100 mg 依曲利组单抗的受试者中, 具有较高水平GZMA mRNA 和ITGAE mRNA 患者的临床缓解率和黏膜愈合率更高 (高表达GZMA 比低表达GZMA 为41%比19%,高表达ITGAE 比低表达ITGAE 为44%比19%)。 在基线高表达GZMA 的UC患者中, 依曲利组单抗使用10 周后, T 细胞活化相关的基因表达和炎性因子的基因表达对比基线降低40%~80%。 这提示对UC 患者结肠组织中GZMA 和ITGAE mRNA 水平测定可作为依曲利组单抗的使用决策参考指标, 并且在依曲利组单抗治疗有效的患者中,GZMA 和ITGAE mRNA 表达降低。
另一项用于评估及比较未使用抗TNF 抑制剂的中至重度活动性UC 患者的依曲利组单抗和IFX 的疗效和安全性的3 期、随机、多中心,双盲、双虚拟临床研究GARDENIA 试验 (Phase Ⅲ, Randomized, Multicenter Double-Blind, Double Dummy Study to Evaluate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Etrolizumab Compared With Infliximab in Patients With Moderate to Severe Active Ulcerative Colitis Who Are Naive to TNF Inhibitors), 旨在比较依曲利组单抗与IFX 治疗既往未接受抗TNFα 单抗治疗的中、 重度UC 患者的疗效和安全性, 首要观察终点为用药后第10 周和第54 周是否临床缓解,定义为梅奥评分≤2 分且单项评分≤1 分,直肠出血评分为0 分。 依曲利组单抗组为每4 周(第0、2、6 周)皮下注射105 mg 依曲利组单抗,往后每隔8 周静脉滴注安慰剂,直到52 周试验结束,IFX 组每4 周(第0、2、6 周)皮下注射安慰剂,往后每隔8 周静脉滴注IFX,直到52 周试验结束。这项3 期随机平行双盲的前瞻性研究仍在招募患者中,其结果可帮助特定药物的选择性应用,以达到更好的疗效。
三、Ontamalimab (SHP647、PF-00547659)
MAdCAM 是一种重要的肠黏膜细胞黏附分子, 分为可溶性(soluble MAdCAM,sMAdCAM)和跨膜蛋白mMAdCAM,通过白细胞表面表达的整合素介导白细胞滚动或黏附到高内皮静脉(high endothelial venule, HEV),从而转导细胞内的炎症级联信号,扩大炎症反应[24]。
Ontamalimab 是一种人源性抗体,通过和MAdCAM 结合从而抑制其与α4β7 整合素的识别。 一项评估ontamalimab在中至重度UC 患者中的疗效和安全性的双盲、随机、安慰剂对照、平行、剂量范围控制研究(a Double-blind, Randomized, Placebo-controlled, Parallel, Dose-ranging Study to Evaluate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Pf-00547659 in Subjects with Moderate to Severe Ulcerative Colitis,TURANDOT) 已经证明ontamalimab 治疗组较安慰剂组的临床缓解率更高, 且实验室指标恢复正常。一项评估ontamalimab 用于抗TNF 应答不足的CD 或UC 患者的脑脊液(cerebrospinal fluid,CSF)淋巴细胞效果的1 期、多中心、开放式研究(TOSCA),旨在说明该药物对肠黏膜细胞的高度特异性以及ontamalimab 的用药安全性,治疗组和对照组在治疗3 次后,比较治疗前后CSF中淋巴细胞计数的变化值。 初步结果提示尽管中、重度CD患者已经接受了抗TNFα 制剂和免疫抑制剂 (硫唑嘌呤、甲氨蝶呤或6-巯基嘌呤)治疗,在接受ontamalimab 最大剂量治疗后,CSF 淋巴细胞计数无明显变化。另外,在2 期临床试验中[25],PF-00547659 治疗后无严重感染发生,胃肠道、鼻黏膜、脾脏、泌尿系统和肺等MAdCAM 高表达的部位无局部感染发展,亦无PML 相关病例报道。
TURANDOT 试验评估了ontamalimab 在357 例活动性UC 患者中的疗效和安全性,主要终点是缓解。 在第12 周,与安慰剂组(2.7%)相比,积极治疗组的缓解率更高(7.5、22.5、75 mg 组分别为11.3%、16.77%、15.5%),但225 mg 组(5.7%)差异无统计学意义[25]。
小分子药物
生物制剂主要通过静脉注射或皮下注射方式给药,有引起免疫反应的风险,从而导致抗药物抗体的产生,使疗效降低或者丧失[4]。 小分子药物(相对分子量<1 kU,通常<500 kU)可通过细胞膜扩散到胞内发挥作用,一般无免疫原性。 因此在给药途径、药物动力学及抗原性产生等方面具有较大的优势[26]。
一、Janus 激酶(Janus kinases, JAK)抑制剂
靶向抑制肠道内的JAK 可以阻断慢性肠炎的炎症反应。 JAK 属于胞内酪氨酸激酶家族,由JAK1、JAK2、JAK3 和酪氨酸激酶2 组成,在与不同的细胞因子和受体结合后,激活下游JAK 相关炎症信号通路,从而扩大炎症反应[27]。 因此通过阻断JAK,可减轻肠道炎症。
1. 托法替尼(tofacitinib):托法替尼是一种口服剂型的小分子类药物,可抑制JAK1 和JAK3,抑制JAK2 较弱,从而抑制大部分炎症细胞的胞内信号传导,包括IL-2、IL-4、IL-6、IL-7、IL-9、IL-15、IL-21 和IFN-γ[28]。 尽管这类药物可强烈抑制机体免疫功能,但在IBD 临床试验中,该药物耐受性良好。
在托法替尼对UC 患者的3 期临床试验(OCTAVE 试验)中,与安慰剂组相比,接受托法替尼10 mg、2 次/d 治疗8 周的患者具有更高的临床缓解率(18.5%比8.2%)、临床应答率(59.9%比32.8%)和黏膜愈合率(31.3%比15.6%),且用药安全性尚可,随着治疗累积剂量的增加,受试者低密度和高密度脂蛋白的浓度随之增加,一旦治疗结束即逐渐恢复正常。除此之外的不良反应有白细胞减少以及带状疱疹感染。 托法替尼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rheumatoid arthritis, RA)中不良反应也有带状疱疹[29],RA 的相关研究提示托法替尼引起带状疱疹感染多见于亚洲国家, 与合用其他免疫抑制剂或生物制剂相关,提示具有一定的地域差异。 对于这些患者可以提前注射带状疱疹疫苗以预防其感染或复发。 总体而言,托法替尼是有望成为治疗UC 的口服抗炎症药物[30]。
在CD 治疗方面,2 期临床试验结果提示, 对于活动性中、重度CD,托法替尼未能有效诱导临床缓解[31]。
2. Upadacitinib (ABT-494):upadacitinib 是一种选择性JAK1 抑制剂[32]。 在该药的2 期多中心临床试验研究(CELEST-NCT02365649) 中,评估了upadacitinib 对于中、重度常规治疗不耐受或者无效CD 患者的治疗作用及用药安全性,共纳入220 例患者,分为5 个剂量组,分别为3、6、12、24 mg,2 次/d,或24 mg,1 次/d,双盲用药至第36 周,主要观察终点为临床缓解和内镜下缓解。 结果显示治疗组达到内镜缓解的比例更高, 特别是在24 mg、2 次/d 治疗组内。 与安慰剂组相比,服用该剂量药物达到内镜缓解的比例更高。 此外,与安慰剂组相比,接受upadacitinib 6 mg、2 次/d的患者显著增加临床缓解率。 次要终点结果显示,治疗组患者的临床应答率约是安慰剂组的2 倍(24 mg 和6 mg,2 次/d 的应答率分别为61%和57%,安慰剂组为32%)。 与安慰剂相比, 接受upadacitinib 剂量≥6 mg,2 次/d 的患者,内镜缓解率显著增加。 用药安全性方面,虽然使用upadacitinib 的总体不良事件和感染事件高于安慰剂组, 但这些事件的发生似乎与治疗剂量无关。该试验用药结束后将对受试者进行长达52 周的观察,以评估其疗效及安全性。
在CELEST 试验之后,2 期试验(NCT02782663)和3 期试验(NCT03006068)将分别评估在CD 和UC 患者中,重复使用upadacitinib 的安全性以及长期疗效。
3. Filgotinib:filgotinib 是选择性JAK1 抑制剂。 在为期20 周的2 期临床试验(FITZROY 试验)中[33],研究者 拟 评价filgotinib 对于活动期中、 重度CD 患者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共纳入175 例患者,无论既往是否接受过抗TNFα 治疗,随机接受filgotinib 200 mg 或安慰剂治疗10 周,然后受试者继续服用filgotinib 200 mg 或100 mg、1 次/d 或安慰剂治疗10 周,主要观测终点为临床缓解,用药后第10 周的数据提示,治疗组患者临床缓解率为48%,而安慰剂组为23%,且治疗组患者具有更高的临床应答率、IBDQ 评分以及更大程度的炎症指标降低。 接受filgotinib 治疗的患者更容易发生严重感染,但其安全性仍在可接受范围。 针对CD 和UC 患者的Ⅲ期临床试验正在进行[33]。
二、1-磷酸鞘氨醇(sphingosine 1-phosphate, S1P)受体调节剂
S1P 可与5 次跨膜G 蛋白耦联受体(S1P1-5)结合,调节炎症反应涉及的不同过程,包括淋巴细胞迁移和从外周淋巴器官进入体循环、内皮细胞的渗透性、血管新生和凋亡等[34]。
在炎症部位可发现S1P 浓度增加, 可以促进炎症信号转导并促进免疫细胞的聚集。 抑制S1P 及其与受体的相互作用可阻止白细胞迁移到炎症黏膜组织中, 从而使其成为炎症性疾病的治疗靶点[35]。
三、Ozanimod
Ozanimod 通过特异性组织S1P 和S1P1-5 结合阻断其介导的下游炎症反应。一项Ⅱ期临床试验(TOUCHSTONE 试验)用于评估该药对于中、重度UC 患者的诱导治疗和疗效,共纳入197 例受试者,治疗组予ozanimod 0.5 mg 或1 mg每日口服治疗至第32 周[36],使用梅奥评分评估临床疗效,第8 周小剂量、 大剂量和安慰剂组的临床缓解率分别为13.8%、16.4%和6.2%,临床应答率分别为54%、57%和37%;治疗第32 周小剂量、大剂量和安慰剂组的临床缓解率分别为26%、21%和6%,临床应答率为35%、51%和20%。无严重不良事件报道, 针对CD 和UC 的Ⅲ期临床试验正在进行中。 但由于该研究为一项短期研究,需要进一步长期观测数据来支持其是否可用于临床。
四、Amiselimod(MT-1303)
Amiselimod 和ozanimod 类似,是一种S1P1受体调节剂。该药在多发性硬化的治疗中耐受性良好[37]。一项旨在评估该药在中、重度难治性CD 的疗效及安全性的Ⅱ期临床试验已完成,但目前尚无相关数据报道。总体而言,S1P 受体调节剂在IBD 治疗方面具有较大的前景,有望成为新的治疗靶点。
五、Mongersen (GED 0301)
转化生长因子(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 TGF)β1 是一种由免疫细胞和非免疫细胞合成的具有重要免疫调节功能的细胞因子。 由于Smad7(TGF-β1 蛋白合成的天然抑制剂)的过表达,CD 患者的TGF-β1 异常降低[38]。因此,Smad7 可作为阻断肠道炎症的治疗靶点。
Mongersen 是Smad7 mRNA 的反义寡核苷酸链,可特异性结合Smad7 mRNA 终止其蛋白表达, 其可被靶向输送到末端回肠以及右半结肠肠腔中。 一项旨在评估mongersen 对于166 例活动性CD 患者的疗效和安全性的Ⅱ期多中心临床试验已完成[39]。 与安慰组对比,治疗组患者临床缓解比例更高,40 mg 1 次/d 治疗组、160 mg 1 次/d 治疗组和安慰剂组临床缓解比例分别为55.0%、65.1%和9.5%,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10 mg 1 次/d 组与安慰剂组在临床缓解上差异无显著性(12.2%比9.5%)。 与安慰剂组(16.7%)相比,治疗组的临床应答率更高,10 mg 1 次/d 组、40 mg 1 次/d 组、160 mg 1 次/d 组分别为36.6%、57.5%、72.1%, 不良事件的发生率在各个治疗组相似。 进一步3 期临床试验将纳入炎症标志物和内镜检查数据,以更客观地反映mongersen 对于CD 患者的治疗作用。
近年来,随着IBD 研究不断深入,不断出现新的治疗药物,将逐渐弥补既往治疗方案的不足,并为IBD 患者提供更多的治疗选择。 本文回顾了近年来较有代表性的新药,临床试验所展示的数据也提示无论是临床症状还是内镜下表现,治疗后均有一定程度的缓解,相比于传统治疗药物的缓解率,与安慰剂对比,5-氨基水杨酸类(29%比17%)[42-44]、激素(47%比26%)[45-46],硫唑嘌呤(23%比18%)[47]、甲氨蝶呤(46.7%比48.6%)[49-50]、生物制剂及小分子药物的缓解率较安慰剂组有较大提升,但仍需纳入更多病例的对照临床试验。
然而,这些药物是否能真正改变疾病病程,改善IBD 患者的最终治疗结局仍不可知。尽管抗TNF 抗体、抗整合素药物和抗IL-12 / IL-23 抗体是治疗IBD 的有效药物,但从长远来看,相当多的患者远期获益不大。 在许多难治性患者中,迫切需要更新、 更有效和更安全的药物来显著改变IBD 的病程。 近年来,已开发出几种新药,目前正在Ⅱ期或Ⅲ期试验中进行测试。 新治疗方案将引发大量针对个性化和基于机制方面的研究。 个性化医疗将成为IBD 疾病管理的理想模式。 为获得基于大量证据的个性化医学方案,需要正确设计随机、 对照试验。 这些试验应包括客观评估疾病活动性(如内镜检查、CRP 和FC)的患者,客观且具有临床意义的研究终点(深度缓解),并包括临床上显著的对比物(安慰剂、生物制剂或小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