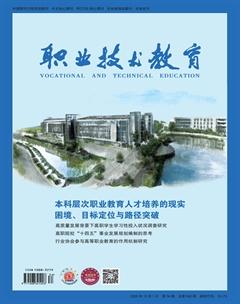“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东盟职业教育校企共同体建构
王忠昌 李晓娟
摘 要 中国—东盟职业教育校企共同体是“一带一路”背景下职业院校及企业响应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促进国际职业教育创新发展和满足国际化企业对技术技能人才急切需求的必然选择。根据中国—东盟职业教育校企共同体在地位、责任和愿景三方面的意蕴,在真实界、想象界和象征界三层次的境界,在主导方、关联方与受益方三元化的主体,在共商、共建、共治、共享四层面的特征,可以通过构建中国—东盟职业教育校企共同体的顶层机制、多样化人才培养模式、特色项目、多种信息共享渠道、合作共享平台等路径,进一步加强中国—东盟职业教育校企共同体建构。
关键词 “一带一路”;中国—东盟;职业教育;校企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 G71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0)34-0068-06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逐步推进,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交流与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得到了极大拓展,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纷纷到东盟国家投资办厂,助力东盟国家的经济建设与发展;而且随着中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东盟国家有实力的企业也被中国的政策和市场所吸引。在这种背景下,职业院校通过与跨国企业合作共建中国—东盟职业教育校企共同体,为中国和东盟国家的跨国企业培养国际化技术技能型人才成为必然。但是,由于职业院校与企业在本质、属性以及利益等各方面都存在着显著不同[1],加之东盟各国之间经济发展水平、民族文化等方面的复杂性和差异性,使得双方在合作过程中面临权责关系失序、失衡等现实桎梏,致使合作效果不明显、成果不突出,因而通过中国—东盟职业教育校企共同體的建构促进校企不同主体之间在要素、价值等方面实现供给和融合,能够有效破除校企合作之间的现实藩篱[2],从根本上促进职业教育国际化中的校企一体化发展。
一、“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东盟职业教育校企共同体的建构基础
“一带一路”建设是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举措,也是为顺应经济全球化时代所提出的促进世界经济共同发展的重要举措。中国—东盟职业教育校企共同体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积极响应,是顺应世界职业教育发展潮流的必然选择,也是培养具有国际素养技术技能型人才的迫切需要。
(一)响应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应然选择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赋予了“一带一路”建设新的内涵,也赋予了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新的视角。“一带一路”作为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举措,为沿线各国之间经济、文化以及教育的交流互动搭建了一个新型区域合作平台,东盟国家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地区。“一带一路”背景下,职业院校和企业都需要扩大对外开放,充分开展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与交流,实施“走出去”和“引进来”战略,实现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优势互补,充分带动东盟各国经济的发展,促进其产业结构的转型。而中国—东盟职业教育校企共同体正是这样的一个新型合作平台:一方面,他能够吸引境外优质院校、优质企业到中国办学、建厂,提升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化办学水平和办学质量,也能够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引进来”的重要表现之一;另一方面,通过在境外办学建厂,与境外优质企业实现协同育人,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为国外输入源源不断的人才资源,并提供先进技术的支持,既帮助中国企业实现“走出去”,也能够充分带动沿线国家经济的发展,促进沿线各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因而,建构中国—东盟职业教育校企共同体是响应“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倡议,充分展现了中国的大国担当和国际形象。
(二)国际职业教育创新发展的必然选择
国际职业教育发展由“政府主导”转为“校企主导”,是职业教育创新发展的主旋律,也是促进职业教育创新发展的驱动力。中国—东盟职业教育校企共同体在人才培养模式、课程开发、师资建设、实训模式等方面的国际化探索促进了职业教育的创新发展。职业教育的本质属性在于职业性,应然状态下的办学模式应是“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西方职业教育模式偏向内生模式,与企业的联系十分密切,而我国则更多是趋向于设计模式,在设计模式下由于政府过多管控而导致其职能出现错位,迫使职业教育游离于社会和企业发展之外[3],与企业联系不够密切。因此,要实现从“设计”向“内生”的转向,积极与企业对接,其前提是改变错位的政府职能,同时也要转变企业角色,实现职业教育由“政府主导”到“校企主导”的转向。中国—东盟职业教育校企共同体则属于“校企主导”模式,是顺应国际职业教育创新发展的潮流和必然选择。
首先,人才培养模式的国际化。中国—东盟是由多个国家组成的新型国际合作组织,国家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要满足各国对技术技能人才的不同需要,就要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具有国际素养的高技能人才,通过学校与企业共同制订人才培养目标,实现诸要素与国际区域经济发展以及产业结构的对接。其次,课程开发的国际化。课程是培养人才的载体和中介,人才培养的最终落脚点在于课程的改革与建设,课程内容的序化则是国际化课程改革与建设成功与否的关键[4],在中国—东盟校企共同体中,通过职业院校与企业联手共同开发国际化的课程,并依照工作体系的本质对课程内容进行序化,能够满足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的本质需求。再次,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的国际化。师资队伍国际化是促进中国—东盟校企共同体构建的核心力量,中国—东盟校企共同体要求培养一批国际师资队伍。一方面,通过交流、派遣、访学等方式,将教师送入境外企业或职业院校进行访学和交流,提升教师的国际化教学水平和国际化视野;另一方面,积极吸收境外优质企业中具有较高实践技能的企业人员作为兼职教师,与境内院校进行长期的合作交流,促进双方师资质量的提升。最后,实训模式的国际化。中国—东盟校企共同体为职业院校学生的实习实训提供了广阔的国际平台,通过在优质跨国企业中以特色项目为载体开展实训,使人才培养更加符合“跨国”素养的要求,从而满足跨国企业的需求。
(三)国际化企业对技术技能人才的急切需求
经济全球化、教育国际化的趋势不可逆转,跨国企业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产物。跨国企业所需要的人才是具有国际素养的技术技能人才,不同国家之间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有着较大差异,只有根据本土实际情况,培养当地所需要的人才,才能满足差异化的需求,而中国—东盟职业教育校企共同体的建构能够促进教师、学生等人员的国际流动,满足跨国企业对国际化人才的需求。一方面,该共同体采用境内境外办学相结合的方式,不仅引进优质企业来中国办学建厂 ,吸引国外企业与中国职业院校进行合作办学,积极吸纳东盟优秀职教学生来华留学,中外联合培育人才;同时大力支持国内优势企业走出国门在海外办学,输出优质资源以充分实现资源之间的共享,因而能够在互相交流中较好地根据实际需求培养具有国际素养的技术技能人才,满足国际化企业的需求。另一方面,通过校企创新共同体的建立,共同探寻创新人才的培养之道。因其二者之间有着共同的美好愿景,能够使校企双方朝着同一个目标共同发力,协同探索人才培养的成功之路,充分发挥资源的集约与聚集作用,实现职业教育的生态发展,最终实现跨国企业人才供给侧与需求侧之间的平衡,满足跨国企业对人才的需要。
二、“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东盟职业教育校企共同体的内涵
中国—东盟职业教育校企共同体是中国和东盟各国的职业院校、企业为解决中国和东盟国家跨国企业的技术技能人才缺口、解决职业院校校企融合不充分而打造的国际新型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关系。
(一)三方面的意蕴
“共同体”是由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在《共同体与社会》中提出,意为建立在共同目标之上,自然有机整合而形成的具有紧密联系的一個社会性整体[5],成员内部具有强大内在凝聚力,各成员围绕共同愿景互相进行经验交流和资源共享。职业院校和企业作为中国—东盟职业教育校企共同体的主体成员,主要有三个方面意蕴。
第一,职业院校、企业双方之间处于相互平等和彼此尊重的地位。互相平等和彼此尊重是构建中国—东盟职业教育校企共同体的前提和基础。“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在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以及文化习俗等各个方面都存在巨大差异,一方面,这些差异为中国—东盟职业教育校企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多元异质化的发展机会;另一方面,这些差异也是中国—东盟职业教育校企共同体构建进程的阻碍因子。由此,要建立一个平衡协调发展的中国—东盟职业教育校企共同体,要求尊重各国不同之处,允许差异的存在,企业与职业院校双方是基于求同存异前提下的一种平等地位。
第二,职业院校、企业双方秉持各自的道德伦理和社会责任。诚然,职业院校和企业是在本质上存在差异的两种不同组织机构,学校坚持以育人为前提的公益导向,企业则坚持以经济效益为前提的利益导向。但毋庸置疑的是,双方要实现共同发展,因此双方都应该承担各自的社会责任,发挥各自的作用。职业院校作为育人主体,要充分发挥社会服务功能,根据东盟各国对技术技能人才的不同需求,培养具有国际化素养和标准的国际型技术技能人才。而企业要为职业院校提供服务,与职业院校协同育人以促进共同发展。
第三,职业院校、企业双方都有着共同的愿景。共同愿景是中国—东盟职业教育校企双方基于各自发展需求所作出的一项长期承诺,为双方合作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二者通过共同愿景的整合,能够促进内部组织成员主动而真诚的投入,而不是迫于压力的被动式遵从[6]。由于职业院校的落脚点在于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经济发展中最活跃的因子也在于技术技能人才,因此在中国—东盟职业教育校企共同体中,双方的共同愿景便是培养符合东盟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高水平的国际型技术技能人才,以达到促进中国与东盟各国社会经济共同发展的目的。
(二)三层次的境界
法国心理学家、哲学家拉康的“主体三界说”是阐述中国—东盟职业教育校企共同体构建层次的理论基础[7],共建“一带一路”进程中,中国—东盟职业教育校企共同体的构建要经历真实界、想象界以及象征界三个不同层次的境界。
第一层次为真实界。这一层次的中国—东盟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处于初级阶段,校企合作双方初步达成合作意向或者签署合作协议,尽管在协议中明确了合作的目标、内容、标准等,但却没有开展实质性的合作,更未明确真实界中合作双方主体身份的认同。而主体身份的认同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社会道德、社会责任意识的形成,由于合作双方缺乏对身份认同的明晰,会导致该共同体生态失衡,不利于其建构和发展。处于真实界的中国—东盟职业教育校企双方仅仅是低层次的合作关系,职业院校将企业简单视为学生的实习基地,与跨国企业之间缺乏深度的对接融合,未能适应东盟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而培养相应的人才,而企业也只是单纯将职业院校看作提供技术技能人才的来源机构,缺乏深度参与职业院校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愿望,不利于中国—东盟职业教育校企共同体内部的生态平衡。
第二层次为想象界。这一层次的中国—东盟职业教育校企合作进入到实质性阶段,校企双方合作按照预定计划展开,此时企业和职业院校的合作进入到了一个中间过渡期,虽然还未能在本质上认识到自身的主体身份,距离高度一体化发展还有一定差距,但此时双方合作已经有了统一和固定的方式并趋于稳定,能够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合作内容和方式等。
第三层次为象征界。这一层次的中国—东盟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方式趋于稳定,合作的广度和深度进入到一个理想的境界,与前两个境界不同的是,此时职业院校与企业二者都能够清晰地认识到自我主体地位,产生身份认同感,在合作过程中能够自觉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树立起长远且清晰的共同愿景,并且能够为实现双方愿景而共同努力,促进优质资源的共享,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东盟职业教育校企共同体。
(三)三元化的主体
校企合作的实质是教育与经济之间的合作。“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东盟职业教育校企共同体的实质是教育领域与经济领域之间的合作,其主体就是教育领域的主体“职业院校”和经济领域的主体“企业”,以及与双方密切相关的政府机构、行业组织及协会等第三方机构,同时还有企业员工以及职业院校学生等诸多直接受益人员,这些机构和人员都直接或间接参与了中国—东盟职教校企共同体的构建并产生重要影响。
首先,作为主导方的中国和东盟国家职业院校和企业,应该充分发挥各自的主导作用。一方面,无论是中国或是东盟各国的职业院校,都应该在深度分析各国经济发展模式和产业结构的基础上对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进行精准定位,培养具有国际化视角的技术技能人才,从而满足不同国家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同时,要与企业积极合作对接,坚持科研反哺功能,提升职业教育的社会服务能力,为企业提供相应的前沿技术,促进企业转型升级。另一方面,企业要发挥自身的主导作用,与职业院校开展深度合作,共同制订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国际标准,参与国际化的课程开发、教材编制、实训基地建设等,并随时向职业院校反馈自身的需求,使所培养的技术技能人才符合国际行业产业发展的本质需求,最终达到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
其次,作为关联方的中国和东盟国家的政府、行业组织、协会等机构以及职教专家、行业专家等人员。在推进中国—东盟职业教育校企共同体构建的进程中,政府扮演着政策制定者的角色。而政府同时又能够获取一定的利益补偿,通过中国—东盟职业教育校企共同体的建构,既带动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又扩展了对外文化的交流。此外,行业组织、协会、职教专家、行业专家等也要发挥各自的作用。如行业组织可以通过行业协会的形式扮演第三方机构的角色,为中国—东盟职业教育校企共同体“牵线搭桥”,同时也应该发挥三方监督者的角色,对其合作进行有效的动态监督与评估。而职教专家以及行业专家则为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共同体长远合作提供有借鉴意义的规划和建议等。
最后,作为受益方的中国和东盟国家的职教学生、职教教师、企业员工等。该共同体中,除了主导方和关联方以外,还有作为受益方的学生、教师以及员工等,他们同样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中国—东盟职业教育校企共同体建构的关键目标之一是培养具有国际化视野的技术技能人才,提升职教教师的国际化素养,促进企业员工的职业技能发展。由此,要重视受益方的发展诉求,建立健康发展的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共同体生态系统,实现该系统内能量流和资源流的富集流动,促进中国—东盟职业教育校企共同体的生态发展,最终实现中国与东盟国家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四)四维度的特征
中国—东盟职业教育校企共同体不同于以往被动式发展的“校企双主体”,而是一种共商、共建、共治、共享的新型协同发展的一体化组织关系,具有十分显著的特征。
一是共商国际新型校企合作关系,改革传统外压式、被动式的校企合作关系,职业院校主动对接跨国企业,推动校企供给侧改革,实现人才供给与人才需求的平衡。开放性是职业教育的核心属性[8],职业教育作为一个生态系统,系统内外各生态因子都对其发生产生重要影响,社会背景与产业结构则是其重要的外部生态因子[9],因而职业院校要积极主动与外界联系,将自身发展置于整个生态环境中,与经济社会发展环境相一致,积极主动与跨国企业对接融合,促进人才供给侧与需求侧无缝衔接,从而实现中国—东盟职业教育校企共同体的生态平衡。
二是共建国际新型校企合作平台,创新职业教育办学方式,采取境内办学和境外办学相结合的方式,全方位满足跨国企业对国际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中国—东盟职业教育校企共同体不同于单纯的校企合作模式,其具有境内与境外两个市场,若是单一在境外办学,或单独在境内办学,不利于形成紧密的校企对接关系,体现不出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特色,所培养的技术技能人才也不能适应国际化发展诉求。因此,要采用境内办学和境外办学相结合的方式,实现双方的互动交流以搭建国际新型校企合作平台,满足跨国企业对国际化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
三是共治国际新型校企合作格局,积极吸引政府、行业企业、科研院所等参与校企共同体治理,实现在国际技术技能人才标准制定、国际通用型课程开发、国际专兼职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的多元共治。实现主体共同治理的格局,有利于推动真正意义上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共建校企共同体格局的形成,通过加快境内外學历证书以及资格证书的统一认定,制定国际通用标准,从而形成稳定、可持续发展的校企共同体。
四是共享国际优质校企合作资源,充分发挥校企共同体中各相关方的优势,整合各方资源,在课程资源、实训基地、师资队伍等方面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美国社会学家霍曼斯的交换互动理论认为,“报酬”是指能够满足有机体的需要,并使有机体作出反应的一种刺激物[10],而在中国—东盟职业教育校企共同体构建过程中,东盟各国之间优质资源的共享与交换作为校企双方所获“报酬”,能够刺激、加深二者的合作深度与广度。因此,整合各方资源,实现国际资源之间的优势互补,也是中国—东盟职业教育校企共同体建构的显著特征之一。
三、“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东盟职业教育校企共同体的构建路径
中国—东盟职业教育校企共同体的建构是一个多主体共同参与的过程,要求多方共同发力,优化结构布局,构建与发展相契合的顶层机制,探索多样化的人才培养方式,推进特色项目建设,形成多渠道的信息共享通道,搭建多元化合作平台等,最终架构起中国—东盟职业教育校企共同体国际化的治理体系。
(一)构建中国—东盟职业教育校企共同体顶层机制
顶层机制是一个宏观上的政策设计,为共同体建构提供了方向引领,也为其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因而顶层机制的完善与否直接影响共同体建构的质量。当前,“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东盟职教校企共同体的发展因政府职能的缺位而面临着兼顾性配套政策的缺失,以及区域性政策的不完善等现实桎梏[11]。因此,要加强政府政策层面的现实关照,明确政府职能,制定完善且适配的政策法规,充分发挥宏观政策的指导、引领和保障作用。面对各国之间的多元化差异,要充分体现出顶层机制设计的科学性,在协调多方主体共同利益的前提下,根据各国实际情况进行精准设计,以期保证校企双方在合作过程中的各个方面都能做到有章可循和有法可依,更好地保障多方权益不受到侵害,促进共同体的协同发展。例如,广西在2015年及2016年先后制定、颁布和签署了《职业教育区域(国际)合作工程实施方案》《开展“一带一路”教育行动国际合作备忘录》等方案、文件和协议,加快职业教育国际化步伐,提升中国与东盟职业教育的开放共享共建水平,促进中国与东南亚各国之间的互动交流,实现共同发展。
(二)探索中国—东盟职业教育校企共同体多样化的人才培养模式
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是职业院校与企业合作的落脚点,长期以来受到体制的制约与阻碍,校企合作往往由于缺乏长效合作机制而或多或少存在一些“合而不融”的困境,未能从根本上建立校企一体化协同发展的实践育人共同体[12]。因此,中国—东盟职业教育校企共同体的建构要从根本上突破机制的藩篱,实现人才链与产业链以及创新链的协调发展,尤其要与产业链积极对接,实现校企共同创新、探索多样化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模式,协同培养“链式人才”。如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通过与企业联合,共同开发了中国—东盟会计专业人才标准,旨在依托北部湾经济发展区以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培养具有国际金融意识的、能够适应现代发展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以满足当地和沿线国家的人才需求。这一办学模式既能促进学校的特色发展,又能实现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以及与国际水平相接轨,保障了校企生态位的平衡。
(三)推动中国—东盟职业教育校企共同体特色项目建设
中国—东盟职业教育校企共同体的建构要立足跨国企业和服务国际行业[13],因此要遵循行业企业发展的内在逻辑,以特色项目建设为桥梁实现项目化运作,促进校企双方的无缝对接。校企之间以签署协议的方式,以特色项目为载体进行合作,体现了职业教育的本质特征。首先,特色项目建设能够满足职业教育教学需要。项目化教学是职教领域特色之一,将教学内容以项目的方式呈现,让学生在动态且真实的工作场景中,通过小组合作的方式共同完成一个项目[14],体验完整的工作过程,能够使学生习得技术技能相关的默会知识,也能够培养学生合作、团结等职业道德意识;同时通过亲身参与、实践操作,丰富其动手实践能力,为高水平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奠定基础。其次,特色项目建设能够为企业创造价值。项目一般是真实的经济项目,特色项目的建设往往以企业特色发展为依据,职校教师和学生的参与能帮助企业完成一些技术上的难题,可以为企业带来较大的经济收益。因而,通过推动特色项目的建设,不仅有利于职业院校以及学生的发展,也能够促进企业的发展,与双方的利益相契合,加深了校企的纵向合作。例如,中—老合作农作物优良品种试验站、中—印尼上汽通用五菱汽车教育培训中心、罗克韦尔自动化实验室平台、“伊尹学堂”项目等一大批中国—东盟职业教育校企特色项目的建设,在解决中国与东盟国家跨国企业对国际化技术技能人才需求的基础上,持续推动了中国与东盟各国的经济发展。
(四)形成中国—东盟职业教育校企共同体信息共享的多种渠道
信息共享是进行决策的前提条件,是形成共同体的基本表现之一,信息的不对称会加大校企合作共同体建构的成本,因而校企共同体的建构离不开完善的信息共享渠道支撑,多途径的信息共享渠道能够助推东盟各国与中国之间建立良好的伙伴关系,能够随时了解各国发展最新动态,因此必须要构建和完善信息沟通机制和渠道。首先,职业院校要充分信任企业,将企业视为忠实合作伙伴,主动对接企业需求,培养企业所需要的人才,同时充分发挥院校的优势,与企业共享学术科研成果,帮助企业实现技术创新。中国—东盟的跨国企业也应积极寻求与职业院校的合作与交流,将其作为促进企业改革创新的助推器,通过与职业院校共同制订人才培养方案、共同开发课程等深度参与职业院校育人的全过程。通过校企双方共同努力,实现双方的互相信任,建立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亲密融合关系,从而实现信息的实时共享。此外,实现信息共享需要一定的载体和平台,可以通过交流会、论坛的形式促进双方信息的交流。定时定期举办职业教育发展论坛,如中国—东盟职业教育联展暨论坛、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发展论坛、中国—东盟职业教育高峰论坛等,在论坛中企业与院校可以进行深度交流讨论,互相分享各自的需求和交流相關经验,共同探讨职业教育未来发展趋势等。
(五)搭建中国—东盟职业教育校企共同体合作共享平台
校企共同体合作平台的完善与否制约着对外交流的广度和深度,是促进校企双方深度融合的重要内容与关键突破口,平台缺失会增加校企合作的难度,不利于共同体的建构。因而要搭建多层次、立体化的中国—东盟职业教育校企共同体国际合作交流平台,加强平台之间的资源整合,建立平台运行评价机制,实现全方位无障碍无时差的沟通交流。首先,要搭建能满足学生实践学习以及提供就业机会的平台。通过搭建该平台,能够吸引更多优质企业入驻,为学生提供更广阔的实习就业机会,让学生和跨国用人单位之间实现直接交流,促使人才供给侧和需求侧直接对接,满足学生和跨国企业双方的诉求。其次,要搭建国际师资共享平台。中国—东盟校企共同体内的教师通过合作平台与企业的技术专家共同开展项目研究,在研究中提升自身的专业素质和国际化素养。最后,要搭建资源共享平台。平台的搭建能够使校企双方充分发挥平台的资源聚集作用,双方在共同的平台上进行深度合作交流,共同商讨发展战略,实现优质资源共享,促进合作的更进一步发展。
参 考 文 献
[1]李欢,林克松.“一带一路”倡议下高职院校“走出去”的多重治理逻辑[J].职业技术教育,2018(19):39-43.
[2]戴汉冬,石伟平.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共同体的内涵、要素、价值和建构[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5(30):59-63.
[3]徐国庆.职业教育原理[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9.
[4]姜大源.职业教育学研究新论[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17.
[5]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M].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53.
[6]彼得·圣吉.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M].郭进隆,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9-12.
[7]卢永欣.真实界与意识形态——阿尔都塞和齐泽克对拉康的继承[J].前沿,2010(12):26-29.
[8]寧云涛.协调与转型:新时期高等职业教育开放化的路径研究[J].职教论坛,2017(2):84-87.
[9]吴鼎福,诸文蔚.教育生态学[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5.
[10]特纳(Torner,J.H).社会学理论的结构[M].吴曲辉,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293.
[11]杨剑静.职业院校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挑战与推进策略[J].中国高教研究,2019(1):34-37.
[12]刘志敏,张闳肆.构筑创新共同体深化产教融合的核心机制[J].中国高等教育,2019(10):16-18.
[13]张炜.基于校企共同体的“校中厂”运行机制及对策研究[J].职业技术教育,2016(17):12-15.
[14]祁占勇,任雪园.扎根理论视域下工匠核心素养的理论模型与实践逻辑[J].教育研究,2018(3):70-76.
Construction of China-ASEAN Vocational Education School-enterprise Communit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ang Zhongchang, Li Xiaojuan
Abstract The China-ASEAN vocational education school-enterprise community is an inevitable choice for vocational schools and enterprises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o respond to the concept of the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promote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meet the urgent needs of international enterprises for technical and skilled personnel. The China-ASEAN vocational education school-enterprise community has three meanings in status, responsibility and vision, has three realms in the levels of realism, imagination and symbolism, three subjects of the ternary subject of the leading party, related party and beneficiary, and four characteristics of co-consultation, co-construction, co-governance and sharing. Furthermore, the China-ASEAN Vocational Education School-Enterprise Community can construct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top mechanism, diversified talent training models, unique projects, multiple channels for information sharing, and effective paths such as cooperation and sharing platform.
Key word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hina-ASEAN; vocational education; school-enterprise community
Author Wang Zhongchang, research associate of School of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Education of Nanning Normal University, Deputy Director of China-ASEAN Vocational Education Research Center(Nanning 530001); Li Xiaojuan, postgraduate student of 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 of Nanning Normal Univers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