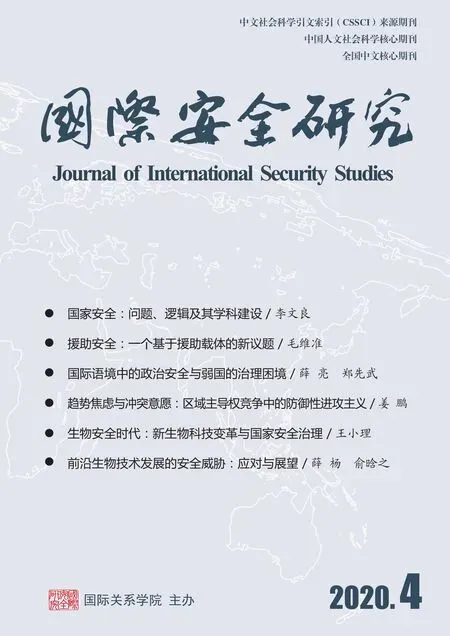国际语境中的政治安全与弱国的治理困境*
薛 亮 郑先武
安全理论
国际语境中的政治安全与弱国的治理困境*
薛 亮 郑先武
国际语境中的政治安全日益呈现出一种以国家主权为核心,既分门别类又相互联结的“多流模式”。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弱国对国际安全的整体影响愈益提升,弱国政治安全动态以其对政权安全的追求及其与公共安全间的张力为核心,关涉“统治精英及其支持机制的统治免于主要来自内部的威胁”的“政权安全”遂构成弱国政治安全的特定称呼。弱国政治安全的核心逻辑形成于弱国政权对“短期政权安全追求与长期国家建设间的深刻矛盾”的“弱国政治安全治理困境”的应对。弱国政治安全困境的治理离不开对政权安全与人的安全的智慧融合。此种困境具有长期性,在其驱动之下,弱国政治安全的理论探索表现出弱国联盟与安全区域主义等议题的演进,而其进一步的发展则离不开对弱国语境的领会,围绕弱国政权安全的模式和相关的内外政策,探索弱国政治安全对“软权力”的追求、弱国政治安全对特定国家安全观的推动等问题。
政治安全;弱国;治理困境;多重价值
近年来,弱国政治安全在国际安全研究中与日俱增。[1]作为一个与广大发展中世界息息相关的安全概念,弱国政治安全亦在其日益进入国际安全中心舞台的进程中臻于成熟,具备愈益丰厚的研究价值。
已有研究在概念辨析、国别和区域研究、历史回溯、冲突与合作研究、系统性介绍和初步理论性探索等方面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亦存在三方面不足:第一,缺少在国际安全研究和政治安全总体框架下的探索。其后果是缺少一种必要的整体视野、概念适用对象的不清晰和不可通约。第二,仍缺乏对作为一个安全概念的弱国政治安全的系统性论述。这对于其概念化进程、准确地运用和进一步研究而言有所不利。第三,未能指出弱国政治安全研究的发展态势。其后果是核心议题与研究价值的隐而不见。对此,本文探寻并力求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国际语境中的弱国政治安全议题从哪里来,向何处去?其症结怎样化解,困境如何克服?本文致力于三个层次的探索:一是在政治安全概念之中发掘弱国政治安全的国际安全定位,聚焦作为弱国政治安全的政权安全;二是在此基础上系统论述作为一个安全概念的政权安全,并直指其要害——政治安全与弱国的治理困境,在探讨困境应对与化解的同时,明确政权安全的核心逻辑;三是追踪由弱国政治安全困境及其治理所引发的各国行为模式对主要着眼强国的传统理论构成的挑战,并补充所主导的弱国政治安全研究的发展前沿,展现其丰富的研究价值,从而助推理论创见和更加深入的探讨。
一 国际语境中的政治安全与弱国指涉
政治安全[2]的概念化经历过一段演进的历程。原先,“政治安全”一词运用广泛,但缺乏明确所指。托马斯·格迪思·达科斯塔(Thomaz Guedes da Costa)指出,“政治安全作为一个概念在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中的缺失使得这个词的概念化并不容易。虽然这个概念被广泛地运用于决策者的讲话或各类安全议题的汇编中,但并不明确,亦缺少可操作的定义”。[3]而作为近似的概念,“国家安全”(national security或state security)、“政治—安全”(political-security)与“军事—政治安全”(military-political security)却在传统文献中出现较多并沿用至今。其中,“政治—安全”往往指“政治的”与“安全的”两种相对独立而又互相补充的深层次追求;[4]而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安全”与“军事—政治安全”则有大体一致的含义,即指以民族国家为安全的“指涉对象”(referent object)、常常涉及军事和政治的“安全领域”(security fields)的安全概念,或者说国家的“根本安全”。如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从“国家安全”出发,坚持认为安全研究可以被界定为“对威胁、军事力量的使用和控制的研究”;[5]戴维·纽曼(David Newman)从“军事—政治安全”出发,提出传统的军事政治安全概念“大体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军事安全,二是领土安全,三是人口安全(影响对领土和主权的政治主张)”,而主权、领土与人口正是构成国家的三要素。[6]奥利·维夫(Ole Wæver)认为,“以往的聚焦在于政治的和制度的单元——国家——相应的在于其政治和军事的部分”,[7]其核心在于国家主权受到军事与政治的威胁。
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人们愈益认识到战争作为很多国家间关系的选项正在消逝,或在某些情境下已然消失,军事—政治安全议题在安全考虑的中心部分明显衰落,现实主义关于军事安全首要性的预设也备受质疑。[8]与此同时,1982年帕尔梅委员会提出的“共同安全”概念在西方的发展,推动了将军事以外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安全作为目的本身的思考,[9]而亚洲国家(当时以日本为首)对政治与经济安全的强调乃至一种综合安全的观点,也日益进入安全研究的国际话语之中,使得“一个‘安全的非军事层面’的标识指向经济和政治安全的‘东方’论断,并因此对超越军事威胁领域的系统稳定性的担忧合法化”,[10]两者共同导致上述趋势进一步强化。伴随后工业时代技术变革和意识结构转变而来的个人技能的上升、权威的分化与多中心世界的兴起,多层次的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事务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11]在安全议题中,其作为安全的指涉对象与威胁来源的趋势也愈益凸显。在此背景下,一个由国家行为体主导的相对统一的军事—政治安全动态的图景让位于多部门的安全概念和一系列更广泛的行为体。[12]巴里·布赞(Barry Buzan)认为,20世纪“80年代末,主导世界超40年的军事—政治安全议程急剧崩溃,一个‘新世界失序’的意向开始主导对未来的认知,带来一项新的安全议程”。[13]
这项安全议程的更新在冷战结束后更加活跃,并围绕对“国家中心”和“军事聚焦”的态度呈现出“传统主义者”(traditionalists)、“扩大论者”(wideners)和“批判安全研究”(critical security studies)三大流派。其中,即便被认为是固守传统而难以应对变局的传统主义者,也不同程度地放松了对国家中心性的强调,或坚持政治安全与国家的关键性而放松对军事安全核心地位的主张。[14]批判安全研究则将个体视为真正的安全指涉对象,注重人的解放。对此,前两者被视为对国际安全相对边缘的理解;而“争议最小的安全议程的拓宽者是那些遵循前人的国家安全观念,同时将军事、政治安全与环境、族群、经济或健康问题相联结,并选择很大程度上客观和物质主义(且常常是经验主义)路径的人”。[15]他们既主张依据形势变化拓宽安全议程,又探索安全本身之逻辑以避免泛化,渐渐走出一条受到广泛认可的中间道路。在此过程中,政治安全也从统摄状态演化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安全领域,这集中反映在其中流砥柱哥本哈根学派的演进中。以杰夫·胡思曼(Jef Huysmans)的观察,政治安全在其早期文本中具有一定的模糊性,一方面指影响安全的部分因素,另一方面又指代定义安全的一个过程,直到《安全新论》才将之“还原到1/5”。[16]于是,政治安全由政治威胁的次群体构成,不包含大规模军事的、身份认同的,经济的或环境的手段,在聚焦国家的同时又兼顾非国家的政治单元和系统层次的指涉对象,从而在总体上“关涉对政治单元及其关键模式(结构、进程或制度)的合法性或承认的威胁”,而在核心问题上关涉“对国家主权的威胁”和“国家、政府系统与给予它们合法性的意识形态的组织性稳定”。[17]
此外,就近来政治安全概念的应用而言,对应于变动中的国际安全秩序,不同层次的指涉有不同内涵,且与其他安全领域相互动,从而呈现出一幅丰富的政治安全图景。实践方面,有学者就“政治安全”的概念咨询具备丰富从政经验者,得出两种意见的汇合:一是指一个社会中的人政治参与的稳定合法;二是指一系列范围广泛的统治活动,[18]这与学术探讨一致。首先,仍然是聚焦于国家主权的政治安全。这方面主要关涉一国政府政治体系在政治发展进程中的协调运转,[19]赋予特定国家统治者合法地位的意识形态,[20]或者说一国以及一种能够追求和实践国家行为者认为至关重要之目标的合理的行动自由。[21]一方面,政治安全与其他安全领域乃至资源安全、环境安全之间建立了日益紧密的关联;[22]另一方面,它在主权上有了进一步的开拓,主要表现为愈加重视塑造政治安全动态的内部机制、政权合法性、民众认同,[23]以及延伸至外部的政治安全区域化的态势。政治安全得益于全球化和个人、共同体、政权与国家安全的地方化之间的张力,以“双边的或微复合体的”为主,“朝向一个政治安全区域化的时代”,乃至关涉“国际体系和平有序地变化”。[24]两方面亦交相作用,产生如“非洲统一组织(非盟前身)将与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与艾滋病等相对抗纳入非洲战略来增进这块大陆的持久和平与政治安全”等政策结果。[25]
其次,在“人的安全”之下的政治安全的纵深发展。发轫于冷战结束前的关于安全意义之辩论的人的安全,在内战和国家内部冲突发生率日益增加、民主化的传播、人道主义干预和全球化及与之相关的经济危机造成社会失序的多重趋势下获得了发展,[26]强调人是安全的首要指涉对象。其标志是1994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对人的安全的七个维度的界定,其中,政治安全指面对冲突、战争与政治压迫时基本人权和自由受到保护,而最有效的政治不安全指标被认为是国家动用军事力量的优先性。[27]但这种定义广受批评,通常被认为过于狭窄,不足以指导实证研究。[28]此外,这方面的政治安全亦关涉人的政治生存,包括对若干政治权利,如代表权、参与权、异议权以及对法律、社会和政治生活的规则进行有效修改的真正机会的保障;相反,人的政治不安全则表现为有些人无法进入公共机构、由于贫穷而受到政府忽视、由于地位低下而无法进入决策层、穷人无代表和无发声等。[29]总的来看,人的安全下的政治安全议程经历了从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前十年的演变,其长期价值在受到学界和政策界肯定的同时,亦在全球竞争加剧之际的辩论中受到了一系列广泛的质疑,因而呼唤更为复杂和微妙的辩论。[30]
再次,关涉跨国行为体的政治安全的应用。它一方面关涉跨国行为体的根本性生存,另一方面聚焦其面临的政治威胁。以跨国公司为例,“对于跨国企业而言,政治不安全集中表现在东道国的国有化和征用,直接暴力、不稳定或限制以及整体营商环境受到政治变革的影响这几个方面”。[31]因此,有学者将如今的政治安全分为三类:跨国安全、国家安全和人的安全。[32]
虽然不同指涉对象的政治安全间具备一定张力,但不妨碍政治安全系统形成较为协调的整体,其关键则仍是国家的政治安全。如以人的安全为例,虽然它已成为联合国政策议程的一个主导性概念,但仍然很难厘清“集体安全通过谁、如何形成”的问题,[33]加之人们常常因为一些价值追求而求诸集体的生存。[34]格奥尔格·索伦森(Georg Sørensen)认为,“即使我们主要关心的是人的安全,国家也需要在分析中占有重要地位,因为国家构成对个人安全产生影响的最重要的单一宏观结构,任何对安全问题的全面研究,既需要宏观基础,也需要微观基础,个人和团体与国家之间的联系是最重要的焦点,即使是在分析以人为目的而不是手段的当代安全问题时也是如此”,因此即便站在人的安全的视角下也仍然不可否认,“一个强大的国家,即具有高度社会政治凝聚力的国家,是个人和国家安全的必要先决条件”。[35]实际上,学者们对所谓“强国”(strong states)的探讨便有意于调和各类安全主张之间的张力,维护国际安全的整体性和政治安全的核心逻辑。在此意义上,多种多样的政治安全界定中具备统合性的依然是“关涉社会秩序组织性的稳定”。[36]以此为中心,日益形成一种既分门别类、又相互联结的政治安全体系,或是一种政治安全的“多流模式”,[37]其中,不同的分析对象对应于不尽相同的政治安全重心。
一般情况下,政治安全的研究者往往会探讨一种不同于传统研究对象的“弱国”(weak states)情境。[38]此种“弱国”与“强国”相对应,而与“弱权”(weak power)区分,指国家作为政治实体的“国家性”(stateness)之弱,而非国力之弱。核心是国家社会政治凝聚力、国家观念和制度上的虚弱,乃至大规模暴力垄断的无能。[39]在此意义上可视之为政治维度上的“发展中国家”,或者说相对稳定的政治不安全国家。在界定弱国的关键特征方面,理查德·杰克逊(Richard Jackson)综合了卡洛琳·托马斯(Caroline Thomas)、巴里·布赞和乔尔·米格代尔(Joel Migdal)的三种观点,突出“基础结构能力”“强制性能力”“民族身份认同与社会向心力”三个维度,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判断标准。[40]围绕大体的标准,不同学者在具体操作中作出了不同的划分。[41]毫无疑问,区分强国和弱国是重要的,“因为它强调了面对政治威胁的不同脆弱程度”:当国家强大时,安全主要从保护国家各部门免受外部威胁和干涉的角度来看待;而在弱国中,内部威胁却构成了典型威胁,“安全化的进程开始从国家向次国家行为体移动”,因此,以国家内部竞争性的团体、组织和个人作为主要的安全对象来看待安全或许是更为合适的。[42]实际上,当国家虚弱时,安全重心便被认为落在其“政权”(regime)之上。洪永培(Yong-Pyo Hong)对李承晚政权的动态分析表明:“随着李政权合法性的减少,其政策优先项也从国家安全向政权安全转移”,[43]此时,政权安全便构成该国的政治安全。另据穆罕默德·阿约布(Mohammed Ayoob)的界定,“第三世界国家”及个别其他“虚弱和不安全的大国”的安全/不安全可以定义为关于“脆弱性”(vulnerabilities)——“不管是内部的和外部的,都威胁或有潜力搞垮或削弱国家的领土、制度结构和统治中的政权”。根据这一定义,弱国安全的核心即为“政权安全”(regime security)。[44]
综上,政权安全是涉及弱国或发展中国家时给予政治安全的特定称呼,在此语境下,“政治安全”即政权安全。[45]对弱国的强调和对政权安全的重视,两者相伴而生。
二 政治安全与弱国的治理困境
在论述了政治安全概念总体的背景、演进、现有形态和趋势及其对弱国的特定指涉之后,这里对政治安全与弱国的治理困境作出系统的界定与探讨。
作为政治安全的弱国指涉,“政权安全”(简称RS)的概念演进是一个晚近持续的进程。在此过程中,一以贯之的是其浓厚的政治性质和与实质上弱国的相伴而生。据约兹兰·凯古苏(Özlem Kaygusuz)的考察,“政权安全最初是冷战时期的称谓,指的是一种安全范式和一套做法,当统治精英开始将自己在权力中生存的安全视为首要的政治优先事项时出现,其安全关切由一个政党、家庭、卡特尔或寡头网络所组成,决定了安全机构的结构和运作”。[46]就其概念的界定而言,应用最广的是理查德·杰克逊的定义:“政权安全即确保统治精英不受对其统治的暴力挑战的状况”。[47]其他定义包括:免于对领导人政治生存的内部威胁;[48]统治精英对强制性机构的准垄断;[49]在位统治者及其政治追随者对权力的安全控制和维护;[50]“现有领导者被移除出政治办公室的可能性”[51]等。此外,也包括对政权本身的不同理解,如“掌握最高机关的小群体或有效控制国家机器(尤其是其强制力量)的精英”;[52]“最高掌权人物和对国家实现有效控制的精英的统治”或“位于政体中心的政治—军事制度和最高级别的官员”。[53]总的来说,政权安全关涉统治精英及其支持机制的统治(或政治生存)免于主要来自内部的威胁(尤其是暴力挑战),其指涉对象则视具体情况而定。其他类型的脆弱性,包括内部的和外部的、军事的和经济的、规范的和物质的,乃至生态多样性的脆弱性,只有当它们变得足够尖锐,足以进入政治层面并威胁政权的生存和影响政权的威胁认知时,才成为这一安全关涉的组成部分。
弱国政治安全即政权安全核心逻辑的形成与弱国在政治安全上有迹可循的因果、特征、困境和治理规律密不可分。
首先,弱国有着大体一致的根源。不少学者对弱国之弱的原因进行过较为系统的探讨。[54]其原由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外部民族国家框架的强加与该国所在区域的历史发展模式之间的张力;其二,殖民或半殖民状态的政治遗产。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国界的划定对族群原有机理的拆分,或在某些情况下造成的新的跨界族群认同,带来了种族的、宗教的叛乱和分离运动,增强了其边界和制度面临内部挑战的强度,并且殖民国家出于行政便利或帝国基于内部权衡的划分也造成许多国家资源基础不足,难以提供能促进其合法性并创造更强的国家意识的产品;其三,时间框架的急剧缩短和业已建立的国际规范对国家构建施加的巨大压力与限制。经验表明,国家建设是一项棘手、困难、漫长且充满暴力的事业,而与西欧国家数百年的长期国家发展历程相比,新兴国家需要在数十年的极短时间内构建相对成熟的国家,且需要遵循由业已成熟的国家创设的规范。一方面,这会限制历史上国家构建时所采用的手段和方式,使得新兴国家的事业更加艰难,并面临来自先行国家当代政治模式的结构性政治威胁(在苏联解体后加剧);[55]另一方面,又会给予那些几乎没有实质国家性的国家以正式主权,继而保有国家资格,使得一些难以为继的实体不会合法消亡。同时,优势国家通过主导国际体系,构建所谓“主从模式”及施加长期干预。无论是军事、政治、经济还是技术层面的国际力量,都对国家构建的命运和其他安全问题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外部的介入也鼓动了区域和内部的动乱,使得本已脆弱的国家结构不胜其扰。另外,统治政权本身采取的一些安全战略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恶性循环。
其次,大体一致的根源使弱国呈现出相近的特征。除了上文所述的“基础结构能力”“强制性能力”“民族身份认同与社会向心力”三个维度较弱这一综合性的根本特征以外,弱国往往还具有一些连带性的共同特征,包括易受政治威胁,往往受意图性的和结构性的双重政治威胁;对领导人最有压力的威胁往往来自内部的政治挑战,包括政变、派系斗争、暴动和反叛等;因此,大量资金支持的军事力量也常常指向内部,使得武装部队(“安全部门”)在弱国的内部安全作用相当大,甚至在一些情况下构成它们的主要职能。[56]同时,弱国的权力极度集中,有一套平行的决策网络,取代政府负责的决策机制;政治运作亦在根本上不受宪法—法律制衡,经常将例外做法迅速纳入立法,简化为执政工具,并导致依赖性的司法,缺乏广泛的合法性。[57]而这些又会一同导致安全动态分散于政权安全与人的安全两大方面,并互相削弱,构成所谓“不安全困境”(insecurity dilemma):短期的政权安全追求与长期的国家建构目标之间存在矛盾,统治精英越要建立有效的统治,越引发社会群体对他们权威的挑战,极端情况下甚至导致弱国的政权成为其国民的最大单一威胁,而个人与社会安全的缺乏保障又会进一步恶化政权的安全处境。[58]
此种“不安全困境”驱动着深层次的恐惧,使得弱国的统治精英采取了一系列的安全战略予以应对。即便具体情境和执行有所不同,但这些安全战略在抽象层面上仍然存在着相对的统一。它们大体分为两种:一是短期速效而长期却加深困境;二是中长期有效但长期效果仍待检验。
首先,弱国的领导人倾向于诉诸魅力型权威,以加强其权威的合法性。但是除非其权威转变为制度化的形式,基于个人魅力的领导往往最终会导致政治不稳定。其中尤其重要的是权力交接引发的问题。事实上,在权力交接制度化之前,弱国的内部政治将充满安全问题。[59]其次,弱国领导倾向于将对外强硬或表达统一意愿(如李承晚政权的“北进”)作为增强政治安全的工具。此举能够在短期内增强其政治合法性和得到国内的民众支持,但长期来看往往会使安全政策变得僵化而自缚手脚,压缩了灵活变通的空间,同时,难以兑现的承诺也会大大减损领导人及其政权的权威。再次,弱国政权倾向于通过军队、安全武装乃至恶性社会势力实行内部镇压和清除异议,以应对紧急的政治不安全事件。但此类武装的长期培育和安全部门的支出更有可能阻碍而不是促进弱国的经济增长和发展,并牺牲社会中的平民群体,[60]同时,该类举措也会一次次地削弱政权合法性并增强军队反噬政权的风险。对此,替代性的措施是一些弱国对民兵的开发和与雇佣兵及私人军事公司(PMCs)的合作。这些团体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常规军的政变风险,短期内还会降低政府管理冲突的成本,并在提供效力和信息方面补充常规军,但最终这些群体往往会因武力使用方面的矛盾而疏离政府,乃至助推政权更迭,并常常会给平民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61]而在对外方面,弱国往往会出于政权安全动机与外部强有力的行为体联合。但是,国内人民通常认为外来影响的渗透限制了国家主权,从而削弱了该政权的合法性。并且,与外部大国的联系也可能会令其陷入大国竞争的漩涡,使全球不安全成为自身的不安全。这些意图确保政权安全的措施对政权安全的维护而言往往收效甚微,反而构成政权不安全的一大来源。[62]
另外一些为弱国一致采用的政治安全战略相对经受得住时间的考验,而其长期效果则有待进一步的观察和检验。
首先,弱国政权常常会在掌权时建立详尽的赞助体系或庇护政治。[63]虽然其后果包括敷衍广大公众的需求和使政府难以进行实质性的政治改革,但不可否认其对政权安全起到的较长时段内的作用。同时弱国政权会对包括军队在内的其他群体采用“分而治之”的安全战略,以防止联合反对现政权。其次,因弱国的根本特征,其政权合法性会在更大程度上寄托于经济的发展。因此很多弱国甚至将经济的长期增长视为其政权安全的首要支柱。尽管经济增长是维护政权安全的有效手段,它也同时创造了国内动荡的新根源,如内部的移民、收入不平等、贪污腐败等,并增加了经济抵御外部冲击的脆弱性。这两方面如未有应对,都可能损害未来的前景。[64]再次,军事力量不仅关涉对外国家利益的维护,也直接关乎弱国政权的存亡,因此发展军事生产技术构成一项重要的政权安全战略。[65]其极端形式则是有条件的弱国出于政权安全对核武器的追求。不同于“领土完整、激发民族主义、更大掌控的欲望”等所有领导人追求核武器的一般动机,弱国领导人还会在相对不受制度性限制(但往往总体军事能力和经济能力不佳)的情况下,出于使政权免于外部威胁与干预、减少更大代价的传统军事力量投入和提高现政权支持率等考虑而开发核武器。[66]据贾利勒·罗珊德尔(Jalil Roshandel)对伊朗案例的观察,民众对核武器的支持率非常之高,即便是反对现政权的公民,似乎也普遍支持其核野心。[67]但此种战略的实施过程也常常伴随着莫大的风险。此外,主要由美国和西方国家发起的全球反恐议题为弱国应对种族的、宗教的叛乱和分离运动引起的政权安全问题提供了契机。有志于国家建设和长期政权安全的弱国往往倾向于采取综合的和长远的解决方法,因此其“反恐”举措与美国等强国相区别。
而在对外方面,弱国则渐渐地倾向一种有着鲜明政权安全旨向的区域防卫安排,这被一些学者视为“颜色革命”后愈益增强的“虚拟的区域主义”(virtual regionalism)或“保护性的一体化”(protective integration)。[68]作为对国内政治反对的一种反制方案和协调对外政治团结的一个基础,此类区域组织的核心功能便是确保政权安全与合法性,实现其他相关的安全、经济或贸易目标,并抵制输出“民主”和“良治”的西方国际组织和捐赠机构。另外,也有一些由弱国构成的综合性区域组织渐渐吸纳成员国的政权安全需求,并反映到宪章的修改之中,如《非洲联盟宪章》第四条(h)款关于联盟干预权的次段落将“……(战争罪、种族灭绝、反人类罪)和外部侵略”修改为“……和对合法秩序的严重威胁,来恢复成员国的和平与稳定”,即反映出其对政权安全考虑的吸收。[69]不过,相似的目的或许更多体现在区域组织的不干预原则中。[70]此外,对广受认可的国际行动的参与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政权安全战略。例如,卢旺达的统治政党能够通过在维和行动中的参与和对“非洲问题非洲解决”的贡献来保障它的国内地位并吸引关键捐赠者的支持。[71]不过,也有学者将对外维和与对内救灾等举措一同归并为一种军事的“非战斗性运营”(Noncombat Operations)的政权安全战略,即国家的军事战略愈加强调除了传统的战争任务以外开展救灾和维和等非战斗行动的能力,从而能够提供国家服务、维持政治稳定。其统一逻辑则在于军事力量的多元目标与基于内外条件的经济增长的相辅相成。也缘于此,其经济增长向战斗性军事力量的转化率也较传统强国的认知值更低。[72]
尽管如此,政权安全的追寻本身就是一个深刻矛盾的过程,鲜有全然克服不安全困境的案例。至今,很多政治学学者认为的根本性的解决方案仍未超出多党民主和自由市场的路径。但经验表明,弱国促进西式民主往往会造成更多而不是更少的暴力冲突,有时甚至会导致所谓的国家崩溃。[73]而从政治安全的视角来看,根本挑战在于弱国精英将短期政权安全让位于长期国家构建战略的意愿和能力。但在此基础上也有两种不尽相同的看法。一是主张以尽可能人道的方式建设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二是倡导探索顺应时势的新型国家和新型“强国”。[74]无论如何,在笔者看来,一些针对弱国根本特征及其政治不安全之根源的战略追求对于缓解乃至走出此番困境仍是无可回避的。
弱国的安全在很大程度上分化到政权安全与人的安全两端,两者有着共生的关系,[75]因此根本性的政治安全追求离不开对两者的兼顾、平衡乃至融合。安德里亚斯·克利格(Andreas Krieg)指出,阿拉伯世界的政权没有认识到这两种安全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因此“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如果要充分地把握阿拉伯地区根本的不安全的话,必须重新界定他们对阿拉伯世界采取的安全路径”,尤其是“安全需要在社会政治的语境下被包容地界定”。[76]首先,这要求一种宏观的安全战略设计,在提倡与弱国相适配的综合安全观的基础上,注重吸纳和平衡人的安全,并在其要义中兼顾西方偏好的“免于恐惧的自由”与东方重视的“免于匮乏的自由”,[77]同时避免政权安全的泛化和对“政权安全”的公开宣扬(鉴于其与公共安全间的张力),争取导向一种包容性的“人民安全”,并在实践上以合适的次国家和区域手段相辅助。其次,在两者实体性的衔接上,一个相对稳定的认同度高的衔接群体必不可少,在此意义上,中间阶层加上法治与负责制仍是难以替代的选项。“对法治中心地位的不同看法不应掩盖法治对政治实用主义的最终权威”,[78]但中间阶层的具体政治态度与法治和负责制的具体形式则可以有很大的差别,并可能体现出与历史渊源的调和,而绝非外部所能规定。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强调,“特定国家采纳的制度形式并不构成普遍的模式,不同的社会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落实这些(国家、法治和责任制)制度”。[79]最后,尽管对政权不安全的恐惧很难克服,结构性的困境亦难以消解,但不应为此而免去主要的政权安全行为体的责任。罗纳德·韦泽(Ronald Weitzer)以津巴布韦为例表明了,“后殖民国家的性质既不取决于过去压迫性安排的坚韧,也不取决于基层政治和游击斗争的群众动员,相反,它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当前时期的主导力量和自身的原因”。[80]这同时也符合安全化路径对安全作为“可改善之选择”的强调,[81]构成政权安全的应有之义。
以上便构成弱国政治安全与治理的核心逻辑。
三 弱国政治安全治理研究的多重价值
伴随着全球化时代弱国对国际安全的整体影响愈益提升,对政治安全与弱国治理所作的研究更加受到重视。在此过程中,对弱国“在减少其结构、制度和政权的脆弱性方面对安全的压倒一切的关注”[82]也得到更为系统的论述,形成了一个行之有效的安全概念——“政权安全”的核心逻辑。政权安全概念的日益厘清,弱国政治安全治理困境的艰巨性和长期性及其促生的行为模式,又使得相关研究很大程度上呈现出进一步纵深发展的态势,并延伸到更多的研究议题之中,具备难以忽视的丰富价值。
首先,在深刻剖析弱国政治安全治理困境的同时,政权安全也有益于促进政治安全整体内外两个维度的统一。这符合日本学者猪口孝(Takashi Inoguchi)的期待:“内部的自我重构是论证政治安全的一种必要模式,政治安全应有更广的安全研究框架”。[83]而以政权安全为重心的政治安全研究也是对政治安全体系整体如何与特定适用对象相结合的一种说明。在此意义上,它也丰富了政治安全整体的研究价值。
其次,政权安全概念和逻辑的日益厘清以及弱国政治安全困境的稳定性和长期性,使得政权安全迈向了理论建设的阶段。在此过程中,出于政权安全考虑的内外政策后果对主要着眼于强国视野的传统理论构成了挑战与补充。据格雷戈里·库布伦茨(Gregory Koblentz)对“作为一种理论的政权安全”的理解,即“政权安全预测该政体的领导人会采用努力减小其统治面临的内外部威胁的安全战略,应用于安全政策的不同领域”。它与新古典现实主义相似,强调国际因素和国内因素在政府的防御和外交决策中的互动。同时它又与新古典现实主义有所不同:后者主要强调外部威胁,而前者至少视内外威胁同等重要;后者基于总体国家利益,而前者主要关注统治政权的利益。[84]围绕政权安全的模式和相关的内外政策,这部分的理论思考目前主要分布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作为一种弱国政治安全战略的经济发展。它有利于解释传统政权实施大规模经济现代化计划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穆罕默德·阿约布以沙特阿拉伯为例阐述道:“可以下结论,理解沙特阿拉伯事态发展的方向,并解释一个传统政权实施大规模经济现代化计划这一看似矛盾的事实的关键,无法在现代主义和传统主义力量的竞争间找到,而是在于领导阶层(无论是传统主义者还是现代主义者)确保政权持续有效性的努力之中……在沙特社会的最高处,传统和现代的各部门互相补充并相互利用,以维护这一政权的可行性,在其中,这两种部门都有着巨大的利害关系”。[85]此外,在经济发展对军事能力的贡献上,一般认为高速的经济发展会带来战斗性军事力量的快速提升,因此不少学者将经济能力作为对外军事能力的指标。以上视角指出政权安全对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选择发展军事能力类型的塑造,即政权安全战略同时倾向于发展相当比例的非战斗性军事能力以开展对内的救灾、维稳、反恐等行动,很大程度上需要不同于传统战斗行动的训练,其结果则是此类国家战斗能力的发展可能会比传统强国预期得更慢,乃至有益于缓释与其他国家的安全困境。[86]但这种态势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且不宜过分强调。
第二,弱国政治安全对特定国家安全观的推动。它有利于解释多层次的和多部门的综合安全观的形成。唐纳德·麦克米伦(Donald McMillen)指出,在亚洲国家的总体安全目标中,国家政治巩固、经济增长和繁荣、社会团结被视为优先事项,这些在它们对国家和区域安全问题的强调方面几乎一致,[87]而阿约布对沙特安全观的探究表明,“海湾国家的国际安全和区域安全观往往与政权安全考虑直接相关”,“对于沙特统治者来说,从家庭到国家再到区域,各个层次的安全是相互关联的”。[88]当然,对于综合安全观的起源也有不同看法。彼得·卡赞斯坦(Peter J. Katzenstein)认为,日本国家安全政策的综合性由日本政治的结构所塑造,而日本安全政策由已界定的规范语境解释政策变化中的灵活性和僵硬性,“结构和规范的互动解释了综合的安全定义以及政策调适的模式”。[89]
第三,弱国政治安全立意对“软权力”追求的补充。即软权力建设的一般指向是对外的,表现为“A运用吸引或说服改变B的既有偏好、A运用吸引力或制度使B视议程为合法以及A运用吸引力或制度塑造B的最初偏好”这三个层面被用于国际关系之中。[90]而软权力建设的政权安全逻辑则指示国家将之作为对内部安全挑战的回应,以此增强政权合法性和民族向心力。以金斯利·艾德尼(Kingsley Edney)的理解,即该做法对内旨在增强文化向心力,鼓励国内利益团体和个人与政权相向而行,使政权反对者难以吸收地方民众的物质资源支持,因而使国家易于应对安全威胁;对外旨在消解威胁该政权的其他各方的软权力;而内外联动之处则在于增加国际吸引力,让政权更易使公民相信其所宣称的国家在其领导下的国际地位的改善。通常的特点包括不对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作严格区分,亦不对软权力的多种政治或社会来源作明确辨别。总的来说,“软权力理解的‘去西方化’需要检验软权力战略背后的不安全”。[91]
第四,作为弱国政治安全战略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WMD)的开发。除上文阐述的核武器战略以外,也包括化学和生物武器(CBW)的开发、储存和使用。政权安全提供了洞见,表明一些弱国开发或宣称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主要是为应对内部政治威胁,而传统强国则失于理解此种隐秘的安全关切,因此其主导的核不扩散战略被认为可降低外部威胁,却未必能够减少针对内部的威胁。此种论断也被用于对历史事件的解释中,如认为政权安全考虑是当年伊拉克抵抗联合国武器核查行为的重要因素。[92]其后果是,“对政权安全如何影响一个国家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政策缺乏了解,意味着决策者可能会制定无效的威慑战略,并实施不恰当的防扩散措施”。[93]尽管很多问题有待进一步的思考,但深化这方面的研究有助于制定更加有效的国际防扩散政策。
第五,对传统理性威慑理论下的风险承担行为的修正。即在政治心理学既有成果的基础上,将国内政治稳定和外部安全威胁作为领导人政治安全认知的两个尺度,认为当政权面临严重的内外挑战,处在“损失区”时,更可能选择风险承担(如军事强制)政策;而当政权安全得到保障,处在“收益区”时,更可能选择风险规避(如较少风险的政治施压)政策。[94]但在同样承认政权安全状况重要性的基础上,有学者持相反意见,认为政权不安全的认知更可能导向一种“抚外安内、息事宁人”的政策。[95]这也提醒相关研究者对政权安全与传统理论视角间的关系作进一步厘清,以便在操作中更好地控制变量,同时放下成见,真正进入研究对象的语境之中,以便对风险决策具体的关涉对象之于决策政权的意义有更精准的把握。
第六,一种“全方位制衡”(omnibalancing)的弱国联盟理论。[96]传统结盟理论认为国家主要出于保护自身免受他国的权力或威胁而结盟,即强调结盟的决定因素绝大多数来自国际体系的结构,特别是各国面临的实际和潜在的外部威胁。[97]在接受威胁制衡理论,即“与其他国家结盟以反对具有优势的威胁”[98]论断的基础上,“全方位制衡”理论认为国家内部威胁也构成结盟时予以考虑的所谓优势威胁的一种来源,而对于弱国来说内部威胁往往就是优势威胁,因此它假设“最强有力的结盟决定因素是其领导人确保政治和物理生存的动力”,从而修正了传统联盟理论对弱国的适用。[99]柯蒂斯·瑞安(Curtis R. Ryan)认为这种政权安全的路径难能可贵地沟通了阿拉伯世界联盟和结盟行为中的外部威胁、内部政治经济和国内政治,甚至“架起了一座桥梁,联结新现实主义的外部安全担忧,自由制度主义热衷的政治经济因素甚至内部政治斗争,以及为社会建构主义所检验的规范的和意识形态的争论”。[100]而有学者则进一步表明政治不安全的领导人更愿意组成军事同盟,并且在选择伙伴时更少挑剔,但也在短期的军事联合(military coalitions)与长期的联盟(alliances)之间作了区分。[101]此种区分对于这类理论独立于传统联盟理论的纵深发展实属必要,后者也离不开在此基础上对“同盟”(coalition)、“结盟”(alignment)和“联盟”(alliance)间相互转化的研究,同时,弱国与强国间同弱国彼此之间的相关行为亦有待进一步辨别。
第七,也是尤为重要的是一种扎根于政权安全的区域主义的发展。罗伊·艾利森(Roy Allison)以中亚的区域框架为例,说明一种区别于传统区域主义的所谓“虚拟的区域主义”。[102]但这不否认在一个有着国家构建难题、根深蒂固的地方冲突、区域大国的地缘政治竞争、非互补性的贸易经济关系的所谓“并非支持深化区域主义之地”,政权安全推动区域主义建设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进展。这反而证明了政权安全之于发展中世界区域主义建设的价值。何况,更进一步的区域经济和功能性合作很可能基于对经济发展、政权安全和政治稳定的共同担当而获得。[103]实际上,在特定条件下,区域主义未尝不可以与政权安全相互动。郑先武对东南亚安全区域主义的探索表明,“东南亚国家认为,区域主义可以增加其国家认同和政权安全,并将之当做实现国家建设目标的工具,在它们看来,东盟的中心任务就是凸显国家内部安全议题,尤其是政权安全在区域或次区域安全建构中的重要性”,而这并不妨碍东南亚安全区域主义的纵深发展。[104]
以上探索都具有不可磨灭的价值,展现出弱国政治安全治理研究近年来的生命活力,亦是作为弱国概念之载体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国际地位抬升的真实写照。
四 结论
本文在国际语境和政治安全的总体框架下探讨了弱国政治安全的概念基础、核心逻辑与多重价值。随着国际安全议程的演进,政治安全日益呈现出一种以国家主权为核心,既分门别类又相互联结的多流模式。其中,政权安全是涉及弱国时给予政治安全的特定称呼。弱国政治安全即政权安全核心逻辑的形成与弱国在总体上有迹可循的因果、特征、困境和应对密不可分。在对政治安全进行论述的过程中,其指涉对象、安全主体、安全因素、治理困境与安全战略得以厘清。弱国政治安全治理困境的消解离不开对政权安全与人的安全予以调和并导向人民安全的宏观安全战略设计,同时需要实体性的衔接和次国家与区域手段的配合。但治理困境具备长期性,其所引发的各国一系列的安全战略和行为模式及其对主要着眼于强国的传统理论构成的冲击与补充,主导了弱国政治安全治理研究的前沿思考。本文对此进行了剖析,在追踪理论反思之动态的同时亦指出其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其中,尤可注意的是一种扎根于弱国政治安全的安全区域主义的探索。
本文虽弥补了既有研究在宏观视野、安全逻辑、系统阐释、核心聚焦和追踪前沿等方面的不足,对于进一步的研究具有一定程度的参鉴价值,但由于特定的研究旨向,在实证研究、案例说明、一手材料和议题细化等方面亦存在较大的局限。例如,在议题细化方面,各国的体制差异等因素对弱国政治安全的影响及其与弱国共有的不安全困境的关联性,便有待进一步的厘清。
推动此项议题研究并获得实质性进展的大多是有着非西方背景的杰出政治学者,他们在理解特定对象的政治安全脉络时有着西方学者所不具备的优势。安全的逻辑在一定程度上基于特定的文化和历史经验,它与权力结构、领导动态以及复杂的决策过程密切相关,因此其分析必须对特定的历史、社会和文化语境保持敏感。在此意义上,深谙发展中世界和政治安全分析之道的中国学者一定会在此基础上作出无可替代的贡献,在促进中国对发展中国家进一步认识和了解的同时,推动政治安全与弱国治理研究更上一层楼。
[1] 已有研究主要包括:Mohammed Ayoob, “Perspectives from the Gulf: Regime Security or Regional Security?” in Donald Hugh McMillen, ed.,, London: MacMillan, 1984, pp. 92-116; Amitav Acharya, “Regionalism and Regime Security in the Third World: Comparing the Origins of the ASEAN and GCC,” in Brian L. Job, ed.,, Boulder: Lynne Rienner, 1992, pp. 143-164; Mohammad-Mahmould Mohamedou,, Lanham: Austin & Winfield, 1997; Yong-Pyo Hong,,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Inc., 2000; William Reno, “External Relations of Weak States and Stateless Regions in Africa,” in Gilbert M. Khadiagala and Terrence Lyons, eds.,, Boulder: Lynne Rienner, 2001, pp. 185-206; Brent E. Sasley, “The Effects of Political Liberalization on Security,” in Tami Amanda Jacoby and Brent E. Sasley, eds.,,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150-172; Roy Allison, “Virtual Regionalism, Regional Structures and Regime Security in Central Asia,”, Vol. 27, No. 2, 2008, pp. 185-202; Curtis R. Ryan,, Gainesville, FL: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09; Matteo Fumagalli, “Islamic Radicalism and the Insecurity Dilemma in Central Asia: The Role of Russia,” in Roland Dannreuther and Luke March, eds.,, London: Routledge, 2010, pp. 234-251; Jalil Roshandel,, Santa Barbara, California: Praeger, 2011; Abiodun Alao,,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35-105; Gregory D. Koblentz, “Regime Security: A New Theory for Understanding the Proliferation of Chemical and Biological Weapons,”, Vol. 34, No. 3, 2013, pp. 501-525; Nael Shama,, London: Routledge, 2013, pp. 11-12; Lawrence Rubin,, Palo Alto: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Richard Jackson, “Regime Security,” in Alan Collins, ed.,, 4th ed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 200-212; Sabine C. Carey, Michael P. Colaresi and Neil J. Mitchell, “Risk Mitigation, Regime Security, and Militias: Beyond Coup-proofing,”, Vol. 60, No. 1, 2016, pp. 59-72; Andreas Krieg,, Cham, Switzerland: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AG, 2017; Kemel Toktomushev,, New York: Routledge, 2017, pp. 29-62; Özlem Kaygusuz, “Authoritarian Neoliberalism and Regime Security in Turkey: Moving to an ‘Exceptional State’ under AKP,”, Vol. 23, No. 2, 2018, pp. 285-298,等等。
[2] 关于政治安全概念核心的阐述,参见郑先武:《安全、合作与共同体:东南亚安全区域主义理论与实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6-99页。
[3] Thomaz Guedes da Costa, “Political Security, an Uncertain Concept with Expanding Concerns,” in Hans Günter Brauch, ed.,, Heidelberg: Springer, 2008, p. 561.
[4] 参见 Julian Lindley-French, “My End Is Going Down... Iraq and the Transatlantic Political- Security Mess,”, Vol. 25, No. 6, 2003, p. 479; Melissa Boyle Mahle, “A Political-Security Analysis of the Failed Oslo Process,”, Vol. 12, No. 1, 2005, p. 80; Mike M. Mochizuki, “Political-Security Competition and the FTA Movement: Motivations and Consequences,” in Mireya Solís, Barbara Stallings and Saori N. Katada, ed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pp. 54-72,等等。
[5] Stephen Walt, “The Renaissance of Security Studies,”, Vol. 32, No. 2, 1991, pp. 211-239.
[6] David Newman, “Environmental Schizophrenia and the Security Discourse in Israel/Palestine,” in Hans Günter Brauch, ed.,, Heidelberg: Springer, 2009, p. 856.
[7] Ole Wæver, “The Changing Agenda of Societal Security,” in Hans Günter Brauch, ed.,:, Heidelberg: Springer, 2008, pp. 585-593.
[8] Barry Buzan, “Rethinking Security after the Cold War,”, Vol. 32, No. 5, 1997, p. 6.
[9] Emma Rothschild, “What is Security?” in Barry Buzan and Lene Hansen, ed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7, p. 3.
[10] Ole Wæver, “Securitization and Desecuritization,” in Barry Buzan and Lene Hansen, ed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7, p. 94.
[11] 参见James N. Rosenau, “Patterned Chaos in Global Life: Structure and Process in the Two Worlds of World Politics,”, Vol. 9, No. 4, 1988, pp. 327-364; James N. Rosenau, “The Relocation of Authority in A Shrinking World,”, Vol. 24, No. 3, 1992, p. 261; James N. Rosenau, “A New Dynamism in World Politics: Increasingly Skillful Individuals?”, Vol. 41, No. 4, 1997, pp. 655-686。
[12] Barry Buzan and Ole Wæv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19.
[13] Barry Buzan, “Rethinking Security after the Cold War,”, Vol. 32, No. 5, 1997, p. 8.
[14] Barry Buzan, “Rethinking Security after the Cold War,”, Vol. 32, No. 5, 1997, p. 10.
[15] Barry Buzan and Lene Hansen, ed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7, p. xxxiv.
[16] Jef Huysmans, “Revisiting Copenhagen: Or, On the Creative Development of a Security Studies Agenda in Europe,”, Vol. 4, No. 4, 1998, p. 488.
[17] Barry Buzan, Ole Wæver and Jaap de Wilde,,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8, pp. 144, 141, 8.
[18] 参见Thomaz Guedes da Costa, “Political Security, an Uncertain Concept with Expanding Concerns,” in Hans Günter Brauch, ed.,, Heidelberg: Springer, 2008, p. 562。
[19] 舒刚:《新安全观视域下政治安全的内涵分析及其体系构建》,载《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第28页。
[20] Russell Ong, “China’s security interests in Central Asia,”, Vol. 24, No. 4, 2005, p. 427.
[21] Takashi Inoguchi, “Political Security: Toward A Broader Conceptualization,”, Vol. 40, No. 2, 2003, p. 106.
[22] 参见Martin Doevenspeck, “Lake Kivu’s Methane Gas: Natural Risk, Or Source of Energy and Political Security?”, Vol. 42, No. 1, 2007, p. 104; Úrsula Oswald Spring, “Peace and Environment: Towards A Sustainable Peace as Seen From the South,” in Hans Günter Brauch, ed.,, Heidelberg: Springer, 2008, p. 122; Anders Jägerskog, “Functional Water Cooperation in the Jordan River Basin: Spillover or Spillback for Political Security?” in Hans Günter Brauch, ed.,, Heidelberg: Springer, 2009, p. 633。
[23] Takashi Inoguchi, “Political Security: Toward A Broader Conceptualization,”, Vol. 40, No. 2, 2003, p. 105.
[24] David Dewitt, “Common, Comprehensive, and Cooperative Security,” in Barry Buzan and Lene Hansen, ed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7, p. 421; Emma Rothschild, “What is Security?” in Barry Buzan and Lene Hansen, ed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7, p. 3; Georg Sørensen, “Individual Security and National Security: The State Remains the Principal Problem,”, Vol. 27, No. 4, 1996, pp. 380-382.
[25] OAU,, Abuja, Nigeria: Organization of African Unity, 2001, pp. 1-7, http://www.un.org/ga/aids/pdf/abuja_ declaration.pdf.
[26] Amitav Acharya, “Human Security: East versus West?”, Singapore: Institute of Defence and Strategic Studies, 2001, pp. 2-9.
[27] UNDP,,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33.
[28] Thomaz Guedes da Costa, “Political Security, An Uncertain Concept with Expanding Concerns,” in Hans Günter Brauch, ed.,, Heidelberg: Springer, 2008, p. 561.
[29] M. Á. Pérez Martín,,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7, p. 108; Max Schott, “Human Security: International Discourses and Local Reality - Case of Mali,” in Hans Günter Brauch, ed.,, Heidelberg: Springer, 2009, p. 1113.
[30] Oz Hassan, “Political Security: from the 1990s to the Arab Spring,”, Vol. 21, No. 1, 2015, pp. 86-99.
[31] Derica Lambrechts and Lars B. Blomquist, “Political-security Risk in the Oil and Gas Industry: The Impact of Terrorism on Risk Management and Mitigation,”, Vol. 20, No. 10, 2017, pp. 1320-1321.
[32] 参见D. Lambrechts, C. Weldon and M. J. Boshoff, “Political Insecurity and the Extraction Industry in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 Moving towards an Industry Specific Political-Security Risk Analysis Mode,” in Gerrie Swart, ed.,, London: Adonis & Abbey, 2010, pp. 107-128。
[33] Barry Buzan and Lene Hansen, ed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7, pp. xxxv, xxxvii.
[34] Barry Buzan,, Sussex: Wheatsheaf Books, 1983, p. 28.
[35] Georg Sørensen, “Individual Security and National Security: The State Remains the Principal Problem,”, Vol. 27, No. 4, 1996, pp. 371-375.
[36] Barry Buzan, Ole Wæver and Jaap de Wilde,,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8, p. 141.
[37] Barry Buzan and Lene Hansen, ed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7, p. xxxviii.
[38] 文中所使用的国际语境下的“弱国”概念与通常中文语境中所谓“弱国”的概念并不相同,后者更偏向于“弱权”,而前者则源于巴里·布赞等学者的界定,强调包括执政、认同等多个维度之弱,并以“弱国(家)”的经典译名沿用至今。其只是在本文政治安全的背景下,更凸显政权之弱。
[39] Barry Buzan,, Sussex: Wheatsheaf Books, 1983, pp. 66-67.
[40] 其中,基础结构能力指国家机构执行基本任务和制定政策的能力;强制性能力指国家使用武力应付对其权威的挑战的能力;民族身份认同与社会向心力指民众认同民族国家,并在生活中接受其合法角色的程度。弱国至少在其中的“多数”维度上较弱。经验上则主要是三者皆弱和强制性能力尚可、而另外两者较弱两种。参见Richard Jackson, “Regime Security,” in Alan Collins, ed.,, 4th ed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 200-212; Caroline Thomas,, Boulder, Colo.: Lynne Rienner, 1987; Barry Buzan,, Harlow, United Kingdom: Prentice Hall Europe, 1991; Joel S. Migdal,,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41] 大体上有三种分法,一是将弱国大致对应于发展中世界或“非西方国家”,部分学者强调其中的威权主义国家,参见Yong-Pyo Hong,,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Inc., 2000, pp. 3-7; Curtis R. Ryan,, Gainesville, FL: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09, pp. 13, 26; M. Taylor Fravel, “Economic Growth, Regime Insecurity, and Military Strategy: Explaining the Rise of Noncombat Operations in China,”, Vol. 7, No. 3, 2011, p. 180;二是对应于冷战时的“第三世界”,认为弱国集中分布于非洲、西亚、中亚,包括南亚、东南亚的多数国家,也包括拉丁美洲国家,或“除美国、苏联、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欧洲国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外的所有国家”,或除以色列、古巴、中国、日本、越南、台湾地区、韩国以外的“亚非拉的所有国家”。参见Joel S. Migdal,,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269; Steven R. David, “Explaining Third World Alignment,”, Vol. 43, No. 2, 1991, p. 238; Barry Buzan and Ole Wæv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24, 104, 128, 252;三是采用“中心—边缘”分析,将弱国大致对应于有别于“中心”的“边缘”国家乃至一些“半边缘”国家,甚至包括冷战时的一些主要国家。参见Barry Buzan, “New Patterns of Global Securit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Vol. 67, No. 3, 1991, pp. 431-451; Barry Buzan,, Sussex: Wheatsheaf Books, 1983, p. 66。同时,几乎每一种分法都会列出一些例外情况,如史蒂文·戴维(Steven R. David)指出,“这些对第三世界的概括并不意味着所有第三世界国家都有同样的特征(将政权安全作为核心关切),不同的国家表现出不同的优势和劣势,这些概括也不仅仅适用于第三世界,正如1989年东欧政府倒台清楚表明的那样,第三世界以外的国家也面临着缺乏共识和合法性薄弱等问题”。见Steven R. David, “Explaining Third World Alignment,”, Vol. 43, No. 2, 1991, p. 242,这些都表明区别于已有分类的“弱国”类型学的独特价值。
[42] Barry Buzan, Ole Wæver and Jaap de Wilde,,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8, p. 152; Barry Buzan,, Harlow, United Kingdom: Prentice Hall Europe, 1991, pp. 99-103; Barry Buzan and Ole Wæv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24.
[43] Yong-Pyo Hong,,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Inc., 2000, p. 10.
[44] Mohammed Ayoob,, Boulder: Lynne Rienner, 1995, pp. 9, 15.
[45] Brian L. Job, ed.,, Boulder: Lynne Rienner, 1992, p. 15; M. Taylor Fravel, “Regime In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Explaining China’s Compromises in Territorial Disputes,”, Vol. 30, No. 2, 2005, p. 51; Mustafa Aydin and Sinem Acikmese, “Identity-based Security Threats in a Globalized World: Focus on Islam,” in Hans Günter Brauch, ed.,, Heidelberg: Springer, 2008, p. 416; Scott Wolford and Emily Hencken Ritter, “National Leaders, Political Security, and the Formation of Military Coalitions,”, Vol. 60, No. 3, 2016, pp. 540-551.
[46] Özlem Kaygusuz, “Authoritarian Neoliberalism and Regime Security in Turkey: Moving to an ‘Exceptional State’ under AKP,”, Vol. 23, No. 2, 2018, p. 285.
[47] Richard Jackson, “Regime Security,” in Alan Collins, ed.,, 4th ed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 201.
[48] M. Taylor Fravel, “Economic Growth, Regime Insecurity, and Military Strategy: Explaining the Rise of Noncombat Operations in China,”, Vol. 7, No. 3, 2011, p. 178.
[49] Takashi Inoguchi, “Political Security: Toward A Broader Conceptualization,”, Vol. 40, No. 2, 2003, p. 108.
[50] Roy Allison, “Virtual Regionalism, Regional Structures and Regime Security in Central Asia,”, Vol. 27, No. 2, 2008, pp. 185-202.
[51] Joe D. Hagan, “Regime, Political Opposition, and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oreign Policy,” in Charles F. Hermann, Jr., Charles W. Kegley and James N. Rosenau, eds.,, London: Routledge, 1987, p. 346.
[52] Brian L. Job, ed.,, Boulder: Lynne Rienner, 1992, p. 15.
[53] Gregory D. Koblentz, “Regime Security: A New Theory for Understanding the Proliferation of Chemical and Biological Weapons,”, Vol. 34, No. 3, 2013, pp. 505-507.
[54] Joel S. Migdal,,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269-277; Barry Buzan, “New Patterns of Global Securit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Vol. 67, No.3, 1991, pp. 439-440; Mohammed Ayoob, “The Security Problematic of The Third World,”, Vol. 43, No. 2, 1991, pp. 266-271; Georg Sørensen, “Individual Security and National Security: The State Remains the Principal Problem,”, Vol. 27, No. 4, 1996, pp. 377-378; Yong-Pyo Hong,,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Inc., 2000, pp. 3-7; Mohammed Ayoob, “Security in the Third World: The Worm About to Turn?” in Barry Buzan and Lene Hansen, ed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7, p. 325.
[55] 政治威胁可能是意图性的,也有可能是结构性的。结构性政治威胁是当两个国家的组织原则彼此矛盾,国家之间无法简单地忽略彼此的存在时兴起。无论它们愿意与否,它们的政治系统构成了一定程度的零和博弈。参见Barry Buzan,, Sussex: Wheatsheaf Books, 1983, p. 78。
[56] Takashi Inoguchi, “Political Security: Toward A Broader Conceptualization,”, Vol. 40, No. 2, 2003, p. 109; Nicole Ball,,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393.
[57] 参见Özlem Kaygusuz, “Authoritarian Neoliberalism and Regime Security in Turkey: Moving to An ‘Exceptional State’ under AKP,”, Vol. 23, No. 2, 2018, pp. 285-287, 297-298; Christos Boukalas, “No Exceptions: Authoritarian Statism, Agamben, Poulantzas and Homeland Security,”, Vol. 7, No. 1, 2014, p. 123。
[58] 学界以“不安全困境”指代此种特定的内部驱动的安全困境,以与国际关系中经典的“安全困境”相比较而存在。笔者以为,前者与后者的共性主要包括:维护自身安全的初衷导向彼此不安全的后果、不确定性导致做最坏打算、“螺旋式上升的恐惧”效应、对困境的应对导致困境的加深。特性主要包括:以弱国为背景和以政权为中心(主要为内部驱动)、关涉具备政治意义的次国家群体、聚焦政治生存和政治威胁(军事色彩相对较淡、认同色彩相对较浓)、安全边界更为模糊(相对于主权)、内外联动作用。概念的发展见诸布莱恩·乔布(Brian L. Job)、穆罕默德·阿约布、巴里·珀森(Barry R. Posen)、约翰·格伦(John Glenn)、斯蒂芬·赛德曼(Stephen M. Saideman)、保罗·罗(Paul Roe)和罗尼·利普舒茨(Ronnie Lipschutz)等人的相关著作,本文的理解有助于调和其内部的矛盾。
[59] Yong-Pyo Hong,,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Inc., 2000, p. 5.
[60] Nicole Ball,,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388-390; Andrew Goldsmith, “Policing Weak States: Citizen Safety and State Responsibility,”, Vol. 13, No. 1, 2003, p. 18.
[61] Sabine C. Carey, Michael P. Colaresi and Neil J. Mitchell, “Risk Mitigation, Regime Security, and Militias: Beyond Coup-proofing,”, Vol. 60, No. 1, 2016, pp. 59-72; Kate Meagher, “The Strength of Weak States? Non-State Security Forces and Hybrid Governance in Africa,”, Vol. 43, No. 5, 2012, pp. 1073-1101.
[62] Yong-Pyo Hong,,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Inc., 2000, p. 121.
[63] 庇护政治与强国常见的依附主义的区别,参见Francis Fukuyama,,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4, pp. 86-87。
[64] M. Taylor Fravel, “Economic Growth, Regime Insecurity, and Military Strategy: Explaining the Rise of Noncombat Operations in China,”, Vol. 7, No. 3, 2011, p. 179.
[65] Mohammed Ayoob, “The Security Problematic of the Third World,”, Vol. 43, No. 2, 1991, p. 274.
[66] Christopher Way and Jessica L. P. Weeks, “Making It Personal: Regime Type and Nuclear Proliferation,”, Vol. 58, No. 3, 2013, pp. 705-719.
[67] Jalil Roshandel,, Santa Barbara, California: Praeger, 2011, pp. 146-150.
[68] Roy Allison, “Virtual Regionalism, Regional Structures and Regime Security in Central Asia,”, Vol. 27, No. 2, 2008, pp. 185-202.
[69] Evarist Baimu and Kathryn Struman, “Amendment to the African Union’s Right to Intervene: A Shift from Human Security to Regime Security?”, Vol. 12, No. 2, 2003, pp. 37-45; AU,, Addis Ababa: African Union, 2003, p. 2, https://au.int/en/treaties/protocol-amendments-constitutive-act-african-union.
[70] Amitav Achaya,, London: Routledge, 2009, pp. 57-58.
[71] Danielle Beswick, “Peacekeeping, Regime Security and ‘African Solutions to African Problems’: Exploring Motivations for Rwanda’s Involvement in Darfur,”, Vol. 31, No. 5, 2010, pp. 739-754.
[72] M. Taylor Fravel, “Economic Growth, Regime Insecurity, and Military Strategy: Explaining the Rise of Noncombat Operations in China,”, Vol. 7, No. 3, 2011, pp. 177-190.
[73] Georg Sørensen, “Individual Security and National Security: The State Remains the Principal Problem,”, Vol. 27, No. 4, 1996, p. 379;Georg Sørensen, “After the Security Dilemma: The Challenges of Insecurity in Weak States and the Dilemma of Liberal Values,”, Vol. 38, No. 3, 2007, pp. 357-378.
[74] Georg Sørensen, “Individual Security and National Security: The State Remains the Principal Problem,”, Vol. 27, No. 4, 1996, pp. 383-385.
[75] Helen James,, London: Routledge, 2007, p. 2.
[76] Andreas Krieg,, Cham, Switzerland: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AG, 2017, pp. 5, 9, 133, 240.
[77] Kenneth Christie, “Regime Security and Human Rights in Southeast Asia,”, Vol. 43, No. 1, 1995, pp. 210-218; Amitav Acharya, “Human Security: East versus West?”, Singapore: Institute of Defence and Strategic Studies, 2001, pp. 1-18. 实际上,这两种安全要义的结合也是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面对经济危机时的主张,其原话便是“免于恐惧的自由永远与免于匮乏的自由相联结”,参见William F. Felice, “Introduction: A Study Guide to the Four Freedoms,” Carnegie Council for Ethics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September 28, 2005, https://www.carnegiecouncil.org/education/001/four_ freedoms/5221。
[78] John F. McEldowney, “Political security and democratic rights,”, Vol. 12, No. 5, 2005, pp. 780-781.
[79] Francis Fukuyama,,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4, p. 542.
[80] Ronald Weitzer, “In Search of Régime Security: Zimbabwe since Independence,”, Vol. 22, No .4, 1984, pp. 556-557.
[81] Barry Buzan, “Rethinking Security after the Cold War,”, Vol. 32, No. 5, 1997, p. 24.
[82] Mohammed Ayoob, “The Security Problematic of The Third World,”, Vol. 43, No. 2, 1991, p. 258.
[83] Takashi Inoguchi, “Political Security: Toward a Broader Conceptualization,”, Vol. 40, No. 2, 2003, p. 108.
[84] Gregory D. Koblentz, “Regime Security: A New Theory for Understanding the Proliferation of Chemical and Biological Weapons,”, Vol. 34, No. 3, 2013, p. 501.
[85] Mohammed Ayoob, “Perspectives from the Gulf: Regime Security or Regional Security?” in Donald Hugh McMillen, ed.,, London: MacMillan, 1984, p. 98.
[86] M. Taylor Fravel, “Economic Growth, Regime Insecurity, and Military Strategy: Explaining the Rise of Noncombat Operations in China,”, Vol. 7, No. 3, 2011, pp. 177-200.
[87] Donald Hugh McMillen, ed.,, London: MacMillan, 1984, p. 218.
[88] Mohammed Ayoob, “Perspectives from the Gulf: Regime Security or Regional Security?” in Donald Hugh McMillen, ed.,, London: MacMillan, 1984, pp. 93, 98.
[89] Peter J. Katzenstein and Nobuo Okawara, “Japan’s National Security: Structure, Norms, and Policies,” in Barry Buzan and Lene Hansen, ed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7, pp. 322-323.
[90] Joseph S. Nye, Jr.,, New York: PublicAffairs, 2011, pp. 81-109.
[91] Kingsley Edney, “Building National Cohesion and Domestic Legitimacy: A Regime Security Approach to Soft Power in China,”, Vol. 35, No. 3-4, 2015, pp. 261-263, 266-269.
[92] Gregory D. Koblentz, “Saddam Versus the Inspectors: the Impact of Regime Security on the Verification of Iraq’s WMD Disarmament,”, Vol. 41, No. 3, 2016, pp. 1-38.
[93] Gregory D. Koblentz, “Regime Security: A New Theory for Understanding the Proliferation of Chemical and Biological Weapons,”, Vol. 34, No. 3, 2013, pp. 501-525.
[94] He Kai and Feng Huiyun, “Leadership, Regime Security, and China’s Policy Toward Taiwan: Prospect Theory and Taiwan Crises,”, Vol. 22, No. 4, 2009, pp. 501-521.
[95] M. Taylor Fravel, “Regime In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Explaining China’s Compromises in Territorial Disputes,”, Vol. 30, No. 2, 2005, pp. 46-83.
[96] Steven R. David, “Explaining Third World Alignment,”, Vol. 43, No. 2, 1991, pp. 233-256.
[97] Stephen M. Walt,,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6-11, 17-26.
[98] Stephen M. Walt,,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17.
[99] Steven R. David, “Explaining Third World Alignment,”, Vol. 43, No. 2, 1991, p. 236.
[100] Curtis R. Ryan,, Gainesville, FL: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09, pp. 10-12.
[101] Scott Wolford and Emily Hencken Ritter, “National Leaders, Political Security, and the Formation of Military Coalitions,”, Vol. 60, No. 3, 2016, pp. 540-551.
[102] Roy Allison, “Virtual Regionalism, Regional Structures and Regime Security in Central Asia,”, Vol. 27, No. 2, 2008, pp. 185-202.
[103] Amitav Achaya,, London: Routledge, 2009, p. 34.
[104] 郑先武:《安全、合作与共同体:东南亚安全区域主义理论与实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31-232页。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一带一路’与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构建研究”(项目编号:17ZDA042)的研究成果。作者感谢《国际安全研究》匿名评审专家的审稿意见,文责自负。
D815.5
A
2095-574X(2020)04-0059-24
薛亮,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硕士研究生;郑先武,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 邮编:210023)。
10.14093/j.cnki.cn10-1132/d.2020.04.003
2019-07-29】
2019-09-24】
【责任编辑:谢 磊】
- 国际安全研究的其它文章
- 前沿生物技术发展的安全威胁:应对与展望*
- Abstra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