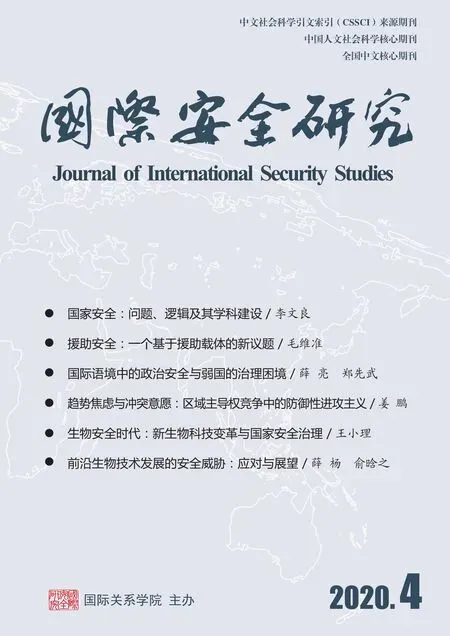前沿生物技术发展的安全威胁:应对与展望*
薛 杨 俞晗之
安全议题
前沿生物技术发展的安全威胁:应对与展望*
薛 杨 俞晗之
以基因编辑、基因驱动、合成生物学为代表的前沿生物技术正处于日新月异的飞速发展中,在医疗、农业等诸多领域为人类发展带来福祉的同时,也对国家乃至全人类的生物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在此背景下,世界大国在应对前沿生物技术安全威胁的几个共性问题值得重点关注:一是技术发展与技术安全的双重目标难以统筹;二是未知技术安全威胁导致不可避免的法律惩治效力滞后;三是监管的多部门合作需求与权职分工困境;四是多方利益主体参与的民主审议机制有待加强。由于中国前沿生物技术发展正处于从“跟跑”向“并跑”和部分领域“领跑”转变的关键节点,及时调整“促进”与“规制”前沿生物技术的应对措施已刻不容缓。前沿生物技术安全威胁的应对必须走到科技的前面去,对安全主体的规制更应走到科学的内部去。唯有在即将出台的国家《生物安全法》引领下全面推进生物技术安全的体制机制建设,逐步完善生物技术安全的法治体系建构,在政府主导下鼓励各利益相关方积极参与其中,才能确保前沿生物技术更好地造福于人民。
基因编辑;基因驱动;合成生物学;生物技术安全;生物武器;生物恐怖主义;生物实验室安全
以基因编辑、基因驱动、合成生物学为代表的前沿生物技术正处于飞速发展、日新月异的变革中,既能通过促进疾病诊疗和健康福祉来造福人类,也可能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造成威胁。由于涉及对人类自身的改造、对人类疾病的理解、对人类社会安全的影响,着手应对前沿生物技术所蕴涵的安全威胁并非像面对失控机器人“拔掉插头”般简单。1975年2月,著名的阿西洛马会议在美国召开,第一次面向基因工程潜在的生物危害及应对展开讨论;美国在1976年建立了世界首部生物技术研究安全管理规定《重组基因分子研究准则》,并由此拟订出确保基因工程安全的志愿性准则;英国等欧洲国家也相继通过国家立法开始面向生物技术的安全监管。[1]2001年九一一恐怖袭击和炭疽邮件事件后,美国及世界各国开始重视生物恐怖主义威胁。2003年10月,美国国家科学院研究理事会发布《恐怖主义时代生物技术研究》,首次将生物技术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视野。[2]2005年,英国科研资助机构开始关注前沿生物技术安全风险,包括医学研究理事会(MRC)、生物技术和生物科学研究理事会(BBSRC)召集生物学家、政府、资助机构及其他利益主体共同讨论如何对前沿生物技术安全实施监管,确立了独立的同行专家评审机制,以筛选涉及伦理、安全等问题的不端科研行为。[3]2011年9月,美国、荷兰科学家公开发表针对高致病性禽流感H5N1病毒基因改造的研究成果,在全球范围内引起广泛争议。[4]美国开始意识到国际社会针对前沿生物技术的监管存在重大缺失,随后几年,接连发布了多部监管政策,包括美国国家生物安全科学咨询委员会(NSABB)发布的《美国政府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监管政策》(2012年)、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OSTP)发布的《美国政府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机构监管政策》(2013年)[5]和美国政府颁布的《国家生物防御战略》(2018年),等等。
近五年的美国生物技术监管政策透露出某种微妙变化。首先,政府预判前沿生物技术被滥用或误用可能性在持续增加。美国国家科学院2018年发布《合成生物学时代的生物防御》报告,强调了合成生物技术被生物黑客制造用于恐怖活动“病毒武器”的威胁日趋迫近。其次,美国总统生物伦理咨询委员会和美国国家科学技术理事会先后发布《新方向——合成生物学和新兴技术的伦理问题》《美国国土生物防御领域科技能力评估》等报告,美国在强调生物技术风险管控的同时,实际上却对基因编辑、基因驱动、合成生物学等技术开绿灯。[6]这种看似割裂的应对策略凸显出“安全”与“发展”这一涉及国家重大战略的现实命题。在此背景下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包括:其一,前沿生物技术正在产生哪些生物安全威胁?其二,针对上述生物安全威胁,存在哪些已有的应对措施,又有什么样的难点与挑战?其三,中国亟须在哪些方面进行改进和完善,从而更好地应对前沿生物技术安全威胁?
一 引发生物安全威胁的前沿生物技术
前沿生物技术是指生物技术领域中具有前瞻性、先导性和探索性的重大技术。这类技术既代表着世界生物技术发展的前沿方向,也对未来生物医药产业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引领作用。近年来,前沿生物技术在基因编辑、基因驱动、合成生物学等领域探索的步伐加快,在造福于人类的同时,也增加了生物武器、生物恐怖主义、生物实验室安全等现实安全威胁。全球实践和国际经验表明,前沿生物技术引发的生物安全威胁,直接原因通常是防控措施的缺失,根本原因则是在内外部环境综合作用下多方主体行为的失控。[7]因此,厘清前沿生物技术安全威胁来源、技术类型及威胁的主体和方式,需要对生物技术安全防控形势进行分析与研判,也需要对生物技术安全应对策略进行阶段性总结。
(一)生物技术安全、前沿生物技术安全及其面临的威胁来源
第一,“生物安全”涉及以下八个方面:(1)防控重大新发突发传染病、动植物疫情;(2)研究、开发、应用生物技术;(3)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4)人类遗传资源与生物资源安全管理;(5)防范外来物种入侵和保护生物多样性;(6)应对微生物耐药;(7)防范生物恐怖袭击与防御生物武器威胁;(8)其他与生物安全相关的活动。其中,研究、开发、应用生物技术的安全问题即所谓“生物技术安全”,指的是国家核心利益和安全未受到通过科学和工程原理对生物进行认识、利用和改造的危害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8]作为生物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生物技术安全属于总体国家安全观下的非传统安全范畴。
第二,前沿生物技术安全是由生物技术领域中具有前瞻性、先导性和探索性的重大技术所引发特定的生物安全问题。与分子生物学发展之前的传统生物技术相比,前沿生物技术可称之为生物技术领域的“高技术核”。生物技术的“核爆炸”,既能给国民健康和社会经济带来变革性影响,也会产生技术性风险,即“人类在利用技术时违背技术自身规律以及技术发展初衷而产生的社会风险”。在传统生物技术风险评估策略与手段尚无法有效针对前沿生物技术特征的当下,前沿生物技术引发的生物安全威胁往往破坏性更强、杀伤力更大、蔓延范围更广。[9]
第三,生物技术安全面临的威胁来源大致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客观因素导致的非故意技术谬用。[10]其一,因技术缺陷导致的不良后果,尤其是因技术安全性、有效性未经严格验证就应用于人类临床而引发的危险;[11]其二,生物实验室安全事故对社会安全、人类健康造成的严重后果,包括在实验室试验、中间试验、环境释放和生产性试验等环节有意(无意)将各类遗传修饰生物体向环境释放造成的生物安全事故。[12]第二类是主观故意的技术滥用引致的生物安全威胁,目的就是要造成对人类社会的危害,后果往往是引起生物恐怖主义活动或生物战争。
(二)引发生物安全威胁的前沿生物技术主要类型
从近五年世界大国在生物科技领域的重要战略和政策布局来看,基因编辑、基因驱动、合成生物学等前沿生物技术,都给人类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带来了全新风险,值得我们高度关注。
第一,基因编辑技术及其形成的安全威胁。得益于CRISPR-Cas9基因敲除技术等一系列新型基因编辑技术的出现,基因编辑技术近年来在全球范围内发展迅猛,已成功实现对特定基因片段的精确剪切,在疾病治疗、遗传育种、生物工程等方面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13]目前,基因编辑技术的应用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基因功能研究,即通过基因敲除或者敲入,实现物种的单个或多个靶基因的敲除;[14]二是基因治疗,即通过基因编辑在基因水平上实现错误基因序列的矫正,彻底治愈遗传疾病;[15]三是基因调控,在不改变基因序列的情况下可逆抑制目的基因的表达;[16]四是生物防御,即针对入侵物种及其传播媒介物种进行基因编辑,抵抗大规模突发的物种入侵威胁。[17]
基因编辑面临非常显著的技术风险与安全威胁。一是目前尚无法完全保证基因编辑技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可能发生脱靶效应;二是关键技术信息公开化降低了技术门槛和关键实验材料获取愈发便捷等原因,导致走私、携带病原微生物菌毒种和生物两用设备的隐蔽性更强;三是最新型基因编辑技术可在短时间内完成对病原体、动植物甚至人类生物性状重大改变,且不留任何操作痕迹,甄别生物体是否发生基因编辑的难度加大;四是利用基因编辑技术和基因片段组装技术,在病毒序列原有的基础上增强病毒侵染力,组建致死率高、传染能力强、侵染宿主范围更广的新型病毒。[18]
第二,基因驱动技术形成的安全威胁。基因驱动技术是一种通过刺激特定基因的有偏向遗传,改变某些物种生殖能力,从而导致种群规模发生重大变化。[19]基因驱动技术的潜在应用领域广泛,例如,通过改变昆虫以及鼠类等啮齿动物群体的基因,切断相关传染病的传播源;又例如,在农业中防控农作物害虫,弱化其对杀虫剂等农药的抵抗力。
但基因驱动技术的风险同样不可小觑。在理论上,基因驱动技术可被用以降低人类生殖能力、改变人类特定种群数量。[20]同时,基因驱动技术还可能被用来制造昆虫武器,进行登革热、寨卡等疾病的跨国传播。近年来,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的生物科学家多次呼吁采取适当的生物安全防范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基因驱动技术对环境、动植物和人类健康的不确定风险。[21]
第三,合成生物技术及其形成的安全威胁。合成生物技术主要是基于合成生物学系统地采用工程手段、有目的地涉及人工生命体系,即“自下而上”地构建“最小基因组”或“自上而下”地合成“人工基因组”。[22]以基因合成为代表的合成生物技术在医学领域的应用前景广泛,通过改造人体自身细胞或改造细菌、病毒等合成出人工生命体,形成对疾病特异信号或人工信号、特异性靶向异常细胞以及病灶区域等的感知能力,从而实现对人体生理状态的监测以及对典型疾病的诊断与治疗。[23]人工生命体因其智能性、复杂性和安全可控性等优点,将提升人们对肿瘤、代谢疾病、耐药菌感染等顽疾的诊断、治疗和预防水平。[24]
然而,由于合成生物技术可在原有病毒或细菌基因组上任意增加生物毒性元件,形成了生物安全的新威胁。[25]通过合成生物技术对脊髓灰质炎病毒、天花病毒基因序列等进行人工设计,合成出高致病性细菌和病毒。[26]目前,通过基因合成技术已实现对“已灭绝”致病性病毒的“复活”。[27]2018年,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病毒学家戴维·埃文斯(David Evans)通过邮件订购的方式获得遗传基因片段,成功合成了类似天花病毒的马痘病毒。此外,人工改造生命体通常具有普通生物体所不具有的生存优势,一旦发生逃逸,有可能因无限增殖而破坏原有的自然生态平衡,导致生物多样性方面无法挽回的损失。[28]
除上述三类重点技术外,包括纳米生物学、神经科学等前沿生物技术都需要予以重点关注。特别是生物科技与互联网、高性能计算、人工智能和自动化等多学科技术交叉融合正在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前沿生物技术正在衍生出更多类型,可能引发的安全风险也日益加剧。如果任其无约束地发展,在可能造福人类的同时,也有可能摧毁人类的生存条件与社会秩序。
二 前沿生物技术引发的生物安全威胁
前沿生物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源于其多样化的风险属性,具有一定程度上的不可预见性,且涉及多方主体利益诉求的差异,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各类生物安全潜在威胁的形成。
(一)某些国家主体对传统生物武器的升级和颠覆
近年来,前沿生物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创新应用愈加广泛。基因编辑、基因驱动、合成基因技术先后被美国军方融入包括神经科学类新概念生物武器在内的新兴武器装备开发。例如,针对如何精确影响特定参战对象、生态微环境或者削弱受影响武器装备的性能,美国军方明确提出合成基因技术可将传统生物武器攻击范围扩大至包括“损毁橡胶和金属零件、降解燃料、食物及设备”等非生命物质。基因工程技术对微生物的改造被用于生产“材料损毁因子”,用以加速腐蚀武器的橡胶和金属零件,对军用燃料、军需补给、军事仪器设备实施破坏。[29]基因驱动技术可实现将传统生物武器投送载体从当前的“活性载体”扩展到“非活性载体”。基因编辑技术辅以高通量测序技术、光遗传学技术、生物大数据技术等新一代研究工具,可将对人类、动植物的关键核糖核酸(RNA)功能的破坏提升到前所未有的精细度,大幅提升未来军事生物科技操控手段,制造出更具有“针对性”的基因武器。[30]
(二)非国家行为体制造生物恐怖主义活动的可能
国际生物军控领域已将生物武器防扩散的重心,从传统的国家主体转移至非国家行为体上。涉及民族分裂分子、跨国犯罪组织、恐怖组织或邪教组织和以生物黑客为代表的新型生物技术制造主体,是生物恐怖威胁的主要来源。[31]这类非国家行为体更加隐秘,研究自由度更大且难以被监管,已经具有基因编辑操作平台等典型两用技术的应用能力,并成为在美国除尖端学术机构、企业、政府研究机构、独立实验室之外第五大生物类研究组织。如在《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第八次审议大会上,美国政府特别列举了肯尼亚、摩洛哥所报道的生物恐怖主义阴谋被相继挫败,以及美国近十年超过15起涉及生物武器的刑事案件,表达了对非国家行为体从事生物恐怖主义的担忧,强调在全球范围对生物恐怖主义进行防范的严峻性和迫切性。[32]
当前,非国家行为体之所以能够利用前沿生物技术制造生物恐怖主义活动,主要有两方面原因:第一,前沿生物技术门槛的日益降低。[33]随着关键基因序列信息的公开化,美国基因银行、英国欧洲分子生物学实验室、日本基因数据银行等网站每天进行基因组序列的全球信息共享与更新,从学术会议、期刊、公开数据库中可轻易获取高致病性病原体和病毒的关键基因序列。例如,目前涉及H5N1高致病性流感病毒、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病毒核酸序列的学术文章,已将生产、改造病毒并提升传播能力的方法公之于众。第二,包括基因序列在内的关键实验材料获取的便捷化。[34]当前,生物科技型企业可提供实验所需的全部技术服务和相关试剂。任何人都可通过网络订单方式轻易获取高致病性病原体或病毒的基因序列、实验设备、耗材及替代品,且成本逐年下降。
(三)生物实验室操作不当引发的安全威胁
近年来,全球范围内很多生物实验室已经突破了诸多前沿生物技术的操作“瓶颈”。首先,对高致病性细菌和病毒的设计与合成成为可能。[35]随着近十年来针对各种原核真核基因组的研究陆续取得突破,加之合成人类基因组国际计划的启动,目前生物实验室内人工设计合成SARS病毒等高致病性细菌和病毒已无任何技术障碍。其次,对生物性状重大改变的人工技术。[36]如基因编辑技术可短时间内在生物实验室完成对病原体、动植物甚至人类生物性状的重大改变;动物病原体种属屏障频被突破等导致新发和烈性传染病为人畜共患疾病的几率大幅度提升。最后,基因合成技术已可实现对“已灭绝”致病性病毒的“复活”,[37]不仅能够形成更高毒性和更强抗药性,同时还可能伴随出现某些前所未有的生物特性。
此外,温室效应、病原体自身进化等因素也大大提高了疫情预警、监测、诊断、溯源、药品研发等防控工作的难度。[38]人工合成病毒在感染能力、扩散能力、致死能力和逃逸能力等方面较天然病毒能力更强,对病毒溯源涉及的范围更广、难度更大,稍有不慎就会引发操作人员感染或病毒外泄,继而造成安全隐患。
三 应对前沿生物技术安全威胁的难点与挑战
在当下和可以预见的未来,前沿生物技术的发展必然会引发更多的安全威胁。
(一)技术发展与技术安全的双重目标难以统筹
大力发展前沿生物技术必将成为很多国家未来的重要战略目标,但与此同时,进一步保障技术安全也将是无法回避的重要议题。[39]如何在上述双重目标中寻求平衡将越发困难,如何统筹技术发展与技术安全,将是对各国以及国际社会政策决策者们的重大考验。
在国家层面,既要考虑生命科学进展对人类健康、科学发展和社会进步带来的益处,又要关注其一旦被用于有害目的而形成的风险以及可能给经济社会带来的严重后果;既要通过法治手段维护安全,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又要通过政策和法律鼓励科研攻关、产业创新,依法保障生物技术的进步。如何在生物技术领域更好地统筹安全与发展,已经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在国际层面,对于生物技术“两用性”(Dual Use)的识别和应对存在很大的灰色地带。一是对“两用性”存在多种不同的解释,诸如有益与有害、和平用途与非和平用途、民用与军用等;二是特指具备极高危险度的两用性研究被称为“值得关注的两用性研究”(Dual Use Research of Concern,简称DURC),但DURC如何识别?标准是什么?执行程序是什么?目前,全球缺乏统一且明确的界定标准和判定程序机制,由此引发了诸多国际军控履约困境。例如,前沿生物技术的“两用性”导致《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各缔约国对其他国家生物科技发展的意图难以研判,防御性和进攻性生物武器研发在加剧相互猜疑的同时,还迫使各缔约国基于潜在对手的能力不断加大自身研发投入,以预防潜在对手在生物技术和能力的不可预知性,进而形成国际间生物武器军备竞赛的恶性循环。[40]前沿生物技术本身很难严格按照“有益”或“有害”目的进行清晰划分,导致《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第一条以“和平用途”为目的的认定存在相当大的灰色地带。
(二)未知技术安全威胁导致不可避免的法律惩治效力滞后
由于当下的前沿生物技术发展仍然存在很多技术路径和后果的不确定性,科学界对于前沿生物技术的安全评估讨论只能建立在对未知可能发生风险的推测基础上。[41]例如,关于采用基因编辑技术对人类胚胎进行基因编辑的研究,科学家承认往往在被编辑的胚胎成活、发育、生存,甚至代际传递后,才能确定其是否存在风险以及风险与后果到底是什么。哪怕是经过科学界内部充分讨论、进行风险评估的前沿生物技术,其背后所蕴涵着对人类的威胁与风险只是目前尚不得知而已。因此,一旦出现相关法律纠纷案件,由于缺乏必要的司法认定因果关系而无法有效惩治,导致突破“红线”科研行为的有恃无恐。美国2007年伊利诺伊州乔尼基因治疗致死案、英国2016年网络贩卖蓖麻毒素的刑事诉讼以及中国2018年贺建魁“基因编辑婴儿事件”,都释放出了令人担心的信号:以政府为主体的单一监管模式,在面对前沿生物技术违规应用时失去了令人期待的惩治效力。
(三)前沿生物技术监管的多部门合作需求与权职分工困境
生物技术的特殊性决定了对其安全监管需要多部门协同开展,这就必然涉及各监管机构的权力职责分工问题。目前,美国涉及生物安全的管理部门包括国家卫生研究院、农业部、联邦环境保护局、食品药品管理局、职业安全与卫生管理局等,这些部门颁布了诸多法规、标准和指南。此外,美国还设立了诸如公共生物安全委员会、重组基因顾问委员会、国家科学顾问生物安全委员会、科技政策办公室等协调机构。但如何科学合理地确立各监管机构的权力分工,确保执行效力困扰着美国政府。类似的情况在中国也同样存在,中国涉及前沿生物技术安全监管的部门包括科学技术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等。然而,由于各个部门权力分散,同时缺少对国家生物安全实施统筹监管的机构,在实践环节暴露出多头管理、职责重叠、执行效力不强等问题。
(四)多方利益主体参与的民主审议机制有待加强
在应对前沿生物技术发展的安全威胁中,如何构建生物科学家、社会学家、产业界、媒体及公众等利益主体的民主审议机制,正在考验着各国决策者的管理智慧。
不同的利益主体对于前沿生物技术及其安全存在不同的理解和诉求。例如,参与政府相关法律政策制定的社会科学领域专家,往往从法学、伦理学、经济学、公共管理、风险防控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出发提供政策建议。但由于社会科学专家往往不具备相应的生物专业知识和生物安全监管经验,仅从其专业角度出发参与政策制定,产生了政策法规针对性不强的问题,易与一线科研工作脱节。而生物科学家群体,往往对于非本专业领域制定出的监管措施存在排斥与抵触,倾向于制定行业内部的自规范。从1975年阿西洛玛会议到2018年人类基因编辑国际峰会,都体现出这一倾向,引发了不同领域专家学者之间的激烈争议。因此在今后的政策制定过程中,需要构建涉及生物技术安全的“民主审议”机制,以平衡和协调生命科学与社会科学领域的观点与主张,深化彼此的信任与融合,兼顾各方利益以形成共识。
四 应对前沿生物技术发展的安全威胁:以美国为例
面对前沿生物技术引发的种种安全威胁,一些国家已经开始采取特定监管应对措施。本节对美国政府的应对措施进行梳理,分别从监管原则、监管体系、顶层设计与立法保障三个维度展开分析。
(一)监管原则:以“亲行原则”为主导
美国对前沿生物技术安全监管采取的是先行动起来,通过行动积累相关领域经验,以建立涉及安全、伦理等公共政策审查的技术性评估标准。为继续巩固其全球生物科技战略竞争的霸主地位,美国给予生物技术发展以优先级别,在强调国内生物安全源头管控的同时,却对基因编辑技术、基因驱动及合成生物学等前沿生物技术开了政策绿灯。例如,在处理合成生物学研究带来的“双重用途”争论时,美国总统生物伦理咨询委员会《新方向:合成生物学和新兴技术的伦理问题》报告指出,“由于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目前包括通过合成和操控基因而创造新物种的技术存在的风险极少。因此,没有必要暂时停止对有争议的新兴领域的研究,也没有必要对其施加新的控制。”[42]美国主张在对安全风险尚未得到科学权威确认之前,政府默认不使用过于苛刻的监管政策对前沿生物技术予以限制,在必要安全预测的前提下,首要保证的是科研创新的自由。[43]这与倡导“预防原则”的多数欧洲国家在应对策略上存在本质区别:“预防原则”强调,科学技术的不确定性不能成为推迟采取防止危害或威胁措施的理由;主张谁发展谁承担证明其无害的责任和义务。[44]多数欧洲国家坚持,如果某项生物技术成果存在尚未取得科学共识的可疑风险,就必须采取事先防范和谨慎态度加以监管。[45]而美国则认为,“预防原则”的运用将有可能阻碍新技术的发展与进步,将使政府决策部门在面对无法准确预知风险时容易陷入过于保守的政策倾向之中。美国主张,从人类技术发展的历史来看,所有革命性技术创新在其发展初期往往并不为人们完全理解与接受,一旦因噎废食,不仅会丧失巨大的应用前景和经济利益,还将在国际竞争中丧失技术主导地位。因此,当美国从“成本—收益”角度确认某项前沿生物技术具备巨大经济价值时,往往先于他国实施政策和资金方面的扶持,抢占该领域的技术制高点。
美国上述的风险防控思路符合英国哲学家马克斯·摩尔(Max More)于2004年提出的“亲行原则”(proactionary principle)。“亲行原则”是指决策者考虑技术活动的所有后果,部署预防的措施来应对实际的威胁,重视技术创新所能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也充分相信人类有能力去适应和补救技术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46]因此,该原则倡导不仅要对技术发展的“负面效应”进行事前预测与评估,更强调通过行动来学习。但美国所采取的“亲行原则”存在功能上的缺陷。[47]例如,先行动后学习的发展模式决定了美国监管经验的形成更多依赖对负面效应成因的因果关系解释,但前沿生物技术安全受到复杂的、综合的多因素共同作用的威胁,单一因果逻辑下的学习经验往往因缺乏系统性考量而无法适应事后的补救性实践。再如,美国采取“亲行原则”的前提是对技术“成本—收益”分析仅停留于单一经济价值的定量分析,而对前沿生物技术可能造成的威胁生命健康、侵犯人类尊严、冲击传统文化伦理等社会价值成本的考量有限。物质世界的有限性和地球生态的脆弱性决定了人类改造自然、改造人类本身的行为应当受到限制,政府有责任强化人类理性以约束技术能力的滥用和经济利益的非法获取。但在美国,资本力量推动下的“亲行原则”实践已暴露其维护社会价值方面的缺陷。
2月16日,由国家防办主办、水利部水文局承办的全国旱限水位(流量)确定工作研讨会议在江西南昌召开。通过旱限水位(流量)的制定,将首次建立全国江河湖库干旱预警指标体系,有力推动全国抗旱应急管理工作。
(二)监管体系:注重对技术“成果”的监管
第一,监管部门。美国政府于1986年公布的《生物技术管理协调框架》规定,由美国农业部、环境保护署、食品药品管理局负责对利用现代生物技术开发的产品进行评估,并对生物工程安全进行管理。[48]在此框架下美国生物技术安全监管由多个平行机构分工负责。[49]当《反恐与有效死亡刑法案》在1996年被通过后,美国农业部、美国健康和人类服务部负责认定和登记涉及危害国家安全的生物选择性制剂和毒素的名单,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下属的“联邦选择性制剂计划”(FSAP)对“生物选择性制剂和毒素的保存、使用和转移”进行监管,并根据《微生物和生物医药实验室的生物安全》(BMBL)对其能否获得科研资助和科研立项进行考核。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根据《涉及重组或合成核酸分子的研究指南》(简称《指南》)为操作重组或合成基因分子提供安全指导,任何涉及基因的实验必须经由国家卫生研究院批准、或经具有相应管辖权的联邦机构的审批方可进行,其下属的生物科技活动办公室对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所支持的境内和海外机构的研究活动进行生物安全政策的管理与评估。美国生物安全委员会(IBCs)负责处理涉及生物安全的事故上报。国家生物安全科学咨询委员会针对生物安保和生物技术两用性研究的关注,在国家卫生研究院《指南》下为美国政府提供相应政策建议。此外,在配套制度建设方面,美国环保局对“微生物实验室获得和保存微生物所需工作安全措施”进行监管;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下属的劳动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负责确保生物实验室雇员的教育、经验和培训达到相关要求;美国国家科学院通过发布《科学家之路:规范学术行为培养指南》等自律性文件对科学家行为进行规范。[50]
第二,监管模式。美国倾向于针对技术“成果”而非“技术”进行监管。首先,国家实验室的成果审批制度。美国针对不同等级的生物实验室实施分类管理,对国家实验室、P4级实验室实施最为严格的成果审批制度。以美国国家实验室为例,投稿之前须经所在单位技术主管和律师审核,审核周期至少为一周。其中,律师审核对研究方向和研究内容是否符合国家实验室的任务和要求,是否会对国家实验室带来负面影响进行评估。其次,根据研究经费来源实施研究成果的分类管控。如果经费来自国家卫生研究院或国家科学基金会等政府机构,对成果发表的限制往往较为严格;但经费属于自筹资金,或资金来自私人企业或组织,对成果发表的限制则相对宽松。最后,设立国家层面的咨询委员会对涉及敏感成果的发表实施具体指导。如美国国家生物安全科学顾问委员会,其职责之一就是为高等级实验室的两用性研究结果公开发表、交流与传播提供政策指导。此外,美国在强调“事前—事中”风险评估的基础上,特别重视“事后补救”的作用。[51]
第三,监管措施。首先,针对危险病原体监管实施分级管理制度。《微生物和生物医学实验室的生物安全》根据对人体的致死性、治疗可干预性以及感染性将生物制剂划分为四个风险等级,其中BSL1级风险最小,BSL4级风险最大。[52]其次,突发事故上报制度。根据美国《微生物和生物医学实验室的生物安全》规定,凡涉及操作BSL2以上等级病原体的生物实验室,一旦出现生物技术安全事故,必须立即向实验室主管人员上报。根据美国“联邦选择性制剂计划”规定,一旦发生生物制剂意外释放、遗失等突发事件,所在实验室必须立即向美国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动物和植物健康检查服务中心上报相关情况,并于7日内提交事故报告。
(三)顶层设计与立法保障:基于国家生物安全战略的“软法”建设
为支撑国家生物安全战略的实施,美国制定了一系列配套的准则、指南和规定等“软法”。1976年,美国发布的《重组基因分子研究准则》(简称《准则》),是其最早制定的有关生物技术研究安全管理规定,首次提出“生物安全”的概念, “为使病原微生物在实验室得到安全控制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53]《准则》规定,风险评估应考虑致病因素及其操作方法;在确定物理控制等级时,应考察包括毒力、感染剂量、传染性、传播途径、致病性、环境稳定性、是否具有治疗预防措施及基因产物的毒性、生理活性和致敏性等诸多要素。《准则》针对六种重组基因实验类型规定了不同的管理方法。《准则》分别规定了项目负责人、单位生物安全专员、生物安全委员会、国家卫生研究院重组基因咨询委员会和国家卫生研究院主任等的职责和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根据《准则》,任何涉及基因的生物实验必须经由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批准。针对那些使用高致病性、高致死性基因或毒素的基因重组性研究,国家卫生研究院出台《实验规制指南》予以规制。
作为一项行业准则的“软法”,尽管《重组基因分子研究准则》并不具备较强的法律效力,但其对整个行业起到了非常大的约束作用。在以《重组基因分子研究准则》为主体框架的基础上,美国先后在涉及生物技术安全的四个方面构建政策法规体系:一是面向实验室生物安全形成的《微生物和生物医学实验室生物安全手册》《美国生物实验室安全的操作指南》《加强实验室生物安全和生物安保下一步举措》等;二是面向菌种毒种运输保藏管理形成的《选择性制剂和毒素的保存、使用和转移》《关于潜在大流行病原体管理和监督审查机制的发展政策指南建议》等;三是面向生物操作管理形成的《美国实验室生物安全标准操作程序》《美国微生物实验室人员标准操作程序的培训指南》等;四是面向近年来引人关注的生物两用性研究出台了《生物安保和生物技术两用性研究的关注》《美国政府生命科学两用研究监管政策》《美国政府对生命科学两用研究的机构监管政策》。
自2001年起,美国开始着手构建其生物安全法治框架。小布什政府时期先后出台《公共卫生安全与生物恐怖准备与应对法》《21世纪生物防御》《公共卫生与医学准备预案》,在《21世纪生物防御》中明确了国家生物安全的战略地位,进一步突出生物技术在国家生物防御威胁评估、预防保护、监测检测、应对恢复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奥巴马政府时期,先后发布了《应对生物威胁国家战略》和《实现生物技术产品监管体系现代化备忘录》。前者强调通过强化全球生物技术安全合作和科学家负责任的行为准则以应对生物技术滥用引发的生物武器扩散、生物恐怖主义等威胁。[54]后者基于平衡科技型经济发展与健康环境维护的双重目标,在推动“生物技术产品安全监督管理体系”和“实验室生物安全安保管理体系”进程的同时,通过制度的形式将鼓励科研攻关、产业创新的政策固定下来,发挥监管体系在生物科技研究与转化应用中的护航作用。[55]特朗普政府于2018年9月和10月发布《国家生物防御战略》和《国家卫生安全战略实施计划2019~2022》。在这两项国家层级生物安全战略中,《国家生物防御战略》将生物技术蓄意谬用和偶然误用正式列入美国国家生物安全威胁之中,并寻求生物技术的持续发展以全面评估生物防御需求,持续监测国家生物防御战略的实施;《国家卫生安全战略实施计划2019~2022》则强调了微生物制剂的迅速获取、分发、发放、管理和安全监测工作。
美国应对生物安全的实践表明,由于相关配套“软法”的调整更灵活,更新成本更低,面向前沿生物技术不同类型的针对性更强,因此美国在该领域并不仅仅依靠制定传统法律法规等“硬法”,更多是通过国家层级战略政策的指引,构建一系列行业准则、指南和文件以适应技术进步的需求。
(四)美国应对前沿生物技术安全威胁的实践启示
第一,大国战略目标的必然选择。美国为巩固在全球生物科技战略竞争中的领先地位,给予前沿生物技术发展的优先级别,执行的是首要保证科研创新自由的“亲行原则”。被誉为“全球军事科技发展风向标”的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在2014年正式设立生物技术办公室,预示着生物科技将成为未来科技革命和大国博弈的战略制高点。[56]在前沿生物技术领域,谁先抢占技术先机和治理主动,谁就能在国际产业竞争新格局、全球产业经济大变局中占据主导地位。由于中国前沿生物技术发展正处于从“跟跑”向“并跑”和部分领域“领跑”转变的关键节点,按照“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的总体要求,[57]突出“预防原则”,对前沿生物技术采取引导和规范,在防治和减少可能出现的危害和损失的同时,尽可能地促进生物技术的快速发展。这是作为发展中国家和技术后发国家的中国在平衡“促进”与“规制”应对策略上的理性选择。
第二,抢占国际生物安全治理制高点。国际经验表明,一国如率先完成对某项新兴生物技术治理整合并得到国际社会的公认,将有助于其占据社会、法律、伦理和环境等方面的国际制高点。美国作为国际生物技术的头号强国,持续加强其生物技术安全立法规制和治理建设的目的,一方面强化内部法规体系和治理体系,另一方面对外营造“符合自身需求”的国际氛围,力图保持世界各国生物技术研发处于其认可的“良性”轨道。美国通过建立行业准则、标准和规范等系列“软法”,更有利于其政策的“输出”效应。
第三,各大国为应对前沿生物技术安全威胁,正在经历一个不断试错、充满不确定性的过程。其原因在于,前沿生物技术正在大踏步地持续前进,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对其可能引发的社会矛盾形成全景式的认识,其中蕴涵的某些风险与隐患也远未真正暴露出来。随着前沿生物技术力量的不断积聚,与固有监管体系之间必然还会产生更多不可避免的冲突,技术发展的不确定性也增加了监管难度。因此,各大国始终保持对生物科技变革前沿的感知,推进提升生物技术治理效能的体制机制建设;超前谋划以建立政策制高点,形成前沿生物技术领域国际治理规则的政策储备。
五 中国应对前沿生物技术安全威胁的对策建议
在以基因编辑、基因驱动、合成生物学为代表的前沿生物技术飞速发展之际,本文针对中国可能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对完善中国生物技术安全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提出如下建议。
(一)推进生物技术安全体制机制建设
第一,制定中国生物技术安全国家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建议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下设生物安全专门委员会与职能部门常规工作小组,形成党中央直接领导下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聚焦最近3~5年、着眼于未来20~30年,组织科技部、农业农村部、卫健委等相关部门共同编制面向生物技术安全的中长期战略。论证和制定基因编辑、基因驱动、合成生物学等两用生物技术发展规划,加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风险评估,积极抢占未来国际前沿生物技术的制高点。
第二,尽快完善中国生物技术安全监管体制机制。中国生物技术安全监管制度坚持以政府为主导,以公共安全为监管核心,通过强有力的手段予以规范,在平衡生物技术利益和风险之间关系的基础上,形成“管促结合”“可调可控”的动态管控机制。一是在现行国安办生物安全委员会协调管理机制之下,成立专门性的生物技术安全专家咨询委员会,对生物技术安全提供专家咨询与指导;二是建立各地方配套管理体系,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成立生物技术安全办公室(行政)及地方专家咨询委员会,形成从中央到地方的生物技术安全网络式管理体系。
第三,推动生物安全智库建设。从目前国际生物安全治理领域的趋势看,生物安全智库将成为未来在全球生物技术安全领域合作的探路者和催化剂,是健全全球生物技术安全合作的重要机制之一。美国已形成了大学、科研机构、企业和非政府组织等不同类型、不同侧重、不同层次的生物安全智库群。中国生物安全战略智库应在国际生物安全治理领域积极发出中国声音,系统介绍中国生物科学家的主张,不断推进与其他国家智库组织建立“生物技术安全二轨对话”机制。
第四,强化国家生物安全人民防线建设。随着生物安全事件的日趋增多,公民对生物安全的敏感度和关注度迅速提升。公民对国家生物安全防范的认可度,包括对生物技术安全的认知程度将影响其执行国家各项政策法规的自觉性,直接决定国家生物安全建设的最终成效。建议系统调研中国公众对生物技术安全的理解、认知、可接受性及相应的科普需求,重视中国生物科学家群体对公众认知和参与的建议,形成符合中国生物技术安全需求的科学传播路径,建立生物技术安全科普平台,在生物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方面形成常态化的沟通参与机制。
(二)推进生物技术安全法治体系建设
第一,遵循生物技术安全的法治原则。一是人民利益优先原则。明确生物技术必须以促进人民健康福祉为宗旨,综合考量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随时警惕可能出现的风险与危害。二是权责明晰原则。法律法规应对各级政府的生物安全监管权限和责任,作出清晰明确的具体规定,在操作运行方面做到无缝对接,不留死角和空白,同时各级政府监管机构必须具备通过技术手段对潜在风险进行监测与识别的能力。三是风险预防原则。它是绝大多数国家普遍采用的生物安全监管原则,是成本最低也是最为有效的管理原则,强调对建立科学发展安全风险评估的重要意义。[58]四是分级管理原则。根据安全风险等级的不同,对生物技术的风险评估、事故报告、科研诚信记录等采取有区别的监管对策。五是全程控制原则。将包括科研立项审批、研究实施、成果传播、科技普及、国际交流等环节的科学研发全周期、全过程都纳入监管范围。六是动态监管原则。根据前沿生物技术发展的特征和趋向,动态调整和完善监管的手段与措施。七是国际合作原则。国际生物安全面临着复杂的形势,中国应本着平等互利原则与各国开展广泛的沟通与合作。
第二,完善法律法规体系。根据生物技术内容和范围,中国生物技术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应由四个层次构成。第一个层次,具备统筹各种社会关系的统领性、基础性法律《生物安全法》,作为上位法对涉及生物安全的立法目的、基本原则、基本制度、管理体制、管理程序、违法责任等作出全面规定。第二个层次,由国务院颁布涉及生物技术安全的综合性管理条例以及《生物安全法》的实施细则,对生物技术安全监管作出全面、具体的规定。第三个层次,由国家科技主管部门在2017年《生物技术研究开发安全管理办法》的基础上,出台《生物技术研究开发安全管理条例》,以弥补前者缺乏必要惩治效力的不足。第四个层次,各省级政府通过地方立法出台相应的规定与措施。
第三,注重多方主体共同参与的“软法”体系建设。目前,中国的现行法律法规覆盖了实验室生物安全、病原微生物、基因工程和转基因、人类遗传资源与生物资源保护、伦理管理、两用物项和技术管控等六个领域,但在“软法”的建设方面仍有更大的发展空间。[59]前沿生物技术涉及科学家群体、科研机构与组织、学术期刊、产业界和公民等众多利益主体,完善对涉及生物安全、生物伦理的自我约束能力的“软法”体系,单纯依靠政府自上而下的发号施令绝非良策,唯有建立在利益相关方充分的对话协商基础之上。特别是要加强科学家群体的生物技术安全教育,提高风险意识,培育负责任的科研氛围,强调生物科学家自身的职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突出科学家群体对自我行为约束的主体性和自发性。因此,生物技术安全领域的指南、规范、准则等“软法”建设,在创制主体、制定程序、规则实施和规则遵守等各环节均将体现出更多刚性化、自律化精神。
(三)推进生物安全科技支撑能力建设
第一,明确前沿生物技术发展的优先方向和技术路线。首先,加大财政投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建成一批新的生物安全领域的国家级重点实验室。目前美国公开的P4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已达15个,P3级生物安全实验室达1 300多个,且包括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在内的数十家已接近P4级防护能力;而中国大陆地区已运行的只有武汉、哈尔滨两家P4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实力差距非常明显。其次,加大病原体溯源及传播监测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强化疫情预警能力。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近年来加大了对病原体进化规律、病毒传播规律、人与动物间潜在中间宿主形成规律三大方向的研发力度。建议中国在加强上述领域科研投入的同时,提前布局面向未来的人工合成病原体快速甄别技术。最后,根据《人间传染的病原微生物名录》中第一类危害等级的病原体,建立中国高致病性病原体数据库及风险直报系统,设立国家级科研专项面向因环境变化导致病原体致人患病的机理预测模型研究,全面提升旨在预测病原体暴发和疾病传播进程的科技防御能力。
第二,大力培育和扶持复合型人才队伍建设。培养瞄准国际前沿的基础研究人才、立足应用的技术创新人才、与产业密切对接的技术应用人才以及具备多学科知识背景的生物安全防控和监管人才。建议鼓励与生物技术领先国家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学习先进监管经验和做法,积累生物技术安全领域的典型案例和有价值的信息及数据,为维护国家生物安全发挥科技人才支撑作用。
第三,加强生物安全学科建设。生物安全是一个新兴交叉领域,配备既熟悉生物技术,又通晓国际规则的人才。中国从事生物安全领域战略研究和技术研究的人员配备还很匮乏,相关学科建设尚未形成体系。建议在高水平大学加快设立交叉领域的独立学科、设立研究生学位点、制订系统培训计划,培养生物安全领域专业人才;布局生物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聚合生命科学、计算机、风险管理、法律等学科的交叉研究,发挥应对生物安全的学科支撑作用。
六 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强调,要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尽快推动出台《生物安全法》,加快构建国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制度保障体系。这标志着中国对生物安全问题的重视提升到一个新的战略高度,也对提升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和生物安全法治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前沿生物技术为代表的生物技术安全是生物安全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前沿生物技术安全治理的前提是对技术发展与技术安全双重目标的统筹,它既关注和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又鼓励科技攻关和产业创新,依规依法保障前沿生物技术的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决定了中国完全能够做到统筹安全与发展,在提供人民健康福祉的同时,有效防止生物技术的滥用和利用生物技术获取非法经济利益的行为,为建设人类生物安全共同体作出重要贡献。在当前经济和技术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以完善自身生物安全治理体系、强化生物技术安全风险防控能力为基础,中国主动参与和推动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周边国家及世界公约组织的国际合作,在国际生物安全治理体系中发出中国的声音、体现中国的担当。
[1] 董时军:《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风险监管政策分析与启示》,军事医学科学院博士论文,2014 年,第4页。
[2]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Washington, D. C.: National Academies, 2004, pp. 12-14.
[3] Nation Research Council and National Academies of Science,, Washington, D. C.: National Academies, 2006, pp. 43-45.
[4]董时军、刁天喜:《高致病性禽流感H5NI病毒基因改造引发争议案例剖析》,载《军事医学》2014年第8期,第635页.
[5] 王磊、刁天喜、楼铁柱:《H5N1病毒基因改造及两用生物技术监管的进展与启示》,载《2012年度世界军事医学进展报告》2012年第121期,第103 页。
[6] 王小理:《展望2050年国防生物科技创新前景》,载《光明日报》2019 年2 月23 日,第7版。
[7] Edward B. Chuong, Nels Elde and Cédric Feschotte,‘‘Regulatory Activities of Transposable Elements: From Conflicts to Benefits,”, Vol. 18, No. 2, 2019, pp. 71-86.
[8]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Article 2: Use of Terms,” November 2006, https://www.cbd.int/convention/articles/default.shtml?a=cbd-02.
[9] Pamela Sankar and Mildred K. Cho, ‘‘Engineering Values into Genetic Engineering: A Proposed Analytic Framework for Scientific Social Responsibility,”, Vol. 15, No. 12, 2015, pp. 18-24.
[10] Huigang Liang, Xiaowei Xiang, Haixia Ma and Zhiming Yuan, ‘‘History of and Suggestions for China’s Biosafety Legislation,”, Vol. 1, No. 2, 2019, pp.134-139.
[11] David Maslove, Anisa Mnyusiwalla, Edward Mills, Jessie McGowan, Amir Attaran and Kumanan Wilson, ‘‘Barriers to the Effective Treatment and Prevention of Malaria in Africa: A Systematic Review of Qualitative Studies,”,Vol. 9, No. 1, 2009, p. 26.
[12] James Lavery, Paulina Tinadana, Thomas Scott, Laura Harrington, Janine Ramsey, Claudia Ytuarte-Nuñez and Anthony James, ‘‘Towards A Framework for Community Engagement in Global Health Research,”,Vol. 26, No. 6, 2010, pp. 279-283.
[13] Maria Patrão Neves and Christiane Druml, ‘‘Ethical Implications of Fighting Malaria with CRISPR/Cas9,’’, No. 3, 2017, pp. 1-2.
[14] Robert Unckless, Andrew Clark and Philipp Messer, ‘‘Evolution of Resistance against CRISPR/Cas9 Gene Drive,’’, Vol. 205, No. 2, 2017, pp. 827-841.
[15] Charleston Noble, Jason Olejarz, Kevin Esvelt, George Church and Martin Nowak, ‘‘Evolutionary Dynamics of CRISPR Gene Drives,’’, Vol. 3, No. 4, 2017, e1601964.
[16] Patrick Hsu,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s of CRISPR-Cas9 for Genome Engineering,’’, No. 157, 2014, pp. 1262-1278.
[17] Alison Hottes, Benjamin Rusek and Fran Sharples, eds.,, Washington D. C.: National Academies, 2011, pp. 133-136.
[18] Eric Lander, Françoise Baylis, Feng Zhang, Emmanuelle Charpentier and Paul Berg, ‘‘Adopt A Moratorium on Heritable Genome Editing,’’, Vol. 567, No. 7747, 2019, pp. 165-168.
[19] Kennth Oye, Kevin Esvelt, Evan Appleton, et al., “Regulating Gene Drives,”, Vol. 345, No. 6197, 2014, pp. 626-628.
[20] Kevin Esvelt, ‘‘Conservation Demands Safe Gene Drive,’’, Vol. 15, No. 11, 2017, e2003850.
[21] National Academies of Sciences, Engineering, and Medicine,, Washington, D. C.: National Academies, 2016.
[22] Arjun Bhutkar, ‘‘Synthetic Biology: Navigating the Challenges Ahead,”, Vol. 8, No. 2, 2005, pp. 19-29.
[23] Hans Bügl, John Danner, Robert Molinari, John Mulligan, Han-Oh Park, et al.,‘‘DNA Synthesis and Biological Security,”, Vol. 4, No. 25, 2007, pp. 627-629.
[24] Pamela Sankar and Mildred K. Cho,‘‘Engineering Values into Genetic Engineering: A Proposed Analytic Framework for Scientific Social Responsibility,”, Vol. 15, No. 12, 2015, pp. 18-24.
[25] Gigi Kwik Gronvall, ‘‘Safety, Security, and Serving the Public Interest in Synthetic Biology,”, No. 45, 2018, pp. 463-466.
[26] George Church, Michael Elowitz, Christina Smolke, Christopher Voigt and Ron Weiss, ‘‘Realizing the Potential of Synthetic Biology,”, Vol. 6, No. 15, 2014, pp. 289-294.
[27] Ryan Noyce, Seth Lederman and David Evans, “Construction of An Infectious Horsepox Virus Vaccine from Chemically Synthesized DNA Fragments,”, Vol. 13, No. 1, 2018, e01888453.
[28] Patrick Heavey, ‘‘Synthetic Biology Ethics: A Deontological Assessment,”, Vol. 27, No. 1, 2018, pp. 442-452.
[29]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rticle I: Reinforcing the Core Prohibition of the Biological Weapons Convention,” BWC/CONF.VIII/WP.14, October 2016.
[30] John Marshall and Omar S. Akbari, ‘‘Can CRISPR-Based Gene Drive Be Confined in the Wild? A Question for Molecular and Population Biology,’’, Vol. 13, No.2, 2018, pp. 424-430.
[31] Germany, “Strengthening 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 in Regard to Dual Use Materials,” BWC/CONF.VIII/PC/WP.35, August 2016.
[32]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cquisition and Use of Biological and Toxin Weapons: Addressing the Threat,” BWC/CONF.VIII/WP.19, November 2016.
[33] D. Ewen Cameron, C. J. Bashor and James J. Collins, ‘‘A Brief History of Synthetic Biology,’’, Vol. 12, No.2, 2014, pp. 381-390.
[34] Alec Nielsen and Christopher Voigt, ‘‘Deep Learning to Predict the Lab-of-origin of Engineered DNA,’’,Vol. 9, No. 1, 2018, p. 3135.
[35] Roberta Kwok,‘‘Five Hard Truths for Synthetic Biology,’’, Vol. 5, No. 463, 2010, pp. 288-290.
[36] Jennifer Kuzma and Zahra Meghani,‘‘Regulating Animals with Gene Drive Systems: Lessons from the Regulatory Assessment of A Genetically Engineered Mosquito,’’, Vol. 1, No. 5, 2018, pp. 203-222.
[37] Kevin Smith, ‘‘Synthetic Biology: A Utilitarian Perspective,”, Vol. 27, No. 1, 2013, pp. 12-14.
[38] B. M. Gandhi, ‘‘An Overview of the Advances Made in Biotechnology and Related BTWC Concerns,”, Vol. 4, No. 3, 2011, pp. 11-32.
[39]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February 2012, http://www.who.inVinfluenza/human_animal_imerface/mtgreport_h5n1.pdf.
[40] 张雁灵:《生物军控与履约:发展、挑战及应对》,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11年版,第151页。
[41] Leigh Dayton, ‘‘Dual Use Research: Australian Researchers Rattled by Export Control Law,’’, Vol. 339, No. 6125, 2013, p. 1263.
[42] National Human Genome Research Institute, “New Directions: The Ethics of Synthetic Biology and Emerging Technologies,” December 2013, http://bioethics.gov/sites/default/files/PCSBI- Synthetic-Biology-Report-12.16.10_0.pdf.
[43] Patrick Heavey, ‘‘Synthetic Biology Ethics: A Deontological Assessment,’’, Vol. 27, No. 8, 2013, pp. 442-452.
[44] Seumas Miller and Michael Selgelid, ‘‘Ethical and Philosophical Consideration of the Dual-use Dilemma in the Biological Sciences,”, Vol. 13, No. 4, 2007, pp. 523-580.
[45] Mylene Botbol-Baum, “Research Ethics: A Comprehensive Strategy on How to Minimize Research Misconduct and the Potential Misuse of Research in EU Funded,” March 2010, https//ftp.cordis.europa.eu/pub/fp7/docs/guidelines-on-misconducmaisuse-of-research_en.pdf.
[46] 龚超、王国豫:《纳米技术不确定性的应对路径与困境》,载《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第31页。
[47] J. Britt Holbrook and Adam Briggle, “Knowing and Acting the Precautionary and Proactionary Principles in Relation to Policy Making,”, Vol. 2, No. 5, 2013, pp. 15-37.
[48] John Kraemer and Lawrence Gostin, ‘‘Public Health and Biosecurity: The Limits of Government Regulation of Science,’’, Vol. 335, No. 6072, 2012, pp. 1047-1049.
[49] Margaret Somerville and Ronald M. Atlas, ‘‘Ethics: A Weapon to Counter Bioterrorism,”,Vol. 307, No. 5717, 2005, pp. 1881-1882.
[50] Brian Rappert, ‘‘The Benefits, Risks, and Threats of Biotechnology,”,Vol. 35, No. 1, 2008, pp. 37-43.
[51] 最直接的例子就是1999年美国亚利桑那州男孩杰西·格尔辛基(Jesse Gelsinger)由于基因治疗副作用死亡的事件,不仅促使美国政府彻查在用的基因治疗方案,也直接导致了对基因治疗临床试验的资本大幅度受限,可以被视为美国政府“事后”弥补性措施。
[52] 徐畅、杜然然等:《国外两用性生物技术研究监管现状与启示》,载《军事医学》2019年第3期,第217页。
[53], 1976, http://www4.od. nih.gov/oba/rac/guidelines/guidelines.html.
[54] Shay Weiss, Shmuel Yitzhaki and Shmuel Shapira, “Lessons to be Learned from Recent Biosafety Inci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Vol. 17, No. 5, 2015, pp. 269-273.
[55] Marko Ahteensuu, “Synthetic Biology, Genome Editing, and the Risk of Bioterrorism,”, Vol. 23, No. 6, 2017, pp. 1541-1546.
[56] 王小理:《展望2050年国防生物科技创新前景》,载《光明日报》2019年2月23日,第7版。
[57]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共产党员网,http://www.12371.cn/ 2017/10/27/ARTI1509103656574313.shtml。
[58] 孙佑海:《加快生物安全立法,全面提升生物安全治理能力》,载《光明日报》2020年2月22日,第7版。
[59] 中国生物技术发展中心:《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相关法律法规规章汇编》,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1-4页。
D815.5; E863
A
2095-574X(2020)04-0136-21
薛杨,天津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天津大学生物安全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天津 邮编:300072);俞晗之(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研究员,浙江大学“百人计划”入选者(杭州 邮编:310058)。
10.14093/j.cnki.cn10-1132/d.2020.04.006
2020-03-28】
2020-05-05】
*本文是2019年天津市科技发展战略研究计划项目(软科学研究项目)“合成生物学伦理框架与政策监管体系研究”(项目编号:19ZLZXZF00380)的阶段性成果。作者感谢《国际安全研究》三位匿名审稿专家的审阅意见,文责自负。
【责任编辑:谢 磊】
- 国际安全研究的其它文章
- 国际语境中的政治安全与弱国的治理困境*
- Abstra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