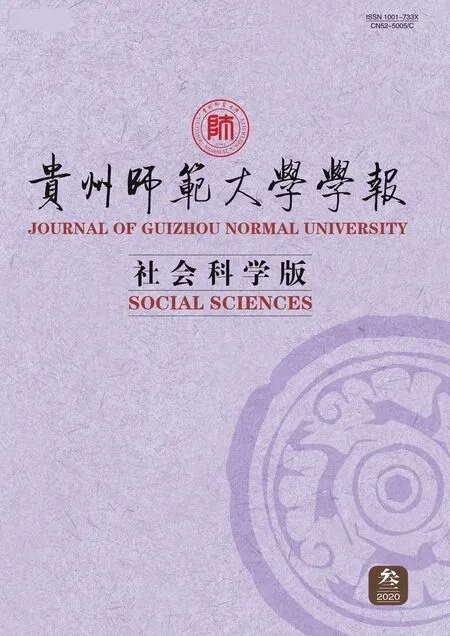反乌托邦小说之“反”的二重性论略
姜文振
(河北师范大学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24)
一
作为西方近现代科幻小说中的一个独特文类,反乌托邦(Dystopia / Anti-utopia)小说以对现代西方社会的政治、人性、社会结构、生活方式、文化生态、科技发展等方面问题的深刻省察与反思及其独特的书写方式,“将当今社会、政治和技术秩序中某些令人担忧的趋势投射到灾难性的未来极端状态”(Abrams 302),展示了可能出现的人类社会丑恶、可怕的前景,表达了对于传统乌托邦写作中那种理想社会的“否定”和“拒绝”,从而成为一系列足以引起人们警醒和反思的警世之作。其代表作有扎米亚京的《我们》(We,1921)、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Leonard Huxley)的《美丽新世界》(BraveNewWorld,1932)、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1984》(1984,1949)、威廉·戈尔丁(William Golding)的《蝇王》(Lordofflies,1954)、安·兰德(Ayn Rand)的《阿特拉斯耸耸肩》(AtlasShrugged,1957)、伯吉斯(Anthony Burgess)的《发条橙》(AClockworkOrange,1962)、艾拉·莱文(Ira Levin)的《这完美的一天》(ThisPerfectDay,1972)、厄休拉·勒古恩(Ursula Le Guin)《一无所有》(TheDispossessed,1974)、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的《使女的故事》(TheHandmaid'sTale,1985),等等,在近30年来更有多层面的拓展和泛化。
学界对于“反乌托邦”概念的使用以及对其对应的英文词汇有各种不同的认识和理解。与dystopia相关的常见概念有anti-utopia、cacotopia、kakotopia等(1)此外还有许多与dystopia同义反复或意义相近的词如utopian satire、reverse utopias、negative utopias、regressive utopias、non-utopias、satiric utopias、nasty utopias等,见Authur O.Lewis Jr.,"The Anti-Utopia Novel: Preliminary Notes and Checklist,Extrapolation": A Science-Fiction Newsletter 2,no.2 (May 1961): 27-32.。亦参见王建香.反乌托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其汉译词汇也有相应的“反乌托邦”“反面乌托邦”“恶托邦”“敌托邦”“废托邦”“坎坷邦”等诸多翻译方式,其中最常用的英文词汇是dystopia和anti-utopia,最常用的汉译词汇是“反乌托邦”“敌托邦”和“反面乌托邦”。这些概念之间有何内涵与外延上的差别?学界关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存在诸多分歧,在这些概念的使用及翻译上也异见纷呈。
围绕着“反乌托邦”“反面乌托邦”等汉译词及其外文词汇含义的诸多争议,表明这些概念、范畴本身所具有的模糊性、多义性或兼容性。在持续的讨论中,它们的含义似乎并未越辩越明、趋于统一。其实,即使是在西方学术界,人们在dystopia和anti-utopia及其他相关词汇的使用上亦未加刻意区分而常常并行使用(2)在《思考与界定:“反乌托邦”“恶托邦”小说名实之辩》中,王一平对于外文大型数据库EBSCO host系统全文网络数据库中dystopia和anti-utopia及相关词汇的使用情况进行了详细的比对分析,发现dystopia及相关用语的使用频率是anti-utopia的数倍乃至数十倍,并且该词覆盖面广,意义非常宽泛。见《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1):55-63。笔者曾利用美国爱荷华大学图书馆的论文检索系统进行简要调查分析,在检索系统中输入关键词dystopia或anti-utopia,其检索结果是基本相同的,远程校际图书馆文献检索亦复如此。虽然这只属于技术层面的检索系统设置,但查阅到的大量关涉到此类主题的专业文献本身都通常是在一种较宽泛意义上使用这两个关键词,着意强调二者的区别使用的文献数量极为有限(不完全统计,不超过5%),其研究对象也高度一致地指向那些经典反乌托邦作品。相对而言,美国当代反乌托邦文学及影视作品创作热度不减,在作品主题及类型上也极具多样性,“反乌托邦”的思想观念表达亦泛化而多元,批评界对这些作品的研究同样也往往在较宽泛意义上使用“反乌托邦”的概念。,在强调其与乌托邦(utopia)的对立性或关联性上也是比较一致的。当然,anti-utopia更强调它所呈现的想象性未来与传统的乌托邦作品所描绘的理想世界的对立意义,dystopia则更凸显了想象中的未来社会的黑暗、恐怖、糟糕、混乱;前者体现着其思想意蕴的“反乌托邦”特质,体现着对于传统乌托邦及现代性乌托邦的反思批判的致思方向,后者则主要呈现为作品的文学形象和具体描写,表明的是与乌托邦之“美好”相背反的乌托邦之“反面”特征。我们认为,anti-utopia意在揭示各种utopia的虚妄本质,体现着对于utopia的失望与不信任,而dystopia显然具有更为宽泛的意义,它不仅涵盖了一般的anti-utopia作品的思想内涵,更有貌似疏离乌托邦实则同样隐含的创作者乌托邦理想的意义呈现。因此,二者的重叠远远大于二者的差别,在很多情况下它们被视作无须分别的同义词。另外,我们还应看到,在文学批评实践中,人们并未对二者进行明确的区别使用,其典型表现便是:无论讨论dystopia还是讨论anti-utopia,无论使用的核心概念是“反乌托邦”还是“反面乌托邦”(或“敌托邦”、“恶托邦”),其批评的对象都是反乌托邦小说发展历史上的那些重要作品,诸如“反乌托邦三部曲”《我们》《美丽新世界》《1984》。
关于“反乌托邦”及“反乌托邦小说”之概念理解的异见与分歧,实际上意味着人们“反”的意涵以及所“反”对象的不同认识和阐释方式。我们认为,要厘清“反乌托邦(小说)”之“反”的意涵及对象,需要结合西方社会历史的进程与乌托邦文学的发展变化进行更为宏观的考察与分析。在《不完美的图像:反乌托邦时代的乌托邦想象》中,拉塞尔·雅各比曾写道:“历史不是由没有个性特征的世界精神(Weltgeist)组成的,而是由不可胜数的个体——作家、学者、政治家和普通大众所构成。如今,他们都或多或少达成了共识:乌托邦思想结束了。
16世纪赋予了我们一个崭新的概念——“乌托邦”(utopia),20世纪则赋予了我们另一个概念“敌托邦”(dystopia),或称之为反面乌托邦(negative utopia)。赫胥黎之《美丽的新世界》(Brave New World)和奥威尔之《1984》所呈现的世界,正是一个狂暴的乌托邦。也许这已经说明了一切。乌托邦向敌托邦转变,印证了历史。[1]伴随着反乌托邦小说以及其他各类反乌托邦艺术类型的繁盛,乌托邦思想及乌托邦写作似乎走向了终结。20世纪波诡云谲的社会历史文化变迁,使得任何完美幸福的社会理想设定都显得那样苍白乏力。考察从乌托邦到反乌托邦文学创作的这一演进历程,需要我们既关注文学发展自身的规律与路向,探察促成这一文学类型创作重心转换的内在而深刻的思想文化动因,又要将这些考察与探析置于20世纪复杂多变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之中,从而更为全面地阐释反乌托邦小说产生的深微复杂的社会文化机理。
二
1922年,美国历史学家乔·奥·赫茨勒(Joyce Oramel Hertzler)完成了他的社会学著作《乌托邦思想史》(The History of Utopian Thought)。此时的西方世界已经历了多次经济危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刚刚消散,但赫茨勒似乎并未丧失他对于未来的那种贝拉米式的乐观期待(3)1888年,爱德华·贝拉米出版了他的长篇小说《回顾:公元2000-1887年》。此时正是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发展的历史时期,尽管经济危机频现、贫富分化严重、各类社会问题广泛存在,美国社会整体上仍是处于上升期。贝拉米在《回顾》中虽然对于美国社会现实中的各种矛盾和弊病做了深入的反思和批判,但他总体上还是相信整个社会正在向好的方向快速发展。在《回顾》的后记中,贝拉米写道:“我写《回顾》一书持有这样的信念:黄金时代不是已经过去,而是在我们前头,并且也不遥远了。我们的孩子们无疑将会亲眼看见;而我们这些已经成年的男女,如果能以我们的信念和工作来做保证,也是可以看到的。”这种乐观主义倾向是19世纪欧美“拟乌托邦”小说创作所体现出的一种共同风格。:“更美好的东西就在前头……我们看到人类征服了天空和海底,我们已经能用无线电把信息送过海洋,在数百里以外就可以听音乐会,我们已经看到诸如麻风和破伤风之类可怕的疾病得到治疗,我们看到妖魔般地制造死亡和破坏(同样的智慧可用于建设性的用途)的机器的巨大进步,我们可以断言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做到的。”[2]赫茨勒的《乌托邦思想史》的出版颇具某种象征意味——似乎象征着乌托邦思想的破产和乌托邦文学的终结,因为在他这部自身就饱含着确定的乌托邦思想意味的总结性著作之后,随着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共产主义运动在欧亚大陆的不断深入、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进步和人的生活方式的深刻变化,特别是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那种表达着某种“无根据的乐观主义”(乔·奥·赫茨勒语)的乌托邦文本所能引起的关注度越来越低,即使再有人写出19世纪式的那种“乐观乌托邦”来,也几乎不再有多少反响。
“旧启蒙运动所树立的乐观进取的历史理念在残酷至极的世界大战的血泊中宣告终结。历史进步观、普遍历史观(法国大革命的信念)的瓦解,成为奥斯维辛之后西方思想的正常反应”[3]。人们在现实的加速发展和生活场景的快速切换中越来越深刻地体验到了未来的不确定性,反思意识、批判意识、危机意识甚至末世意识成为越来越多的西方知识分子思想探索的主题。在这样思想文化氛围中,在19世纪乌托邦写作与空想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实践热潮中就已经开始出现、迥异于传统乌托邦文学的另类乌托邦写作——反乌托邦小说迅速发展壮大并成为一股引人瞩目的西方文学创作潮流。
其实,就在赫茨勒完成他的《乌托邦思想史》的前一年,叶甫根尼·伊万诺维奇·扎米亚京就已经完成了他的反乌托邦小说、被列为“反乌托邦三部曲”之首的《我们》——这部作品在诸多的评论中都被认为是反乌托邦小说的奠基之作(4)关于“反乌托邦小说的奠基之作”有多种看法。在扎米亚京的《我们》之前,各种类型的早期反乌托邦作品就已经出现,例如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1823)、奥拓耶夫斯基的《无名城》(1839)、H.G.威尔斯的《时间机器》(1893)、《莫罗博士的岛》(1896)、瓦·勃留索夫的《南十字星共和国》(1905)、H.费德洛夫的《2217年的一个夜晚》(1906)、E.M.福斯特的《机器停转》(1909),等等——有学者称《南十字星共和国》为“反乌托邦小说的开山之作”。即使是那些常常被视为乌托邦的作品如萨缪尔·巴特勒的《埃瑞璜》、威廉·莫里斯的《乌有乡消息》等也带有鲜明的现代性批判的反乌托邦色彩。这些作品的存在,表明从反乌托邦小说的出现到反乌托邦小说兴盛为创作思潮经历了一个较长时间的渐变过程。。当然,这部著作在政治氛围浓厚的苏联显然没有出版的可能。1924年,《我们》的英文版在美国纽约出版,其后捷克语、法语版本相继出版,与此同时及以后,伴随着两次世界大战、冷战、核武器竞争及20世纪国际政治风云的波诡云谲,反乌托邦小说越来越多出现在人们的阅读视野。但《我们》的完整俄文版则于1952年方出版于纽约,1988年才获准在苏联出版。
反乌托邦小说的出现,标志着延续到20世纪的西方乌托邦文学写作范式开始呈现出一种迥异于传统的面貌,那就是与西方传统乌托邦文学对于未来的美好设想相背反,各种以未来社会的自由丧失、技术理性至上、人性异化、人类面临灭顶之灾的梦魇式书写大量出现。
这种文学写作范式的转换呈现着一系列主题、题材、文体、格调上的剧烈变化:从乐观、轻盈到悲观、沉重,从超越现实到强化、外化现实中隐含的变异倾向,从对未来充满信心到对未来充满恐惧,从准文学的未来筹划到富有文学性的未来黑暗图景描绘,从逐渐向现代性凝聚到对于现代性各层面的全面反思、批判甚至否定。
“在反乌托邦叙事中,科学、技术、进步、正义、自由、平等、理性等人们崇尚的现代性宏大叙事开始全面受到质疑和反思。由于其反乌托邦和反现代性的双重特征,西方社会和乌托邦小说中曾经引以为傲、奉为圭臬的现代性,在反乌托邦叙事中恰恰成了将人类带入永久黑暗甚至引入地狱的恶魔”[4]。尽管在传统的乌托邦写作中并不乏对于现实社会的讽刺、嘲笑甚至批判,但那些作品都还是对未来充满了坚定的信心和热切的瞩望、并对解决当下的现实问题提出了各种解决方法和途径的——尽管这些解决问题的方案大多过于理想化而难以在实践中具体实施。但是,19世纪以来新式乌托邦文学的未来书写大都以怀疑、批判乌托邦甚至反乌托邦的面目出现,以扎米亚京的《我们》、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奥威尔的《1984》等作品为代表的20世纪反乌托邦文学创作更是以一种激进的书写方式,表达了对传统乌托邦和近代以来的现代性建构方案的否定或不信任精神。在这些作品中,一种激进地切入当下社会文化的反思激情成为反乌托邦写作的基本情感底蕴。它们所描绘的社会往往让读者有一种切身体验甚至切肤之痛,往往带给读者亦真亦幻、亦虚亦实之感,在惊悚、震撼之余,激发读者对自身生存状况和社会发展前景的思考与忧虑,对盲目乐观主义和绝对的社会进化论保持应有的警惕。
反乌托邦小说在现代社会的出现是人类的幸事。它的种种反思与批判是在深刻体验乌托邦的矛盾与现代性的困境之后的一种毅然决然的救赎。反乌托邦小说确乎表达着对于未来的某种绝望和恐惧,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救赎的可能,人们也不能因此消解人类解放自已应有的乌托邦冲动。正如扎米亚京的《我们》末尾所描述的,尽管“我确信我们一定获胜”,但“西部街区仍然是一片混乱,哭叫声不绝于耳,尸横遍地,野兽出没,而且令人遗憾的是,为数不少的号民背叛了理性”[5]——这是一种暗示,它暗示着在看似绝望的未来图景中,仍然存留着反抗、超越与救赎的希望。
三
从上述讨论可见,反乌托邦小说之出现,其针对性是双重的:既针对历史悠久的乌托邦传统中内在地包含的矛盾与问题,又针对近代以来西方现代性在其建构过程中逐渐暴露出来的悖论与异变,由此构成了乌托邦、现代性与反乌托邦之间密切复杂的相互关系。
乌托邦与现代性之所以成为近代以来反乌托邦小说广泛的社会文化批判的共同靶标,源自二者相异、相通、相互纠缠并共同贯穿西方近现代历史的复杂而密切的关系。从知识学的层面考察可以看到,现代性与乌托邦具有相当鲜明的异质同构性,在其价值指标、主导原则、社会理想、政治经济体制设计乃至人的主体定位等方面,都既有诸多的相通、相似,又有明显的相异之处。
在西方近现代文明进程中,乌托邦与现代性因其相互之间诸多的相通、相似和相异之处而既相互对立又相互支撑,它们彼此成为对方的一部分,又彼此互相否定:空想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否定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现代性,认为私有制是万恶之源,追求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一切均衡平等;乌托邦强调人人遵循国家、集体道德规范而走向自我完善,否定现代性的根基即启蒙理性畸变为工具理性所导致的人性趋于自私的“恶”。与此相应的是,现代性强调个性自由、个人主义的价值目标,否定那种过于强调集体意志、集体主义而忽视、抹平个性差异的乌托邦;现代性追求现代民主政治,否定强调清明政治而寄希望于公正、清廉、智慧的最高领导人和正义的社会治理体系的乌托邦。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近现代乌托邦是“反现代性”的,西方现代性也是“反乌托邦”的。
但是,作为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文化近现代发展所孕育的两种现代社会构建理想与规划,现代性与乌托邦在很多方面是相通或重合的:它们都标志着一种乐观进取的理想主义,都相信人类社会不断改善、人性不断趋于完善的进步主义,都主张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解决人类与自然的矛盾、推动物质文明进步并进而推动精神文明不断发展,都郑重许诺将为未来的人类带来更为幸福完美的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乌托邦是现代性的,现代性也是乌托邦的。
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从《理想国》《乌托邦》《大洋国》到空想社会主义,形成了传统乌托邦的发展线索,其核心价值取向是公有制和集体主义,它强化管制,强调服从,包孕着多种反乌托邦的因子。启蒙运动之后,在启蒙理性的导引之下,逐渐发展出以“自由”“理性”为核心价值观的现代性乌托邦,现代性乌托邦实际上是对传统乌托邦那种均质化社会建构理想的反拨和否定。现实历史的发展表明,现代性乌托邦虽然将自由作为自己的核心价值指标,但它并未真正解决理性与自由自身所包含的矛盾与问题,在理性自身的发展中逐渐失衡,工具理性的无限抬升导致对于人的更为严酷的压制,对自由的追求反倒带来自由的丧失,而自由自身也因其难以取得一致的理论定位与价值认同而有可能被滥用,成为肆意满足一己之私、放纵挥洒个人欲望的漂亮借口。如果从作品的题材与主题方面进行考察,则可以明确地看到,反乌托邦小说直接地是针对现实社会的具体发展,外在的是对于传统乌托邦的种种规划设计的推演和戏仿,内在的则是对于传统乌托邦中隐含的现代乌托邦中的自由变异、科技僭越、工具理性极端化的反思与批判,由此延伸到更为深入的人性思考。
因此,反乌托邦小说之“反”具有鲜明的“反—乌托邦”与“反—现代性”的二重性,它以乌托邦和现代性为双重靶标,既与历史悠久的乌托邦写作一脉相承、有着强烈的互文性,又与19世纪以来聚讼纷纭的西方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相契合,表达着对于西方现代性的深刻反思与批判,从而凝聚了与乌托邦文学既相互悖逆又相互关联的独特思想意蕴。这种二重性意味着反乌托邦小说的主题命意是多元综合的,其价值指向也是辩证统一的。反乌托邦小说对乌托邦之“反”,“反”的是乌托邦蓝图设计的悖谬与不切实际以及它所包含的崇尚专权、抹平个性、片面强调技术的力量等内容或倾向,但并未因此全然否定乌托邦精神的必要性和乌托邦理想的合理性;反乌托邦小说对现代性之“反”,“反”的是现代性乌托邦自身所包含的悖论,包括启蒙理性向工具理性的收缩、自由价值观的异变、科技发展带来的更严酷的人的操控和科技伦理问题等等,但并未否定现代性所包含的理性、自由、平等、民主等核心价值指标,反而通过这些价值指标的反面呈现进一步强化了对于这些目标的执着追求。从这个意义上说,反乌托邦小说对乌托邦和现代性之“反”,从根本上是一种批判性反思。在每一部反乌托邦小说写作者那里,努力走出现代性的困境、摆脱乌托邦蓝图的虚妄、避免现代性建构和乌托邦追寻中的各种谬误和迷失,都是他们着力描写乌托邦的反面形态和未来社会阴暗前景的一个隐含动机。从这个意义上说,反乌托邦小说的潜在的核心命意既是乌托邦的,也是现代性的,它追求的是更“好”的乌托邦和更“合理”的现代性,体现着更为坚定执着的乌托邦精神。
四
反乌托邦小说所展示的激进、恐怖、令人绝望的未来图景正如一面镜子,映照出了“应然”的健全、合理的未来社会的反面镜像。“它们不仅仅是在构思,而且是在预言,其预言是建立在对诸如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当下各个领域的人文科学知识基础之上的”[6]。只不过在反乌托邦小说中,这种建立在当代社会实践与人文科学知识基础之上的“预言”是以“反方案”的方式表达的,恰如达科·苏恩文(Darko Suvin)所说:“所有的乌托邦小说都是反方案,反对坏的组织,反对作者身陷其中的道德混乱和(常常是)物质混乱,而反方案的实质必然是一种得到清晰阐明的拟换性秩序,它必须对拟换性的国家进行详尽的勘查。”[7]因此,与其说反乌托邦小说是“反”乌托邦的,不如说它反的是以科学技术僭越、政治与科技合谋为标志的“现代性的观念的专制”[8]65。反乌托邦否定的并不是自由、平等、科学、理性这些原则本身,而是担心人们的乌托邦实践可能会导致对这些原则的颠倒——民主异化为专制,科学导引出野蛮,理性蜕变为非理性。
由此可见,反乌托邦小说的兴起虽然源自深刻的现代性反思与批判,但其根基仍是对于现代性的看护与守望。如果深入考察从乌托邦到反乌托邦小说的主题转换,可以看到:乌托邦文学创作的主题经历了从古典乌托邦写作的理想瞩望,到近代乌托邦文学的现代性方案设计,再到20世纪反乌托邦小说对于现代性方案的反思和批判三个阶段。库马尔曾指出:“自1516年莫尔的《乌托邦》出版以来,乌托邦有着连续的历史。主要的乌托邦著作,如莫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1623)、安德里亚的《基督城》(1619)、培根的《新大西洲》(1627),在欧洲文学工作者中赢得了巨大声誉,为批判性评论与尊敬性模仿提供了主题。所有的乌托邦作者们都熟知这些伟大的著作,他们甚至还在霍尔(Hall)的《相同与不同的世界》(1605)或乔纳森·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1726)中看到了对之的挖苦或驳斥(这就给乌托邦传统增加了反乌托邦或敌托邦的内容)。到了20世纪,在贝拉米、莫里斯、威尔斯、赞亚丁(扎米亚京)、赫胥黎及奥威尔的乌托邦与反乌托邦中,我们仍旧可以看到近代早期伟大乌托邦著作及其系谱后裔的持续影响。”[9]可以说,西方乌托邦文学创作已经成为一种传统,包含着理想和愿景的乌托邦精神也已凝聚成为人类难以割舍的一种情结。尽管反乌托邦小说表达了对于传统乌托邦理想和现代性方案的反叛,在相当程度上引起了人们对于传统的乌托邦文学对未来社会的和谐美满的理想描绘的“拒绝”与“否定”,但是,反乌托邦小说仍然内在地熔铸着传统乌托邦文学的理想意蕴。
因此,“反面乌托邦富有政治寓言和政治讽刺小说的意味,但是绝不能简单地把它看成只是针对某一政体的政治讽刺小说。正如扎米亚京在1932年对《我们》的主题这样解释:‘目光短浅的评论家在这部作品中只看到政治讽刺,这当然是不对的。’其实,反面乌托邦所揭示的往往是现代性的一些根本原则所带来的恐怖和压迫的结果。他们所采取的方式是将‘现代性’的基本原则推到极致,从而使其自我暴露出它的虚妄和谬误。”[8]66反乌托邦小说即是以这种“反方案”的形式让人们从反面透视应然的、合理的社会建构方案。正如弗里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在评论《我们》时所说:“《我们》是一个真正的反乌托邦,但在其中,乌托邦冲动仍然在起作用。”[10]202反乌托邦小说熔铸着人们的乌托邦理想和愿景,是人类乌托邦精神的另类的形象表达。
在《科幻文学的批评与建构》中,弗里德里克·詹姆逊曾写道:“批判性的反面乌托邦是正常的乌托邦的否定性远亲,因为它的结果产生于某种关于人类可能性的肯定性概念,而它的政治立场则来自乌托邦理想。”[10]198每一部反乌托邦作品都有与之形成强烈互文关系的乌托邦“潜文本”,每一个反乌托邦小说作家都同时又是乌托邦的潜在书写者。当他们以各种激进的、讽刺的、寓言的、隐喻的、象征的方式描绘出一幅幅表达着对于未来可能出现的可怕的社会生活景象的恐惧与担忧时,一种作为创作思想与情感语境的潜在的乌托邦图景实际存在于其文学创构的现场。所有的反乌托邦小说都是一种关于未来社会或未来生活状态的“反方案”,这些“反方案”的言说似乎意味着“正方案”(如果可以这样表达的话)的“不在场”——它虽然并未呈现于作品的形象体系的现场,却“在场化”于作家的整个创作过程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的反乌托邦小说家,实际上本来都是乌托邦主义者。20世纪西方反乌托邦小说作为乌托邦文学在现代的一种逆向延伸,实际上正是以一种悖逆的方式展现着作家们对于当代社会科技与政治领域严重弊害的深切反思,以一种“反方案”的方式表达着作家们对于未来的筹划与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