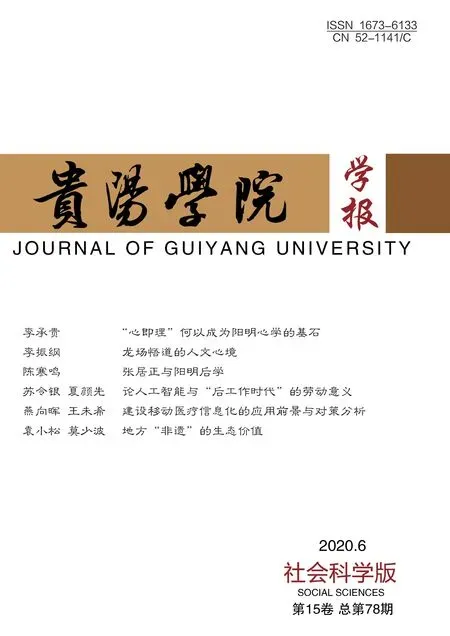冯友兰对《老子》宇宙观的解读
——以对第四十二章的阐释为中心
王金驰
(陕西师范大学 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冯友兰先生是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他同时对道家哲学也情有独钟,其中对《老子》的思想研究最具特色,表现为不同时期的不同解读。其中,以对第四十二章的解读最具代表性。《老子》第四十二章云: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1)通行本此章有两段,后一段为“人之所恶,惟孤、寡、不毂,而王公以为称。故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当以为教父。”陈鼓应等人疑其错简,今从之。参阅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12月第1版,第238页。
历来学者对此章的解释众说纷纭,冯先生对《老子》此章的解释,成体系的主要包括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以下简称《中哲史》),是以气化的宇宙论的方式解读。完成于抗战期间的《新原道》,以及1948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用英文写成的《中国哲学简史》(AShortHistoryofChinesePhilosophy,以下简称《简史》),是按照语言逻辑关系和本体论的方式解读。80年代后陆续出版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以下简称《新编》)、《三松堂自序》等,则主要延续“共相殊相”的逻辑式解读,同时又表现出对逻辑思维方法的反思和超越。
一、前期:“宇宙论”的解读方式
《中哲史》是冯友兰先生前期最重要的著作,上卷完成于1929年,下卷完成于1933年。冯先生晚年对自己这部书有一个积极的评价,他说:“它反映了当时中国学术界的一些问题、一种风气和一定的水平。除了它所讲的中国哲学的历史之外,它本身又是中国哲学史的一部史料。”[1]9-10并从史料的角度指出,自己晚年的《新编》并不能代替这部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二者都是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产物。在《中哲史》中,他以《庄子》解《老子》第四十二章,说:
《庄子·天下篇》云:“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庄子》卷十,页三十五)常无常有,道之两方面也。太一当即“道生一”之一,“天地万物生于有”,“有”或即“太一”乎?二者,天地也。三者,阴气、阳气、和气也。《庄子·田子方篇》曰:“至阴肃肃,至阳赫赫。肃肃出乎天,赫赫发乎地(天地二字,疑当互易)。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庄子》卷七,页三十三)即此意也。[1]189
可见,冯先生以“太一”释“一”:道有“常无”“常有”之两面,太一似偏就道“常有”一面而言;以天地释“二”;以阴气、阳气、和气释“三”。依据是《庄子》“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这里的“两者”是指阴阳,而阴阳又出乎天地,阴阳交通成“和气”。显然冯先生对“二”与“三”的解释,皆是从阴阳气化的角度出发的,太一、二(天、地)、三(阴、阳、和气)成一个平铺展开的相生关系。此种解读方式可归结为“阴阳气化”的宇宙论的解读模式。此模式盖始于《庄子》,至汉成一大传统,陈鼓应先生曾指出:“历来解《老》者,对于这一章的解释众说纷纭,但多用汉以后的观念作解。”[2]如《淮南子·天文训》篇说:“道曰规,始于一,一而不生,故分而为阴阳,阴阳合和而万物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3]134《淮南子》直接以阴、阳释“二”,其阴阳气化宇宙论的气氛更重。徐复观先生在《中国人性论史》中亦以“天地”释二,但他给出的理由是道创生天地在创生万物之先,他说:“因为中国传统的观念,天地可以说是一个时空的形式,所以持载万物的;故在程序上,天地应当生于万物之先,否则万物将无处安放。”[4]304徐复观的解释显然不是从阴阳气化的角度出发的,他明确反对以“阴阳”释“二”,说:“这种解释若是正确,原文何不干脆说‘一生阴阳’,而要说‘一生二’呢?”[4]302-303认为若以阴阳为创生万物的两个基本元素,则与后文“万物负阴而抱阳”冲突(2)徐复观说:“若仅就阴阳二气自身而言,则在层次上应居于万物的上位;不可言‘万物负阴而抱阳’,阴阳反在万物的下位。而成物以后,则阴阳已融入于万物之中,亦不可谓‘万物负阴而抱阳’;因为若果如此,则是阴阳与万物为二。”认为后文“万物负阴而抱阳”是形容万物生成以后的情形,并不能成为以“阴阳”释“二”的依据。参阅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九州出版社,2014年,第303页。。
冯友兰先生也注意到阴阳气化说的局限性,他在《新原道》中比较汉代《淮南子》与《老子》《庄子》不同时说:
在老庄哲学中,道、太一、无、有等名词,所表示底观念,都是形式底观念。但写《淮南鸿烈》底这些道家,都予以积极底解释。……此所谓道,似乎是先天地而有底一种原质。如此说,则道即是一物。[5]852
冯先生认为汉代道家受阴阳家的影响,关注“实际世界发生的程序”,这些实际的问题,“不是靠形式底观念及形式底命题所能讲底”[5]854。他们关于宇宙的生化问题的思考被拘于形象之内,是知识性的,而非哲学性的。此外,笔者认为 “阴阳合和而万物生”,似等于说阴阳相交而成的“和气”就是万物,那么“二生三”的三就成了次序或步骤上的三,而非具体三个构成万物的元素(阴、阳、和气)。这样“三”没有具体所指,就不能承担与万物的相生关系了。冯先生似乎也是从这一角度出发,在《新原道》中对前说予以了修正。
二、过渡时期:逻辑与本体论的解读方式
出版于抗战时期的《新原道》是对“旧作《中国哲学史》之补编也”[5]761。《新原道》对《老子》宇宙观的解读,集中在第四章“老庄”篇。冯先生一开始就着重谈论了《老子》中“有”“无”的问题,认为“有”“无”实则就是“有名”与“无名”的简称。他进一步指出:“‘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这两个命题,只是两个形式命题,不是两个积极命题。这两个命题,并不报告什么事实,对于实际也无所肯定。”[5]814这实则已经把问题导向“名言”的逻辑关系问题,关于第四十二章的解释,他说:
有就是一个有。《老子》又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四十二章)道所生之一,就是有。有道,有有,其数是二。有一有二,其数是三。此所谓一二三,都是形式底观念。这些观念,并不肯定一是什么,二是什么,三是什么。[5]815
可见此时冯友兰已经不从阴阳气化的宇宙论的角度进行诠释了,而是转为从语言逻辑上立论。他说:“万物之生,必有其最先生者,此所谓最先,不是时间上底最先,是逻辑上底最先。……《老子》说:‘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不一定是说,有一个时候只有无,没有有。然后于次一时间,有从无生出。这不过是说,若分析天地万物之有,则见必须先有有,然后,可有天地万物。”[5]814-815所以他认为一、二、三都是“形式底观念”,没有具体事实。二、三皆表示数量关系,由此也否定了以具体的“阴、阳、和气”释“三”的可能。相对《中哲史》的含糊,此时他对“一”进行了明确的回答,认为“一”就是“有”。当然,这个“有”是形式上的有,是万有逻辑上的最先者,与“道”“无”“一”同是超乎形象的。
冯友兰先生的这一观点在他的《简史》中得到了加强,但在逻辑之外,他又提出了“本体论”上的解释,他说:
“道”是“无名”,是“无”,是万物之所从生者。所有在是“有”之前必须有是“无”,由“无”生“有”。这里所说的属于本体论,不属于宇宙发生论。它与时间,与实际,没有关系。因为在时间中,在实际中,没有“有”,只有万有。[6]82
因为是从本体论的角度,道创生万物必然在时间之先,按冯先生的意思也可以说是在逻辑之先,冯先生的本体论是建立在逻辑之上的(下详)。在时间之内才有“一”“二”“三”及万物,所以冯友兰先生把一、二、三与万物归到了同一个层面,即“有”的层面,他说:“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也可能只是等于说万物生于‘有’。‘有’是‘一’,二和三是‘多’的开始。”[6]82也就是说,无论从逻辑出发,还是本体论出发,“一”“二”“三”都没有具体的所指。
其实早在魏晋时期,王弼已经从“有无”的名言关系和本体论的角度上来解释这一章,王弼注《老子》四十二章云:
万物万形,其归一也。何由致一?由于无也。由无乃一,一可谓无?已谓之一,岂得无言乎?有言有一,非二如何?有一有二,遂生乎三。从无之有,数尽乎斯,过此以往,非道之流。故万物之生,吾知其主,虽有万形,冲气一焉。[7]117
王弼认为“无”是道之名,当我们以“无”来指称道,就是有言,有言即是一。有了“无”的名,则有了一,有了一则有了“有”的名,“无”“有”之名立,则二生。二既生,则一加二为三。冯先生说:“经王弼的解释,道、无、有、一等观念,又只是形式底观念,不是积极底观念。有道,有一,等命题,又只是形式底命题,不是积极命题。”[5]868在王弼这里,“一”“二”“三”依然没有具体的所指。汤用彤先生亦曾说:“汉代寓天道于物理。魏晋黜天道而究本体,以寡御众,而归于玄极(王弼《易略例·明彖章》);忘象得意,而游于物外(《易略例·明象章》)。于是脱离汉代宇宙论(Cosmology or Cosmogony)而流连于存存本本之真(ontology or theory of being)。”[8]但实际上,王弼没有否定气的作用,多少还有宇宙论的影子。王弼认为“道之流”尽于“三”,似是说,道、一、二、三都是形而上的部分,从三以后万物已生,就属于阴阳合和的过程,即所谓“虽有万形,冲气一焉”,究其根本是以道为“其主”,是本体论与宇宙论不分。而冯友兰则从语言逻辑角度出发,只把道看作形而上的。
冯友兰先生从语言逻辑处立论,有其新实在论的哲学学术背景,同时更与他对《老子》一书成书时间的认定密切相关。冯先生认为《老子》后出于名家,《老子》对“名”的思考,是出于对名家的反动,他说:“道家经过名家对形象世界底批评,于有名之外,又说无名。无名是对着有名说底。他们对着有名说,可见他们是经过名家底。”[5]813值得注意的是,徐复观先生亦曾对此予以了反驳,他说:“《老子》一书,既常说‘无名’,便有人以为若非名家思想盛行之后,便不会出现反名家的‘无名’思想。”[4]300徐复观认为名与礼互为表里,“春秋是重礼的世纪,也是重名的世纪。礼发生了问题,名也发生了问题”[4]300,老子对名的反省实则与“礼”有关。因此徐复观也不赞成王弼的解释,他说:“王弼援《庄子·齐物论》的‘一与言为二,二与一为三’作解释,当然不适当。因为《齐物论》是表述‘道’与‘言’的关系;而此处则是表述创生的实际过程。”[4]302
三、后期:“共相与殊相”的解读方式
新中国成立以后,冯友兰先生希望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他在20世纪60年代曾出版过两册《中国哲学史新编》,后因为历史原因停作。为区别于80年代重写的《新编》,前者被合称为《中国哲学史新编试稿》(以下简称《试稿》)。在《试稿》中冯先生把《老子》的“道”与阿那克西曼德的本原概念——“无限”并论,认为两者都是否定的概念,并借用黑格尔对阿那克西曼德哲学的论说,来说明“道”的三种“规定”(3)冯友兰先生认为“道”作为一个否定概念,本身没有规定性,但也需要有一些规定性以说明它究竟是什么。参见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七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51页。:一是道不生不灭,为万物之宗;二是道对立统一;三是道具有连续性与无为性。其中第二条讲“对立统一”,就是对第四十二章的一种阐释,冯先生说:
第一个从“道”分化出来的就称为“一”。从“一”之中分出对立;这就是“一生二”。对立统一,与原来的对立,成为三;这就是“二生三”。……后来《淮南子》说:“道始于一,一而不生,故分而为阴阳,阴阳合和而万物生。”(《淮南子·天文训》)这就是《老子》四十二章的注解。[9]
这一解释似又回到了《淮南子》阴阳气化的宇宙论,但不同在于其出发点偏重于逻辑。逻辑的宇宙论与气化的宇宙论最根本的不同在于,前者的起点是语言“形式”,而后者的起点是“质料”。
冯友兰先生对《试稿》的不满有复杂的历史背景,按他在《新编》自序中的说法:“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要在长期生活、工作和斗争中锻炼出来的。专靠读几本书是不能懂得的,更不用说掌握和应用了。”[10]1认为自己前期的工作是“生搬硬套”“对对付付”,而《新编》则是在“生活、工作、斗争中学了一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完成的。但就《新编》整部书的哲学基础来说,并不溢出其新实在论的哲学学术路向。在《新编》中,冯友兰依然把《老子》宇宙观的有、无理解为了 “有名”“无名”,即他所说的“第三种说法”[10]330。他认为历来对《老子》宇宙观的解读不外乎三种说法,前两种说法分别是带有宗教性的说法和“有”生于“无”的说法。第二种说法相比于第一种说法有了“有”“无”的概念,韩非和淮南王都采用这种说法。而第三种说法始于王弼,按冯友兰先生的理解,第三种说法就是把“道”或“无”理解为共相[10]329-334。《老子》哲学的含混,就在于这三种说法它都有,这也影响人们对于第四二十章的理解。对此冯先生作了一个总结式的概括,他说:
对于《老子》的这几句话,可以作宇宙形成论的解释,也可以作本体论的解释。如果作宇宙形成论的解释,一,二,三都是确有所指的。……如果作本体论的解释,一,二,三都不是确有所指,不是什么具体的东西。……就《老子》第四十二章说,它大概是一种宇宙形成论的说法,因为它在下文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照下文所说的,一就是气,二就是阴阳二气,三就是阴阳二气之和气,这都是确有所指的,具体的东西。[10]335
虽然冯友兰认为宇宙生成论的解释更符合文本,但说到底《老子》没有很好地区分本体论与宇宙论。张岱年先生也曾指出:“老子的‘道’既是‘万物之母’,又是‘万物之宗’;‘道’是天地万物的根源,又是万物存在的依据。”[11]天地万物的根源即宇宙论,万物存在的依据即本体论。冯友兰已经不满足于这种模棱两可的解释了,因而站在“一般与特殊,共相与殊相”的立场对老子的宇宙观进行批判,他补充说:
《老子》所讲的道、有、无,都是一般,共相;它所讲的天地万物是特殊、殊相。……但是,它对于一般和特殊,共相和殊相的关系认识得不是很清楚,或者不是很正确。它的本体论的说法,还没有和宇宙形成论的说法划清界限。对于一般和特殊,共相和殊相的关系的正确认识,是一般寓于特殊之中,共相寓于殊相之中。但是,照《老子》的说法,好像是一般居于特殊之上,先于特殊,共相居于特殊之上,先于殊相。因此,一般和特殊,共相和殊相的关系就成了母子关系。[10]336
冯先生认为《老子》没有很好地区分“道、有、无”这样抽象的“有”与“天地万物”的“有”的区别,因而把“有”“无”理解成了“母子关系”,即“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四十章)的相生关系。但按冯先生的理解,这里的“有”“无”不应是相生关系,而是同一个共相的“异名同谓”。“异名同谓”本于《老子》首章:“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老子》第一章)冯友兰先生则赋予它“共相”的解释:
“有”是一个最概括的名,因为最概括,他就得是最抽象,它的外延是一切的事物,它的内涵是一切事物共同有的性质。事物所有的那些非共同有的性质,都得抽去。外延越大,内涵越少。“有”这个名的外延大至无可再大,它的内涵亦小至无可再小。……但是,没有一种仅只存在而没有任何其他规定性的东西,所以极端抽象的“有”,就成为“无”了。这就叫“异名同谓”。[10]332
按冯先生的理解“异名同谓”只能从共相角度进行理解,因为道、有、无是一回事,“不可以说‘道’是有、无的统一,也不可以说有、无是道的两个方面”[10]332。这里所说的极端抽象的“有”(无),等于冯先生《新理学》中的“大全”概念,“大全是一逻辑底观念,但其所指,却是万有之整个”[5]231,此时“大全”是天地万物的总名,是最大的类,是逻辑上的天。需要说明的是“大全”这个概念在不同时期,冯先生亦赋予了它不同的意义,他在《三松堂自序》中说:“《新理学》所讲的‘理’都是抽象的共相。《新原人》所讲的‘大全’是具体的共相,和《新理学》所讲的‘理’是不同的。”[12]298-299这与他后期对逻辑思维的反思有关。
四、反思
冯先生属于“新实在论”的哲学路向,他自述自己对哲学的兴趣始自对逻辑学的兴趣[12]305,“共相”“殊相”成了冯友兰思想中最重要的哲学范畴。他不仅用此解释道家哲学,亦用此来解释宋明理学的理气关系。如他说:
伊川所谓之理,略如希腊哲学中之概念或形式。以后道学中之理学一派,皆如此主张。[7]753
理即如希腊哲学中所说之形式(from),气即如希腊哲学所说之材(matter)也。[7]777
“新理学”的自然观的主要内容,是共相和殊相的关系的问题。共相就是一般,殊相就是特殊或个别。[12]275
总之,冯先生试图用西方形式与逻辑来诠释《老子》的宇宙观,似把《老子》的哲学限制在了认识论。他反思《新理学》中的抽象方法时说:“‘真际’是人的思维从‘实际’中用抽象的方法分析出来的,是有‘天地境界’的人的精神生活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关于认识的问题,并不是一个关于存在的问题。”[12]282-283在这种方法下,“共相”只是名言或概念,似不再与现实发生作用,而成为一种“纯思”,“‘纯思’就是纯粹的以共相为对象的思”[12]295。这般“纯思”至少会造成两方面的后果:第一,以西方形式与逻辑构建的形而上学,难免会陷于西方哲学唯名论与实在论之争的窠臼。他所说的“逻辑之天”(大全),既可以存在于自然之天前(实在论),也可以存在于自然之天后(唯名论)。第二,纯粹的认识论难以承担“价值”体系,王弼说:“《老子》之书,其几乎可一言而蔽之。噫!崇本息末而已矣。”[7]198中国哲学总是以“道德”“境界”之类的对宇宙人生终极意义的思考为归宿。客观认识体系与主体价值自觉间有一条不可逾越之鸿沟——如陆象山对朱子“即物穷理”的批评——总不免有支离之嫌。
关于第一点的反思:方东美先生曾比较《老子》的本体论与西方本体论之不同时说:“在希腊哲学里,巴门尼德与柏拉图将实有视为全部实在界的永恒形式,而无被贬低为最低级的幻觉。老子则总以无来指提升的道之本性,并构建了优先于关于变易的现象世界之有的动态本体论或超本体论体系。”[13]是将《老子》哲学中的“无”归为“超本体论”。从源头上看,逻辑学(logic)一词来源于逻各斯(logos),其最初的意思就是语言。在亚里士多德那里,逻辑学是探讨形而上学(是者)的语言工具。“是者”的哲学意义与系词“是”的逻辑功能密不可分。如他用语言逻辑对实体(ousia)进行说明:“实体,就其最真正的、第一性的、最确切的意义而言,乃是那个既不可以用来述说一个主体又不存在于一个主体里的东西。”[14]认为实体处于主词地位,其他属性依附于实体,处于谓词的地位。可以说由逻辑学建立起来的形而上学,不溢出可言说可思议的范围,是在巴门尼德规定的“是者”(toon)之内寻找“存在之为存在”的答案。而《老子》的哲学开篇就讲“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第一章),是在万有之上,继续向上向后,寻找世界的本根。道不仅超乎形象,且不落言诠,甚至不可思议。冯友兰先生从形式与逻辑出发,只抓住了“道”“无”超乎形象的一面,把“无”定义为最大的殊相(大全),实则是对《老子》“道”“无”本体意义的减杀。
关于第二点的反思:牟宗三先生曾指出:“西方的哲学从亚里士多德以来,一直是在这个表象的思想范围里面打转。”[15]27牟宗三先生把这些由概念、范畴揭示的普遍性称之为“抽象的普遍性”(abstract universality),是海德格尔讲的“表象的思想”(representative thought),认为“这种思想是不能进入存有论的堂奥的”[15]27。而中国哲学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佛家,揭示的是“具体的普遍性”(concrete universality),属于内容真理(intensional truth)。西方直到黑格尔才讲具体的普遍性(concrete universality),“具体的普遍”这个词就是黑格尔造的。牟先生顺着“具体的普遍性”的思路,认为道家的“无”是就着“无为”讲的,“无为”是一种超越的境界。他说:“从无为再普遍化,抽象化而提炼成‘无’。无首先当动词看,它所否定的就是有依待、虚伪、造作、外在、形式的东西,而往上反显出一个无为的境界来,这当然就要高一层。所以一开始,‘无’不是个存有论的概念(ontological concept),而是个实践、生活上的观念;这是个人生的问题,不是知解的形而上学之问题。”[15]72总之,他将道家的形而上学归结为“境界形态的形而上学”[15]87。
有意思的是,冯友兰先生对逻辑思维的反思亦跟黑格尔有关。他说自己真正懂得西方哲学是“真正认识到共相和殊相的区别以后”。他又说:“我认识到抽象和具体的分别以后,觉得眼界大开,心胸广阔。”[12]305-306这种区别即概念或共相与具体事物的区别。但认识并不能止步于此,他说:“既认识了这个分别,又要超过这个分别,上面所讲的黑格尔所说的‘具体的共相’就是超过了这个分别。‘超过’也是一种飞跃。不过这个飞跃是困难的。《新理学》就没有‘超过’,到《新原人》才‘超过’了,但我当时还没有自觉其‘超过’。”[12]307所谓“超过”,就是认识到“具体的共相”,并超越共相与殊相的区别。这与牟宗三所讲的“具体的普遍性”是一回事,冯先生亦指出:“中国哲学家的著作大都是从殊相讲到共相,从特殊讲到一般,从具体讲到抽象,西方哲学家的著作大都是从开始就讲一般,从共相到共相。”[12]305他在《三松堂自序》中对“具体的共相”有这样的一段表述,也可以视作他是对道家哲学“有”“无”的“共相殊相”问题的一个最终定论,他说:
“群有”就是一大群殊相,一大群具体的事物。寓于一大群殊相的就是“有”这个共相。“有”这个共相不可能是任何殊相,不可能是任何具体事物,……在理论上说,它可能是任何东西;在实际上说,它不可能是任何东西,它是不是任何东西的东西。可是实际上不可能有不是任何东西的东西,因此“有”又变成了“无”。在中国道家哲学的关于“有”“无”问题的纷争,大概是由此而起。如果把“有”了解为“群有”,“有”就是“群有”,“群有”是殊相,“有”这个共相就寓于这一群殊相之中,那就没有这样的纠纷了。不过照这样的了解,“有”这个共相就不是一个抽象的共相,而是一个具体的共相了。[12]298
冯先生这里所讲的一大群殊相的“有”变成为了“无”,相当于黑格尔《小逻辑》中所讲的“存有”与“无”,黑格尔说:“但这种纯有是纯粹的抽象,因此是绝对的否定。这种否定,直接地说来,也就是无。”[16]“纯有”(无)有别于“具体的共相”,但具体的“有”又寓于“群有”之中,“群有”就成了“具体的共相”。
五、超越
冯友兰先生在《新原人》中提出的“觉解”,以及由“觉解”而不断向上直至超越的四种人生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可以视作他试图超越逻辑思维,回归中国哲学对“价值”追求的传统。天地境界属于最高的境界,所谓“天地境界”,即从大全、理、道体或永恒形式的观点看事物而获得的一种全新意义,也即我们常说的“天人合一”境界,道家的天地境界即与道同一。冯友兰先生解释说:“在天地境界中底人的最高底造诣是,不但觉解其是大全的一部分,而且自同于大全。”[5]687在《新原人》中“大全”已经成为了一“具体的共相”,即冯先生认识到人对“大全”的认识虽来源于理智逻辑的分析,但它又超越于理智与逻辑,按他自己的话说“大全是不可思议底”[5]690。
人生境界之高底,与人对宇宙人生的“觉解”程度有关,冯先生认为“天地境界”是一种完全的“觉解”,“人必有最深底觉解,然后可有最高底境界”[5]689。所谓“觉解”即“了解”和“自觉”,人依靠经验对概念的理解就是了解,再进一步,经验与概念联合而有了意义,“得此种印证底人,对于此经验及名言即有一种豁然贯通底了解”[5]567,即所谓悟或觉,有“转识成智”的意味。觉或悟就是对意义的把握,而觉必自觉,是主体自觉其意义,“自觉是一种心理状态,它只是一种心理状态,所以并不依概念”[5]571。觉解的意义在于,“宇宙间底事物,本是无意义底,但有了觉解,则即有意义了”[5]57。由上可见,“觉解”包括了两种认识方法:逻辑分析的方法与直觉的方法(悟),这不同于《新理学》所讲的“纯思”。冯先生在《新知言》中将此称为“正的方法”与“负的方法”,“正底方法是以逻辑分析法讲形而上学。负底方法是讲形上学不能讲,讲形上学不能讲,亦是一种形上学的方法”[5]944。“负的方法”在《简史》中又被称为“神秘主义的方法”[6]275。冯先生说:“正的方法与负的方法并不是矛盾的,倒是相辅相成的。一个完全的形而上学系统,应当始于正的方法,而终于负的方法。如果它不终于负的方法,它就不能达到哲学的最后顶点。”[6]275“正的方法”是在语言、思维之内,用于可了解可思议者。“但同天的境界,却是不可了解底”[5]689,是 “所谓神秘主义底”[5]689,所以需要神秘主义的方法。“但不可思议者,仍须以思议得以之;不可了解者,仍须以了解了解之。以思议得之,然后知其不可思议底;以了解了解之,然后知其是不可了解底。”[5]690
总之冯先生希冀于人自身之“觉解”,并不断超越理性主义与神秘主义的界限,超越“共相”“殊相”的界限。完全觉解于之后,“就可以对于自然和社会持有一种正确的态度”[12]297-298。这种态度就是“知天”“事天”“乐天”,最后“自同于大全”[5]609。从这个角度看,冯先生把包括道家哲学在内的整个中国哲学的最高追求,归结到了境界形态。但说到底,这种“觉解”缺少中国哲学传统的工夫论,它依旧建立在逻辑思辨之上,在缺少工夫实践下,理性能否超越自身而达到他所讲的“天地境界”就很值得怀疑了。而神秘主义的方法又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天地境界”至多成了人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价值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