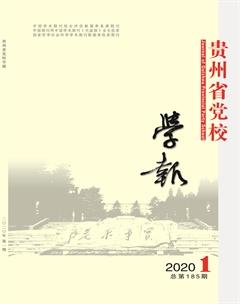现代乡村治理体系中传统治理因素和民族文化资源的融入
贺金瑞 龙立
摘要:云南罗平鲁布革乡腊者村在建构现代乡村治理体系过程中,在党的建设、市场经济组织和传统乡村治理力量中找到了结合点,把传统威权治理因素和传统文化融入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系,提升了社会治理能力。研究民族传统治理因素向现代治理体系转型,对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价值和有益启示。
关键词: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民族传统文化;传统威权
中图分类号:C95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81(2020)01-0011-05
2018年3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全国“两会”山东代表团审议时提出,“要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和公共文化建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深入挖掘优秀传统农耕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培育挖掘乡土文化人才,弘扬主旋律和社会正气,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改善农民精神风貌,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1]这是针对农业、农村和农民全面进步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的重要阐释,是对广大基层社会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新要求。云南罗平鲁布革乡腊者村在构建乡村治理体系过程中注重融入传统乡土文化、传统民俗乡风,使村民在乡土文化和民族文化资源发挥作用的背景下建立村民的乡村治理主导权,乡镇积极培育新型社会组织,动员村民参与乡村社会治理。在构建乡村治理体系中,村支“两委”主要是发揮好治理体系的协调保障作用,并通过调动积极因素共同承载乡村治理目标、改造乡村落后社会面貌等任务。
一、罗平鲁布革布依族苗族乡腊者村概况
云南罗平鲁布革布依族苗族乡位于滇黔桂三省结合部,辖9个村委会、58个自然村、100个村民小组,世居布依、苗、彝、汉四个民族,是云南省布依族人口最多的乡镇。
腊者布依族村坐落于美丽的多依河源头,号称多依源头第一村,处于山原地带,适宜种植玉米、水稻、豆类、芭蕉等农作物,农民收入以畜牧业、种植业、林业等为主,青壮年多半外出打工。因为毗邻多依河风景区和鲁布革电站,市场经济比较发达。为云南省30佳最具魅力村寨、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单位,被评为云南省生态乡镇、省级特色旅游小集镇,目前正在开展国家级生态乡镇、省级文明小城镇、省级园林城镇、省级平安乡镇的创建工作以及实施市级清洁乡村试点项目。全村人口526人,皆讲布依族语言,老人、妇女、小孩全部穿布依族传统服饰,是云南省布依族传统文化保留最为完整的村寨。
民国时期,由于国民政府政权组织的渗透能力有限,少数民族地区基本上还是传统的自治。新中国成立后,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权组织建设虽然滞后于汉族地区,但地处边远的云南、贵州等地的少数民族村寨也按照社会主义改造逐渐变成人民公社管理下的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乡村管理体制。“文革”期间,传统乡村文化资源和传统社会治理因素基本消失。与社会变迁相伴随,乡村村民在社会整体流动、个体生命历程的代际更替和价值取向方面也发生了变化。改革开放后,被压抑多年的民族传统文化逐渐得到恢复。在这个过程中,村民首先重视恢复象征民族传统文化承载者的威权文化,支持复活布依族长老和“寨老”在村寨生活中的影响力。当前,布依族的长老和“寨老”与村委会等力量同时在村寨治理中发挥作用,呈现国家政权组织与少数民族传统权威双轨并行体制。当然,在布依族村寨治理中起主导作用的仍然是代表国家政治体系的党支部和村委会。
二、在乡村治理体系中吸收“寨老”和长者
由于地理边缘、民族交融情况复杂,鲁布革乡从上世纪末叶开始构建覆盖三省交界的乡村治理体系。一是在鲁布革乡、马蚌乡、三江口镇联合成立滇黔桂跨省区联合党工委创新联动体系,形成“联合党工委—乡镇党委—党建和产业联动区,并下沉到行政村党支部—合作社党支部—专业党支部小组”,这是乡村基层党组织与产业发展融合的治理体系; 二是鲁布革乡镇党委和政府通过党建文化创新,把腊者村“寨老”和长者吸收进入乡村治理体系,成为乡镇党委、联合党工委党支部、合作社党支部、行政村各级会议的参与者。在乡村治理体系中吸收“寨老”和长者起到了积极作用:基层村民的民情和意见反映到上级政府,使政府掌握更多第一手信息和村民诉求;不仅如此,“寨老”和长者还协助村组干部传达国家政策。基层组织平时开会宣传国家政策时间大部分安排在布依族集体过传统节日时,在具有神圣性和仪式感的民族文化节日中,通过“寨老”、长者的威望和他们村民利益代言人的身份,协助政府贯彻政策,减少政策的执行阻力。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寨老”和村中长者的支持,很多政策难以推行。充分发挥“寨老”和长者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中上传民情和下达国家政策的中间人角色,还增强了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的权威性和有效性。
管理视界贺金瑞,龙立:现代乡村治理体系中传统治理因素和民族文化资源的融入腊者村的治理效能来自于治理体系不同层级的分工协作。(1)基层政权组织是治理体系指挥协调的核心。基层政权组织包括联合党工委、乡镇党委、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专业党支部小组、农民维权组织等,一杆插到底的基层政权是治理体系协调指挥中心。(2)治理体系中起“善治”效能的社会组织。治理体系发挥传统乡治的“寨老”和长者作用,与之配合的有乡村的家族组织、慈善组织,例如“爱心妈妈”“五老协会”等,这是治理体系发挥“善治”治理效能的重要组织。(3)充分利用蕴含在少数民族传统节日活动中的地标性文化。民族地方特别是乡村社会的传统乡土治理文化是一种重要的治理文化资源,是乡村的地标性文化,村民是坚定的守护者和传承者。乡土的地标文化蕴含着边疆乡村永续发展的地方知识和民族智慧,是边疆民族地方乡村振兴的重要历史遗产和文化创新资源。(4)利用现代经济技术社会组织。鲁布革乡有农村专业经济协会、农民经济合作社、各类村办企业、党建产业联动区等。现代经济技术社会组织与乡村地标文化的创造性融合,将为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提供持续的创新动力和品牌支持,为实现村民与传统文化和谐共生、建设传统宜居的乡村创造可靠的物质条件和文化灵感。比如腊者村布依族每家每户都有传统的织布机和纺纱机,妇女基本都会织布、刺绣,鲁布革乡政府为此成立了滇黔桂跨省区布依族刺绣合作社党支部,构建“支部+合作社+农户+客户”的运作模式,吸纳腊者村40多名妇女参加,党支部和村小组建立治理约束规范,由合作社统一购买布料、丝线发给社员做刺绣,实行统一生产、统一收购、统一价格和订单生产,目前38个国家和地区的游客纷纷前来订购,民族传统文化传承与市场经济发展相结合,实现了共同富裕。
民族地方的乡村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党建和产业联动至关重要。腊者村进行了“联合党工委—乡镇党委—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专业党支部小组”党建创新,党委政府和村党支部、村小组秉持的管理理念是“以保护为主,开发为辅”,实现开发与保护均衡,在保护好布依族传统文化的同时发展民族旅游业,留住村民建设家乡,也保留住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民族学者何明指出:“政府、民间组织和企业分别属于三种不同的组织类型,具有不同的组织目标和运作逻辑,对于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开发自然呈现出不同的召唤意识和话语诉求,从而使得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开发显现出复杂的文化色彩。调和与平衡三种组织取向冲突而达致良性互动,其关键路径是立足于民族文化本身及持有者,即于新文化语境中发掘民族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和存续意义,并获得文化持有者的认同和特定社会文化环境的认可,在开发、变迁中持续获得自我创生不断延续的激活力量。”[2]
在构建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系进程中,鲁布革乡腊者村传统乡村精英发挥治理功能主要体现在参与乡村社会治理、协调乡村社会关系、处理乡村社会公共事务、维护乡村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改革开放后,村民首先重视恢复象征民族传统文化承载者的威权文化,支持复活布依族长老和“寨老”在村寨生活中的影响力。当前,布依族的长老和“寨老”与村委会等力量同时在村寨治理中发挥作用,呈现国家政权组织与少数民族传统权威双轨并行体制,正如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所指出的:“社会的运行主要不是靠法律或者横暴权力,而是靠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长者威望来维系。”[3]由于腊者布依族世居于原生性的乡土社会,形成了稳定的宗亲关系,具有一定宗族意识,血缘和地缘关系重合联结起来形成宗族社会组织。有文化研究学者指出:即使在城镇化不断推进和人口流动频繁的当前背景下,只要是同姓同宗族的人与地缘重合,甚至只是同宗同姓的人通过现代传媒工具的联系和沟通,加之现实中一定实质性的接触,也会形成宗亲圈子。[4]腊者村通过发挥“寨老”和长者在乡村社会治理中的连接作用,在镇政府、市场与村民之间构建治理体系,加强政府与社会威权组织、基层党组织、市场合作组织以及村民等不同乡村治理主体之间的沟通与对话,克服乡土熟人社会隔膜的弊端,协调政府与村民之间的关系,建立深厚的社会资本和信任感。腊者村的民间纠纷如果是发生在家族内部,一般是请家族内长者进行调解,家族内部传统认为如果纠纷传到家族外会被其他家族笑话;如果发生的是邻里矛盾冲突,则按照《村规民约》及习惯法,由村组长主持,邀请正直无私的“寨老”进行调解,村寨里的矛盾纠纷很少闹到村外或者乡镇一级调解,一般也很少通过法律途径解决,这在很大程度上节约了国家的司法成本。犹如辜鸿铭老先生曾说:在中国,“一般的纠纷,依据礼义廉耻就可以解决,所以警察用不着那么多。在这一点上,是值得欧洲人好好学习的”[5]。我国实行村民自治制度已有多年,但乡镇政府行政权力与村民的自治空间缺乏协调力量,乡村社会传统威权力量恰好弥补了这一缺失,有利于乡村社会自治空间的拓展,有利于乡村社会治理方式的创新,有利于对原有乡村治理结构的突破,从而构建新型的乡村治理体系。
三、现代乡村治理体系以民族传统文化为底色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鲁布革乡腊者村的治理体系注重以民族传统文化为底色,逐渐取得明显成效。具体做法有:(1)治理体系坚持布依族长者主持制定的村规民约,广泛开展“晒晒我家好传统”等家风、家训活动。在乡党委和政府指导下,腊者村依靠布依族德高望重的长者主持或参与制定一系列村规民约,通过发动长辈口述、家人共议,村民积极参与,征集大量布依族家规、家训和谚语,制定的乡规民约经过乡政府文明办审核后村民自主执行。(2)乡规民约由“寨老”参与的村民理事会监督执行。村寨注重监督完善治理体系,不仅注意将好的家风家训通过总结融入村规民约,还实行由全体成年村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由“寨老”参与的村民理事会监督执行,很多时候都是在家族祭祖、结婚仪式、村社祭祀寨神等特殊场合由“寨老”宣布,从而增加了神圣性和仪式感。诚如马凌诺斯基所言,“一切文化要素一定都是在活动着,发生作用,而且是有效的”[6]。鲁布革乡腊者村的治理体系通过依靠布依族“寨老”和长者监督,对村寨秩序认同和文明风尚的维护已经养成了自觉执行的习惯,这些年村寨很少发生偷盗、坑蒙拐骗等现象,村民如果不遵守和维护民族传统文化必然受到冷遇甚至孤立,这种人家里有了红白喜事都没有人去帮忙,在村民中抬不起头。(3)治理体系注重布依族传统文化的延续和治理因素的融合。腊者村布依族传统文化延续比较完整,村寨里的各种文化活动具有鲜明的基层社会治理因素。全村寨的人经常集体过传统节日,以此增进村民交流,培养民族感情,传承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增强村民民族认同感与凝聚力。如腊者村绝大部分布依族村民家庭有供奉祖先和村落保护神的传统习俗,村民家庭的堂屋左右两面,一面供奉村落的传统保护神灵——“绵蛙”,另一面供奉祖先——“中央”。“绵蛙”和“中央”都是用一尺见方的木板做成,经过“毕摩”主持仪式请回家置放。家庭供奉寓意消灾解难,村民相信供奉象征“上天”的神看着,谁干坏事都将受到惩罚,这对村民心灵有自我净化和约束作用,这也是腊者村民风淳朴的由来。(4)腊者村把延续下来的传统“长者议事会”转化形成社会治理元素。直到解放前夕,腊者布依村寨都依靠自治,由深受村民支持的“家族议事会”“长者议事会”进行社会调节。村寨里对家族有威望的年长者女的稱“报啊”,男的称“雅老”,[7]家族内发生纠纷,首先由“家族议事会”处理,很少直接走法律途径,避免被其他家族耻笑。处理过程主要由当事者各自向长者陈述事由,长者按照习惯和传统明辨是非曲直,提出处理意见。由于议事会一般都秉公处理,很少有人反对,否则,当事者将受到全族人的谴责和孤立,所以执行力很强。
四、布依族民族传统文化融入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系启示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不会因为现代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而消失,而是依然具有巨大的价值。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不一定要保持封闭,可以在汉族包围的地区建立一个与外界不同的社区共同体,通过这个共同体,可以传承和保留自己的传统文化。腊者村虽地处交通和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但其做法证实了传统文化在现代乡村治理体系中有着重要价值。
现在,民族传统社会权威由于时代的变迁和经济基础的变化已经失去了历史上乡村社会治理的强大合法性,也没有过去那么大的约束力,但并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将来也不应该退出。在改革开放背景下,国家与社会逐渐分离,国家基层组织现代行政权力与民族传统权威将在民族村社长期处于一个并存和互动维系村寨公共生活的状态,民族乡村社会秩序的良好运行和维护是多元权威互动和影响的结果。现实中,国家政治的权威和少数民族的传统社会权威并不是针锋相对的零和博弈,只要政府加以正确的引导和应用,可以为乡村社会的和谐稳定提供坚实的辅助和支持,同时也“极有可能成为中国乡土社会多元权利主张形成和发展的契机,进而从不同方面制约长期处于一元化状态下的国家权力”[8]。当前,在少数民族地区基层社会借助传统权威的影响力维持社会秩序的良好运行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现代化不是与传统彻底分离,也不是对立,而是在对历史的继承和保留的基础上进行创新的结果。诚如马克思所说:“人类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他们自己不能选择创造的条件,而是只能在直接面对的、已成事实的、从过去传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那些已经离去先辈们创造的传统,依然根深蒂固地埋藏在现世人的头脑中。”[9]对于这些少数民族传统社会权威和民族文化的复兴,政府不仅没有必要过度的警惕或进行压制,而应当予以支持和推广,将少数民族权威融入国家基层社会治理体系,调适少数民族传统权威和国家政治体系权威。如周星所言,“各族人民既生活在统一的国家政治体系与政治运营之下,又同时不等地生活在他们本民族的政治生活之中”[10]。
在现代化转型期,政府对民间社会控制能力减弱,建立民族社区的社会治理体系以弥补相应的“权力真空”就尤为重要。“寨老”等民族传统权威对地方社会秩序和权力平衡起到重要作用,而民族传统文化和“寨老”的复兴也刚好说明民间社会对多元权威的需求,这是历史和现实的选择。目前“寨老”等传统权威在民族村社生活中发挥的作用还远远没有挖掘出来,只要政府引导得当,完全可以借助这些民间传统权威对乡村社会实施治理,维护基层社会秩序稳定,打破过去那种原子式、碎片化,游离于政府控制之外的社会形态。比如,在四川凉山地区利用传统权威人物的影响力,把德高望重的德古选拔到人民陪审员队伍中,通过司法培训,利用他们的传统调解机制调解司法案件,收到不错的效果,节约了司法资源。[7]顺应少数民族群众对本民族传统权威人物和文化的爱戴,把少数民族人士引导到基层社会治理中来是民族地区国家现代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1]习近平李克强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分别参加全国人大会议一些代表团审议[N].人民日报,2018-03-09(1).
[2]何明.当下民族文化保护与开发的复调逻辑——基于少数民族村寨旅游与艺术展演实践的分析[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1).
[3]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79.
[4]姚周辉,何华湘.宗族村落文化的范本[M].杭州:杭州出版社,2011:180.
[5]辜鸿铭.辜鸿铭文集:下[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309.
[6]马凌诺斯基.文化论[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99.
[7]伍文义.关于布依族原始社会的探讨[J].贵州民族研究,1982(4).
[8]潘志成.传统权威与当代少数民族村寨社会控制[J].民族法学评论辑刊,2009(6).
[9]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2.
[10]周星.民族政治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264.
He Jinrui,Long Li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ng modern rural governance system, lazhe village of Buyi Nationality, Lubuge Township, Luoping, Yunnan Province, has found a joint point among the party construction, market economic organization and traditional rural governance powers, integrated the governance factors of traditional authority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into the modern rural soci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improved the social governance capacity. The research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national governance factors to modern governance system has important value and beneficial enlightenment for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Key words: National traditional culture; Traditional authoritarity; Moderniz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capacity
責任编辑:王廷国 孔九莉 王廷国 孔九莉 李祖杰 邓卫红 刘遗伦 余爽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