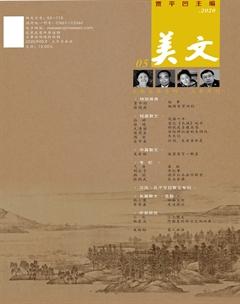迷人的乐园
韩小蕙
对于我们的少年时代来说,协和大院里最迷人的,还属千花万草之间、浓密树叶里面、墙角泥土深处……隐藏着的各种小生灵。
昆 虫 世 界
那时,一到夏天,尤其是快要天黑的傍晚,晚霞红光灼灼地映亮了天上、地下的整个世界之时,蜻蜓们便在我们眼前飞舞起来。越早的年头,飞得越多,轻轻盈盈地在天空中溜着冰,跳着舞,最后,大大咧咧地落在小树枝上、花瓣上、草叶上,甚至飞过来落在小洋楼的纱窗上。此时,只要蹑手蹑脚走上前,用两根手指一捏它的翅膀,它就是我们的俘虏了。轻捏着它的小身子,让那一对薄薄的翅膀像滑翔机一样放开,它的大眼睛便咕噜噜地转,小细爪子不停地挠动,有时还把肚子尖弯成一个勾,不知是抗议被抓?还是表达失去自由的疼痛?
据网查,目前世界上已发现了63种蜻蜓,学名都特别深奥,比如异色多纹蜻、低斑蜻、白尾灰蜻、线痣灰蜻、异色灰蜻、黄蜻、红蜻、玉带蜻、黑丽翅蜻、北京大蜓、北京弓蜻……可惜我只知道4种:最普通的叫“红果”,个子中等,全身呈浅红颜色;还有一种叫“黄果”,顾名思义,它的身体是黄色的;叫我们孩子们最稀罕的是“老杆儿”(雄性)和“老籽儿”(雌性),据说学名叫“碧伟蜓”,个子比一般蜻蜓都大,身体呈绿黑色,像一架小直升飞机,灵敏度和警惕性极高,不容易逮,一般只有男生才能逮着它们。有一次,我突然发现一只“大老杆儿”飞了过来,就落在我面前的小树枝上,心里又惊又喜,就轻手轻脚地去逮。正在此时,大院男孩儿里的“淘包”高XN也看见了,但他在我身后好几步远,就小声嚷着让我别动。我没听,依然走上前去,但就在我张手快接近它时,它却警觉地飞走了。身后的高XN实在是气急了,过来就给了我一拳,好疼啊,所以我到今天还记得——哈,君子报仇,一百年不晚,高XN,你还该我一拳呢,何时还?
后来随着时光一天天逝去,我们长大一些了,逐渐知道蜻蜓是益虫,就不再逮它们了。乃至于有时看见它们傻傻地落在触手可及的花叶上,还要去摇摇花叶,叫它们高飞,免得遭受屠戮。如果有外院的孩子来逮它们,就赶快去告诉传达室的爷爷,把他们赶走……可惜现在,蜻蜓越来越少了,连普通的“红果”“黄果”都难以见到了,更何况“大老杆儿”!
树上的蝉儿也是我们一天到晚都想得到的宝贝,但大院孩子都不叫它们“蝉”,也不称“知了”,而是叫“季鸟儿”——大概全北京的孩子都管它们叫“季鸟儿”吧?多么形象、生动的名字,它们真的就是一季的“鸟儿”呀,一生经过受精卵、幼虫、成虫三个阶段,每到夏天,早年产下的受精卵会孵化成幼虫,钻入土壤中,以植物根茎的汁液为食,等幼虫长大后,爬到地面上,蜕去黄澄澄的外壳,就羽化成有翅膀的蝉儿,飞到高树上去鸣叫啦。孩子的阶段与成人的就是不一样,那时听惯了季鸟儿叫,一点儿也不觉得吵,也不烦,相反,它们突然在窗外叫起来的时候,还会兴奋地扒头去找,真希望能逮到一只,放到家里让它叫。我记得有两三次,真看到它们像一枚小炮弹似的,“腾”地在树叶间弹起身,由一棵树弹到另一棵树上。可是我从来也没逮着过它们,那是男孩子们的绝招儿,他们在长长的竹竿头绑上一根小细棍儿,抹上用猴皮筋儿熬制的胶,然后挥舞着竹竿,炫耀地从我们面前走过,身上的小网兜里装着他们的战利品,有时那些季鸟儿还特给力地叫上一声。
我很早就知道季鸟儿是害虫,每当它们渴了、饿了,就用自己坚硬的口器插入树干,吸吮汁液,把大量的营养与水分吸入身体中,用来延长自己的寿命,所以我们逮季鸟儿都理直气壮,一点儿也没有负罪感。但我直到今天读了相关的书籍,才知道只有雄蝉会鸣叫,它的发音器在腹肌部,像蒙上了一层鼓膜的大鼓,鼓膜受到振动而发出声音,由于鸣肌每秒能伸缩约1万次(天呐,太天才了!),盖板和鼓膜之间是空的,能起共鸣的作用,所以其鸣叫声特别响亮。它们还能轮流利用各种不同的声调,激昂地唱出不同的歌曲。雄蝉的喊叫,一是为引诱雌蝉来交配,二是与其他雄蝉的集合声,三是被捉住或受惊飞走时的吼声。但好玩的是,雄蝉只会叫,听不见;雌蝉不会叫,只会听,你看,大自然是多么高明的缔造师啊!
还让我大为惊愕的是,你道世界上有多少种季鸟儿?说出来吓死你,居然已知的就有3000种!因此,它们的名字也特别多,自古以来,有:蜩、蜺、蝒、螓、蠽、五色、日暮、丕蜩、茅蜩、秋蜩、蚱蝉、寒蜩、寒螀、螂蜩、蜻蜻、蜓蛛、螗蜩、蟪蛄、螗蛦、马蜩、螇螰……哎哟,有些字,我学中文的都是第一次看到,不认识,念不出发音。还有,虽然它们是害虫,但中国古人认为它们栖息于高处,餐风饮露,生性高洁,故对它们颇有偏爱,很多古诗写到了它们。最有名的有三首,都是唐代大诗人的:
其一:
《蝉》 虞世南
垂緌饮清露,流响出疏桐。
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
其二:
《在狱咏蝉》骆宾王
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
不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
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
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
其三:
《蝉》李商隐
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
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
薄宦梗犹泛,故园芜已平。
烦君最相警,我亦举家清。
文学史上的评价是,虞世南“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是清华人语;骆宾王“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是患难人语;李商隐“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是牢骚人语。
从前我以为“蚂蚱”和“蚱蜢”是同一种昆虫,后来才知道“蚂蚱”就是蝗虫,平头圆脑袋的那种;而“蚱蜢”是我们俗称的“呱嗒扁儿”,长身子,尖头,上面有两个尖角的须须。论地面上的活物,这两种是我小时候见得最多、捉得最多,因而也是最熟悉的朋友。
刚搬到协和大院那会儿,草木多,人少,所以蚂蚱特别多,个头儿还大,稍不留神就飞到脚面上来了,对了,它们带翅膀,会飞。有两种颜色,绿的和土黄色;两种个头儿,大的能有大人的食指那么大,小的有半个小指头尖儿大。我当然喜欢大个儿的、绿色的,其他孩子也是一样,有的还给拴根粗一点的棉线,遛蚂蚱玩。它们也不难逮,你只要看著它们双腿一蹬,“噗”地一跳,你跟过去拿手一扑,就有了。捉在手里,给它掐个草叶儿送到嘴前,它便凶狠地咬住,不撒口,那样子还满吓人的。而“呱嗒扁儿”就温顺多了,拿在手里,一般不拼命反抗,捏住它的双腿末端,它就会僵住上身,一伸一屈地蹬腿,导致身体呈90度上下杠悠,十分有趣,这一“绝技”,蚂蚱就不会。呱嗒扁儿的学名叫“中华剑角蝗”,飞起来能发出“呱嗒、呱嗒”的声音,所以才得了这么个别名。在大院里,呱嗒扁儿比蚂蚱少,依据“物以稀为贵”的原则,身份就比蚂蚱金贵些。我不知道它算不算“蝗灾”的一种?
记得特别清楚的是,差不多我七八岁那一年,有一天我放学回家,发现大院里的蚂蚱特别多,在地上蹦来蹦去,竟然还有两只落在纱门上。可把我乐坏了,逮了好几只大个儿的,拿回家玩儿。奶奶看见了,叹了一口气,说是“又不(知)道哪儿闹蝗灾了”?果然,第二天我听小同学说,最厉害的地方,竟然有警察也不指挥交通了,拿着大簸箕在大街上扫那些蝗虫!说来,那时我一个城里的小屁孩儿,真的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哪知道蝗灾的厉害?后来我读到普希金的《蝗虫》诗:“蝗虫飞呀飞,飞来就落定。落定顷刻全吃光,从此飞走无音讯。”心里隙隙有所动,据说这首诗是嘲讽沙皇派出的钦差大吏的,讽刺他们像蝗虫一样,所到之处,就把百姓全吃光。对于普希金这样写出《致大海》《假如生活欺骗了你》《致西伯利亚的囚徒》等杰作的伟大诗人来说,这首《蝗虫》诗简直像白话一样简单,起初我都不相信是他的作品,直到看了背景介绍才明白,这也算是表达诗人心境的一方面作品吧。
而最让我接受不了的是,有一回在山东,吃饭时候的一道菜,居然是炸蚂蚱。主人还将之作为珍肴,一而再、再而三地盛情邀请客人们“尝尝高蛋白”。我知道山东人爱吃昆虫,以前就见他们吃过蝎子、蚕蛹、蝉蛹,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哈哈,不知山东人的豪爽里面有无这些“高蛋白”的贡献?
北京孩子管螳螂叫“刀郎”,有时候,青绿色的它们也会从草丛里面钻出来。样子很萌,煞有介事地二目圆睁,朝你举着大刀,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表情。可是肥胖的大肚子拖在地上,一边举刀,一边沉思,倒把它们的游移不定表露得纤毫毕现,让人哈哈一笑,捉住它们了事。不过它们毕竟是条好汉,你别以为这时你就赢定了,不,你一个不注意,它们的大刀就到了,能一下子把你的手指割出血,它可就趁机得胜回朝了。
蟋蟀是蟋蟀,油葫芦是油葫芦,两种小虫长得差不多,可是“社会地位”差远了。记得小时候在大院里,俩男孩儿趴在草地上斗嘴,一个贬低另一个,轻蔑地说:“你那个哪儿是蛐蛐儿呀?那是油葫——芦,嘁,不值钱!”最后那个“芦”字,在他嘴里,不发二声“卢”音,也非轻声,而是发成第三声“鲁”,而且还用重音、还要拐上一个弯儿,以示强调。那是我第一次听到“油葫芦”这个名字,又因为他如此之蔑视,所以就记住了。
他俩扑腾得浑身都是土,是在捉蟋蟀。北京人不叫“蟋蟀”,而是叫“蛐蛐”,连盛它们的罐子都跟着叫“蛐蛐罐”,这是因为这种小虫能发出“瞿--瞿--瞿”的叫声,因此而得名。严格说起来,那不是蛐蛐在叫,而是利用翅膀在发声:在蛐蛐右边的翅膀上,有一个像锉子一样的短刺;左边的翅膀上,长有像刀一样的硬棘,左右两翅一张一合,相互摩擦,就发出“瞿--瞿--瞿”的悦耳动听声响,让人以为它们在唱歌。这些声响有不同的音调和频率,表达着不同的意思,比如在夜晚,蛐蛐们大声地发出长节奏的鸣响,既是警告别的同性禁止进入其领域内,也是求偶的歌唱;而当有别的同性来犯,它便改为威严而急促的短鸣,以示严正警告。但油葫芦就不会鸣叫,所以它们的身价一落千丈。
蛐蛐好斗,阴险的人类就利用这弱点,让它们互殴,给自己找乐。据考证,这从唐代就开始了,还有名称,叫“斗蛐蛐”,亦称“秋兴”“斗促织”。从那以后的一千多年过去了,华夏最爱斗蛐蛐的是宋代和清代,朝野内外俱大兴斗蟋蟀之风,并有官宦富商将“万金之资付于一啄”的,就是赌博,据说这还成了“具有浓厚东方艺术色彩的、中国特有的文化生活”。据说,甚至还形成了三种境界,第一种叫“留意于物”,其最典型代表是南宋宰相贾似道,竟然因玩虫而误国;第二种称“以娱为赌”,把斗蟋蟀作为赌博手段;第三种是“寓意于物”,境界最高,多为文人雅士所为。直到今天,还有不少闲人持“文化”之名而乐此不疲。
对小孩子们来说,捉蛐蛐乃天性,当然不夹带赌钱,但输了,也很可能被小伙伴“讹”去一个心爱之物,比如一根冰棍或一个弹球什么的。这一般都是男孩子的玩意儿,我们小女生不敢把那小虫子抓在手里,一是因为它们长得丑,土黄色,土里土气的;二是它们爬得太快了,我们可怕它们钻到衣服里面去。
蝈蝈也不少见,但大院里基本没有,都是快秋天的时候,有人推着自行车,上面拴着高高厚厚的一大堆小笼子,带着“嚯--嚯--嚯--嚯—嚯--”的一大堆叫声,来叫卖蝈蝈。和卖别的不同,他也不用吆喝,蝈蝈们自己就喊了:“谁把我买走?5分钱一个!”现在早市上偶尔也还有卖的,但是得涨到10块钱一个了吧——哎哟我还真不知道。
小时候,奶奶也给我们买过蝈蝈。拿回家来,叫我们去摘一朵不结果的老窝瓜小花,插进小笼子的眼儿里,说是蝈蝈爱吃,然后就把蝈蝈笼挂在窗户框上。可把我们高兴坏了,一会儿就去偷偷看上一眼,过一会儿再去偷看一眼,直到发现蝈蝈爬到花上了,便兴高采烈地跑去报告:“爬上去了,蟈蝈吃花了!”待大肚子蝈蝈吃饱喝足了,心情好了,情绪高涨了,便开始唱歌:“嚯--嚯--嚯--嚯—嚯--”嘿,歌声嘹亮,高亢动听,连白云都听得呆了,驻足不走了……
我们大院里有一株巨高的大椿树,得有二三十米高,两个大孩子都合抱不过来的那么粗。椿树对我们有特殊的吸引力,是在于夏天时,树干上经常会趴有两种叫“大姐”的虫子——为什么会叫“大姐”呢?这叫我至今也不明白,按理说在人世间,“大姐”的称谓可全都是褒义的正面形象呀。
第一种叫“臭大姐”,指甲盖大小,黑色身子,冷不丁“嗡”地就飞来了,落到人眼前,可是千万不能打,因为它会释放一股臭气,非常臭,久久不散,是属于惹不起的地痞流氓。它的中文学名叫“椿象”,别称“臭腥龟仔”,因体后有一个臭腺开口,遇到敌人时就放出臭气,俗称“臭屁虫”。据说世界上已发现其有3万多种,多数是害虫,而且居然还分门别类地加以祸害,比如有专门危害水稻的稻黑蝽、稻褐蝽、稻绿蝽等,有专门危害果树的荔蝽、硕蝽、麻皮蝽等,有专门危害蔬菜的菜蝽、短角瓜蝽、细角瓜蝽等,只有一小部分以猎捕其他软体昆虫为食的是益虫。此外,还有一种名叫“瓜黑蝽”的可以做成名贵药材,李时珍《本草纲目》将其称为“九香虫”,具有很好的保健作用,于是在我朝就必然引来“吃货”了,一盘炒瓜黑蝽要价数百元;于是就必然还有后续,有人专门养殖瓜黑蝽当作食材卖,暴利呢——当然,这是当年的我们所万万想象不到的!当年的我们只知道,可以在爹妈面前撒娇,可以在哥姐面前耍赖,可以在小朋友面前“臭讹”,但绝对不能在“臭大姐”面前任性。
第二种叫“花大姐”,居然有一个学问颇深奥的学名,叫“斑衣蜡蝉”,也是飞虫,北京人形象地叫“灰蛾子”。成年的有小拇指上端那么大小,落在树上时全身灰褐色,很难看,但一旦张开翅膀,内侧膀尖上居然有一片鲜艳的大红色,上覆小黑点,还缀着一小块翠蓝,也很晃眼呢。不过我们小孩子对这些漠不关心,也不碰它们。让我们大感兴趣的是它的幼虫 “小象”,那时我真不知道“小象”就是花大姐的童年,还以为它们是另一种爬虫。“小象”比蜜蜂还小一点儿,细瘦,浑身上下黑白碎点儿,有一只像管子般的尖鼻子,长得的确很像浓缩型的大象。它们爬在树干上缓缓挪动,仔细点儿就看见了,很容易捉到手,而且它们温顺,女孩子们也不怕。放在手心里,起初它装死不动,过一会儿看看没什么动静了,就一下子弓起身子快速爬动,企图逃走。大孩子告诉说它们是害虫,用那管子似的长鼻子吸吮树汁,大树就会被吸干,然后枯死。对此我表示出一小点儿怀疑:一是它的体量那么小,能吸多少树汁?能把那么粗壮高猛的大树吸死?二是这么多年了,不仅没见大树被吸死,它反而越长越高、越粗、越壮,可见迷你的小象根本没什么杀伤力。不知为什么老让我想起一句诗“蚍蜉撼树谈何易”——当时,毛泽东的37首《诗词选》已经出版,大人孩子都会背“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
我小时候挺喜欢天牛的,也敢抓,然后拎着它们的两条大“辫子”玩。因为它们长得不难看,黑色油亮的小身子,上面有漂亮的小白斑点,头顶上那两条大辫子也是一截黑一截白的美丽图案,甩嗒甩嗒的,像极了穆桂英挂帅的那两条大翎子。天牛也不鬼鬼祟祟的,不像蟑螂那样见人就抱头鼠窜,而是大模大样地守护着它们自己的心情。
其实天牛挺凶的,有一张类似铁钳型的嘴巴,把一片树叶放到它嘴前,立刻就能被咬烂,看着它那穷凶极恶的样子,你心里还真袭上些许忌惮。但它实在是很好玩,比如当你抓住它时,它会愤怒地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拼命挣脱,企图逃走。男孩子们抓到“天牛”,玩法特别多,什么天牛赛跑、天牛拉车、天牛钓鱼、天牛赛叫等等,比起充斥市场的电动玩具来,玩这种活物自然有趣得多。比如“天牛赛跑”,就是用一根根细棉线把一只只天牛拴起来,然后把线拴在一起,放开手,天牛们就会向不同方向角力,结果谁也拉不动谁,就在原地团团打转,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再比如“天牛钓鱼”,方法是端来一盆水,将一个系着细线的鱼形小片系在天牛角上,再将天牛置于另一个浮在水面的小木条上,天牛四周环水,局促不安,就频频挥动触角,拉动细线,形同钓鱼;而鱼若离了水,钓鱼就算成功。有时候还把两只天牛放在一起比赛,以先钓起者为胜,各自天牛的主人给各自的天牛“加油”,勾心斗胆,满紧张的呢。
据说天牛最喜欢呆在枫树上,因为枫树汁含糖量高,它们喜食枫树的嫩叶、枝条和树皮,还在树干上打洞产卵,对树木生长损害很大,是害蟲。大院里只有一株枫树,在42号楼前,它分杈而长,树干不粗,便于攀爬,男孩子经常在这株枫树爬上爬下,捉到了就拿着他们的战利品炫耀。我小时候跳过墙头、上过房,但还没淘到爬过树,有一次是我从那株枫树下走过,刚好看到一只天牛趴在矮矮的树干上,就一顺手把它抓住了。
42号楼原来住的是中国第一号病理学家胡正祥教授一家,胡教授位在“大神”级别,当年孙中山逝世的病例解剖就是他做的。他和夫人都特别喜欢孩子,经常允许大院孩子们去他家看电视,有空时还陪看,边陪边讲解。一旦发现有孩子爬上枫树林,便惊呼一声:“小心!”赶紧双手接住抱下来。可惜这一对恩爱老夫妻均没有熬过“文革”。现在,42号楼前的那株老枫树还在,年年春抽青芽,秋落红叶,只不知道上面还有没有天牛了?
大院里的昆虫还多着呢,比如瓢虫,几乎任何时候都能在院子里发现它们,有黄色、桔色、红色、米色、枣色、黑色的,身上一般都有斑点,有的2个、7个、9个、12个、28个……网查,全世界有5000多种瓢虫呢,中国有将近400种。以我可怜的知识,只知道“七星瓢虫”是益虫,“二十八星瓢虫”是害虫,有时也会把它们放在手心里玩一玩。
蜘蛛更可怕,全世界的蜘蛛居然有42055种,这还是2010年的统计,近8年来不知又发现了多少种?中国有记载的约3000种。人们普遍认为蜘蛛是一种昆虫,但实际上,它们与蝎子、蜈蚣一样,不属于昆虫而是动物。小时候,家里出现蜘蛛,奶奶都不让我们孩子打扰它们,说是“喜蛛”,报喜来了。典籍上居然有印证,陆玑《诗疏》载,“喜子(喜蛛)一名‘长脚,荆州河内人谓之‘喜母,此虫来著人衣,当有亲客至,有喜也。”即是说,荆州那地方的人把喜蛛喻为吉祥,认为喜蛛落下象征着“喜从天降”。这在中国北方农村也有此讲:平时住在房角的一种小蜘蛛高悬在头顶,一旦它们下来,从人的眼前跑过,家里准会有客人来,就像喜鹊一样,跑到谁家门口的树上叫,那家就有客人来……
所以,我不怕蜘蛛,也不伤害它们。可是不知为什么,我女儿天不怕地不怕,却独怕蜘蛛,怕得要死,从心里极度恐惧。我最怕的是壁虎,北京人称“歇了虎子”,每年春夏一旦发现它们出现了,我就开始天天生活在恐惧中,晚上几乎不敢出门。这心里阴影一直持续到现在,一把年纪了,还是怕,真怕!二十世纪90年代末,我跟着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缅甸,启程时特高兴,但到那里的第一天就急切地盼着打道回府了,因为缅甸是热带,生态环境又好,到处都是壁虎,大的能有一尺多长,连房间里都有——你洗个手吧,它“嗖”地钻出来了!你刷个牙吧,它“嗖”地又跑过去了!半夜,本来我就紧张得睡不着,不料黑漆漆中,它们竟然又来了,还嘹亮地唱起歌来,声音大如鸟叫,特别瘆人,把我吓得头皮一阵又一阵发麻……可是说来蹊跷,我女儿却不怕壁虎,就像我奇怪问她“蜘蛛有什么可怕的”一样,她也不明白壁虎有什么可怕的?因此,别那么相信基因吧,看来也并不是那么靠谱哦。
鸟儿们
协和大院里树多,鸟儿就愿意来呼吸新鲜空气。每天早上一醒来,就能听到它们在窗外练声的练声,唱戏的唱戏,热烈极了。记得施特劳斯有一首钢琴曲《森林波尔卡》,我相信,他一定是听到了晨光中的众鸟和鸣。
我在大院里见过的鸟,有燕子、喜鹊、灰喜鹊、麻雀、老鹰、啄木鸟、布谷鸟、乌鸦、鸽子,据说还有小伙伴见过猫头鹰。有一天傍晚,我还生生地看到天上飞着一排南归的大雁,它们已经飞得很低了,可以清晰地看到夕阳照在它们身上,把每一只的羽毛都染得一片金红,它们一只只伸着长颈奋力飞着,队伍整齐得像是用尺子划出来的,那场面可真是壮丽的诗啊……
喜鹊的叫声不用我形容,大家都听过,“喳喳喳,喳喳喳”的,也有人听到的是:“喜喳喳,喜喳喳……”从古代开始,古人就谓之为报喜之声。我有一本《唐宋词一百首》,开篇第一首便是写喜鹊来送喜讯的:“叵耐灵鹊多谩语,送喜何曾有凭据!几度飞来活捉取,锁上金笼休共语。比拟好心来送喜,谁知锁我在金笼里。欲他征夫早归来,腾身却放我向青云里。”(无名氏《鹊踏枝》)这是唐代民间流传的一首爱情词,上半阕是少妇口气,说多嘴的喜鹊呀,没凭没据的,你来送什么喜?下半阕换成喜鹊的口气,委屈地说,我好心好意来送喜,她却把我锁进笼子,盼她出征的丈夫赶紧回家来吧,就能把我放回到蓝天白云里了……哈哈!
中国民间也有很多类似的传说,比如“喜鹊叫,贵客到”“喜鹊喳喳,财宝到家”。到不到家先不说,那“喳喳喳”的叫声确实好听,给人带来愉快的感觉,因为里面充满了一个好字——“明”:明朗、明快、明晓、明畅、明净、明澈、明晰、明理,还有光明、聪明、鲜明、启明、精明、神明、圣明……总之各种好词吧。其实,这都是人类心目中自己设定的主观美好想象,实际中,喜鹊为了个体的生存,也是很凶悍的鸟呢,饿了或是要喂食自己的雏鸟时,它会狠心地盗食其他鸟类的卵和雏鸟,痛下杀手,毫不心慈手软。可见在自然万物中,什么都不能看表面现象,决不能看他(她、它)穿了一件美丽的花衣裳,或者说一嘴腻得流油的阿谀话,就认定他(她、它)们的心灵也像鲜花一样,看鸟与看人,同理。
燕子的叫聲也好听,“啾啾啾”的,古人形容为“啁啾”,古诗中提到它们的也很多。不过北京燕子的最美特色不在协和大院,而是在正阳门箭楼,也就是前门楼子。老北京人都知道正阳门的夕阳西下时,甚是壮美,蓝濛濛的澄天,一座被晚霞皴染得流光溢彩的高大门楼,大群大群“啁啾”着飞过来、飞过去的嬉燕,那幅壮美的图画,简直都能把人的心美“化”了。顺便说一句,正阳门是北京最大的城门,正阳门箭楼是北京最高大的箭楼,从它建成的那天起,一直是老北京的象征。
灰喜鹊的外形跟黑白喜鹊有点像,但身上的“衣裳”不同,便不以为它们是同类了。灰喜鹊长得不难看,甚至还可以说有点儿漂亮:黑头黑喙,小脸嫩白,翠蓝色的身上披着一件浅灰色的“小坎肩”,下面拖着一条长长的深灰色大尾巴,在树上栖息的时候,宛若坐在龙庭上的帝王,我每次看到它们这个高贵的姿态,都有一种想画下来的冲动。
但是,它们可万万不能开口,因为那厮们的叫声实在是太难听了,“嘎——嘎——嘎”的,然又不像鸭“嘎”那么清清亮亮和正大光明;而是压着嗓子,憋着闷气,像是积了多少年的仇怨,刻毒地从胸腔里挤出来,听着真叫人从心里往外不舒服——很多时候,能叫我联想到大院里的一位长舌妇“三脚鸡”,伊虽然也是干部,却连家庭妇女都不如,整天揣着一肚子怨毒在大院里溜达,碰上谁就趋过去搭茬儿,追着探问人家的隐私,然后牢记在心里,伺机下手,陷害一下。在人类社会中、起码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劣根性中,确实有这么一种整天盯着别人的小人,他(她)们对别人的兴趣远远超过自身,唯恐别人过得舒心,那是他(她)们非常痛苦的事。我真的是不能理解他(她)们,想不透他(她)们想要的到底是什么?反正大院人,都像讨厌听灰喜鹊的叫声一样,厌恶跟“三脚鸡”说话,一见到她的身影就赶紧闪人。不过伊不以为耻,反而转换了另一种“迂回战术”,通过接近各家保姆来打探其主家的隐私,何其可怕也!
我于鸟类学真是无知,不知道啄木鸟会不会发出叫声?但我听过它们啄木头的声音,“磕、磕、磕、磕、磕、磕……”敲梆子似的一串连音响过,之后还有余音。小时候读童话书,啄木鸟的身份是“大叔”,便以为它有多大个儿,起码也像老鹰那么高大吧?谁想,直到多少年之后,我都长成大人了,才在某一天的某一刻,在开着的窗子前,突然听到一阵“磕、磕、磕、磕、磕、磕……”,抬头一看,有一只比鸽子还小一些的瘦鸟,正在外面的大洋槐树干上坐着呢,它有花冠毛,长长喙,身上的羽毛是花的,有白色、橘色、黑色,自然流畅地组合在一起,还有一顶红冠子,随着它转动身体,美丽的图案不停地转换。一道灵感的亮光突然划过我的脑际,啊,这就是传说中的啄木鸟吧?这只啄木鸟的家似乎就安在我们大院里,此后,我又好几次看见它,每次都是在用力地“磕、磕、磕、磕、磕、磕……”,不由得又想起小时候的童话书,那上面说,在树林里,啄木鸟大叔是最勤快的“劳动模范”。
也许,布谷鸟是中国传统诗词里写到最多的鸟儿吧?但一般没有直接写成“布谷鸟”的,而是写作“杜鹃”“子规”“杜宇”,为什么?
有典出自《史书·蜀王本纪》:约在公元前666年,望帝称王于蜀地,后来他认为宰相鳖灵的能力比自己强,把国家交给他打理将会是万民之福,就主动禅位,自己去了西山隐居修道。谁知鳖灵坐上王位之后,不仅把国家治理得乱七八糟,还霸占了他的妻子和女儿。望帝心急如焚地赶回都城,想奉劝鳖灵回心转意,但城门紧闭,根本不让他进城。望帝只得郁郁寡欢地回到西山,日夜掩泪痛哭,不久就因伤心过度断了气。死后的望帝化作一只杜鹃鸟,望着远处的都城哀声啼鸣,昼夜不止,发出的声音极其哀切,所以叫“杜鹃啼归”,简称“子规”;它甚至常常啼出一片片红红的鲜血来,滴到大地上,化作一片片杜鹃花……还有另一个传说版本:也是在古代蜀国,国王杜宇勤勉治国,爱子爱民,常常跟老百姓一起下田劳作。他死后仍然心系百姓,变为一只杜鹃鸟,每到春季便叫人们:“布谷!布谷!布谷!”啼得嘴里流出鲜血,染红了漫山的杜鹃花……这两个传说殊途同归,便是成语“子规啼血”的来历。
悲剧性的伤怀本是文学的最热度题材,故此,古往今来,有关“子规啼血”的诗词数不胜数,比如王维“万壑树参天,千山响杜鹃”;李白“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李商隐“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苏轼“萧萧暮雨子规啼”;秦观“杜鹃声里斜阳暮”;文天祥“从今别却江南路,化作啼鹃带血归”……
布谷鸟的叫声很大,有时在屋子里安静读书,便能听见一声声地从外面传来,其音疾疾,其情切切,直催得人放下书,去到窗前张望。但可惜,它总是藏身在白云深处,只能闻其声,不得见其影。我也曾多少次在大院里蹀躞,想与它们碰个面,哪怕只交流一个眼神也好,哀乎哉直到今日,没有缘分得见它们的真容。
小时候在大院里疯玩时,常常突然被一个疾音提醒:“快看,老鹰!”男孩、女孩便一起停下手里的各种忙活,抬头去寻找老鹰。就见当空有个矫健的“一”字,忽上忽下,忽远忽近,飘移在蓝色的高天上,自由自在,相当傲然。便把我们一帮孩子羡慕得纷纷乱喊:“大老雕!大老雕!”
其实,老鹰与老雕还是有区别的:老鹰叫鸢,“纸鸢”是风筝的别名,顾名思义,可想而知;老鹰一般捕食兔子、田鼠、小鸡等一类小型动物,有个著名的儿童游戏“老鹰捉小鸡”即为印证,不然它为什么不叫“老鹰捉母鸡”或“老鹰捉雄鸡”呢?老雕是比老鹰还要大而凶悍的猛禽,是人们心目中真正的“雄鹰”,它们甚至能猎取鹿、山羊、狐狸等比它们自身的体形还大、还重的大型兽类,可称得上是真正的“空中霸王”。
一般我们在城市里看到的,基本都是老鹰而非老雕,可是,大院孩子都爱管老鹰叫“大老雕”。可惜,现在已经看不见了,大老雕们都飞走了!
没飞走的,最常见到的是这三种鸟——麻雀、乌鸦和鸽子,不知道它们是在忍辱负重地坚守阵地?还是厚颜无耻地苟且偷生?
麻雀是最大的冤案,曾经与老鼠、苍蝇、蚊子一同为伍,被统称为“四害”,必欲除之而后快。其罪名是吃掉大量粮食,与老百姓争食——现在想想,也是真滑稽,中华煌煌五千年,难道在什么朝代养不起小小麻雀而必须让它们闭嘴?说实在的,麻雀在我朝也真没什么好待遇,印象深刻的是一个光秃秃的冬日,我在大院的石板甬道上走着,忽然飞来一只小麻雀,就落在我面前的地上。我一看,不由得“扑哧”笑了,问它说:“小东西,你怎么这么脏啊?”一冬天没下雨雪,它就跟一颗小黑煤球似的,身上的羽毛几乎都看不出色儿来了,还又小又瘦,也真是可怜!我看到过英国的麻雀,一只只膘肥体壮,还都特别干净,身上的羽毛虽不华丽却也鲜艳,那是因为英格兰雨水多,几乎三天两头洗澡,所以一只只都捯饬得跟贵族似的那么有范儿。
乌鸦是人见人恶的鸟儿,不在于它们是益鸟还是害鸟,而在于它们长得太难看,在这个越来越重颜值的时代,尤其招人不待见。其叫声又是最难听,有时候你正好好走着路,它不远不近地突然在你脑袋上怪叫几声“啊!啊?啊——”,能把你吓一个激灵。说来特别奇怪,很多鸟都“啊”,很多走兽也“啊”,可谁都没有乌鸦那一声声怪叫瘆人——乌鸦的“啊”是明显带着丧气的,就像是从地狱里传上来的鬼叫,立刻就能使人联想到黑色、阴暗、肮脏、祸端、不祥……用北京话说,它们就是“丧梆子”,谁遇见谁倒霉。尤其是在暮色苍茫的傍晚时分,它们会成群成群地、成大群成大群地在半空盘旋,一边不停地、蛮不讲理地、混不吝地“啊!啊?啊——”。此刻,再好脾气的人也都加快脚步,缩起头,想要赶紧离开那是非之地——对啦,就是“是非”二字:比起猫头鹰是凶枭,乌鸦还不是黑老大,也就算是个“小人”吧?不过,小人不可得罪,他们比真正的敌人还可怕,你若不小心得罪了小人,得,大祸来了,他们会片刻也不放松地缠斗你,死缠烂打,没完没了,咱们干正经事的人可真没工夫陪啊!
现在的鸽子似乎只剩下了圆滚滚、胖乎乎的形象,加上饭店里来不来就“烤乳鸽”,仿佛它们就仅仅成为了美味佳肴。过去,鸽子可不是这德行,它们与人类伴居已经有上千年历史了。《圣经》里第一次提到鸽子是《旧约》里诺亚与和平鸽的故事:诺亚方舟停靠在亚拉腊山边,洪水过后,诺亚把一只鸽子放出去,要它去看看地上的水退了没有?由于遍地是水,鸽子找不到落脚之处,只好飞回方舟。七天后诺亚又放鸽子出去,黄昏时分,鸽子飞回来了,嘴里衔着橄榄叶,很明显是从树上啄下来的。诺亚由此判断,地上的水已经消退。后世的人们就用鸽子衔橄榄枝来象征和平。在后来的年深日久里,鸽子曾长时间被人类派出承担通信任务,曾屡立奇功。中国也是养鸽古国,隋唐时期在广州等地,已开始用鸽子通信……
不过现在,人类的通讯手段实在是太发达了,什么互联网、短信、微信,3G、4G、5G,科技越来越神通,绝对不劳驾鸽子了,于是它们只剩下两个功能:卖萌和被吃——吼,忘恩负义的人类哦,当太平盛世时,鸽子是我们观赏的宠物;一旦“禽流感”来了,就远避它们而不及,完全都是从我们自身出发想问题,这也太自私自利了!
热带鱼
不知您还记得不?反正我记得,二十世纪60年代末,暴烈的“大革命”搞了好几年,人们疲塌了,厌倦了,就不可遏制地走向了反面——北京人中兴起了一股养热带鱼之风。协和大院也被带动起来,尤其是干部家庭中有男孩子的,屋里基本上都摆着一两缸热带鱼。
说是“缸”,可真有点大言不惭。那时生活还普遍贫困,一般干部家庭也不富裕,家家那点工资都是要一分錢掰成两半花的;所以所谓“缸”,只不过是不知道从哪儿寻来的几根铝带,用铆钉一铆,再买一毛钱腻子,把四块玻璃往上一腻,大业就算完成了。
我们家的鱼缸小得可怜,还没有16开杂志大,多亏热带鱼个儿小,不然在里面就转悠不开了。最困难的是热带鱼怕冷,北京的冬天难熬,就必须要有加热器,可那玩艺儿比鱼缸还贵,对于当时每月只领15元生活费的父亲,我们无论如何也开不了口。还是我15岁的哥哥有办法,花1块多钱买了一根试管,还有电阻、石英砂什么的,自造了一根土加热器,居然也安安然然地保佑着热带鱼们过了冬。至于鱼的吃食,全是哥哥走路到护城河边上去挖线虫,然后回家来,切开半个乒乓球,扎上许多小眼儿,把线虫放进一小坨,吊在鱼缸上面,线虫往下钻出头,就被鱼儿们吃了。有一回哥哥生病了,我替他去了一次,走了将近一个小时才到,腿酸得都不会打弯儿了。
就这么穷了巴叽的,您想我们能养出什么好鱼?也就是孔雀、黑玛丽和红箭,这是当时最普通、最不值钱的三种,十分好养,自己家都能让它们生下一群群小鱼。也听说过神仙、斑马等品种,但只是存在一份美好的神往中——今天想起那一条条灵动的小热带鱼儿,我的心上还会滚过一阵阵波涛,在当时那种人整人、人斗人,甚至人吃人的社会大动荡中,怡然的热带鱼给人们释放了多少能量(正能量、负能量)和压力;也给处于“黑五类子女”恶境里的我们兄妹,带来了多少心灵慰藉呵!
后来,“四人帮”垮,岁月回到了正常轨道。时间的钟摆不停,世事急急缓缓,一下子就到了二十世纪90年代。有一天到一位朋友家做客,迎面一座大鱼缸闯进眼帘,有半个书柜大,里面一群群七彩缤纷的鱼儿在穿梭,不是热带鱼是什么?可惜我只认识少年时代的那三位老朋友,余下的,听主人一一报出名字:神仙、红绿灯、斑马、银鲨、白箭、吻嘴、蓝宝石、地图鱼、珍珠鱼……主人每报出一个,我便在心里惊呼一声,没想到,孩提时代视若神明的那些热带鱼,竟然还有缘得见风采。
我想起少年时代的穷养,便叙述起来。朋友静静听完,徐徐吁出一口气,笑着说:“现而今养鱼,可跟咱们小时候的穷折腾不一样喽。”说着,他按下第一个插销,缸里立即“咕嘟嘟”地冒出一串气泡,“这是给鱼加氧气。”又按下第二个插销,“这是吸脏东西。”第三个插销是净化自来水,第四个是换水,第五个是恒温……就连鱼吃的线虫也准备好了,一块钱一份,可以喂一个礼拜。朋友说:“现在养鱼早现代化了,什么都给你准备好了,差不多你只管欣赏就好了……”
今天又二十多年过去了,还有没有孩子“穷养”或“富养”热带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