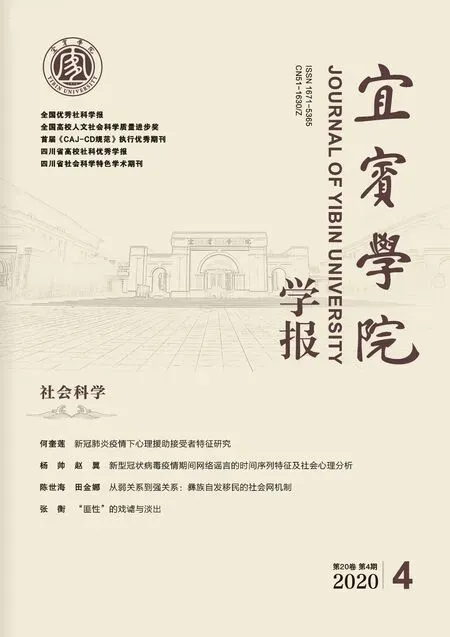邻里关系对社区居民安全感的影响
——基于CGSS2015的实证分析
王菲菲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北京100038)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基于地域认同基础上的传统社会关系开始瓦解,我国城市社区结构在城市变迁过程中出现了解组现象。社会变迁以一种强有力的方式对置身于其中的个体产生影响,使得个体安全需求增强[1]。安全感作为一种主观感受,是反映客观环境的重要因素。马斯诺编制的《安全与不安全问卷》使得安全感这一概念可操作化。国内公安部课题“ 公众安全感指标研究与评价” ,则开启了对安全感指标体系构建的研究大门。对于安全感问题的研究层出不穷,但从社会治安角度的对居民安全感进行的实证研究相对较弱。社区居民的安全感是社区成员对社区治安秩序水平的反应,对社会整体治安水平把控有着重要意义[2]。
社会变迁所引发的邻里关系的重构是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大议题。以往学者在对社区居民安全感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时,鲜有从邻里关系角度切入进行深入的实证分析。目前有大量实践试图解决伴随社会变迁而凸显的社区安全问题,其中邻里关系作为关键措施不容忽视。
20世纪70年代,美国为探寻解决社区安全问题的主动方案,率先开展了社区警务改革,其中邻里守望制度作为社区警务的一项重要内容,为解决邻里关系衰落、维持社区秩序起到了重要作用。其具体措施包括动员社区居民承担邻里守望职责、建立邻里守望组、维持与警方良好的伙伴关系、及时提供治安线索与情报等。邻里守望制度拓宽了犯罪预防的途径与渠道,被认为是解决社区问题行之有效的措施[3]313-338。20世纪80年代,英国从美国引进了社区警务制度,以期抑制与警力同步增长的犯罪率。该制度以英国约翰·安德逊提出的社区警务树理论为指导,通过强化情境预防与社会预防,着力改善警民关系,对犯罪实行由多方主体参与的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治安防范[4]270-301。社区警务着力强调社区合作在预防和控制犯罪中的作用,动员群众参与,强调邻里守望,注重情报主导,起到了很好的犯罪预防效果。邻里守望作为邻里间非正式的安全防范制度在实践中受到广泛推崇,其功能也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得到扩展。我国在吸收国外社区警务理论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我国国情发展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针,构建了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使得群众性治安组织力量在公安机关的组织下、领导下更好地形成合力,有效维护社会秩序。
如上所述,大量社区工作通过强化邻里间的关系纽带、增强社区的非正式控制来预防违法犯罪。基于此,本文将运用实证分析方法从社会治安角度探讨社区的居民安全感,论证邻里关系对社会居民安全感的影响。
一、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安全感,伴随着人类社会的诞生与发展,体现了人们对安全价值的基本追求。社区居民安全感作为反映一定区域内社会稳定的重要指标,引发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和调查,以此为基础研究社区居民安全感的影响因素具有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文献综述
国外关于安全感的研究最早见于心理学,弗洛伊德认为胎儿脱离母体,面对复杂的外部刺激而产生的焦虑感就是不安全感,其从心理学角度阐述外部环境对人的安全感知产生重要影响。马斯诺在需要层次理论中将人类对安全的渴求定位为第二层级的需要。吉登斯从社会学角度,阐述贯穿于个人生命历程中的社会环境与个体不安感以及其的交互作用对安全感的影响。国内一项关于安全感问题的研究结合心理学和社会学相关理论从社会环境和个人因素两个层面探讨了公众在人身、财产、食品、信息等涉及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安全感[5]。在影响安全感的众多因素中,社会治安是不容忽视的影响因素。有学者从社会治安情况,地域情况和个体差异三个维度对安全感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社会治安状况是影响公民安全感的最重要的原因[6]。另一学者在其构建的一项关于安全感的综合评价体系中,通过各影响因素的权重比计量,肯定了社会治安对居民安全感影响的重要性[7]。从社会治安角度分析居民安全感的影响因素时,学者认为警民间的信任对社区居民安全感有着显著影响。维持公众对民警的信信任是提高社区居民安全感的应然途径[8]。也有学者通过对北京等城市的实地调查得出社区环境作为的宏观性因素对城市居民安全感有着深刻的影响,社区环境、邻里认同对社区的认同感和整体的安全感都有着显著的影响[9]。
社区是社会的细胞,是社会治理的基本着力点,学者滕尼斯最早提出“社区共同体”的概念,开始了对以血缘为纽带的传统乡村小社会的研究[10]232-236。但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原来乡村社会中明确的社会规范在不熟识的社区居民中变得越发不确定,社区对于个人行为的控制力正在弱化,据此肖和麦凯提出了著名的社会解组理论。社会解组认为在经历快速变迁的转型区域易导致犯罪高发,这是因为邻里关系发生了变化,邻里间的非正式控制减弱[11]。随着社会发展,面临动态的社会治安环境,英国学者克拉克首先提出了情境犯罪预防理论。邻里守望作为情境预防的一项重要内容对改善社区治安状态,提高社区居民安全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12]。我国有学者提出现代社会社区居民归属感日益减弱、邻里互动频率日渐下降,社区参与意识降低,这种淡漠的邻里关系在商品房社区尤为突出[13]。有学者通过北京老城区的实际调查发现,在外来人口流动频繁的北京老城区,邻里间互动弱化,交往日益呈现表面化的特征,社区居民的情感维系力减弱[14]。有学者从多个角度对现代邻里关系进行了描述和分析,揭示了现代社区邻里关系与传统邻里关系在社会互动、社会认知等四个方面所体现的不同[15]。
基于以上文献,我们认识到随着社会变迁,基于传统地域认同基础上的传统邻里关系开始解体。邻里关系淡化,邻里互动减弱,同时,社会联系这一非正式的社会控制随着社会的频繁流动,在犯罪预防上发挥的作用在减弱,使得居民的安全感受到了极大挑战。这也使得本文的研究主题“邻里关系与社区居民安全感”更具现实价值。邻里关系是现代化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议题,社会解组理论认为淡漠的邻里关系将弱化对社区违法犯罪行为的控制力,影响社会治安秩序水平。在社会解组理论的指导下,我们进一步提出相关假设。
(二)研究假设
20世纪20年代,肖和麦凯提出了社会解组理论。社会解组理论认为犯罪与转型区域的邻里密切相关。社会解组是指一个社区无力实现其成员的共同价值追求并维持有效的社会控制[16]160-170。社会解组理论从犯罪学角度阐述社会解组的邻里对犯罪行为产生所起的促进作用。本研究受社会解组理论启发,从该理论出发阐述邻里关系对社区居民安全感的影响:减弱的邻里关系会导致邻里居民对社区违法犯罪控制力的减弱,无序的社区治安状况必然会导致社区居民产生不安感与焦虑感;反之,与社区居民之间强而有力的社会联系和社会纽带会对犯罪的产生起着抑制作用,进而强化居民内心的安全感。一方面强大的社区纽带对社区居民形成道德、情感等方面的非正式的控制,对维护社区治安、犯罪预防和震慑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密切的邻里关系、强化了社区成员间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整体上提高了社区居民安全感。
根据社会解组理论,我们做出假设:邻里关系越密切,社区居民安全感越高。《中国百科全书》(社会卷)将邻里定义为毗邻的人们,认同特定的一组角色,据此形成密切的互动关系,有着显著的认同感和感情联系,由此构成相对独立的小群体。邻里关系作为最基本的社区社会关系反映了所在社区居民共同的特征。为了进一步揭示邻里关系对社区居民安全感的影响,我们将进一步分解做出三个小假设。
熟悉的邻里情境使得居民的社会活动置于无形的受控状态,能够有效地实现社区的监督控制功能[17]。邻里间熟悉程度对维持社区的凝聚力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在一项以北京回龙观社区为对象的研究调查中,学者将邻里之间的相识、交往程度作为制约邻里关系的重要因素加以分析[18]。学者对深圳某社区进行介入调查后发现,该社区居民对邻居熟悉度较低,警惕性较强,对社区缺乏安全感,反映了对邻里交往的渴望[19]。
据此我们提出假设一:邻里熟悉程度越高,社区居民安全感越高。
交往机会与频繁的邻里互动有利于改善淡漠的人际关系,缓解人们对缓解的陌生感[20]。李芬在研究邻里关系的现状时,认为邻里互动的频繁程度反映了邻里交往的深度并将邻里互动、邻里交往的频繁程度作为衡量城市邻里关系现状的重要影响因素。吴昭挺在调查西安市某社区的邻里关系时,发现现代邻里的交往互动交往只流于表面,居民很难再进行深入交往,这在邻里的交往互动层面反映了重构邻里关系的重要性与满足居民安全感的需要[21]。
据此我们提出假设二:邻里交往越频繁,社区居民安全感越高。
此外,基于地域认同基础上的邻里在互动中易产生人际信任,对社区邻里更具信任感的居民对社区认同感与安全感越高[22]。袁振龙在其研究中将社区居民间的信任作为衡量社区治安状况的一项指标,并从四个维度来论证两者之间的关系。其认为邻里之间的信任度有助于成员之间形成团结、互助的社区邻里关系,从而使得社区的秩序得以有效进行,社区的治安状态得以良好[23]。
据此我们提出假设三:邻里信任度越高,社区居民安全感越高。
二、 数据与测量方法
本研究选取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社会综合调查2015年度调查数据(CGSS2015)。CGSS是中国人民大学主持的一个连续性、全国性的社会调查项目,数据客观、真实、具有权威性。该调查涉及全国28个省、市、县、自治区的478个村居,样本代表性较强。本文采用Stata15对数据进行分析。
(一)因变量
本文的因变量社区居民安全感是一个多分类变量,是通过问卷题“从治安角度考虑,你认为所在社区的安全吗?”建构而来。该题作为非必答题位于问卷中的法制模块,被答题者抽答到的概率是1/3,问卷中关于社区居民安全感的样本量有3 777个。在剔除缺失值后,统计发现有3 769位被调查者对该问题进行了有效回答。居民对社区安全与否的回答分为5类,安全感由低自高分为:非常不安全,不太安全,一般安全,比较安全和非常安全。由于认为社区非常不安全的被调查者占总回答人数的0.9%,为了保证分析结果具备统计学上的意义,故将因变量转化为三分变量,分别为不安全、一般安全和安全,如表1所示。其中认为社区安全的人数较多,占73.55%,但仍有18.02%的居民认为社区的安全等级为一般,甚至还有8.44%的居民认为社区处于不安全的状态,因此,研究社区居民安全感的影响因素,对提升社区居民安全感、提高社区居民满意度具有重要意义。
(二)自变量
本文的自变量邻里关系依赖邻里熟悉程度、邻里交往程度与邻里信任程度加以体现。
第一,邻里熟悉程度。这是根据问卷题目“与居民之间的熟悉程度”回答提取而来。熟悉程度分为五类我们将其演化成三分变量,按熟悉程度由低到高分别为不熟悉、一般熟悉与熟悉。通过对邻里熟悉程度的统计,我们发现,一半以上的居民都认为与邻里熟悉,占比达到了62.97%。但有13.91%的居民和23.11%的居民认为邻里分别处于不熟悉与一般熟悉的状态。
第二,邻里交往频繁程度。该自变量来源于题“您与邻居进行社交娱乐活动的频繁程度是?”该回答有7个层级,我们将其转化为4个层次,如表1。通过对邻里交往频繁程度的表述性统计分析,可知:从来不与邻居进行社会娱乐交往活动的在总被调查人数中占10.72%;而偶尔进行社交娱乐,每年进行几次的占22.50%;每月进行几次的占24.63%;交往频繁,来往密切几乎每周至少一次的达到了42.15%。自变量邻里交往程度中的参照组是“从来不与邻居交往”。

表1 影响社区居民安全感的自变量描述统计
第三,邻里信任程度。该变量源于题“在不直接涉及金钱利益的一般社会交往,您觉得邻居的信任度如何?”将其转化为三分变量后,可知:绝大多数人认为邻居是可以信任的,认为邻居可信赖达到了75.47%,也有7.37%和24.53%的人对邻居任保持警惕心理,选择不信任或者一般信任邻居。
(三)控制变量
考虑到安全感作为一种主观感受与评价,具有一定的个体差异性,性别的差异导致个体对安全的感知程度不同,同时在教育水平与收入等因素上存在差异的主体也会对安全感存在不同的认知。因此在控制变量的选择时,选定性别、年龄、民族、教育程度、收入等基本的人口学上的变量。其中年龄、收入是连续变量;性别(1男,0女)是二分变量;民族是分类变量为汉族与非汉族;教育程度分为四类:小学及以下、中学、专科、大学本科以上。其中“0”为参照组。
三、 社区居民安全感影响的回归分析
本文研究的因变量社区居民安全感是一个序次多分类变量,因此采用序次Logistic回归进行分析,首先分析控制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再依次在模型中加入各个自变量,得出以下分析。如表2所述,随着因变量的不断加入,模型的对数似然值在增加, 由模型一中的-1 698变为模型四的-1 530, 这说明了模型的拟合优度在增强。此外4个模型的伪R2数值呈上升趋势,说明拟合效果变好,模型更具解释力。
(一)模型一用以分析性别、年龄、民族、教育程度、年收入等人口学特征的变量与社区居民安全感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民族与社区居民安全感之间在统计上是不显著的(p>0.05);性别、年龄、教育程度、个人总收入与社区居民安全感之间在统计上是显著的(p<0.05)。其中,与女性相比,男性的社区安全感是女性的1.28倍。此外,年龄也是影响社区居民安全感的重要因素,年龄每增加一岁,社区安全感增强1.88。不同的教育程度对社区安全感知状况也存在差异,教育程度在大学本科及其以上的居民的社区安全感是大学本科以下学历的居民的1.42倍。
(二)模型二加入自变量邻里熟悉程度,用以分析邻里熟悉程度与社区居民安全感之间的关系。如模型二所示,自变量邻里熟悉程度在0.05以上的水平显著,其p值小于0.001这表明邻里熟悉程度对社区居民的安全感影响十分显著。该模型风险比的含义是指:在控制人口学特征下,与邻居熟悉的居民的社区安全感是与邻居不熟悉的居民的社区安全感的1.7倍。这验证了假设一,邻里熟悉程度越高,社区居民安全感越高。根据社会解组理论,转型区域社区邻里面临的首要困境便是邻里的陌生感。城市化进程使得传统的居住格局发生改变,一座座的居民小区使得人们的人际联系伴随着陌生的社会环境日益弱化。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提出,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血缘与地缘为纽带遵循人治、遵循人情、遵守惯例的熟人社会[24]1-8。知根知底的关系犹如一张蜘蛛网联结着个人,形成无形且稳定的控制。而今,相对隔离的居住环境减少了交往机会,使得邻里间熟悉程度与紧密程度减弱。弱化、松散的邻里意识,导致社区无法形成牢固的共同体意识,为滋生犯罪提供了社会环境条件。而松散的社会环境、无序的社区状态会逐渐内化成个人内心的不安感,使得个人社区安全感较低。
(三)模型三在模型二的基础上引入自变量邻里交往程度。研究表明p值在每年几次、每月几次和每周至少一次三个交往频率上均小于0.05,这表明邻里交往程度对社区居民安全感有显著影响。回归结果显示:邻里交往无论是每年几次、每月几次还是每周至少一次的居民的社区安全感均比从来不与邻居进行社交活动的居民的社区安全感高,也即邻里交往频繁的居民比邻里社交不频繁的居民拥有更高比率的社区安全感。这就验证了假设二。社会解组理论认为,一个在社会层面组织有序的社区,具备三个特征:团结一致、凝聚力和整合。其中整合是指居民定期进行社会互动的频率。高度整合的社区使得居民采取一种非正式、非官方的形式预防犯罪、控制犯罪,并在无形中强化了居民的安全感。如社区居民能对单元、楼道内出现的陌生面孔做到有效察觉、重点关注,又如居民能对邻里间可能萌发的纠纷及时发现,并有效化解。然而,现代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交往的匿名性。当人们从传统的道德共同体中抽离出来,新型的浅层化人际交往使得原先紧密的邻里关系受到挑战。在人口大规模集中的城市,相对隔离的现代社区居住环境限制了人际互动与交往,使人际间日渐呈现陌生化,匿名化,冷漠化的特征。这种匿名感、陌生感与冷漠感不仅使得社区天然的监控功能在丧失也在不断加剧社区居民的不安感与焦虑感。
(四)在模型四中加入自变量邻里信任程度。统计显示自变量邻里信任程度与因变量社区居民安全感之间在统计上是显著的(p< 0.05)。研究表明认为邻居可以信任的居民的社区安全感是认为邻居不能信任的居民的社区安全感的1.52倍,这证明了邻里的信任程度与社区居民安全感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验证了假设三。社会解组理论对此可作出合理的解释,其认为当居民存在相互信任和凝聚力时,便会认识到社区中的问题以及就如何处理社区中存在的问题形成共识,且将会以更加集体性的方式解决问题。然而,在现在社会环境中,地缘信任逐渐被消解,社会环境中的不安全状态会内化为个人的不安感。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曾指出,本体性安全感与信任是紧密关联的。信任是本体性安全感的重要基础[25]80-98。在前现代性社会,信任有四种类型,其中之一就是地缘。在为人所熟悉的地域环境下,有助于本体性安全的构成。换言之,即使是在现代语境下的社区,只要保持邻里间频繁的交往互动,在为人熟悉的社区地域环境下邻里间仍然能产生信任感。这种邻里间的信任感相互交织、相互感染则形成稳固、持续的社区安全感。

表 2 对社区居民安全感的Logistic分析
注:*p< 0.05, **p< 0.01, ***p< 0.001
四、 结论与建议
通过分析得出结论:邻里熟悉程度、邻里交往程度、邻里信任程度对社区居民安全感有着显著正相关关系。邻里熟悉程度越高,邻里交往越频繁、邻里信任度越高则社区居民的安全感越高。以上三个方面构成邻里关系对社会治安形成了无形的控制,对社区居民安全感的增强具有促进作用。
鉴于文章结论:紧密的邻里关系是发挥社区的非正式控制功能,增强社区居民安全感的必然要求,本研究建议:
(一)实行邻里守望计划。在英国、美国等国家,邻里守望作为社区警务战略中的一项重要计划,在维护社区治安,改善居民生活质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英国的邻里守望制度不仅限于对社区犯罪的防控而更多是一个综合性质的守望相助项目,涉及便利邻里生活、改善社区环境、帮扶社区弱者、向警方提供犯罪预防与治理意见等诸多方面。该制度为改善现代社会由于急剧变迁造成的淡漠、疏离的人际关系,提高社区居民的安全感带来了一丝希望的曙光。社区的管理不仅需要社区民警与居民之间保持良好的互动与联系,也需要邻里之间配合与互助。引入邻里守望制度,将邻里互助工作作为社区基层建设的重点工作,由此改善社区治安环境、提高居民安全感。
(二)强化社区居民的社会联系,形成紧密的邻里关系。第一,重视社区文化建设。社区文创活动的经常性开展,促进社区居民交往与沟通,形成邻里和睦互助的氛围。第二,建立邻里间的信任感。通过增强信任,强化成员间的认同感,突出社区共同体的内涵,提高社区居民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