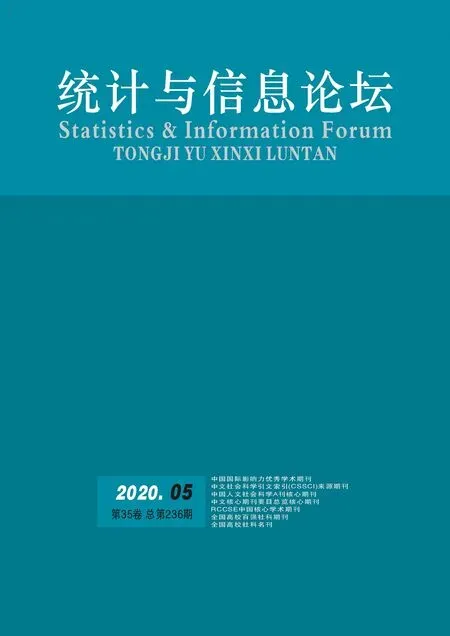独生子女父母养老准备
——基于群体差异的潜在类别分析
封铁英,范 晶
(西安交通大学 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049)
一、引 言
1982年,计划生育政策被纳入宪法,此后独生子女及其家庭以每年440万的速度持续增长,在20世纪90年代,“4+2+1”结构的城市独生子女家庭比例已约占90%,2010年中国独生子女的总量达1.45亿人左右,预测2050年将产生约3.1亿的独生子女,独生子女家庭成为主流的家庭模式[1-2]。随着占到社会相当比例的独生子女父母相继步入老年,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资源劣势逐渐显现。与多子女家庭相比,子女养老资源上的“唯一性”极大地增加了独生子女父母未来的养老风险,赡养与抚养结构“倒三角”和“养老倒挂”同时并存,加之“失独”和“空巢”家庭数量迅速增长使得传统养老资源受到严重挤压,“养儿防老”的传统家庭养老功能不断被削弱,独生子女父母面临的养老保障、养老服务等复杂的养老困局亟待突围。
对于独生子女父母这一特殊群体,各级政府相应出台了一系列的优惠帮扶政策来保障其老年生活。除全国性的老年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补贴等基础政策之外,四川、河南、广西等9省份还建立并实施了“独生子女带薪护理假”制度。然而,由于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尚不完善,财政养老支出规模受限,社会养老服务体系仍不健全等现实问题存在,使得独生子女父母单纯依靠政府和社会支持难以保障和维持未来高质量的老年生活。自身养老的充分准备成为独生子女父母发挥主观能动性,应对未来养老风险的必要途径。本文基于群体差异视角,应用潜在类别分析技术对独生子女父母养老准备的潜在类型进行科学细分,以准确掌握独生子女父母异质性养老准备现状,并通过构建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进一步识别影响不同养老准备类型的关键变量和障碍因素,在有效区分独生子女父母养老准备差异条件下,多角度、多层次、多主体地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以期合理规避养老风险,提升老年生存质量。
二、文献回顾
(一)独生子女父母
根据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和《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领取资格规定,“独生子女父母”是指自愿终身只生育一个子女或者未生育且依法只收养一个子女的育龄夫妻。考虑到中国计划生育国策实施的时间跨度,本研究着眼于1976—1986年出生的第一代独生子女,将独生子女父母初始生育年龄界定为20岁,则调查对象为年龄在52~62岁之间,处于中老年过渡阶段的独生子女父母,为了保证调查样本的代表性和充分性,本文将老年独生子女父母年龄范围适度扩大,将研究对象界定为年龄在45~65岁之间,且只生育一个孩子,并领取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独生子女父母。
(二)养老准备
养老准备是对未来养老做出的准备行为,是规避养老风险的预防性手段,是指为提升未来老年生活质量提前做出的准备和积累,可分为从政府等正式组织获取的正式养老准备和个人、家庭自主进行的非正式养老准备[3]。现阶段,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仅能为老年群体提供基础性保障,若享有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老年生活,需要老年群体自身的努力与积累。张玉美强调中老年人群养老资源的纵向积累,在尚未步入老龄阶段之前提前进行养老储蓄、知识、心理等安排[4]。Carmel等认为通过“准备”等积极的应对措施,可保证老年人在身体功能衰退情况下同样拥有和保持较高的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5]。本文在借鉴2015年花旗银行和友邦保险联合发布的《中国居民养老准备洞察报告》的养老准备维度基础上加入“偏好准备”维度,将“养老准备”定义为个人为有效应对未来养老风险,提高老年生活质量所自主进行的信心准备、计划准备、知识准备、储蓄准备和偏好准备[6]。
(三)独生子女父母养老准备
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有效缓解了人口压力,控制了人口增速过快引发的部分社会和经济问题,同时对传统的家庭结构、家庭功能和家庭关系的转变产生影响[7]。徐俊等认为独生子女家庭面临更为复杂、多元的养老风险,子女的道德风险、失独风险、家庭的经济保障和非经济保障风险均会导致父母陷入养老困境[8]。
独生子女家庭的特殊性决定了父母养老方式与路径显著不同于多子女家庭。纪竞垚认为独生子女父母养老的独立意识更强,更愿意选择社会化的养老方式[9]。周长洪等发现农村独生子女父母在未来养老规划上没有足够的经济和信心准备,并对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依赖性较低[10]。
不同社会人口学特征的独生子女父母,其养老准备存在显著差异。男性比女性更倾向于积极准备和规划未来的养老生活;随着年龄增长、文化水平提高、健康状况和经济水平的改善,养老准备水平也更为充分[11]。随着职业地位的上升,养老准备呈现倒“U”型状态[12],党政机关人员等高职业地位人群的养老准备水平低于企业职工等中等职业地位者[9]。宋雅君利用潜在类别分析法研究发现,倾向于居家养老的群体对养老准备持回避态度,多数独生子女父母对未来养老方式未能进行理性预估[13]。
(四)简要评述
伴随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步入老年阶段,其养老问题及可能面临的养老困局亟待解决。已有研究多涉及养老担心度、养老意愿和养老方式选择,忽视了独生子女父母个体为应对老年生活所需进行的养老准备,且弱化了养老准备存在形式的多样性,未能对其进行更为具体和科学的分类。因此,本文在界定“养老准备”概念的基础上,运用潜在类别分析技术探讨中老年独生子女父母养老准备的潜在形式,并从独生子女父母群体特征视角对不同类别的养老准备进行实证研究,挖掘影响养老准备类别的关键因素,为提高独生子女父母自身养老准备水平、享有高质量老年生活提供支持和决策参考。
三、理论分析
(一)理论基础
1.20世纪30年代希尔和汉森首次提出家庭生命周期理论,1947年格利克(Glick)在《美国社会学评论》发表“家庭生命周期”一文标志着该理论最终确立,他提出一个典型的、完整的核心家庭的家庭生命周期依次经历形成、扩展、稳定、收缩、空巢和解体6个阶段[14],后续研究将其扩大到非核心家庭,及其对家庭经济行为和社会的影响[15]。
关于独生子女家庭,熊汉富将其生命周期划分为形成期、稳定期、空巢期和解散期4个阶段,各阶段的家庭成员结构和经济行为具有鲜明特征[16]。为了更加直观展示各阶段独生子女家庭在心理、经济和社会等资源的动态发展,本文对已有研究表述进行转换,将独生子女家庭生命周期划分为形成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老期,更准确地表现出独生子女家庭的倒“U”型发展历程。通过进一步分析独生子女家庭不同时期家庭结构特征和经济行为,归纳各阶段独生子女父母的主要任务与基本目标,从而科学识别独生子女父母开展养老准备活动的核心准备阶段和拓展准备阶段,细化独生子女父母养老准备过程,突出养老准备的阶段性和必要性。
2.社会分层理论中“分层”一词引入社会学领域后,用以反映社会划分的层次结构。德国社会学家鲁曼提出现代社会以经济水平、文化程度、职业地位等功能系统属性的分层标准[17]。现代西方社会分层理论强调以教育水平为基础的职业地位等因素成为划分社会层次的主要标准。
独生子女父母在年龄、性别等自然属性以及教育水平、职业地位、政治阶层等社会属性上存在差异,是识别社会层级的重要标志。年龄和性别作为社会分层的原始因素,对独生子女父母心理和生理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在成长过程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下,决定了独生子女父母养老准备程度与水平。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独生子女父母的文化程度和职业地位成为决定其所在社会阶层的核心要素,导致其养老准备可利用的资源类型、资源质量和数量具有明显差异性。社会分层理论及其发展脉络为本研究奠定了群体差异分析的理论基础。
(二)理论分析框架
根据家庭生命周期理论,独生子女家庭先后经历形成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老期四个阶段。形成期的独生子女父母年纪相对较轻,处于事业奋斗初期,以追求较高生活质量为主要目标,尚未考虑养老准备相关事宜。相比于多子女家庭,独生子女家庭的成长期存续时间较长,独生子女父母年龄跨度增大,因此面对步入中年压力的独生子女父母需在这一时段的中期开始对未来的养老进行规划与安排,开展针对性地储蓄、保险、投资等经济性准备活动,是养老扩展准备阶段的起始时期。成熟期是独生子女父母进行养老准备的关键阶段,该阶段是子女离家就业,家庭成员减少的空巢期,此时的独生子女父母即将步入退休阶段,养老成为该阶段关注的重点问题。为此,独生子女父母开始积极获取养老政策与健康常识,为退休生活进行较为详细和长远的安排,对未来可选择的养老方式进行心理规划,工作年限与经验积累使得家庭收入达到峰值,用于进行养老准备的资源较为充裕,是进行养老准备的核心准备阶段。衰老期初期的独生子女父母仍具有一定财力和精力开展经济性活动(就业、投资、储蓄等)、社会性活动(锻炼保健、文化娱乐等)以丰富其养老准备,并计划和开展养老活动。然而伴随工资性收入消失,经济水平整体下降,身体机能日渐衰退,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准备拓展阶段结束,前期所积累的养老准备在该时期的中后期得到充分应用和发挥。
相较于多子女家庭,独生子女家庭具有人口数量少、父母与子女间依赖程度高、家庭结构小型化与核心化的特征,生命周期中成长期和成熟期提前且持续时间延长。由此导致独生子女父母中老年阶段延长,养老风险增加,有必要提前积累养老资源,进行充分的养老准备。本文将独生子女父母养老准备分解为信心准备、计划准备、知识准备、储蓄准备和偏好准备。信心准备反映了受访者对未来养老是否乐观和理想;计划准备是指对未来老年生活的具体设想与规划;知识准备是对各类养老政策、知识等信息的了解程度;储蓄准备则是对养老的经济积累与投资收益等金融准备;偏好准备用以反映独生子女父母对各类养老方式的选择偏好和接受程度。在独生子女家庭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其具体的养老准备分布呈现显著差异(见表1)。基于社会分层理论,独生子女父母自身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进一步导致其养老准备潜在类别同样具有群体性差异。

表1 独生子女家庭生命周期的养老准备内容分布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本文构建独生子女父母养老准备潜在类别的群体差异理论模型(见图1),直观、系统地呈现独生子女父母养老准备的阶段性、多元性和差异性特征,为养老准备潜在类别及其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奠定基础。

图1 独生子女父母养老准备潜在类别及影响因素理论分析框架
四、变量设计、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变量设计
1.养老准备变量。本文将养老准备分解为5个维度,其中信心准备由“您对您的养老有信心吗”测量,分为“信心不充分=0”和“信心充分=1”两类;计划准备由“您是否有关于未来的养老计划”测量,分为“计划不充分=0”和“计划充分=1”两类;知识准备由“您是否了解国家关于养老的政策”“您是否了解您当地关于养老的政策”和“您是否了解一些养老保健知识”三题项测量,分为“不了解=0”“一般=1”和“了解=2”这3类,各问题累加得分为独生子女父母养老知识准备得分,得分范围为0~6分,将知识准备转化为二分类,得分0~3分为“知识准备不充分=0”,得分4~6分为“知识准备充分=1”;储蓄准备是指受访者个人积累的养老储蓄程度,“养老储蓄不充分=0”和“养老储蓄充分=1”两类;偏好准备同样通过三题项测量,涉及独生子女父母对居家养老、子女养老和机构养老3种养老方式的实际态度,分为“不接受=0”“一般=1”和“接受=2”这3类,得分范围为0~6分,得分越高说明其对于各种养老方式的接受程度越高,其偏好的养老方式越多,在其偏好准备上越充分,得分0~3分为“偏好准备不充分=0”,得分4~6分为“偏好准备充分=1”。
2.群体差异变量。根据社会分层理论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主要划分依据,本文选取性别和年龄、文化程度和职业地位分别作为研究对象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表征变量,其中“性别”为二分类变量,“男性=1”“女性=2”;将“年龄”划分为“45~55岁=1”“56~65岁=2”两类;将文化程度归纳整理为三个有序变量,分别为“小学及以下=1”“中学、中专=2”和“大专本科及以上=3”;综合考虑各职位在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上的占有状况,将职业地位划分为三类,“低职业地位=1”代表农业劳动者和失业人员,“中等职业地位=2”代表商业服务人员、产业工人和个体工商户,“高职业地位=3”代表党政机关公务员、企事业单位管理技术人员、经理人员和私营业主。
3.影响因素变量。本文强调独生子女父母作为准备主体为未来老年生活在心理、计划、知识、经济和偏好上进行的积累,与其自身社会学特征紧密相关。除性别、年龄、文化水平、职业地位4个变量之外,根据已有研究成果,加入健康状况自评、经济状况自评、夫妻关系和与代际关系等变量[4],将其纳入影响因素变量的范畴。
(二)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只生育一个孩子且领取了独生子女证的独生子女父母为目标群体,于2017年7月至9月在陕西省西安市开展“独生子女父母养老准备”问卷调查,调查对象为年龄在45~65岁之间的西安市辖区内独生子女父母,调查内容为父母基本信息、社会特征、家庭状况和养老准备等。综合考虑西安市各区(县)距市中心的地理位置和人均GDP,第一步采用典型调查法选取新城区、雁塔区、未央区、长安区和鄠邑区5个具有典型性、经济差异明显的区(县),第二步对所选择的区(县)下的乡(镇或街道)、村(社区)进行分层多阶抽样,并对抽取的村(社区)中的符合研究对象要求的全体独生子女父母进行问卷调查。本次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410份,收回有效问卷399份,有效回收率97.3%,样本分布见表2。

表2 独生子女父母养老准备调查样本分布统计
(三)研究方法
1.潜在类别分析。本文从自我感知和行为特征聚焦独生子女父母养老准备状况,应用Mplus7.0统计软件对其养老准备5个变量下9个可直接测量题项进行潜在类别分析(LCA),通过潜在的类别变量对养老准备各外显变量间关系进行估计和解释,最终判断养老准备的潜在类别及分布比例,从潜在类别模型上表示为t个类别的潜在类别变量X,存在A、B、C这3个显变量的潜在类别模型可以表示为[18]:
(1)

2.卡方检验与多元逻辑回归。利用SPSS20.0对各个类别在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地位中的分布进行卡方检验,了解不同类别养老准备下独生子女父母的群体差异。卡方检验是以χ2分布为基础的一种常用于计算独立列联表中两个分类指标关联性的检验方法,基本假设H0为独生子女父母群体特征与其养老准备不存在关系,基于此计算出统计量χ2,根据χ2分布及自由度可以确定在H0假设成立的情况下获得当前统计量及更极端情况的概率P。当P值<0.05,说明观察值与理论值偏离程度太大,应拒绝原假设,表示群体特征在各养老准备类型之间有显著差异,否则接受原假设。
本文选取独生子女父母的性别、年龄、夫妻关系、代际关系、经济状况自评、健康状况自评、文化程度和职业地位等自变量,应用多项逻辑回归分析识别出影响独生子女父母养老准备类型的关键变量。多项逻辑回归用于响应变量类别在两类以上的多因素分析,本文基于潜在类别分析技术将独生子女父母养老准备进行类别划分,设定养老准备为K个类别,以其中第k个类别为参照类,将各自变量记为Xi,α与β分别表示第j类的常数项和各解释变量系数,多项逻辑回归模型可表示为:
(2)
其中j=1,2,…,k-1;π1+π2+…+πk=1。
五、结果与分析
(一)样本描述性分析
通过对399份问卷数据进行整理、清洗,处理和删除关键变量上存在缺失值和无效值的样本,最终得到用于实证分析样本368份,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3。
(二)独生子女父母养老准备潜在类别分析
本文采用Mplus7.0软件,对独生子女父母养老准备进行潜在类别分析。由潜在类别模型(1)~(4)配适度结果可知(见表4),随着分类数目的增加,当类别为4时模型的LMR和BLRT的P值不再显著,潜在类别的选取结束。AIC指标适用于小样本量情况,当潜在类别为3时,模型的AIC(2 175.207)统计量最小,表明模型(3)配适度最高。同时,模型(3)的Entropy值为0.758近似于0.8,表明分类准确率超过90%。因此将独生子女父母养老准备划分为3种类别最为合适。
依据潜在类别模型配适度检验结果,本文得到独生子女父母养老准备的类别概率和条件概率。结合独生子女父母养老准备的5个维度——信心准备、计划准备、知识准备、储蓄准备和偏好准备的类别系数(见表5)对3种养老准备类型进行命名,类型1:养老准备缺失型,该类独生子女父母在各项养老准备上都严重缺乏,充足程度皆低于其他两类;类型2:养老准备不足型,该类的独生子女父母养老准备整体水平高于类型1,且在储蓄准备(100%)和偏好准备(72.9%)上的准备充足;类型3:养老准备充足型,该类独生子女父母群体的养老准备整体水平最高,具有充足信心准备(80.7%)、计划准备(83.1%)、知识准备(66%)和偏好准备(89%),概率显著高于前两个类型。

表3 调查对象基本信息(m=368)

表4 独生子女父母养老准备潜在类别模型配适度比较
注:***表示1%的显著性水平上,k个类别的模型显著优于k-1个类别的模型。

表5 独生子女父母养老准备的条件概率
(三)独生子女父母养老准备群体差异分析
根据后验概率将每个独生子女父母匹配到最能代表其养老准备状况的3个潜在类型中,根据社会分层理论中的自然属性标准(年龄、性别)和社会属性标准(文化水平、职业地位)对不同类型的独生子女父母养老准备进行群体差异比较。由潜在类别分析结果(表6)可知,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准备水平整体偏低,“养老准备不足型”的独生子女父母占比最大,为58.2%,其次是占比33.2%的“养老准备缺失型”,“养老准备充足型”的独生子女父母占比最少,仅为8.7%。不同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和职业地位的独生子女父母群体在养老准备中存在显著差异。相对于年龄较轻(45~55岁)的人群,年龄较长(56~65岁)的独生子女父母养老准备更加充分;独生子女母亲的养老准备水平高于独生子女父亲,这与王树新的研究结论“独生子女母亲对养老的担心度高于男性”相一致[20];与养老准备不足型群体相比,在养老准备充足型和养老准备缺失型两类群体中,独生子女父母的文化水平和职业地位都较高。

表6 独生子女父母养老准备类型的群体差异分析
注:**、***分别表示1%、5%的显著性水平。
(四)独生子女父母养老准备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构建多项逻辑回归模型分析3类独生子女父母养老准备类型的影响因素(见表7),研究表明,独生子女父母的年龄、性别、夫妻关系、健康状况自评、经济状况自评对其养老准备具有显著影响,而文化程度、代际关系和职业地位则对养老准备的影响不显著。与准备充足型相比,年龄越长的独生子女父母更倾向于准备充足型,而年龄越轻的独生子女父母在养老准备上越不充分,这与年龄群体差异分析中的结果相互印证,年龄较长的独生子女父母多处于工作向退休转换的过渡期与老年生活适应期,相比于年龄较轻的父母,老年独生子女父母面临的养老问题更为严峻和迫切,对退出劳动领域后即将面临的养老问题产生更多思考和计划,养老准备相对充足;独生子女父亲更倾向于准备缺失型,受到“男主外,女主内”等传统文化的影响,男性承担着家庭生计的主要责任,因此其将更多的精力投入于工作,相比于女性较少考虑较为远期的养老问题,养老准备程度低于独生子女母亲;子女养老资源的唯一性促使独生子女父母将对子女的依赖转移到伴侣之间,因此独生子女父母的夫妻关系越和谐,相互给予的养老支持越多,其在养老准备上越充分;认为自身健康状况一般的独生子女父母在养老准备上更倾向于准备缺失型和准备不足型,健康状况不佳使其在养老准备上力不从心,医疗、保健等费用支出削减了其财富积累,养老准备水平低于健康状况良好的独生子女父母;经济状况是决定养老准备程度的重要因素,经济状况自评一般的独生子女父母更可能属于养老准备不足型,经济拮据使得该群体难以有较多剩余资金和精力用于养老准备的积累,相比于经济状况良好的独生子女父母在养老准备上较不充分。
六、结论与建议
独生子女父母养老准备涉及心理、计划、知识、储蓄和偏好等多个维度,为客观、清晰且简洁地反映独生子女父母养老准备类型及群体差异,识别独生子女父母养老准备类型的关键影响因素。本文基于家庭生命周期理论和社会分层理论,构建独生子女父母养老准备潜在类别及影响因素理论分析框架,从理论层面论证独生子女父母养老准备的必要性与差异性,以及开始着手养老准备的最佳时期;应用潜在类别分析技术识别和提炼独生子女父母养老准备类型,将其划分为“养老准备缺失型”“养老准备不足型”和“养老准备充足型”3类,发现“养老准备充足型”的独生子女父母占比最少,养老准备整体水平偏低;对独生子女父母养老准备群体特征进行卡方检验后发现,不同性别、年龄、文化水平、职业地位的独生子女父母群体在各养老准备类型中存在显著差异;由多元逻辑回归分析结果可知,独生子女父母的年龄、性别、夫妻关系、健康状况自评和经济状况自评均对其养老准备类型归属具有显著影响。

表7 独生子女父母养老准备潜在类型影响因素的多项Logistic回归结果
注:参考类别为准备充足型。*、**、***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
基于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结果,本文从政策保障、社会支持和自身积累三方面提出有利于加强独生子女父母养老准备的对策建议:
1.建立和完善政府对独生子女父母养老的政策补偿机制。本文研究发现独生子女父母的自身养老准备水平整体较低,且不同群体间的养老准备差异较大,仅依靠单一主体努力难以保障独生子女父母较高质量的养老生活。对于独生子女父母这一特殊群体,政府应承担起保障性、基础性的必要责任,根据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和独生子女家庭的收入水平,对不同社会经济层次的独生子女父母提供相应的经济补偿,对高龄、失独、失能、孤老等困难独生子女父母给予政策倾斜,建立困难独生子女父母养老专项基金等帮扶机制。关注以农民和农民工为主体的低职业地位与文化水平的独生子女父母,加大对独生子女死亡伤残家庭的扶助力度,为其养老准备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
2.完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提升独生子女父母社会养老服务可得性。本文研究发现独生子女父母与子女间的代际关系对其养老准备的影响不显著,表明独生子女父母对以子女为供养主体的传统家庭养老方式的依赖性明显减弱,对社会养老服务的需求迅速增加。社区作为老年独生子女父母家庭养老生活延伸的主要场所,应增设养老活动空间与养老设施,增强社区养老服务能力,打造社区居家综合养老服务平台。充分发挥机构养老的补充作用,建设一批专业化、层次化、可及性强的养老机构,对不同需求偏好的独生子女父母提供针对性、配适性强的机构养老服务,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和政策倾斜,降低独生子女父母养老服务购买成本,保障其基本养老生活。
3.“多管齐下”缓解独生子女赡养压力,强化家庭养老主体地位。本文研究发现,当独生子女父母的健康自评状况越差时,其养老准备程度与水平越低,抵御未来养老风险的能力越弱。此时独生子女父母亟需来自亲人的照护与慰藉,但相对于代际关系而言,配偶间关系的融洽程度对独生子女父母养老准备类型的影响更为显著,子女唯一性迫使其父母降低了对子女的依赖性,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家庭作为养老主要场所的作用。因此,应通过适度延长独生子女探亲假期,建立独生子女护理假制度,鼓励和补贴母子房供给等多元政策措施,突破子女赡养父母的时间和空间限制,强化多部门协调联动,为独生子女“尽孝”与“尽职”创造便利,提升独生子女父母老年生活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