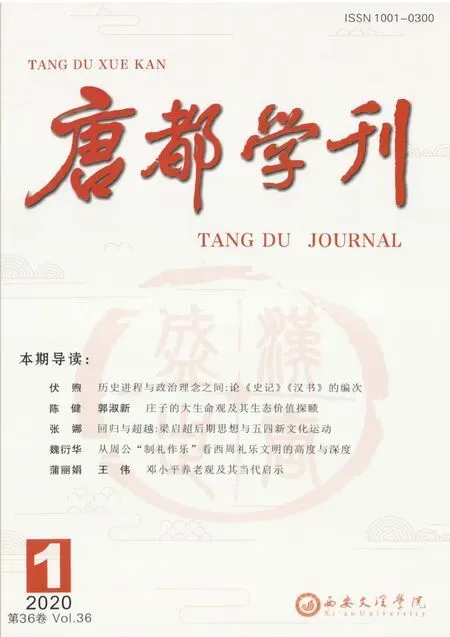自然灾害视域下的西周末期政治重心东迁
潘明娟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关中历史文化研究中心,西安 710126)
关于西周末期的政治重心东移,大部分学者等同于“平王东迁”的历史事件。平王东迁的原因,《史记》提出“周避犬戎难,东徙雒邑”。由于文献记载语焉不详,近现代学者就平王东迁原因提出异议,钱穆先生指出:“《史记》不知其间曲折,谓平王避犬戎东迁。犬戎助平王杀父,乃友非敌,不必避也。”[1]蒙文通先生也认为:“犬戎党于平而夺平地,秦敌于平而平封爵之,皆事之必不然者。”[2]王玉哲先生指出:“平王东迁,明为避秦”,而不是逃避犬戎[3]。晁福林认为:平王东迁洛邑“一是丰镐不仅残破,而且邻近西戎和正在崛起的秦国,故不如迁往东都洛邑安全。二是洛邑位居天下之中,八方辐凑,经济发达,并且支持周王室的晋、郑、卫等都在洛邑附近。”[4]于逢春则持“投戎避秦”之说[5]。王雷生推而广之,认为平王东迁是因为“受逼于秦、晋、郑等诸侯”[6]。董惠民在逐条批驳于逢春的观点后,提出东迁的原因是“王室衰微,东依晋郑”[7]。以上观点,有相近之处,如晁福林、王玉哲、于逢春、王雷生等学者均持“避秦”之论;有的则完全相反,如晁福林认为东迁避戎,于逢春则认为“投戎”,又如王雷生认为东迁避晋郑等诸侯,晁福林、董惠民等则认为晋郑诸侯支持周王室。这些论述主要是从当时的政治斗争及诸侯势力、戎周关系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仅于逢春在其文章中提到了平王东迁的原因之一“是为了摆脱连续几百年的天灾所造成的困境”[5],但这并不是其论述的重点。
政治重心的东移是一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不能仅局限于平王东迁事件本身进行论述;同时,政治重心的东移是诸多因素包括内政外交、军事力量、社会经济等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着重探讨自然灾害对西周末期政治重心变迁的影响。
就本文主题而言,有两个问题需要界定:第一,研究时段。西周末期应是周厉、宣、幽三王在位时期,自公元前878 年周厉王即位至公元前770 年周平王东迁(1)关于平王东迁的时间,学界有不同观点,参见王雷生《平王东迁年代新探——周平王东迁公元前747 年说》(《人文杂志》1997年第3 期,第62-66 页)、王红亮《清华简〈系年〉中周平王东迁的相关年代考》(《史学史研究》2012 年第4 期,第101-109 页)。本文采用学界普遍观点,认定周平王东迁时间为公元前770 年。108 年的时间。第二,政治重心。西周时期有三座都城:岐周、宗周、成周。岐周是先周时期的政治重心,即主都;西周初期的主都为宗周丰镐,岐周为圣都、陪都,成周洛邑为陪都;西周末期,政治重心逐渐东移至成周洛邑,至东周初年正式迁都。政治重心的转移过程,与政治、军事、社会、经济等各方面因素分不开,当然,自然灾害也是影响政治重心转移的因素之一。
一、西周末期黄河流域的自然灾害
关于西周时期的自然灾害研究,学界有先秦灾荒的总体研究(2)参见刘继刚《中国灾害通史·先秦卷》,郑州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聂甘霖,陈纪昌《先秦时期的自然灾害与政府应对》,载于《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刘进有《先秦灾害问题述论》,载于《兰州工业学院学报》2015年第6期。;有不同灾害的专题研究,包括水灾、旱灾、虫灾、地质灾害等(3)参见尧水根《先秦至秦汉水旱灾害略论》,载于《农业考古》2013年第4期;程天宝《试论先秦时期的水灾与赈济》,载于《河南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刘继刚,何婷立《先秦水灾概说》,载于《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2007年第2期;胡其伟《先秦农业中的虫灾简析》,载于《农业考古》,2016年第4期;王元林,孟昭锋《先秦两汉时期地质灾害的时空分布及政府应对》,载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有灾异观念、应对措施等(4)参见李亚光《周代荒政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陈艳丽《先秦防灾救灾经济思想研究》,山西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李瑞丰《先秦两汉灾异文学研究》,河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其中,《中国灾害通史·先秦卷》汇总了西周旱灾11 次,火灾1 次,地震4 次,风灾1 次,雹灾2 次,饥荒1 次,瘟疫1 次,天气异常1 次[8]P26。西周自然灾害研究最为详细的是吉林大学李亚光的博士论文《周代荒政研究》,其论述了西周时期的灾情,分析了西周灾害发生的规律。在灾害影响的研究方面,上述论著普遍关注了灾害对经济(尤其是农业经济)的影响,较少关注灾害与政治的互动,尤其西周末期厉、宣、幽时期灾害情况及其对政治的影响,尚未见专题论述。
(一)西周时期黄河流域的气候变迁
气候的变迁在周人的兴衰史中起着巨大的作用。邓拓认为中国先秦灾害的形成与其历史上气候的变迁和具体的地理环境是密不可分的[9]。
西周时期的气候变迁,学界有诸多论述,范围大多集中在黄河流域甚至黄河中游地区。竺可桢先生指出,公元前11世纪到8世纪黄河流域发生了持续不断的旱灾。而长江流域受旱灾影响较小,相反却是一个比较寒冷的时期[10]。杨铭、柳春鸣认为“从周平王以降,历经厉、宣、幽、平时期,将近三百年,至少在黄河流域,经历了一个寒冷转向干旱的气候变化”[11]。具体到黄河中游地区,黄春长通过对渭河流域全新世黄土的研究也证明西周早期渭河流域气候干旱[12]。李喜峰认为:西周时期,黄河流域气候的主要特征是干早寒冷, 尤其是在西周后期的厉、宣、幽王时期, 黄河中游地区气候严重干早[12]。还有学者认为我国商周时期正处于气候上的一个冷期, 地壳活动剧烈导致当时地震频繁[13][14]。
以上研究都证明:西周时期确实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寒冷与干旱的气候变化。这种变化影响了气温和降雨,给人们带来了严重的灾荒,进而影响农业生产,重创当时的农业经济。不仅如此,灾荒还影响着周王室的内政外交及军事力量的重新分布,导致政治重心的转移。
(二)西周末期黄河中游的自然灾害
西周末期黄河中游的灾害主要为旱灾、寒灾和震灾(5)灾害统计原则,见 《古代旱灾及政府应对措施——以西汉关中为例》一文(《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1 年第6 期,第1064-1068 页)。。
1. 旱灾
西周末期旱灾是非常严重的。《隨巢子》曰:“厉幽之时,天旱地坼。”[15]梳理文献可知:周厉王、周宣王、周幽王在位108 年间,共发生旱灾14 年次,平均每7.714 年发生1 次,频率为0.130 次/ 年。以每10 年为一个时段整理旱灾发生次数,可以看出公元前828—前819 年的10 年间旱灾爆发7 年次,最为频繁;前858—前849 年的10 年间旱灾爆发5 年次;前808—前799、前788—前779 年两个时段旱灾为1 年次;其他时段没有旱灾发生。

图1 西周末期黄河中游旱灾次数
因此,蒙文通先生总结这段历史时说:“厉、幽、宣、平凡历一百五十余年, 而旱灾与人民之流徙不绝于诗, 此国史上一大故也。”[16]
2. 寒灾
西周末期气候逐渐变冷,寒灾也逐渐增加。相关文献记载,西周末期黄河流域发生寒灾2 年次,分别发生于周幽王四年(前778)(6)《今本竹书纪年疏证》记载:“(幽王四年)夏六月,陨霜。”、周幽王九年(前773)(7)《纲鉴易知录》记载:“戊辰,九年,夏六月,陨霜。”。夏六月出现陨霜,是天气寒冷的极端表现。
3. 震灾
据文献记载,西周末期地震灾害2 年次,分别发生于周幽王二年(前780)(8)据《国语·周语上》记载:“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史记·周本纪》也有同样的记载:“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和六年(前776)。《诗经·小雅·十月之交》(9)郑玄《毛诗传笺》定此诗为厉王时诗,但诗序认为:“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清人马瑞辰认为“(郑)笺以为刺厉王者,实本鲁诗及中侯。但梁虞廣刂、唐傅仁均及一行并推算幽王六年乙丑岁建酉之曰辛卯朔辰时日食,……与此诗‘百川沸腾,山冢崒崩’正合,则仍从《毛诗》刺幽王为是。”记载了前776 年这次地震的情形,“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
统计西周末期黄河中游的旱灾、寒灾和震灾,得出:西周末期旱灾、寒灾、震灾三种自然灾害共计18 年次,平均每6 年发生一次,频率为0.167 次/ 年。
西周末年自然灾害的频繁,正如《国语·周语下》所记载:“自我厉、宣、幽、平而贪天祸,至于今未弭。”[17]P99
二、自然灾害对西周末期政治重心迁移的影响
在严重的天灾背景下,西周末期的社会经济、政治统治也是岌岌可危。西周末期政治重心的转移是在特定灾害背景下的一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灾害严重打击了黄河流域的社会经济,导致周王朝的政治重心逐渐转移。
(一)西周末期自然灾害对黄河流域社会经济的严重打击
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对西周末期黄河流域尤其是黄河中游地区的社会经济是非常严重的打击。
周厉王二十二年至二十六年连续五年的大旱,具体情况我们无从得知。但是公元前842 年爆发的国人暴动的背景是周厉王任用荣夷公实行“专利”政策。则周厉王的经济改革,可能与之前连续大旱造成的农业歉收、财政困难是分不开的。从政治上来说,国人暴动直接打击了周王室的统治权威。

表1 西周末期自然灾害发生年次表
共和十四年(10)《古本竹书纪年》“厉王”条:“共和十四年,大旱,火焚其屋,伯和篡位立,秋又大旱,其年,周厉王死,宣王立。”至宣王初年,是连续七年的干旱。周宣王二十五年(前803)也发生了一场大旱。《春秋繁露·郊祀》记载:“周宣王时,天下旱,岁恶甚, 王忧之。”[18]《诗经·大雅·云汉》描述的旱灾,虽然学界对旱灾时间有不同观点,但大部分都认为是周宣王时期(11)学界对《诗·大雅·云汉》写作时间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认为做于宣王初年(见朱鹤龄:《诗经通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9 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年,第642 页),历代学者如王质、严粲、牟庭等赞同此说。另一种意见是《诗·大雅·云汉》做于宣王中期,何楷(见《诗经世本古义》,《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1 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年,第513 页)、钱澄之(见《田间诗学》,《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4 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年第697 页)赞同此说。不论作于宣王初年还是宣王中期,《云汉》描写的旱灾都是非常严重的。。周宣王时期的旱情非常严重,“旱既大甚”,没有任何方法阻止“则不可推”“则不可沮”。旱灾造成的后果,首先是农业颗粒无收,“昊天上帝,则不我遗”;其次,百姓流离失所,“周余黎民,靡有孑遗”;第三,政治秩序散乱,“散无友纪”。这次大旱“岁恶甚”,从社会经济、政治秩序各方面打击了周王朝的统治。
周幽王在位12 年,发生旱灾1 年次,寒灾2 年次,震灾2 年次,平均2.4 年发生一年次灾害,较之周厉王和周宣王时期更加频繁。寒灾“夏六月陨霜”,未到时节而严霜下,会使大豆等农作物枯死。寒灾加上旱灾,对农业经济的影响尤其巨大。《诗经·小雅·谷风》:“习习谷风,维山崔嵬。无草不死,无木不萎。”传曰:“虽盛夏万物茂壮,草木无有不死叶萎枝者。”[19]严重震灾又造成了河流山川地形、地貌的巨大变化,“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这些灾害对西周末期黄河流域社会经济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尤其是震灾严重的宗周。
(二)宗周与成周军事地位的变化
西周末期一百多年的天灾导致黄河流域生存环境恶化,经济大幅衰退,社会秩序也迅速崩坏。为了稳固政治统治,周王朝开始把经营重心转移向南方、东南江汉和淮河流域,进行军事扩张和经济掠夺。许倬云认为:“自从昭穆之世,周人对于东方南方,显然增加了不少活动。昭王南征不复,为开拓南方的事业牺牲了生命,穆王以后,制服淮夷,当时周公东征以后的另一件大事。西周末年,开辟南国,加强对淮夷的控制,在东南持进取政策。”[20]在这种背景下,宗周和成周的军事、经济、政治地位发生了明显变化,政治重心开始东移。上述的“谓尔迁于王都”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周末期政治重心的变化。
首先,气候灾害背景下,宗周成为被动防御戎狄入侵的前线。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一方面导致黄河流域的社会秩序和农业经济遭受严重打击,另一方面,也会迫使游牧民族南下(12)面对干旱和寒冷的气候,“受影响的狩猎居民只有三种出路:一是追随他们所习惯的气候环境,追随猎物向北或向南移动;二是留居原地,靠不怕干旱的生物勉强过活;三是仍然留在原地,通过驯化动物和从事农业把自己从恶劣的环境中解脱出来”。大部分情况下,游牧民族是追随他们习惯的气候环境移动的。(见阿诺尔德·汤因比著,曹未风等译:《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86-87 页),导致戎狄入侵,宗周地区沦为对战游牧民族的前线。


其次,成周成为对东南夷掠夺战争的基地。丰镐地区的被动性防御军事行为动摇周王室政治权威的同时,随着周王朝的经营重心向南方、东南江汉和淮河流域转移,成周洛邑成为重要的军事基地。以洛邑为基地的与东夷、徐戎、淮夷等方国部落之间的主动战争则不断取得胜利。“更多的是周王朝主动派军对南方蛮夷‘不臣’或‘不贡’的征伐”。[23]相关战争青铜器铭文中的记载很多。如厉王时期的虢仲盨盖、宗周钟、敔簋、禹鼎、鄂侯御方鼎、晋侯稣编钟等铜器铭文均提及对南夷或南淮夷的军事行动,最终“厥献厥服”。其中,晋侯稣编钟详细记述了晋侯稣随周厉王东征的经过。厉王三十三年,王亲省东国南国,正月,从宗周出发,二月至成周,随即往东,三月王亲会晋侯率乃师伐夙夷,进击城,大获斩俘。王还归成周。六月,王两次召见晋侯稣,亲赐弓矢、马驹等,晋侯稣因此作钟。[24]宣王时期也有对南方征伐的文献资料,如《诗经》中的《小雅·采芑》《大雅·江汉》《大雅·常武》。幽王时期,即使已经衰微,周人仍然没有放弃对南方和东南地区的经营,如《小雅·渐渐之石》毛诗序曰:“下国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乃命将率东征。役久病于时,故作是诗也。”
比较以宗周为中心的对西北戎狄的防御战争和以成周为中心发动的对东南夷的掠夺战争,会发现西周末期宗周和成周的军事地位出现了很大差别。
(三)宗周和成周经济地位的变化
旱、寒等气候灾害对宗周和成周均有影响,震灾则严重打击了宗周的社会经济。随着周王朝经营重心的转移及宗周成周军事地位的变化,二者的经济地位也发生了明显变化。成周洛邑拥有大量的诸侯贡赋和从东南夷掠夺来的物资囤积,也就是说,在丰镐地区经济实力锐减的同时,洛邑逐渐成为经济中心。
成周作为西周在中原地区统治的据点,主要的经济职能是征收赋税,囤积物资。洛邑的经济地位在“四方入贡道里均”[21]133这句话中有鲜明的体现。应该说,洛邑不仅是对周围郊甸地区征发人力物力的中心,而且是对四方诸侯征收贡赋的中心,更是对四方被征服的夷戎部族或国家征发人力物力的中心。分封制规定,各诸侯国对天子必须承担纳贡的义务。而洛邑为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相对均等且水陆运输都很方便,自然成为四方诸侯入贡的中心。
西周末期,成周作为对东夷和南淮夷进行财富掠夺的军事基地,囤积了大量的掠夺物资,导致成周进一步成为经济中心。西周末期,虽然周王室已日渐衰弱,但南夷淮夷仍然不得不向周王室缴纳贡赋。《兮甲盘》铭文:“王令甲(兮甲)征司成周四方积,至于南淮夷。淮夷归我帛亩人,毋敢不出帛,其积、其进人、其贮,毋敢不即次,即市。敢不用令,则即井(刑),菐(扑)伐。”[25]周宣王派出辅佐大臣兮甲,也就是尹吉甫,亲自主持征收东方的贡赋。南淮夷是向西周贡纳粮食和布帛的少数族,所以称为“归我帛亩人。”兮甲到了南淮夷,强迫征收粮食、布帛,并且还要进献奴隶,否则就要用武力征伐。西周晚期的驹父盨盖也说明了周王室对南夷和东夷的贡纳征收。驹父盨盖属西周晚期,有铭文82 字,记录了周王十八年正月,“南仲邦父命驹父即南诸侯,率高父见南淮夷”,索取贡纳,淮上小大诸侯无敢不奉王命,“不敢不敬畏王命”,“厥献厥服”。四月驹父还至于蔡,历时三月。[26]西周末期,诸侯的贡献集中到洛邑,从东夷、淮南夷掠夺的贡纳品也聚集在洛邑。据此看来,西周末期丰镐和洛邑经济地位是不同的。
(四)宗周和成周政治地位的变化
很明显,连年的严重灾害,影响了农业收成,社会经济遭到打击,使百姓陷入饥馑,四散流亡;社会秩序迅速崩坏,人心不稳;政治局面混乱,朝廷对内对外的政治控制力都在下降。周王室统治所依赖的社会、经济、政治基础分崩离析,政治重心的转移、政权的覆亡就是必然的结果。《史记·周本纪》云:“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原又塞,塞必竭。夫国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征也。”[21]145-146《国语·周语》也有类似的记载[17]26-27。将西周末期与夏商之末的自然灾害进行对比,论述的重点是“山崩川竭,亡之征也”,即在自然灾害的背景下,西周的统治秩序会发生较大的变化。
自然灾害背景下,西周末期丰镐和洛邑军事地位、经济地位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会促使政治重心随之变化。
当然,如文首所言,西周末期政治重心的迁移,有其政治、军事、经济等各要素的影响。从政治上来说,内政方面,秦、晋、郑、卫等诸侯与王室错综复杂的关系是其内政影响对政治重心的主要因素;外交方面,戎狄对周王室的威胁是外交因素,也对政治重心的迁移造成一定的影响。从军事和经济上来说,丰镐和洛邑军事地位和经济地位的变化,也是影响政治重心迁移的因素。而西周末期的旱灾、寒灾和震灾等自然灾害,对周王室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等方面均有重大影响。一方面,直接削弱了周王室的经济实力和政治控制力;另一方面,通过西北方戎狄的入侵打击周王室的军事力量,扰乱内政外交,从而成为影响政治重心逐渐东移至洛邑的因素之一。发展到东周初年,由于自然灾害的摧残、戎狄的入侵导致宗周丰镐残破不堪,加上各诸侯的推波助澜,成周洛邑终于成为主要都城,完成了西周末期政治重心的迁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