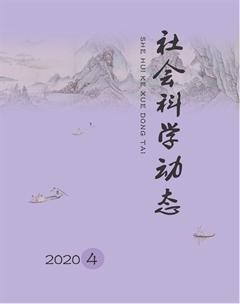荆棘上的明珠:梦幻现实主义风格的雀啼
摘要:胡梅仙的长篇小说《荆棘与珍珠》首创梦幻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让作品成为一个整体的象喻系统。其手法打破了传统的小说叙事章法,运用自然的素材、心灵的镜像、客体化的语境去表达人性的要缈幽微和生命的美好神性。它以心理感应和行为判断,去寻觅个体世界与外部世界的关联,从而将文学即人学的本质得以深层次的呈现。
关键词:《荆棘与珍珠》;梦幻现实;情爱心理;生存困境;女性觉醒
梦是超验的,还是来自生活经验的体验?梦是可以解析的,还是不可理喻的?梦和现实的关系以及和灵魂的关系是神秘不可测的,抑或是具有因果关系且可以被理性认知的?我们只知道梦幻是人类独有的意识方式,和思考一样,属于造物主给予人类独特的礼物。弗洛依德关于梦的解析是从心理学的取样分析入手进行的学术阐释,而胡梅仙的长篇小说《荊棘与珍珠》通过历经生活伤痛和命运磨砺的女主人公珠月的个人心灵成长史,关照其身边诸多女性的生活命运,从而刻画出一个追求美好生活而不得、遭遇困境而不折、梦幻情爱而不能的知识女性的高贵形象。
爱情与婚姻,总有一个在腐坏;身体与灵魂,总有一个不在路上;梦幻与现实,总有一个充满了虚假。这是小说《荆棘与珍珠》呈现出的主体意义。主人公珠月被自我的梦幻牵制和启迪,努力洞悉其中的真实预言,勘破个中虚妄,获得生命能量的迸发,推动自身心灵成长。小说变传统的叙事主线为意识流方式,书写出灵魂之不朽、人生之孤独、爱情之纯正和生命之神圣。在小说艺术手法方面,作品以梦幻现实主义风格的叙事构建尤为突出。本文试从梦幻现实、情爱心理、生存困境和女性觉醒四个层面阐释梦幻现实主义写法的生成原理、演绎机制、哲学认知以及审美意义。
一、梦幻现实
在笔者看来,梦是人类生活在这个星球上的一套隐形的意识系统,是潜伏于日常思维行为里面的,同时具备了相对相向两种特质。现实中想得而不可得的人与事,在梦中得到收割和满足;现实中想避免的危机灾祸,在梦中得到预警和演绎。其深层心理意识则是为了避免灾难真正降临,而潜意识产生的推导式的演绎则强烈地暗示自我,及早进行现实里的危机预防。由此可以推论:梦来源于个体的自我心理保护机制。梦既是心理层面的脑电波副产品,具有记忆备份和自我优化的特点,同时也具有“通灵”的属性,可以接收到所谓“神秘的指引”,梦是一个灵性的空间所在。
梦具有神秘属性和诱引的特性。梦的神秘指引通常被理解为玄虚的或非科学的诱导,笔者对此并不认同。之所以称之为神秘,是由于当下的人类还没有完全透彻研究大脑的思维规律,大脑的开发利用率极低。如果一个人相信宗教神明,对此自然会指认为是“上帝”带来了恩典和启迪;如果他是个佛教徒,自然会认为是“佛陀”带来祝福和礼物。笔者的理解是,梦的通灵来自未知脑力引起的对事物的崭新判断。在极端困境中,一个人在梦中找寻解决方案的路径必然超越狭窄的已知领域,进入到未知层面去探寻答案。故此,梦的答案常常令人匪夷所思。对于认同灵性存在的人而言,大脑在白天是生活和利益的计算器,到了晚上则还原为人与神明之间的交流容器。人向神明或佛陀去倾诉自己的困扰和希望,后者会将答案发送到睡眠中的大脑里,通过梦的方式告知答案。此类的说法皆为一种巧妙的故事性阐释,其真正的核心要点是——梦是有灵性的,可以使现实中僵化的自我得到解救。女性,尤其是像小说中身为知识女性的珠月,恰恰具有这样的灵性特质。
显影与消失,逃遁与闪回,重复与变异,绵延与定格……等等带有非逻辑性的动态画面均属于幻的范畴。幻是梦的附加形式,梦是幻的基本成因。在作者的笔下幻呈现出多样的色彩。梦只是一个平台、一个时间性的场域而已。诱惑才是幻的生成源头。诱惑附着在客体上,对主体欲望的合理性进行了釜底抽薪般的解构。法国后现代主义哲学家让·波德里亚认为:“如果我们从诱惑的角度看,不再是主体来欲求,却是转为由客体来引诱,一切都由客体出发并回归于它,正如一切都始于诱惑而非欲望。”① 幻的根本原理,是来自他者的诱惑。
《荆棘与珍珠》中,现实处境里的情绪投射、现实困境下的他者诱惑以及现实幻境中的本体觉醒,构成了小说女主人公珠月的感情生活全历程,三者循序渐进,也构成了这部现代知识女性生命孤寂的个体史诗小说。具体到小说本身,我们可以发现这三者的表现:现实处境里的情绪投射表现为余清的自私与伤害,因颉的纯正与干净,诗的魅惑与破坏;现实困境下的他者诱惑表现为余清对珠月的怨念,因颉对珠月的渴想和诗对珠月的诱导;现实幻境中的本体觉醒则是珠月对婚姻过往的舍弃,对真爱不可得的释然,对身心侵害者的宽容。
当代法国思想家雅克·朗西埃在《马拉美:塞壬的政治》中谈道:“梦是一种力量,通过目光惊扰另一场表演,通过话语给这场表演打上印记。表演是清晰可见的,比庞大的支架更为清晰。梦是选择显像的视点,充满了景致而非幻象。”② 《荆棘与珍珠》里,在珠月对生命中的三个男人爱恨怨的梦境里,本体的幽怨诉求多以再现式的场景重新演绎,并未过多溢出非理性幻象成分;及至对因颉的思念和自我“心灵赎罪”的时刻,珠月的梦里多了许多幻象的成分,如对因颉身体状况的感应、对因颉情感倾诉的形象透露等,这可以理解为是由客体人物因颉发出的讯息变体。在小说的中间部分,旷诗的出现和他对珠月的感情冲击与生活伤害,也正是多由珠月自身汹涌的精神幻象所预示而引起旷诗性情不成熟的连锁反应,导致现实的行为映入梦中,使女主人公遭受巨大的身心损耗和伤害,进而带到现实生活里构成外在的困境。
阅读这部小说,有些读者会以为通篇都是在讲珠月的梦。珠月梦中和心上人因颉交流,预感弟弟的灾祸,预知余清的背叛等等,梦似乎道出了所有故事。笔者以为,从客体主义哲学的角度看,作者身披主体叙述视角的外衣,行进客体诱惑的身躯,这是带有主观视角的有迷惑性的客体主义写作。客体主义写作更能够征服主体观念,甚至反噬,具体到小说文本,即形成梦幻与现实的并行与交叉的艺术效果。
梦提供拟真的图景,幻造就了心理的变种,梦幻与现实推动了小说情节“超真实”的发展。作者自觉舍弃了传统的主体情感自白和线性的时间架构,改为从心灵底部出发,借助梦幻引出客体为叙事主脉的方式,讲述比表面真实更加具有现实意义的女性自我的灵魂升华。
以加西亚·马尔克斯为代表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家们的创作原则倡导变幻想为现实而不失为真实,而梦幻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则尝试以梦幻阐释指导现实并抵达灵魂的最大真实,这是二者的不同。魔幻现实主义风格写作通过夸张、神话、离奇的情节和人物塑造去反映现实生活;梦幻现实主义则通过客体诱惑对主体欲望的颠覆从而实现精神生活的塑造。两者的手段、用力方向和实现对象都不一样。魔幻现实主义充满了主体的表现主义的幻想,而梦幻现实主义里充满了客体的仿像秩序的投影,这是两者之间本质的不同。
由此,面对珠月这样一位生活经历并不复杂、情感故事脉络集中的小说核心人物,倘若贸然运用魔幻现实主义手法,显然无法有效揭示女性自我的本真情感与成长。这部小说写的是人,是聚焦透射的个体塑造,而不是散射式的群像刻画。因此,梦幻有助于呈现珠月善良纯洁又柔弱坚韧的人格品质,从一个女性的心灵谷底回望她在现实世界的种种困境,这样的写法是合理又可信的。
二、情爱心理
小说《荆棘与珍珠》对当代女性在情感、婚姻、家庭、社会环境中的描画达到了相当繁复多样的境地。灵魂得到自我救赎,孤独保留应有的品味,知识女性的隐忍与修养始终超越平庸生活之上。在不断的内外突围中,珠月的灵魂丰腴起来,在历经苦难之后,她最终懂得了自我如何与外在世界协调,处世更加圆润得当,保护了本我的洁净,达到了精神的自洽。这一切的眼观、耳听、身处与心念,孵化出一位“荆棘遍体、涕血化珠、弹性自如、神性美好”的知识女性形象。
主人公珠月貌似内心波涛汹涌,缠纠于旧爱苦痛无解,滥觞于心上人可望不可及,但在长达八年的离婚冷战阶段,珠月不因余清的冷血而淡忘余清的小善;但她也不会因为余清的自我辩解和花言巧语而迷惑,因余清的品质之退化已成事实,无可挽回。珠月用无视来宽恕对方,开解自己,这也充分证实了夫妻两人之間矛盾的不可调和性,不是因为身体出轨那么简单,而是人与人心灵本质的差别使然。
面对糟糕的几近僵死的家庭生活,珠月的态度是积极的,可敬的,也是无奈的。人性的弱点导致的种种掩饰和伪装行为显得那么不堪。当纯粹的美好心灵遭遇残缺的人格侵犯,其结果必然是前者一败涂地。从社会层面看也是如此。主人公为了保证自我的精神生活不被侵犯,保证和女儿构成的家庭结构不被改变,她选择了有原则的前提下相对弹性的生活态度:有底线的隐忍和精神自救。
珠月出离于现实的被压抑困境,其精神层面反而超越了世俗生活,对比之下人格更庄重又富有高度,情爱更显得珍贵而脆弱。她对外在事物的抵御和对内在情感的守护构成了情爱的弹性空间。一面是自我人心的美好信仰,一面是客体无情的侵略与伤害,珠月如何自处?——灵性帮助了她。
珠月被吉祥的梦境牵引着,得到因颉的现实呼应和网络交流,得以验证灵性的准确性。由此开始认可梦的作用。梦既然是现实的投影,自然需要回到现实中去回应。得到现实回应后的下一个梦,自然会有更新的启示,指导珠月继续去观察、体悟和行动。梦的信息里有记忆痕迹,有事件预演,也有杂芜的、变形的客体投影,即幻。如果没有灵性的潜移默化,珠月显然无法辨析清楚。人们常说女人是感觉的动物,直觉力其实正是从属于灵性主义的范畴。尤其在爱恋中的女性更容易关注生活的点滴细节,从而推衍出各种事件背后的动因,加以质疑和验证。女性的思维里很多细节不是平面式铺陈的,而是立体化突兀的形态,一个又一个不相关的证据,彼此却能产生有效的联系。常识可知,女人的感性判断力远强于仅靠理性思维去思考的男人。
作为一位从底层依靠自己的奋斗攀爬而上的知识女性,珠月曾经遭遇过荒芜岁月里艰辛的生活磨砺,又接受了懵懂爱情的怜悯式心灵悸动的历程,当她发现丈夫余清的背叛行为,她和所有女性一样,焦灼无措。然而不同点在于,知识女性的矜持、尊严、善良和自我清洁的心灵洁癖等特点,使珠月较早地领悟到她与余清的感情的本质其实不是爱情。折磨于显性的冷战与隐性的背叛,女主人公错过了生命中最好的年华。因此可以理解,她随后寄心于网络,在与因颉的博客互动和旷诗的留言中,希求卑微的情感抚慰,然而又在全然失去因颉消息和经受旷诗折磨后不得不退缩到现实唯一的居所,猫成了她唯一的心灵寄托的处境。作者对猫和人的同居生活的着力描写,反映了另一份匠心:通过对猫的描写折射出人的灵性本真,可谓妙笔。——梦境、网络和猫构成了珠月日常的心灵壁垒。“只有有灵性、悟性的人才能获知这些(指梦和感应)信息,他们会找他们的灵魂交流者,听得懂他们语言的人,这是幸事还是不幸,很难说。唯有让人受伤最真实。”③
西蒙娜·德·波伏瓦在《第二性》的扉页上写道:“女人不是天生的,女人是后天形成的。”④ 女性只能作为第二性而存在。社会认知造成了女性天然的情爱损耗,哪怕受尽生活和精神的磨难,女性依然寄居在男性社会的语境下,这是客观而无奈的现状。作者并没有直接将珠月包装成一个百折不挠、一往无前的女战士,她在诸多困境里有挣扎也有沉浸,有惊醒也有反复的消沉。正是这样逼真的原生态的写法,使得情爱的损耗巨大,因此情爱的自我充盈必不可少。面对世俗之余清,精神之因颉和现实之旷诗,珠月所依赖的唯有自我的觉醒与激励、自我的抒情与反省。珠月的自我心灵成长是内化的、渐进的、间接性的。
可以说,去中心的、碎片化的、漫游式的后现代客体主义特征构成了这部小说的结构特点。作者避开传统叙事结构,所有的人物和事件以心灵漫笔和梦幻故事的形式解构,没有强烈的现实剧情和场景故事,只是依赖作者的自述、自白、梦境和周围人与事的倾听等方式徐徐铺展,貌似不经意的提起和念及,的确能够减缓读者的进入难度,但这也增加了阅读的专注力。特别在描写自身对美好情爱的渴求上,作者充分运用意识流加散文诗的自白式写法,诗情激荡,诗意美句和哲理佳句众多,欢心灵爱的形象翩然如仙,充分将灵性与自然、个体意识与宇宙意识接通,语言的主体隐喻和诗化抒情达到极致。“爱你就是在疼痛的泪水中流出珠贝,就是在心痛的每一个瞬间折叠疼痛绽放最心酸最美丽的花朵给你。爱你就是不说话,在每一个晨昏和黑夜,就像抱着一个婴儿,抱着我的一颗心脏。爱你就像你爱我一样,即使自己是疼痛的,也要拼力让天空开满花朵,来给你。”⑤ 这类诗句比比皆是,无疑有助于提升小说整体的语言品味。
三、生存困境
珠月的生存困境来自三个方面:一是离婚前后的生活困境,这是物质的困境;二是情爱苦海里的感情困境,这是精神的困境;三是人生各阶段事业的打击与压力,这是发展的困境。物质的困境,珠月是有生存经验的,她勤劳持家的本性不变;发展的困境,珠月有办法克服,那就是个体不懈的奋斗;唯独精神困境最为致命——被好梦蛊惑,被噩梦惊吓,被情感辜负,这一切负累重压在身,前行艰难。珠月必须解决好本我和自我之间的内在冲突,从而最终抵达超我。“死,是多么令人绝望啊,可活着,又是那么步步艰难。”⑥ 珠月很是明白自己的处境。
海德格尔这样辨别孤寂,“在大城市里,尽管人们可以很轻率地说自己几乎比任何地方的人都孤单,但他在那里从不可能有真正的孤寂。因为孤寂具有母于自己的力量,它不是把我们分成单个的人,而是把整个此在放归一切风物之本质的宽阔的近旁。”⑦
孤单是一种个体陷入群体中被隔绝的心理感受。孤寂则大于心理感受,是一种哲学式的本质体验和人生氛围特质。孤寂不仅衍生出个体的孤单,也会衍生出存在感的虚无和空洞。后者是更为紧要的。形体在,神魂不在;形体在,神魂被抽离放置在旁边,却永无重新融合的可能性,纵使风物宽阔无边,又如何?——这样感知的人显然超越普通的无感之人,会进一步反映到个体与其他群体或个体的差异感上。
珠月不是一个因婚外恋而主动离婚的平庸的女性文学形象,也不是追求柏拉图式精神欢愉的女性心灵自慰者,她是从人的本体论视角出发,置身于窒息的生存环境的灵魂自由流放式的女性形象。她从最初将爱与怜悯混同而误识他人的、不懂真正的爱为何物的年轻阶段,到经历家庭生活情感冷战、生存养育困境、挣扎于理想爱人的不可得和欲望爱人的破灭中,她所经受的不单纯是身体的孤单和精神的孤独,而是生而为女人被婚姻制度、家庭负担以及生存困境所裹挟的人生大孤寂。
一个人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就可以忍受任何一种生活。珠月在原生家庭中的勤勉懂事,在自我家庭中的忍辱负重,并非單纯由于个人心性资质,而是来源于自觉意识的能动性,这样的能动性既然可以深爱一个人到宁可自身孤寂,也必然可以为了灵魂的深爱坚持生存下去。
命运拥有这样一种形式,它是圆球形的:你越是远离那一点,就越是向它靠近。我们无法思考世界,是因为它在某处思考我们。珠月所代表的当下知识女性的情感与人生际遇充分验证了命运不可测、混沌而随机的特征。
正如余清及其周身庸俗的情人们对珠月身份和精神的伤害;正如因颉和他的稳固家庭对珠月的困扰和祝福式的妥协;正如旷诗和他背地里打压阻挠珠月事业的发展。珠月纵然选择冷战、离婚、躲闪、无视和忍耐,依然无法摆脱这些灰暗深处的人性干扰。命运混沌的合理性反衬出人自身存在的荒谬性,这是命运捉弄人的一种表征。作者将珠月置身于不可逆的宿命背景——生活背景、身份背景、物质背景,但珠月偏不信邪,决意与不可见的命运抗争,她的刚强意志和柔软情怀一样难能可贵,直到命运咒语的封印解除——“所谓的命运,原来是自己手造的。只要有一颗良善的心,人必心地安宁,人必然有一个心底澄澈的未来。”⑧
“珠月相信万物有灵,相信有一个上天,这个上天不是神,不是一个具体的有生命的物,而是一种灵性,一种感应,一种生命与生俱来的趋向性,它接近人的心灵,常能产生一种意念一种能量,会告知自己或他人他物,并会相互影响。”⑨ 万物有灵即承认天道的存在,这是一方面。“珠月认为梦就像静默的大自然一样,在那里面蕴藏的是真理,就像爱她的人的心脏,心脏是不言语的,可是它却能在梦中通过神语得到传达。”⑩ 这是另一方面,承认人心良知的王阳明的心说。“不要被自己的心魔束缚,真的,这世上没有什么主宰人的神,神就是每个人的良心,如果把你的良心法则破坏了,你就没有神来保护了。”{11} 历经无数外界的磨难,珠月的抗争也是一种修行。虽然梦境可以接通有情人在宇宙中爱的信息,但梦幻控制了珠月的心眼手足,也即被客体的人物诱惑吸引。当她一旦失去自控力,就陷入了自我的苦情套局,而这不过是自己拟想出来的。“肉体,原来是灵魂的面影啊,她赖以支撑的不就是灵魂吗?即肉体是被灵魂支使,肉体不过是灵魂的魅惑啊。”{12} 珠月没有选择身心的放纵,而是遵从梦境的旨意,主动地把握住精神的方向性。表面上她依然是一位传统意义上的东方女性,照顾有女儿成长的家庭,照顾有猫咪陪伴的家庭,这是她的生存使命,无法推卸更无法退缩。
“你是一个天神,天神要挡魔道。凭着自己的良心做事,人就成了神。你就是我心里的神,我相信你。我爱你。永远都爱你。”——这是菜对辰的耳语。{13} 菜和辰,是珠月在梦中孵化的新梦主人公,也就是梦中之梦。这个梦的潜意识是要摆脱陈旧循环的苦恋之梦而诞生,是主观驱使下的主体介入的隐喻之梦,是虚构的镜像,在对抗主体世界的现实和客体世界的引诱。菜与辰的故事将女主人公的精神梦幻和生存现实进行了奇妙的象征耦合。很明显,菜与辰就是珠月本心和旷诗本心的映象。这个主体主义的绮丽之梦为什么会在通篇的客体主义诱惑的梦里突现呢?这里要谈到一个关于珠月心理机制的转化。珠月一直忍受着焦灼、痛苦、忧伤、期待、猜疑、印证、预警等各种无头绪的乱梦中,早已退无可退,对现实的思念之人丧失了巨大的激情,对自我之梦丧失了巨大的依赖;因其淳朴与善良之本性,她只能忍受现实的伤害,而不会反击迫害之人,那么她如何宣泄自身的困闷?依然只能通过梦。与其旧梦伤痕不断,不如新梦重建未来。菜是珠月真诚单纯信我的维度空间的人,辰也是这样。
作者将珠月内心的渴求抽象化操作,再借用珠月的梦的空间重构了新故事和新人物设定,以此抚慰,以此疗伤,以此否定以前的虚幻之梦、荒诞之梦和无望之梦,可谓顺理成章,令人眼前一亮。这不是在做同义反复的事,而是以一种基于生活经验之上的超验之梦超越了过往所有的梦。这个梦预示着主人公真正的自我觉醒。
四、女性觉醒
本书贡献了数十个人物,除了珠月和三个男主人公、两个虚拟人物外,还有很多旁线人物的塑造和刻画值得一读。这些旁线人物或为珠月的家人,或为童年玩伴、青年同事、领导师长,均起到了烘托主人公精神情操的作用。尤其是对珠月青少年时期家乡的女性们,早期医院工作时期的女同事们,现在身边的女性朋友——通过这三类女性里的很多生动代表,作者写出了时代女性的总体生活需求和抉择方向及各自的命运走向。其中,勇敢追求真爱的吉红姑姑,和美生活的禾月妹妹,选错郎君跳楼而去的思美,单身母亲叶曦之死——无不令人印象深刻。这些女性或幸福,或追求幸福,或苦难,或难逃苦难,无一不在揭示珠月的命运个案背后潜藏的巨大的陈旧伦理观念。而众多女性感情案例也从正面揭示了女性群体的婚姻生活共性与苦乐根源,将珠月的个体遭遇赋予了真实可信的社会现实意义。
睡前原谅一切,醒来便是重生。女性天生的感性和来自于理性认知的矜持,使珠月逐渐从感性中生发出灵性,从理性中生发知性。梦如嗅觉和幻听幻视,孤寂如修行的道场氛围,都使得珠月的觉知能力得到增强。觉知带给珠月追求幸福生活和精神共鸣的大觉醒契机。
恨也罢,爱也罢,思想、感觉、观察也罢,无非都是在领悟。我们看到珠月面对三个男性角色身上的觉知领悟,不仅仅是通过对方的或者说外在的事件的影响,更主要的是通过自我认知后的心灵感应与意识反馈,造就了她日益成熟的正念。正念通过她的梦,作为载体和行为,对无望的现实生活产生了强大的抵御效应和突围冲力。
现实是什么样的现实?残缺的、破碎的、窒息的、令人遗憾的。因此梦境才可能成为超越现实的理想现实。对现实的冷静描写,其实是在帮助梦幻提供合理性和有效反衬。“让梦见鬼去吧,梦永远只能见鬼,不能见人。如果梦能在白天站在她的面前对她说话,那她就服它了……梦不过是自己的灵魂对自己的私语罢了。它总是自以为聪明,可是却天天在改变。”{14} 从小哀愁到大孤寂,从大磨难到大觉醒,这个过程对于独木难支、孤立无援的珠月而言,生命的修行万分不易。她宁愿相信是人的生命的奥秘无穷,而不愿相信有什么神——由此获得了新生。如同仙子一样美好的荷花,珠月身在淤泥的尘世,忍受着静湖一样死寂的生活,依然保持着内心的高尚与洁净。
身体之爱与灵魂之爱不可或缺,这是珠月的泣血收获。对灵魂之爱的坚持,珠月体会很深——“终于愿意相信有灵魂,愿意知道永恒,不灭。因为这世间有你,即使是一辈子也不够,还需要永远的相伴。一直到魂灵也失去灵性、失去能量、消失的那一天。我们也消失了,如宇宙中的一丝风,轻轻地消失,消失于无形。”{15} 珠月再也不会认为仅有灵魂之爱就是完整。爱需要有机融合,正如梦和现实终究会接壤,生命才会重现生机活力。珠月让梦中梦的女主人公“菜”代言她的心语,并去完成自己不可能完成的爱的主动。“性并不仅仅是为了繁育后代,更重要的是只有通过身体的密切接触,只有把生命和身体真正的融合,才会觉得和爱的人真正连为一体了,才能确证自己与爱人是一体的。这个一体的感觉非常重要,它是密切相关,生死相依的。需要拼命地吸取对方的身体,才能证实是被自己所拥有的。”{16} “爱不是婚外情,不是故事,是内心的需要。爱不是事件,不是简单的一个行动,是血水之需,是身心之美的完成。爱,就是我爱你时的欣喜、明澈的高贵心灵。”{17} 珠月由此顿悟,爱是唯一信仰,来自天神的祝愿,也来自人心的良知,天神就是天道的形象,天神就是良心的至上投影,二者是合一的。从荆棘到珍珠,正是从生存的山野到精神的海洋,从世俗的苦痛到意志的养成,从草木爱情到智慧修为的过程。
梦是载体、空间、叙事工具,幻是镜像、情节、心理暗示;现实是叙事的基石,梦幻与现实的结合正在将彼此印证或反写。现实信息抽象化之后,变成了梦与幻的舞台;造梦者的觉知推动现实情节的演变。世界是平的,但人心是幽深的,梦幻现实主义风格就是要钻探人心的纯度和深度。
由此不难得出结论,梦幻现实主义风格写作是多重生命空间的写作,也是对生活深度呈现的写作,本质上属于客体主义的哲学驱动。这一风格打通了灵魂与空间的穿越通道,搭建了情感与梦境的互生链接,也营造了心理孤寂与众生喧哗的对峙本相。尤其在后现代的叙事语境下,信息时代的人类存在普遍的无归属感,存在普遍的自我身心封闭意识,需要用自如随性的方式去表达思绪和情感的弥漫性,抒发个体生命深层的欲望、痛苦和理想。这种风格的写法有其值得播撒种子和文本生长的土壤。
梦幻现实主义的写作打破了传统的小说叙事章法,取消了以情节设计为骨架的叙事方式。它用自然的素材、心灵的镜像、客体化的语境去表达人性的美好质素和神性成分。它以心理感应和行为判断,原生态地呈现出故事的全貌。在这个过程里,真实和幻象丛生,没有绝对的伊始和结局,读者可以从任何章节自由进入其叙事语境,从而更切进小说主人公心灵的感触和灵魂的共鸣,实质上它是一种人人可以阅读介入的异质小说。《荆棘与珍珠》是梦幻现实主义风格小说的雀啼,势必唤醒更多心灵被禁锢的春天,献唱天道的不朽与灵魂之美。
注释:
① [法]让·波德里亚:《密码》,戴阿宝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6页。
② [法]雅克·朗西埃:《马拉美:塞壬的政治》,曹丹红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41页。
③⑥⑧⑨{11}{12}{13}{14}{15}{16} 胡梅仙:《荆棘与珍珠》(不知是太阳还是月亮)(下册),长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748、752、716、826、667、744、780、731、824、825页。
④ [法]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郑克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扉页。
⑤⑩{17} 胡梅仙:《荆棘与珍珠》(不知是太阳还是月亮)(上册),长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321、225、327頁。
⑦ [德]海德格尔:《思的经验》(1910—1976),陈春文译,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9页。
作者简介:温经天,诗人、自由撰稿人,北京,100121。
(责任编辑 庄春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