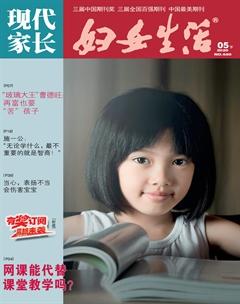秦春华:教育的价值在于挖掘每一个孩子的潜能
小单
人物名片
秦春华:1993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学院,2002年获得北大经济学博士学位。毕业后留校,历任北大团委宣传部部长、党委办公室兼校长办公室副主任、教务部副部长兼招生办公室主任、考试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研究员。
近年来,作为北京大学考试研究院院长,秦春华专注于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本科人才培养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对美国顶尖大学本科招生录取制度有深入的研究,发表论文百余篇,出版专著多部。日前,笔者采访了他,请他谈谈高考改革的情况。
高考制度要为那些创新型的优秀人才留一扇门
笔者:众所周知,高考是衔接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桥梁,也是我国选拔人才的主要途径。您如何看待我国的高考制度?
秦春华(以下简称秦):过去我们一直有一种说法,说高考是成本最低、效率最高、最公平的大学招生录取制度。现在看来,这有可能需要修正。成本的确是最低;效率是不是最高其实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是不是最公平也有待商榷,因为公平本身就是一个难以讨论清楚的问题。
在我国,其实人们并没有把高考看成教育制度的组成部分,而是把高考看成资源分配的手段,实现阶层跃升的途径。这既符合科举制的传统,也能印证“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社会心理。这些观念是难以破除的。
笔者: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高考呢?
秦:我觉得,我们应当在尊重这些社会传统和观念的同时,赋予高考制度更多的教育内涵和功能。也就是说,它应当更好地帮助学生发现自我,从而更好地成长为下一代的建设者;它应当使教师更好地履行自己的使命,实现自我价值;它应当着眼于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就不会再把高考看成一场战争,需要动员、誓师。我们所需要的,只不过是平静,是成长,是喜悦。
笔者:您曾担任北京大学本科招生办主任,现在担任北大考试研究院院长,对高考有深入的研究,请您简单介绍一下高考改革的情况。
秦:我国高考正在经历自1977年恢复以来最全面、最深刻、最根本的变化。“全面”体现在不同于以往的局部改革或者修修补补。事实上,自恢复以来,高考一直處于改革之中。目前的改革是全面改革,是最高决策层的顶层设计。这一点从《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国务院2014年9月发布)的制定颁布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深刻”体现在它既是教育改革,但又不完全是教育改革。它跳出了教育本身的范畴,并没有将注意力全部集中于考试招生本身,而是站在政治与社会的高度,通过考试招生制度这一具体改革,进一步强化考试招生制度作为国家基本教育制度所内生的,在实现代际转换、社会阶层流动、改变个人和家庭命运方面具有的不可替代的功能,努力实现中国社会阶层的正常流动,重建社会的正义、公正与公平。“根本”体现在它一竿子插到底,通过改变大学招生录取的结构——“两依据,一参考”来实现教育改革的终极目标,即把促进学生健康成长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次是动真格的。
笔者:高考改革的进程顺利吗?
秦:改革正在进行中,尽管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情况,但总体而言比较平稳。我认为,在接下来的进程中要关注以下两个重要问题:
一是要坚定改革的信心。改革是很难的,高考改革尤其难上加难。出现个别问题很正常,只要不发生系统性风险都可以承受。
二是要妥善处理好公平和卓越之间的关系。当前社会比较关注公平,但高考的公平问题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对于当代中国来说,创新型的优秀人才依然匮乏。特殊人才的寻找、发现、选拔往往是极其困难的。高考制度要为他们留一扇门,否则,对他们个人而言是遗憾,对国家和社会来说则是无法弥补的损失。
高考应该去除显著的工具性特征,否则“读书无用论”必将抬头
笔者:作为访问学者,您曾多次去美国考察高考招生。您觉得美国哪些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秦:我认为,我们需要借鉴的是美国顶尖大学的“整体性评价”招生录取制度。它关注的是未来的社会领导者所具备的核心素养,其中最重要的是公共服务精神。美国社会通过在顶尖大学的招生录取中考察学生的社会服务经历,成功实现了对青少年价值观的引导,所花时间不过20年。我想,如果我们能够把“立德树人”目标也列入顶尖大学招生录取的目标,再加上其他严格的落实措施,也许用不了20年,中国教育的面貌就会和现在完全不一样。
笔者:说到中美高考制度的差异,我们似乎不能回避一个尖锐的问题:基础教育方面,中国明显比美国强,但是高等教育方面,中国远远落后于美国,这是为什么呢?
秦:这个问题的确够尖锐。一方面,中国学生普遍基础扎实、勤奋刻苦、学习努力——特别是在数学、统计等学科领域——超乎寻常,在国际大赛中屡屡摘取桂冠,将欧美发达国家的学生甩在身后。另一方面,中国科学家在国际学术舞台上的整体地位不高,能够影响世界和人类的重大科研成果乏善可陈,至今只有一位本土科学家获得了诺贝尔科学奖。难怪钱学森先生临终会发出感慨: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其实美国的情况看上去也很奇怪:一方面,美国基础教育质量在世界上被公认竞争力不强,就连美国人自己也承认这一点。和其他国家特别是和中国、印度相比,美国学生在阅读、数学和基础科学领域的能力较差,在各种测试中的成绩常常低于平均值。另一方面,美国的高等教育质量独步全球,美国科学家的创新成果层出不穷,始终引领世界科学技术发展。一个水平很低的基础教育却支撑起了一个水平最高的高等教育体系,这也许是世界教育史上最吊诡的现象。
通常情况下,就整体而言,优秀学生的基数越大,未来从中涌现出优秀学者的可能性就相应越大。然而,当下的中国教育正在验证我们的担忧:优秀的学生和未来优秀学者之间的关联性似乎并不显著。
笔者:是的。许多家长有这样的疑问:我们的教育是有效的吗?您能回答这个问题吗?
秦:教育是否有效,要看它是否幫助人们实现了教育的目的。然而,今天越来越多的人——无论是教育者还是被教育者——已经忘记了教育的目的。恢复高考以来的四十多年里,我们一直在不停地奔跑,跑得越来越快,也越来越累,却很少停下来问一问,我们为什么要奔跑?教育似乎正在变成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得不去完成的例行公事:教师上课是为了谋生;学生上学在义务教育阶段是国家规定,在非义务教育阶段是为了通过上一级的考试;校长看上去像是一个企业的总经理;等等。凡此种种,无不显示出教育的有效性正在慢慢消失。
笔者:在古代,教育的有效性体现在科举制度上,对吗?
秦:古代中国的教育,实质上是一种关于社会和人生的伦理学训练。教育固然有其功利化的一面,但也有其超越性的一面:学生们通过反复阅读经典的经书来完善自己的道德,管理家族和宗族事务,进而服务于国家和天下苍生。
科举制废除之后,基于政治经济文化的颠覆性变革,中国教育走上了向西方学习的道路,由此形成了一整套语言、学制和评估体系。这一源于特殊历史环境中的教育体系尤其强调功利性的一面,即教育是为了解决现实中的某种问题而存在的:教育为了救国,教育是实现现代化的工具和基础,等等。
到了当代,教育更加呈现出相当显著的工具性特征:学生希望通过教育获得一些有用的技能,使他们能够通过竞争激烈的考试,增强他们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进而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和更多的物质财富。如果教育不能帮助他们实现这些目标,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抛弃教育——这就是为什么近年来“读书无用论”有所抬头的思想根源。
教育就像远方的一座灯塔——孩子一旦认识到自己未来将成为什么样的人,就会激发出无穷动力,去实现这一目标
笔者:看来,严重功利化是教育的大敌。那么,如何扭转这种倾向呢?
秦:扭转这种倾向,关键在于如何把价值观教育自然而然地融入教育。这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因为教育的过程正在异化为应付考试的训练过程。目前,这个训练过程越来越低龄化。由于“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比拼心理,对儿童的早期智力开发正在进入历史上最狂热的阶段。越来越多的孩子不能从教育中享受到快乐,不快乐的时间一再提前。教育提供给人们的,除了一张张毕业证书外,越来越难以使人感受到精神的愉悦和心灵的平和。
笔者:有些家长认为,花钱供孩子接受教育,孩子大学毕业后却找不到理想的工作,那么教育就是一桩亏本的买卖。您对此有何评论?
秦:正如储蓄不能直接转化为投资一样,上学也不意味着一定能接受到好的教育,也不意味着一定能找到好工作。我们之所以送孩子上学,是因为孩子要为未来的生活做好准备。上学是一个人为了实现人生目标而必须经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也是首要的一件事是:认识到你未来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教育的价值就在于挖掘每一个孩子的潜能。和上哪所学校,考多少分相比,知道自己未来将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是更为重要的目标。回避或忽略这个问题,只是忙于给孩子找什么样的学校,找什么样的老师,为孩子提供什么样的条件,教给学生多少知识,提高学生多少分数,这些都是在事实上放弃了作为家长和教师的教育责任。
实际上,孩子一旦认识到自己未来将成为什么样的人,就会从内心激发出无穷的动力去努力实现自己的目标。无数的研究结果已经证明,对于个人的成长而言,这种内生性的驱动力要远比外部强加的力量大得多,也有效得多。
笔者:有人说,教育就像一场通关游戏,只要投入时间和金钱,配置强大的装备就可以通关。您同意这个比喻吗?
秦:我不同意。人生不是一场由他人设计好程序的游戏。人生是一段发现自我的旅程,路要靠自己一步一步走出来。如果一定要比喻的话,我认为教育就像远方的一座灯塔,能够指引我们前进的方向。
【编辑:陈彤】